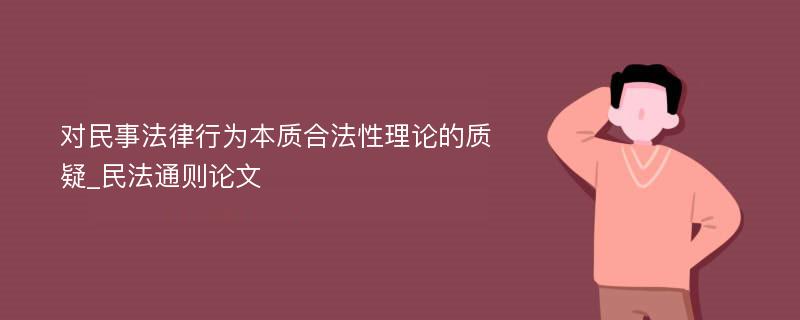
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民事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规定,采用了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立法观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在法理逻辑上存在着诸多自相矛盾和理论缺陷,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
我国《民法通则》之所以采用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立法观点,其主要理由据说是为了回避使用“无效法律行为”的术语。那么,为什么要回避使用“无效法律行为”这一术语呢?按一些学者的解释,“无效法律行为”这一术语本身是有矛盾的,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将其与“法律行为”的术语分开,“把无效法律行为当作一个单独的名词看”,“把得撤销的法律行为,也应当作单独的名词看”〔1〕, 从而形成不包含无效法律行为与得撤销法律行为的“法律行为”概念。循此思路,在《民法通则》中,“民事法律行为”被界定为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素,旨在发生民事法律后果的合法行为;无效法律行为则被称为“无效民事行为”,指虽有意思表示但并不合法的行为,并作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相对立的独立概念;得撤销的法律行为被称作“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仍是与民事法律行为相对应的独立概念。这三个概念之间呈并列状态,而统辖这三者的则是“民事行为”概念,这显然是用“民事行为”取代了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为了完成这一取代,就不得不对“民事行为”概念作具有特别意义的重新界定,即不仅把意思表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而且也作为民事行为的构成要素。这一作法显然具有关键性意义,但其结果却导致出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与理论方面的一系列新的矛盾。
第一,以意思表示作为“民事行为”必不可缺的构成要素,也即视意思表示为“民事行为”质的规定,不仅是对这一概念应有的科学内涵的一种变异,而且也是对这一概念内涵的任意强加。因为,不管是从语言逻辑角度,还是从法理逻辑角度,甚至只是顾名思义,“民事行为”只能被理解为是指依照民法规定,能够导致一定民事法律后果的一切行为。可见“民事行为”的本质规定性在于其依法具有民事法律意义,而不在于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素。换句话说,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素的行为固然是民事行为,而不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素的行为,甚至无从具备意思表示的行为,只要具有民事法律意义,均是民事行为。诸如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及侵权等行为,无一不是民事行为。
第二,把意思表示强加给民事行为概念的内涵,自然是不科学地缩小了该概念的应有外延,从而不仅破坏了该概念的科学完整性,同时还脱离了民事行为的客观存在。从民事行为的定义中可以看到,该概念的外延不仅包含了合法行为,而且包括了适法行为和违法行为,不仅包括了意思表示行为(表意行为),而且还包括了非表意形式的事实行为。如果一定要把意思表示强加给民事行为,显然是缩小了该概念的外延,其结果必然是在一方面增加了围绕该概念进行不应有的辨析负担〔2 〕,另一方面则使该概念无法涵盖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种种民事行为,从而难以承担对现实存在的民事行为进行科学地抽象概括的任务。
第三,把意思表示强加给民事行为概念的内涵,还会在这种变异了的民事行为概念与原本囊括着一切民事行为事实的民事行为概念之间制造出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在此,为方便起见,不妨把前一种称为变异的民事行为概念,后一种称为原义的民事行为概念。
原义的民事行为概念,在传统民法中,也有称作“民法上行为”的,还有简称为“行为”的,尽管表述稍有不同,但其所指均是可成为民事法律事实的一切行为。在我国民法学中,为了同变异的民事行为概念相区分,原义的民事行为概念往往被简化为“行为”。这一简化的意义与传统民法中的简称并不相同。如果说传统民法中的简称是一种同义简称,那么我国民法学中的简化则是一种具有改变原义民事行为概念的含义和定位的简化。其目的是为了使《民法通则》中的“民事行为”,即变异的民事行为概念能够成为原义的民事行为的属概念,使两者能够较为协调地相互存在。但是,这种协调只能在字面上予以应付,而无法在文义层面上完成,从而暴露出新的矛盾冲突。把原义的民事行为概念简化为“行为”概念,并把变异的民事行为概念作为其属概念,这在事实上是将变异的民事行为概念在法理逻辑上的矛盾转嫁到“行为”概念上,致使“行为”概念出现词不达意的弊端。因为,就行为概念的原义来说,是指“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在外面的活动”〔3 〕或“由人的意志支配发生的任何事件”〔4〕。它既可具有法律意义,也可不具法律意义; 既可具有民法意义,又可具有其它部门法(如刑法、行政法等)意义。而原义的民事行为概念,则只能是指具民法意义的行为,它与行为概念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根本无法等质互换。行为概念如果是指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的意思,就必须加上“民事”二字予以限定。如果不作限定,行为概念失之宽泛,无法确切表示民事法律意义行为的内涵。如果加上“民事”二字限定行为,则立法者按照民事法律的本质合法说所创造的民事行为概念的新含义又无法体现,这显然将行为概念与民事行为概念置于一种两难境地。
二
对于民事法律行为,我国之所以采用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立法观点,据说还有两个方面的理由:其一是为了满足我国民法对于表意行为不能采用法定主义的规律要求;其二是通过贯彻该立法观点,可以使我国的表意行为制度具有立法技术上的简明性和司法操作上的简便性的特点。然而,《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表明,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条件与有效条件是“合二为一”的。这一作法导致了一系列值得怀疑的结果:
第一,民法对于表意行为不能采用法定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法始终应当以保障行为人享有不为法律禁止的行为的自由为己任,否则民法就不成其为民法。因此,在传统民法中,区分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有效,并推行不同的原则,设立不同的条件与规则。如对法律行为的成立,所实行的是“法律行为自由主义”,亦即“私法自治”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只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法律行为即行成立:其一,有行为人;其二,行为人须有一定目的,且该目的具有民法意义;其三,行为人须有意思表示。但对法律行为的有效,则采行“国家干预”原则,即“法律行为只有合法时才能有效”。这一原则决定了法律行为有效条件乃是:其一,行为人须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其二,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其三,行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违反社会公益及公序良俗。如此区别对待的用意,首先是为了尊重并依法严肃行为人在实施法律行为方面的自由、权利及利益,其次还是为了使行为人的个人利益、非行为人的个人利益及社会公益都能得到法律的公平兼顾。但是,《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却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条件与有效条件合并起来,从而便将法律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同时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条件,这不就表明了我国对民事法律行为有采法定主义立场的嫌疑吗?
第二,依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只有合法的表意行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而依据第58条的规定,不合法的表意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这种非此即彼式的法理逻辑模式,既无法解释《民法通则》第59条所规定的可变更、可撤销的表意行为,也无法解释第60条所规定的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表意行为。但无论是从民事生活实践方面考察,还是从民事立法方面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立法观点都无法将自己不能容纳的表意行为排斥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之外。因为,在民事生活实践中,民事主体所实施的表意行为在客观上必然是复杂多样的。这种客观存在不受任何立法观点所左右,相反立法必须反映这种客观存在。《民法通则》并没有、也不能把上述诸种行为排斥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之外。这一作法本身,其实就蕴含着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立法观点的否定。
第三,《民法通则》关于可变更、可撤销的表意行为规定了两种:一是显失公平的表意行为,二系有重大误解的表意行为。在此,显失公平也好,重大误解也罢,应属于不合法的表意行为,按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观点来衡量,都应按绝对无效来对待。然而,《民法通则》却明确规定,这两种行为如经行为人请求而变更或被撤销,就不是民事法律行为;相反,如果被行为人认可和接受,就获得了民事法律行为的名义,并具有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与此同时,《民法通则》又明确规定,对这两种行为的变更或不变更、撤销或不撤销,实际上是取决于行为人的意志。这不就直接否定了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立法观点吗?
值得提及的是,由于《民法通则》设立有可变更、可撤销的表意行为制度,才使我国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多少具有意思自治味道,也才表明《民法通则》对于民事法律行为有采意思自治主义的成分。换句话说,《民法通则》中的可变更、可撤销的表意行为制度,才是我国表意行为制度中具有可信性和合理性的内容。但遗憾的是,在整个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具有这种可信性和合理性的内容太少了。
三
从民法法理上说,合同理论及制度无疑是表意行为理论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合法说立法观点既在理论上存在诸多缺陷,又在法理逻辑上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结果就使得我国的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及制度与我国的合同理论与制度,乃至与合同的审判实践发生了一系列不应有的矛盾冲突。全面、系统地阐述这些矛盾冲突,不是本文篇幅所能容纳的,故在此仅以合同定义为例稍作探究。
关于合同的定义,我国法学界的法律行为说已成为通说。意思表示本身是一种行为,而法律行为又以意思表示为基本构成要素。因而,所谓合同,说到底不过就是双方当事人所实施的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而已。然而,颇为有趣的是,在我国民法学界,合同定义的法律行为说与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竟然同出于一家之手〔5〕。 这不但使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自置于尴尬境地而无法自拔,而且还使这一观点在我国的合同理论、合同制度及合同纠纷的审判实践面前处处碰壁,难以自圆其说。这至少有三方面的表现极为明显:
第一,既然合同的本质规定是民事法律行为,依照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立法观点,就唯有合法与有效的合同才算是合同,无效的合同就不能成为合同。但有目共睹的下列事实,没有一件不是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否定:
1.作为合同法学中的概念,“无效合同”已为我国民法学所完全接受,并成为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专门性研究课题。
2.在我国合同法中,不仅使用了无效合同概念,而且还对无效合同设立了专门性的系统规定。
3.按照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观点来理解,合同就都是合法的。那么,我国的促裁、审判机构在受理合同纠纷案件时,就毋须审查合同的是否合法与有效,只须直接审理其所诉纠纷并无不可。但恐怕没有哪个仲裁、审判机关能这么做,其实也绝不允许这样做。
4.依照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观点,合同立法就只能以合同的合法为轴心,其结果必然是绝对取消合同当事人在合同关系方面的自主性。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合同关系运作规律能允许这样做吗?
第二,为了给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寻找理论依据,我国民法学界曾经有人发明过一种可称之为“借用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的无效法律行为、无效合同及无效遗嘱,本质上并不是法律行为、合同及遗嘱;其中的“无效”一词所表示的只是已有名词的借用。这一观点在学理上的根据乃是“泥人不是人,纸马亦非马”的逻辑命题〔6 〕。从表面上看,这一观点似乎不无道理,但若稍加深究,就会发现其不合逻辑。
“借用说”所持的学理依据与其所阐述的命题在逻辑上乃是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如以“人”这个概念在法律上的含义而言,至少是指具有生命力与社会性的人,而“泥人”概念则仅指形同于人,在本质上是用泥制作的物品。这种泥制品与人显然不能等质而论。与此同时还应看到,与“泥人”概念在文字构造上相同的还有“健康的人”、“病人”,以及“男人”、“女人”等概念。“泥人”这个概念中的“人”固然可以说是借用的,但却无法说“病人”或“男人”概念中的“人”也是借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合同与无效合同,法律行为与无效法律行为;遗嘱与无效遗嘱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人与泥人、马与纸马之间的关系,而只能是人与“健康的人”或“病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无法证明“病人不是人,男人亦非人”的命题能够成立,则“借用论”之不合逻辑就非常明显。
第三,由于受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立法观点的干扰和制约,我国合同法中的合同概念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和完善,甚至还有倒退之嫌。1981年颁布的《经济合同法》第2条对合同概念曾予专门规定:“经济合同是法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这一定义除了对合同主体规定得稍嫌狭窄外,对合同的本质规定倒也符合合同法理的要求和精神。但经修改后于1992年颁布的《经济合同法》,却将合同的定义性规定删除了。究其具体原因,无疑是因为1981年制定《经济合同法》时,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还仅仅只是一种学理上的见解,未能对《经济合同法》的制定产生根本性影响,但通过《民法通则》的制定和颁行,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已成为我国民事立法在表意行为制度上的立法观点,这就使得在修改《经济合同法》时,关于合同的概念不得不处于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立法观点与合同法理精神及其逻辑要求的夹缝之中,从而成为立法中的一大难题。因此,只有通过回避合同概念问题而采用折衷办法,似乎才有可能平息争议。但是,矛盾和冲突既然是客观的,采取消极回避态度就绝非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在法理逻辑上存在着一系列无法克服的自相矛盾和重大缺陷,将其作为我国表意行为制度的立法观点已经严重制约着我国民事法律的发展和完善,使之无法适应改革开放,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因而,不但应从理论上对之提出质疑,而且应在立法实践中抛弃这一观点。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原理》第168页,全国第三期法律专业师资班1983年7月整理。
〔2〕如《民法通则》颁行前后, 我国民法学界就“民事行为”概念曾进行过大规模争辨,其实似属多余,参见《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版第134~135页。
〔3〕《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版,第1277页。
〔4〕《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5〕《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136页。
〔6〕凌相权、余能斌:《民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155页。
标签:民法通则论文; 无效民事行为论文; 有效合同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法律论文; 民事违法行为论文; 民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