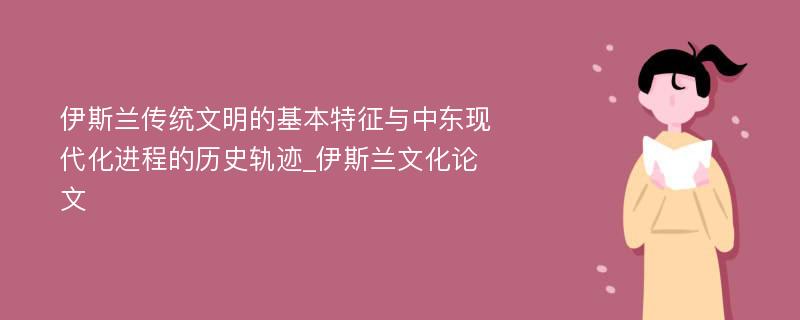
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基本特征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中东论文,轨迹论文,基本特征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若从宏观角度审视世界历史,不难发现,人类经历两次解放的过程。人类的第一次解放,发生于自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其核心内容在于个人摆脱血缘群体的束缚而走向地域的时代,个人不再是“整体的肢体”而成为完整意义的社会存在,是为文明化。人类的第二次解放,发生于自传统文明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其核心内容在于个人作为社会的主体摆脱依附状态而走向自由的时代,是为现代化。
所谓的现代化即从传统文明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无疑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东地区的现代化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东地区现代化的特定内涵在于封建主义的衰落、传统秩序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传统的封建主义与新兴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运动贯穿中东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西方的冲击固然构成深刻影响中东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外部因素,而伊斯兰传统文明的特定历史背景从根本上决定着中东现代化进程之区别与其他诸多地区现代化进程的特殊道路。本文拟从分析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基本特征入手,结合西方冲击的国际环境,探讨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并就相关问题略陈管见。
一
伊斯兰传统文明形成于中世纪的特定社会环境,个体生产、自然经济、超经济的强制和广泛的依附状态以及思想的束缚构成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历史基础,伊斯兰教的诞生和阿拉伯人从野蛮向文明的演进则是深刻影响伊斯兰传统文明的重要因素。
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国有倾向;国家土地所有制的长期存在,构成中东历史的突出现象。伊斯兰传统文明脱胎于阿拉伯半岛的野蛮状态,原始公有制的财产关系在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半岛广泛存在,土地无论作为耕地抑或作为牧场皆由血缘群体成员共同支配。先知穆罕默德时代,阿拉伯半岛的土地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古兰经》规定一切土地皆属安拉及其使者所有,进而阐述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原则。① 血缘群体诚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依旧构成世袭占有土地的基本单位,而先知穆罕默德至少在理论上开始超越血缘群体的狭隘界限,获得支配土地的最高权力,作为“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和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② 《古兰经》阐述的国家土地所有制,根源于阿拉伯半岛的客观物质环境,是原始公有制的土地关系在文明时代的历史延续。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依据《古兰经》的相关启示所征纳的天课,不仅具有宗教意义,而且是国家权力得以实现的重要形式,其实质在于宗教形式下租税的合一。“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③。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服和穆斯林统治的建立,《古兰经》阐述的国家土地所有制成为中东地区的基本经济原则,“伊克塔”则是伊斯兰世界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外在形式。“伊克塔”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整体地产之一部的赐封”,源于《古兰经》的相关启示,即国家土地所有制构成地产赐封的前提条件。哈里发时代,“伊克塔”逐渐演变为军事封邑,兼有国家土地与民间田产的双重性质,处于国有与私有之间的过渡状态。传统伊斯兰世界的封邑制度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封邑制度,其实质在于土地受益权的赐封而非土地所有权的赐封,受封者与封地之间往往表现为分离的状态,无权支配土地,仅以享用封地的岁入作为目的。“伊克塔”作为军事封邑的另一特点,是土地占有的非世袭性和非等级性。尼扎姆·穆勒克(1018—1092年)认为,军事“伊克塔”的连续占有时间应当限制在2—3年之内。“受封者必须清楚,他们对于耕种伊克塔的农民绝无统治权力可言,只能局限于征纳国家规定的产品份额。农民对其人身、财产和家庭享有自主权,受封者不得随意侵犯。因为,无论是国家还是臣民,都只属于苏丹”④。国有土地的经济制度与私人支配土地的经济现实之间的矛盾运动,贯穿中东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伊克塔”的频繁更换,诚然是国家控制受封者的有效手段,却无疑排斥着地权私人化与地产市场化的进程。
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基本特征,还表现为非穆斯林臣民,即吉玛人的自治地位和孤立状态。吉玛人的概念,源于先知穆罕默德时代阿拉伯半岛的圣战实践。《古兰经》严格区分多神崇拜的阿拉伯人与一神信仰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将前者称作“以物配主的人”,而将后者称作“有经典的人”;“以物配主的人”只能在皈依与死亡之间做出选择,“有经典的人”则可通过缴纳贡税作为条件换取穆斯林的保护。所谓的吉玛人特指在穆斯林的统治下通过订立契约的形式接受保护的非穆斯林臣民,是所谓的“有经典的人”之宗教概念在现实领域的逻辑延伸。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哈里发国家征服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广大区域,非穆斯林臣民数量剧增,犹太人和基督徒无疑处于被保护者的地位,琐罗亚斯德教徒亦被纳入吉玛人的行列。《古兰经》规定,“你们(即穆斯林)只可信任你们的教友”,至于所谓“有经典的人”,“无论在哪里出现,都要陷于卑微之中,除非借安拉的和约与众人的和约不能安居”。⑤ 哈里发国家援引《古兰经》的相关启示,承认吉玛人原有宗教的合法地位,进而赋予吉玛人广泛的自治权利,同时禁止吉玛人出任官职,将吉玛人排斥于政界和征战领域之外,导致吉玛人颇受歧视的社会地位。吉玛人固然在民事和司法领域处于相对自治的状态,沿袭各自原有的法律和习俗,但是,吉玛人如果涉及与穆斯林之间的诉讼,必须依据伊斯兰教法予以裁决;穆斯林法庭在裁决时,往往拒绝接受吉玛人的誓言和所提供的证据。《古兰经》承认奴隶存在的合法地位,而吉玛人却不得拥有穆斯林作为奴隶。穆斯林男子可以娶吉玛人中的女子为妻,反之则被禁止。吉玛人尽管享有保留原有宗教信仰的权利,其宗教活动却常受种种限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沿袭哈里发时代形成的吉玛人制度,实行所谓的米勒特制度。基督徒和犹太人在缴纳人丁税的条件下,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利,处于二等臣民的地位。穆斯林与基督徒、犹太人的居住空间错综交织,分别遵从各自的宗教法律,操各自的传统语言,恪守各自的生活习俗,隶属于各自的宗教首领,相安无事。与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相比,奥斯曼帝国奉行宗教宽容的政策,允许异教信仰的合法存在。然而,奥斯曼帝国坚持伊斯兰教统治的传统原则,穆斯林贵族垄断国家权力,非穆斯林不得担任政府官职,不得从军征战,不得分享国家权力。诸多宗教社团俨然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国中之国,诸多宗教的文化传统在奥斯曼帝国长期延续,进而导致奥斯曼帝国社会结构之浓厚的多元色彩。
中东地区素有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小农经济与灌溉农业的结合以及普遍的封闭状态是中东专制主义长期存在的物质基础。从阿拉伯人的哈里发国家到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专制主义构成中东地区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阿拔斯时代,哈里发俨然是国家权力的化身和伊斯兰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宫廷则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所在。巴格达金碧辉煌的圆形宫殿不仅堪称伊斯兰建筑的杰作,而且象征着哈里发与臣民之间的森严界限。阿拔斯王朝的创建者阿布·阿拔斯当政期间,刽子手杀人时用来垫地的皮革在伊斯兰史上首次铺放在哈里发的御座旁边,成为御座不可或缺的附属物。“突然的处决和随意的刑罚,提高了哈里发的威严”⑥。曼苏尔首创使用御号称呼哈里发的先例,并为其后历代哈里发长期沿用。在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自诩为“信士的长官”和阿拔斯哈里发的继承人,拥有军政财税和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保卫伊斯兰世界、统率穆斯林对基督教世界发动圣战和捍卫伊斯兰教法,是苏丹的首要职责。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的传统理论强调君权神授和君权至上的政治原则,强调君主的统治权力和臣民的从属地位;统治者是其臣民的牧人,他将为自己的行为和臣民的行为对安拉负责,而选择统治者和惩罚统治者的权力只属于安拉。“信士的长官!安拉赋予你(治理温麦的)重任,(这件事的)报酬将是最大的报酬,惩罚也将是最严厉的惩罚。”⑦ 至于臣民享有的权利,在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论中则缺乏明确的阐述。所谓臣民终止顺从统治者和反抗统治者的规定往往只是理论上的虚构和道义上的制约,现实意义微乎其微,而忠君思想则是传统伊斯兰政治理论的实质所在。
在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诸国,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长期并立,教会与国家自成体系,分庭抗礼。至于华夏文明及其周边区域,世俗权力极度膨胀,皇权至上构成封建社会的政治传统。相比之下,在中东地区,自伊斯兰教诞生开始,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先知穆罕默德作为安拉的使者,不仅负有传布启示的神圣使命,而且行使驾驭社会的世俗权力。先知穆罕默德创立的温麦,作为穆斯林的宗教政治共同体,既是伊斯兰国家的原生形态,亦是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基本政治框架。根据传统伊斯兰教的政治理论,宗教是国家的基础,温麦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外在形式起源于安拉的意志,捍卫沙里亚即伊斯兰教法的神圣地位是伊斯兰国家的目的,“维持伊斯兰社会存在的基础是共同接受沙里亚的约束”。⑧ 温麦兼有国家与教会的双重功能,教会与国家则被穆斯林视作同一概念。穆斯林与异教徒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和对立;超越宗教界限和纯粹世俗的政治行为与温麦的原则大相径庭,并无存在的空间。因此,政治理论不可避免地体现为形式各异的宗教学说,政治群体往往体现为宗教派别,政治对抗大都采取宗教运动的形式,政治斗争的首要方式便是信仰的指责。换言之,宗教运动皆有相应的政治基础、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反映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政治利益的矛盾对抗。
二
大约自15世纪开始,封建社会首先在欧洲趋于衰落,资本主义逐渐兴起。此后,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亦相继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从而卷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包含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生产力的进步和财富的积累无疑构成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物质基础,农业的市场化、生产的社会化、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秩序的法治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以及意识形态的个性化则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若干基本层面。中东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固然根源于传统秩序的崩溃,西方的冲击则是中东传统秩序崩溃的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自18世纪末开始,西方的冲击首先表现为工业品的倾销。西方的工业品充斥于中东伊斯兰世界,否定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和相对封闭的社会状态,货币地租逐渐取代古老的实物分成制地租,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不断增加,货币关系日趋扩大,农作物的商品化和农业生产的市场化长足发展,传统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趋于瓦解。西方的冲击所带来的另一重要的历史后果,是现代工业在中东诸地的初步建立。19世纪的突出现象,是西方诸国相继投资中东,筑路建厂。西方的冲击挑战着中东统治阶级的传统利益;奥斯曼帝国、波斯的恺加王朝和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亦纷纷兴办工业,以求开辟财源,强化统治。对于货币的渴望和财富的追求,驱使统治阶级致力于所谓的新政,客观上推动着现代化的进程。经济领域的剧烈变革,导致新旧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资产阶级和自由劳动力阶层逐渐登上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舞台。“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穆斯林社会全面衰落的标志”。⑨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谓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在于西方冲击之下,中东地区社会形态的新旧更替和由此导致的矛盾冲突;作为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最终结果,中东诸多现代民族国家相继形成,无疑体现历史的巨大进步。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实质在于中东地区传统秩序的解体,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构成中东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内容。
国家土地所有制通常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密切相关,货币关系的扩大和农业生产市场化进程的逻辑结果则是土地所有权的剧烈运动。1858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颁布《农业法》,在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扩大租种国有土地的农民的经营自主权,直至赋予农民对于所租种土地的交易权。⑩ 同年,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政权的赛义德帕夏颁布法令,废除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国家垄断权以及农产品的政府专卖制,授予农民自由支配土地和决定生产内容的权利,允许个人购买和拥有土地。根据该法令,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不仅局限于用益权,而且包括抵押和继承的合法权利,甚至外国人亦可在埃及购置地产。(11) 在恺加王朝统治下的伊朗,王室土地和贵族封邑自19世纪中叶开始逐渐减少,私人支配的民间地产不断增加,进而形成区别于传统封邑领有者的地主阶层。贵族宠臣和军事将领不断扩大封邑的支配权,“封邑的领有者开始演变为地产的所有者”。此外,许多商人亦投资乡村,购置田产,进而成为新兴地主阶层的重要来源。(12) 此后,国家土地所有制在中东地区逐渐衰落,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地权的非国有化趋势日渐明显,而地权的非国有化运动直接导致土地兼并和乡村剧烈的社会分化。进入20世纪,地权分布的严重不均成为中东诸国乡村社会的普遍现象,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埃及和伊朗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发生于纳赛尔时代和巴列维时代,既是否定乡村社会传统模式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环节,亦是极权政治自城市向乡村广泛延伸的历史形式,而土地改革的深层经济背景在于特定的地权状态,即国家土地所有制崩溃后小农经济的普遍衰落与大地产的急剧膨胀。土地改革本身并非是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直接原因,只是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而小农经济存在于不同的社会阶段,并不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然而,在现代化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中东诸国的土地改革通过发展小农经济、排斥和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乡村社会和农业领域实现深刻变革的逻辑起点,是削弱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杠杆,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乡村社会和农业领域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
吉玛人制度和米勒特制度无疑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诸多非穆斯林群体之依附状态和从属地位的外在形式,而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社会界限的淡化和法律地位的趋同则是中东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内容。1839年,奥斯曼帝国颁布“花厅御诏”,规定帝国臣民无论信仰何种宗教,皆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进而初步阐述了权利分配的世俗原则。坦泽马特时代,奥斯曼帝国在沿袭传统法律框架的同时,开始尝试世俗的立法实践,引进西方的世俗法律,进而形成伊斯兰教法与世俗法律并存的二元局面,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法律界限和社会地位的差异逐渐淡化。与此同时,诸多非穆斯林宗教群体内部亦经历世俗化的过程,世俗法律逐渐取代宗教法律,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教士阶层的地位随之下降,米勒特制度趋于瓦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东地区诸民族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宗教隔阂逐渐缓解,民族意识增强,世俗民族主义应运而生。非穆斯林宗教群体的孤立状态和封闭倾向趋于削弱,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宗教群体借助于世俗民族主义的历史形式实现广泛的政治联合。1882年奥拉比兵变期间,反对英国的殖民侵略成为埃及穆斯林与科普特派基督徒的共同目标;兵变期间的著名口号“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强调埃及人超越宗教界限而共同致力于埃及的政治解放,具有世俗民族主义的历史内涵。1922年,图坦卡蒙陵墓被成功发掘,法老主义以及其后的基督教传统和伊斯兰教信仰均被视作埃及新国家的重要历史遗产,传统的回归和古老民族的再生成为时尚的思潮。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凯末尔亦明确强调世俗的民族忠诚取代传统意义上与温麦和哈里发制度相联系的宗教忠诚,强调以顺从国家取代顺从宗教作为土耳其公民的首要义务,宣称“为土耳其人民进行奋斗,不是为超出民族边疆以外的不论根据宗教或种族来规定的任何更加模糊、更加广泛的实体进行战斗”。(13) 1924年颁布的土耳其宪法规定:土耳其所有的人民,无论其宗教和种族如何,就其身份而言,均属土耳其人;所有土耳其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团体、等级、家族和个人的特权均在被取消和禁止之列。1928年,土耳其国民议会修改宪法,甚至删除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共和国国教的内容。
现代化的主体是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实践则是实现经济进步和财富增长进而使民众获得权利、自由和尊严的前提条件。纵观世界历史,各个地区由于具体条件的差异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却是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和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16—17世纪,宗教改革在西欧诸国风行一时,否定教会的权威和排斥罗马教廷的传统势力是宗教改革的宗旨所在。民族教会的建立包含着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世俗化构成推动西欧地区民族独立和民族国家兴起的重要举措。1776—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堪称西方民族革命的典型范例,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束导致北美地区现代化的长足发展。相比之下,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与西方的冲击密切相关。西方的冲击固然推动了中东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和初步的工业化进程,促进了中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关系的扩大,加速了中东传统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的衰落。但是,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作为西方冲击的历史形式,对于中东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殖民主义的实质在于宗主国对于殖民地财富的掠夺;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导致中东诸国长期缺乏完整的主权和独立的国际地位,在政治上从属于西方,在经济上依附于西方,是束缚中东诸国经济社会进步的枷锁和制约中东诸国现代化长足发展的障碍。中东诸国的现代化进程尽管一度包含西化的倾向,然而所谓的西化只是西方制度的扩张和西方殖民主义的逻辑延伸,诸如议会和宪政等西方制度的移植并未根本改变中东诸国的历史进程,亦未带来真正意义的自由和民主。自20世纪初开始,民族解放运动的日趋高涨标志着中东诸国的现代化步入崭新的阶段。1905—1911年伊朗宪政革命、1908—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和1919—1922年埃及反英运动,是20世纪初中东诸国与西方列强之间民族矛盾的集中体现。民族主义、极权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三重倾向的错综交织,构成此间中东诸国现代化的基本模式。礼萨·巴列维、凯末尔和纳赛尔的统治,无不体现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广泛实践。摆脱从属于西方的政治地位和依附于西方的经济地位,是中东诸国实现深刻历史变革的客观需要;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是中东经济社会长足发展的前提条件。极权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逻辑延伸,构成从传统的君主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过渡的中间环节;从民族主义的胜利到极权主义的实践,标志着中东诸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域的深刻革命。国家资本主义亦被称作现代形式的重商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干预。国家资本主义既是极权主义的经济基础,亦是否定封建生产关系的有力杠杆。民族主义的高涨构成国家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
三
传统社会的政治模式,在于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差异和对立,表现为依附与强制的明显倾向。相比之下,现代政治模式的突出特点在于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趋于吻合,而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构成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趋于吻合的历史基础。农业的统治地位和自然经济的广泛存在,构成传统政治模式赖以存在的客观物质环境。工业化的长足发展和交换关系的扩大,排斥着依附与强制的传统倾向,进而导致传统政治模式的衰落和现代政治模式的逐渐成熟。通常认为,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诸多宗教属于传统范畴的意识形态,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构成传统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而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则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所谓的世俗化与现代化表现为同步的趋势,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互动则是现代化进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14) 实际情况不然。诸多宗教尽管根源于特定的社会现实,却非处于静止的状态,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基督教诞生于古代地中海世界,在中世纪的欧洲构成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15世纪以后逐渐演变为适应现代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教兴起于7世纪初,自阿拉伯半岛传入中东诸地,进而形成适应中古时代特定历史环境的思想体系和具有浓厚传统色彩的宗教理论。然而,伊斯兰教绝非浑然一体,亦非处于一成不变的状态。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和客观物质环境的新旧更替,不可避免地导致伊斯兰教作为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传统伊斯兰教与现代伊斯兰教的此消彼长,集中体现为中东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社会势力的激烈抗争。另一方面,纵观世界历史,世俗政治并非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神权政治亦非仅仅属于传统社会。在西方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对于初兴的民族国家而言,罗马教廷的广泛政治权力意味着外部因素的干涉,教权的排斥和世俗化构成民族革命的重要形式和现代化的必要环节。至于在民族主义时代的中东诸国,极权政治往往表现为世俗化的明显倾向,排斥传统教界的政治影响构成强化极权政治的重要手段。政治现代化的实质并非世俗化,而是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至于所谓的世俗化,其特定内涵在于宗教的非政治化,并非政治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世俗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和明显标志,现代化国家无一例外地应是世俗化国家”(15)。如此看法显然过于武断,缺乏起码的逻辑依据和历史依据。至于“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也可能出现形式上是政教合一,实际上是世俗化的多种形式”(16),实属令人费解。
自19世纪后期开始,从民族主义运动的胜利到民主主义运动的实践构成贯穿中东诸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主题。有学者以埃及的萨达特与穆斯林兄弟会为例,强调民族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的互不相容。(17) 实际情况不然。首先,民族主义者不可等同于世俗主义者。其次,民族主义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为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不同形式。第三,伊斯兰主义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亦具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不同政治倾向。所谓的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均为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矛盾对抗和此消彼长,根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东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轨迹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而所谓的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只是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与现代民主政治建立抑或从民族主义到民主主义之历史运动的外在形式和政治工具。在中东诸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无论世俗主义还是伊斯兰主义,皆曾经历从民族主义到民主主义的深刻变化。中东诸国从民族主义运动到民主主义运动的突出现象,在于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错综交织。换言之,中东诸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既有伊斯兰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亦有世俗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既有伊斯兰主义的民主主义运动,亦有世俗主义的民主主义运动。从民族主义到民主主义无疑构成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实质,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则是实现民族主义胜利和推动民主主义高涨的外在形式。
西方民主的核心思想是主权在民和宪法至上,自由和人权是西方民主的基本主题,立宪制、议会制、普选制和政党政治则是西方民主的经典模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和人权成为中东民众竞相追逐的时尚和潮流,以西方的自由主义取代中东传统的宗教保守主义和以宪政制度取代君主独裁被视作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选择,西方民主的政治形式随之初步登上中东诸国的历史舞台。然而,西方的民主政治源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崛起,是西方诸国经济社会变革的逻辑结果,通常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过程。相比之下,在中东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传统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封建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工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新兴资产阶级尚无力与封建地主阶级角逐政坛,包括立宪制、代议制、普选制和政党政治在内的所谓西方民主制度的移植,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具有明显的历史缺陷。民众的权利源于统治者的恩赐,所谓的民主政治缺乏必要的经济社会基础,尚属无源之水,徒具形式。国王和总统往往凌驾于宪政之上,宪法常若一纸空文,议会形同虚设,诸多政党只是极权主义的御用工具,并未成为广泛体现民众意志的政治组织。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阶级社会的诸多宗教作为阶级对抗的产物和体现,具有双重的社会功能。一方面,阶级社会的宗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和压迫民众的精神枷锁,是“人民的鸦片”。(18) 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19)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为民众反抗现实的苦难提供神圣的外衣,进而构成社会革命的外在形式。至于理性通过神性的扭曲形式而得以体现和发扬,在历史长河中亦非鲜见。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教无疑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改造阿拉伯社会的重要手段。“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是一种表面上的反动,是一种虚假的复古和返朴”。(20) 在中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伊斯兰教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趋于保守和僵化,进而演变为捍卫封建秩序的思想理论。自20世纪中叶开始,现代伊斯兰主义在中东诸国悄然兴起,成为推动民众广泛政治参与和挑战极权政治的重要形式。现代伊斯兰主义不同于教界传统的政治理论;后者是传统社会的客观现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与传统社会群体的既得利益密切相关,是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舆论工具。相比之下,现代伊斯兰主义强调《古兰经》和“圣训”的基本原则以及早期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崇尚穆罕默德时代和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社会秩序,其核心内容在于借助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而倡导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原则,是中东诸国摆脱传统的政治模式和推动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形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裂变和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构成现代伊斯兰主义兴起的客观基础。借助于宗教的形式否定传统政治模式进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则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实质所在。所谓宗教与世俗的对抗,在中东诸国并非“现代化的难题”,亦非体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是包含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激烈抗争的明显倾向。
现代伊斯兰主义存在于中东的诸多地区,埃及和南亚则是现代伊斯兰主义的重要发源地。早在1926年,印度的穆斯林学者阿布·阿拉·毛杜迪首倡现代伊斯兰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暴力倾向,宣称伊斯兰教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的实践,其宗旨是摧毁当今世界的社会秩序而代之以崭新的社会秩序。继赛义德·毛杜迪之后,埃及人哈桑·班纳和赛义德·库特布相继阐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提供了否定极权政治的理论基础,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政治实践构成埃及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外在形式。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基础是处于政治舞台边缘地带的下层民众,支持者遍及城市和乡村。1970年纳赛尔去世以后,极权政治在埃及出现衰落的征兆。与此同时,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的演进,导致贫富分化明显加剧,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日趋高涨,伊斯兰教反对贫富不均和倡导社会平等的信仰原则随之广泛传播。宗教政治挑战世俗政治抑或所谓的宗教对抗国家,成为萨达特时代埃及政治的突出现象。以安拉的统治取代当代“法老”的统治以及实践《古兰经》的信仰原则和重建先知时代的神权秩序,则是穆斯林兄弟会挑战现存政治秩序的基本纲领。萨达特时代,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坚持温和的政治立场,致力于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作为角逐权力的基本手段。80年代,穆巴拉克政权亦与穆斯林兄弟会保持合作的关系。1984年,穆斯林兄弟会与新华夫脱党组成竞选联盟,获得议会450个席位的57席。1987年,穆斯林兄弟会与工党、自由党组成竞选联盟,获得议会的60个席位,其中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获得37席,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反对派。(21) 进入9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逐渐由温和的政治反对派演变为激进的政治反对派,其与埃及政府的关系逐渐恶化。
现代伊斯兰主义自70年代在伊朗的广泛传播,根源于巴列维王朝极权政治的社会现实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需要,标志着崭新的政治文化借助于宗教的形式初露端倪。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杰出理论家阿里·沙里亚蒂主张摒弃教界传统理论,回归经训的道路,恢复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伊斯兰教的本来面目,实现安拉与人民的原则,建立平等和民主的秩序。阿里·沙里亚蒂声称:“真正的伊斯兰教是追求公正、平等和根除贫困的宗教……我们需要的是自由和进步的伊斯兰教。”(22) 霍梅尼认为,现存的世俗政治与经训阐述的原旨教义不符,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度背离早期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而“伊斯兰教与君主制的全部观念存在根本的对立”。(23) 霍梅尼声称:伊斯兰政府不是专制的政府,而是立宪和法治的政府。“我们的义务是拯救被剥夺者和被虐待者。我们有责任帮助被虐待者和与压迫者进行斗争。”(24) 1979年巴列维王朝的覆灭,标志着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退出伊朗的历史舞台;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和所谓的“头巾取代王冠”,为伊朗民主政治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巴列维时代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朗教俗关系的传统模式,什叶派伊斯兰教由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转变为民众反抗的政治武器和“被压迫生灵的叹息”,进而由捍卫传统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倡导现代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
自80年代开始,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土耳其趋于高涨,现代伊斯兰主义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政治要素和政治力量。始建于1983年的“繁荣党”作为土耳其最重要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反对国家控制宗教的政治框架,强调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主张建立公正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秩序,保护劳动者的福利和权益,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地区发展的平衡,在下层民众中影响广泛。统治模式决定反抗模式。伊朗巴列维国王时期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氛围,导致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之间矛盾对抗的暴力形式和激进倾向。相比之下,由于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和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权力角逐在土耳其并未表现为尖锐的对抗和激烈的冲突,尤其是没有形成否定现存政治秩序和重建伊斯兰政体的政治纲领。1995年,“繁荣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土耳其的第一大政党。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的广泛合作,构成土耳其政党政治与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
注释:
①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3:109,19:40。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
④ Nizam al—Mulk,Siyasat Nama,London,1978,p.28.
⑤ 《古兰经》,3:73,3:112。
⑥ J.Wellhausen,The 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London,1973,p.562.
⑦ Abu Yusuf,Kitab al—Kharaj,Cairo,1933,p.9.
⑧ A.K.S.Lambton,State and Government in the Medieval Islam,Oxford,1985,p.44.
⑨ 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⑩ K.H.Karpat,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s in Turkey,Leiden,1973,p.43.
(11) P.J.Vatikiotis,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Baltimore,1991,p.55.
(12) J.Foran,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Boulder,1993,p.120.
(13)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1—372页。
(14) 曲洪:《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15) 王京烈:《当代中东政治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16) 王京烈:《当代中东政治思潮》,第110页。
(17) 曲洪:《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第121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0页。
(21) 杨灏城、朱克柔:《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393页。
(22) E.Abrahamian,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rinceton,1982,p.470.
(23) D.Hiro,Holy Wars:The Rise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New York,1989,p.161.
(24) L.Davidson.Islamic Fundamentalism,London,1998,pp.136—138.
标签:伊斯兰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伊斯兰建筑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伊斯兰教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吉玛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