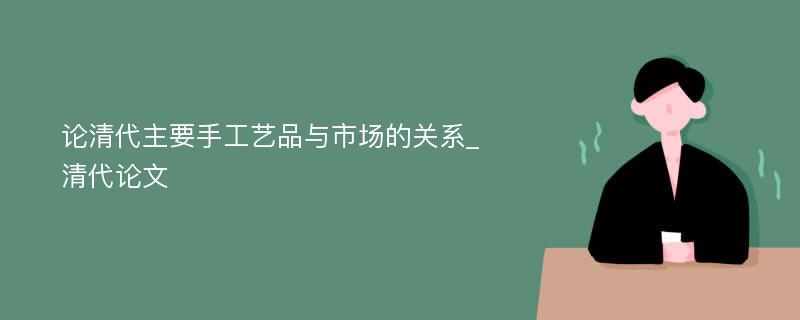
论清代主要手工业品与市场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品论文,清代论文,关系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022X(2000)03—0085—06
明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作用的冲击下,明政府被迫改变传统的官专卖政策,使被切断的主要手工业品与市场的联系得以恢复。清王朝继承前明的各项工商业政策,以特许商代替政府职能,鼓励民营手工业的发展,由此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豪商阶层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清代主要手工业品与市场的关系和市场的规模都有了较大变化,工商业税收也和明代有所不同。本文准备分四个方面分析研究这些发展和变化,以期对封建社会末期的市场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清代工商业政策的逐渐宽松
满清入关后,虽然废除前明政权的一些弊政,诸如匠籍制、“和买”、“当行”等,并减轻关税,严禁关吏滥征,以利于工商业的恢复,但是,由于统一战争远未结束,因而很多惠政没有落到实处,清初的工商业政策仍呈现严紧的状态。如在盐政方面,清政府虽提出了“恤商裕课”、“免征浮课”的方针,但截止到康熙二十二年以前,军费浩大,盐政无法正常;在茶政方面,清初继承明朝政策,东南实行茶引制,陕甘则因需要大量战马实行官商分茶制,西北茶叶的流通仍然受到官府的行政干预;在矿业方面,清廷因害怕矿徒聚众闹事,禁止民间开矿;在对外贸易方面,为防止东南抗清势力,实行禁海甚至迁海政策;在官府织造部门,仍实行明末落后的“佥派”制,企图以搜刮民间机户来弥补经费不足。
康熙二十二年清统一台湾后,战争平息,军费减少,恢复经济成为头等大事,各项政策开始实施。在专卖政策方面,较彻底地实行明后期开始出现的商专卖。如盐政实行纲引制,盐的生产和销售由商人管理,政府只征收盐税和用行政手段保证专商的利益。西北茶马贸易自康熙初在察哈尔建牧马场、军马供应有余而战事减少后逐渐衰落,清政府不再对陕甘茶叶交易进行控制,全国茶市在交纳茶税后基本上是自由贸易。在对外贸易方面,自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后,除对出洋船的载重量、输出品、携带武器方面仍多有限制外,将进出口贸易委托给专商负责,让其在经营外贸的同时代行政府涉外职能。在矿业方面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逐渐放松禁令,到乾隆时期则实行鼓励政策,民营矿业比明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官府织造和御窑实行“买丝招匠”和“官搭民烧”的雇佣生产方式,其原料主要来源于购买,因此多数官府工业的经营方式已与民间手工业基本相同。
在商品流通领域,清廷早在顺治初年就针对满洲贵族依仗特权欺行霸市、短少价值、扰乱市场秩序、侵犯商人阶层利益等行为,谕令禁止,“传谕百姓,如遇此等妄行之人,即拿送该部(户部),治以重罪”(《清世祖实录》卷15)。为防止管关官吏对商人的非法勒索,顺治八年谕令吏部,每关只能设官一员,其余全部裁去。从康熙五年开始,刊税例木榜于各关,“并商要往来之孔道,遍行晓谕。或例内有加增之数,亦明白注出,杜吏役滥征之弊”(《清圣祖实录》卷18)。对于违反规定,“私行滥收”的官吏“依律治罪”,以促进全国各地商品的流通。雍正帝也曾一再下令,“所有刊刻则例之木榜务令竖立街市,人人其见,不得藏匿屋内或用油纸掩盖”(《清朝文献通考》卷26,《征榷》)。乾隆帝除也重视这些外,还于乾隆元年在江西省九江、赣江二关采取发放三联单的方法,即商人将应纳银自行投柜,收银后发三联单,一联给商人,一联交巡抚衙门,一联存税署,以“免需索侵隐之弊”(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7,《关税》)。同时为方便商品流通, 改进度量衡,如统一尺度,长度以十为单位;每文钱重一钱二分,以防盗铸或销毁。
为了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经济,清政府很注意对吏治的整顿。对执行政府命令得力、清正廉洁的官吏进行鼓励表彰,如乾隆时对招商开矿得税一万两者,准其优升。反之,对贪官污吏和欺行霸市、非法需索者,则“王公以下,文武大小各官家人……在原犯之地枷号三个月。系民责四十板,旗人鞭一百。其纵容家人之藩王罚银一万两;公罚银一千两。俱将管理家务官革职。将军督抚以下文武各官俱革职”(《清康熙实录》卷23)。豪强土棍“私抽诈索,播虐贾民”,如果“监司令守各官,知情徇纵,觉察不严者,一体连坐参处”(《抚粤政略》卷5, 《文告》)。乾隆之弟弘赡被削去王爵的罪证中,就有利用权势贩卖人参、牟取暴利等内容(《东华录续录》卷20)。
康熙中期以后,清政府在工商业领域实行商专卖政策,这种由专商代理制虽然是封建王朝垄断控制工商业的另一种形式,但较之弊端丛生的官专卖制有了明显的改进,国家变直接干预经济为利用专商间接遥控,既保证了政府的各项税收,又相对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商业的繁荣及其伴随而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不能超越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界限,否则就要危及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因此清政府便用榷关、牙行和行会制对民间商业资本进行控制。在榷关方面,当经济有待恢复、商业资本萎缩的时候,清廷往往减轻税收,限制管关官吏的额外敲榨,就像前述清廷的一系列保护商业的政策和法令。当商业资本发展超过了封建经济、政治所能允许的限度时,又往往加重关税以分商人之肥,放任管关税吏的侵渔,使大部分商业利润变成朝廷的国帑或流入贪官污吏的私囊,以压抑商业资本的过度发展。
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牙行固然有促进商品交易的作用,但在清政府的庇护下,牙人控制市场,操纵物价,滥抽牙佣,盘剥商人和百姓以坐地分肥,妨碍了正常的商业活动,尤其是割断了商业资本与生产者的联系,阻止了商业资本向生产领域的渗透,使商人通过包买商的途径投资产业的道路变得极为狭窄。清政府还在城市工商各行业中强化行会制度,利用它来统制工商业活动,并协助官府执行榷关和牙行制度。允许适当发展,但又不许超过限度,清前期的主要手工业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有了一定的发展。
二、清前期主要手工业品与市场关系的加深
清朝的商专卖品主要是盐和茶。其中的食盐产量在鸦片战争前年产达24亿斤,连同私盐在内共32.2亿斤,价值银5852.9万两,远远超过明代水平(注: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8页。)。尽管清代食盐实行官督商销制, 生产和销售主要由盐商经营,食盐与市场的关系比明代直接而密切,但由于盐课在国家税收中占有较大比重,因而清政府仍通过引岸制对食盐运销的各个环节进行监控,并于沿途各处设卡稽查掣验,以防禁私盐。所以食盐与市场的关系呈现出与其他非专卖品不同的特点。
比如山东盐运司,其行盐范围包括本省及相邻的河南、江苏、安徽的15个州县,是引、票兼行省区。引盐以水运为主,比陆运的票盐集中。为了监控食盐基层销售,康熙中期清廷在山东广泛推行了公店集场制,即大约30公里左右设盐店一处,之下又设子店作为分销机构。如清中叶巨野县设子店29处,商河县设有12处等。在较小的集市又设若干销售点,“逢集运销”。这样,与各州县集市网在空间分布上基本重合、但又有其独特运转系统的食盐销售网,一直延伸到乡村的最基层。清代盐法的引岸制使盐商销售和百姓买盐都被限定在销售网的某一特定点上而丧失了自由,所以山东及其他各地的食盐运销网是一个封闭性的网络体系,外盐不许进入这一流通圈,本区盐也不许越界销售。清政府对食盐销售的种种限制,使与市场联系比明代大为加强的清代食盐和一般商品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清代前期,随着饮茶风气的更加盛行和茶树种植的普遍,茶叶产量比明代有了很大增加。截止到鸦片战争前,有茶田520万亩,茶农130万户,年产毛茶250万担(注:许涤新、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7~328页。)。乾隆时期西北茶马贸易逐渐废弃后,政府已不需要大量官茶,对茶叶的统制实际已不起作用,到嘉庆时,各地茶引仅及产量的十之一、二。官府控制的放松,使清中期茶叶市场迅速发展起来。当时茶叶市场遍及全国,像安徽六安茶主要销往华北及华中一带,各地商人每年千里而来挟资大量购买。福建武夷山茶“水浮陆转,鬻之四方”。云南普洱茶年产百余万斤,主要销往西北及西南地区,并入贡京师。四川所产砖茶,分销内地、边地、土司三路。各地茶叶除内销外,还大量销往国外,每年经海路陆路出口毛茶60万担,为清朝第一出口商品。
茶叶市场的扩大刺激了茶叶生产的增加,也使徽商、西商、闽商、粤商等大商帮程度更深地卷入茶叶贸易之中,并通过买卖、借贷关系控制了茶的生产。当时茶商主要通过预买制,即春节前后放款给茶农,清明前往收茶,所谓“经千里挟资而来,投行预质”(《光绪霍山县志》卷二,引《乾隆吴志》),利用牙人居间控制和剥削茶农。
从康熙后期开始,随着清廷矿业政策的松动,各种矿藏有了更进一步的开发,到乾隆四十八年,全国各种矿开采达313处。 其中铁年产量约在4000~5000万斤之间,铜年产量在1200万斤左右(注: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第464~490页。)。清代铁铜等矿的开采范围和产量都超过了明代,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铁产量的提高为铸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其在明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像佛山“炒铁之炉数千,铸铁之炉百余,昼夜烹炼,火光烛天”(《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气侯》)。佛山铸锅制造精良,市场广阔,行销大江南北,还大量出口国外,最多一次贩运7000只,重20000斤(注:许涤新、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2页。)。除佛山外, 湖北汉口、浙江桐乡、安徽芜湖等也是著名的铸铁炼钢之地。
清代丝织业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其中南京、 苏州、 杭州有织机50000多张,加上周围的市镇,江浙两省约有织机80000张(注: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江宁地不产丝而缎业兴旺,原料皆由浙西一带供给, 所产绸缎种类繁多,市场广布全国。在原料和加工均为上乘的情况下,江南各市镇以其名优产品形成许多贸易集散中心。如浙江嘉湖乌青镇既是蚕桑的集散地,所产丝绸又通向全国市场。江苏吴江县盛泽镇是绫绸的集散中心,“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乾隆《吴江县志》卷38)。湖州府南浔镇则是湖丝的贸易中心,“每当湖丝告成,商贾辐辏”,每天的贸易量约几十万至百万两丝,整个旺季的贸易额约有500 万两银(注:樊树志:《南浔镇与湖丝贸易》,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
自明中期以后,景德镇瓷器几乎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到清代这种状况更为突出。除了宫廷用瓷外,社会上的民间用瓷也绝大部分由景德镇供应。其民窑年产量由明代的3600万件值银180万两, 上升到乾隆时的30万担,值银约500 万两(注: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0页。), 在外销瓷方面比明代也有很大增加,据统计,广州在1792年对美国瓷器出口1492担, 对法国出口180担,对英国出口约400担。鸦片战争前,中国瓷器每年出口约5000 担(注: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其他地区的窑场,多数只生产一些缸、 坛之类的日用陶器,只有少数名窑如宜兴的紫砂陶、广东石湾的仿钧器和福建德化的白瓷,因其独有特色,在清代仍各具有市场。
由于清政府对远洋船的限制较多,所以清代造船业主要集中在近海平底船——沙船方面。沙船平底方头,甲板宽,干舷低,稳定性较好;排水量和速度虽不如尖底船,但吃水浅,阻力相对小,可依靠多桅多帆以快航。沙船多在福建、浙江等木材产地制造,一般需银七八千至一万两,载重大者3000石,小者1500多石。由于上海既是南北洋航运的中心,也是连接海运和内河航运的枢纽,因此各类沙船云集上海。据记载,嘉庆初上海千石以上的海运沙船最多曾达3600只左右。在嘉庆中,这些船载运“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注: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5~661页。)。
除以上产品外,清代的粮食、棉布、木材、纸张、蔗糖等也形成区域性的生产基地和市场。如湖南、江西、四川、广西、河南、山东等省粮食大量输出,由长江、运河、黄、淮、海河水系转运,形成远距离的粮食贸易;棉花棉布则在江南、华北、两湖、四川等地形成种植与加工中心;木材纸张主要产于秦岭、赣闽浙皖等山区;蔗糖则产于广东、福建、四川、台湾等地,并运销国内外。
三、全国统一市场的初步形成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各地区域市场的逐渐兴盛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统一市场的初步形成提供了前提。唐代以前,全国农作物与手工业分布呈现明显的自然均衡状态,政府用行政手段调拨物资以实行远距离货物交流。商品流通在品种上多局限于名优特产,在时间上局限于丰歉调剂,在空间地域上跨度也不大,尤其是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稀少。宋代时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几个地区间的商品粮流通突破了丰歉调剂的模式。如太湖米谷供给杭州、浙东以至福建,长江中游各地商品粮下销江淮,两广米谷供给福建及浙东等。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专业化商品生产区,如河北东路、京西东路的蚕丝区,成都的蜀锦,两浙路湖、杭、越、婺州的绢和罗等,都开始进行跨区域的流通。这些变化自明中期以后继续深化和扩大,在作物引种推广、产区重组优化的过程中,各地农作物的商品生产、手工业品的加工制作,经过市场竞争作用的筛选,到清中期,自然均衡分布状态被打破,全国范围内的区域性商品基地出现。这种变化尤以蚕桑丝织业、陶瓷业、稻米业、冶铁业等最为突出。
清代经济地理布局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果。在市场调配中,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优先发展能够充分利用地力和自然资源的农作物与手工业,从而使各自的生产效率提高,社会总产量相应增加。例如湖南地宜水稻种植,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江南,生产成本较低,而江南种棉植桑,则能获得较之水稻生产更好的经济效益。这样,湖南与江南的地域分工就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共同提高。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发生导向作用,价格机制开始有效地调节全国商品的地区平衡,这在商品粮市场中较为明显。像江西、湖广米运至浙西,销售网络完善,货源充足,价格稳定,行户因此“有恃无恐”。即使偶然货源减少,也不至于造成价格的大变动。
由于区域性商品基地的出现和商品流通量的加大,清代的商路也有了很大的扩展。首先是东西贸易有了较大发展。明代商运主要以南北方面为主,且受政治的影响较大。而清代长江中上游航运的开拓,使长江成为联系东西贸易的黄金水道。长江各支流域的货物汇入长江,顺流而下,使重庆、汉口、沙市、九江、芜湖等一批沿江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大运河在清代虽仍承担着相当大的运输量,因运河而兴盛的一些城市如临清、天津、淮安、扬州等仍是重要的商业中心,但由于其他航运的开通,运河的重要性比明代有所下降。像明代八大钞关有七个在运河上,运河七关在八大钞关商税总额中所占百分比,万历时为92.7%,天启时88%。清代运河七关在全国关税总额的百分比,康熙二十年为50.5%,雍正三年为40.9%,乾隆十八年为33.1%,嘉庆十七年29.3%,道光二十一年33.5%(注: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1页。)。
清代沿海北洋航线自康熙二十三开海禁后重新开辟,南洋沿海航线则继续发展。清中叶以后,随着南北商品贸易的不断深化,运河逐渐不堪负荷,海运的重要性逐渐超过运河。海运的兴盛为全国市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使沿海一些城市应运而起。如天津成为华北最重要的对外联系港口,上海则早已超过松江府城,渐有取代苏州成为全国性中心城市之势。史称:“自从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谢占壬:《古今海运异宜》、《皇朝经世文编》卷48)清代商品流通重心由内河航运向海运的转移,标志着传统市场在全国范围内联系的进一步加强。
清代各区域市场的发育和交通运输的发达,使清代商品流通总量比明代大为增加。截止到鸦片战争前,商品粮约有245亿斤, 占总产量的10.5%,值银16333.3万两。其中长距离运销约45亿斤, 为明代的三倍。国产棉花的商品量为255.5万石,占总产量的26.3%,值银1277.5 万两。国产棉布的商品量为31517.7万匹,值银9455.3万两,占52.3%。 全国丝的产量为7.7万担,商品量为7.1万担,值银1202.3万两,占92.2%,全部丝织品(包括出口部分)值银1455万两。茶的商品量为260.5万担,值银3186.1万两。盐的销售量为32.2亿斤,值银5852.9万两。七大商品总额为38762.4万两。此外铁值银880万两,靛值银382.69万两,全国必需品生活消费总计为186118.87万两。以非必需性消费占7%~10%计算,则有13028.32~18611.86万两,那么,商品零售总额为53053.41~58636.98万两(注:许涤新、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页。)。
宋代形成的以府、州、军等治所城市为核心的等级市场体系中,政治因素对市场的影响以及经济的封闭性与地方性仍很严重。经过明代的发展至清代,新兴市镇在市场规模和功能上出现等级分化,它们不再只是与县治同级的区域,有许多已超过县城、州府治所。有十几个巨镇甚至超过省府治所或与之等量齐观,成为省级乃至更大范围的经济中心。这种区域既是商品集散中心,又是初级产品加工中心;它对本区域内部有巨大聚合力,又释放出强大的能量把本地产品推向外地和远方市场。它的价格波动能引起区域内各地的价格变化,从而在价格机制作用上起核心作用。清代各区域市场和省级市场的中心地带,一般不是省会或不由省会独任。例如岭南区域市场,由广州和佛山共同组成核心区域,组织广东及广西的商品流通,担负该区域与省外、国外的交流。在广东,商业核心功能由梧州府及戎墟完成。晚明后即超过两湖省会之上的汉口镇,以其核心地位组织湖广区域市场。在湖南,湘潭是清前期最大的米市和商业中心。江西省内外的物资周流以樟树、吴城为枢纽进行,超过省会南昌。
华北和江南因政治沿革,情况有些不同。华北的核心区是北京,但直隶治所的保定府,其市场中心功能远次于后来居上的天津。山东商业中心城市为临清,而省会济南在省内外商品流通中的作用则很小,不仅远逊于临清、济宁,甚至不如该府邹平县下的周村。河南的开封和朱仙镇是核心区域,清前期则几乎由朱仙镇独当其任。江南核心区在苏州,它可以称为江苏的第二省会,但在区域市场的核心区等级中高于南京和浙江省会杭州。此外,山西的区域核心带在南部的潞安、泽州及绛州一带,与省会太原相距尚远。以福建为主体的东南沿海区域,受自然地理的影响,以各条江河入海处城镇为中心,分别自成一个地方市场,与国内外的联系密切,但区域内尚未整合成一个有机的区域市场。云南、贵州等省在清代尚未形成区域市场。由此可见,清代真正一直由省会城市承担市场中心者,大约只有陕西的西安、浙江的杭州、四川的成都等。这样,至清中叶虽然没有出现如近代上海一样凌驾于各大城市之上的中心城市,但全国范围内仍然形成几个超区域的中心城镇,如华北的北京,华东的苏州,华南的广佛,华中的汉口,有效地发挥着全国市场中心的功能。
总之,自宋明以来全国性经济地理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动,清代作物专业产区重组与优化过程显示出市场导向下资源配置的作用。经济核心区的等级体系,自宋明至清逐渐与行政治所等级分离,各大自然地域的区域市场相继形成,并配合全国市场的发展不断调整与重组。以长江和大运河为主的航运网络的消长变动以及海运的发展,亦深刻地反映了传统市场整合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市场机制没有成为全国经济运行的轴心,但传统社会下全国性统一市场已趋形成。
收稿日期:2000—0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