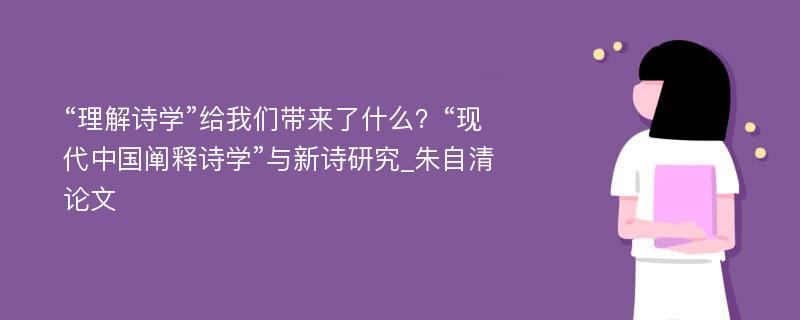
“解诗学”为我们带来什么?——“中国现代解诗学”与新诗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新诗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解诗学”从哪里来?
“中国现代解诗学”的概念,是孙玉石先生在1987年首次提出的。他在《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中国新诗批评史札记之一》①一文中说:“中国现代解诗学是新诗现代化趋向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的诗学批评形态”,是“以理解作品为前提,在理解中实现对作品本体的欣赏和审美判断”。具体地说,这是一种注重诗歌文本的分析,在尊重现代主义诗歌的多义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既追问诗人创作的意图,又允许并启发批评者的审美和再创造。它通过分析意象的涵义及意象间的联系等方法,达成一种对诗歌主题、情绪、语言等多方面的全面理解和欣赏。
虽是首次为“解诗学”命名,但孙玉石先生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概念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历史的‘重建’”。因为,“解诗”的思想是在1930年代随着现代主义诗潮的兴起而出现的,并且已为朱自清、闻一多等前辈批评家所实践,“解诗”一词即直接源自朱自清《新诗杂话》中的一篇论文的题目。对此孙玉石先生提出:“朱自清先生是中国现代解诗学最早的倡导者。……他随着时代与艺术的发展而更新自身的诗歌观念,提出了多元化的新诗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尺度,从宏观上来审视新诗发展的思潮流派、趋向和规律。与此同时,他比别的批评家更早地注意对诗的本体进行微观的解析,并以现代人的诗的自觉意识,把这种实践加以理论化,名之为‘解诗’。这种理论与实践,我称之为中国现代解诗学。”②
也就是说,孙先生关于“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主张,既是一个学术史问题的提炼,又是一种新诗研究与批评方法的提倡;它既来自对中国新诗艺术史、批评史和学术史的史实的尊重和考察,同时又直接指向新诗研究现状中的问题与困境。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1930年代“解诗学”思想的产生是适应于新诗艺术的发展与变化,在诗歌批评领域表现出来的一种对于现代派诗潮的回应。它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和解决了新诗中出现的“晦涩”和“看不懂”的问题,并以其注重和解析文本本身的方式,在新诗潮的探索者与读者、批评者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解的桥梁。而时至1980年代,“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主张则一方面上承“解诗”传统,重新肯定了现代诗的象征手法和多义特征,重新高度评价了现代主义诗潮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它更在新诗批评的领域里回应了近十年间诸如朦胧诗的论争、“九叶派”的重现,以及新生代诗群的勃兴等等现代主义诗潮发展中的新现象,以学术研究的姿态强调了对文本细读的尊重、对文本复杂性的尊重,以及对于现代审美心理与传达方式的尊重。可以说,“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是在用历史来为当时的诗人、读者和批评家提供一种启示,呼吁重新建立一种以强调和尊重诗歌的多义性和复杂性为核心思想的诗歌审美和批评方式。这种方式,看似“旧”法,其反映出来的精神和观念其实又是非常“新”的。这种接通与呼应,也就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打通了一个新的历史脉络。
在“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主张提出后至今的二十多年间,孙玉石先生本人的学术研究始终体现着对这一思想的不断深入探索与实践。他不仅多次撰文阐述“解诗学”的理论内涵、实践原则和历史脉络,同时更在自己的新诗研究和教学中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其成果结为《中国现代诗导读》(两卷)、《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诗人与解诗者如是说》等多部著作。甚至可以说,“解诗学”的思想不仅是孙玉石先生新诗研究的内在脉络,深刻影响着他的新诗流派——尤其是自初期象征派开始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研究,同时,在他的鲁迅研究,尤其是《野草》研究当中,也贯彻着这样一种以“解诗”为基础的研究思路。
在对“解诗学”思想发展历史的发掘中,孙玉石先生深入研究了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以及废名、袁可嘉、唐湜等人的解诗学思想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诗学的理论内涵的三个方面,即:“解诗学是对作品本体复杂性的超越”;“是对作品本体审美性的再造”;“是对作品本体理解歧异性的互补”。同时也总结出解诗实践应遵守的三个原则:“正确理解作品的复义性应以本文内涵的客观包容性为前提”;“理解作品的内涵必须正确把握作者传达语言的逻辑性”;“理解或批评主题的创造性不能完全脱离作者意图的制约性”。③显然,这些理论和原则的总结都是源自“解诗学”前辈的思想与实践,是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实践的基础之上的,绝非孙玉石先生的一时兴起或凭空臆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深入探讨朱自清“解诗学”思想与实践的时候,孙玉石先生特别强调了朱自清“解诗”思想的渊源。他提出,朱自清的“解诗学”思想是在西方诗学理论资源和中国文学传统的碰撞与双向吸收之中建立起来的。他一方面深谙中国古典诗歌文本与诗论批评方法,另一方面又较为系统地接触和接受了英美新批评的方法,受到瑞恰慈、燕卜荪等人的影响。因此,他既有《新诗杂话》等解读新诗的著作,又有大量的古典诗歌细读与分析的成果,在这样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他注重文本分析、尊重诗歌多义性的批评观念,体现了对东西诗学批评传统的沟通。孙玉石先生如此总结说:
朱自清对新理论的接受,还是非常清醒的。他大胆实验运用瑞恰慈、燕卜荪倡导的西方新的理论方法,在篇章字句阐释中,竭尽全力去寻求多义的实际例子,说明他在自觉把握这样一个审美尺度:既不能以狭隘单一的观念,忽略了当句当篇的文义和背景,忽略了比喻本身的背景,要尽量找出字句与比喻背后可能隐含的多重意义,也不能望文生义,罗列各说,对于诗句和比喻,随心所欲地进行超越文本自身限度的阐释。他赞同朱熹说的:“晓得文义是一重,识得意思好处是一重。”……欣赏的时候,文本对于欣赏者,是无限度的。解诗的时候,文本对于说诗者,是有限度的。欣赏的时候,欣赏者对于作品文义,可以“曲解起来,发挥开去”,可以不一定要求“切合”原则,可以“无中生有”,任意添加属于自己理解的东西,也就是西方理论所谓的“一千个读者,即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解诗的时候,说诗者对于作品文义,却不能曲解和发挥,不能不要求努力“切合”原作,不能不要求“自圆其说”,不能不重在一种“意旨”或多个“意旨”的发现与认同。这种有限度的开放阐释,在多元中追求一种或多种“意旨”,反对那种“无中生有,驴唇不对马嘴”的曲解,反对“见仁见智”的过度阐释,正是朱自清解诗学思想与传统的“诗无达诂”观念之间的一个重要分野。……对“诗无达诂”持一定的认同与保留,在传统与西方解诗学资源的双向接受中间,保持某种理论的清醒和必要的张力,这是朱自清发展中国诗歌阐释学,建立中国现代解诗学思想中的精髓。④
孙玉石先生的这段话,突出强调了“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精髓与特性,这正是在“解诗学”的概念之前必须冠以“中国”和“现代”这两个限定的原因。这种“解诗”的观念和方法博采中西方诗学传统之所长,它一方面以西方新批评以文本为核心的思想改写了中国传统诗学批评中过多流连于诗歌文本之外的随意,为“诗无达诂”设置了一定的限度,另一方面它也以中国传统诗学批评中的“知人论诗”思想克制了西方新批评理论中对于作者本意的刻意疏离。所以说,“中国现代解诗学”是一种针对中国新诗文本——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文本——并扬弃了中国诗学批评传统的一种现代的诗歌批评观念和方法。它既与新诗艺术发展相伴生,同时又是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有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解诗学”与谁相关?
“解诗学”既然是一种与现代主义诗潮相伴生的批评观念和方法,那么它当然与现代主义诗学中的诸多问题相关,其中至少包括诗歌的写作、阅读、接受、传播、教育和批评。
首先,它与诗歌的写作和接受相关。“解诗”的需要首先源于新诗艺术风格的新变,亦即源于诗歌开始出现了“不易解”甚或“不可解”的问题。1920年代后期,当新诗经过了近十年的实践和探索,诗歌写作的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初期白话诗的“明白晓畅”已经不能满足新诗人的需要,一种更加含蓄、婉曲,甚至“晦涩”的诗歌效果开始出现,一个又一个新诗人群体的聚集也开始呈现出新的流派和诗潮的意义。对此,穆木天曾给出过非常著名的总结,他称这种新的写作观念和方法为“诗的思维术”和“诗的逻辑学”。他在《谈诗》一文中说:“我们如果想找诗,我们思想时,得当诗去思想。……先当散文去思想,然后译成韵文,我以为是诗道之大忌。我得以诗去思想。我希望中国作诗的青年,得先找一种诗的思维术,一个诗的逻辑学。作诗的人,找诗的思想时,得用诗的思想方法。直接用诗的思考法去思想,直接用诗的旋律的文字写出来:这是直接作诗的方法。”“我们要求的是纯粹诗歌,我们要住的是诗的世界,我们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分界。”⑤这也就是说,在穆木天这样的新诗人看来,诗歌的写作和传达方式、诗歌的语言和结构方式,都是——而且必须是——一种不同于散文的独特的方式。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才能维护诗之为诗的文体特征,从较低的目标上说,是“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分界”,从最高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对于“纯粹诗歌”理想的追求。
因此,当诗歌写作的思维和逻辑表现出它独有的特性,那也就意味着读诗与读散文的方式必不相同。读者显然也必须掌握“诗的思维术”和“诗的逻辑学”,方能进入到“诗的世界”中去。这就间接涉及“解诗”的问题了。
穆木天说:“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要有大的暗示能。……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的世界里的东西。诗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但诗不能说明哲学。”因此,明晰的“说明”被诗人抛弃,而“暗示”则被认为是最适合的表达方式。正如朱自清在评论李金发的诗歌时所说的,他“不将那些比喻放在明白的间架里。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⑥。这种方式很好地符合了诗人所信奉的“诗越不明白越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诗是最忌概念的”之类的观念,因此,那些被“藏起”了“串儿”的“珠子”就造成了一般读者的阅读的困难。而“解诗”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语言和意象的分析,找出那些被藏起来的“串儿”,并由此展示出红红绿绿的一串珠链的整体的美丽。
因此很显然,“解诗”的思想与诗歌传达方式的改变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不易懂”,所以要“解”,而通过“解”,更能让人对这艺术方式的改变产生新的、正确的认识。正如叶公超在1936年曾说过的:“近来因为有人讨论诗的意义,我们渐渐也与西洋一样的感觉到解诗之难了。这实在是一个极好的现象,因为惟有大家公开发表自己的了解,我们才能对于诗有进一步的认识。”⑦的确,正是“解诗之难”引起的广泛争论和带来的解诗学的思想与方法,不仅在解读的层面上切实帮助了读者,更在广泛的范围内带来了对于诗歌艺术变化的“进一步的认识”。沈从文当时也曾说过:“既有读者,作者当然就会多起来”,指的就是读者的理解与批评者的认同对于艺术发展的支持作用。
沈从文这话是在1937年与胡适、梁实秋之间发生的一场关于“看不懂”的争论中说出来的,那场争论也常常为后人提及,并被看做是两种诗歌美学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在这次争论中,同样为新风格的出现进行辩护的还有周作人。他认为,那些所谓“晦涩”的、“看不懂”的诗文并不是如胡适所讥讽的那样“表现能力差”,而是诗人们艺术创作的“作风如此”,“他们也能写很通达的文章,但是创作时觉得非如此不能充分表达出他们的意思和情调”。⑧对此,沈从文有更加尖锐明确的说法,他说:“文学革命初期写作的口号是‘明白易懂’。文章好坏的标准,因之也就有一部分人把他建立在易懂不易懂的上头。……文学革命同社会上别的革命一样,无论当初理想如何健全,它在一个较长实践中,受到外来影响和事实影响,它会‘变’。……因为变,‘明白易懂’的理论,到某一时就限制不住作家。……若一个人保守着原有观念,自然会觉得新来的越来越难懂,作品多晦涩,甚至于‘不通’。……作者既如此,读者也有两种人,一是欢喜明白易懂的,一是欢喜写得较曲折的。这大约就是为什么一篇文章有些人看不懂,有些人又看得懂的原因。”“事实上,当前能写出有风格作品的,与其说是‘缺少表现能力’,不如说是‘有他自己表现的方法’。他们不是对文字的‘疏忽’,实在是对文字‘过于注意’。凡过分希望有他自己的作者,文章写来自然是不大容易在短时期为多数人全懂。”⑨沈从文与周作人在此都强调了批评的作用,尤其是批评家面对艺术的发展变化所应采取的积极主动的批评姿态问题。因为文学会“变”,所以批评也需相应有所发展,而一味指斥作者“表现能力差”,却认识不到这正是他们“有他自己表现方法”的批评家,不仅是没有跟上艺术变化的趋势,更有可能因为武断而对新鲜的艺术风格的生成产生一种伤害。这就是沈从文提醒胡适等人的不要“保守着原有观念”的意思,也道出了艺术与批评之间时时相互催生和促进的规律。
通过这场论争可以看到的是,“解诗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建立起来的。它包含有对于“晦涩”风格的肯定、对于诗歌审美标准变化的尊重、对于诗歌审美多元化的鼓励,以及对于读者的有意识的引导与塑造。周、沈两人的观点代表了论辩一方的认识,即在诗歌的写作新风格与接受的新标准方面,通过这种公开的讨论,维护了新的美学标准,并对读者、批评者进行了一种明确的观念上的引导。
这些其实都已说明,“解诗学”不仅与诗人和读者相关,更与批评者相关。可以说,需要更新“思维术”的,不仅是诗人、读者,更包括能够同时对作者和读者都具有影响力的新诗的批评家。通过批评者的“解诗”,不仅可以给读者提供串起“珠子”的线索,更能提供一座帮助他们理解现代诗歌艺术的桥梁,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于读者群体的教育和培养。
对于那些风格幽曲、意义深邃的诗来说,“解诗”既是批评的一部分,又是批评的前提。即如朱自清所说:“意义的分析是欣赏的基础。”“相信文艺的欣赏和了解是分不开的,了解几分,也就欣赏几分,或不欣赏几分;而了解得从分析意义下手。意义是很复杂的。”⑩叶公超也说过:“懂与不懂可以有很明显的界限,如关于文字的字典意义,你或认识或不认识,但有时候就苦在不能有明显的界限。凡我们不懂的东西,我们就不能说它是好或坏,因为评价是要在传达之后发表的。”他们所说的都是一个简单明确的道理:理解是批评的前提。因此,“解诗学”就是“一种以作品本体为中心的批评诗学”(11),它的出现宣告了“众口一声简单地认为现代派诗‘晦涩朦胧’、‘不好懂’而加以否定的时代”的结束;而它的重建也就宣告了1980年代以前那种对于现代主义诗歌的误解和贬抑的时代的结束。
但必须强调的是,单纯的“解诗”并不等于批评。“解诗学”必须同时包括对文本意义的分析和艺术的批评,而作为一种批评方式的“解诗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充分体现了它的现代意义。孙玉石先生曾经说过,“解诗学”代表了一种批评的新的趋向,即“以客观的文本(包括作品小文本与作家大文本)阐释为主的本体性批评,开始向批评者与作家双向经验互动的主体性批评转变”。“这种主体性批评的特征是:批评本身被看做是一种与创作同等重要的艺术创造。批评家与作家、诗人,在文本意义蕴藏上,进行更深层面上的交流,以及由此而开展两个或多个艺术创造者之间的相互对话,直接介入了文本的阐释,这样就为现代文学批评,特别是中国现代解诗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30年代中期,李健吾与巴金,李健吾与卞之琳,朱自清与卞之琳,他们关于小说诗歌文本内含阐释的对话,就是这方面颇具文学史意义的探索。”(12)孙玉石先生的总结非常准确而重要,他提出的“批评本身被看做是一种与创作同等重要的艺术创造”的思想的确是“解诗学”的精髓。“解诗学”高度肯定和尊重解诗者(批评者)的主体意识,这一点,在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思想中有着最为典型的体现。李健吾认为:“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一件真正的创作,不能因为批评者的另一个存在,勾销自己的存在。”因此,批评就是“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不是挺身挡住另一个人性”,而“看一篇批评,成为看两个人的或离或合的苦乐”。(13)
这种强调“另一个人”的加入的对话性的批评,不仅确立了批评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的地位,同时也明确了作者、文本和批评者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也不仅维护了批评的独立和尊严,更体现了一种批评观念的更新。李健吾曾经在较为感性的层面上指出:一个真正公正的批评家“永久在搜集材料,永久在证明或者修正自己的解释。他要公正,同时一种富有人性的同情,时时润泽他的智慧,不致公正陷于过分的干枯。他不仅仅是印象的,因为他解释的根据,适用自我的存在印证别人一个更深更大的存在,所谓灵魂的冒险者是,他不仅仅在经验,而且要综合自己所有的观察和体会,来鉴定一部作品和作者隐秘的关系。他不应当尽用他自己来解释,因为自己不是最可靠的尺度;最可靠的尺度在比照人类自己以往所有的杰作,用作者来解释他的出产”(14)。李健吾本人的很多文学批评,正是这样的“灵魂的冒险”,虽然也曾被指出有“误读”之处,但也同样“实现了对一个美丽而蕴蓄的文本内涵的深入开掘,而且因此将现代解诗学在繁复经验的多向思考中推到了歧义互补的互动层面。一个对话形态的深层解诗学时间系统,就因此而得到了完整的呈现”(15)。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当然不仅止于诗歌的批评,但他的思想对于“解诗学”的建立却大有启发。可以说,现代“解诗学”是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突出作者与批评者之间的对话的现代的批评方法,其在批评史上的创新意义绝不亚于在诗歌解读方面的实践意义。
最后,“解诗学”还与新诗的传播与教育有关。
在1937年的那场争论中,周作人曾经说过,“看不懂”的问题“有两方面,应该分开来说,不可混合在一起,即一是文艺的,二是教育的”。沈从文对此说得更加直接,他说:“一个中学教员若对这种发展缺少认识,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我认为真真成问题的,不是絮如先生所说‘糊涂文’的普遍流行,也许倒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在当前情形下,我们应当如何想法,使他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过去,现在,得到一个多方面的合理的认识。且从这种认识上,再得到一个‘未来可能是什么’的结论。把这比较合乎史实的叙述也比较健全的希望,告给学生,引导学生从正面去认识一下中国新文学,这件事情实在异常重要。不过关于教员这点认识,是尽他自己去努力好些?还是由大学校帮他们一个忙好些?中学教员既多数是由大学出身的,由大学校想办法应当方便得多。”(16)这段话非常明确地指明了新诗在写作、阅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它的传播与教学,因为这其实正是对于更多的读者的培养与塑造,而“解诗学”在教育与教学中所能起到的实际帮助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孙玉石先生本人就是同时从事新诗研究和教学的大学教授,他曾经说过,“解诗”于他而言,首先也是授课的需要。由此也可见“解诗”在新诗教育和教学中的必要性和实用意义。它不仅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一些主题较为婉曲,存在歧义可能的作品,激发他们的多重理解和阐释,同时也可以逐步培养他们对于新诗各种风格的欣赏和分析能力,更能够像沈从文所说的那样,帮助他们对于新诗的历史与未来建立一种合理的认识与结论。说到底,新诗在高校文学专业中的教学,是在进行诗歌阅读能力与批评能力的培养,而不是仅仅传递新诗史和批评史的知识与结论,因此,“解诗学”作为一种方法,既能破除很多学生对于新诗——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的隔阂、畏惧的心理,又能带领他们进行一次次“灵魂的冒险”,让更多的杰作在他们的心头重生。
三、“解诗学”为我们带来什么?
“中国现代解诗学”带来了一种新诗批评和阐释的方法,它的意义和影响涉及新诗的阅读、接受、传播、教学和批评等诸多方面。与此同时,如果深入讨论“解诗学”背后的思路就会发现,这不仅是一个文学批评的方法,更是透过美学的层面,从文化的角度对于现代文学经验的一种理解。
正如孙玉石先生所说,“现代诗人的玄想思维和文化结构,具有极大的自创性、神秘性和丰富性”(17)。“象征派、现代派诗人的思维,往往与潜意识的作用或者对隐曲的追求有关。思维巨大的跳跃性,心理活动的非连贯性,造成诗的意象和句子的间隔与空白。意象的模糊性与多义性,乃是象征派、现代派诗重要的基础。”(18)从心理和思维的层面上说,象征派、现代派等现代主义诗歌是直接源于现代诗人在经验、心理、思维等方面的复杂化的结果,也即是诗歌经验与艺术思维的发展的结果。因此,“解诗学”的建立或重建,也就是对这种复杂性的肯定,是一种在文化和文学的层面上对于现代人的现代经验的理解与肯定。若再进一步说,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对整个新诗乃至现代文学的理解,即如施蛰存对现代诗所下的定义:“……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19)在现代派诗人看来:“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这种生活所给予我们的诗人的感情,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们从他们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吗?”事实上,不仅仅是自然景物的巨变,同样变化了的还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等很多方面。真正的“现代文学”就是要用现代的形式表达出这一切。这不仅是现代派诗歌的追求,其实也是中国新文学的理想。就连不很赞同现代派诗歌的胡适也说曾过这样的话:“我当时希望——我至今还继续希望的是用现代中国语言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诗。这是我理想中的‘新诗’的意义——不仅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也不仅是‘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来装进外国式的诗意’的诗。”(20)
当然,“解诗学”在为我们带来如此重要的观念和方法的同时,也带来了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空间。比如,在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同时,还应避免在“解诗”的过程中将“诗的思维术”还原或替换为散文的思维。因为,“解诗学”的最终目的在于让读者和批评者与诗人一起,通过“诗的思维术”来进入“纯粹的诗的世界”,如果操作不当,难免有以散文的思维重新取代诗性的思维,导致在“解诗”的过程中丢掉诗之为诗的那个部分。正如金克木曾经说过的:“几乎所有情绪微妙思想深刻的诗都不可懂,因为既然不用散文的铺排说明而用艺术的诗的表现,就根本拒绝了散文的教师式的讲解。”(21)这当然并非对“解诗学”的否定,而是一种有益的提醒。他提醒解诗者不能将“解诗”看做一种简单的操作层面上的文本意义的解读,那样就必然有以易懂的“铺排说明”和“散文的教师式的讲解”来代替“艺术的诗的表现”的可能,那样的话,既无法真正领会诗美、欣赏诗艺,也起不到培养读者、健康批评的作用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解诗学”的认识,必须超越技术的层面,进入到批评理念的层面,认识到其真正的核心价值是在于它作为新诗批评本身的重要意义,而绝不是仅仅作为阅读和理解的辅助,也不是一种批评的中介或附属品。
这可能仅仅是由“解诗学”开启的问题领域的一个部分,它为我们带来的一定还有更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以及由此更进一步地完善诗歌批评的可能。我想,问题的价值也正说明了“解诗学”本身的意义,相信它今后仍将受到继续的关注和讨论。
注释:
①该文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2期,1990年作为《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代序”,形成更为广泛的影响。2010年被编入《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
②孙玉石:《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代序)》,《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第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③孙玉石:《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代序)》,《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第7—16页。
④孙玉石:《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代序)》,《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第16—17页。
⑤穆木天:《谈诗——寄沫若的一封信》,《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
⑥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⑦叶公超:《谈读者的反应》,《自由评论》第33期,1936年7月18日。
⑧知堂:《关于看不懂(一)(通信)》,《独立评论》第241号,1937年7月4日。
⑨沈从文:《关于看不懂(二)(通信)》,《独立评论》第241号,1937年7月4日。
⑩朱自清:《〈新诗杂话〉序》,《新诗杂话》,作家书屋,1947年。
(11)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2)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40页。
(13)刘西渭:《爱情的三部曲——巴金先生作》,《咀华集》,第2—3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
(14)刘西渭:《边城——沈从文先生作》,《咀华集》,第68页。
(15)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55页。
(16)沈从文:《关于看不懂(二)(通信)》,《独立评论》第241号,1937年7月4日。
(17)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38页。
(18)同上书,第30页。
(19)施蛰存:《有关于本刊中的诗》,《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
(20)胡适:《寄徐志摩论新诗》,《胡适文集》第3卷,第2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21)柯可:《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新诗》第4期,1937年1月10日。
标签:朱自清论文; 诗歌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散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