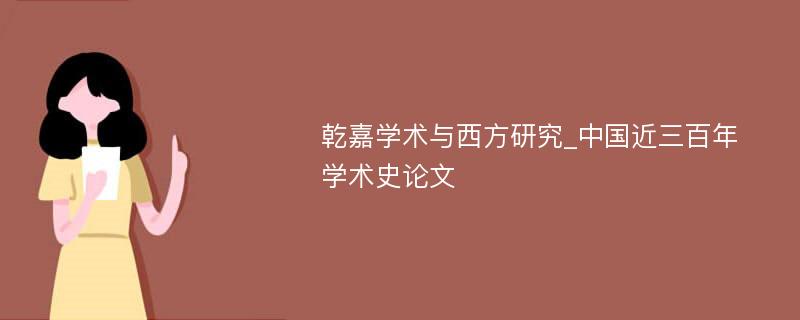
乾嘉学术与西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学术与中国学者在17世纪和18世纪相遇之后,使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考察这些变化,已经成为学术史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本文意在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儒家学者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的反应与西学究竟在何等层面上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研究。
从17世纪初期开始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经过明末清初的动乱,在清代前两任皇帝执政年间更牢固地站稳了脚跟。虽然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持不同意见的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4)神父抱怨中国人不承认与物质分离的精神实质,而且在人类社会的伦理原则和宇宙的自然原则之间不做任何绝对的区别;虽然梵蒂冈在1705年派遣了铎罗(Charles de Tournon)主教出使中国以禁止传教士对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有丝毫宽容以及崇拜孔子和祖先,因而导致许多人离开基督教并且增长了对基督教徒们的仇恨,然而,仍有大量的传教士不断地涌入中国。他们分别来自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德意志、法国等地。
这批人有自己使徒的使命和宗教义务,来到中国后勤奋地工作,学习汉语、满语,除了承担传教的使命之外,还展开测绘和天文学研究、编制地图集、地理学著作,一方面将西方的有关著作翻译过来,一方面又将中国的一些经典翻译过去。这些传教士的科学知识以及绘画和音乐方面的才能,赢得了皇帝和士大夫们的尊重。薛凤祚(仪甫,?~1680)与来自波兰的传教士穆尼阁(Jean-Nicholas Smogolenski,1611~1656)合作撰成20种著作,汇集为《历学会通》或称《天学会通》,他们的著作以阐释天文学和历法为主,并顺便将球面三角形和对数介绍给中国。(注:参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2),第900页。)
1622年,出生于科隆(Cologne)的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到达北京,在清兵入关前,他一直担任钦天监正。1650年,他获准在北京建造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南堂,这座教堂在两年后峻工。但是在此期间,汤若望受到更信奉伊斯兰教的杨光先(长公,1597~1669)的攻击,1655年,汤若望被判处死刑,在最后一刻,他却由于一场颇富戏剧性色彩的地震而获救。汤若望的继承者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在1688至1689年间,战胜了杨光先的盟友,令皇帝明确地相信欧洲天文学的优越性,同时也加强了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注:参见刘梦溪:《汤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角色意义》,《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46-67页。另外参见杨光先《不得已》(黄山书社,2000)及附录一中所录各家对于这次事件的反应。)
一、科学与经史的交融
虽则如此,乾嘉学术与西学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却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然而问题又最多的学术课题——不是过分地强调了就是过低地估计了西学对乾嘉学术的影响作用。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才更准确地展示出了西学与乾嘉学术间的复杂关系。
在1668年至1669年中国历法与西洋历法孰优孰劣展开争论之际,康熙帝开始注意科学事物并对数学发生兴趣。当他发现朝中大臣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时,他亲自加以钻研。而耶稣会士们的测算在被证实是准确的之后,他任命他们来执掌钦天监,并向他们请教西方科学。在康熙帝的最后10年中,他选拔了一批满汉青年交由耶稣会教士传习,这批人共同编纂了一部包含数学、历法、音乐的丛书,名为《律历渊源》。由于康熙的提倡,西学风靡一时,而“西学”或“天学”这门自晚明兴起的新异之学,在清初也成为最优秀学者争相谈论和研究的对象之一。(注:不过,马国贤神父对康熙帝却有这样的评价:“这位皇帝认为他自己是位出色的音乐家,又是卓越的数学家,但是,尽管总的说来他对科学以及其他知识怀有兴趣,他对音乐一无所知,也几乎不懂最基础的数学知识……”见《清代名人传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上册第679页。)
西学在康熙一朝迅速兴起,其原因当如梁启超所说以下两种:
其一,跨越明末清初持续了数十年的中西历法优劣之争与轰动一时的“康熙历狱”的最终结局,既使西方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获得了远较中法“精密”的声誉,也大大地刺激了中国学人对于天文历法的关注与研究之热情。他们普遍相信,在实测方法和事实验证方面,西学可为中学借鉴。
其二,明末清初以来所刊行的大量的西学书籍,尤其汇辑了明末传入的西方宗教与科学的《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以及它的修订本《西洋新法历书》等,为清初及以后的士人研习西学提供了基本的参考读物。《天学初函》是西方宗教与科学的丛书,《西洋新法历书》则是欧洲古典天文学的百科全书,黄宗羲和梅文鼎等人都曾经阅读过它。(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486页起。)
毫无疑问,耶稣会士们的著作有助于加强考证学派的科学倾向,同时他们也促使了中国一些古老学科——如数学——的复活。中国学者欣喜地发现,出现在西方科学中的某些内容在中国的典籍中同样也有所体现。清初最著名的科学家王锡阐(寅旭,1628~1682)和梅文鼎(定九,1633~1721)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对乾嘉学术有着直接的影响。
出于对西方天文学的信任,清廷采用西洋新法编制历书,王锡阐则认为西法在回归年长度变化、岁差、月亮及行星的拱形运动、日月视直径、交食时刻、食分等多个问题上并不完善,根据这样的批评,王锡阐主张中西兼用。王锡阐曾这样说:
欲知新法之诚非,须核其非之实;欲使旧法之无误,宜厘其误之由。然后天官家言在今可以尽革其弊,将来可以益明其故矣。旧法之屈于西法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者无其人也。若是则何从而可?从乎天而已。古人有言:“当顺天以求合,不当为合以验天”。法所以差,固必有致差之故;法所吻合,犹恐有偶合之缘。测愈久则数愈密,思愈精则理愈出。以古法为型范,而取才于天行,考晷漏、审圭表、慎择人、详著法,则异同之见渐可尽泯。成宪一定,不难媲美羲和,高出近代矣。(注:引自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第309页。)
对于王锡阐来说,折衷中西学术是一件可能而且值得做的事情。王锡阐最重要的天文著作是1663年著的六卷《晓庵新法》,在另一部著作《五星行度解》中,他建立了自己的宇宙模型。该模型与主张行星绕太阳转、太阳绕地球转的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体系颇为相似。(注:罗素曾经认为,第谷的体系比哥白尼倒退了一步,见《西方的智慧》(崔权醴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第401页。)他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虽然价值不大,但较之理学家所惯用的以阴阳二气解释一切现象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西学的启示下,中国学人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已经发生变化。
梅文鼎在1647年中秀才之后将学习的兴趣集中在历法和数学方面,这些学科在1645年官方正式采纳了耶稣会士修订的历法之后曾经引起广泛的议论。梅文鼎的主要贡献在于复兴中国传统的天文和算学知识,并且推动了中西天文学的融合。梅文鼎在著作中再次阐明了已失传的古代历理——如郭守敬的三次内插法、黄赤相求术——并使之大放异彩。他写了《交食》、《七政》、《五星管见》、《揆日纪要》、《恒星纪要》等书介绍第谷式的西方天文学。他还借鉴西方天文仪器的原理制成璇玑尺、揆日器、侧望仪、仰观仪、月道仪等多种仪器。梅文鼎在另一部著作《历学疑问》中论述了中西历法的异同,并将许多西方天文知识纳入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如他称西学的“地球寒暖有五带”,即《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六间说”。梅文鼎的这部书由李光地出资刊印,康熙帝也因这部书而对梅文鼎大加赏识。对于他的贡献,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总结了以下五项:
一,历学脱离占验迷信而超然独立于真正科学基础之上,自利、徐启其绪,至定九乃确定。
二,历学之历史的研究——对于诸法为纯客观的比较批评,自定九始。
三,知历学非单纯的技术而必须以数学为基础,将明末学者学历之兴味移到学算方面,自定九始。
四,因治西算而印证以古籍,知吾国亦有固有之算学,因极力提倡以求学问之独立,黄梨洲首倡此论,定九与彼不谋而合。
五,其所著述,除发表自己创见外,更取前人艰深之学理,演为平易浅近之小册,以力求斯学之普及。此事为大学者之所难能,而定九优为之。(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86页。)
梅文鼎在自然科学方面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创造与发明,然而通过他的影响,许多学者都将精力投入到天文历算方面。而他的“会通以求超胜”这句口号,也成为后人接受西学时的一个指南。
1672年,梅文鼎在完成一部关于代数的论著《议程论》后惊奇地发现,西方人在这方面的成就被高估了。许多代数和几何学定律在像《九章算数》这样的中国早期著作中就已经早见端倪。但他在重新协调自然哲学与数学研究时,还是把“理”作了与宋明理学不同的归纳,即“理”是可以用数学推演来进行把握的。艾尔曼曾经认为:“在清代数学从象数学向数学科学转变中,数学在儒学话语中的运用出现根本性变化。”(注: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26页。)有许多精通数学的考据学家相信,数学是研究实学的关键性学科之一。而研究明清实学,也必须把科学技术的因素考虑在内。
戴震的老师江永可能是那个时代中最确信西学的人,这种态度深刻地影响了戴震。
早年戴震的学术兴趣尽管体现在研究儒家经典注疏以及音韵训诂方面,但看一下戴震著作的编年就可以发现,最先让世人熟知的是他在名物礼制与天文历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在中年以前就已经写出《原象》、《历问》、《历古考》、《策算》、《勾股割圜记》等著作,从而把数学、天文方面的知识与精湛的小学研究融为一体。(注:梁启超认为《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学类的提要,也全部出于戴震之手。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88页。)因为他发现,没有精湛的天文历算造诣就不可能理解六经里面与天文、工艺、历法有关的章节与内容,因此也不能正确地理解经典中的重要内容与准确含义。他最早刊行的《考工记图》,就是他相信没有受过科学知识训练的学者无法理解经典记录的古代实用工程技术的原则的应用,他利用数学知识计算和测定了《考工记》中提到的古代礼器铜钟的形状与尺寸,并且准确地恢复了铜钟的原形。程瑶田受他的启发,也开始运用数学知识以恢复古文献之真。
在四库书馆时间,戴震以整理古代的算学著作为首要任务,他整理出了《周髀算经》、《五经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曹算经》。(注:刘师培《戴震传》还特别提到:“尝谓《周髀算经》即古盖天之法,自汉迄明,皆主浑天,惟欧罗巴人入中国,始称别立新法。”见《戴震全书》(黄山书社,1995)第七册附录之二,第84页。)对于戴震的这一贡献,阮元有很清楚的认识:“九数为六艺之一,古之小学也……后世言数者,或杂以太一、三式、占候、卦气之说,由是儒林实学,下与方技同科,是可慨矣!戴庶常……网罗算氏,缀辑遗经,以绍前哲,用遗来学。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则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下哉!”进言之,从江、戴二人开始,历算成为经学研究者所必须掌握的知识,这在明以前的儒家学者中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位乾嘉学术大师钱大昕的一出场,竟也是以精于天文历算而闻名。《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记:“先生在京,与同年褚寅亮、吴朗辈讲明《九章算术》暨西洋测量弧三角诸法,尚书何宗国久领钦天监事,精于推步,先往候之,与论宣城梅氏并明季利、徐诸家之学,洞若观火,何辄逊谢,以为不及……又以御制《数理精蕴》兼综中西法之妙,悉心探核,曲鬯旁通,由是用以观史,则自太初、三统、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时,尽能得其测算之法,故于各史朔闰剥蚀凌犯进退强弱之殊,指掌立辨,咸为抉择而考定之。”(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第31页。)这段文字提醒我们注意到钱大昕十分精通于《九章算术》、西洋测量弧三角诸法、梅文鼎、利玛窦、徐光启以及《数理精蕴》等知识——这些正是由于康熙帝的喜爱而流行一时的显学!不过,同江永或戴震比起来,他并不是一个热烈的自然科学的信奉者,而毋宁是一个历史人文主义者或文化保守主义者,因此他虽然精通西法,但却以提倡中法自任。在钱大昕的眼中,中国古代历法向称先进,因此弄清中国古代的历法更为重要。
在中国有历史文献记载的两千多年中,先后改历达七十余次,其大致情况皆载于历代史书历志之中,它形成了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因这一部分内容横跨历史、天算、数学几个领域,不少史学家束手无策,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面对这种情况,钱大昕运用丰富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并以其原理对历代史志所载天算一一加以审核验证。1754年,钱大昕撰成《三统历术》一书,对《汉书·律历志》中保存的中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历法《三统历》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于其错谬之处刊正脱误,于其文简意奥之处疏通疑难,从而使二千年已绝之学昭然若揭。他的《元史朔闰表》、《三统术衍》、《算经答问》等著作都是发扬中法的代表性著作。
钱大昕还极力提倡宋人秦道古的《数学(书)九章》,顾广圻曾经仔细地校正过这本书,后来又有沈钦裴和宋冕之再次精校并写出札记,使这部书不仅变得可读,并且成为中国算学与西方算学一个可资比较的资源。钱大昕的学生李锐(尚之,1768~1817)也是著名的数学家。(注:李锐在嘉庆间佐浙江巡抚阮元修《畴人传》,又佐扬州知府张敦仁校《缉古算经细草》、《求一算术》等。鲍廷博刻《知不足斋丛书》时,李锐又参与校注《测圆镜海》、《益古演段》。二书在传写中有许多讹误,李锐加注语百余条。自己的著作则有《勾股算术细草》和《方程新术草》等,他的《开方说》最为学者们所称颂,与汪莱、焦循齐名,有“谈天三友”之誉。他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四时成岁,首载《虞书》;五纪明历,见于《洪范》,历学乃致治之要,为政之本。《通典》、《通考》置而不录,不亦慎乎?”见《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第320页。)
阮元相信,数学是研究实学必不可少的和关键性的学科与途径之一。对于他来说,中国早期的数学遗产是研究儒家经典必不可少的辅助性学科之一,阮元区分了邵雍(1011~1077)在研究《易经》时所用的象数学方法和数学的差异,这种差异显然是重要的。他的学友焦循(里堂,1763~1820)也是18世纪晚期以及19世纪初期著名的数学家。他早年曾以大量的时间研究数学,并把自己在数学方面的著作合称为《里堂学算记》,其中包括五个项目。他依靠数学以及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发现运算逻辑是《周易》数理的核心内容,它包括了严密的数学规则,因而使用数学法则排列了《易经》的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他这样说过:“非明九数之齐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画之行;非明六书之假借转注,不足以知彖辞、爻辞、十翼之义。”他进而认为,如果不能做到上述的一些事情,就“不足以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所以阮元在为《里堂学算记》作序时认为:
数为六艺之一,而广其用,则天地之纲纪,群伦之统系也。天与星辰之高远,非数无以交其灵;地域之广轮,非数无以步其极。世事之纠纷繁颐,非数无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谓儒者可以不知数乎!自汉以来,如许商、刘歆、郑康成、贾逵、何休、韦昭、杜预、虞喜、刘焯、刘炫之徒,或步天路而有验于时,或著算术而传之于后。凡在儒林,类能为算。后之学者,喜空谈而不务实学,薄艺事而不为,其学始衰。(注:阮元:《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4),第681页。原标点有错误,已改正。)
对于阮元来说,能够精通天文历算之学,是恢复实学的一个标志,而且也是承继汉魏三国时期儒林传统的一条有效的回归之路。
相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数学是种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纯科学,而数学在文史考证中的运用,也使得清代的学者们开始向纯学术方面递进,这种学术因不受当时解经学中浓厚的道德观点的影响,因此更多地充满了一种知识主义的特征。
二.“西学中源”:儒者的应对策略
西学传来,为中国人的学术生活与知识观念打开了一扇从来没有开启过的天窗。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至少在19世纪晚期之前,西方科学的渗透并未使传统的儒教受到置疑;(注:谢和耐提到:“西方的数学知识甚至在两个世纪中导致了有关中国数学史上的一场大运动,但这些新鲜事物并没有动摇实质性的内容,即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入华耶稣会士的儒教观》,《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耿昇译,巴蜀书社,1993),第84-85页。)西学最早的接受者中间有许多人都企图用西学来为儒学再次注入活力。虽然在耶稣会士以及一些信徒那里并不缺乏对儒学表示置疑的思想,然而当他们把能使儒教的基础受到置疑的论据都收集在一起时,其最后结果却是朝廷决定把基督徒遣返欧洲——这是儒教中国面对外来教理时所能做出的最为真实的反应。
一位法国学者在研究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与北京人文科学二百年间的共处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基督教可以填补一种神修的空白;
——西方科学也可以有其用途;
——耶稣会士们在明末的中国知识界形成了一个从内外均可以看得清楚的边缘集团;
——耶稣会士们自己也关心艺术爱好者们那蒐集了奇异物之样品的特藏(其中无疑也包括欧洲物品);
这位学者最后强调,在做了这样的分类之后,他们便被中国社会吞并了,也就是说大家从此以后不再讲论他们了。(注:约翰·圣索利厄(Jean Sainsaulieu):《入华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前引书第147-148页。)
我们可以想象二百年间耶稣会士与中国文人之间的频繁交流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一些纠葛。中国学人确实从西人那里学到了有用的科学知识,然而却有一种观念阻止了中国学者虚心地学习、接受和吸收西学精华,这就是盛行于朝野上下的“西学中源”说。即使是在黄宗羲与王夫之那里,也认为西学乃从中国传去,西学不过是“剽袭中国之绪余”而已。(注:另外,王夫之还对利玛窦“地形周围九万里之说”加以批判,竟谓“而百年以来,无有能窥其狂呆者,可叹也。”见《思问录》。《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92),第12册第459-460页。)梅瑴成《数理精蕴》卷一认为:“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既有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其真。”钱大昕更是认为:“祖冲之《缀术》,中土失其传,而契丹得之,大石林牙之西,其法流转天方,欧逻巴最后得之,因以其术夸中土而踞乎其上。”(注:钱大昕:《赠谈阶平序》,《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377页。)《四库全书总目》评《周髀算经》也说:“西法出于周髀……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阮元虽然在表面上所持观点不偏颇于任何一方,认为中之与西“枝条虽分,而本干则一”,然而,他却将“西学中源”的观点一一加以坐实,在《畴人传》的凡例中肯定“西方实窃于中国”。
“西学中源”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士人对于西学的认识,即使在晚近,仍有许多人持这种看法。对于乾嘉时期的学者来说,这样认识问题可能是一种策略,即他们可以根据传统来接受或判断他们所要接受的内容,因为他们确实比较容易接受那些与传统相吻合或可能比较容易与之相融合的内容。这样,关于计算的技术与方法就可以融入儒家学者的视界之中。(注:详见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2000)第八章《从会通中西到中学西源》。)
然而,在乾嘉学者中,不论是有限度地还是敞开地接受西学,都清楚地展现出他们拒绝与西方科学知识密切相关的世界观以及伦理意识,这可以从乾嘉学者对一件事情的反应中充分地看出他们对西学的态度。
1660年,安徽人杨光先以《正国体呈》上礼部,控告汤若望所编《时宪历》有“依西洋新法”字样,乃属“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1664年,杨光先再上礼部《请诛邪教状》,告钦天监汤若望造妖书和谋反两项罪名,执政鳌拜准予受理,在次年判处汤若望死刑并禁天主教,将在京的教士发配充军,外省教士则驱逐出境,钦天监被株连的官员有12人。随后,清廷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本不精通天文历法的杨光先虽然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为由推辞了5次但都没有得到批准。处境十分尴尬的杨光先将所写的历次奏疏在1659年汇为《不得已》后就职,尽废西法,改用已经早被徐光启弃用的《大统历》,后来又改用回历。不难想象,他所颁的历书屡有错误。此后正值康熙亲政,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上疏反杨,杨遂下狱。1670至1671年,天主教才再次被允许传教,西人也渐渐重新得到信任。(注: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5),第340-350页。南怀仁留下了许多著作,关于科学者,主要有《仪象志》十四卷,1673年刻于北京。阮元《畴人传》题作《新制灵台仪象志》,分十六卷;《仪象图》二卷,1673年刻于北京;《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1678年刻于北京;《坤舆全图》;《坤舆图说》二卷,1672年刻于北京;《赤道南北星图》,1672年刻于北京;《测验纪略》一卷,1668年刻于北京;现藏于巴黎气象台图书馆的《各种天文研究》,以及满文译本欧几里德《几何》前六卷;在1687年,他还写有《康熙亲政后在清帝国一度遭受遏抑的欧洲天文学又大放异彩》一书,第十三章至第二十八章历述诸传教师实验物理、数学各门,若日时计制造法,弹道学、引水法、机械学、光学、反射光学、透视法、静力学、流体静力学、动力学、气体学、音乐、气象学等科之成绩;1668年还有《康熙皇帝时代中重新采用欧洲天文学综述》一书,内有图画125页,大都是关于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学、光学、水力学、农业及其他应用方法的图画,每图附以汉文说明。诸图皆为南怀仁所制之仪器,即《大清会典》中的“黄道经纬仪”。此外,他还将一些哲学著作介绍给康熙皇帝看。)
1669年十月,“康熙历狱”的中方主角人物杨光先获释出狱,而汤若望已经在1666年病故。随着杨光先的死去,“历狱”一事渐渐从人们注意力中消失,然而围绕“历狱”事件所引发的各种议论却并未平息。钱大昕作《不得已》的跋语说:“杨君于步算并非专家,又无有力助之者,故终为彼所诎。然其诋耶稣异教,禁人传习,不可谓无功于名教矣。”(注:引自《清初士人与西学》,第108页。)孙星衍作《杨光先传》,更是这样认为:“光先文不甚雅驯,而謇谔之节有可取。孟子云:‘能言拒杨、墨之徒。’西人以此敛迹,先生之功,固亦伟哉。”(注:《五松园文稿》卷一,岱南阁丛书本。钱绮(1797~1858)跋《不得已》中甚至以为杨光先为“本朝第一有识有胆人,其书亦为第一有关名教、有功圣学、有济生民之书”,而且甚至还认为杨氏是“正人心,息邪说,孟子之后一人”,今天看来这些观点固然荒唐可笑,但反映在其中的心理,却应为我们所注意。)此二人都是乾嘉时期学术界重要的人物,他们的看法反映了乾嘉时期学人对于西学的态度:一方面承认“新法”比“旧法”(即中国传统历法)要先进和精确得多,一方面又挟持来自于严持夷夏之防的文化态度而不允许西学凌驾于中国学术之上。这种态度,使他们对于西学的吸收有了相当的限定性。钱大昕在写给戴震的信中说:
前遇足下于晓岚所,足下盛称婺源江氏推步之学不在宣城下,仆惟足下之言是信,恨不得即其书读之。顷下榻味经先生邸,始得尽观所谓《翼梅》,其论岁实论定气,大率祖欧逻巴之说而引申之,其意颇不满于宣城,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识之高,何也?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注:《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六,钱大昕对西学的理解,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认为“西人之术止实测于今,不复远稽于古”。)
对于钱大昕来说,“用西学”与“为西人所用”并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面对学术的价值或态度问题。在此意义上,钱大昕已经表现出乾嘉学人对于西学的态度——当面临价值或态度问题时对西学所采取的策略是:“西士之术固有胜于中法者,习其术可也,习其术而为所愚弄不可也。”另外,官方的观点也值得注意。在《四库全书》之中,也收集了多种西方人的著作,农家、天文算法、杂家、谱录等著录了传教士利玛窦、熊三拔(Sabbathino de Ursis,1575~1620)、邓玉函(Jean Terrenz,1576~1630)、艾儒略(Julio Aleni,1582~1649)等十余种作品,并肯定了西方数学、天文、科学、技术的成就(见表,据《四库全书总目》)。
书名 部类撰者 著录存目
依据书本
西儒耳目次韵书金尼阁 存目 两江总督采进本
类利思、安文思、南
西方要纪 地理外纪怀仁
存目 程晋芳家藏本
别本坤舆要纪 地理外纪南怀仁 存目 黄廉采进
表度说天文推步熊三拔 著录 两江总督采进本
简平仪说 天文推步熊三拔 著录 两江总督采进本
天步真原 天文推步穆尼阁撰 薛凤祚译 著录 汪启淑家藏本
辨学遗牍 杂学(宗教) 利玛窦 存目 两江总督采进本
二十五言 杂学(宗教) 利玛窦 存目 浙江巡抚采进本
天主实义 杂学(宗教) 利玛窦 存目 两江总督采进本
畴人十篇 西琴曲意 杂学(宗教) 利玛窦 存目 两江总督采进本
交友论杂学(伦理) 利玛窦 存目 两江总督采进本
七克 杂学(宗教) 庞迪我 存目 两江总督采进本
西学凡(附唐大秦寺 杂学(教育) 艾儒略 存目 两江总督采进本
灵学蠡酌 杂学(宗教) 毕方济 存目 两江总督采进本
空际格致 杂学(理科) 高一志 存目 直隶总督采进本
寰有铨杂学(宗教) 傅汛际 存目 汪启淑
乾坤体义 天文推步利玛窦 著录 两江总督采进本
天问略天文推步阳玛诺 著录 两江总督采进本
几何原本 算书欧几理得 利玛窦译 著录 两江总督采进本
龙华民、邓玉函、罗
算法新书 天文推步雅望、汤若望
著录 陈昌齐家藏本
泰西水法 农家熊三拔 著录 两江总督采进本
奇器图说 谱录类器物之属 邓玉函 著录 两淮盐政采进本
坤舆图说 地理外纪南怀仁 著录 内府藏本
职方外纪 地理外纪艾儒略 著录 两江总督采进本
我们把一些评语列在下面,大体上可以看到《总目》是如何评价这些书籍的:
——评利玛窦《乾坤体义》:“虽篇帙无多,而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者。是以御制《数理精蕴》多采其说而用之。当明季历法乖舛之际,郑世子、载堉、刑云路诸人虽力争其失,而所学不足以相胜。自徐光启等改用新法,乃渐由疏入密。至本朝而益为推阐,殆尽精微,则是书固亦大辂之椎轮矣。”(注:《四库全书总目》,第894-895页。)
——评熊三拔《天问略》:“……前有阳玛诺自序,舍其本术而盛称天主之功。且举所谓第二十重不动之天为诸圣之所居、天堂之所在,信奉天主者,乃得升之,以歆动下愚。盖欲借推测之所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可诬,用意极为诡谲。然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据之术,削去原序,以免荧听。其书中间涉妄谬者,刊除则文义或不相续,姑存其旧,而辟其邪说如右焉。”(注:《四库全书总目》,第895页。原句读有误,今改正。)
——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其于三角、方圆、边线、面积、体积、比例变化相生之义,无不曲折尽显,纤微毕露。光启序称其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非虚语也。又案此书为欧逻巴算学专书,且玛窦序云:前作后述,不绝于世,至欧几里德而为是书,盖亦集诸家之成。故自始至终,毫无疵纇,加以光启反复推阐,其文句尤为明显。以是弁冕西术,不为过矣。”(注:《四库全书总目》,第907页。)
——评艾儒略《西学凡》:“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谓勒铎理加者,文科也;斐禄所费亚者,理科也;默第济纳者,医科也;勒义斯者,法科也;加诺搦斯者,教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致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注:《四库全书总目》,第1080页。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将中国学科与西方学科进行比较并加以评价的起始之作,显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不难从中发现西学在清代考据学家眼中的地位与价值。
这些出自于传教士笔下的著作大多在有关数学和天文著作的绪论或正文中从不忘记提醒读者存在着一个创造主即上帝,是他在治理着万物——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最令信奉儒教的士人感到不安。进一步,他们可能甚至要排斥虽然是科学但却“危害”到儒家经典的内容。为此,西学以及精通验算制造之法的人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对晚近一些的西学著作《四库全书》却所收甚少,像汤若望、(注:《四库全书总目》只是在《新法算书》中提到汤若望所作的《历法西传》、《新法表异》二书时才对他的学术做了评价:“其中有解、有术、有图、有考、有表、有论,皆钩深索隐,密合天行,足以尽欧逻巴历学之蕴。”第896页。)南怀仁、蒋友仁等人的著作都被摒弃于《四库全书》之外,恰是他们的著作代表了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谢和耐就提到,虽然人们一直认为17世纪中叶左右的某些传教士向中国介绍了哥白尼(N.Copernicus,1473~1543)学说,但是经过仔细研究,却发现支持这种假设的标志是不可靠的,无论是在出自传教士们的著作中还是在当时的中国文献中,都找不到任何有关太阳中心论传入中国的明确证据。谢和耐还谨慎地推测,传教士应该提过哥白尼的名字,但是丝毫没有提到过哥白尼的学说。(注:谢和耐:《17世纪基督徒与中国人世界观之比较》,《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72页。)
戴逸在《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论到《四库全书》时,把它和法国的《百科全书》作过比较,希望从中可以看出中西学术的差距:前者的着眼点在收集、保存前人已经撰写的书籍,用力于“汇编”;而后者的着眼点则是综合过去的知识成果,加以阐述发挥,因此用力于“撰写”。(注: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394页。)还有一点是特别不一样的:狄德罗从打算编撰《百科全书》的一开始就拒绝了官方的干预,(注:法国司法部长阿格索向狄德罗建议,编撰工作可以得到国王路易十五的支持,狄德罗断然拒绝。他说:“如果政府参预这项工作,工作就无法完成。君主一句话可以叫人在荒草中造出一座宫殿,但一部百科全书不能凭命令完成。”见安德烈·比利:《狄德罗传》,第64页。)而《四库全书》却是在乾隆皇帝的直接干预下完成的——美国的列文森曾着意提到法国百科全书派中狄罗德的哲学与18世纪中国和法国的思想之间的区别。他引用狄德罗的话说:“今天……为了坚持理性法则,我们正在开始摆脱权威和传统的束缚……我们敢于对一贯认为正确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理论提出怀疑……世界早就期待着一个理性时代的到来,这是一个不再从古典的作家中,而是从自然中寻找法则的时代。”(注: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21页。)——正是这样的差别,使18世纪以后的中国开始和迅速走向近现代的西方拉开距离。
西方在经过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的教徒十分巧妙地使体现上帝意志与科学研究联系在一起。默顿(R.K.Merton)认为,在新教伦理科学领域中,科学家对待科学工作的态度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表达自己的动机时,在预见可能的研究对象时,在面对实际的责难时,科学家便到清教教义中寻找动力、核准和权威等等。(注: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125页。)于是,科学家可以摆脱世俗政治势力的干预而独立开拓自身的空间;而中国儒家的经典却只能提供世俗祖先(包括皇权)的遗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科学不能超越它们而独立存在,因此也无法演化出适合科学生长的研究范式。
三、乾嘉学术之后
西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只限在天文、历法、地理学以及数学等方面以及再次唤起中国人对自己传统中类似学科(如数学)的兴趣。从积极的方面说,学者们从西方科学那里所获得的学术训练,使他们成功地避开了宋明理学中非科学的一面,也为近代中国接受西学留下了合理性的空间。
1955年,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在《世界史丛书》中重复了一种别人已经说过的论点,即中国最早诠释文献的考证学仅限于学术范围内,它随着时间的发展而“破坏了传统以便能尽快进入实业”(注: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第145页。)。为什么非要“破坏了传统”才能“尽快进入实业”?我们从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寻求答案。他将乾嘉以后从事天文历算的人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在钦天监供职的人,因为工作之便,所以会有许多发明,像明安图(静庵)在康熙末由法人杜德美那里得知格列高里和牛顿的三个无穷给数展开式,研究三十余年,用中西二法合解,草成《割圜密率捷法》一书,成为三角函数展开式研究的先导人物。
第二类是经师。他们本非以算学名家,因为研究经典或研究历史需要天文历算方面的知识,因此天文历算也成为他们副业。这一派从黄宗羲、惠天牧那里发源,到戴震、钱大昕时达到顶峰,其后像焦循、程瑶田、凌廷堪、俞正燮等人,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们的目的在于借天文历算来解决经学或史学问题,因此对于天文历算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发明与贡献。但是,后来的一些数学家却出于他们门下。
第三类是专门的算学家,全部的兴趣都在研究和解决数学问题方面,而对于经学或史学的一些问题往往没有太多的创见。(注: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第492-494页。)
我想,这最后一类就是“破坏了传统以便能尽快进入实业”的那些人吧——它的具体含义应该是:从事科学研究与经学传统无关。(注:而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等人,却都并不精通西学。对西学展开最严厉批评的人,恰是最坚决地支持儒家学说的知识分子。)精通西学或验算制造的人同那些精通科学的耶稣会士一样,在18世纪形成了一个鲜明的边缘阶层。他们虽然有特殊的技能与学问,然而却在科举之外,更在经学、史学之外。直至中西冲突迫使朝廷以及文化大员必须重视儒学一向所不屑的“艺”或“技”时,这些人才会脱颖而出,成为19世纪自强运动中的中坚力量。文化大员的幕府中也更愿意招纳拥有这种知识的学者,曾国藩在《求阙斋日记》卷九中就曾经为我们记下了这样的一笔:“李壬叔(善兰)带来二人,一张斯桂,号鲁生,浙江萧山人,工于制造洋器之法;一张文虎,江苏南汇人,精于算法,兼通经学小学,为阮文达公所器赏。”(注:另见李俨编:《李善兰年谱》,《清华学报》1928年第5卷第1期。)非常明显,这些人没有参加科举,也不以博通经史为惟一的目的。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在《万国公报》第15册里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专尚举业论》的文章,试图提出应该采用西国学制分科教导的主张;1899年,他更在《设立专门学堂聘西洋教师教习议》中提出:“宜循欧美各邦高等学堂之制,有一学即有一专门之学堂,士子既领青衿,各因其材之所长,而专习一门。长于格致者,入格致学堂,究天算、形性、博物、重化等学,精益求精,以成全业。”林乐知甚至还设想建立律法学堂、词章学堂、医理学堂、矿务学堂、制造学堂、军政学堂、农政学堂等等。当这些学堂建立之后,林乐知乐观地认为:
门径既专,致精有自,其所成就,益远且大。数年之后,各种人才斐然皆备,不可胜用矣!(注:《汇报》,1899年8月12日,第101号。)
当18世纪的学者为西学在中国的渗透留下合理性的空间,19世纪的文化大员则加速了分科培养学术专门人才的制度化进程,经古之士身上相当浓厚的非政治性以及非道德性色彩,此时已迅速地被更加浓厚的科学色彩所代替,也为完成传统学术向近现代知识的转型做好了准备。(注:杨模编《锡金四哲事实汇存》中有一段话是:“自通商六十年来,代数、微积、声、光、化、电、热力之学,今日习见习闻,能者渐多,问津自易。而当其始,西法初来,扜格不入,苟世无一二人专开通途径,指示方法,提倡于数十年之前,则今日之传习推行,亦未必如是之速。”见《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8册。)
标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文; 中国历法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汤若望论文; 数学论文; 天文论文; 周髀算经论文; 钱大昕论文; 耶稣会论文; 数理精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