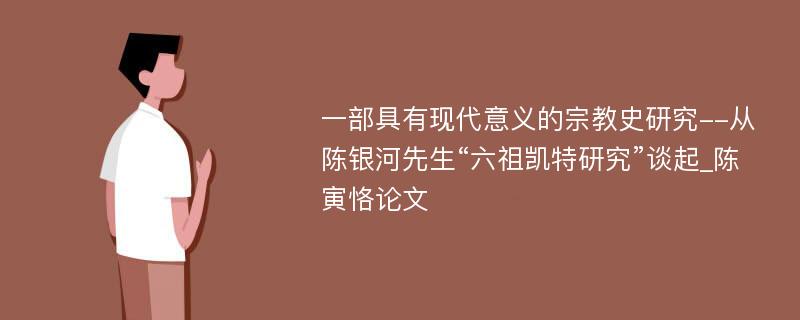
富于现代意味的宗教史研究——从陈寅恪先生关于六祖偈语的研究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宗教论文,意味论文,陈寅恪论文,六祖偈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2年,蔡元培先生在《新维识论序》里说到,“现今学者对于佛教经论之工作,则又有两种新趋势”,一种是欧阳竟无等人从逻辑学、心理学理路以求结论的佛教义理研究,一种则是寻找藏文、梵文、巴利文佛经,与中国的汉译佛经比较,“胪举异同,说明其故”。他说,将来整理内典的事业,必将从这里起步,“然今日所着手者,尚属初步功夫,于微言大义,尚未发生问题也”。这一学术趋势的代表,他只举出两个,一个是在中国的洋人,叫钢和泰,一个是出过洋的中国人,就是刚刚回国几年的陈寅恪(《蔡元培全集》第6卷,207—208页),可见当时陈氏虽然没有发表多少论文,却已经以新的研究方向引起关注。但蔡氏所说略有疑问,说陈寅恪进行佛经的比较研究是不错,不过,说陈寅恪“于微言大义,尚未发生问题”则不合适,这里涉及到一个文献考据与义理研究是否不可贯通的老问题,也关系到对陈寅恪佛教研究价值的评价问题,所以我们不妨对此作一个个案的分析。正是在这一年发表于《清华学报》第7卷第2期的《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是一篇很有趣的论文(已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在这篇论文里我们可以看到陈寅恪先生非常富于现代意味的宗教史研究的思想和方法。
一般来说,传统的禅宗史叙述者都对传说中的“六祖传法偈”采取一种深信不疑的态度,到近代敦煌卷子问世之后,研究者又对它采取存疑的态度,在这一转变中,研究者所站的大体上是判别真伪的历史学或文献学立场。本来,这种研究的立场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判别真伪并不是历史学的终极目标,如六祖传法偈语影响后世禅宗千余年之久,仅仅以敦煌遗书证明其真伪,却并不足以说明其在禅宗史上的意义,而陈寅恪之《分析》则进而探究所有人都不注意的问题,即“此偈之譬喻不适当”和“此偈之意义未完备”。
粗看上去,这首偈语的譬喻与意义之恰当完备并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因为譬喻是文学之事,当与不当只是表达意思程度不同,而意义是佛理之事,完备与否且不论,它已经是被传诵千年的文本,禅宗史上它已经是既成事实。但是,陈寅恪之《分析》则引印度所出佛典指出,印度佛教观身之法“往往比人身于芭蕉等易于解剥之物,以说明五蕴俱空肉体可厌之意”,而传法偈中以菩提树来比喻人身,恰恰与佛教意思相反,因为菩提树是永久坚牢之宝树,“决不能取以比譬变灭无常之肉身,致反乎重心神而轻肉体之教义”(168页),进一步他又指出,传法偈以身、心对举,本来是要说明“身则如树,分析皆空,心则如镜,光明普照”,但是神秀偈中的“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和慧能偈中的“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明镜本清净,可处染尘埃”,都只是说“心”,而没有说到“身”,他举出《楞伽师资记》中求那跋陀之“磨镜”和《续高僧传》中昙伦之“剥葱”来比较,说明传法偈“仅得关于心者之一半,其关于身之一半,以文法及文意言,俱不可通”。
那么,说明其“以文法及文意言俱不可通”又是为了什么?难道要对古代神宗大德进行讨伐么?古人已经逝去,禅宗已立千年,传法偈的修改本“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尽管也不太通,却被禅宗后人当作金科玉律传颂了千三百年,在人们的理解中,都明白它的意思,绝不至于把它弄错,而把肉身当成坚牢不坏的金身,忽略了“心”的意义。说起来,陈寅恪对于传法偈的分析不免有些苛求过分之处,慧能本是文化程度颇低之樵夫,拼凑前人成语也是难免,而能表达佛教大意,已经实属不易,而以《续高僧传》中昙伦“若见有葱,可有剥削,本来无葱,何所剥也”一语在神秀、慧能之前,就断定传法偈“必从此脱胎,无可疑义”,则未免单线孤证,难以成立。但是,我体会陈寅恪之意思,是要以此文表示一种学术的范型,第一,虽佛教史是一个前后传承的思想过程,但后人看上去一些很有思想的表达,其实常常脱胎于前人的只语片言;第二,对于现成的一些观念思想,研究者应当尽可能地追问其来源,把它与最早的一些说法比较,以确认它在思想上究竟多了一些什么或少了一些什么,这样就能了解宗教在历时性变化中的轨迹;第三,陈寅恪的《分析》并不仅仅是说明这首偈语的错误,而是在这一个错误中,说明宗教史中常常有被视为权威的经典。其实往往是一些拼凑起来的语句,它的权威并不来自其本身的真理性,而是来自人们对它的顶礼膜拜,这才使它成为“经典”,他说:“使参究禅那之人,得知今日所传唐世曹溪顿派,匪独其宗风溯源于先代,即文词故实亦莫不掇拾前修之绪余。”
思想史上常常有文献的真伪之争,其实,事情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观察,透过一层看,真史料中有伪,伪史料中有真,正如陈寅恪自己所说过的,“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以为其所依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可是,很久以来,我们的思想史总是要依照一种很简单也是很粗率的进化论来勾勒历史的线索,于是处处时时的历史仿佛都应该是流水一样顺畅合理的,为了使历史合理化,所以常常要把文献解释得很妥帖,把逻辑解释得很完满,于是对于并不那么合乎逻辑的文献资料,要么就说明其为伪造,从而开除出思想史,要么就说明它了不起,从而纳入思想史的逻辑线路。可是,思想毕竟是人的产物,有时它会倒退,有时它会超越,碰上慧能这样不识字的六祖,又刚好他开创了南宗禅,偏偏他又被后人奉上了天,于是思想史应该怎么解释他那似通不通的偈语?米歇尔·福科曾经说,历史中的非连续性应该占据中心,又说,文献即文物,意思就是,历史除了时间线索外,本来不一定有什么逻辑上的连续性,把文献记载排出一个富于逻辑的历史过程,其实很多是主观的建构,应当把文献当做没有主观叙述者出现的文物来看待,以防止文献的撰述者在不知不觉的叙述中把意志渗透到了后人这里,这样,就可以把文献按照考古中确定地层关系式的思路,重新进行排序与解释。
其实,陈寅恪这篇论文的思路中,也已隐隐含有这两层意思。
1996年8月10日于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