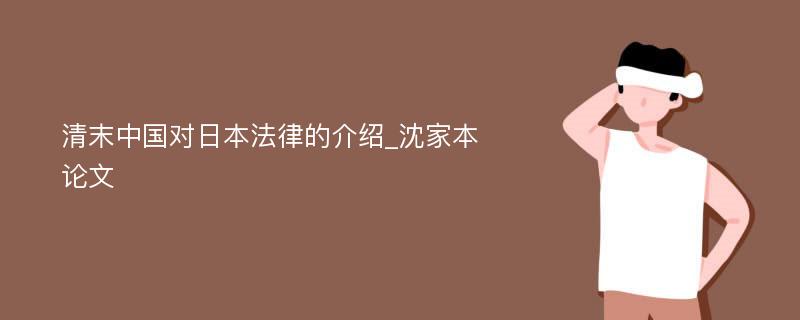
清末中国对日本法学的引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法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6)03-0073-03
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革过程中,日本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学习样板。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向日本学习,借以富国强兵,几乎是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随着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对日本近代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全面介绍,清末的所有改革差不多都会不同程度的从日本吸取营养。1901年后清廷推行法制改革,日本自然又成为借鉴的一个蓝本。从1901年到1911年的十年间,日本的法学著作大量涌入中国。中日法学文化的交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考察清末对日本法学文化的引进途径、内容及其对晚清法律改革的影响,无疑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拓展了对清末新政文化源流的新认识。
最早将日本法学介绍到中国来的是黄遵宪。光绪三年(1877年)黄遵宪跟随中国第一任日本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并担任清朝驻日使馆参赞。当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已进行了差不多十年,现代法学对日本社会变革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已经十分明显。面对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法制日益健全的客观现实,矢志改革又思想敏锐的黄遵宪对法制文化非常感兴趣,多方收集日本明治维新的资料,并撰写成《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他在全面介绍日本社会文化的基础上,更注重对日本法学的评述。《日本国志》卷二十七到卷三十一就是《刑法志》部分。在《刑法志》中,黄遵宪将日本明治13年(1880年)颁行的《治罪法》(480条)和《刑法》(430条)(为同20世纪初颁布的《刑法》相区别,现今日本称其为《旧刑法》)全部翻译为中文,并对不易理解的条款加上自己的注解。这是中国人了解日本近代法学的第一读本。黄遵宪能在日本第一次仿效西方制定近代法律之时,就立即将其翻译成书,引入中国,我们不能不承认其远见卓识。不过,黄遵宪毕竟不是法学家,他的翻译难免有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但历史地看,能在19世纪率先比较系统地引进日本学习西方法律的成果,黄遵宪的功绩不可低估。
更大规模的对日本法学文化的引进几乎是和晚清法律改革同步进行的。20世纪初年晚清的法制改革涉及官制、行政法规、商法、民法、刑法等许多方面,还有法学理论、法学体系等总体构架的许多问题。所以对日本的法学资源求之若渴。在清末法制改革时期,引进日本法学几乎是第一位的头等大事,清廷也确实在这方面下了一番工夫,取得了一定成效。概而观之,最突出的:一是通过对日本法律文本的翻译,积累文化资源:二是派人到日本进行法制考察,取得实际经验;三是聘请日本法制专家来中国工作,脚踏实地推进法制建设;四是通过派留学生学习日本法学知识和在国内创建法制学堂,培养掌握日本现代法学的新型人才。这些讲究实效的措施,虽然在贯彻当中打了一定的折扣,但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它直接为清末的法律改革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和改革依据。
(一)关于大量翻译日本法律和法学著作。
翻译外国法律和法学著作,是清末法律改革中一项重要活动。在修律期间,沈家本带领修订法律馆馆员翻译出一批数量可观、质量较高的外国法典和法律图书。其中,日本法典和法学著作为数最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沈家本对修订法律馆开馆以来近一年中翻译成果进行统计,在翻译的4个国家的12种法典和著作,译自日本法的有7种,超过半数。光绪三十三年(1907),沈家本在《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同办理折》中总结翻译情况,在共计11个国家33种法典和法学著作,日本有15种,约为一半。宣统元年(1909)正月,沈家本对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修订法律馆离部独立以来的翻译工作统计,在共计10个国家的45种法典和法学著作中,日本占13种。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沈家本等将预备立宪期间修订法律馆应办事宜开单奏报朝廷。清单开列已译出4个国家13种法典和著作。日本占3种,所占比例是各次统计最少的一次。
从这几次统计可以看出,修律之初,由于需要迫切,最易翻译和借鉴的日本法典和法学著作被翻译得数量最多,所占比重最重。4次统计(有重复),共103种译作,日本为38种,约占全部的38%。即使不包括重复的统计,共91种,日本为31种,也占约三分之一。
(二)关于考察日本法制。
清政府对日本刑法制度的考察,从为实行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开始。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二十二日到次年正月十二日,载泽一行先后到日本神户、京都、名古屋和东京进行观览,对日本的政治法制有了初步了解。为达到清廷“切实平允,中外通行”的要求,参酌东西择善而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沈家本、伍廷芳专折奏请清廷派员赴日考察法政。次年四月,考察人员到达东京后,日本政府派司法省参事官斋滕十一郎、监狱局事务官小河滋次郎,引导众人到各处裁判所和监狱参观,并于司法省和监狱协会开会讲演。十二月,赴日考察诸人先后回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沈家本奏“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情形”,进呈调查清单,交代考察情况。《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包括调查裁判清单和调查监狱清单,并附《松冈义正日本裁判沿革大要》和《冈田朝太郎死刑宜止一种论》。通过调查,沈家本更坚定了司法独立的立场,指出司法独立是现今“刻不容缓之要图”。考察成员之一董康还就赴日考察所得,编成《裁判访问录》和《监狱访问录》。《裁判访问录》是记录日本司法省参事官斋田十一郎(又译:斋滕十一郎)关于“日本裁判所构成法”的讲述。《监狱访问录》则系小河滋次郎讲演之收录。
(三)关于聘请日本专家。
晚清法律改革奉旨要达到法律的中外通行,按照西方法律模式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的法律体系,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举措。早在刘坤一、张之洞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时,他们就提出要聘请外国法律专家帮助中国修订律例。在他们与袁世凯连衔保举沈家本和伍廷芳时,提出“由出使日本大臣,访求该国法律博士,取其专精民法、刑法者各一人,一并延订来华,协同编译”[1](p.476)。沈家本在主持修律期间,前后共聘请四名日本法律专家(有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志田钾太郎和小河滋次郎)。受聘协助修律的外国法律专家全部是日本人,几乎在整个修律过程中都有日本法学家的参与。他们中间,冈田朝太郎在中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他在中日两国分别出版了数量可观的汉文法学著作。现所能见的他的第一本汉文法学著作是《汉文刑法总则讲义》,该书于日本明治39年(即光绪三十二年),由日本有斐阁书房发行。该书篇幅简短,仅 72页,但是据现在所知,在它之前还没有外国人写汉文法学著作,因而意义匪浅。又如,1908年北京有正书局发行的《大清刑律草案·大清违警律》也是其作品。该书辑录了法律馆编纂而未经确定颁布的刑律草案和经审查复奏颁行的违警律。因为它们都是采用最进步之学理,根据同样的宗旨编纂,故将其合而为一,以便学者参考。冈田朝太郎在礼法之争中参与了对礼教派的斗争。冈田朝太郎起草的近代化的新刑律上奏之后,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非议。沈家本等为使新刑律颁行,与礼教派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冈田“亦助沈氏辞而辟之”,撰文,如《冈田博士论刑律不宜增入和奸之罚则》、《冈田博士论子孙违反教令一条应删去》以及《论大清新刑律重视礼教》等,从法理上驳斥礼教派的谬论。
由于冈田、松冈、志田、小河四位日本法学专家的加入,在清末短短五六年时间里,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监狱法等一系列不同于传统法律的法典草案陆续被制定出来。在中国急切地炮制“中外通行”的法律,移植西方法律之时,不但起草各种新法需要日本法律顾问的协助,大量陌生的法律概念、名词和术语也有赖于他们的解说。这在宣统年间,熊元翰所编的《京师法律学堂笔记》和汪庚年的《京师法律学堂讲义》(1911年5月京师法学汇编社发行)中可见。他们还通过演讲,向不熟悉新法的中国人讲授他们自己才从西方接受过来的法律知识。例如由于司法人员对推行的新式审判机制“多未谙习,临事每有龃龉”,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在1907年发起检察研究会,请四法学家担任演讲,“都凡一月蒇事,于是在京司法人员乃益知检察职务”[2]。
总之,受聘的日本法律专家从起草新律,解释西法,著书立说,教授学生,担任演讲等方面,深刻影响着晚清的法律改革,以至于中国的中华法系在20世纪初终于被日本法学家引进的大陆法系所取代。
(四)关于推广法学教育,培养法学人才。
晚清修律时期,日本对于中国法学教育的影响从两方面得以实现:
1.留学日本。
1896年,清廷首次派出13名留学生前赴日本,从此拉开了留日序幕。由于留学一衣带水的日本较留学远渡重洋的欧美有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文化、风俗相通等许多好处,清政府对留日采取鼓励政策,到20世纪初,中国形成一股“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3](p.22)的留日热。最多时留学生达到1万多人。
当时日本对中国留学生持着接纳态度。日本教育界在不少大学,如: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日本大学、中央大学、法政大学、明治大学等,都设立了专门教授中国学生学习法政的机构和课程。然而,这样正规的培养,入校前要经过考试筛选,培养的学生有限,仍不能满足中国急需法政人才的要求。为此,当时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倡议设立法政速成科。清朝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对此十分支持,并为之多方奔走。1904年,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终于在东京开设。速成科招收学生条件比上述大学部和专门部宽,只要是清朝官员及候补官员,或地方绅士在 20岁以上有汉文根底,不需考试,都可入校学习。速成科,于光绪三十年(1904)开始招生,鉴于急需法政人才的情况,清政府向日本大量派遣“速成生”。这些“速成生”到日本后,集中编班,日本教师用日语授课,由翻译转述。当时许多青年学子急于求成,趋之若鹜。有一篇报道介绍当时的情况说:“法政大学开设法政速成科五月始开学,十月间复开第二班,入学者计已二百余人,后之来者正未有艾,夫法政乃中国今日最重之急务,自此科之设,其发达如此之速且盛。”[4](p.196)但速成科招收与培养都有粗滥之嫌,常遭舆论批评。两年后,梅谦次郎访问中国,会见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觉得法政速成科问题不少,经反复商讨之后,决定不再招生。
据统计,辛亥革命以前毕业于法政大学的中国留日学生计1364人[5](p.196)。加上其他正规、非正规的各种法政毕业生,数目更多。这些人虽然不乏鱼目混珠之辈,但亦有不少合格的法政人才。他们留学回国后,成为法律改革的一股力量。
2.创设新式学堂和延聘日本教习来华。
仅仅靠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不能满足中国实行新政的需要。为大量培养“讲求法律之人”,在沈家本诸人的努力下,中国国内的新式法学教育也开始设立。
光绪三十一年(1905),沈家本、伍廷芳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并附奏片,提出:“新律修订,亟应储备裁判人才。宜在京师设法律学堂,考取各部属员入堂肄业,毕业后派往各省,为佐理新政、分治地方之用。”[6](p.9)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京师法律学堂正式开学。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由中央官办的法律专门学校。其章程规定学堂以“造就已仕人员,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智识,足资应用为宗旨。并养成裁判人才,期收速效”[7]。据宣统年间熊元翰所编的《京师法律学堂笔记》(安徽法学社印行)和汪庚年的《京师法律学堂讲义》(日人寺岛荣之助印刷,京师法学社发行)记载担任京师法律学堂授课的主要是日本教习。
京师法律学堂就像一场春雨,催发了各种法政学堂的苏醒。从此,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法政学堂及速成学堂纷纷设立。新式法学教育的大规模举办,自然需要大量接受了近代法学教育的新式教员。这种专门人才,在国内十分缺乏。而日本自明治之后法学发达,高薪聘请日本教员成为必要之举。此外,归国的留日法政学生亦是师资来源之一。据汪向荣先生的《日本教习分布表》,京师法律学堂聘请日本教习6人,除了协助修律的冈田朝太郎 (任总教习)等4位之外,还有岩井尊文和中封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聘请了岩谷孙藏、杉荣三郎、法贵庆次郎、冈田朝太郎和织田万。京师法政学堂聘请了11名日本教习,而高等巡警学堂则聘请了19名。而叶龙彦先生的《直隶法政学堂教员表》显示,该学堂教员共14名,其中日本教习与归国留日学生各占5名,两者大约共占总教员的71%[8](p.208)。
由于新式法律学堂大量聘用日本教习和留日归国学生,而他们讲授的课程,大多以日本法学为内容。他们将业已日本化的西方近代法学,通过各地学堂输入中国。在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建立之初,中国接受的法学教育主要是日本的法学。
【收稿日期】2006-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