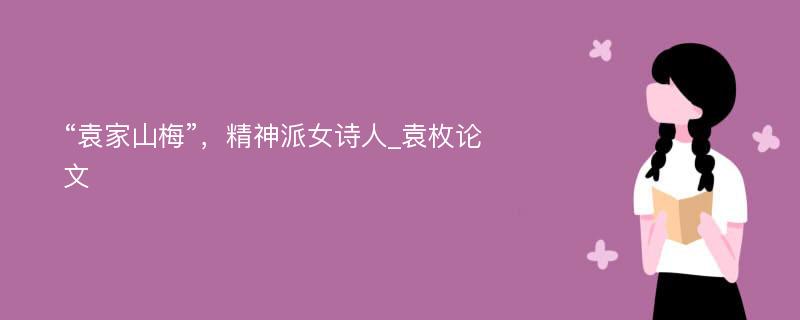
性灵派女诗人“袁家三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灵论文,女诗人论文,袁家三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袁家三妹”袁棠、袁杼、袁机是袁氏家族女性诗人的代表人物,亦是性灵派中女性诗人的佼佼者。“袁家三妹”的诗作皆抒写真情实感,但又独具艺术个性。“袁家三妹”以性灵诗的清新诗风,冲击了诗坛格调诗的拟古形式主义以及肌理诗的以学问考据为诗的习气,为使诗歌回归抒写真性情之正途作出贡献,在性灵派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性灵派以袁枚为主将,赵翼为副将,孙原湘、张问陶等著名诗人以及众弟子为主力。此外有两支偏师:一支是由席佩兰等四十余位才女组成的女弟子诗人群体①;一支则是袁枚之兄弟姐妹等亲属所构成的袁氏家族诗人群体。
袁氏家族诗人可分男性诗人与女性诗人。男性诗人以袁枚堂弟袁树为中坚,另有袁枚堂大妹袁杰夫婿胡德琳,袁枚二姐之子、外甥陆建,袁枚大姐之子、外甥王健庵,袁枚堂四妹袁棠之子汪庭萱,袁枚堂弟袁步蟾、袁履青等。②女性诗人以“袁家三妹”袁棠、袁杼、袁机为骨干,另有袁枚堂大妹袁杰以及孙女辈袁妽、袁绶、袁淑、袁嘉等。无论男性诗人还是女性诗人,其主要成员皆于袁枚身边生活过,聆听过袁枚关于作诗的教诲指点,深受袁枚性灵说与性灵诗的影响,其作品亦不同程度地具备性灵诗的审美特征,从而成为性灵派诗人。
“袁家三妹”是袁氏家族女性诗人的代表人物,亦是性灵派女性诗人的佼佼者。“袁家三妹”之工诗,与袁枚等一批具有一定程度男女平等思想的文士提倡女子写诗、批判“女子不宜为诗”的陈腐传统观念密切相连。袁枚称“圣人以《关睢》、《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③。其所言尽管牵强,但对扫除女子为诗之障碍、鼓励其“三妹”创作具有很大作用。而袁枚大力倡导性灵说,主张诗人独抒性灵,抒写个人生活遭际,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必囿于唐诗格调,更不必卖弄学问,这对于像“三妹”这样学问不深的女性诗人来说,亦打消了写诗的种种顾忌。加上“三妹”皆为聪慧有才的女子,又有阿兄指点扶持,因此在创作上小有成就、并成为杰出女诗人亦是很自然的。下面对“三妹”的诗歌创作分别作简略评述。
一、袁棠
《袁家三妹合稿》④四卷有《盈书阁遗稿》与《绣馀吟稿》两卷,皆为袁棠之作,达220余首。袁棠不仅存诗最多,诗才亦最高,就诗歌思想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以及艺术表现的生动性来看,在“三妹”之间应以袁棠为翘楚。
袁棠字秋卿,一字云扶,籍贯杭州,为袁枚叔父袁鸿第四女,袁枚堂四妹。袁棠雍正十年(1732)生于广西桂林,时其父袁鸿正于广西巡抚金鉷府中任幕僚。乾隆九年(1744)袁枚归葬叔父于杭州,始见十三岁的袁棠,曾“读其《中秋》、《七夕》等作,爱其清绝,色然而骇。亟饷一钗以劼毖之。妹窃喜,自负益奋,从此以诗名噪于时”。乾隆二十三年(1758)袁棠嫁扬州汪孟翊(楷亭)为继室,家颇温饱,伉俪情笃,深得翁姑欢心,且以其才学得汪氏亲友“有林下风”之誉。袁枚尝过扬州探望,袁棠于热情款待之后,又“捧草稿出,拭几磨墨”,视袁枚而笑。袁枚乃戏曰:“女弟子又索诊诗耶?”应声曰:“阿兄之聪也。”⑤可见袁棠颇钟情于诗,又大受益于袁枚的批点。可惜乾隆三十六年(1771)袁棠死于难产,年仅三十八岁。
袁枚评袁棠“诗渊雅,志洁而情深”⑥,汪孟翊则评其妻“所为诗,皆发于至情至性,无香奁气”⑦。“情深”、“至情至性”,这正是袁棠性灵诗之真谛。
作为闺阁女子,袁棠及袁杼、袁机一生基本上是封闭在闺房庭院之中,很少有出游拓宽眼界的机会,生活单调,内心空虚;而可以作为感情交流对象的夫婿与兄弟却长年外出游学或任职,因此怀念亲人、渴望团聚是她们感情世界的重要内容,亦是其作为宣泄感情之渠道的诗歌作品的重要主题。袁棠思夫外出之作颇引人注目。这类作品有写于不同时期的同题《寄怀夫子》五首,以及《绿暗》、《七夕不寐有感》等。且看题为《寄怀夫子》的两首七律:
因君几度感行藏,惯向江湖老客装。秋逼画堂亲鬓老,霜飞荻港客舟凉。休憎蕊榜功名薄,且喜诗囊姓字香。何日湖山归计好?烟萝同醉菊花黄。
叶展新荷艳艳红,炎途遥念客行踪。云蒸赤日舟千里,帆向青山路几重?书案昼闲人影淡,晚窗风净月华浓。路旁名利何人足?江南江北憔悴容。
前诗写凉秋怀夫,后诗写炎夏思婿。作者想象丈夫或于秋逼霜飞或于赤日炎途的时空环境中,长年奔波,备尝艰辛,心中充满疼爱之情;但又认识到,是士子所追求的“功名”、“名利”害得丈夫与自己天隔一方,享受不到“烟萝同醉菊花黄”的夫妻团圆的生活,因此公然宣称:“路旁名利何人足?江南并北憔悴容”、“休憎蕊榜功名薄,且喜诗囊姓字香。”这些诗句是作者轻视功名利禄、渴望夫妻幸福的“至情至性”,是发自性灵的真实的心声,而其个性亦颇鲜明。
袁棠有兄弟姊妹多人,他们是袁棠生活中的伴侣,酬唱时的诗友。袁棠又是极重手足情份的人,但自出嫁扬州之后,手足之间相聚之日甚少,因此于思夫之馀,怀念兄弟姊妹之作颇多。这些诗一是“情真”;二是借景寓情,比如作者特别喜欢选择秋夜明月之景作为抒写离情的媒介。这种构思固然有“千里共婵娟”的传统含义,同时亦因作者于孤独的处境中,无人可共语时,只能将感情别移于明月,赋之以性灵,视之为可以倾诉思念之情的知己。如《秋夜怀兄》、《秋夜对月呈步蟾三兄》、《对月有怀兄姊》、《对月呈香亭二兄》、《送赛英大姊入蜀》等,莫不借月抒怀。诗人的真情仿佛融入千里月色之中。其诗中之月多为作者主观化、性灵化了的意象。其实,不仅秋月,其他许多自然物象在诗人笔下亦都被点化为性灵之物,成为寄托其抒写手足深情的载体。如《送赛英姊入蜀》“岸柳恨牵离合梦,官河愁听可怜声”,移恨、愁于岸柳、官河,使它们替诗人表现离别之苦;《舟中再送赛英大姊、步蟾三兄》,又将无生命之秋水转化成为感情的信使,带着作者思念之梦进入大姊、三兄所在之四川,“秋水”自蕴含着深情。
袁棠的“至情至性”在悲悼诗中有更感人的表现。与兄弟姐妹生离尚且令诗人牵肠挂肚、怀念不己,而一旦死别自然更悲不自禁,并借诗追悼之。如七律《哭素文三姐》两首之二:
诸兄来说泪纷纷,无限伤情不忍闻。旧梦难寻他日约,招魂空奠隔江云。半生辛苦狂夫怨,中路凄凉弱女分。剩有千秋遗韵在,清风林下吊斜曛。
前三联乃直抒胸臆,尽情倾吐哀思,既哀姐妹永诀,又叹素文命运悲惨,充溢着深至的同情、怜惜与凄怆。诗末则将悲哀凝聚在“清风林下吊斜曛”的凄楚画面中,飘忽的感情为之“定格”,让人去品味。此诗可以说是以抒怀为主,而《寄焚五弟周忌灵几》三首,则仍重在以景寓情,其前二首云:
回想当年同夜课,弟吟我绣共灯清。沉思执卷工须静,着意轻轻放剪声。
一篇遥寄付阴曹,知弟孤灵何处飘?古刹云封帏幙冷,可怜寒月照清宵。
前诗以平浅的语言,白描的手法,描绘了当年姐弟于清灯下“同夜课”的动人情景:弟吟诗作文”,“沉思执卷”,姐刺绣陪伴,唯恐打扰弟的思考,故“着意轻轻放剪声”。生动的细节,传神地写出作者对五弟的体贴。而今日在弟灵几前追思往事,皆为虚无,该何其悲痛!后诗前半写情,后半写景。写情固在显露难觅五弟“孤灵”之哀,写景亦极凄凉,古刹、帏幙、寒月,无不蕴藉着悼念之情,而且十分深沉。袁棠这两首以白描见长的抒情诗尤具性灵诗之本色。
在袁家三妹中,相比而言,袁棠是最有个性、有思想的女子。前已述及其怀夫诗中鄙薄功名利禄的可贵思想,另外《古意四首》其一:“贤哲雅可恃,富贵何足崇!”亦颇有“富贵于我如浮云”之襟怀。在其他诗中还有个性的张扬,《古意四首》其三即公开宣称:“每写平生怀,颇负男儿志。断物传太阿,逢时贵利器。试看北斗光,横空有奇气。”其“男儿志”虽未详说,但欲为“太阿”、“利器”,对社会有所作为还是可以看出的。可惜对女子来说这只能是幻想,现实是行不通的,故《寄香亭二兄》于感叹二兄仕途多舛之后,又自叹:“常对芙蓉染衣镜,堪嗟侬不是男儿!”如此直率无忌,真乃性灵之言,正如袁枚所说,“诗写性情,惟我所适”⑧,显示出性灵诗的特点。自叹之馀,袁棠又发出“看来皓魄偏怜我,恨杀青云尽属男”⑨的不平之声。既然身处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社会,自己又不能变成大丈夫,亦只能“恨杀”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了。而《小园杂咏》三首其一云“也有不平闺阁事,海棠窗下读《离骚》”,又表叠有明其“不平”与屈原忧国忧民之愤恨相通。这些诗句毫不掩饰自己渴望与男子平等以有所作为的自尊好强的个性,内含几分阳刚之气。故其夫汪氏称她诗“无香奁气”,堪称知音。
袁枚于《绣馀吟稿》序中誉袁棠“可谓扫眉之才人,不栉之进士矣”,虽不无溢美之处,但其艺术表现确实可圈可点:首先,袁棠想象力甚强,常常创造出并未亲眼目睹的意象、意境;其次,袁裳善于运用比喻、拟人的手法,构思出新鲜、有情致的意象;再次,袁棠长于锤句炼字,化静为动,使诗歌形象活泼有趣。此皆符合袁枚性灵说对诗的审美要求。在袁家三妹中,袁棠之诗才确实最高,笔性最灵,堪称第一。
二、袁杼
袁杼为袁枚四妹,字静宜,号绮文,籍贯杭州。嫁松江韩思永,但早寡,只好依兄居南京随园。其生卒履历不甚详,袁枚著作亦很少提及。她既为袁机妹,则生年不会早于袁机生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其诗集中有《重悼方姬》诗,则其卒年不会早于方姬卒年乾隆三十八年(1773)。另其《病危作》有“未了三生事,公然五十春”句,又可知其享年五十左右。其《楼居小草》一卷,存诗60余首,基本上是律绝近体诗。集前有白门(南京)严长明《题辞》七绝八首,称袁杼“自镜明流自写哀”、“自怜身世小沧桑”,道出其诗作以自哀自怨的题材为主。这完全由其早年守寡,晚年丧子,身体多病又寄居兄家之“少福泽”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
袁杼体弱多病,加之多愁善感的个性,抒写哀思愁绪、生老病死成为其创作的主流。这类题材的作品“愁肠成九曲”⑩,自然难破自哀自怜的樊篱。如“预防秋后病,多点佛前香”(11),“病躯难下深深拜,仙乐遥闻远远流”(12),“黄泉源旧路,重证昔时因”(13),皆抒发生命之忧以及表现病中情态。典型的是两首《病中作》:
柳娇莺啼病初生,匝月经旬二竖成。欲对青山聊遣意,岂知白昼最无情?穿梁鼠斗心犹怯,绕帐蛾飞胆又惊。一角帘垂何日卷?重帷犹自怕风声。
终日恹恹是弱躯,懒持中馈食无鱼。阴雷半夜惊孤影,骤雨三更怕湿书。教女挽头先理发,感人问病强牵裾。九原若不栽荆棘,愿撇红尘地府居。
二诗皆写生理上的疾病及因此而出现的心理的脆弱病态,无论是“穿梁鼠斗”、“绕帐蛾飞”的外界干扰,还是半夜阴雷、三更骤雨的天气变化,无不使作者产生心惊胆战的忧生之意,真实细致地表现出内心的痛苦与虚弱。而“九原若不栽荆棘,愿撇红尘地府居”的设想,又分明流露出对生活与生命的厌倦。联系作者的遭遇与处境,这些表白都是肺腑之言,性灵之句。袁杼这种脆弱悲哀的心态,若遇上亲人死亡则更受刺激,故往往借悼亡诗以宣泄悲思。如《悼亡》追悼亡夫韩氏,“欲图梦里模糊见,惨见凄雨梦不成”,连梦中与亡夫相见的念头都被惨风凄雨惊破,其惨凄的生活现状真可催人下泪;《哭云扶妹》“异乡姐妹空肠断,难渡长江奠酒卮”,不仅表现了未能亲奠袁棠妹的遗恨,亦暗寓自哀之意;而《悼老仆》“从此阶前无汝至,落红飞处也伤神”,固然怀念忠厚的老仆,更为自己的命运“伤神”。类似之作皆感情沉挚,发自性灵。最为令人肝肠欲断的是《哭儿》七绝二首:
容易芝兰膝下生?一朝缘尽夜三更。阿娘知汝《离骚》熟,苦诵《招魂》坐到明。
顷刻书堂变影堂,举头明月望如霜。伤心拟拍灵床问:儿往何乡是故乡?
诗前有小序记云:“儿名执玉,九岁能诗,十二岁入学。十五岁秋试毕,病。病危,目且瞑矣,忽强视问:唐诗‘举头望明月’,下句若何?余曰:‘低头思故乡。’曰:‘是也。’一笑而逝。”可知执玉是一神童式的早熟少年,不幸十五岁即夭折。其死前与母亲的问答,竟还借用李白《静夜思》诗句以表白其思念故乡之情,可谓聪明绝顶。诗人并不采用号天抢地般的强烈方式抒发悲哀,而是以貌似平淡的语言表现内心的巨痛。诗人于二诗后两句皆采用动作细节,将前两句的哀思具象化,使人可深长思之。前诗写因儿子熟知《离骚》(此指代《楚辞》),故通宵“苦诵”《楚辞》之《招魂》,此句一石双鸟,既是满足亡儿钟爱《楚辞》的意愿,又是表白自己招儿亡魂归来的深情。后诗“拍灵床问”的动作与“儿往何乡是故乡”的问语,更饱含悲肠寸断的强烈感情。袁枚性灵说推重”诗有极平浅,而意味深长者”(14),这二首《哭儿》诗足以当之,是典型的性灵诗。
袁杼才力不及袁棠,主要表现在诗的想象力不强。她很少有“精鹜八极,心游万仞”(15)之句,笔下写景咏物基本上是写实,是眼前景,身边事。这一方面是限于思维的封闭,一方面是囿于闺阁生活,加之性格柔弱,笔力纤巧,故只能构思庭院小景,其清幽意境与袁棠诗之壮阔意境自然相异。但袁杼写景观察细致,感受真切,纤巧清新,同样属于性灵诗,如七律《咏雪》中间两联写雪中之景云:“满径馀光银烛冷,连天晓色镜花空。鸥飞鹭立难寻觅,掩却栏杆一角红。”因为下雪,“银烛”之光亦为之变“冷”,“镜花”为之变“空”,白色鸥鹭与雪相融似亦为之消失,这些景物于雪中之变化,皆诗人细致独特的感受与发现,道人所未道,具有清新之意。又如《春燕》写春燕“带雨香泥湿,穿花羽毛新。势低因舞倦,不是为依人”,简直明察秋毫,细致而真切,又纯用白描手法,形象地写出春燕的特征。袁杼的才力不足,又决定了其所关注的只能是小景琐事,所选择的是琐屑意象。如《秋斋闲咏》所写无非是庭院内外的“落叶”、“林梢”、“老竹”、鹊巢”等纤细意象,以及“描花”、“写字”、制酱、呼婢等生活琐事,平淡无奇,亦无深义,但真实具体地反映出一个多病闲居女子的生活状态与生存方式。
袁杼笔下的自然之物亦常拟人化,赋予性灵,尽管不是很出色,但体现了性灵诗人的共性。如《不寐》之“替掩双扉风作主,代翻空柜鼠求粮”,“风”与“鼠”皆有人情味,可为作者掩扉、翻柜,不仅有一定情致,更映衬出诗人清夜难寐的孤寂心境。而《迎春》之“雪花飞六角,如与玉梅争”,一方面观察细致,写出雪花“六角”之形;一方面又赋雪花以争强好胜的个性,突出其洁美的气质,暗寓作者艳羡之意。
要之,袁杼诗具有性灵诗的某些特点,如抒写真性情,不用或少用典故,语言平浅,构思别致。而意象纤巧,题材狭窄,风格单一,思想肤浅,则是袁杼诗的特点或不足。
三、袁机
袁机字素文,号青琳居士,袁枚三妹。籍贯杭州。据袁枚《女弟素文传》,“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一月死,年四十”,袁枚又称自己“长妹四岁”,袁枚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则可证袁机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在袁家女子中,袁机命运最为悲惨,名副其实的“多坎坷,少福泽”。据袁枚《女弟素文传》、《祭妹文》可知大略:袁机“晳而长,端丽为女兄弟冠。年幼好读书,既长,益习于诵”。其未满周岁时,就由父亲作主许与如皋高八之子(时尚在母腹中)。乾隆八年(1742)高八曾以“其子病,不可以婚”为由要求解除其子与袁机婚约。袁机闻后竟“持金锁而泣,不食”,“意复高氏”,“高之侧人惊,欢传高氏得贞妇”。后高八殁,其侄继祖又来劝说袁父:“婿非疾也。有禽兽行,叔杖死而苏;恐以怨报德,故躛言辞婚。贤女无自苦。”但袁机听而不闻,最后硬是嫁给高氏子。高氏子丑陋躁戾,不许袁机写诗作女工,还常对袁机“手掐足踆,烧灼之毒毕具”。最后高氏子为还赌债,竟欲将袁机卖掉。至此袁机才被其父解救回家。但袁机“自离婿后,长斋,衣不纯彩,不髲剃,不闻乐,有病不治,遇风辰花朝,辄背人而泣”。乾隆二十三年(1758)高氏子死,两年后袁机亦卒,留下哑女阿印。袁机自幼习经读书,深受“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毒害,故一生信奉“女子从一而终”的伦理道德,终于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故其堂弟袁树《哭三姊》感叹:“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袁机“少时吟咏极多”,“嫁后,良人戒诗,稿亦散失”,今存袁枚所编《素文女子遗稿》一卷,乃“归宁以来之作”,仅30余首,“粗存梗概”而已。(16)袁机婚后之悲剧自然决定了其存诗的内容与风格。
袁机与袁杼创作题材与风格比较接近,与袁棠则相差较远。由于她性格温顺,韧性甚强,颇能忍受生活的不幸与煎熬,因此其抒写愁怨比袁杼更含蓄蕴藉,或者说“温柔敦厚”;即使内心有大波大澜,亦不声泪俱下,而是尽量克制而以温柔出之。其《有凤》云:
有凤荒山老,桐花不复春。死悲怜弱女,生已作陈人。镫影三更梦,墨花顷刻身。自伤明镜里,日日泪痕新。
首联采用比兴手法,以“凤”与“桐花”自喻,表现青春凋零之悲。颔联、颈联写生死两难的心境与孤独凄凉之处境。尾联“自伤”天天以泪洗面的悲惨命运,但感情似乎并不冲动,仅以叙事之笔出之。又如《感怀》亦只是发出“回首夕阳芳草路,那堪憔悴恨悠悠”的叹息而已。此类诗均不失袁枚所谓“诗贵温柔”(17)之旨。袁机咏物诗隐然是咏怀,如《镜》、《洒》等同样为“自伤”之作,但更加含蓄温柔。写镜“无人来照影,抛掷井栏边”,写灯“有焰尚能争皎月,无花只可耐孤吟。平生一点分明意,每为终风恨不禁”,皆蕴含其孤独、哀伤以及遭受摧残之意。倘不知人论世,仔细咀嚼,是不容易探清其底蕴的。
袁机为人太善良,加之“从一而终”的观念根深蒂固,以至对于恶婿竟无仇恨之意,或者说从感情深处终于原谅了他。因此高氏子死后,仍写下《追悼》三首。其三云:
死别今方觉,生存已少缘。结褵过十载,聚首只经年。旧事浑如昨,伤心总问天。萧萧风雨际,肠断落花烟。
首联二句乃倒装,夫婿生时已与自己少缘,但今日丈夫亡故才真正意识到两人缘份已尽,永远地诀别了。其中不无惋惜之意,袁机即使曾有怨恨,此时已冰释矣。这种感情的流露真实而自然,毫不矫饰。颔联承首联意,叙写夫妻虽已成婚十余年,但同居一处不过年把,又暗寓遗憾。颈联乃追忆往昔之痛苦旧事,但“伤心总问天”,有呵问苍天何以不使其夫妻和睦恩爱之意,却并不责怪恶婿。尾联乃以景收束,营造出凄苦的气氛,又分明寓夫亡而“肠断”之哀。其意蕴亦耐人寻味,既因夫婿之亡而肠断,更因自己从此无缘享受夫妻无伦之乐而肠断。作者的感情与观念或许近乎迂,不足为训,但却是真挚的,符合其性格的。
袁机离婿归宁,内心既痛苦不堪,又时时渴望、羡慕伉俪情笃的生活,其中不排斥有恶婿改邪归正与之重归于好的幻想。这是其写出《追悼》之作的思想基础。因此她在“无家叹我因缘恶”(18)之时,又写下《闲情》、《春怀》这样的绝句:
欲卷湘帘问岁华,不知春在几人家。一双燕子殷勤甚,衔到窗前尽落花。
三月清明柳最娇,春痕红到海棠梢。寄声梁上双飞燕,好啄香泥补旧巢。
二诗皆写作者因春天降临产生了“春女思”(19)式的渴望。春天象征生命,亦催化着爱情。作者作为独居的年轻女子,难免春心躁动,因此特别怜爱、羡慕“双燕”、“双飞燕”。它们比翼齐飞,恩恩爱爱,在桃红柳绿的春天,衔花筑巢,是何等惬意幸福。这不正是作者梦寐以求的夫妻生活之写照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补旧巢”三字,分明蕴含着作者与丈夫亦能弥合其破裂家庭的企盼,亟想自己亦有个温暖的“巢”。只是这种期待的实现极其渺茫,作者只能“寄声”即表示一种祝愿而已。此外如《闻雁》写“秋高霜气重,孤雁最先鸣”之“孤雁”,适与“双燕”相对照,是作者的影子,正因为深知“孤雁”“只影”之凄冷寂寞,才羡慕春燕之“双飞”。可惜至死袁机仍是一只“孤雁”,令人可怜。
由于袁机存诗皆婚后归宁之作,难以全面显示其成绩。但可见其诗抒写真性情,并有个性特点,喜用比兴,温柔含蓄。由于苦难深重,心情忧郁,故不具性灵诗常见的灵活风趣特征。
综观袁家三妹的诗作,可以说皆抒发真情实感,但具有不同的艺术个性,堪称“独抒性灵”(20)。三人皆自幼读书,腹有才学,但却不掉书袋,基本上以白描取胜。抒情多凭借写景,不脱离时空环境直摅胸臆,而是透过景象的映衬予以形象化,使感情形象鲜活有致,又含蓄蕴藉。语言平浅易懂,常采用拟人、比喻的修辞方法,增加诗之生趣。风格以阴柔为主,但亦不乏袁棠的阳刚之美。整体上看,袁家三妹与袁枚女弟子创作上是相近的。这些性灵派的女性诗人皆以其性灵诗清新的诗风冲击了诗坛格调诗的拟古形式主义以及肌理诗的以学问考据为诗的习气,其诗作自身思想意义的深浅却是次要的。她们为使诗歌之回归抒写真情的正途是作出了相当贡献的,在中国妇女文学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
注释:
①详参拙文:《随园“闺中三大知己”论略》,《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大家之女与贫者之妇》,《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扫眉才子两琼枝》,《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5期。
②详参拙文《论袁氏家族男性诗人之功过》,《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③《随园诗话补遗》卷一。
④袁枚于《随园诗话》卷十记云:“三妹皆能诗,不愧孝绰门风;而皆多坎坷,少福泽。余已刻《三妹合稿》行世矣,兹又抄三人佳句,以广流传。”《三妹合稿》全称《袁家三妹合稿》,收堂四妹袁棠《绣馀吟稿》一卷、《盈书阁遗稿》一卷,四妹袁杼《楼居小草》一卷,三妹袁机《素文女子遗稿》一卷。《三妹合稿》由袁枚编定而付梓,为随园自刻本,成书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之后一段时间。“袁家三妹”之诗作能流传至今,全赖其兄袁枚编辑、刻印之功。今《袁家三妹合稿》收拙编校点本《袁枚全集》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⑤⑥袁枚《女弟〈盈书阁遗稿〉序》。
⑦《〈盈书阁遗稿〉跋》。
⑧《随园诗话》卷一。
⑨《秋夜坐月有感》二首其二。
⑩严长明《题辞》。
(11)《咏怀》。
(12)《老母生日病中口占》。
(13)《病危作》。
(14)《随园诗话》卷八。
(15)陆机《文赋》。
(16)袁枚《〈素文女子遗稿〉再跋》。
(17)《随园诗话》卷六。
(18)《挽陶姬》。
(19)《淮南子·缪称训》。
(20)《随园诗话补遗》卷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