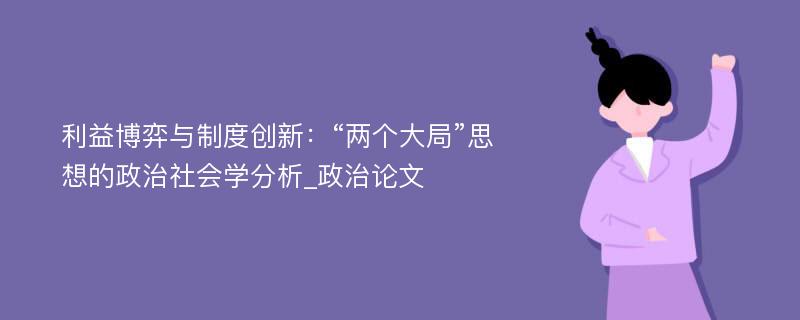
利益博弈与体制创新:“两个大局”思想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局论文,社会学论文,体制创新论文,利益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动力与发展:“两个大局”的涵义解读
社会发展的动力往往隐藏于人类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之中。利益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一定的物质利益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列宁曾经将人们的物质利益称之为“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1](P113)。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中最深层次的结构,利益的分化与重组构成了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因。所以,利益分析是把握社会系统结构、功能变化的一个关节点。任何一个社会,利益资源总是稀缺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布也总是有差别的,多元、分化、异质、不平衡是社会利益配置中的常态现象,它如同一个动力装置,带动社会的有机运转,造就社会的活力和效率,并使社会有机体呈现出开放性、动态性、流动性。就像河水,只有有落差,才有激荡的浪花;就像电流,只有有位差,才有强大的势能。
利益的分化、多元和差异是社会前进的原动力。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利益分化与重组的过程。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使社会利益关系呈现出新的形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几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和机会,利益结构是一种总和性结构,在这种结构下,人们的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利益单元之间是一种平均化、同质化的分布状态,由于没有利益的分化,也就没有利益的竞争,蕴藏于社会的活力资源得不到应有的开发、配置,整个社会就会死水一潭,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可以说,改革就是对这种高度统合的旧体制合法性危机的一种积极反应。分化、分权的改革,打破了旧的、僵化的利益结构。市场竞争机制的引人,也就意味着利益分化的开始。利益分化是新的利益关系形成的过程,利益分化表明新的利益差别的扩大,社会异质性因素的增加。利益分化唤醒了人们压抑多年的利益意识,利益意识又强化了人们对利益的诉求,对利益的渴望,促使人们在市场上表现自己,在自由、自主的选择中实现自己的利益价值。这样,整个社会焕发出特有的活力和生机,社会资源得到了空前的开发、盘活。
把利益的适度分化和差异作为推进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动力机制,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应有之意。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自觉地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市场机制的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说:“要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2](P111)并强调,在这个过程中,“内地要支持沿海,暂时无条件富的人要支持有条件富的人,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2](P111)。这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后发式现代化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推动发展,首先必须解决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这种动力从何而来?过去我们主要靠超强的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的革命话语的激励,这种动力开发方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可能长久地维持。由于物质决定精神,人们对利益的渴求,也许可以一时地压抑,但不可能永远地处于匮乏状态。从利益中寻找动力,从竞争中开发活力,这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经验。可以说,“两个大局”思想就是对这种基本经验的有力回应。
一个成熟、稳定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有分化而无悬殊的社会。利益竞争带来了利益的分化,利益分化造就了社会的活力和效率,这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市场永远追求的是效率,它不可能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然而,没有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的,最终将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正如英国社会学家汤因比所说:“没有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个人自由是人类做出成就(无论是善的或是恶的)所必要的条件,而社会正义是主宰人类相互关系的准则。放任个人自由,则强者横行,弱者向隅。没有自由,人的本性就不能有创造性;但对个人自由不加压抑,则社会正义就不能彻底实现。”[3](P414)如果利益分化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如果先富起来的群体、阶层不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果利益受损者的利益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福利不能得到相应的增进,那么,必然会带来社会有机体的断裂,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对此,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同时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的发展,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4](P278)由此可见,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另一层深刻涵义就是必须实现多元利益的协调与整合,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整合、凝聚多元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靠市场的力量无法完成,这就自然地落在了政府的肩膀上。所以,现代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应建立在对社会多元利益的有效整合、调控上,政府的有效性,归根到底体现在它对多元利益的整合能力、特别是对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怀能力上。因此,利益平衡、利益整合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分化与断裂:“两个大局”实现进程中面临的新挑战
利益实现要求的自我性与利益实现途径的社会性矛盾,决定了人们的利益需求只有在社会互动、利益博弈中才能实现。利益博弈有“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之分。所谓零和博弈,就是利益的不对称发展,一方得到的,正是另一方失去的,呈现出“赢者通吃”的格局。所谓“非零和博弈”,就是利益互动中主体之间的利益分享与共享、利益双赢或多赢的局面。一方面,“两个大局”是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源;另一方面,经济市场化的改革也带来了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两个大局”在实现进程中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P92)。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进程,实际上就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端于旧体制边缘的、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空前的资源扩散、财富增长的“平等化效应”。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成为改革的最早收益者。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基层社会也出现了自由活动的空间和自由流动的资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呈现出空前的创新活力。可以说,80年代是一个共同富裕的时代,改革增进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群体的福利,这个阶段的改革可以说是一种利益的“非零和博弈”。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与体制双重转型的推进,利益急剧分化、资源加速积聚的态势日益明显,改革越来越呈现出“零和博弈”的格局。这表现在:一方面,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上出现了暴富阶层。新崛起的资本集团、权力集团和知识集团成为社会的强势利益群体,并日益出现利益结盟化的趋向。另一方面,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一个由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失业者所构成的底层社会正在形成。底层社会的形成,表明中国社会日益出现两极化的态势。原来中国社会的贫困者群体主要在农村,虽然人们知道有贫困农民的存在,但毕竟处于体制的外围,离社会中心较远,而现在作为社会中心的城市本身出现了一个比较庞大的贫困者群体,格外引人注目。如果说80年代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向好的方向转化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来,底层社会出现了绝对贫困的现象。
从目前来看,中国底层社会的构成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贫困的农民。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体制改革的能量基本上释放完毕,农民收入增长的幅度开始明显放慢。90年代,乡镇企业不断暴露出发展的局限性,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农村、农业、农民呈现出日益衰败化、边缘化的迹象。据专家推定,在90年代中期,粮食价格下降30%多。同时,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一方面是农民收入的下降,一方面是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据统计,1978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2.4∶1,到1983年缩小到1.7∶1,但到1997年迅速扩大到2.5∶1,2000年为2.79∶1。种种迹象表明,农业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赢利的产业,甚至越来越不能成为一个产业,而成为农民自我消费、自我维持生存的一种自然经济活动。[6]二是农民工群体。农民工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一个底层群体。从90年代初期开始,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到目前为止,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工达到1.5亿的规模。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工一开始就是以不平等的身份进入城市的,在制度上他们不是城市中的一员,农民工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三是城市中下岗失业者为主的贫困者群体。城镇中的核心与边缘的新二元利益结构日益明显,出现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1996-2000年期间,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增长率分别为1.2%和1.6%,而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增长率分别为9.7%和9.3%。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由1996年的4.12倍和2.98倍迅速扩大为2000年的5.70倍和3.99倍。若按照过去4年的增长趋势,5年以后,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扩大为8.33倍和5.74倍。
现代化意味着分化,现代社会必然是一个多元化、异质性的社会。在多元的社会结构中,不同的利益群体相互承认各自利益的合法性、正当性,尤其是对少数群体利益的承认、尊重和保护;多元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压力释放机制,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提供了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途径;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互包容、和谐共处。中国底层社会的出现和利益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平衡的现实表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日益表现出一个断裂社会的特点。断裂社会从表面上看好像也是一个多元社会,存在着差异性、多样性,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分化深刻,社会各种力量并存,多元价值观分立。但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上处于同一时代,他们相对独立又互相依存、不可分割,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种如杜尔克姆所说的“有机的团结”。而断裂社会的各个部分几乎处于不同的时代,既有农业文明的陈迹,又有工业文明的课题,还面临信息文明的挑战,三大文明呈现错位效应,他们之间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断裂社会是一个不稳定社会。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于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不同的社会成分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而政府只能集中精力来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这样,很容易造成对社会某些群体利益要求的忽视,面对来自不同群体的相互矛盾的、又各有正当性要求的交叉压力,执政党必须具有超强的利益整合能力、平衡能力和凝聚能力,否则,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如何在制度创新中,实现多元利益之间的有效协调,推进“两个大局”的良性进程,是执政党在新世纪所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
三、整合与调控:在体制创新中推进“两个大局”的实现
市场永远解决不了利益的失衡问题,它总是按照效率的逻辑为自己开辟道路。只有政府才能有力量解决利益整合、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利益分布严重不平衡的现实,面对断裂社会中的多元交叉压力,执政党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通过价值整合、制度创新来协调各个阶层、群体的利益,为改革、发展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首先,建立政治文化的凝聚机制,提升政治系统的亲和力、向心力。
任何一个政治系统都离不开价值理念的支撑。政治系统必须努力塑造、整合公民的价值和信仰,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同与忠诚,实现政治秩序的长久维持。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认为:“只有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拥有一套核心价值和信仰,才能实现道德上的统一。如果没有这种道德上的统一,任何制度都迟早会堕落下去。”[7](P134)利益决定立场,有什么样的利益诉求,就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必然引起价值观的多样化,价值观的多元化必然给政治文化的社会认同带来新挑战。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发掘新的社会认同的生长点,为改革、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实践证明,政治系统只有在多元价值取向的交汇点上,建立主流政治文化的凝聚机制,才能有效整合多元利益,实现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说:“正义是任何社会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任何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8](P1)社会公正、正义是任何一个政治系统获取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性资源。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正义是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粘合剂,确定什么是正义,是政治社会秩序的本原。”[9][P8]
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地解决社会公正、实现社会稳定。不公正、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也许能带来暂时的经济繁荣,并制造出一种盛世的景象,但这种盛世绝不意味着太平。如果社会所有的阶层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共同成果、达到帕累托最优,而是一部分人或群体享受增长的“红利”,而大多数人承受改革的代价,那么,这种增长所造就的秩序是脆弱的秩序,最终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人类创造国家和政府是因为它代表着社会的公共利益,超越了各个特殊利益,能够运用公共权力来缓和“冲突”并把它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所以,提供社会公正和正义等公共产品的任务就内在地落在政府的头上,实现社会公正,避免社会利益分化的过度悬殊就成了一个现代政府的核心责任。
当代中国,实现社会公正,关键体现在对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利益关怀上。“五个统筹”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执政党协调社会利益、实现社会公正的重大举措。它不仅是一种公正的价值追求,更重要的是一种体制、机制的创新。如在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支持力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加快西部大开发进程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创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为贯彻“两个大局”的思想、在利益协调中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坚强决心。
其次,建立利益表达机制和压力释放机制,提升政治系统的吸纳力、糅合力。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任何一个政治系统都是一个由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等环节组成的有机体系。社会成员的利益表达、意见、要求是政治系统有序运行的信息和“原料”[10](P24)。畅通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不但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发泄不满、诉说委屈、交流感受、释放压力的空间,同时也为政治系统实现有序的政治输入提供了“原材料”。一个政治系统只有具备充分的吸纳能力、包容能力,才能有效整合、凝聚社会利益,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因此,一个有生命力的政治系统必然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政治系统,这是任何一个政府政治合法性的源泉。“政治合法性就是政治系统能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的信仰的能力。”[12](P56)
如果说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认可和忠诚,那么这种认可与忠诚的源头就是社会成员对自身利益的满足感、满意感。随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人们温饱问题的基本满足,安全需要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需要。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温饱需要满足之后,就是安全需要,特别是利益安全。没有安全感,就不满意,不满意就会产生挫折感、沮丧感。如果不满情绪不能通过体制内的表达得以释放,就可能导致矛盾的积累,当矛盾的积累能量超过所承受的临界值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爆炸式爆发,形成对政治系统的破坏性冲击。实践证明,当人们合法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制度化的表达的时候,必然求助于非制度化的手段,从而造成政治系统的超负荷压力,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
社会心态是社会政治稳定的晴雨表和衡量社会治理水平的温度计,政治稳定的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因此,了解人心、了解民意是政府“善治”的基础。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的J型曲线理论认为,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心态,当社会实际满足水平低于人们的需要期望时,人们便产生一种期望挫折感或相对剥夺感,进而滋生对社会的不满,政治稳定与否,取决于人们期望与社会满足之间的差距。“经济发展加剧了经济不平等,而社会动员又降低了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加在一起,导致的政治不稳定。”[13](P6)建立社会成员的利益表达机制,拓展利益表达空间,完善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机制、压力释放机制,是当代中国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课题。当前,除了完善传统的信访渠道外,还必须拓展制度创新的空间,开设政府首脑热线电话、电子信箱、首长接待日等多元渠道,使人民群众的声音、意见和要求,真正能够通过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整合到政治系统中去。只有这样,“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才能转换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再次,遏制累积性不平等,调控流动性不平等,提升政治系统的公信力、凝聚力。
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从不平等中找到动荡的根源。”[14](P205)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听任不平等的滋长或蔓延,必然导致社会认同的消解和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不平等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社会资源、机会等价值分配的差异问题。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的需要的无限性的矛盾,决定了平等永远是一个相对的历史范畴。问题并不在于消除不平等,而在于人们不能忍受的是以不公正的方法有意制造不平等。“平等不过是个理念,是理想目标,但平等问题关系到权力、权威的分配方法。不仅如此,它还关系到财富、威信等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平等是关于权力、权威的政治现象。[15](P2)因此,在对待不平等的问题上,一个关键的前提是,必须搞清楚究竟是积累性不平等还是流动性不平等的问题。积累性不平等是以门第、身份、血统、出身、特权等先赋元素来决定价值资源的分配结构。它的核心原则就是世袭性,一切都是由先天的因素安排好的,贫困只能滋生着贫困,富贵不断延续着富贵。由于缺乏制度化的社会流动机制和精英再生产机制,社会成员本人后天的努力和能力锻造,与自身的命运变迁几乎不存在任何正相关性,它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不平等的制度化累积。因此,这种累积性不平等是一种扭曲的、畸形的不平等。流动型的不平等前提是机会的平等、规则的非歧视性,它强调个人的将来由其自身的努力及能力决定,不受与其本人意志无关的门第、性别、身份、权力等背景因素的制约,即由程序化的公平竞争来决定人的命运走向。流动性的不平等承认机会永远是开放的、流动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精英,同时也可能成为被淘汰者。从累积性不平等走向流动性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历史进步,因为它第一次驱除了世袭原理和身份社会的正当性,确立了业绩社会、法理社会、契约社会的合法性地位。
中国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从累积性不平等不断走向流动性不平等的社会。在当代中国,如果说市场机制是产生流动性不平等的源头的话,那么,滋生累积性不平等的土壤就是非市场化、泛市场的交织与泛滥。一些人或组织利用新旧体制转型中的漏洞而大肆进行走私、偷税漏税、资源垄断、侵吞国有资产、市场欺诈、不公平竞争等非市场化手段而成为暴富群体;一些腐败的政府官员利用公共权力大搞“寻租”活动,用资本化的权力迅速实现了自己的财富积累,加入暴富者的行列。累积性的不平等是挑战中国政治合法性、威胁社会政治稳定的核心因素。因此,推进“两个大局”进程,一个紧迫的课题就是打击非法收入,遏制累积性不平等的泛滥,铲除滋生累积性不平等的土壤。这就要求执政党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快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进程。对由规范化、程序化的市场竞争而导致的流动性不平等,政府必须深化社会保障体系、分配体系的改革,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财政转移支付、对高收入群体征收所得税、累进税等手段,调节过高收入,平衡利益分配关系。
改革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对利益受损阶层、群体进行利益补偿,是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当代中国,政府整合、调控利益关系的重心应放在对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关怀上,使他们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诚然,共享并不意味着各个阶层在整个改革发展中都享受到同样的份额。事实上,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同,他们享受到的成果在时间上有先后,份额上有大小。但是,共享应该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和福利都能有所增进,达到“帕累托改进”。如果某个阶层的利益在某一时段受到损失,那么,就要适时地进行合理的补偿,从而达到“卡尔多改进”,不能有哪个阶层长期地成为单纯的利益受损者。必须防止国家在协调社会利益方面软弱无力,听任利益矛盾激化而束手无策。同时,防止偏袒某些阶层的利益,使社会利益矛盾不仅得不到妥善处理,相反冲突加剧。因此,要协调利益,党和政府必须站在社会公正的立场上,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起到驾驭矛盾、总揽全局、兼顾各方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