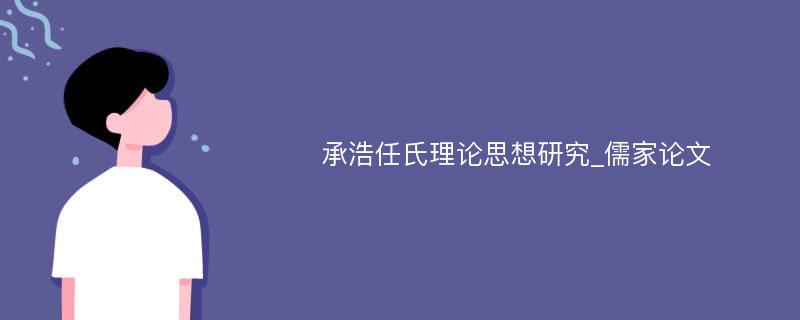
程颢仁说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程颢仁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程颢,字伯淳,称明道先生,生于北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一○三二年),死于北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一○八五年)。其弟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称赞程颢:“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①在《明道先生墓表》中又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②在程颐的这两篇文中,盛赞明道得不传之“圣人之学”于孟子死后之千四百年。孔孟所开创的儒学,其精髓是仁学。明道继承孔孟的仁学传统,提出了自己的新仁学,成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学者一般认为,“理”在程颢的思想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此固然不错。但是,更进一步说,“仁”才是程颢思想的核心,黄宗羲在《宋元学案·明道学案》中就明确地说:“宗羲案:明道之学,以识仁为主”,③从“仁”来理解程颢的思想,或许更贴近其思想的实质。《宋朝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二载:“先生每见上,必言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④ 宋神宗元丰二年己未(公元一○七九年),程颢四十八岁时,弟子蓝田吕大临东见程颢,记有《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其中有后人称为《识仁篇》的语录,其全文如下: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一本下更有“未有之”三字)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以昔日习心未除,却须存习此心,久则可夺旧习。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也。⑤ 《识仁篇》是北宋最著名的仁说文献,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开启了此后从二程到朱子关于仁说众多而热烈的辩论,成为当时儒学界主要话语。下面我们便仔细地释论程颢的《识仁篇》,以阐明程颢的仁说思想。 一、学者须先识仁 程颢《识仁篇》开篇就说“学者须先识仁”,这也说明程颢认为“识仁”在其仁说思想中具有首要的地位。《识仁篇》中所谓的“识”,不是认识论所说的“知识”,而是一种体悟、觉解、默会、感通,是中国哲学德性修养的基本方法。在程颢看来,宇宙万物的生生之意、春意、感通意最可以“识仁”“观仁”: 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⑥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⑦ 观鸡雏。(此可观仁。)⑧ 仁便是一个木气象,恻隐之心便是一个生物春底气象。⑨ 从万物的生意、春意、生长畅茂中,最可以体贴出“仁”意,这是程颢的一种点化语,要在人默而识之,从中体会“仁”的深意。程颢以生意观仁的思想,主要是受《易传》的影响。《易传》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传》),生就是天地大德,又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卦·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坤卦·彖传》),在《周易》中,乾、坤两卦分别指象天、地,而“资始”、“资生”便是天地生生之大德。对生的强调可谓是中国哲学的重要传统,但是《周易》却没有把天地生生大德与“仁”联系起来,程颢则明确用万物的生意、春意来指点仁,是儒家仁学思想的重要发展。 程颢仁说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从感通来指点“仁”。以生意观仁可以说是从肯定的方面来体贴仁;从感通的角度来识仁,则是从否定的方面,作为个体人的生命之一体贯通来默契仁: 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⑩ 医家言四体不仁,最能体仁之名也。(11) 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痒,谓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犹是也。盖不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也。(12) 仁的其中之一个重要含义是一种当人面对同胞或宇宙万物处于苦难、不幸情境时,自然从心中流出的一种恻隐之心,不安、不忍之心。人之所以会有这种恻隐之心,是因为人与万物的息息相通、相感,而不仁则是一种漠视、硬心肠、麻木。程颢认为人的这种不仁的状态,最可以从“医家言四体不仁”中体解出来。因为若“四体不仁”,则“不知觉”、“不识痛痒”,是一种病态。程颢借医家的说法来体仁,应该说是非常生动的,人人皆可一语而悟,与孟子“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一样,皆活生生的。这说明程颢对仁有很深的体悟,故能随机而化、随缘而点。另一方面,也说明,程颢对医学知识具有很深的涵养。程颢的这种思想主要源自《黄帝内经·素问》:“帝曰:‘……痹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热,或燥、或湿,其故何也?’歧伯曰:‘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荣卫之行濇,经络时踪,故不通。’”程颢认为人生来就禀赋有仁心、仁德,人只要“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就是“仁”。天地的生生之仁和人的感通之仁是一脉相承的,人的感通之仁是天地生生之仁的贯注,因为人和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体感通的。 二、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程颢在《识仁篇》紧接着“学者须先识仁”后,便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者”是一种具有仁德之人,而他的境界达到了“浑然与物同体”的天地境界。冯友兰先生说:“‘浑然与物同体’,这是程颢对于宇宙、人生的理解。他认为,万物本来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有着休戚相关的内部联系。他认为,学道学要首先明白这个道理。但道学并不是一种知识,所以仅仅‘识得此理’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实在达到这种境界,要真实感觉到自己与物同体。”(13)冯先生此语甚是。程颢认为天人是一体的,天地就是一个大身体,从万物的春意、生意中最可观解天地之仁;而四体痿痹不仁,最可以从反面说明不仁的一种状态。程颢说:“道,一本也。”(14)“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15)“须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16)程颢所说的一本,就是天人同一根本、根源,天人原本就是息息相通的同一整体,如同人之身体一样,自然感通,痛痒相知。所以程颢又说: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17) “刚毅木讷”,质之近乎仁也;“力行”,学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曷尝支离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贡以为仁之方也。医书有以手足风顽谓之四体不仁,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与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无恩者,其自弃亦若是而已。(18)程颢认为,仁者把天地万物看作是一体的,无不是自己的一部分。仁者有这样的觉解,就会把万物看成与自己是息息相关的。否则,就像医书所说的手足痿痹不仁时,由于气已不贯,本来是自己的手足,也痛痒不关,就跟不属于自己的一样。在《论语·雍也》篇中,“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程颢同意孔子的观点,认为“‘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因为仁很难形容,所以孔子能近取譬,给子贡指点仁之方。程颢认为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陈来先生认为,先秦儒家的仁学强调博施济众的人道主义,“在程颢看来,这样的仁学还不是‘仁’的最高境界。他认为,博施济众只是仁的‘用’(表现),还不是仁的‘体’(根本)。仁在根本上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与万物为一体’‘浑然与万物同体’。程颢的这个思想与周敦颐提出孔颜乐处一样,都是突出儒家思想中对于最高精神境界的追求。”(19)程颢也说:“‘博施济众’,云‘必也圣乎’者,非谓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济众’者乃功用也”,(20)“语仁而曰‘可谓仁之方也已’者,何也?盖若便以为仁,则反使不识仁,只以所言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则使自得之以为仁也。”(21)陈来先生此解可谓得程颢之意。 程颢“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仁说,继承了先秦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程颢的发展在于把天人合一、浑然与物同体,与“仁”联系起来,认为是仁者的一种最高境界。程颢的这种思想,也受到了张载《西铭》的影响,《识仁篇》中,程颢就说“《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22)《订顽》即是《西铭》,“备言此体”的“体”指的是“仁之体”。张载在《西铭》中提出了一种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的天地境界,但是张载在《西铭》中,还没有直接指出这种把天地万物看成与自己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境界,就是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这是程颢与张载不一样的地方。程颢说:“《西铭》某得此意,只是须得佗子厚有如此笔力,佗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且教佗人读书,要之仁孝之理备于此,须臾而不于此,则便不仁不孝也。”程颢对张载的《西铭》推崇备至,认为孟子之后,无人能达此仁者境界。同时,认为仁孝之理备于《西铭》。不过,程颢说话浑沦、圆融,他又说:“《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学者其体此意,令有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别有见处,不可穷高极远,恐于道无补也。”(23)程颢在此提醒学者,不可穷高极远,因为这样于道无补。这也说明在程颢极力称赞张载《西铭》“意极完备,乃仁之体”的同时,也指出其中不足之处在于,只提示学者最高的仁者境界,且未言如何达到此境界,即没有提示学者识仁、观仁的功夫,而这是程颢认为学者必须首先解决的,所以程颢说“学者须先识仁”。 三、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 上面我们讨论了程颢如何指点学者识仁、观仁,以及仁者所达到的“浑然与物同体”、“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者境界。但是,仁者与万物同体的最终根据是什么?在《识仁篇》中虽未提及,但是程颢在其他地方则明确指出:“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 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24)程颢引用《易·系辞下》“生生之谓易”,认为宇宙乃一生之大流,易就是宇宙变化流行的总体。宇宙万物在生成的同时,都同时禀赋有理,这理就是所以万物一体的最终根据。程颢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25)程颢认为,宇宙万物的生成是一个“无声无臭”的自然过程,没有所谓人格神的主宰者,其流行变易的总体、统体就是易,其所以变易流行的根据、原理就是道,其流行变化的奇妙作用、神秘莫测就是神,天所命予、赋予人的就是性,人按照天性行事就是人道,修养、陶冶这种人道就是教化。朱子在解释程颢上段话时,说“体,是体质之体,犹言骨子也。易者,阴阳错综,交换代易之谓,如寒暑昼夜,阖辟往来。天地之间,阴阳交错,而实理流行,盖与道为体也。寒暑昼夜,阖辟往来,而实理于是流行其间,非此则实理无所顿放。犹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实理寓焉。故曰‘其体则谓之易’,言易为此理之体质也。”(26)朱子的说法是比较正确的,在此处,易不是指形而上的本体,而是形而下的气化流行的总体、体质。(27) 程颢说:“天者理也”,(28)又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29)这说明程颢认为天理或理在其学说体系、个人修养工夫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黄宗羲之子黄百家说:“百家谨案:《乐记》已有灭天理而穷人欲之语,至先生始发越大明于天下。盖吾儒之与佛氏异者,全在此二字。吾儒之学,一本乎天理。而佛氏以理为障,最恶天理。先生少时亦曾出入老、释者几十年,不为所染,卒能发明孔、孟正学于千四百年无传之后者,则以‘天理’二字立其宗也。”(30)“以‘天理’二字立其宗”,说明了“天理”在程颢思想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程颢当然知道“天理”二字并不是其首先提出来的,因为在《礼记·乐记第十九》中便有:“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礼记》虽拈出了“天理”的思想,但是还限于人生心性修养论的层面。而程颢的突出贡献是认为“天理”是贯通天人的所以根据、原理,并与其仁说联系起来,这“理”就是形而上的道: 《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31)在这里,程颢明确提出阴阳也是形而下者,而道则是形而上者,是所以一阴一阳的根据和原理,程颢这里所谓的道,也就是其所说的理或天理。因为理是形而上的,所以紧要在人“默而识之”,它不能仅仅通过闻见而得。程颢据此批评张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一作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32)程颢批评张载所说的“清虚一大”乃是气,属于形而下的器的层面,不能和形而上的道的层面相混淆。 二程认为理是形而上的,它没有时空的限制,亘古常存,与人事的善恶无关:“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佗元无少欠,百理具备。”(33)天理没有穷已,亘古亘今都在起作用,不为尧善而存,不为桀恶而亡。人只要体贴出此天理,就能大行不加、穷居不损,因为人人都生而完具此天理,无少欠缺。所以程颢又说:“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34)“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35)这说明程颢充分认识到了理的客观性、普遍性、超越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善恶和社会的好坏为转移。所以又说:“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则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颠沛造次必于是。’又言‘吾死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难名状。”(36) 程颢体贴出天理,认为它是万物变易的所以根据,区分形上、形下,并认为理是仁者与万物为一体的所以原理,这是他的突出贡献。但是程颢还没有用下定义的方式明确把仁和理联系起来,虽然程颢已有“仁孝之理”的说法。 四、义礼智信皆仁 宋明儒者不但强调对最高境界的体悟与觉解,更重视仁者境界在人伦事务中的践履与发用,在日常事务中体现仁,而不是把仁作为一个空洞的教条。所以程颢在《识仁篇》中接着“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便说:“义、礼、智、信皆仁也。”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五常,作为个人修身的道德法则、规范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二程说: 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仁,体也。义,宜也。礼,别也。智,知也。信,实也。(37)仁义礼智信是天赋予人的本性,天然完具,自然而有。用人来做比喻,仁是人身的全体,而义礼智信是四肢。仁既是全德,也是义礼智信的本体,义礼智信都是仁在各方面的表现,如义是仁之合宜的表现,礼是仁之别异的表现,智是仁之觉知的表现,信则是仁之诚实的表现。这里,隐约有仁为体,而义礼智信为用的思想。在下面的一条语录中,二程明确提出了仁体义用的思想: 仲尼言仁,未尝兼义,独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孟子言仁必以义配。盖仁者体也,义者用也,知义之为用而不外焉者,可与语道矣。世之所论于义者多外之,不然则混而无别,非知仁义之说者也。(38)二程认为,孔子多言仁,但未仁义兼说,即没有把仁义联系起来,而孟子则仁义并举,如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其实孟子不但仁义并举,而且把仁义礼智作为人的四种最基本的德性,认为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之心,而且仁义礼智根于心。不同之处在于,二程认为仁是全体,义礼智信则是仁之分殊的表现。所以程颐又说: 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39)程颐认为,天道元亨利贞四德中的元,犹如仁义礼智信五常中的仁。如果单说,则仁和元只是一德,如果兼说,则仁包括仁义礼智四德,为全德之称、众德之摄。 程颢不但强调一本、一体,同时又强调义礼智信皆仁,这是其思想圆融的表现。后来的程颐、杨时、李侗、朱子等都非常强调理一分殊,可以说和程颢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不过,程颢的思想还是偏于强调一本、同体、理一、浑然,对分殊的强调还是不够的。因为程颢的思想主要还是一种道德伦理的思想,在道德的修养中,强调一本、贯通、圆融,这是道德修养的特点所致。而程颐、朱子的思想体系中,在强调德性修养的同时,其思想学说融入了较多知识论的成分,要格事事物物之理,必须强调分殊。道德论和知识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知识论强调分析、即物穷理,而道德论则强调圆融、反身省察,二者不能混同。 五、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 程颢在《识仁篇》中接着说:“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所谓“识得此理”中的“此理”,当是作为仁者所以浑然与物同体的根据的天理,“以诚敬存之”中的“之”,也应是“天理”。因此,可以说程颢在仁者通过识仁的功夫,认识到仁者所以浑然与物同体的根据是天理后,剩下的只是“诚敬”的“存理”功夫。在先秦,《中庸》特别强调了“诚”在宇宙、人生中地位,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又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认为有“诚”、“诚之”,“自诚明”与“自明诚”两种修养功夫,认为“诚者”是天之道,是一种“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功夫,率性而行,便是天道的流行和表现,这也就是孟子所谓“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的功夫,《孟子·离娄下》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程颢也认为仁者“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如果“诚敬”存理的功夫发生了松懈,则需有防检;天理未得,才需要穷索。仁者已经体贴出“天理”,只需存久自明,不待穷索。程颢认为“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一本下更有未有之三字)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也就是说“识仁”是仁者体悟、觉解仁道、仁理的手段,“浑然与万物同体”是仁者“识仁”之后所具有的一种境界,“天理”是仁者所以浑然与物同体的根据、原理,“义礼智信皆仁”是仁之全德在日用伦常之中分殊的表现,而“诚敬”则是仁者存养仁理的一种功夫,五者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义理栽培。如求经义,皆栽培之意。”(40)也就是诚敬存理的功夫。又说:“诚者合内外之道,不诚无物。”(41)又说:“‘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则无间断,体物而不可遗者,诚敬而已矣,不诚则无物也。《诗》曰:‘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纯亦不已’,纯则无间断。”(42)程颢认为人应该无间断地以诚敬之心事天,就像文王一样,天赋命不已,人也应以此诚敬的心态来体物,这样,自己的德行也就能“‘纯亦不已’,纯则无间断。”诚敬是一种对越在天的一种心境,“‘忠信所以进德’,‘终日乾乾’,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可谓尽矣。(一作性。)故说‘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诚之不可掩如此夫’。彻上彻下,不过如此。”(43)也就是诚敬是一种终日对越在天,彻上彻下的存仁功夫,不可稍有间断。就像天道一样,无声无臭,变易不息,孟子所说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功夫也就是诚敬的功夫。又说:“‘毋不敬’,可以对越上帝。”(44)程颢认为仁道与物无对,人只要做诚敬存养功夫,便能“只心便是天”(45),“大而化,则已与理一,一则(一无此字。)无已。”(46)“纯于敬,则己与理一,无可克者,无可复者。”(47)也就是仁者实现了天道与人道、心与理的合一,达到了合一便无可克、无可复,而且没有间断。程颢认为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反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的浑然与物同体的一种天地境界,拥有此种境界的人,心中便能自然生发出大乐。如果反身未诚,则己与物有对,有边界、隔阂,以己合彼,则不能实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乐也无从生发了。张载的《西铭》同样体悟到了此仁体,觉解到了浑然与物同体的仁者境界,但是却未言“诚敬”的存养功夫,这是不够的,即有本体而无功夫,学者不知道此仁体、境界是从哪里来的,也容易丧失。 六、明道气象 儒家向来不但注重仁者境界的觉解,而且注重行仁、修仁、为仁的日用功夫。因此,不能仅注重其仁说,同样要善观其气象。盖气象是一个人修为达到一定境界后,在身体和言行上所自然呈现的一种表征、一种气息。《大学》说“德润身,心广体胖”,即人的德性的修养会对身体有一种滋润、浸润的作用。《孟子·尽心上》也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啐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也就是说人的德性,都根源于人心,人心的存养达到了一定境界、程度之后,必然会在人的外部身体上表现出来,所谓啐目盎背就是这个意思。 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 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48) 程颐可谓善观人之德性与气象者,这也表明,程颐晚年之修养与境界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颜子言孔子,孟子言尧、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见如是。”(49)伊川之言,可谓有德之言。“纯粹如精金”,按宋明理学家来说,即是天理流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的一种修养与境界。如王阳明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50)“温润如良玉”,则是说程颢待人接物温润、和泽;“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则是说其人能从容中道,虽宽却不失节制,虽温和却不流荡;“忠诚贯于金石”,即是程颢《识仁篇》所说的一种“诚敬”的功夫,“孝悌如神明”,亦如“纯亦不已”地“对越上帝”的诚敬态度;“春阳之温”、“时雨之润”,则犹如天地生物的气象;“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则是“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万物皆备于我”的宇宙胸怀和天地境界。“侯仲良曰:‘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州,逾月而归,告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51)《宋元学案》亦载:“游定夫访龟山,龟山曰:‘公适从何来?’定夫曰:‘某在春风和气中坐三月而来。’问其所之,乃自明道处来也。”(52) 程颢说:“人必有仁义之心,然后仁与义之气睟然达于外”(53),可谓有德之言乎。 注释: ①《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第638页。 ②同上,第640页。 ③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542页。 ④《宋朝名臣言行录外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98页。 ⑤《二程集》,第16-17页。 ⑥同上,第120页。 ⑦同上,第60页。 ⑧同上,第60页。 ⑨同上,第54页。 ⑩同上,第33页。 (11)同上,第120页。 (12)同上,第366-367页。 (1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4)《二程集》,第117页。 (15)同上,第81页。未注明谁语。《宋元学案》认为是明道语,其文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若不一本,则安得先天而天无违,后天而奉天时?” (16)同上,第59页。 (17)同上,第15页。 (18)《二程集》,第74页。 (19)陈来,《宋明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90-91页。 (20)《二程集》,第15页。 (21)同上,第4页。 (22)同上,第17页。 (23)同上,第15页。 (24)《二程集》,第33页。 (25)同上,第4页。 (26)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7册,第3186-3187页。 (27)牟宗三先认为“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此中其体、其理、其用,皆指“上天之载”本身说,即皆指无声无臭、生物不测之天道本身来说,是故易、道、神,亦是此天道本身之种种名,所指皆一实体也。此无声无臭之帝、天、天道、天命,既转为道德的、形而上的创生实体,寂感真几(creative reality,creative feeling),则就易之穷神知化以明天道言,此天道之“体”即是易。牟先生认为易、道、神“所指皆一实体”的说法值得商榷。另认为其都是“道德的、形而上的创生实体”,也值得商榷。这更应该看作是牟先生的自己的哲学创发。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二册,第26页。至于程颢在其余地方论“易”时是否有形而上的意味,则须就具体的文本具体进行分析。 (28)《二程集》,第132页。 (29)同上,第424页。 (30)《宋元学案》,第569页。 (31)《二程集》,第118页。 (32)同上,第118页。 (33)《二程集》,第31页。未注明谁语。 (34)同上,第4页。 (35)同上,第30页。 (36)《二程集》,第38页。 (37)同上,第14页。 (38)同上,第74页。未知谁语。 (39)同上,第699页。 (40)《二程集》,第15页。 (41)同上,第9页。 (42)同上,第118页。 (43)同上,第4页。 (44)同上,第118页。 (45)同上,第15页。 (46)同上,第135页。此语在《遗书》卷三十五,伊川先生语一,入关语录,(或云明道先生语。) (47)同上,第1171页。 (48)《二程集》,第637页。 (49)同上,第21页。未知谁语。 (50)《阳明全书》,四库备要本,第46页。 (51)《二程集》,第346页。 (52)《宋元学案》,第578页。 (53)《二程集》,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