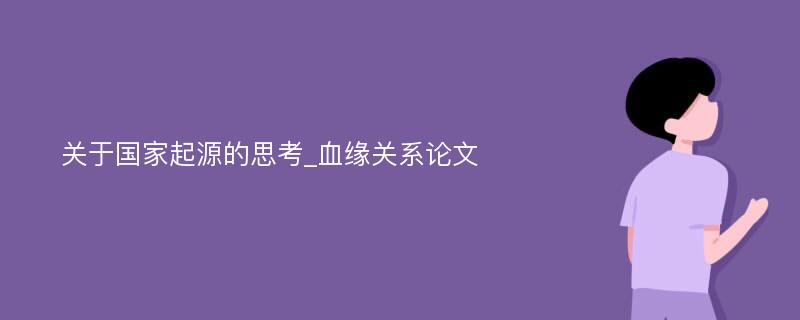
关于国家起源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是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结果和定式。在中国文字中,不管造字时是否带有象形或者会意的成份,单就简单意义和望文生义的效果来看,国家应该就是家之社会组织——国;或者是以国为形式的家。本文以为,家在任何意义和任何时代总是国的基本前提和范式,国是家的膨胀和扩大。从家中走出去的人亦如治家般治国。国的结构,尤其在封建制的国家,是以家庭血缘谱系为脉络而伸展的。因此,民主化的现代人发现了这一深层的谱系后,总想要摧毁它,以便使不同血缘关系的人能平等地在权力的张扬中都有所表现。即使如此,现代社会中的血缘关系仍是现代关系网络中最为可靠的基础,现代关系网络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比照。故此,本文旨在以家庭血缘关系的演变来探讨中国封建国家的起源。
一
首先,“家”是群的前提,群是“家”存活的最初载体。人类从与自然界的其他类分离始,就不得不以群的形式存在。即使这样,群绝不仅仅是单个人的类组合,其中的血缘依赖关系已先于其存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家庭血缘关系是不健全的。人与他类的初期区分绝不是以社会关系为异,人之初的人的关系仍是如同动物的子随母的方式。这就是说,初人的血缘关系只能是单亲血缘关系。
群是人类初期最早的“社会建制”,其功能是为了便于对付自然以求得人的共同生存。然而,群是一种游离和无核心凝聚的集体。即使人类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这种性质依然存在。根据考古资料,大约在距今10 000-8 000年左右,在我国长江以南地区的洞穴遗址中,就发现古人群聚中存在这种松散的结合。随着群生存条件的改善,群的扩大、重组和交往,人们必然会产生增强自身所在群体的凝聚力和固定性的要求。群向有核心的稳定的形态发展也就成为必然。
第二,氏族是家庭存活的第二载体。群的发展、重组,使同一血缘谱系之人聚居一起便形成了氏族。氏族组织的稳定促进了中国早期家庭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早期建立在家庭血缘关系之上的社会组织机构的发展。距今8 000-7 000年前是中国农耕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根据考古资料,我们发现了一批该阶段有价值的关于中国上古社会组织的发展遗迹。比如位于内蒙古东部敖汉旗的兴隆洼聚落遗址。据碳14测定,它在距今7 500-7 000年前。在这个遗址上,考古工作者发现有十一二排半地穴房,每排大约有十个左右。“这些房屋排列整齐,井然有序,显然是经过周密规划、精心设计,统一营造的聚落”。(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49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之后继续在该遗址上发掘,则呈现出更多可以反映聚落社会组织形态的遗址。所以王震中先生认为,这个时期“较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应该是,“若干个核心组成一个家族(即一排房屋),再由若干家族(若干排房屋)组成一个氏族,最后由一二个氏族构成聚落共同体”。(同上书,第49页。)
这种由血缘纽带形成的共同体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有血缘关系的人们肯定已经承认有一个权威的中心。这个权威就是有若干家庭共同形成的氏族组织机构。
构成氏族社会的成熟形态在距今7 000-6 000年前,现在已经发掘了许多该时代的文化遗址。我们从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看到这一社会构成的成熟形态:小家庭—大家庭—氏族(聚落共同体)。大家庭的出现是人类家庭形态的新的阶段,但必将导致氏族的瓦解。
氏族社会是高于群的社会组织,它具有向心凝聚力。这从聚落房屋的排列是向心分布可以得到启示。这一时期聚落房屋皆呈向心分布,有许多考古资料可以证明。这是人类特有的禀赋,这种向心分布既反映了当时人的某种先天观念,也反映出人类天生的依赖性:依赖父系或母系的长辈。它虽是人类的本能或天性,但它却促使了向心凝聚的产生。所以向心凝聚是人类发展到该阶段的必然要求。当然这种特性对人来讲是根深蒂固的,因为即使是今天的人们仍有这种依赖。
第三,家族居于实,氏族居于虚的时代。大家庭的繁荣促使家庭产生。家族的血缘谱系与氏族谱系相比是更为亲近的。大家族的同居共生并繁荣壮大,使氏族的权威有逐渐丧失的趋向。但是家族要代替氏族而成为家庭存活的新的载体,这仍要走很远的路。然而,大家族左右氏族使氏族管理出现软弱性和松散性,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家族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
因为原始平等和公正仍是人们衡量社会组织首领的标准,这就要求氏族仍必须以某种形式或某种权威存在。某大家族挟氏族而令诸小家族,也需氏族以某种方式存在。氏族未被大家族代替说明它仍有存在的必要,于是,被大家族左右的氏族出现了具有神圣权力的氏族图腾。图腾的出现,不管其有几种可以猜测的意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表明了人的自然权力的丧失。图腾是因维系氏族权威中心的要求而出现的,尤其是图腾崇拜的单一性说明图腾的效用是带有强制和集中统一性的。这也明显地反映了权力要求的萌芽。权威的虚设和权力的要求在这一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互补的。然而这种权威的虚设和权力的扩张的共生一直延续到国家形态出现之后,并成为国家政治斗争的核心内容。在这一时期,这种共生只表现在血缘关系的内容,但它在历史演进中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氏族社会是相对稳定的具有较长时段的社会形态,它的社会组织因有超人间力量的介入而显得不可突破和变化缓慢且平和。家族的血缘联系虽然在此时人的生存发展中起着实质性的作用,但氏族社会的权威性组织机构也因可以借助其权威而得以不断完善。在历史演进的形态上,氏族的权力谱系一般认为是由母系血缘关系发展到父系血缘关系,再到氏族的联盟。联盟的出现更是家族权力的权威象征,家族成为联盟的真实性基层单位,其真实性表现为生产、分配、交往等许多生活层面的具体方面。应该说,在联盟之前的父氏家族时代,已具备了国家组织的社会形态。
氏族联盟虽然产生新的权力,但其历史意义不在权力。联盟权威的主体是义务性的,是通过家庭式民主的意义表现出来,因为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庭管理方式已经定格为氏族联盟的管理形式。
第四,宗族是家庭存活的第三种载体。宗族是氏族组织关系鉴于个人或家庭关系的虚设性和管理的对象性而趋向的新的凝聚形态。因为人们在生存的安全和稳定意识上更向往贴近的亲缘关系。在由大家族控制的氏族权力的嬗变中,虽然德行和公正仍是权力和权威主体首要而必备的因素,但由此而萌生的宗族权力意识实属偶然,并不存在后人多方分析出的必然可能。本文以为孟子对禹启相承而一统天下的解释和分析是很有道理的。此后宗法国家的权力因袭是应该具有宗族意识的。
万章问孟子:有人说“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这回事吗?万章的这个问题透泄给后人的是,战国时期的人们已经不能明了禹启相承之事。但孟子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说:“否,不然也。……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孟子集注·万章上》)孟子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原始民本思想的角度,阐述了他对禹启相承之事的看法,实有一定的道理。
同时,我们从孟子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尧舜之时的宗族意识的外观。舜避尧子、禹避舜子而承位,为何?以历史哲学的角度看,此时由家族权力欲望而产生的宗族意识已成为氏族联盟中与氏族权威对抗的主要内容。对历史的发展演变来说,社会组织中固有的矛盾对抗的瓦解,必将产生新的对抗的统一体。
所以,启之后的时代,宗族意识便已经公开化、表面化,并进一步向前——向宗法制方向发展。人们在观念上臣服了权力的因袭,无奈地接受了宗族权力的沿传。我们虽然不能证实启已经意识到内外、亲疏之异,但是其子太康的继位是完全没有孟子所言的“天与之”所需的德行的。
以人类学的角度看,宗族在形式上只是若干个近亲家族的联合体,它并不以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为前提。但是本文以为宗族的形式可以起源较早,而且可以进一步发展下去。考古发现可以为此做出较好的证明。王震中先生分析了“龙山时代”的陕西临潼康家聚落的格局后认为,“在康家聚落后相互靠近或毗连的若干排排房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近亲家族式的同宗关系,每一近亲家族群可构成一宗族”,(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183页。)这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反映了人类聚居的社会形态或形式并不因面积的扩大和建筑格局的变化,而脱离其人群组织联系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脉络——血缘关系。
宗族权力意识经过夏代的发展,使它在组织形态上日趋完善并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宗族权力意识产生之后,社会组织的管理形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且其强权意志表现得更加明显,即国家形态的社会组织表现得愈为明显。首先是划分天下为“九洲”进行管理;其次,对不服宗主意愿的人进行讨伐。
第五,宗法主制的建立,意味着中国封建国家社会形态的健全。它是家庭血缘关系生长的新载体:一个家庭血缘谱系的伸张和健全,千万个家庭成为该宗族下设的具有血缘关系的基层单位,“核心家庭”是真正的社会细胞。
起初具有原始民主意识的分封制总遭至非议,而强权的使用必使微弱的民主成为虚语。在家庭血缘关系意识中成长起来的上古统治者们清晰地认识到,只有血亲血缘关系才是最可靠的。所以向更精确的血缘关系发展,既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商代开始,向血缘血亲关系的回归和将其进一步精致化,成为上层大宗族的强烈要求。
据史料载,商代在王位继承上开始由“民主”意识下的“兄终弟及”向“父死子继”演变,由于商代家庭的特殊称谓关系方式,同一辈人同为兄弟,下一辈同是上一辈人的子女,也即上一辈人同是下一辈人的父母,没有后来的堂兄弟姐妹关系。“父死子继”的实行变成了亲子与兄弟之子之间的王位之争。这种缺陷也就使继承制向“嫡长继承”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中国宗法制中最为重要传承方式便是:继承“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次”、“传男不传女”。总之,嫡长继承制的实行是中国宗法制形成的标志,它为中国国家的健全铺平了道路,它也定格了中国社会发展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形式和传承构架。
二
宗法专制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封建国家真正形成或健全的标志。这种制度的萌芽期在夏,形成期在商,而成熟期在西周。由于“嫡长继承”的实行,分封子弟就成为必然。分封同姓同宗时,对异姓异宗的功臣的分封也必须实行,尤其是建国之初。然而政治统治中权威和权力的矛盾使宗法主在处理异姓王与同姓同宗的关系,以及如何既信任又戒备同姓王的问题上绞尽脑汁。中国根深蒂固的家庭血缘统治的传统,使后来的国家统治者机智地通过通婚的形式,“合理”地将有用的异姓功臣“转化”为同姓同宗或者是有血缘关系的宗室之王。而且从历史上看,这种血缘笼络的方式不仅使用在国内,而且也使用在外交上。通过通婚使异姓王变成与宗主有血缘关系的诸侯的方法,是中国人传统的亲近来往的归附方法。这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家庭血缘关系的亲情策略,在中国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某种特征性的东西。关于这一点,许倬云先生在对西周“分封的本质”的阐论中明确地指出:“综合文献……分封制下的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势须发展地缘单位的政治性格”,他在阐述了“诸侯徙封的例证”、“封建制的层次”等问题之后,得出结论说:“西周的封建制度,一方面有个人的承诺和约定,另一方面又有血族姻亲关系加强其固定性,二者相合,遂有表现于彝器铭文的礼仪,礼仪背后,终究还是策名委质的个人关系”。(许倬云:《西周史》,150、17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
此时我们再去理解西周的“明德慎罚”的政治术和中国的法治传统,就能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的“人法治”与西方传统中的“法人治”的不同。宗法专制的统治,必须以家族、宗族的观念为前提,所以只能是人治,人用法治人,以亲情为法治的原则或前提。西方城邦制强调工具在人类对付自然中的作用,其统治必然是以规则的观念为前提,所以只能是法治,法用人治人,以理性为法治的原则和前提。本文反对那种不了解历史的根本传统而对历史随意加以指摘的态度。中国的传统自有其合理之处,这是经过历史长河的千百次淘汰而渐趋形成和沉淀下来的,其当时当地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岂是后人一言“糟粕”所能否定得了的?法律是国家统治中最重要的理性规则,然而中国的法律仍脱不开人的情理,走不出家庭规范的格局。现在人们再来回顾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进步总离不开家庭发展阶段的影响。
史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他认为这种“新制度兴”、“新文化兴”的剧变就表现在:“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第二册,451、4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至此,天下一家终致于成。侯外庐先生也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是经历了一条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特殊路径进入文明社会,即血缘家庭不仅始终未被打破,相反,国家恰恰是建立在氏族家庭的基础上。西周社会的君臣行政关系实际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子、宗孙和姻亲的亲缘加地缘的关系。这就是说,在单一的家庭沿传天下之权意固定化之后,封建国家的各种建制便稳定而趋于健全。当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因天下权意的诱人而各家相篡。国家战争的结果和社会发展的终极便是国家消退:国家皈依社会,实现国家的各种职能归还社会操作的转化。那时的社会景观会令具“小国寡民”意识的老子叹为观止。
可以预测,国家的形成由家庭而来,将来国家的发展和演变仍惟家庭形态的变化是瞻。国家的消亡仍以家庭发展更高阶段为归宿,到那时一个新的家庭生存发展的载体就会出现,这是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