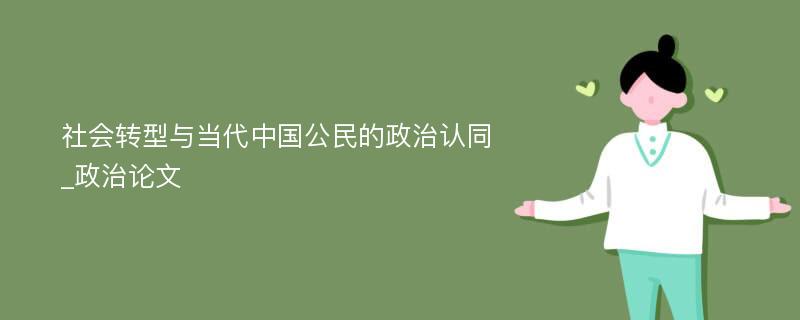
社会转型与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公民论文,当代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4-0102-04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过程,社会转型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多元化。由于公民所处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不同,他们的想法与要求也各不相同,其政治认同也有所差异。社会转型对当代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具体影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社会转型对政治认同客体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要求
政治认同的客体包括国家、政党、政府、制度、政策、利益和价值等多个方面,本文中所使用的政治客体主要是指执政党与政府。社会转型对政治认同客体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与挑战,它要求作为政治认同主要客体的执政党及政府治理的方式要实现政治转型,要求公共权力机关实现从统治向治理的转变,从而适应政治现代化的要求。“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涉及各种新的政治功能的分化……涉及整个社会中更多集团的参政”①,在传统社会里,统治者往往借用超自然的力量(神、上帝等)来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君权神授论”自然难以再生成政治合法性,人们也不仅仅满足于政绩合法性,与民主法治等现代性政治观念相适应的政治合法性成为人们更高的追求。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人们教育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一切大大刺激着人们的经济欲望和政治期待。社会转型对政治认同客体——执政党、政府、制度、主流意识形态等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政府治理绩效、制度公正性、运行机制的科学性等问题随即产生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民原来认同的东西,在市场体制中就可能变得不认同,原来靠理想主义和个人魅力等获取公民认同的方式逐渐失去其应有的作用,公民对原来认同的事物可能就很快演化为不认同或认同度降低,同时公民也会产生新的认同。
二、社会转型使政治认同主体发生了身份与心态上的急剧变化
政治认同的主体是公民。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认同主体的身份发生了从传统社会的“臣民”向现代社会的“公民”的过渡。一方面,社会转型给人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与舞台;另一方面,社会转型使“现代性社会正在发生一个很大的‘认同政治’的变化,就是从以‘解放的政治’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为‘生活的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前者是获得‘生活机会’的政治,而后者是选择‘生活格调’的政治,‘生活格调’与‘生活方式’不同,它不是群体性的选择,而是个体主义化的选择”②。传统社会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和单一的社会,人们的社会联系主要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主要是对权力的顺从;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认同的对象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认同对象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认同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权威的认同。因此,传统农业社会下人们的欲望与要求比较简单,而现代工业社会的公民流动性大大增强,社会分工更加细化,人们的需求与愿望变得更加丰富起来。现代社会的公民也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臣民,传统社会下的臣民认为政治是当权者的事情,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现代社会的公民一般具有自主意识、权利意识、民主和法律意识等内涵,他们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期望值在攀升,要求也呈现多样化,原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问题,现在就可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依据,原来曾经被看作是合法的问题,现在就可能变成非法的。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政治认同客体与政治现代化转型的不同步性,政治认同客体一时难以满足社会公众的期望心理,由此,我国公民政治认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他们的政治心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一)公民的政治功效感低
作为个体的人有着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的人权诉求,如果这些最起码的权利得不到基本保证,那么他们的政治功效感就不可能很高,他们的认同度也会相应地降低。同时,政治参与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政治参与的水平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政治参与的实质是公民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资格,影响政治体系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以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一个人的政治功效感对其政治态度与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
一方面,社会转型使得民众的生存变得相对比较艰难,生活上的巨大压力使大多数人无暇更多地参与政治。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生活中的一切基本上被政府全部包了下来,普遍产生了一种对政府的依赖感,也就有了一种生活的安全感和稳定感。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到来,民众在生活中面临诸多困扰或难题,其中“住房贵”、“看病贵”、“上学难”、“就业难”已经成为当代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四大新的民生问题,而民生之艰难存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直接影响群众心理,左右着社会情绪。根据2006年3—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资料显示,在生活压力感方面:城乡居民遇到最多的生活问题是“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其次是“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再次是“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比例分别为51.3%、45.5%和45%。城乡居民对所遇到的压力评价由大到小的顺序是“住房”、“医疗”、“下岗失业”、“教育”、“家庭收入低”、“赡养老人”、“人情支出”、“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家庭矛盾和邻里矛盾”。由此可见,民众感到生活压力大的方面首先是经济压力。在社会信任感方面: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平均数为3.56,接近很信任;而对法官和警察、地方政府、信访机构的信任程度的平均数从2.79到2.98之间,接近比较信任水平;消费者协会等维权组织、社区组织、环保等公益组织的信任程度与之接近;信任程度更低的是行业协会、宗教组织,平均数分别为2.56和1.85。在政府工作满意度方面:对社会保障和救助最不满意,满意度得分介于2.5—2.92之间。公民面临的生存或生活中的巨大压力会使他们对政治产生冷漠,对政党和政府产生不信任感,由此就会造成公民政治上的一种无力或无奈的感觉。
另一方面,社会转型使得部分公民的一些基本政治权利不能得到切实保证,也导致了公民政治功效感降低。选举是人们的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也是公民对社会的一种政治认同方式。选举中出现的暗箱操作行为,使得民众不愿参与选举。这是因为,民众从心理上和实际中深刻地体会到:即使选举出来的代表也很难真正代表他们,而且代表的权利也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公民参与是以公民对于政党与政府的政治认同为前提条件的,如果公民参与政治的效能感降低,那么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认同度;如果公民不愿意参与政治,不愿意与政府合作,那么,就会降低公民的道德责任感,形成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距离感,降低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减损制度的权威性等。北京大学的刘爱玉教授曾谈到企业产权变革时期工人政治地位受损失的主要表现:“32%的普通工人认为自己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被采纳的情况减少了,38%的普通工人认为自己在企业中所拥有的权力减少了。30.5%的被调查者认为工人的政治地位在改制后受损,有50.8%的被调查者认为工人的政治地位很低。”③ 工会由于不能有效地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而成为一种摆设、工人失去了话语权,这些问题导致工人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度下降。另外,在中国农村,广大农民阶层目前的自主式政治参与仅限于行政村这一基层社区,农民仍然无法通过有效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农民对国家的基层政权一旦不认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上一级或中央政府,靠坚持不懈地上访求得问题的解决。据统计,从1995年至2000年,集体上访的数量已占全国信访总量的56.5%。大规模的群体上访不断增加,实际上意味着大多数社会公众对基层政权的不认同。④ 上访如果再解决不了,就可能逼得农民走投无路,使其产生仇视社会、敌视政府的情绪,有些人还会铤而走险,走上暴力抗法的道路。以上问题继续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导致如亨廷顿在论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动乱时所指出的情况:“如果农民阶级默认并参与现存体系,那么它就为该体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如果它积极反对该体系,那么它就成了革命的载体。”⑤ 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群体,目前,某些高等院校广大教师的民主权利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在某些地方,选举与聘任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这就增加了知识分子对政治不认同的程度,“因为在选举沦为纯粹的形式的情况下,选民无法对候选人进行选择,文化程度越高者越可能以不参与的形式表示不满”⑥。
(二)公民的相对剥夺感强烈
人们需要的满足包括实际的需要与期望的需要,相对剥夺是指在人们实际需要的满足与期望的需要满足之间或自己与他人的需要满足之间产生差距的感觉。马克思曾指出:“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⑦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民的相对剥夺感问题更加突出起来,因为改革本身就是社会各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调整,而调整的结果使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一种相对剥夺感。社会转型促使公民对各种需要的期望迅速上升,公民对满足需要的内容与程度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公民内部各阶层的利益与收入也有较大不同。特别是由于新旧体制的交替和摩擦以及制度上的漏洞,有的人利用权力寻租而成为社会上先富起来的群体,有的则钻了国家法律与政策的空子而富裕起来,有的人是利用国家赋予他的垄断地位与权力大发横财,这就使人们的心理就变得不平衡了,随之而来的相对剥夺感就出现了。随着利益与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这种相对剥夺感也会愈来愈强烈。这是因为,“人们把他们自己与他们自己群体中的那些他们所认识的、像他们自己一样的或他们所了解的人加以对比,有时也与他们想加入的那些群体中的上述人物加以对比,他们对于这些人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报酬的了解影响着他们期望能够得到的社会报酬水平。确定了这种比较,在群体中接受高报酬的人,如果看到其他人在其中同样也接受着高报酬,就可能比那些境况并非更好甚或更坏但处在其他人接受更少报酬的群体中的人对他们的收获更不满意”⑧。
我国公民的相对剥夺感存在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比较中,社会转型时期受益较多的是政府权力部门、垄断行业、影视界的人员和私营企业主,而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与农民等群体就成为改革中受益最少的群体,社会已形成严重的两极贫富分化。不少工人面临失业的威胁,他们生存的压力和成本在不断提升,其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也在不断加剧。他们的自我认同较低,这样就“使一些人对于作为普通工人的身份感到自卑,并在实践中尽量回避这种身份,这种身份带给普通工人的已不再是荣耀,不再是保障,不再是羡慕,有的是无奈以及在生活中为避免这种身份的奋争”。根据《2006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干群关系被认为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有71.4%的人认为近10年来国家干部是获利最多的群体,另有49%的人选择了国有、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公众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公众认为干部更多地享受了改革的成果,拉大了与群众之间的距离。⑨
知识分子是对政治比较敏感的群体,是社会现实的批判者。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被边缘化。如果说过去的知识分子边缘化是发生在政治层面的话,那么这一波的边缘化更多的是在社会意义上。……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变迁,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整个社会不再有中心。更确切地说,政治与意识形态第一次不再占据社会的中心,而经济上升为中心问题”⑩。由于知识分子看问题本身比较理想化,对社会的期望值也较高,他们对政治的认同度并没有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而相应增加,相对剥夺感也在增加。
国家干部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在一般人眼中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但他们也不满意。在关系自己升迁的重大问题上的非正规操作,任人惟亲,帮派体系,使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肖唐镖教授在2003年到2004年上半年对乡镇、县、市厅干部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关于“干部任用怎样的风气?”这一问题,在571份问卷中居然没有一人选择“任用干部风气很正”,选择“风气比较正”与“还过得去”的合计为52.6%(前者占18.6%,后者占34.0%),45%的人认为“不太正”或“很不正”(前者占31.5%,后者占13.5%)。关于“任用干部的风气不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的答卷者中,74.8%的人选择了“拉关系、跑官”,55.3%的人选择了“任人惟亲、分派分线”,28.4%的人选择了“买官卖官”,46.8%的人选择了(干部任用的)“考察不实”,43.1%的人认为在干部任用方面“决策不民主、个人说了算”。(11) 这就使得真正有才华的干部不能够得到重用,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们发展的仕途就被这样或那样的“潜在的游戏规则”堵塞了。
低收入阶层在经济收入与对社会的贡献方面相对剥夺感最为强烈,低收入群体主要指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商业工作者和服务性工作人员阶层等收入较低的社会阶层,他们承担了社会改革的巨大成本,成为收入最低的社会群体。他们自我认同度最低,其他阶层对他们的社会认同度也比较低。
私营企业主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的阶层,他们在经济上收入相对比较高,但认为是凭自己本事得来的,如果没有政府权力对他们的“骚扰”,他们的收入会更多,因此,他们的心理也不平衡。
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人们看问题时往往和自己的以前比,和与自己地位相似的比,结果出现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社会现象。这种情绪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就会逐渐降低他们的政治认同度,甚至会产生不认同。“部分群体的比较利益过低、收入提高受阻甚至绝对收入额下降,使部分人群产生相对剥夺感,在某些突发事件的刺激下,会发生失去理性控制的集体行为。”(12) 根据2005年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的统计资料,1993—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至约307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的于建嵘教授在分析我国最近几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时认为:贵州瓮安事件与近几年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安徽池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大竹事件,在起因、过程、后果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结构相似性。他把这些事件统称为“社会泄愤事件”。在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时,他认为社会大众的“相对剥夺感”甚至“绝对剥夺感”日益增强,为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基础。(13)
注释:
①⑤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8页,第317页。
② 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③ 刘爱玉《选择:国企变革与工人生存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2—103页。
④ 麻宝斌等《新中国社会的群体性政治参与》,载于《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⑥ 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载于《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49页。
⑧ [美]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
⑨ 转引自王俊秀、杨宜音、陈午晴《2006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3期。
⑩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页。
(11) 肖唐镖《地方官员改革态度调查》,载于《决策》2007年第12期。
(12) 李培林《建设和谐社会应注意社会心态的变化》,参见人民网2005年10月13日。
(13) 于建嵘《反思社会泄愤事件》,参见新浪网2008年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