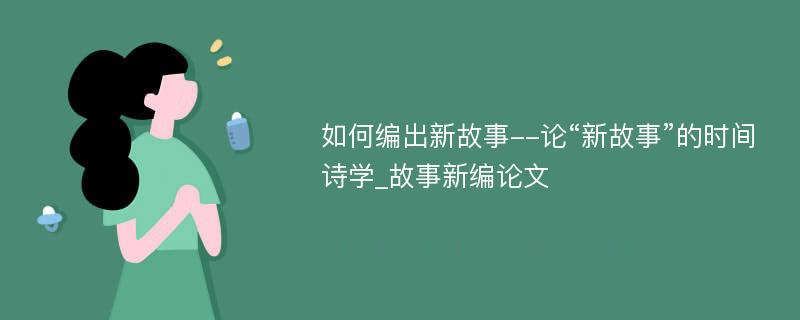
故事如何新编——论《故事新编》的时间诗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编论文,故事论文,诗学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55(2015)04-0129-06 叙事作为表述事件的发生,时间因素占有突出的地位。叙事时间将一种被讲述的故事或事件的时间表达出来,同时,又将其建构成为被语言叙述、被艺术表现出来的时间。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异质性(disparity)造成了小说艺术表达的张力。由于叙述方式的安排与传统故事生成情节的自然顺序不同,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巧妙地运用一种立体的、多层次的、并与意识融为一体的叙述模式,有意淡化消融近代小说对历时性发生的线性叙述,使时间观念呈一种立体的无序延宕(dilatory),在诗性舞台得以成立的状况下,小说的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彻底分开,脱离了物理时间的单一矢向,时间在小说中不再是常量,而是一个变量,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产生了独特的美学效果。 一 此在的生命时间 时间不外在于人的生命,而内蕴于人的生命之中。时间之门既可以对个体生命关闭,也可以为生命超越而洞开。只有通过时间的永恒流变,才使生命趋于无限。杨义指出:“时间意识一头连着宇宙意识,另一头连着生命意识。时间由此成为一种具有排山倒海之势的、极为动人心弦的东西,成为叙事作品不可回避的、反而津津乐道的东西。叙事由此成为时间的艺术。”[1]120“时间体验包容着人生态度,成了独特的生命体验”[1]157。人作为历史的主体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存在于时间之流,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自然物的存在。人的自我意识主要表现在人不仅能意识到其与外在对象的区别,而且还能意识到时间对其生命的限制。因此,时间意识作为人的意识的首要表现形式,促使时间成了个人对生命价值体验的前提。 小说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其时间意识主要体现在小说人物与时间相遇所产生的生命哲理以及与此相关的审美意识,我们正是缘此进入鲁迅小说的时间领地。在鲁迅小说中,时间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是以此在的方式诗意存在。“对生命的关爱”一直是“鲁迅思想的一个亮点,一个底色”[2],鲁迅之所以特别重视现在,就是因为他深刻意识到了现在和生命之间的特殊关系,“通俗的说应该是:现在对于生命,有着生成化的功能;或者说,因为它活生生的‘现在着’,故可以把过去与将来‘当前化’地收摄于‘此’,连接于‘此’”[3]。不难发现,鲁迅大多时候对当下的关注也是出于对人的生命问题的重视,他始终如一地站在对人的生命意义终极关怀的角度来思考人生,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生的追求与归宿以及个体生命的生存境遇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指出:“我们愈是能够人性地把握人类存在的时间性,就愈看得清楚这种存在本身完全是历史性的。”[4]《故事新编》不是我们通常所提及的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尽管每篇都以一个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或历史人物故事作为小说蓝本。鲁迅以洒脱、自由的心态创作了《故事新编》这种新的文学样式,“这些新编的故事,显然又是鲁迅小说文本的创新……《故事新编》以其思想成就和艺术创新,同鲁迅的《呐喊》、《彷徨》一样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成为重写民族神话、传说和历史的典范之作。”[5]从表面上看,《故事新编》是历史讽刺小说,选取神话与历史故事,加以铺陈,同时又注入了时事,予以讽刺。正是由于鲁迅对现实的不满,借写小说来以古讽今,同时也以这样的形式,消解了历史的经典。鲁迅说自己并不想做“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教授小说”(历史小说),而只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做法上也是向历史“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6]354,“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7]不难发现,鲁迅创作《故事新编》的目的十分明确,不是为了复述古人往事,而是在中国历史中“寻出”、“改作”、“注进新的生命”。黄子平把《故事新编》看成是鲁迅为解决“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之紧张关系而进行的静夜挣扎,鲁迅择定了“油滑”的叙述方式,使来自文献与当代的众多引语在同一作品空间中同质地发声,从而将“过去”的故事、“未来”的阐释纳入他写作的“现在”,以反抗那个话语秩序分崩离析的时代里讲故事者的悲喜剧命运[8]。《故事新编》没有停留在对历史和历史事件本身及其过程的简单铺陈与叙述,而是深入到历史及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进行了充分诗意化、哲理化的艺术再创造。这种艺术再创造在鲁迅历史意识的现代转换中得以体现。 二 历史意识的现代转换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指出:“每一部历史首先是一种言语的人工制品,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运用的产物。”[9]同时,“每一个伟大的历史叙事都是一种时间性的暗喻。”[10]245历史被视为现实世界的隐喻、借鉴或说明,也为世人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鲁迅把史书看成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里面充斥着“瞒”和“骗”的伎俩。他深知历史的真义,在古与今的纵向对比中,“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11]149。在鲁迅看来,由于历史言说的主体不同从而产生出不同的言说方式与历史文本,“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查出底细来”[11]17。因此,鲁迅强烈主张:“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明其妙。”[12]不难发现,鲁迅对中华民族宏大的历史经典文本并没有顶礼膜拜,而是用一种全新的手法去解构中国传统历史文本,并成了鲁迅历史小说创作的应然选择与追求。 鲁迅创作《故事新编》的出发点是“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13],故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在发掘“历史”的同时又创造了“历史”,他十分在意情节的“故事性”,同时也注重故事的当下性与寄寓性,他借历史说话,在言说历史的过程中将自身的主观好恶贯穿故事情节始终。王富仁指出,《故事新编》的题材虽然是过去的神话和历史,但是叙事是现在时的,而且鲁迅小说永远是现在时的。就事件而言,鲁迅小说所叙述的事件本身几乎是没有意义也没有趣味的,即便有,也不是这个事件本身的意义和趣味[14]。鲁迅猛烈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并且指向其思考的当下现实语境。《故事新编》关于历史的体认,在鲁迅历史意识的现代性转换过程中被完整地昭示。在鲁迅特有的历史观念的支配下,其关于个人与历史及其运动关系被具体揭示出来。因此,《故事新编》的显在状态是鲁迅历史小说的现代化,其基本结构是“个人与历史、个人作用与历史发展”,鲁迅的历史意识正是在这一结构中形成。 鲁迅的历史意识基于这样一种理论预设:所谓的历史并不是历史上实存的事件,而仅仅是一种话语或一种叙事文本。海登·怀特将历史叙述和文学叙事几乎等同起来,在他看来,历史事件不能像科学那样以试验或观察来检验,而历史理解尤其是历史叙述,完全是一种语言虚构(verbal fiction),必然要有连贯性,对事实进行剪裁,使“事实”符合某一故事形式的要求,从而产生故事或小说的效果,“产生意义”,使人理解[10]63-79。因此,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一样,不仅要通过修辞性叙事赋予过去事件存在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使读者从假定性中寻求真实感,而且也要通过比喻性叙事来阐释过去事件存在的意义。而历史小说作为一种叙事塑形(narrative configuration)的时间艺术,它与其它文学叙事一样,都要通过情节化操作(operation of emplotment)来讲述故事。传统历史小说虽然强调要“据实而书”,试图恢复历史的真实,但在编织情节(emplotment)的过程中,他们不可能去“亲证”和“经历”历史往事。因此,历史小说只能以“故事”新编的图式呈现在读者眼前。 《故事新编》中的人物大都生存于历史延续中的“当下”,几乎每一篇小说都可以找到现代人的身影。郑家建认为,“《故事新编》文本中的古今杂糅的时间形式,正是渗透着这种循环论的体验,是鲁迅特定的对历史文化感受、理解方式的一种自觉和不自觉的投射和表现。”[15]在《故事新编》构筑的艺术世界里,鲁迅将神话、历史与现实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打破了历史的正常时序,小说情节在神话与现实、历史与当下之间随意转换,使人们进入了一个古今杂陈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里,一些历来为人们所尊崇的神、英雄和先贤被拉下神坛,被脱去华丽的长袍,让他们困扰在一系列的日常琐事之间,暴露出其凡夫俗子的世俗相,英雄的时代被无情消解。这既是《故事新编》中人物生存的时间表征,也反映了鲁迅独特的历史意识,这种独特性必然最终显现为小说文本中个体体验的历史言说。 三 个体体验的历史言说 海登·怀特指出:“历史永远不仅仅是谁的历史,而总是为谁的历史。不仅是为某一特定意识形态目标的历史,而且是为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公众而书写的历史。”[16]历史学家“基于一种逆向的因果关系”,即“知道一个结果,我们在时间中回溯它的原因”[17]。正基于此,使得对历史事实的叙述由简单的按时间序列进行描述转变为一种按逻辑论证进行推理的过程,以此印证了克罗齐“历史决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的论调[18]。 鲁迅的写作都是在主体和主体置身的语言之间进行思考。主体不可能直接面对整个真实,因为置于人们眼前的真实本身不蕴含价值,处于无序状态,从而使得主体无法安身立命,只有通过一套符号秩序(symbol order),从语言中寻找栖息地,才能让他真正理解世界的样貌。正如硬币的两面,主体在建构符号秩序的同时又将为他苦心经营的符号秩序所桎梏,忽视了符号秩序只是真实的替代品,而在主体无法悉知的符号秩序之外,却存在着无法直面的真实。这一悖论的存在让天真乐观的启蒙主义者垂头丧气。鲁迅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一直在苦苦寻找一种话语的可能,让主体在符号秩序之内,觉察到符号秩序之外的真实。 鲁迅在创作《故事新编》的过程中,完全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古今界限分明的传统经典范式,创造了古今杂糅、虚构与纪实杂存的艺术旨趣,历史成了现实存在的镜象,许许多多的生活现实都从历史的镜象中折射出来。陈国恩指出:“鲁迅小说叙事艺术的魅力既不在于对真实人物的真实行为和内心真实的叙述,也不停留在对历史结构的模仿阶段,而是在已成为历史记忆的真实的人类经验和个人性的虚构想象之间建立起联系,在过去的真实世界和虚幻世界之间形成叙事空间。”[19]在《故事新编》中主要体现在鲁迅个体体验的历史言说,即历史时间物质化、历史人物世俗化以及历史事件戏谑化,不仅消解了神话、传说以及历史人物的神圣与崇高,同时也是对历史与传说的重新建构。 (一)历史时间物质化 历史时间正是在人们对历史存在和运动形式进行阐释的过程中,展开了时间所负载的历史叙事图景,历史时间是通过对人和活动、人的成长以及社会发展进行叙述,从而向人们讲述历史。“历史时间的可逆性是存在的,但它必须存在于底层为自然时间的基础之上,即存在于一个不可逆的惟一内禀物质中”[20]。 在《故事新编》中,好些作品的时间刻度用吃食来衡量。《采薇》中出现最多的是“大饼”意象,充分展现了伯夷叔齐不断产生出来的饥饿感和物质欲望,对追求名节和声誉的伯夷叔齐构成了莫大反讽。人们可以通过烙饼的大小变化来了解战事进展,也可以用烙多少张饼来计量时间。鲁迅用“烙饼”这个日常化动作来界定和标志历史时间,一方面自然有其所说的“油滑”和“戏说”历史的成分,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伯夷叔齐的人物性格,把伯夷叔齐作为遗老不知变通、恪守传统的礼义道德的老朽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铸剑》则用换松明、煮小米粥等琐事来作为计量时间的手段,并以此来叙述一个惊心动魄的复仇故事。鲁迅用“换松明”来计量时间,把眉间尺性格的犹豫和怯弱展露无余,用“煮熟一锅小米”的时光来表现眉间尺的焦躁性格。而小说起用这样一个矛盾性格的人来担当复仇者,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想法,而整个故事的发展都在荒诞的氛围里进行,用“煮熟三锅小米的功夫”来表示众位王妃和大臣讨论如何打捞办法的时间把这种反讽效果推向最高点。复仇与生命存亡等严肃话题被“换松明”、“煮小米粥”等日常行为所消解,从而完成了对宏大的复仇史诗的解构,凸现出历史时间与现实生活的双重悖论。 (二)历史人物世俗化 鲁迅用一种“油滑”的语言和悖论式结构,剥掉了古人身上庄严而神圣的外衣,让其从高高的云端跌落到世俗的现实,使其面孔变得异常清晰而真实,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化所建构起来的英雄崇拜。旷新年认为,《故事新编》中鲁迅是极度自由地去凝视历史文化中的巨人。这些一代又一代被叙述,被语言浪漫化地建筑起来的人物于是在鲁迅的凝视下被还原了。在鲁迅的凝视中,他们脱落了他们的装饰,只剩下肉体,即生命,直至凝视至骨头,人的最深的层次[21]。人们往日崇敬的英雄、圣人在去神圣化后变得滑稽而可笑,国粹家眼里辉煌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与文明随之黯淡无光,深刻体现了鲁迅的强烈危机感与绝望感。 在《补天》中,鲁迅没有继续演义女娲造人的神话,而试图恢复其自然神性,有意创造出关于“起源”的“现代神话”。从女娲醒来,在空寂的世界里造出了人开始,到最后交待了女娲死后的情形,小说的每一段都向前一段召唤失去的世界,将油滑的此在与原初的存在相连,不断逼近时间先在性,同时也质疑了这个世界的自足与稳固。鲁迅最初的构思带有创世神话的意味:女娲创造了世间众生,也因此耗尽了自己而死去。然而原定的结构却因为意外而毁坏,这意外显然不是来自外界的,而是触及这结构本身内在的隐患。古衣冠的小丈夫手持“一条很光滑的青竹片,上面还有两行黑色的细点”[6]364,暗示了文字的出现,伴随文字出现的是对自然创造设下限制的礼义廉耻等国之常刑。而文字的出现对女娲的造物进行了彻底颠覆,也暗示着文学既是创造,也是创造的消亡。 羿作为传说中的英雄,他射落了九个太阳,除掉了为害老百姓的封豕长蛇。而《奔月》中英雄的神话被夫妻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所替代,羿已经完全失去了英雄的光环,沦为凡夫俗子,他整天都在为日常生计而疲于奔命。然而他又不得不自食成为英雄后的苦果。他只能陶醉于昔日的英雄壮举,而对今日的窘境却束手无策。平庸的生活让他不停地退却与让步,甚而至于走到了生活的对立面。面对俗世的拷问,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同时,昔日的英名反成今日的负累,使他如同进入“无物之阵”,有一种找不到对手的悲哀。在英雄与凡人的博弈中,羿俨然成了生活中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最终难逃英雄末路的凄凉结局。 鲁迅笔下的故事、神话总是预埋着宏大结构,而在油滑面前已不可复得,只是嘲弄的对象与篡夺的替代,在新的叙事结构面前,人们看到的是创造消亡的神话,以及一个油滑时代的反神话。鲁迅把不可复得的神话世界拉进我们身处的反神话世界。 (三)历史事件戏谑化 鲁迅指出:“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交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22]不难发现,鲁迅对“理想家”持否定观点,断然拒绝了温情的“过去”与希望的“未来”,“仰慕往古的,回到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去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11]52。鲁迅小说生命时间观始终执著于现在,执著于现在的时间观同时也构成了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精神的基石。鲁迅执着于现在并不等同于历史的虚无,尽管鲁迅强调当下的在场,但并非割舍过去,放弃未来,而是通过当下观照过去、展望未来。在鲁迅看来,孤零的现在是没有的:“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23] 1、影射当下人和事。许祖华认为,“鲁迅小说的基本幻象也具有这种始终的现在性与当下性”[24]31-32,“鲁迅小说的现在时态,始终具有这样一种艺术规范与艺术意味:就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的表达而言,小说的基本幻象始终以全景式的方式处于主体现在价值视野的观照之下,从而使创作主体对事件的任何评判都呈现出鲜明的当下性与时代性”[24]33。立足当下的人和事,并让过去的人和事当下化,这是鲁迅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鲁迅对当下的重视,其目的是统一过去和将来,他反对形而上学的虚幻的终极追求,只有立足于当下,生命才有所依附。 鲁迅在创作《补天》时中途停笔去看日报,“不幸”看到了胡梦华对《蕙的风》的“含泪的批评”,故他在《补天》里“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古衣冠的小丈夫”暗指胡梦华,胡认为青年作家要为教化负责,不要再写那般形式的诗。鲁迅对此极为反感,他把这个小丈夫置于女娲的两腿之间,刻画出一个淫荡、放纵,但偏偏又冠以正人君子之名的虚伪小人嘴脸。鲁迅借小说来声援湖畔诗人汪静之爱情诗创作。今天我们看来这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而对于鲁迅来说则给他带来了全新的创作手法,也就是鲁迅通常所说的“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6]353。 《理水》中文化山上有一个红鼻子学者,叫鸟头先生,他通过考证,认为鲧和禹都不存在,因为鲧是一条鱼、禹是一条虫,更不会治水。当有人对其说法提出质疑后,他花了27天工夫,将考证用炭粉写在刮去皮的大松树上,并获得了不菲的门票收入。当一个乡下人对其学说提出不同看法时,他恼羞成怒,乃至于吃完炒面后要起诉乡下人。这一故事被人视为是鲁迅对顾颉刚的影射。 2、现代话语的移植。《奔月》中出现了大量现代词汇,如“乌鸦炸酱面”、“饭馆”、“首饰”、“辣子鸡”、“炊饼”、“辣酱”、“丧钟”等。《铸剑》中干瘪少年纠缠着眉间尺要他为自己“贵重的丹田购买保险”。《采薇》中有“养老堂”、“太极拳”、“奴脾”、“官报”,小丙君因伯夷、叔齐不懂得文学概论、只知道“为艺术而艺术”而拒绝与之交往并不肯为之写石碑。《出关》中出现了“图书馆”、“账房”、“巡警”、“税”、“讲义”等,老子给关尹喜等人“面授玄机”所得报酬却是一包盐,一包胡麻,外加十五个饽饽,只因为他是老作家才得到如此优待。《非攻》中出现了“募捐救国队”,有“民生论”的演讲。《起死》中庄子“吹警笛”、“用警棍”,还背诵起《千字文》来。鲁迅将现代事件移植到历史叙事和历史环境中加以表现,使“历史”带有厚重的现代色彩,从而演绎出新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 3、叙事的现在时态。王富仁认为《故事新编》“就其题材,它们是过去时的。但这只是它们的题材,而不是小说本身。小说本身的叙事则是现在时的”[14]。鲁迅习惯于采用现时的手法来描述那段已经远去的历史。《补天》中,“伊似乎是从梦中惊醒的,然而已经记不清做了什么梦;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煽动的和风,暖暾的将伊的气力吹得弥漫在宇宙里”[6]357。《铸剑》中,“眉间尺刚和他的母亲睡下,老鼠便出来咬锅盖,使他听得发烦。他轻轻地叱了几声,最初还有些效验,后来是简直不理他了,格支格支地径自咬。他又不敢大声赶,怕惊醒了白天做得劳乏,晚上一躺就睡着了的母亲”[6]432。《故事新编》中大量充斥着叙事的现在时态,鲁迅把过往“历史”当作“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叙述,其小说人物和在戏剧舞台上的历史人物一样,进行的是即时性的表演。它们不再是遥远时代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而是当代人想像中的世界。通过小说人物这种即时性的表演,从而使《故事新编》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张力。通过历史意识的现代转换以及个体体验的历史言说,《故事新编》把客观的历史时间转换成此在的生命时间,由此获得了一种与历史发生关系的个性化存在方式:在生命进入历史的同时历史也在进入生命。历史在自我的生命中得以伸展,自我生命也在历史中获得延续。就这样,鲁迅以对时间的独特感知来完成了他对历史的体悟和认知,鲁迅小说中的历史意识因而成为关于生命存在与延续的时间诗学。标签:故事新编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神话论文; 铸剑论文; 补天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