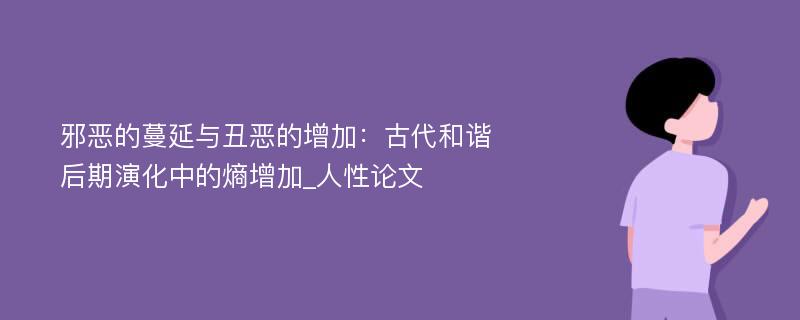
恶扩散与丑增加——古代和谐后期演变的熵增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期论文,古代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原始人零散杂乱的审美心态来说,感性和理性在古代人性结构中所形成的抑制性关联或收敛性结合,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主客融合的审美方式,安恬适度的审美趣味,和谐统一的审美理想等等,古代审美意识的这些方面,对于古代人在自然和社会中寻求其适当的位置,对于他们保持那可以带来慰藉和稳定的心理平衡,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面对着可以不断开发的广阔的外部世界和内在生活,古代审美意识是封闭而狭小的,当古代人的主体水平还保持在与客观世界的自发统一之上的时候,当他还必须依赖这种统一的关系求得其生存和发展的时候,封闭而狭小的审美意识更多地表现出了它的合理性的一面,而那个向往着和谐统一的审美理想,也更多地表现出它的生命活力的一面。然而这种情况在古代审美意识历史演变的后期阶段却出现了变化,人性结构的主体化导致了古代人性结构的松动和古代审美意识的解体,审美的混乱状态随之出现,借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术语,我们称之为审美的增熵现象。
一、理性抑制对感性动力的失控
1.理性的僵固与感性的枯竭 古代人性结构自其形成之时就是建立在理性对感性的抑制性关联之上的。理性对感性的抑制作用,表现为对感性的分割和肢解,即被分离为生物本能和模式情感两个端点。在古代审美意识形成发展的初期阶段,理性对感性的抑制性关联尽管已经形成,但它对感性的分割肢解还只是开始,也就是说,尽管处在被分割肢解状态中的感性是逐渐趋向于弱化和萎缩的,但它作为整体所蕴涵的生命活力和能量,仍然可以注入古代人性结构,而理性作为抑制的力量尽管是趋向于抽象和僵化的,但当它在尚未完成对感性的分割的情况下,或者说在尚未完全凌驾于感性之上的情况下,它也具有某种适应感性变化的宽泛性和模糊性,古代人性结构因此而具有一定的弹性和扩张力。理性分割肢解感性这一过程的完成,同时也就是古代人性结构衰退过程的开始。这时,模式化的情感已完全脱离了感性的整体,真实的生命体验和生动的感性活力被当作生物本能而排除在人性结构之外,这样,残存在人性结构中的感性躯壳便处在无根的萎缩状态。与此相适应,那个曾经支撑了古代人的主体性,曾经对古代人性结构产生了稳定作用的实体化的理性,也成为一种僵固的存在,它不再具有那种与宇宙自然同在的神性,而成为与那无生命的感性躯壳相依存的强制性规范和虚伪的信条。感性与理性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已经走到了人性的反面,成为一种损害和束缚人性正常发展的桎梏。进入后期演变的古代审美意识和进入衰落时期的古代审美理想,就是建筑在这种敌视和扭曲人性的“人性结构”之上的。
感性与理性结构关系与真实人性的背离,在审美理想上则是和谐美追求与真实人生的背离。在古代审美意识演变的后期阶段上,和谐美理想失去了它曾经带给古代人的稳定感以及适度适中的自由感,对于审美意识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一种滞后的制动的力量。与其形成发展时期的社会生活相比,古代审美理想在后期阶段上所面对的现实人生要广阔得多,而与形成发展时期所蕴涵的生命活力相比,古代审美理想在后期阶段上却更多的是排拒吸纳的封闭性。一方面是越来越拓展的主体内外世界,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僵固的审美理想,两者之间的反差是巨大的。然而,古代审美理想的滞后性不仅仅表现在它丧失了适应历史变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还发挥着相反的作用。古代审美理想限制审美感受与真实的生活流变的联系,它以固定的尺度规划审美活动的范围,以僵化的惰性拉开审美体验与生活的距离,凡是它所规划的范围不能容纳的人生现象,都被看作是低下卑污的,凡是那些逼近生活真实的审美感受,都被认为是邪恶变态的。它仍是一片光明,但这光明让人感到窒息,它还是那么高贵,但这高贵却让人感到虚伪;它设立的境界仍然是那样空灵,但同时又是那样的贫乏,它仍具有君临万物的尊严,但同时又是那样的虚弱。这是一个以牺牲审美感受的活力为代价而建立其合法性的审美理想,一个以夷平审美感受的多样性以换取其平衡,以丑恶诽谤人生从而换取纯美的审美理想。古代审美理想的衰落同时就是对人生的疏远,而对人生的疏远就表明了它的历史过程的终结。它的确还有力量来窒息和抑制鲜活的审美感受,但它也在这种负面作用中瓦解。一个新的审美理想,一个与跃动的审美感受共生共存的审美理想,就在这衰落的母体中萌动并将取而代之。显然,现实人生不可能因为古代审美理想与之甚不相合而消失,审美感受不可能因为受到抑制而终止,而鲜活的人性也不可能因为古代结构的僵化而死灭,相反,强有力的方面是现实人生,是个体美感,是自由人性。它们与古代人性结构和审美理想的关系,更多地不是被挤压的规整和被窒息的软弱,而是强烈的抗争、野性的突围和奔涌的超逸;从古代人性结构被毁弃的角度看,我们称之为理性抑制对感性动力的失控。
2.伦理规范对感性意欲的失控 从伦理学的意义上讲,所谓理性对感性的失控,即抽象的伦理教条无力约束情感的扩张。在僵固的古代人性结构中,伦理理性已失去了它调教感性意欲的能力,而感性意欲也失去了它就范于理性调教的驯服。与抽象的伦理理性相对应的,是僵死的感性躯壳,而不是鲜活的感性生命,作为情感冲动,感性随着理性的失控迸发出来,并首先表现为原始能量的释放。在古代人性结构还有能力抑制感性的情况下,感性这一端被当作生物本能受到挤压,而当理性失去这种能力的时候,感性的这一端也只能以生物本能的形式表现出来。沉重的理性曾经使感性驯服温良,而现在,被压抑了数千年的感性从黑暗的底层空前强烈地爆发了。在奔突的感性动力面前,理性的约束不仅失去了往昔的威慑力,而且显得滑稽可笑。感性意欲的突围,其原始能量的释放,这一切使古代人性结构的有序状态无序化了:骚动取代了平衡,浑浊取代了清晰,扩散取代了收敛,狂乱取代了常态。痛心疾首地指责这些现象,气急败坏地贬抑这些现象,对那僵化的人性状态满怀留恋,对那强制的规范大加颂扬等等,这都无助于这些混乱现象的消除,只能表明其顽固的古代立场。当然,我们并非无条件地肯定原始能量的破坏性。在毁弃古代人性结构的意义上,我们充分肯定它那蓬勃的生命活力和冲决牢笼羁绊的野性冲动;在人性结构转化的意义上,我们正视和理解这些现象的不可避免性。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如果仅仅是单纯片面地肯定这些现象,那么这种态度与上面那种古代立场就沟通了。因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在把感性当作生物性这一根本点上,两者是一致的;因而无论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在感性的非主体上,在古代的界限之内两者是共同的。人只要不倒退到动物,感性就只能是人的感性,也就是说感性必须结合着理性。感性在古代人性结构中的状态实际上反映了古代人要求从动物中提升出来的愿望,关键在于,为了求得人与兽的区别,理性是以抑制的方式对待感性的,因而为了求得人与神的区别,感性也只能以排斥的方式对待理性。抑制与排斥在古代人性结构中相反而相成,不过是抑制的方面居优势罢了。因此,感性的扩张如果不能逐渐与理性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那么它最后只能又一次退回到原有的结构关系中。或者说,感性对理性的绝对排斥,最终只能以理性对感性的绝对抑制而告终;完全的生物性的裸露和放纵,其结果只能是自我否定的,或者说它客观上要求理性的介入和整饬。在古代人性结构松动瓦解,主体化人性结构尚未形成的初建时期或过渡阶段,感性的放纵和人性的混乱不可避免,但是这种状态决不是感性变动的目的。如果这种状态是值得肯定的,那么它就必须同时包含着更高的指向,即受到回归主体的理性的指导。我们说,感性意欲的扩张既显示了原始能量的释放,也显示了主体理性的作用和价值。正是因为有后一方面的存在,原始能量的释放才超出了只能重归古代人性结构的循环,才有可能在毁坏古代人性结构的同时转入对主体人性结构的建设,才能作为新感性的有机成分出现在人的真实而完整的存在中。这样看来,理性的力量同时就是感性自身的力量。在主体化人性结构中,感性不是以枯竭为代价顺从理性,也不是以还原本能为代价排斥理性,相反,它以扩张的方式展现理性,以跃动的形态吸纳理性,在主体理性的引导下,感性以奔发的方式创造着人性的新境界。
3.恒定法则对感性体认的失控 感性不再作为那恒定抽象的宇宙法则和理性实体的形象诠释及平面展示,而是投入变动不居的客观世界,并且满足于这个世界的散乱的微观现象,这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对感性的失控。对古代人性结构来说,感性的认识作用不仅无足轻重,而且多余有害;对古代人来说,要把握那个常驻不变的理性实体,超感觉经验的内心冥合较之于依据感性现象的实证,来得更为真实可靠。感性现象只有在尽可能清晰地显示这种理性实体的情形下才有存留的价值,为此,它必须排除其特有的个别性和偶然性,为理性提供一个同样抽象的感性轮廓。但是那个超绝理性实体实际上不过是人的主观虚设,它的超时空的恒定性与感性现象的广阔性、流动性相脱离,它的绝对真理性与感觉经验领悟到的意蕴相矛盾。在古代,需要修正的不是抽象褊狭的理性,而是生动具体的感觉经验;不是理性随感性的变动而作相应的调节,而是变动的感性迁就理性的抽象和恒定。这样一来,理性就限定了感知的范围和方式。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感性的存在和活动因主体性崛起而得到肯定,它这时就不再是理性的注脚,而是把它对客观世界的真实的感觉经验推到了首位,那个超绝的理性所划定的狭小固定的感知范围,也就被突破了,而那些被剔除了的个别偶然的感性现象,也就随之回到了感觉经验。感性不再去供奉永恒真理,它抛弃那些与己毫无关涉的“本质规律”。感性现象的偶然性代替了理性实体的必然性,或者说是个别取代了一般,零散取代了集中,琐碎取代了整一,变易取代了恒定,浑杂取代了明确,一句话,理性的失控导致了感性的失散。这与伦理学意义上的理性失控导致感性的破裂,是一致的。
在古代人性结构解体的意义上,在摆脱对理性的附庸而恢复其独立性的意义上,我们充分肯定感性的破碎化和零散化的倾向,因为这至少是我们从古代感性的愚昧中走出来的起点,至少可以使我们不再感到那抽象理性的压制。但是问题不能绝对化,正如伦理学意义上的感性解放不能没有理性的引导一样,如果我们在肯定感性对古代理性的解构的同时也否定感性对认知深度的要求,那么这种感性实际上是退回到了动物的感觉或直观。动物的直观受本能支配,它的范围狭小而固定,这与主体感性要求尽可能广泛地包容现象世界的倾向相矛盾,而与古代理性所导致的感性蒙昧相通。因此,向现象世界扩散投入的感性如果没有与理性思维重建关联的要求,如果不能产生对普遍性、必然性的专注,那么它就只能退缩回来,停靠在狭小固定的现象的平面上,这时,古代人性结构的认识论模式便会再次出现,那抽象超绝的理性实体就会以凝固来补救感性的迷失,以独断的法则来弥补本应从感性现象中掘除的真理。不仅是理性的毁弃,而且同时是理性的重建,这才是感性投入现象世界的出路。正如主体的目的理性不但不阻止感性意欲的扩张,反而是强化它的动力一样,向主体回归的认知理性不但不限制感觉经验的扩张,反而是它更深广地投入感性世界的保障。实际上,那个别性愈益丰富生动的感性世界,正是理性安顿栖息的场所。
二、恶扩散与丑增加
一方面是僵固的理性实体对感性动力的失控,另一方面是逐渐形成的主体理性对感性动力的强化和引导,这两个方面共同地将一种古代审美意识力求回避的东西推到了现代审美活动面前,这便是丑。对于由古代人性结构制约着的古代审美活动来说,丑在形式上是不规则不平衡,在内容上则是不恒定不统一。丑并不单独地构成审美的形态,也不作为一种成分有机地融入美的形态,它对于古代审美活动的价值只在于对美的反衬,在于以其不和谐的样态突出古代美的规则与稳定。因此我们说古代美是一种封闭的静态的美。然而在古代人性结构解体的情况下,被古代审美意识视为丑的东西,却开始作为美的形态或美的因素出现在审美活动中。丑升入了美的殿堂,但这里的美已经超出了古代人对美的限定。
古代审美意识一方面是混同美与善,另一方面是混同丑与恶。美善混同的结果是美对善的容纳,而丑与恶混同的结果则是美对丑的排斥。恶是不利于生理需求,有害、有损于行为规范和理性约束的东西,它被排除在审美活动之外,只有少量的恶可以经过审美封闭的中和处理而进入审美的领域,恶于是转化为丑。丑是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恶,而恶则是从非审美的角度看丑。古代人在审美活动中有条件、有限量地容纳了丑,这种丑不仅在形式上趋于规则,在内容上趋于恒定,而且作为美的陪衬,丑使美显得更规则、更确定。丑是进入审美活动的恶,古代人可以容纳的丑则是经过中和处理的恶;恶是未进入审美活动的丑,古代审美活动不能容纳的恶则是其无力予以中和处理的丑,因而进入其审美活动的恶则是无损于美的丑。丑与恶相关,但不相同,关键在于是否进入审美活动。古代人性结构受抽象理性的控制,感性单薄脆弱,其审美活动封闭收敛,它无力把可能破坏善的恶转化为可以观照的丑,因此问题不在于恶有无审美价值,而在于审美活动在多大的范围内和怎样的条件下赋予它审美价值,或者说在多大的范围内和怎样的条件下将它转化为美。
审美残缺在古代审美活动中不但具有直接引入善的作用,而且也具有敏感地排斥恶的作用。这两种作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审美转化能力的缺乏:善直接混入美,是因为它无力使占有的意欲转化为观照,而恶难以进入美,也是因为它无力使拒斥的情感转化为观照。恶一旦有条件、有限定地进入古代审美活动,一旦转化为丑,那它就具有较美高得多的审美品位,因为善可以与美相混,而恶却必须经过审美封闭的中和处理,或者说经过一种保护性的处理;恶所引发的非常态的情感体验和冲动,必须有相应的理智形式予以控制,这控制便是审美观照,否则,这种非常态的情感体验和冲动,就会压倒审美所必须的正面体验,丑也只能返回为恶。
古代审美意识的增熵现象,实际上就是恶的扩散和丑的增加。抽象理性的松动瓦解使本来被排斥的恶,开始大量涌入审美活动,而感性动力的强化,也扩大了接触恶的范围,上面所说的理性失控过程中出现的混乱无序的现象,也就是恶扩散和恶入侵的表现。这样,一方面,古代审美意识所追求和营造的那种纯净的境界越来越趋于狭隘和虚伪,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的恶对它的冲击和破坏,它那有限的转恶为丑的能力,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这便是古代审美意识的解体。
恶不等于丑,由恶到丑需要审美的转化。但这并不是说恶只能在古代审美意识中转为丑,或者说被排除在这种转化之外的恶只能是恶。对于古代审美意识来说,熵增大是恶扩散,而对于重构的审美意识来说,熵增大却是丑增加。更具体地说,古代审美活动有丑的介入,现代审美活动也有丑的参与,丑共存于两种审美活动,但两种丑之间却有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既取决于对恶的不同的承受能力,也取决于对恶的不同判别标准。从承受能力的角度看,在判别标准上同为恶的东西,现代审美活动可转恶为丑,而古代审美活动却没有或缺乏这种能力,最多只能作封闭的中和处理,因而承受能力的不同决定了丑在两种审美活动中的范围的大小或量的多少。从判别标准上看,古代审美活动视为恶的东西,对现代审美活动来说则是善,或者相反,古代审美活动视为善的东西,对现代审美活动来说则是恶。因此,被古代审美活动视为美的东西,对现代审美活动来说则属于丑,而被现代审美活动视为美的东西,对古代审美活动来说则属于丑,而更多地是被排斥为恶。这样看来,我们所说的恶扩散和丑增加,就包含了承受能力和判别标准这两个角度。从承受能力的角度看,对古代审美活动是恶扩散,对现代审美活动则是丑增加,因为后者有能力将恶转化为丑;从判别标准的角度看,对古代审美活动是恶扩散,对现代审美活动来说却不是丑增加,而是美扩大,例如个性解放,情欲扩张等等。因此,对古代审美活动来说的恶扩散,对现代审美活动只能是丑增加或美扩大。真正对现代审美活动具有恶扩散意味的,应当说是从判别标准来看在古代审美活动中属于善或美的东西,例如扭曲人性的礼法等。随着古代人性结构和审美意识的解体,这些曾经占有优势地位并被视为美的东西,现在作为敌视主体、歪曲人性的恶散落开来。现代审美活动当然也有能力将这种恶转化为丑,这种转化包含承受能力的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判别标准的方面。综上所述,对于古代审美活动,不论是从承受能力看还是从判别标准看,熵增加都意味着恶扩散,而对于现代审美活动,则不论是从哪个角度看,这种恶扩散都不仅可以转化为丑增加,而且还包含着美扩大。由此看来,熵增加不仅是拆解的力量,而且也是重构的契机,它不仅导致了古代美的消亡,而且标志着另一种美的诞生,这种美不仅包含着由善转化的美,而且广泛地包含着由恶转化的丑。由善转化的美包含着与恶的抗争,由恶转化的丑体现着善的力量。这是美丑浑然一体的美,一种超出了古代人对美的狭隘限定的美,一种显示着人的主体尊严和价值的美,我们称这种美为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