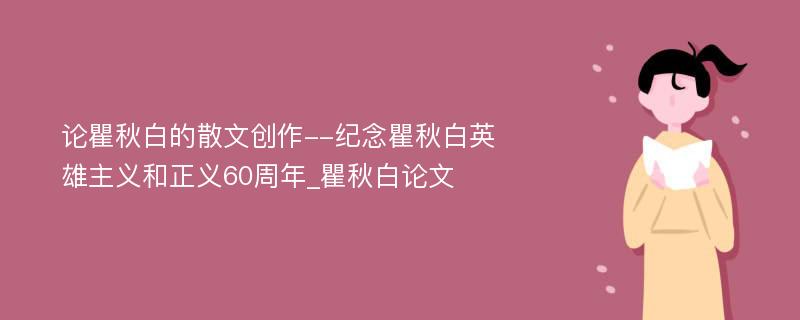
略论瞿秋白的杂文创作——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六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瞿秋白论文,杂文论文,英勇论文,六十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瞿秋白离开我们已经整整60年了。他留下的杂文创作虽然不能说卷帙浩繁,但相对于他短短的一生而言却是相当可观的。他在杂文创作和理论方面的建树,是文学史上无法遗漏的一笔珍贵遗产,这已为世人所公认。不过,事情仍然有它的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仅仅从文学角度考虑,瞿秋白在现代众多杂文作家中很难特别的凸现出来,使他同其他现代作家区别开来的,就是他作为一个“文人”所具有的政治家的身份、他的感觉方式和他进行杂文创作的独特角度。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指出:“当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伸展入文学意识领域后,就产生了一种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他从前者取得了道义承担者的理想形象,从后者取得了这样的认识,即写出的作品就是一种行动。”①瞿秋白正是巴尔特笔下的这种“新型作者”。他在杂文创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所表达的反侵略反独裁的坚定思想,使其杂文创作成为一种政治式写作。
罗兰·巴尔特曾指出:“在写作深处具有一种语言之外的‘环境’,似乎有一种意图的目光存在着。”②杂文背后的“意图的目光”显然来自一种政治的或道德的评判,即杂文必然要赞扬作者所认同的东西,抨击作者所否定的东西。作者认同或否定的准则当然不是存在于文学领域。在文学的写作中,“意图的目光”只能是“语言的激情”,这时的语言就不仅仅是载体,形式也不仅仅是形式,而有着本体的意义。杂文之所以在“社会论文”前加上“文艺性的”,是因为它要宣布对文艺手段的借用,但也只是借用而已,目的还是在于表明作者的褒贬。
以上的认识决定了我们探讨瞿秋白杂文创作的方式:一、研究其题材、内容,从中看出作者在作着什么样的道义承担;二、研究作者是如何用文艺手段帮助表达他的道义承担的,即所谓的作者的杂文技巧或杂文创作的个性;三、在上述两点的基础上,指出作者杂文创作的本质——一种政治式写作。
瞿秋白的杂文创作开始得相当早。1923年,从“赤都”回来才三天,瞿秋白就迫不及待的要“对中国说几句“逆耳之言”,写下了《最低问题——狗彘食人之中国》一文,猛烈地抨击了当时“以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为己任”,“率兽食人”的北洋军阀政府,告诫人们“处于如此严酷的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还只顾坐着静听大家谈最高问题、制宪问题,真是死无葬身之地呵”。急切地呼唤平民、学生、青年发扬“五四”精神,不要再做华盛顿会议的黄梁梦。这是一篇典型的政论性杂文,历来被许多研究者看作是瞿秋白杂文创作的起点。③
刚开始杂文创作的那段时期,正是瞿秋白政治激情日益高涨的时候,此后不久,秋白直接参加了党的活动,以党的理论宣传家的形象被镌刻在中共初期领导者的群像中。他当时的精力主要用于编辑党的报刊,撰写政论文章方面。杂文就成了这些政论文章的补充,其政治目的性是非常明显的。30年代初,瞿秋白被迫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已经失去了发言权,而杂文家的瞿秋白仍然迫切地关心、思考着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并在杂文里敏锐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证之瞿秋白自己的言辞,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种自觉地为政治服务的杂文观:在为鲁迅的杂文辩护时,秋白称赞鲁迅的杂文是战斗的“阜利通”,是“感应的神经,政治的手足”。读着这样的赞语,纸面好象也浮起硝烟的气味,杂文的内容就更不用说了。
瞿秋白的杂文当然比鲁迅带有更多的火药味,因为他是作为政治家而发言的。而鲁迅更多的时候是个思想者,在用词的坚定程度上不如瞿秋白,但瞿秋白的杂文在深刻性上则远远不如鲁迅。对政治家的瞿秋白而言,杂文实际上是把一种政治式的批评推广到了极大的领域,他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共产党的政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表。瞿秋白要揭露的是他们伪善面具下的真面目和现象(或假象掩盖下的本质),《财神还是反财神》④就是这样一篇典型的范文。作者把控制着中国经济命脉的中外大小的“财神菩萨”和广大无产者对立起来,突出地描绘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狰狞面目,指出他们勾结中国地主资本家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是中国灾难的根源,他们依靠“垄断中国的市场,支配中国的经济命脉。”同样,有财神就有反财神。文章热情歌颂了反财神的中国人民“反抗运动”的力量,把这种力量描绘成“从地心里喷出的火山,喷出的万丈火焰”,将“烧掉一切种种腐败龌龊的东西”。这篇杂文所表现的正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写作方式,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合乎逻辑地推演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这几乎是对于现实政治斗争的直接介入。这类文章在瞿秋白的杂文创作中是相当多的,在题为《新英雄》⑤的一组杂文中,他甚至用“阿拉司令”的谑称来相当明显地影射蒋介石。用不着举更多的例子,这类直接面对着现实政治斗争的杂文在秋白杂文中所占比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循着以上这种杂文创作的精神,瞿秋白其他杂文的创作也有着浓郁的政治色彩。这时期的秋白已经不同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时代的秋白了,思想的迷惘、博杂似乎已化为陈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已经广泛地影响着他们这一代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瞿秋白曾称“我是江南第一燕,”其得风气之先自然更不用说。而且,事实上,从20年代中期开始,他长期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首席理论家。作为一个文化人,他的特殊使命就是在“文艺战线”上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众而战斗。这样,瞿秋白就成了罗兰·巴尔特所说的“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而且,对于整个革命的事业来说,他“写出的作品就是一种行动”,是文艺战线上反映出来的政治斗争。譬如,在提倡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瞿秋白就在许多的篇章中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阐发,这些篇章包括《乱弹》、⑥《吉可德的时代》、⑦《反财神》⑧等等。文艺大众化是一个政治色彩非常浓郁的话题,它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并宣布自己是他们的代言人一样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从而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这种斗争还被继续扩大,矛头指向了一些非无产阶级的作家,他们因为没有(或者不打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一套言语方式而遭到攻击,早年对瞿秋白颇有影响的胡适,也被秋白列入了攻击对象之列。《流氓尼德》和《鹦哥儿》⑨等文,在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主权关系同时,也嘲讽了胡适所鼓吹的“人权论”的虚伪本质。这些文章嬉笑怒骂、涉笔成趣,读后余音悠然,耐人咀嚼。
由于政治上的分野,瞿秋白在指向胡适一类知识分子时,的确是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的,政治上的是非自有公论,但秋白并没有就此打“住”,他的杂文攻击的目标又转向了“猫样的诗人”和“红萝卜”(指所谓“自由的知识阶级”,在秋白看来,他们是“红皮白心”的),以及“人道主义文学”的提倡者们。当然,其中最主要的攻击对象是“民族主义文学”。无疑,与“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之争,因而,两者之间的斗争是在文学之内而又超乎文学的。如果说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尚属恰当的话,其他很多的问题却往往被过多地意识形态化了,文学性被放逐到文学的边缘,甚至被驱逐出文学的领地。面对这种情况应该看到,瞿秋白本身是知识分子,但是,当他操起政治的武器后,就变成了一个战斗者。事实上,面对中国现代复杂、动荡的社会状况,知识分子的选择不可能是单一的,对于这种现象应该有一种同情的了解,而不是握住“真理”之剑去乱砍乱劈一气。因为每种巨大的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写作,国民党有国民党的写作(如“民族主义文学”),共产党有共产党的写作(如“普罗文学”),他们为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服务,不可避免地产生斗争。当他们激战方酣时,文学却悄悄退让一边,政治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成为这类文章的“内容”,秋白的杂文也大抵如此。
“社会论文”的性质决定了杂文的内容后,“文艺性的”则给杂文指明了如何写好的出路。在《鲁迅杂感选集·序》中,瞿秋白这样分析杂文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的同情。”⑩其实这不仅仅是杂文的发生论,它还同时是本体论和创作论。我们只说创作,瞿秋白的这段话里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杂文不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说话;二、杂文是文学形式承载的社会(政治)论文。落实到具体的创作中,瞿秋白的杂文抛弃了散文中的描写、铺陈,转而比较明快、直接地发抒己见,所以他的杂文一向被认定为是“明白晓畅的文艺性政论”。同时,瞿秋白向文学借鉴了许多技巧上的长处,以便使杂文更生动,更具有说服、煽动力。
在瞿秋白早年创作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处处留下了作者哲学式的沉思,内心的独白和敏锐的感触,这其中究竟反映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情绪,是难以分清和厘定的,到了杂文时代,情况显然不同了。杂文的目的和功利要求迫使瞿秋白走“明白晓畅”的路子。他对于文学的钟爱只能给他的杂文创作提供一些技巧上的优势,具体的表现如下:
一是为所要阐发的内容寻找合适的体裁、形式,或者说,由于生活、社会中的一点小事而发现微言之中的大义,并就势加以发挥,选用较好的形式来表达。《涴漫的狱中日记》(11)就是这样一篇优秀之作。作者在文章中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假托这是3000年后的文章,把叙述“故事”的时间拉到3000年以后,远距离地观照1923年(写作该文的时间)。并且,还借用了日记的形式,对吴佩孚、曹锟等封建军阀屠杀京汉铁路罢工工人的凶残和罪行进行了揭露、控诉和鞭挞。这样的写法,含义虽然显豁,却比政论式的调子生动、形象,也更易于被读者理解和接受。而且颇有一种悠远深沉的历史感,构思奇崛,笔法老练。再如《曲的解放》(12)是讽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的,文章借用杂剧的形式,揭露国民党政府在“热河战争”中丢掉热河全境,仓惶逃跑,却以“缩短战线”进行狡辩。由于秋白具有音乐方面的修养,故尔他杂文作品的词句音韵铿锵,琅琅上口,使人一见之下而生强烈的印象,所要表现的东西当然也随之凸现出来。总之,社会论文(在瞿秋白这儿可以说是政治论文)而不用社会论文的常规形式,却以日记、杂剧等形式来传达作者的讽剌、控诉、谴责等感情,瞿秋白就是这样使文学和社会政治“联姻”成为杂文,共同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这是瞿秋白杂文创作技巧的一大特点。
二是某些修辞方法的巧妙运用,助成了瞿秋白杂文的说服力,在揭露时也使人更能够一目了然,认清本质。比如作者用了类比的方法,把带有政治色彩的大事与日常的人们习见的小事类比。如在《贼的伎俩》(13)中,作品先写“贼在戏院里偷东西,被人捉住了,贼党忽生急智,狂叫:‘火着了,火着了!’于是大家哄哄地乱跑,拥挤之中,那贼就逃跑了。”这是日常生活中“贼喊捉贼”的一幕,然而作者言在此而意在彼,接着文章点明了所要类比的东西:“英国、日本、美国人杀了人,大叫‘赤化’、‘过激’,也算得个聪明的贼。”在这里,作家不说政治大道理而借用类比的手法却能给人以政治上的影响,可见,类比在其中帮的忙可谓大矣。另外,作者还善于运用对照的手法。杂文家往往比一般人更敏锐,他可以在同一日期的报纸上发现两则看似没有任何关联的消息而觉察到其间的内在问题与联系,这就是通过对照产生的。当然也可能是时间维度上的对照,例如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14)中,作者先指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曾经通行过几年”,这样,“这个口号的历史就十分曲折”。接着作者就把这一口号在不同时期的遭遇逐一进行对照:1921年,“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提出并流传开来;1923年,“有一些人”认为这个口号是为了挑拨“友邦”的恶感;1925年,是“照准”,“以便加以曲解和利用”;……通过这样一系列时间维度上的对照,执政府依赖、投靠帝国主义统治,奴役中国人民的嘴脸就原形毕露了。在瞿秋白的杂文中,无论类比或对照都收到了“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的戏剧性效果。
在瞿秋白杂文的修辞方法中,还有夸张。政治斗争式的杂文写作,决定了瞿秋白的杂文必然有夸张了的讽刺,他对政敌的勾勒也必然地是漫画化的。在涉及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杂文中,瞿秋白对于“五四”以后文学的估价就是夸张的。不可否认,“五四”白话文学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成绩也是明显的,而且是主要的。在秋白笔下,一些缺点(如文言的残留与影响)导致他把“五四”的白话文称为“哑巴文学”之一种,或者更直截了当地称为“新文言”,这种逻辑里含着夸张的思维是非常明显的。在针对“自由知识阶级”而作的讽刺杂文中,瞿秋白指出,他们所宣扬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看似同情弱小,实则助纣为虐。在作了这样的分析后,他更夸张地为“自由知识阶级”画下了一幅漫画肖像——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当然,实际情况要比秋白的分析和描绘来得复杂,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当时秋白杂文中的有些提法是值得推敲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秋白的这种夸张所取得的政治上的效果自然较之客观、公允的分析所取得的效果要好得多,这是毋庸置疑的。
三是象征、隐喻的运用。这里表现出的是瞿秋白诗人般的情怀。瞿秋白在他的杂文中,往往忍不住要对一个抽象的整体发抒议论,而在这种议论中,他不可能作逐一的描述,甚至连漫画化的勾勒也显得难以奏效,于是,瞿秋白采用了一连串的象征。《一种云》(15)就是明显的例证。在这篇短文中,作者描绘了阴云遮蔽下的人间,以此勾画出黑暗的旧中国。文章中的虹、雷电,以及预言了将要出现的霹雳、阳光,无不是一种隐喻。
鲁迅对于瞿秋白杂文的评价是“明白晓畅”、“真有才华”,但“深刻、含蓄不够”。(16)这的确说出了瞿秋白杂文的最大特点。因为政治的鼓动、宣传需要让人看得明白,因而必须“明白晓畅”,所以在语言上总是直陈意见,不留余裕。但又因为“明白晓畅”,因而含蓄不够,一览无余,影响到作品的文学价值。瞿秋白的杂文与鲁迅杂文的最大区别也就在这里。鲁迅是讲究含蓄的,所以他的文章更耐读,更有文学性。
政治式写作是跨文化的世界性现象,在本世纪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都有这种现象。但现代中国的坎坷命运和特殊遭遇使中国的政治式写作表现得更为强烈,更带有阶级论的特点。前面已经说过,瞿秋白就是这样一种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对此,罗兰·巴尔特曾经明确地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政治式写作,即马克思主义的写作和法国大革命的写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式写作来说,“形式的封闭……来自一种象技术词汇一样专门的和可发挥功用的词汇。在这里甚至连隐喻也是被严格编码的。”(17)瞿秋白的杂文写作显然有一套专门的词汇,这一套词汇基本上是政治术语,对应于马克思主义式的阶级分析,如“资产阶级”、“大众文学”,等等。代表的是政治上的分别,这些都是秋白杂文中较高频率使用的专门词汇。至于“隐喻”,我们可以在《一种云》中找到,“一种云”所影射的政治意义简直和直接道出一样的明白。但是,巴尔特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式写作从根源上说,表现为一种知识的语言,它的写作是单义性的,因为它注定要维持一种自然的内聚力。”(18)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在政论还是在杂文中,瞿秋白都不是在发出诗人般的狂叫或呐喊,而是显得按真理、正义所要求的那样讲话。这里的真理、正义的依据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它是发出内聚力的源泉,一切的关于真理、正义的知识都由此产生,并被编码进入杂文文本之中。
还有另外一种形式——法国大革命式写作。它以流血的权利或一种道德辩护做基础,是一种带有鼓动性,而相对忽视知识性的逻辑推理分析的写作形式。实际上,它可能是一种激情的产物,当瞿秋白忍不住露出他诗人的天性时,再加上他的身份,他的杂文写作又具有法国革命式写作的某些特点。如在《匪徒》(19)中,那种对武器的渴望以及得到之后的欣喜,正是一种渴望流血的激情,这种激情和法国大革命式的激情似乎相差也不远。
注释:
①②(17)(18)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写作的零度》,李幼燕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③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9)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6)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20)《瞿秋白文集·序》:载《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