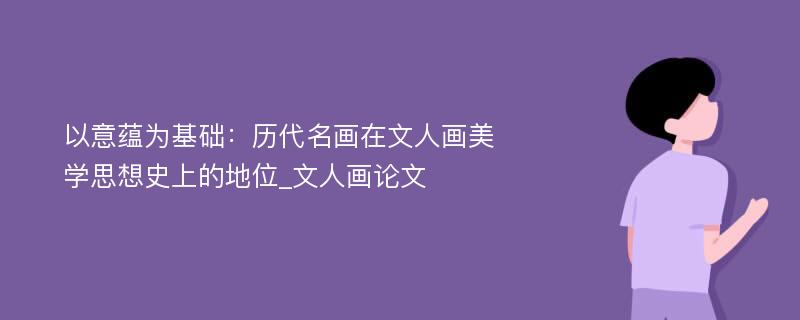
本于立意——《历代名画记》在文人画美学思想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立意论文,史上论文,名画论文,文人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人画”思想的首倡者一般认为是苏轼,原因是他在《跋宋汉杰画山》中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并且对士人画注重写“神”的特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任何一种艺术思想的形成都有一个历史过程,苏轼提出“士人画”之前已经有了“士体”的概念,如南齐谢赫《画品》评刘绍祖的画为“伤于师工,乏其士体”,初唐彦悰评郑法轮的画也说过“不近师匠,全范士体”① 的话。而关于写“神”的理论,则可追溯到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因此,“文人画”思想的形成应该说早于苏轼。在文人画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具有不容忽视的开创之功。从他极力推崇“衣冠贵胄”和“逸士高人”的绘画来看,以及从他所提出的“意存笔先”、“书画同体”等一系列命题来看,张彦远所代表的正是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而他本人也可说是文人画美学思想的先驱。在张彦远的思想中,有很多与后世文人画美学相通的看法,比如他对绘画形上性质的强调,对气韵和骨气的强调,对画家人品的强调,对用笔的强调等等。但最主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即以“自然”为绘画极境的思想,“意存笔先”的思想,推崇天才和妙悟的思想及“书画同体”的思想。
一
中国古代很早以来就把作为事物本性的“自然”视作一种美,而且也把它视作文学艺术创作的最高理想。张彦远虽不是以“自然”为美的首倡者,但就绘画方面来说,他又是第一个如此明确地标榜“自然”的美学家(在张彦远之前,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也讲过“《小列女》……插置丈夫支体,不以自然”的话,但不成其为系统的理论)。
在《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曾多次提到“自然”或“天然”的概念。如在第一卷《叙画之源流》中说:“夫画者……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繇述作。”② 第二卷《论画体工用拓写》中谈到顾恺之的画时说:“遍观众画,唯顾生画古贤得其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在第七卷评嵇宝钧的画并批评姚最重“师范”的观点时说:“彦远以画性所贵天然,何必师范?”此外,更重要的是在他所建构的“画分五等”的评价体系中,“自然”被置于“上品之上”的最高等次,所谓:“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神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贯众妙。”在这种排列中,他明确肯定了“自然”是绘画的最高价值和目标。
张彦远这种把“自然”置于神、妙、能之上的理论,直接影响到“逸品”地位的提升和后世文人画家对“逸品”的推崇。因此徐复观说:“一般人以为在画品中把逸品提在神品之上的是黄休复,而不知实际是张彦远。”③ 宋初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中曾提出画分逸、神、妙、能四格的评价体系,并把唐代朱景玄视为“格外不拘常法”的“逸品”提到了首位,而他对“逸格”的界定就是以“自然”为标准,即所谓:“画之逸格,最其难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在《益州名画录》中,黄休复只列举出一个逸格画家孙位,说他“……性情疏野,襟抱超然。虽好饮酒,未曾沉酩。禅僧道士常与往还……鹰犬之类皆三五笔而成……”黄休复所讲的孙位,与朱景玄视为“逸品”画家的王墨、李灵省、张志和,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隐居不仕;第二,性情疏野,超然物外;第三,好饮酒;第四,不为画而画,故不拘常法,用笔简率④。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曾谈到王墨(默)、张志和的画,但并没有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他的心目中,最符合“自然”标准的是“好酒使气”、“气韵雄壮”、“笔迹磊落”、“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的吴道子。因此张彦远所谓“自然”与朱景玄、黄休复所说的“逸品”或“逸格”似乎并不完全一样,而与后世文人画中那种完全不顾形似的倾向也有相当的距离⑤。但从推崇用笔简洁,反对拘泥于形似和色彩这点来看,以及从他倡导“运墨而五色俱,谓之得意”的水墨画法来看,则他的“自然”概念,又在实质上可以通向“逸品”或“逸格”的概念。因此,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张彦远将“自然”视为绘画最高品格和境界的观点,都事实上影响到后来对“逸品”或“逸格”的推崇,而对“逸品”或“逸格”的推崇,正是文人画美学的核心价值观。清代画家松年《颐园论画》中说:“画工笔墨专工精细,处处到家,此谓之能品……画史心运巧思,纤细精到,栩栩欲活,此谓之神品。此上两等,良工皆能擅长,惟文人墨士所画一种,似到家似不到家,似能画似不能画,一片书卷名贵,或有仙风道骨,此谓之逸品。”在松年看来,文人画也就是逸品画。
张彦远的“自然”,强调的是绘画中形与神(骨气)、形(笔)与意的统一,同时又特别反对离开“神”和“意”的单纯的形似和过分的“谨细”。因此,所谓“自然”,在美学上的一个首要意义就是反对把绘画创作等同于专以摹写事物表面形态为能事的技术性工作。黄休复说逸格的特点是“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所表达的看法与此相同。他所谓“无意于画故得于画”,就是“莫可楷模,出于意表”的意思。此外,他在谈吴道子的画时还说到,“国朝吴道玄古今独步……弯弧挺刃,植柱构梁,不假界笔直尺……守其神,专其一,合造化之功”,又在谈“自然”这一概念时说到,“夫画物特忌形貌彩章,历历俱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这些说法,也与黄休复所论逸格相一致。而反对机械刻板的技巧,反对界笔直尺的界画,也是文人画家的共同主张。而且,所谓“简”、“拙”、“淡”(张彦远所谓“迹简意淡”)等文人画的风格特点,也与这种不专于技巧、推崇自然的审美倾向直接相关。
张彦远的“自然”既是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高度自由的创作心态。而他之推崇“自然”,也还有另一重要意义,那就是强调天才,反对模仿。所谓“画性所贵天然,何必师范”,所谓“无意于画故得于画”,都是这个意思。而且,绘画所要揭示的自然之“道”,所要表出的“气韵”或“骨气”,也都不是单靠模仿就能达到的。直接继承了张彦远思想的宋代画论家郭若虚,就在《图画见闻志》中提出“气韵非师”、“不可以巧密得”、“不可以岁月到”的观点,这个观点也是后来文人画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张彦远虽然没有提出这样的观点,但他的“妙悟自然”的看法,他的“书画之艺皆须意气而成”的看法,以及他重“自然”甚于重“师范”的看法,都事实上与“气韵非师”的观点无异。
二
傅抱石认为文人画的特点之一是“主观重于客观”⑥,这从具体的画面构成而言,就是对神或气韵的重视。而对神或气韵的重视,本质上就是对“意”的重视。
重视“意”的表现甚于重视表现“意”的各种方式——形、言、象等,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和艺术的一贯传统。萧统《文选序》中说:“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在先秦诸子中,老、庄明确表现出反语言的倾向,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老子),又所谓“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庄子)。孔子虽然重视语言的作用,但也仅以表达意思为限,所谓“辞,达而已”。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魏晋玄学家王弼的“得意忘象”和唐代禅宗的“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则更清楚地表现了“立意为本”或“立意为宗”的思想。
受这种思想传统影响,中国美学很早就表现出尚意的倾向。这在深受玄学影响的魏晋南北朝书论(以及诗论和文论)中可以找到大量例证,如西晋成公绥《隶书体》中说:“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又王羲之《自论书》中说:“顷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而在绘画方面,最早将“意”摆在一个显著位置上的,正是张彦远。张彦远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所谓“本于立意”,就是以“意”作为整个创作的出发点和基础,其他一切都是为了服务于“意”的表现。他又说:“张、吴之妙……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可知“意”的重要性又在用笔之上。他认为“笔”可以“不周”,但“意”必须“周”,只有意“周”——即“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对象的“神气”才能得到完整的表现(即其所谓“所以全神气也”)。因此,在骨气、形似、立意、用笔四个方面,最重要的是“立意”。
张彦远在这里事实上对顾恺之重“神”、谢赫重“气韵”及唐代前期重“骨气”(“风骨”)的思想进行了一种主观化的改造。“神”、“气韵”、“骨气”等等,在他看来,都是意中之物,或者说都是“立意”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彦远正是后世文人写意画理论的一个奠基者。虽然他所说的“意”,仍以“神”、“气韵”、“骨气”等等的表现为旨归,并通过用笔和“形”的塑造来加以实现,但他将骨气、形似、用笔统归于“立意”的看法,无疑为文人写意画重视个人情感表现的审美倾向打开了一条通道。
张彦远之后,或者说正是通过张彦远的论述,“意”及“意存笔先”的重要性才在绘画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北宋以后,“意”已成为一个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词汇。如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说:“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彩生于用笔……故爱宾(即张彦远——引者注)称唯王献之能为一笔书,陆探微能为一笔画……笔有朝揖,连绵相属,气脉不断,所以意存笔先,笔周意内,画尽意在,像应神全。”这段话不但直接复述了张彦远的看法,而且还有所发挥,所谓“气韵本乎游心”,正是张彦远“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的进一步凸显。与之同时代的刘道醇在《圣朝名画评》中也非常重视“意”的概念,如其评叶仁遇“好写流俗,能剽真意”,评李成“唯意所到,宗师造化”,评范宽“对景造意,不取华饰”,评陈用志“虽放旷,每得自然之意”,等等。而且,他还明确提出了“写意”的概念,在其评五代画家徐熙的花鸟画时说:“写意出古人之外,自造乎妙,尤工设色,绝有生意。”除郭若虚、刘道醇之外,欧阳修也是尚“意”的代表人物,沈括《梦溪笔谈》曾引其《盘车图》诗说:“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在宋代比较典型的文人画家当中,苏轼和米芾论画也多有尚“意”的言论。苏轼论画既讲“理”也讲“意”,他在《书吴道子画后》中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而米芾论画,则专以“意”为主。在其所著《画史》一书中,“意”是一个核心范畴,如其评董源画山水“岚色郁苍,枝干劲挺,成有生意……峰顶不工,绝涧危径,幽壑荒迥,率多真意”,评赵大年画“汀渚水鸟,有江湖意”,评陈常画山水“以飞白笔作树石,有清逸意”,等等。
宋以后,“意存笔先”或“意在笔先”的命题已成不易之论,其在理论上的地位,可与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谢赫的“气韵生动”相仿佛。而且在有些论者的笔下,“意”的地位甚至高于“神”或“气韵”,如清代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中说的:“意之为用大矣哉!非独绘事然也。普济万化,一意耳。夫意先天地而生,在易为几,万变由是乎生,在画为神,万象由是乎出……物无斯意,则无生气……画无斯意,则无神气。”在布颜图看来,“意”既是宇宙和生命的本体,也是绘画的本体。而且,所谓“传神”与“写意”,事实上也就成了一回事,如清代盛大士《溪山卧游录》中所说的:“意在笔先,神超象外。”在盛大士的这一说法当中,“意在笔先”与“神超象外”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必然结果。
如前所述,文人画不专主于形似。不专主于形似,就是更重视神似。而重视神似,其落脚点就在于写“意”。如明代画家祝允明《枝山题画花果》中说的:“绘事不难于写形而难于得意。”“得意”、“写意”,正是文人画最基本的价值取向,而这种思想的直接来源,就是张彦远“意存笔先”、“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的理论。
张彦远以意为本的理论,一方面是要求画家要有一种超然的审美态度,另一方面是要求深入对象的“内部”并对其进行整体的把握。因此,以意为本,也就是要超出形似和技巧的局限,以表现对象的神气(或“本质”)作为绘画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对象的“形”进行高度简化的处理。张彦远说:“不患不了,而患于了。”“形”的描绘过于谨细(“了”),反而有损于神气的完整,因此,倒不如“意周”而“笔不周”。
从这种理论来看,文人画的简、拙、淡等特点的形成,其实也与强调“立意”和“写意”的看法有关。米芾在《画史》中谈到他自己的山水画创作时曾说:“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尘格者,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所谓“意似”,就是一种简略的画法。
在张彦远以意为本的思想中,同时还包括了将“传神”与“写意”合二为一的看法,或者说,包括了将“神”、“气韵”、“骨气”等等与画家个人的艺术想象合二为一的看法⑦。这种看法,可以说对中国绘画越来越倾向于写意,越来越倾向于个性情感的表现——用傅抱石的话说,就是越来越“主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若虚的“气韵本乎游心”,已经很明确地将“气韵”同画家的艺术想象统一起来了。而晚明唐志契的一段话则更清楚地说明了“传神”与“写意”其实是一回事,他说:“凡画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得其性情,则得山环抱起伏之势,如坐如跳,如俯仰,如挂脚。自然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而落笔不生软矣。亦得涛浪潆洄之势,如绮如云,如奔如怒,如鬼面。自然水情即我情,水性即我性,而落笔不板呆矣。”⑧ 唐志契所谓“性情”,于对象方面而言就是“神”或“气韵”,于主体方面而言就是“意”。从这个意义上说,绘画是不可能离开主体的情感和想象去单独表现所谓“神”或“气韵”的。“神”或“气韵”的表现必须依赖于主体的情感和想象。
从张彦远强调形、神(骨气)、意的统一的角度来说,他的以意为本的思想,更进一步说是对中国绘画从形的描摹转向意境的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绘画所要表现的,既非单纯的事物,也非单纯的心灵,而是建立在心与物相统一的基础上并进而以形与神、象与意相统一的面目出现的、完整的生命形象或意象。这个形象或意象既是客观的(就其表现了对象的本质特征来说),也是主观的(就其同样表现了主体的情感和想象来说)。这种既客观又主观、既主观又客观的境界,正是中国绘画的最高境界。正如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中对“画”所下的定义那样,中国绘画所谋求的,其实是心与物的高度统一。因此他一方面说:“夫画者,形天地万物者也。”而另一方面又说:“夫画者,从于心者也。”这种由心与物的高度统一而创造出来的、处在“有意与无意之间”、“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境界,就是中国画家所向往的高度自由、并且高度自然的境界。
三
张彦远以意为本的理论,同时也强调了画家在创作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尽管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非常重视画家的师承关系,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崇古倾向,但他反对模仿。他所谓“画性所贵天然,何必师范”,就是反对模仿的明证。同时他在论述谢赫的“六法”时也说:“至于传模移写,乃画家末事。”即认为模仿前人的绘画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也谈不上是真正的创造。
宗白华认为,张彦远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认为“艺术是天生的,所以从事的人贵乎天才,贵乎创造,贵乎写实,贵乎气韵,而最所不要的乃是谨细”⑨。张彦远对于天才是非常推崇的,比如他在评论顾恺之的时候说:“自古论画者,以顾生之迹天然绝伦,评者不敢一二。”在评论吴道子的时候说:“吴道玄者,天付劲毫,幼抱神奥。”顾恺之是被他列为“上品上”即符合“自然”标准的画家,吴道子是他在书中谈得最多、并且被尊为“画圣”的画家,自然也是他所谓“上品上”的画家。而“上品上”的画家,也可以说就是最优秀的天才画家。
此外,他在推崇天才的同时,还非常推崇“灵感”、“想象”和“巧慧”,如“仲达画佛之妙,颇有灵感”(评曹仲达),“想象风采,时称精妙”(评郎余令),“幼有巧慧,聪悟博学”(评戴逵)。在张彦远看来,绘画并不是普通的技艺,因此它也不能通过模仿或按照某种既定的法则来完成。所以他说:“书画之艺皆须意气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
“灵感”、“想象”、“巧慧”、“意气”,是他所谓“妙悟自然”的不同说法。“妙悟”既非理性的思考,也非普通的感官感觉,而是对事物本质的直觉。由于张彦远认为绘画不能只是描写对象的形,而且要表现对象的神或骨气,并通过表现对象的神或骨气,进一步表现宇宙万物“幽微”、“玄妙”的“道”、“理”或“天机”,而“道”、“理”或“天机”等等,是不能通过寻常的理性思考和感官感觉来达到的,因此,他认为只能通过“妙悟”来予以实现。
中国绘画美学中所谓“道”、“理”,并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可以用逻辑语言予以描述和表达的本质和规律,而是一种微妙难言的、自由的生命意趣(生生之道、生生之理),而所谓“意”,也不是逻辑语言所指称的抽象概念,因此它不可能通过理性去把握。同时,“道”、“理”、“意”虽要通过有形的事物来表现,但它们本身并不是任何有形之物,因此它们也不能通过一般的感官感觉去把握。既然如此,它就只能依赖于想象和妙悟。而这也正是艺术天才的具体表现。张彦远之前,这方面的论述事实上已经很多,顾恺之说的“迁想妙得”,宗炳说的“应目会心”、“应会感神”,释彦悰说的“灵心自悟”,符载说的“夫道精艺极,当得之于元悟”,都是指的妙悟。在这个意义上说,张彦远只是将这一种看法更清楚地表示出来了。
张彦远之后,郭若虚提出“气韵非师”的看法,其实质也是认为“气韵”不能通过既定的法则和惯常的理性思考去把握。但不能通过这些东西去把握,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把握。他认为这要靠高尚的人品和个人的灵性。在《图画见闻志》中,郭若虚说:“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又说气韵生动虽不可学,但可“默契神会”,“发之于情思”,并且认为气韵的获得“系乎得自天机,出于灵府……本自心源”。他所谓“神会”、“情思”、“天机”、“灵府”、“心源”,其实也都可以说是妙悟。
“妙悟自然”和“气韵非师”是中国绘画美学的一个重要看法,同时也是或主要是文人画美学的一个重要看法。元代刘因《田景延写真诗序》中说:“夫画,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与天者,必至于形似之极,而后可以心会焉。”“心会”即妙悟。而文人画的倡导者董其昌,则在其所著《画旨》的一开头就说:“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他所谓“生而知之,自然天授”,并非真的是指天生的禀赋。他所谓“不可学”,更多的是指不能通过技巧的学习来获得,而是要通过体验和直觉来获得。所以他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邱壑内营,成立郛郭,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
张彦远和文人画理论家的强调天才和妙悟,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美学意义就是指:在绘画创作中,要破除形似和技法的束缚,专注于事物内在精神的领悟和表现。而另一个意义则在于:在绘画创作中,还必须有独特的个人体验和感受,并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趣。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中说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以及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中说的“我自发我之肺腑”,都是这个意思。
四
在《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即“书画同体”。这个命题也是支撑宋以后文人画美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命题。
张彦远“书画同体”的命题,和与之相关的“书画用笔同法”、“工画者多善书”、“画之臻妙,亦犹于书”等命题,在宋代即已被诸多理论家所接受。北宋画家郭熙的《林泉高致·画诀》中说:“世之人多谓善书者,往往善画,盖由其转腕用笔之不滞也。”又郭思《林泉高致·序》中说:“书,画之流也……今之古文篆籀禽鸟,皆由象形之体,即象形画之法也。”郭熙父子的这个观点,不过是转述张彦远“工画者多善书”、“书画同体”的看法。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叙制作楷模》中曾谈到衣纹、林木的画法,认为:“画衣纹林木,用笔全类于书。”这个看法不仅包括了张彦远“书画用笔同法”的意思,而且竟有用书法的笔法来画画的想法。这种想法是对张彦远“书画同体”思想的进一步发挥。被董其昌列入文人画家系列的米芾,就在其所著《画史》中谈到用书法的笔法来画画的实例,如:“章友直,字伯益,善画龟蛇,以篆笔画,亦有意。”又如:“江南陈常以飞白作树石,有清逸意。人物不工,折枝花亦以逸笔一抹为枝,以色乱点,画欲夺造化,本朝妙工也。”米芾认为章友直、陈常以书入画的画法是很有意趣的。尤其是陈常的画,画法虽不取工细,却能欲夺造化并富有清逸意(不俗、超然的意趣或意境),而所谓“不工”,所谓“逸笔”,所谓“有意”,所谓“清”和“逸”,正是典型的文人画风格。
相比于宋朝,元朝文人画的发展更趋成熟,而其引书入画的倾向也更明显。元代赵孟頫在其《秀石疏林图卷》的题款上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在这首倡导书画一律的诗当中,张彦远的“书画同体”论被直接拿来作引书入画的证据。而在赵孟頫之后,这种论调几成为文人画家们的一个创作纲领。如元代画竹名家柯九思的《画竹谱》中说:“尝自谓写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
明清以后,关于书画同体或同源,以及绘画必具有书法笔意的看法可谓俯拾即是。董其昌说:“善书必能善画,善画必能善书,其实一事耳。”⑩ 又说:“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11) 在董其昌看来,以书法的笔法来从事绘画,是文人画之为文人画的必要条件。
这种以书入画的表现方法,最初的理论依据就是张彦远“书画同体”的观点。虽然张彦远并没有明确指出要以书法的笔法来进行绘画的创作,但他已明确提出“书画用笔同法”、“工画者多善书”的观点,并且非常详细地论述了书画同体的历史和书画相通的可能,而且还列举了顾恺之、张僧繇、陆探微、吴道子等人在绘画中已经融合了书法用笔的事实。
从艺术特征上看,绘画与书法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也曾说过“书画道殊,不可浑诘”的话。早期的书法虽带有象形的特征,但最终却是走向了抽象,而中国绘画虽然越来越写意,却并未完全脱离开形似。哪怕是文人画家们所说的“不似之似”,比起书法的抽象来说,也要具象得多。因此完全按书法的要求来画画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中国绘画与书法尽管在造型以至功能上都有所区别,但它们使用的是相同的工具,而且也都以线条作为最基本的造型手段。因此,绘画与书法在用笔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如由力度和形态所带来的美感),并且有相通的可能。而且,文人画家们对张彦远思想的引申,事实上也对文人画风的形成,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首先,书法向绘画的渗透,是绘画走向写意的重要条件。书法是一种抽象的表现艺术,“图形”、“存形”、“象物”都不是它的职能,而抒情、写意则是它的主要长处。因此书法向绘画的渗透,一方面使绘画摆脱形似的束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使绘画在“意”或情感的表现上更加自由,即如元代汤垕《画论》中所说:“画梅谓之写梅,画竹谓之写竹,画兰谓之写兰,何哉?盖花卉之至清,画者当以意写之,不在形似耳。”
其次,由于摆脱了形似的束缚,这也就为文人画家们追求所谓“笔墨趣味”,或赋予笔墨以独立的审美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如清代盛大士《溪山卧游录》中说的:“画有以丘壑胜者,有以笔墨胜者,胜于丘壑为作家,胜于笔墨为士气。”文人画家们之所以可能玩味于笔墨,关键就在于摆脱了形似的束缚,而摆脱了形似的束缚,也就等于摆脱了外物的束缚。这种超出外物或形似局限的笔墨意趣,是他们所谓“士气”或“逸气”的表征。
第三,书法向绘画的渗透,同时也是文人画在艺术风格和审美品格上追求“简”和“雅”(“书卷气”、“卷轴气”)的一种体现。清代画家王学浩说:“王耕烟云:‘有人问如何是士大夫画?曰:只一“写”字尽之’此语最为中肯。字要写,不要描,画亦如之。一入描画,便为俗工矣。”(12) “描”即意味着刻板精细,而“写”则倾向于简洁生动。同时,正如文人画强调画与诗的相互融通对其意境创造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样,画与书(包括以书为基础的印)的相互融通,也对深化其文化内涵产生了同样的影响。而诗、书、画、印四者的结合,加上中国哲学宇宙观所带来的超然的审美意味,正是文人画最佳的艺术构成。
结语
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作为一部集大成的绘画史论著作,可以说是唐代唯一的一部在美学思想上有独特贡献的、自成体系的著作。张彦远的美学思想,不但继承了顾恺之、宗炳、王微、谢赫、彦悰、李嗣真、张怀瓘等人重“神”、“气韵”、“风骨”或“骨气”的思想,而且进一步吸收、发挥了唐代后期书法、绘画、诗歌美学中越来越重视“意”或“意境”的表达的思想。就整个中国绘画美学思想的发展来看,张彦远的美学思想可以说是中国绘画从重“神”、“气韵”、“风骨”转向重“意”或“意境”的一个转折点。在其思想体系的构成中,“意”是一个最核心的概念。他所谓“自然”、“妙悟”,所谓“书画用笔同法”等等,都是围绕绘画“本于立意”的思想来展开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对宋代以后以写“意”为其主要特征的文人画美学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他推崇“自然”、标榜“天才”和“妙悟”和主张书画用笔意趣相通的思想,则为文人绘画最终占据中国画坛主流铺平了道路。因此,就其历史地位来说,张彦远应当说是中国古代文人绘画美学思想的重要的开创者之一。
注释:
① 谢赫、彦悰的话,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138、160页。
②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1页。本文所引张彦远的话皆出是书,兹不一一注明。
③ 徐复观:《论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页。
④ 关于王墨、李灵省、张志和的评论,参见朱景玄《唐朝名画录》,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朱景玄论“逸品”,也是强调简洁和“自然”,如其谓“李灵省……画山水、竹树,皆一点一抹便得其象,物势皆出自然”。
⑤ 邓椿《画继》卷九中说:“画之逸格,至孙位极矣,后人往往益为狂肆。”(邓椿《画继》,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118页)
⑥ 参见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⑦ 张彦远之前,顾恺之的“迁想妙得”和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都已强调了主体心理的作用。
⑧ 唐志契:《绘事微言》,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⑨ 宗白华:《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1期。
⑩(11)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艺林名著丛刊》,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43页,第35页。
(12) 王学浩:《山南论画》,王伯敏、任道斌主编《画学集成》(明清卷),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641页。
标签:文人画论文; 张彦远论文; 历代名画记论文; 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写意绘画论文; 图画见闻志论文; 顾恺之论文; 美术论文; 书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