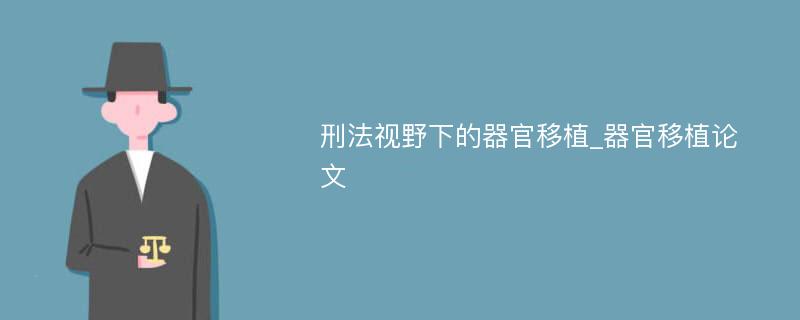
刑法视野下的器官移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器官移植论文,刑法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624 文献标识码:A
器官移植是20世纪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是人类改变传统的药物治疗方式而使伤病器官恢复功能的一种新型医疗模式,它给医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基因治疗、人工生殖和器官移植三大领域中,器官移植的医学和法律实践最为成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进展。”[1] 但是,因器官移植而引发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也最为复杂,有关刑事法律方面的问题自然也在其中。
一、器官移植及其对刑法带来的挑战
器官移植(organ transplantation)是指摘取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器官(也包括某些组织)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内以代替病损器官(或组织)的过程。在器官移植中,提供器官的一方被称为供体(或供者),而接受器官的一方则被称为受体(或受者)。在医学上,根据供体器官来源的不同,可以将器官移植分为四种:一是异种移植,也称跨种移植,就是将一种生物的器官移植到另外一种生物上,如将猴子的心脏移植到狗的身体内、将狒狒的肾脏移植到人体内等;二是同种自体移植,简称自体移植,即将同一生物个体某一部位的器官移植到该个体的另一部位上,如将人头部的皮肤移植到胸部;三是同种异体移植,即将同一种生物某一个体的器官移植到该种生物中的另外一个个体身上,如将张三的心脏移植到李四身上;四是人造机械器官移植,即用人造的机械器官作为供体器官,将其移植到受者身上。当前,“由于自体移植和异种移植不涉及供体权利的转移,一般不发生法律问题”[2],发生刑事责任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小。人造机械器官移植则由于更多地关涉供者的财产权利而较少涉及其人身权利,因而也极少产生刑事责任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器官移植主要是指同种异体移植。
(一)器官移植的历史及现状
人体器官移植一直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这一点,无论是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还是在我国古代的神话故事中,都不难得到印证。早在公元前600年,古印度就有外科医师用从病人本人手臂上取下的皮肤来重整鼻子的传说,这种植皮术实际上是一种自体组织移植技术,它及此后的异体组织移植术成为今天异体器官移植手术的先驱。而我国也在约公元前430年就有了神医扁鹊为两人互换心脏以治病的传说。公元1世纪初,西方还流传有圣徒Cosmos和Domian把一名埃塞俄比亚死人的腿移植到一个白人身上的说法。但上述传说未能得到科学的印证,它们更多地是反映了人类关于器官移植的美好愿望。近代移植实验开始于18世纪后期,有实验外科之父之称的Hunter医生在人身上成功地替换了前磨牙[3]。但器官移植真正得到认真研究并被实用化则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1902年,法国科学家卡雷尔(A·Carrl)和古斯里(C·Guthrie)发明了血管缝合技术,奠定了器官移植临床应用的基础。1936年,前苏联科学家沃罗诺伊(Voronoy)为一位尿毒症患者进行了最早的同种肾移植,但由于对免疫排斥机理一无所知而未采取任何免疫抑制措施,使得病人在术后仅存活了48小时即死去。之后,先后又有多位科学家进行了包括肾移植、皮肤移植等在内的多起器官移植,但均因在今天看起来十分清楚的免疫排斥问题而未能获得成功,“移植外科学因此而步入了黑暗的缓慢发展时期”[4]。
1940年代,皮特·梅达尔(Peter Medawar)在其同事弗兰克·伯内特(Sir Frank Burnet)的帮助下,解释了免疫系统发现及排斥外来组织的原理,为移植免疫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科学家们找到了以往器官移植屡屡失败的根源所在。在此基础上,1954年,美国科学家莫里(Murray)在一对双胞胎之间成功地实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例有长期存活功能的肾移植手术,开启了人类器官移植的先河。1955年,修穆(Hume)在肾移植手术中使用了类固醇激素,使同种肾移植获得了新的进展。1959年,莫里和法国科学家哈姆伯格(Hamburger)各自采用给予肾脏移植的患者全身大剂量放射线照射以抑制异体排斥反应的方法,使非同卵双胞胎间的肾移植手术也获得成功。1960年代之后,医学界又陆续开展了包括肝移植、肺移植、心脏移植、小肠移植、胰腺移植等在内的各种同种器官移植。1978年,新一代免疫抑制剂环孢素问世,使临床同种器官移植的效果迅速提高。1990年代以后,移植学出现突破性进展,存活率、移植数目、开展器官移植的单位数量等都大幅增长,器官移植正日益成为常规手术。现在,器官移植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医疗手段,在各国都得到了普遍应用。
(二)器官移植对现代刑法带来的挑战
器官移植技术的日益成熟及其在医疗临床上的广泛应用,为身患器质性疾病的病人恢复健康乃至延长生命带来了福音。器官移植极大地改进了传统的药物治疗方法,大大提高了病体的存活率与个体生命的质量,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重获健康的希望。据了解,目前全球每年都有近7万人接受器官移植,许多人的生命在凋零之际因此而得以重生并再现生命的光彩[5]。但毋庸置疑,该技术的发展也引发了诸多伦理与法律问题,对当代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带来了挑战,其中包括对现代刑法理论与实践的挑战。器官移植中的很多问题都对传统刑法理论与制度带来了挑战。例如,在活体器官移植中,医生摘取供体器官的行为是否构成伤害罪?被害人的承诺可否作为免除医生承担刑事责任的理由?在尸体器官移植中,死者家属违背死者意愿而出卖其尸体器官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医生在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擅自利用他人尸体器官用于移植是否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罪”?……这些都是器官移植给现代刑事责任理论与制度带来的挑战。
器官移植给现代刑法理论与制度所带来的挑战显然远不止以上这些,因供体器官来源而引发的各类问题就是鲜明的例子。器官移植技术在其应用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即供体器官严重缺乏。由于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相对较少而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又极其众多,导致供体器官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器官移植发展的实际需要,很多患者只能在等待合适器官的漫长过程中痛苦地死去。在这种背景下,医疗实践中经常会因供体器官来源而引发一些刑事案件,如1998年发生在北京的“眼球丢失案”、2006年初发生在沈阳的“窃取骨髓案”以及2006年底发生在河北的“行唐案件”等。在罪刑法定已成为我国基本刑事司法理念的背景下,这些案件的发生及其处理结果都已对刑法正义带来了挑战。此外,围绕供体器官来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实践中也经常会发生买卖人体器官的情况,尽管国际社会普遍将这类行为视为犯罪而要求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理论界关于刑事责任制度应否介入调整这种行为的争论却从来都未停息过。显然,如何从法理上阐释人体器官商业化行为的犯罪性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刑法理论与制度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国内外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理论
器官移植是一种特殊的医疗行为,与传统医疗行为存在明显的区别。传统医疗行为的伦理基础是救治患者,这丝毫不涉及第三人的生命利益,而器官移植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由于跨种器官移植技术和人造机械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还远远无法适应医疗临床的实际需要,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器官移植都需要通过牺牲或损害一个个体的利益去挽救另外一个个体的生命,这就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的权益损害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器官移植自诞生之日起便饱受各国学者的争议,关于刑事责任方面的争论也在其中。当前,各国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医生摘取供体器官的正当化依据与不构成犯罪的条件
关于医生摘取供体器官行为的正当化依据,国外学者通常都将之归结为供体的同意,但在供体的同意能否单独作为医生摘取供体器官行为之正当化事由上则存在争论。法律伦理说认为,即使被害人对侵害其利益的行为表示同意,也要考虑根据该同意而实施的行为是不是为社会伦理所允许,同意而使行为正当化是社会上相当罕见的场合(社会相当性)[6]。因此,假如供体同意医生摘取其器官用于移植没有完全建立在现有生命伦理要求之上,则单纯的供体同意本身并不能作为医生摘取供体器官行为之正当化依据。例如,如果医生摘取器官的行为是建立在供者无效同意的基础之上(如患者的捐献可能会损及其生命),则这种行为并不免除其犯罪性。法益保护说则认为,如果被害人同意侵害自己的利益,则刑法所要保护的利益就不存在,或者说是实现了自己决定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同意的行为原则上就应当是正当行为。“刑法将保护他人权益作为任务,在他人权益遭到侵害的场合,允许国家发动刑罚权进行干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侵害他人是违反他人的意思的。因此,即便说他人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但如果该侵害不违反他人的意思的话,刑法就可以从该任务中解脱出来,没有必要将该侵害行为评价为犯罪。”[6]59 以此为立足点,该说认为,在供体同意医生摘取其器官用于移植的场合,客观上并不存在法益侵害,既然无法益侵害,该行为也就属于正当行为。
关于医生摘取供体器官而致其受损害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国外学者的观点比较一致,即都认为在医生未取得他人有效授权或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从供体体内摘取器官的行为构成犯罪。相反,在符合一定条件下摘取供体器官的行为则应免除犯罪性。杰拉德·德沃金(Gerald Dworkin)在1970年出版的《英格兰有关器官移植的法律》一书中提出过合法摘取器官的三个条件:(1)供者须给予了自由且知情的同意;(2)手术须为治疗性的目的,且为了患者的利益而进行;(3)须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7]。在德日等国,刑法理论上的通说认为,在下列条件下,为移植而摘取活体器官的行为不构成犯罪:(1)必须向移植器官供者充分说明,摘取器官可能对其身体健康带来危险性;(2)必须有移植器官供者基于真实意愿的承诺,即真诚同意捐献器官;(3)必须考虑移植器官供者自身的健康状况,只有在摘取器官对其不会有危险的条件下才能实行[8]。反之,如果采用欺骗、胁迫手段使移植器官供者作出承诺,或者没有供者的承诺而摘取其器官,或者在对移植器官供者有重大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摘取其器官,则有可能构成犯罪。在1914年美国纽约州地方法院审理的Schloendorff v Society of New York Hospital一案中,Benjamin Nathan Cardozo法官就指出:“所有具有健全精神状态的成年人,都有决定对自己身体作如何处置的权利。医生如不经患者同意而对其进行手术,则构成伤害罪,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9] 英国学者厄莱斯代尔·麦克林认为,双方的同意是器官移植有效而不构成犯罪的前提,然而,如果供体的同意可能会导致其死亡,则该同意就属于无效同意,此时医生就可能因为摘除供体的器官而承担刑事责任,除非该同意是出于供体的最佳利益考虑[10]。
笔者以为,知情同意是医生摘取活体器官进行器官移植得以正当化的重要理论支柱。然而,知情同意本身并不足以成为医生摘取活体器官的合法性依据,因为站在生命伦理学的立场上来考量,供体的同意能否成为摘取活体器官的合法性依据还要看该同意是否具备足够的合理性,即要求行为为法律和道德允许;行为对社会和本人有益;行为的实施遵循一定的理性规则[11]。否则,即便是在供体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摘取活体器官也依旧难免具有违法性乃至犯罪性。因此,医生摘取活体器官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才得以免除刑事责任:(1)摘取器官须以移植为目的;(2)器官的摘取具有医学上的适应性;(3)在供者具有意思自治能力、能够自由做出捐献意愿的前提下,摘取器官须建立在供体充分知情同意的基础之上,“任何违背知情同意原则的行为,都应受到刑事处罚”[1]289;(4)器官的摘取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及医疗操作常规,不会对供者今后的生活造成严重不良影响;(5)供者器官的捐献以无偿为条件,且不违反生命伦理。
(二)人体器官法律属性的界定
人体器官法律属性的界定,亦即人体器官是否为物的问题,是刑法学考察人体器官移植所必须予以正视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人体器官的法律定性将直接决定某些人体器官移植行为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以偷取人体器官用于移植为例,假如我们将人体器官界定为一种具有财产性的物,则偷取器官的行为显然将构成盗窃罪,但假如我们将人体器官定性为一种具有人格性的实体,则偷取人体器官的行为显然就不构成盗窃罪。而在强摘他人器官、侵害植入体内的器官等情形下,显然也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关于人体器官的性质,法学理论界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一是“物的范畴说”,认为人体器官或组织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物。王利明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就采纳了这种意见,该《建议稿》第128条第2款规定:“自然人的器官、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以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为限,可以作为物”[12]。二是“人物两分说”,该说认为,当人体器官未与人体相分离时应属于人的范畴,而当其与人体发生分离后则成为物。台湾学者史尚宽就认为,活人的身体,不得作为法律上的物,因为法律是以人为权利主体的,若以其构成部分(即身体的全部或一部分)作为权利的标的,则违背承认人格的根本观念。但人身之一部分自然地由身体分离之后,其部分已非人身,成为外界之物,当然应为法律上之物,而得为权利的标的。然其部分最初所有权,属于分离以前所属之人,可依照权利人的意思进行处分[12]。三是“人的范畴说”,认为人体器官并非法律上的物,而属于人的范畴,无论其是否与主体的人身相分离。因为人体器官作为自然人的人身组成部分,不具有财产性,即不能以经济价值来衡量。以此为基点,人体器官应当是身体权的标的而非财产权的标的。而作为自然人所依法享有的重要人格权之一,身体权的基本涵义和要求也就是要保持自然人身体完整性,任何破坏自然人身体完整性的行为均被认为构成对自然人身体权的侵害[13]。四是“受限定人的范畴说”,该说认为,自然人的人体器官非法律意义上的物,但是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有限的处分权。因为从法理上说,法律意义上的物是指法律关系主体支配的、在生产上和生活上所需要的客观实体[14]。它应当以非人身性为前提,一切具有人身属性的实体均不应作为法律意义上的物。人体器官作为人身体的组成部分,具有自然性和人格性(人身性)两种属性:首先,就其自然性来说,拥有器官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动物所必然具有的生理特征和自然现象之一。从人体器官的产生来看,它是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而非人为创造出来的。换言之,人体器官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属性。基于人体器官的这种自然属性,在不损害自然人生命健康的前提下,将人体器官与其身体相分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医疗技术上也是可行的。其次,就人体器官的人格性(人身性)而言,人体器官是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自然人的身体构成部分,而自然人具有人格属性,这种人格属性集中体现为社会对自然人之存在及其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承认。这种社会承认既不会伴着自然人死亡而毁灭,也不会由于人体器官从自然人的身体中被剥离出来而消亡。相反,在自然人的身体器官被捐献或该主体死亡之后,这种承认依旧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存在。人类社会已形成的传统的、对寄生于人体及其器官之上的生命健康的尊重和保护以及对人之遗体的敬畏与禁忌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明。正是人体器官的人格(人身)属性决定了自然人在自由支配其人体器官时必然要受到道德、伦理以及法律等方面的限制。
在上述诸观点中,笔者赞同最后一种主张。关于人体器官的本质及其法律属性,笔者认为,人体器官是一种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人身属性的客观实体,它既非法律意义上的人,也非法律意义上的物,而是一种应当受到法律特殊保护的“准物”。自然属性和人身属性是人体器官的两个基本属性,而人体器官的这两个属性决定了自然人对其人体器官具有有限的处分权利,其理由在于:人体器官作为一种“准物”,不是也不可能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只可能是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存在,这就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处分人体器官提供了基本的法理依据。但是,人体器官虽然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但由于其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构成部分所形成和具有的人格特质并不会随着其与原主体的脱离而立刻消失,相反,“这种人格特质在被捐献的人体器官被植入另一主体身体之前依旧存在,并成为人体器官区别于法律上的物的一个重要方面”[15]。这就决定了任何对这种“准物”的处分行为都必须要受一定的限制,而任何侵害这种“准物”的行为也都不可能完全依照财产法尤其是物权法的规则来处理。具体到刑法领域,人体器官或组织的这种特殊“准物”性质,决定了任何侵害这种“准物”的行为都不宜直接依照《刑法》关于财产犯罪(如盗窃罪、抢劫罪等)的规定来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三)医生摘取死者尸体器官之正当性
关于医生摘取尸体器官用于移植的正当性,绝大多数学者都是立足于利益衡量的立场去加以论证的。学者们大多认为,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属于最高利益,因此,相对于生者的利益而言,死者的利益只能处于次要地位。摘取尸体器官进行移植尽管对死者造成了一定侵害,但由于传统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都认为死者只能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而不能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这种侵害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不具有犯罪性。而在客观上,这种行为又拯救了另一个个体的生命,其实质是以一个相对较小的利益换取了一个更大的利益,属于紧急避险。而且,在伦理道德上,从尸体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行为具有对受体进行救助的崇高意义,这是为社会通行观念所认同和赞许的。以此为立足点,摘取尸体器官用于移植的行为应当是一种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行为,而否定从尸体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做法显然是不人道的,不宜为立法所提倡。但也有学者认为,医生摘取尸体器官的行为应构成尸体毁损罪。尸体毁损罪的立法意旨在于保护死者家属对死者的感情,即使对尸体有处置权的人也可能触犯此罪,换言之,纵然对尸体有管理处分权,甚至征得本人生前同意,仍不能阻却从尸体摘取器官的违法性[16]。
笔者认为,从法理上来说,生命法是生命伦理的法律化,是从生命伦理中分流出来的一种具有刚性的社会行为规范,它所维系的是最低限度的生命伦理。生命法学作为以生命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是以生命伦理学作为其理论来源的。因此,生命法律现象中的很多问题都必须从生命伦理学中寻找理论支撑。而站在生命伦理学的立场上来看,任何人都是平等、自主的主体,只有自己才具有处分自己利益的最高权利,“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是最高的主权者”[17]。以此为立足点,无论是摘取活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还是摘取尸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都必须建立在尊重器官所有者自主权的基础之上。任何违反自主原则而获得器官的行为都是为生命伦理所不容的、是不正当的,也都会对人类社会所赖以存续的生命伦理秩序带来冲击,从而危及整个人类社会的稳定。对于这种行为,法律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而不宜默许、纵容,更不宜倡导。对于那些违背自主原则利用器官并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刑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医生摘取尸体器官的正当化依据也应当是知情同意。但即便是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也必须首先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例如,应合乎法律的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具有医学上的适应性、符合医学操作常规并做好预后处理等。否则,正如后一种观点所指出的,纵然对尸体有管理处分权,甚至征得本人生前同意,仍不能阻却从尸体摘取器官的违法性。
(四)摘取脑死亡尸体器官是否构成犯罪
在尸体器官移植中,争议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医生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用于移植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总体而言,各国学者一般都认为,如果医生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的行为事前并未获得死者本人(在其大脑尚未进入伤病状态且意识清醒时)或其家属的同意,则该行为构成犯罪。但在具体构成何种犯罪上面,承认脑死亡和未承认脑死亡的国家或地区通常有着较大差异。具体而言,在立法上已经承认脑死亡的国家和地区,通常认为医生未经同意而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的行为构成损坏尸体罪或侵害死者尊严罪;而在那些立法上尚未准允脑死亡的国家和地区,这种行为则构成故意杀人罪。
那么,对医生已经获得同意而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用于移植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呢?对此,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在日本,多数学者认为,如果承认脑死亡,则在获得同意的基础上,医生可以摘取脑死亡者的器官用于移植而不构成犯罪,即“从脑死说的立场出发,认为摘除器官的行为在外形上符合损坏尸体罪的构成要件,但是,通常情况下,由于移植而获得的利益(维持或者延长被植入者的生命)比因为摘除器官而产生的不利(侵害对作为捐献者的尸体的虔诚感情)要大得多,因此,移植器官的行为是合法的”[6]70。而与此相对的少数学者则认为,即便不承认脑死亡,如果有器官提供者生前的同意,也可能摘取其器官进行移植,但是,即使是同意,那也构成故意杀人罪,仍然具有可罚性[18]。
笔者以为,在目前人类医学发展已经证明脑死亡才是人真正死亡的情况下,对传统心死亡观念的坚守其实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拒绝。我国法律应当成为引导人们观念的“导航塔”,尽快认可脑死亡的概念,即便不愿明确承认脑死亡,也不应再抱残守缺,过多地干涉已为医学界所接受并已在医疗临床上频繁操作的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的行为。因此,对于那些已经获得同意而摘取脑死亡者器官用于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的行为,法律不宜以犯罪待之,更不宜对其科以刑罚。
(五)盗取和强制摘取他人器官应如何被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上,器官的摘除客观上是与伤害罪的构成要件相符的,对捐赠者来说,又不属于治疗行为,但对于受者即患者来说,具有伦理性、社会相当性,因此,在得到捐赠者真心同意的情形下,阻却其违法性,摘取器官并不构成犯罪。”[16]185 然而,一旦器官捐献违背了捐献者的自由意志,则会因违背公序良俗而失去其正当性,成为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的犯罪行为。目前,由于在对人体器官的定性上存在争议,学者们对盗取他人器官和强制摘取他人器官的行为应构成何种犯罪以及应如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存在严重分歧。具体来说:(1)在盗取他人器官的问题上,主要存在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盗取他人器官、组织、精液、血液等,只能认定为对所有权的侵害,而不构成对人格权的侵害[19]。以此为基点,盗取他人器官或组织的,应构成盗窃罪,应依盗窃罪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与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人体器官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人格性,即使身体的组织、器官已经离开了人体,也应当将其视为身体的一部分,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般的物[20]。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盗取他人身体器官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而应构成侵犯人身尊严方面的犯罪(如侮辱罪),应当依据《刑法》关于尊严类犯罪的规定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2)在强制摘取他人身体器官的问题上,也存在两种看法。有学者认为,人体器官属于物的范畴,强摘他人身体器官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应依抢劫罪来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但也有学者认为,人体器官并不是物,它依旧属于人的范畴,强摘他人身体器官的行为应构成非法拘禁罪或故意伤害罪。以本文关于人体器官性质的界定为立足点,笔者以为,无论是偷取他人器官的行为还是强摘他人器官的行为,都不构成盗窃罪或抢劫罪等财产性犯罪。由于这类行为所侵害的具体对象及客观方面的差异,其将构成何种犯罪亦即将被依照何种犯罪追究刑事责任,须视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1.偷取他人器官之刑事责任
根据侵害对象之不同,偷取他人身体器官的行为可以分为偷取活人身体器官与偷取死者尸体器官两种情况。在这两种不同情况下,行为人将构成不同的犯罪,并应当被依法追究不同的刑事责任。首先,就偷取活人身体器官而言,应具体区分两种情形:一是在偷取活人器官时附带发生了致人重伤或死亡的结果;二是在不损害他人生命健康的情况下偷取他人身体器官(如偷取他人骨髓、血液、皮肤、卵子等情况)。就第一种情形而言,这种行为实际上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21],因此,应当依据《刑法》对“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规定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而就第二种情形来说,则应当在《刑法》中增设“非法侵犯他人身体罪”这样一种无伤害型的活体器官侵权犯罪,并配设相应的刑事责任。其次,就偷取尸体器官而言,则应当区分三种情形:一是为了牟利或出于其他有损死者人格尊严的目的而偷取尸体器官;二是在特别紧急情况下偷取尸体器官用于医学科研或器官移植;三是在非紧急情况下偷取尸体器官用于医学科研或器官移植。笔者以为,对第一种情形,应依照《刑法》关于“盗窃、侮辱尸体罪”的规定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1];对第二种情形,可以依照《刑法》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免于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21],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者须严格限制“紧急情况”的适用范围,避免“紧急避险条款”的滥用;而对于第三种情形,则应当在《刑法》中增设“非法利用尸体、尸体器官罪”这样一种专门针对尸体侵害的犯罪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1]。
2.强摘他人器官之刑事责任
根据侵害对象的不同,强摘他人身体器官的行为也可以分为强摘活人器官与强摘尸体器官两种情形。首先,强摘活人器官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强摘器官后客观上造成了受害人死亡或严重伤害;二是强摘器官后未对受害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笔者以为,前者构成杀人罪或伤害罪,应依照《刑法》关于杀人罪或伤害罪的规定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对于后者,我国现行《刑法》中则尚无直接适用于这种情形的适宜罪名,在这种情况下,宜修改《刑法》的规定,增设“非法侵害他人身体罪”这样一种专门保护公民身体权的犯罪,并确立适宜的刑事责任。其次,强摘尸体器官显然也会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在死者本人生前同意而其死后家属不同意的情况下强摘尸体器官;二是在死者生前明确表示拒绝捐献遗体或器官而其死后家属也不同意捐献的情况下,强摘尸体器官。对于前者,由于死者本人生前已经同意捐献遗体或器官,只是由于死者去世后其家属违背死者意愿拒不捐献才导致出现的强摘,因而这种所谓的强摘实际上并不违背真正有权处分自己遗体或遗体器官的死者本人意愿。在这种情形下,不宜将医生强摘尸体器官的行为视为犯罪,更不宜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但医生在摘取尸体器官时,应当尽可能地取得死者家属的配合。同样,对于家属阻挠摘取死者器官的行为,法律显然也不宜将之视为犯罪而追究死者家属的刑事责任。对于后一种情形,则应当将其视为犯罪。然而,由于我国现行《刑法》中尚无直接适用于这种行为的合适罪名,因此,宜修改《刑法》,增设“非法利用尸体、尸体器官罪”。
(六)人体器官交易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理论
器官移植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是要有合适的供体器官,然而,由于医疗临床上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人数众多但自愿捐献者又数量有限,从而导致供体器官的数量远远无法满足实际移植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人体器官买卖问题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不少学者开始考虑能否通过商业交易来获取医疗临床上所急需的人体器官。他们主张建立人体器官市场,允许器官的转让。这样一可以解决供体器官短缺的问题,有利于救死扶伤,促进医学进步;二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使转让人的损失得到公平补偿,防止非法交易;三可以通过买方与卖方所达成的协议,确保器官的正常用途[22]。“如果允许人体器官交易,就可以增加供体器官的来源,而依据自主原则,人们应当被允许依其意愿来处理其自己的身体,包括出卖自己的器官,人体器官的买卖可以帮助那些因得不到器官而将死的病人。”[17]151 但也有人认为,人体器官买卖应当被禁止,理由是:(1)人体器官买卖会造成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因为穷人更有可能会出卖自己的器官;(2)人体器官买卖会使器官的出售者处于手术的风险与痛苦之中;(3)如果允许人体器官买卖,将会导致人体构件乃至人的商品化;(4)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自愿同意将自己置于这样一种风险之中;(5)如果允许捐献者获得补偿,则会损害现有的以利他为特征的器官捐献体制[17]151。而从民法学的角度上来看,人体器官作为人格利益的载体,不能成为物权的标的,而且人体器官不具有财产性,不能作为物来交易。以此为基点,对人体器官的买卖、担保、抵债,应视为违反公序良俗,其行为不应有效[23]。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雷尼·福克斯所指出的:“人体器官移植从一开始就不是偶尔为之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人体器官的移植建立在这样的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即人体和无偿捐赠器官都是难能可贵的,不能将它们商品化……尽管器官移植有时可能会触犯禁忌,但是以无偿捐赠为基础的移植,仍不失为一种道德而富有意义的做法。”[24]
站在生命法学的立场上来看,人体器官买卖是一种严重损害人格尊严的行为,如果允许人们随意转让器官,无异于明确承认人格的商品化,而人格的商品化则有可能诱发道德风险,导致自杀甚至是谋杀。同时,人体器官买卖也会造成权利人自身的损害,人们可能因为生活所迫而出卖自己的器官,甚至可能无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谋取一时的利益而进行身体器官交易,以致给自己身体造成严重损害。正因为如此,无偿捐献和反对人体器官商品化已经成为现代器官移植立法的主导趋向,为了贯彻人体器官无偿捐献的理念及防止人体器官商业化交易,国外刑法学界大都主张应当对此设置专门的罪名。有学者甚至认为:“为了贯彻器官提供的无偿性原则,在活体上摘出(器官)的场合,有必要要求供体与受体之间具有紧密的近亲关系”[25],以此避免人体器官商业化的泛滥。尽管目前供体器官严重缺乏依旧是困扰器官移植的主要障碍,而人体器官买卖客观上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供体器官的紧张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利用刑事责任制度防止人体器官的商业化依旧是今后国外学界的主流声音。
三、国内外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
伦理主义法学派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通常依赖于三种社会秩序的稳定,即社会政治秩序、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伦理秩序,在这三种秩序中,社会伦理秩序具有主导性,它决定着人类社会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和谐乃至存续。“任何社会制度的基础都是道德秩序”[26],“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之所以能够维系一定的社会伦理秩序,就在于这种伦理关系的基本稳定,就在于这种伦理关系所滋生出来的社会认知与情感内容的某种公度性”[27]。犯罪作为行为人对人类所赖以存续的各种伦理道德的最严重蔑视与公然违反,是直接危及人类社会存续的一种反社会行为。人体器官移植过程中所引发的各种犯罪现象是对人类社会长久以来所赖以存续的生命伦理秩序的公然破坏,其存在必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此,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专门针对人体器官移植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类违法犯罪进行了刑法规制。
(一)有关活体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立法及医疗实践中承认了活体器官移植得以正当性,然而,为了使活体器官移植得以有序开展,各个国家和地区无一不对活体捐献的程序和条件进行了严格规定,而构成犯罪的器官移植通常都是由于不符合这些条件或程序所导致的。从这些规定来看,各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将违背供体意旨而进行活体器官移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在英国,根据1989年《人体器官移植法案》,活体器官移植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合法:(1)医生已就捐献的风险和程序向捐献者作了说明和解释;(2)捐献者理解了这种说明和解释;(3)供体的同意不是通过强制或物质诱惑而获得的;(4)供体知悉他有随时撤回捐献的权利……以此为前提,供体的同意是医生摘取其器官用于移植而不构成犯罪的前提,然而,如果供体的同意可能会导致其死亡,则该同意就属于无效同意,此医生就可能因此而承担刑事责任,除非该同意是出于供体的最佳利益考虑[10]103。在蒙古,使用暴力或胁迫手段非法采集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的,要被处4年以下徒刑,或者并处禁止3年内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特定职业的刑罚;而明知是孤立无援的人或利用物质上或其他方面的优势而使用暴力或胁迫手段非法采集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的,则要被处以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或者并处禁止3年内担任一定职务和从事特定职业的刑罚。在俄罗斯,器官摘取必须以供体的自愿捐献为前提,违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20条为此明确规定:“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强制摘取人的器官或组织做移植的,处4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犯罪人明知他人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或在物质方面或其他方面处于对犯罪人的从属地位而对其实施上述行为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而在法国,其《公共卫生法典》也对器官移植的条件与程序进行了严格限定,如禁止摘取未成年人活体器官、摘取成年人活体器官须以具备医学上的必要性为前提且须获得捐献人之自愿同意、移植必须在得到法定机构批准的基础上进行等,如果医生违反这些规定,都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28]。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中关于活体器官移植犯罪的规定则是目前世界上最为严厉的。该法典第268.96条规定:“如果符合下列情形,则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战争罪中的为移植而输出血液、切除组织和器官罪:(a)犯罪人为了移植而从一人或数人的身体上转移血液、组织或器官;而且(b)在转移血液的情形中——该转移:(1)不是为了输血;或(2)在没有此人或数人同意的情况下;而且(c)在转移皮肤的情形下——该转移:(3)不是为了移植;或(4)在没有此人或数人同意的情况下移植;而且(d)该转移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病;而且(e)该转移不是在和一般可予接受的医疗标准相一致的条件下执行,也不是为了此人或该数人或接受者的利益而有计划的实施;而且(f)此人或该数人作为某一国际武装冲突的结果被敌方所掌控、拘禁、扣押或者其他方式的剥夺;而且(g)行为发生在某一国际武装冲突中,或者与某一国际武装冲突有关。”依据《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的规定,对这类犯罪可判处25年监禁。
总体而言,知情同意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器官获取原则。对于活体器官移植,医院和医师应当告知供体关于器官摘取所涉及到的手术性质、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和可能的风险等信息,捐赠者本人应当对上述信息有清晰的认识,在没有任何不当干涉和影响的情况下自主、明示地做出同意捐献的意思表示[5]207。
在活体器官移植方面,不少国家和地区除了专门规定强制摘取器官、欺诈摘取器官等违反自愿知情原则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之外,还规定了活体接受瑕疵器官移植的刑事责任问题。《蒙古国刑法典》第102条、第105条就对此作了明文规定。根据这些条文的规定,“因无资格配制、移植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而造成疾病、残疾或者死亡结果的,处3年以下徒刑,或者并处禁止3年内从事医疗职业。从事制造业、贸易业的员工或者药品采购者,没有对其出售的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因而将艾滋病传染给他人的,处以最低工资额51倍以上100倍以下的罚金,并处禁止3年内担任一定职务和从事特定职业的刑罚;或者并处以3年以下徒刑。医务人员过失传染艾滋病或艾滋病病毒的,处以4年以下徒刑。”《瑞士联邦刑法典》第231条规定了故意或过失传播疾病罪,对包括利用器官捐献或移植而传播危险的、可传染的人类疾病的行为进行了惩罚性规定。《芬兰刑法典》也规定了危害健康罪,对利用器官捐献传播危险性疾病而对他人生命健康造成一般危险的,处以4个月以上4年以下的监禁。俄罗斯、法国、丹麦、意大利、韩国等国家也都在刑法中设置了类似的犯罪。这说明,对于瑕疵器官移植所引发的刑事责任,尤其是对于利用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故意传播危险疾病的刑事责任,各国还是相对比较重视的。
(二)有关尸体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一般认为,医生为移植而摘取尸体器官,应该以自愿捐赠为原则,不能违背死者本人或其近亲属的意愿,否则就是非法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常情况下,医生摘取尸体器官前,必须充分考虑死者生前是否有捐献器官的意思表示和死者近亲属现在是否同意捐献死者的器官。对此,各国器官移植法往往都有明文规定,只不过在具体条文上略有差异。而围绕尸体器官移植所引发的犯罪基本上也都是由于医生未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利用尸体所导致的。在英国,根据1961年《人体组织法》的规定,医生必须出具死者生前明确同意捐献遗体器官的证据才可以从死者身上摘取器官,且必须严格根据死者的要求摘取相应的部分,否则,便可能会被诉之以罪责。在法国,尸体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任何未经死者本人生前同意或其家属同意而私自处理其遗体或摘取其器官的行为都构成对死者尸体之侵犯,将会被处以1年监禁并科15000欧元罚金;法人实施这类犯罪的,也将被科以刑事责任。而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刑法典或器官移植法中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只不过所追究的刑事责任的大小有所不同。
在尸体器官移植方面,各国规定差别比较大的是对利用脑死亡者器官行为的处理。由于受文化、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个国家和地区对脑死亡的认同和接受程度大不相同,有些国家制定了本国的脑死亡法,明文规定脑死亡为人的死亡标准,有些国家虽未制定脑死亡法,但也默许医学临床实践中的脑死亡判定操作,而有些国家则不认可脑死亡。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对利用脑死亡者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做法往往有着不同的评价。具体而言,在那些已制定脑死亡法的国家,一般都允许利用脑死亡者遗体或器官,而医生通常不会担心因此而承受刑罚的问题;在那些未制定脑死亡法但认可实践中的脑死亡操作的国家和地区,刑法通常仅追究那些因利用脑死亡者遗体器官而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医生的刑事责任;而在那些尚未对脑死亡加以立法且实践中也不认可脑死亡操作的国家,医生利用脑死亡者器官的行为则通常会被以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毋庸置疑,无论是在已制定脑死亡法的国家和地区,还是在那些未制定脑死亡法的国家和地区,未经死者或其家属同意而利用其遗体或器官的行为都是非法的。至于是否将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则要视其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是否已突破了各个国家与地区法律所容许的底线而定。
(三)有关人体器官商业化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严惩人体器官商业化犯罪,是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方面的基本刑事立场。为此,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专门针对人体器官商业化运作的法律,如英国1989年的《人体器官移植法案》、日本1997年的《器官移植法》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
英国1989年的《人体器官移植法案》(Human Organ Transplants Act 1989)明确禁止人体器官的商业化运作,该法第1(1)条规定:“如果行为人在英国:(a)为提供已经或将要于英国或其他任何地方之去世或在生的人身上摘除并将被移植于另一人体内的器官或为意图提供这样的器官之要约而作出或接受付款,(b)谋求寻觅愿意为获取付款而提供该器官的人或为获取付款而要约提供该器官,(c)提出或商议涉及为该器官的提供或提供该器官的要约而作出付款的任何安排,d)参与管理或参与控制其所从事的事务包含或包括提出或商议作出任何这种安排的法人或非法人社团,则其将构成犯罪[10]107”。此外,该法第2(1)条规定:“行为人如果在英国:(a)从活体身上摘取拟移植入另一人体内的器官,或(b)移植从活体身上摘取的器官到另一人体内,则将构成犯罪——除非器官被植入者与器官供应者有基因联系。”① 日本1997年7月16日实施的《器官移植法》也明确禁止人体器官的商业化操作,该法第20条规定了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罪、非法买受人体器官罪、从事人体器官买卖中介罪以及为获利而非法为他人实施器官移植罪四项犯罪,并规定对这些犯罪可以分处或者并处5年以下徒刑或5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而对法人从事上述犯罪的,除了处罚行为人以外,对法人或者该自然人也科处各条例规定的罚金刑。② 1995年澳大利亚北方区《人体组织移植法》第24条也规定,从事人体组织或器官买卖活动的,处500元罚金或3个月监禁。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则规定得更为详尽,该《条例》第4条明文禁止将人体器官作商业交易,并规定:“(1)任何人就任何已经或将会于香港或外地自任何去世或在生的人身上切除,并拟于香港或外地移植于另一人体内的器官,在香港作出以下行为,都属犯罪:(a)为该器官的提供或提供该器官的要约而作出或接受付款;或(b)谋求寻觅愿意为获取付款而提供该器官的人或为获取付款而要约提供该器官;或(c)提出或商议作出任何安排,而该等安排涉及为该器官的提供或提供该器官的要约而作出付款。(2)任何人参与管理或参与控制属法社团或不属法社团的团体,而该团体从事的事务包含或包括提出或商议作出第(1)(c)款所提述的任何安排,该人即属犯罪。(3)在不损害第(1)(b)款的规定下,任何安排发布或安排分发,或知情地发布或知情的分发以下广告,即属犯罪:(a)邀请任何人士为获取付款而提供任何已经或将会于香港或外地自任何去世或在生的人身上切除,并拟于香港或外地移植于另一人体内的器官的广告,或为获取付款而要约提供该等器官的广告;或(b)显示刊登广告的人愿意提出或商议作出第(1)(c)款所提述安排的广告。……(8)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如属首次定罪,可处第5级罚款及监禁3个月,其后各次定罪,均可处第6级罚款及监禁1年。”此外,根据该《条例》第5条的规定,任何人如果自任何在生的人身上切除拟移植于另一人体内的器官;或将切除自任何在生的人身上的器官移植于另一人体内,即属犯罪。犯这类罪行的,如属首次定罪,可处第5级罚款及监禁3个月,其后各次定罪,均可处第6级罚款及监禁1年。③
除此之外,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智利、西班牙、津巴布韦以及我国台湾、澳门地区等也都明确禁止人体器官的商业化操作,并明确将人体器官的商业化规定为犯罪而科以刑罚。
四、我国大陆地区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
当前,伴随着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医疗临床上的广泛应用,相关的犯罪现象也越来越多,这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负面问题。为此,我国卫生部于2006年3月专门制定了旨在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活动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而国务院也于2007年3月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为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然而,由于上述立法只是行政法规和规章,无权直接规定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过程中所引发的刑事责任问题,而只能在法条中设置一些诸如“依法承担刑事责任”之类的刑事指引条款,因此,对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来说,人体器官移植所带来的许多挑战依旧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加强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应对制度的理论探讨,已成为促进该技术进一步发展所必须予以正视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
(一)我国大陆地区有关器官移植的立法及其对器官移植犯罪之刑事责任的规定
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极其迅猛。自1960年我国开展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以来,器官移植已在我国医疗临床上走过了近50年的发展历程,在器官移植的数量上,我国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是器官移植技术最发达且应用最普遍的国家之一。然而,相比于欧美其他国家,我国大陆地区在器官移植方面的立法步伐却显见滞后。我国器官移植立法是从地方立法起步的。一般认为,我国首部地方性器官捐献移植法是2001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④ 而深圳市于2003年8月22日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则是我国首部地方性人体器官移植法。此后,福建省又于2005年6月2日制定了《福建省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2006年3月,卫生部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该规章是我国大陆地区第一部器官捐献移植法,在此基础上,2007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效力层级更高一级的行政法规形式对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作出了规范。除此之外,我国现行《刑法》中已有的“非法行医罪”、“医疗事故罪”、“盗窃、侮辱尸体罪”以及“故意伤害罪”等也可以适用于围绕人体器官捐献移植而引发的个别犯罪。⑤ 在这些立法的规范和引导下,我国的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工作正在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目前,无论是地方性的人体器官移植立法,还是人体器官移植中央立法,均已在我国起步。综观这些立法,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法规和规章都对因器官移植而引发的法律责任问题进行了规定,有些法规和规章甚至还涉及到了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如《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⑥ 然而,受制于《立法法》的规定、立法技术以及罪刑法定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些规定难以在规范和应对器官移植犯罪方面真正发挥其“刑事指引性条款”的作用。在我国《刑法》未明确规定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这些规定大多成为具文。以《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对人体器官买卖犯罪的规定为例,尽管该《条例》第25条规定了“买卖人体器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我国《刑法》未设置“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该规定基本上形同虚设。而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一些法规或规章中也同样存在。
(二)我国大陆地区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立法建议
随着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医疗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器官移植的负面效应正在逐渐显现,很多违法犯罪现象都在器官捐献与移植过程中产生,1998年发生在北京的“眼球丢失案”与2006年发生在河北的“行唐事件”等都是例证。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刑法手段防止器官移植犯罪的发生,已成为今后我国刑法必须肩负起的一项重要使命。然而,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设置器官移植方面的专门犯罪,缺乏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实质性规定,面对实践中屡屡发生的器官移植犯罪,司法者因受制于罪刑法定而只能参照刑法中涉及人的生命健康保护的传统犯罪来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而在更多情况下则对器官移植犯罪束手无策。⑦ 在此背景下,笔者以为,有必要修改我国《刑法》的规定,在其中增设有关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方面的制度。具体来说,应在《刑法》中增设以下具体罪名:“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走私人体器官罪”、“非法从事人体器官买卖中介服务罪”、“非法商业存储人体器官罪”、“非法利用尸体、尸体器官罪”、“非法侵害他人身体罪”以及“非法刊登人体器官买卖广告罪”等。对于这些犯罪,《刑法》应设置适宜的刑罚,以保证相关犯罪人受到合理有效的刑事责任追究,从而保障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发展和理性应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公共卫生福利的提高。
收稿日期:2008-08-31
注释:
① 所谓“有基因联系”,主要是指器官捐献者是受体的血缘双亲或子女、具有全部或一半血缘的兄弟姐妹、生物学父母任何一方的具有全部或一半血缘的兄弟姐妹,以及具有全部或一半血缘的兄弟姐妹的生物学子女或生物学父母任何一方的具有全部或一半血缘的兄弟姐妹的生物学子女。(厄莱斯代尔·麦克林.医疗法简明案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05.)
② 日本《器官移植法》第11条规定:“1.任何人不得接受、要求及约定作为提供移植手术使用的器官对价的财产利益。2.任何人不得接受、要求以及约定作为提供或者接受移植器官对价的财产利益。3.任何人不得接受、要求以及约定为提供或者接受移植器官进行中介,以及作为中介对价的财产上利益。4.任何人不得为提供或者接受移植器官进行中介,以及提供、要求或者约定作为接受中介对价的财产利益。5.任何人都不得在知晓某一器官违反上述各项规定的任一条款行为有关事实的情况下,摘除该器官或者将该器官用于移植。6.上述第1项到第4项的对价包括交通、通信,用于移植手术器官的摘除、保存或者运送,以及移植手术所需的费用。但是,不包括提供用于器官移植手术,接受移植,或者通常为此所需的必要的、能够为人们认可的必要费用。”
③ 从该《条例》的立法目的来看,《条例》制定的主要动机在于防止人体器官交易商业化运作。因此,其器官移植犯罪的种类相对集中于商业化的器官移植犯罪及个别其他相关犯罪,对其他类型的器官移植犯罪则缺乏规定。
④ 但也有学者认为,《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并不是我国首部地方性器官移植法,因为该《条例》并没有将器官移植纳入立法范畴。参见:陈伟芳,陈洁.对《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一文的商榷[J].上海法学研究,2002(4).
⑤ 关于我国现行《刑法》中某些犯罪在器官移植方面的适用,已有学者进行了论析。参见:康均心.人类生死与刑事法律改革[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407-423.
⑥ 例如,《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5条规定:“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行事责任:未经公民本人同意摘取其活体器官的;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本人器官而摘取其尸体器官的;摘取不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的。”
⑦ 例如,面对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买卖及变相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司法者往往听之任之,刑法在防范这类犯罪方面难以有更好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