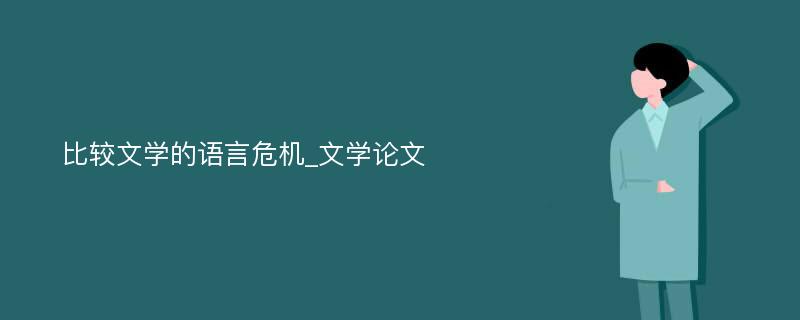
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危机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发现比较文学目前存在着两个危机。一个危机与语言有关,另一个危机与新媒体的发展相关,后一个问题我不想多谈。对于年轻学者来说,那种传统意义上印在书页里的小说、诗歌或戏剧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了,他们现在往往做的是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电影研究、传媒研究、少数民族话语研究以及女性研究,看的是电影、录像、电视,或者在网上冲浪,而不是去读狄更斯、托尔斯泰或福楼拜的作品。当今的大众群体,甚至包括受到良好教育的人,都不再阅读狄更斯、托尔斯泰或福楼拜的著作,更不用说塞利纳、兰波和济慈了,他们不认为这对于自己的生活有多么重要。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轻,成为文化百家衣上的一个小小的补丁。因此,在“‘新媒体’时代中文学的前途”是当今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我姑且把这一危机作为一个背景,接下来我要谈论的是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
40多年以前,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他认为,比较文学的危机是因为学者对这一学科方法论有着很多不必要的分歧,同时他们也很难设定一个研究对象。他认为:“我们的研究很不稳定,其重要标志就是,我们没有设立一个清楚的研究主题和具体的方法。”在韦勒克看来,“比较文学有着巨大的优势,它能避免对各民族文学史的孤立:西方传统中的文学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联系的网络,这一观念显然是正确的,这已得到了广泛的证实。”基于这一信条,韦勒克相信他已通过结合“内在性”与“外在性”的比较而为比较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韦勒克的论文最后以这样一个高尚、甚至充满幻想的结语结尾:“一旦我们掌握了艺术与诗的本质,它们超越了人的命运和生命,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崭新世界,那么人们将不再会有民族的虚荣心。人类,全体人类,不论地点、时刻和种类,都将汇集在一起。文学研究不再是一项考古似的消遣,不再是反映民族的优缺点,甚至不再是各种关系的网络图。文学研究成为像艺术本身那样的想像性行为,从而成为人类最高价值的保存者和创造者。”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些让人惊讶的语句!“人类,全体人类”!“超越人的生命和命运”!文学研究是一种“像艺术一样”的想像性行为!韦勒克认为,既然现在他已经清楚地指出了摆脱危机的道路,那么现在应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即是说,继续来从事“比较文学”。这一短语指涉的是当时发表在哈佛大学的杂志《哈佛之声》上的一个讽刺漫画。漫画上画的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的创始人列文和坡基奥利,他们身穿水管工的衣服,拿着修理工具,正在敲一户居民的房门。漫画的标题上写道:“我们来比较文学。”这幅漫画真是非常诙谐,出人意料地巧妙。它影射“文学”中有些东西坏了,把它们修理好的方法就是加以比较。“比较文学”就像“修理水龙头”,好让水流通畅。
韦勒克这篇文章的题目“比较文学的危机”在提法上也有问题。“危机”这个词意味着转折点、分水岭,就比如在一种疾病的危机时刻,病人要么好转要么死亡。然而,比较文学却总是处在危机之中。作为一门学科,它就是被特别设计成为一个剧烈动荡的载体,包含了文学研究中永远的危机。这一危机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比较文学之所以永远在危机之中,是因为它不像国别文学那样有自己的经典和文学史,而是被指定来“作比较”,不管比较什么。比较文学在最初建立的时候是以较早出现的学科如比较神话学或比较语言学等为摹本的,同这些学科一样,比较文学也力图追求科学性和实证性。人们认为,比较文学缺乏一个具体的经典,只是由方法和理论拼凑而成,而要使比较学者在理论和方法上保持一致,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韦勒克也知道!)。
我认为比较文学永久的危机并不在于理论或方法论上的分歧,而是在于翻译的问题,这里的翻译是广义的概念。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中心问题并不是“理论”,而是难以解决的翻译问题,无论是语言之间的翻译,文化之间的翻译,还是从亚文化到另一亚文化之间的翻译,都十分令人棘手,。
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语言,大约有几千种,仅欧洲就有几十种语言,有人告诉我,在非洲就有两千多种。如果这种语言不是我的母语,我又怎么能够深入地学习它,真正了解它所表达的文化呢?甚至就连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使学习和教授英国文学的美国师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误解。英国文学对我们美国人来说其实是很陌生的,我曾听一个研究美国文学的法国年轻学者称,在我们美国人常用的誓言中有一句“我以乔治·华盛顿的坟墓发誓!”也许在美国有人会这么说,但我这辈子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同样地,我也可能经常对狄更斯或特托洛普的作品产生误解。
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对翻译的问题并不够重视,总以为任何语言都可以被翻译为一种主流语言,而不受损失。如果一个学者在某篇文章或某部书中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一个能够让其他语言作为比较的坚实平台,也不是阿基米德的杠杆,那么比较文学怎样才能继续修理水管的工作呢?
虽然雷内·韦勒克会很多种欧洲语言,但他那本权威的《近代批评史:1750-1950》也是用英文写成的。最初的英文版本把诺瓦利斯、巴赫金、圣—波夫等原版的引文用小字体做了附录,方便读者查阅。这实际就是暗示:“相信我,这些语言我都会,我已经把这些外国批评家的引文翻译成了精确的英文,不信你可以查。”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总是伴随着某种强势语言的文化帝国主义而发展,甚至有时是不自觉的,但这只是比较文学目前的危机之一。另一个危机是,我们发现,多卷本的《近代批评史》这种提法不大合适,不如叫做《西方近代批评史》,因为该书并没有包括中国、日本、印度、非洲,也没有包含小语种以及大部分的妇女文学。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传统西方比较文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应当受到广泛的质疑。那么我们怎么来纠正这一偏颇呢?在今天,人们往往认为纠正的方法就是向比较的世界文学回归。有关世界文学的课程和教科书如雨后春笋般一夜之间到处都是。这类教科书不仅是在美国,在其他国家都大有市场。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比较文学难道不应该也把自身全球化吗?难道我们不该教给学生除了欧洲和美国之外的其他文学吗?我很同意这种做法,我甚至也赞同读一读普鲁斯特和中国《诗经》的译文,这总比不读要好。然而,我们也很容易看出来这种方法的弊病。大多数的世界文学教科书和课程仍然以英语作为基础语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叫我们多数学生只会英语,或者有的只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呢?
即使我们的一些学生会西班牙语或汉浯,但他们也很可能不懂印地语。在美国,比较文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就已经够明显了,而这些教科书又进一步把英语的霸权向全世界扩张。在这样的教科书里,不管是哪种语言的选文都被翻译成了英语,这种思维意味着,任何语言都可以被翻译为英语,而基本上不受损失。这些教科书和课程的第二个问题是。它们的范围太广,所选择的东西尤其局限。世界文学选读必须得呈现出像中国文学(如果中国诗歌可以被称为西方意义上的“文学”)那样复杂的传统,因此就从中国的《诗经》中抽出几首诗,从《红楼梦》中抽取一个章节来表现。这就好像要以《哈姆雷特》的一幕戏和华兹华斯的几首抒情诗来代表英国文学一样。这种以部分代全体的做法太宽泛,没有什么代表性。就这么广的范围而言,任何选文都是有偏颇的。此外,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翻译相邻近的语言如把法国或德语翻译为英语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如果是把一种欧洲以外的语言翻译成为英浯,那岂不是更难吗?
因此,我建议发展一种新型的全球性、非欧洲中心化的比较文学。首先,我欢迎比较文学的全球化,欢迎它脱离欧洲中心主义,这也是大势所趋。其次,要发展全球性的比较文学,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研究具体作品时,应该学习相关的语言。在此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人类学的学者在研究一种文化形态时,把学习相关的语言作为必需的规则。虽然有人说,学习一种异质文化的语言,特别是欧洲人学习非欧洲国家的语言,这是一种文化侵略,但我认为,为了研究某个课题而掌握必要的语言知识,这并不是帝国主义的行为。与其相信什么都可以毫无损失地翻译成英文,不如自己先学会这门语言。最后,一个新型的全球性的比较文学需要规范其课程和要求,就像人类学需要学习除了欧洲语言的其他非欧洲语言一样。为了更负责任地“比较文学”,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即是说,我们必须回应其他文化对我们的召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