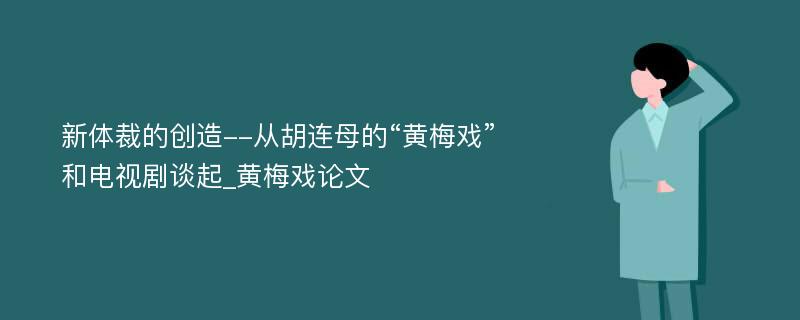
新体裁的创造——从胡连翠的黄梅戏曲电视剧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裁论文,戏曲论文,电视剧论文,黄梅论文,胡连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尤其是近些年来,我们戏曲电视剧的探索尝试,开拓创新,其形式上的主要功绩,似可归纳为一句话,就是经由了电视与戏曲的真正的结合,而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体裁。也就是说,新的戏曲电视剧再也不是以往那种舞台演出加电视转播了。
新体裁的产生
戏曲电视剧这一新体裁的产生,是随着电视特点与写实因素的不断强化和戏曲程式及规范的不断弱化而出现的。安徽电视台的女导演胡连翠的黄梅戏曲电视剧的创作,就透露着个中消息。在《西厢记》中,她淡化了戏曲中的方言道白,淡化了程式化的表演,弱化了舞台时空的假定性;采用普通话念白,利用实景拍摄,利用摄像机的运动,使再现性的时空获得一种自由度,并同时用改变观众的视点的方式,以适应他们鉴赏电视艺术时的审美心理。它保留了较为传统的黄梅戏唱腔和原作的人物、主题、情节,大体上仍然是戏曲,是无可否认的黄梅戏。但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与传统规范意义上的戏曲已有相当的不同了。到了她的第二部作品《朱熹与丽娘》,胡连翠的探索则更为大胆别致。然而她的路数,依然是强化电视剧的写实因素,而进一步弱化戏曲的程式、虚拟的因素,从而使二者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这突出表现在她对于黄梅戏声乐文化的改造上。实景的采用使它更逼近古代生活原形,摄像机的运动与人物的行动也由此而得到了更大辐度的展开。
总之,探索者的实践已经透露出这样的意向:他们已不再把戏曲电视剧视为初始状态的戏曲的“电视化”了。原先艺术家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完整保留戏曲的原貌,只能在摄像机镜头画面的分切组合上下一番功夫;即使再进一步,那也只是将它搬到实景中来演出,只要适当解决好实景与程式化的、虚拟性的表演的严重矛盾就可以了。目前的情况则不然,新体裁的创造者是要把戏曲与电视都视为不同的媒介与元素,是在尝试着多媒介的创作,根据具体作品的构思、艺术追求,来实现独特而且超越常规的大综合,从而产生出新的戏曲电视剧。在这里,戏曲不再是原先舞台意义上的戏曲;电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电视剧。它们是被分割而给予综合的,是作为元素、成份,却不是作为独立的剧种而进入戏曲电视剧的。因而,它既可以侧重于戏曲,使自己保留更多的戏曲的形态;也可以侧重于电视剧,而使自己更接近于“新歌剧”;还可以使两种元素势均力敌,而成为一种“化合”状态的新品种、新体裁。
这种新体裁展现了诱人的前景。借助于它,传统的民族艺术又一次地找到了现代化的契机,而为现代科技所武装的电视则可以又一次地承担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任。它不仅仅是为目前陷于困境的戏曲舞台演出提供了新的出路,缓解了已有危机,也不仅仅是为有欠丰富的电视荧屏新添了一个戏曲的品种。它意味着在二者的结合、融汇中诞生出了一个新的生命;也意味着我们将掌握一种新的、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将使我们获得一片新的审美的天地。
然而,公正地说,新体裁还没有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魅力,它们还未能在深层的艺术精神上获得高度的统一性。单向强化电视的写实性与弱化戏曲的假定性,这一走向不能不显出严重的局限性,而难以再进一步把新体裁推向极致。要使新体裁充分发挥魅力,也需要考虑电视的假定性与戏曲的假定性的结合,考虑电视的时空自由与戏曲的时空自由的结合。对此,仅仅着眼于解决真实的环境与虚拟的表演的矛盾是不够的;仅仅吸取戏曲的声乐文化也是不够的。新的戏曲电视剧所要确立的新的美学原则,是戏曲与电视两强相遇所产生的新的艺术效应,它是超常规的大综合的产物,必须在新的艺术精神的统领下去寻求可能的契合点。
电视与戏曲的相互观照
新体裁一方面要求我们站在戏曲的角度看电视;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站在电视的角度看戏曲。我们既要熟悉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规律,也要善于挖掘、利用它为表现对方所提供的可能性。
站在戏曲的角度看电视,我们首先将看到它的具像性与运动性。正是在这一点上,电视与戏曲完全相通。二者的区别在于影视的具像性是通过摄影、播映的具像性;而戏剧则是演员直接在舞台表演的具像性。它们的运动性的区别在于戏剧主要是演员的运动;而影视却可以有描写对象的运动、摄影机的运动、胶片磁带经过剪辑及产生的运动感。人们常常引用戏曲的时空自由的特性;而时空自由恰恰也是影视的重要特点。然而,它们又有区别。戏曲受舞台、剧场的制约,其时空的自由是通过指意性的替代、象征,最终由观众的联想、想象而完成;而影视的时空自由的结果却是让观众直接看到的。所以,不能简单地把电视与戏曲分别说成是“真实”与“假定”的艺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从特定的深层意义上说,影视的对于“现实”的扮演,以及拍摄播放的二次加工恰恰可能是最大的“假定”。
因此,电视中的“真实”与“假定”是一种依存互换的关系。究其“真实”的本原,实际上只是它的描写对象的“物质性”。不管影视如何重视物质的纪录性,作为一种文化,人总是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创造;作为一种艺术,它总是以传达人的情感与意念为主要任务。因而,人总是在利用、改造对象的物质性,而把自己的主观情感投射其中,使之上升为艺术。这样,我们就必然可以看到,电视不但是“真实”的;同时也可以是“假定”的。它的再现性风格、表现性风格,以及不脱离再现的表现性风格,实际上也就是它在形态上于“真实”与“假定”两极间不同向度上的选择。
所以,不能仅仅把电视看成“真实”的艺术;我们也必须看到它的“假定”与“表现”的巨大的潜能。
那么,站在电视的角度,我们又该怎样认识戏曲呢?关于戏曲的定义,王国维有一名言:“以歌舞演故事”。尽管也有人不很满意,但它毕竟是为多数人所认可了的通俗化的界定。它能够在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来点明戏曲的要义。歌舞,实际上是指它一整套假定性的,虚拟的,程式化的表现方式,故事则指它所表现的往往带传奇性的内容。
应该承认,戏曲在我国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数以百计的剧种,但它们的发展是极不平衡,且各具特色的。如果从艺术精神的高度来把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与中国古典文学、美术、音乐等的相通。它不注理于对客观世界的模仿,而更注重于艺术家主观情感的投注;它不长于叙事,但却长于抒情;它不长于环境描写,而却常常把焦点凝聚在人物的身上;这就形成了它的抒情性、表现性,写意性的美学特征。它以“意象美学”为核心而形成了传神写照追求气韵生动、主客合一的艺术特色。
因而,“新体裁”的创造者不能忘记戏曲的“强项”:这是一种带着强烈主观色彩的、富有概括力的、常常是通过感知而作用于抵达人的情感的艺术。它把再现性与表现性融为一体,把写实性与写意性融为一炉;它的假定性一方面是在客观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寻求和谐,另一方面也在与观众的默契中达到统一。它的核心是“意象”二字。除了过于僵硬的程式,以及借助于想象的表演,不脱离再现的表现性风格的电视,正可以兼融戏曲;而且还可以把戏曲的运动性与表现性再进一步推向前进。写意性的电视剧,所依据的不也正是“意象”吗?它不是也同时在内容与形式上对于生活作着整体性的提升吗?
写意统领下的“两强相遇”
如前所述,影视的“真实性”源于摄像机对象的物质性。离开了这一点,它的假定性便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不但故事的编织,情节的推进,独特形象的刻画,都可以渗透进“假定性”;就连实景的拍摄也可以利用概括、象征、主观情感的灌注而使之获得“假定”的意义。在目前诸多戏曲电视剧中,我们可以见到中近景及特写的大量采用,这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视为一种“假定”。它把人物从环境中分离出来,这样的环境也就成了一种假定的存在。而戏曲的“假定”是作为整体的象征性的假定,三两人千军万马,四五圈千山万水。这是一种借助于想象的假定,它无以直观,是表演与欣赏间长期形成的一种默契。在电视与戏曲的结合上,戏曲势必要作出较大的牺牲,因为你既然要发挥电视的特性,那么你就必须尊重它的“物质可见性”,一味虚拟与程式化,势必与电视格格不入。戏曲在这里必须收敛自己的“精神性”,而去寻求“物质性”的依托。而电视,也需要改变自己的纪录性,而在“物质性”上去寄寓象征、想象性。在这里,电视同样要作出牺牲,它需要改变自己的纪录风格,而采用表现风格。它要在不脱离再现的表现性上与戏曲相融。戏曲电视剧中,愈来愈趋向写实、再现、生活化,这不是一条“两强相遇”的通衢,而是简单地套用电视的一般特点。其结果,一方面是电视的写实风格受到戏曲的虚拟风格的严重制约;另一方面,戏曲的虚拟风格也受到电视纪实风格的严重制约,而难以两全。这不仅带来了一系列技术上的矛盾难以解决,而且也形成了艺术精神的相背而不可能去实现高层次的统一。戏曲与电视的结合,不能不去寻求艺术精神、风格的同一性;有了它,才可能顺利地解决一系列技术问题。它不能象电视那么“实”,也不能象戏曲那么“虚”。它应该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追求气氛足,情意浓,以简驭繁,以意率形,创造出“仿佛然”的效果,从而同时发挥戏曲与电视的所长。又如在人物刻画上,戏曲电视剧的取材立意就必须考虑简炼、传神,考虑设置种种情境,通过人物的唱做来曲尽其复杂的内在心理,考虑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概括力与理想性,以及作品的情感吸引力与冲击力。它不能象一般电视剧那样追求生活化与散文化;更不能故弄玄虚地去追求朦胧艰涩的哲理性。自然,戏曲也要改变自身,那种完全依靠歌舞化技巧来刻画人物的方法,不能不有所限制;那种过于明显的类型化与脸谱化的创作方法,也不能不考虑加以改进。表面看来,电视与戏曲都失去了一些常规性的东西,但它们却统一在了更有力的描绘人物之“神”的新体裁之中。失去的必然会得到补偿。
也许这种想法只是一种幻想,但我们确实是从目前的戏曲电视剧中看到了希望。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新体裁也可以被视为现代人文意识与古老的东方艺术的结合,不过它的形式体现为电视艺术与戏曲的结合罢了。
自然,新体裁的产生与确立是一个历史的运动过程,我们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新体裁将有效地发挥电视与戏曲的优长,是大综合所形成的复杂系统工程。它不是导演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编、导、演,摄、录、美等通力合作的成果。从目前的实际看,至少理想的剧作是一个急待解决的课题。剧本毕竟是一个基础,主题、情节、人物、风格等在拍摄之前,不能不依靠着文学剧本来奠基。如果从文学剧作开始就没有一种新体裁的自觉;那么,导、演等的二度创作就很难走在“大综合”的理想的轨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