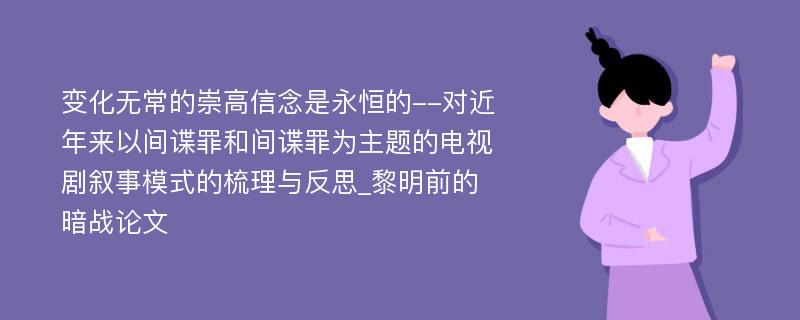
风云变幻诡谲 崇高信仰永恒——对近年来优秀热播谍战题材电视连续剧叙事模式的梳理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诡谲论文,风云变幻论文,电视连续剧论文,崇高论文,热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第一部谍战题材电视连续剧①是1981年播出的由王扶林导演的《敌营十八年》(九集)。这也是我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②其后,虽有《一双绣花鞋》、《梅花档案》、《无名英雄》(朝鲜)、《春天的第十七个瞬间》(苏联)等国内外谍战剧的不间断播出,但谍战剧在中国荧屏上并未形成创作与播出的热潮。2006年《暗算》播出后,谍战剧异峰突起,涌现出一大批同类题材电视剧的制作与播出。2009年《潜伏》红遍大江南北,紧接着,《永不消逝的电波》、《黎明之前》等优秀谍战剧踵事增华,在中国荧屏上掀起谍战剧播出的高潮③,2011年央视的开年大戏又是谍战剧《黎明前的暗战》。可以说,谍战剧是继家庭伦理剧、历史剧、戏说剧、古典名著改编剧、情景喜剧、军事题材剧等之后,中国电视剧创作的又一热点与鲜明的审美文化现象。这其中,优秀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现阶段创作的高峰,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创作模式,并由此拓展了电视剧叙事艺术的审美维度,在英雄形象的谱系与画廊中增添了崭新的人物形象,提升了以往同类题材创作的人文内涵。在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相融合的叙事模式中,赋予文本鲜明的时代感和精神高地的现实意义,优秀谍战剧所提供的新鲜的文化内涵,无疑是不容忽视和具有分量的。但同时,它们也显露出诸多不足之处,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题材的叙事模式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反思,以使它们能够在今后的创作中进入更为开阔与深广的天地。
一 崭新而智趣的“谍语”叙事技巧
谍战剧走红荧屏并不是偶然现象。当下文化语境中,影视作品等大众文化载体要与主导意识形态形成某种包容、互渗与联袂。主旋律作品吸纳大众青睐的娱乐性元素,以增强吸引力与传播影响力;通俗娱乐作品则内蕴主导意识形态及其精神钙质与人文内涵,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艺术图景中,这已是一种常规样态。因此,谍战剧的走红不难理解。因为谍战剧叙事系统中的悬念、惊险、枪战、斗智斗勇,以及隐蔽战线上舍生忘死的英雄形象,他们崇高而坚定的信仰,相关情感的演绎,恰恰使“娱乐意味”与“主导意识形态内涵”获得了自然的融合与衔接。可以说,《潜伏》、《永不消逝的电波》、《黎明之前》、《黎明前的暗战》等优秀热播谍战剧充分发挥与展示出叙事的技巧与智慧,将迭宕起伏的戏剧情节与平凡浪漫的生活诗意相融合,反映大时代背景下的时局变化,在引人入胜的戏剧情境中镶嵌与折射现实镜像,它们珠联璧合、相映成趣,充分满足了观众的审美情趣,赢得了大众现实的共鸣与会心的体味。因此,近年来的优秀热播谍战剧在叙事技巧上,比以往同类作品成熟,它们挖掘与拓展了电视剧叙事艺术的优长,新颖的叙事方式与内涵,恰当融合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娱乐元素,探索出了谍战剧独特的叙事“言语”体系,创造出了崭新的、富于魅力的电视艺术文本。
(一)叙述视角
谍战剧故事吸引人,情节惊心动魄,在叙述技巧上,最重要的是叙述视角的选择。讲述扑朔迷离、拨云见日的情节,采用何种叙述视角是叙事的关键。“叙事角度是一个综合的指数,一个叙事谋略的枢纽,它错综复杂地联结着谁在看,看到何人何事物,看者和被看者的态度如何,要给读者何种‘召唤视野’。这实在是叙事理论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④
谍战剧讲究叙述中多重视角变换带来的神秘与悬疑色彩。间谍身份的隐蔽性、多重性,所置身的复杂环境,使视角的出发点、“透视关系”参差交错,观察的细腻度、层次感,更具“放大”效应。在叙事信息的发送与接受中,“症侯”、“隐喻”的叙述效果被凸显,它们暗含着逻辑推理、解谜猜谜、细节的穿透力,斗争态势的错综复杂,这样的叙事既“炫耀”着叙述者的智慧,编织着叙述的“趣味”,也考验着观看者的智慧,构成审美的愉悦。因此,全知与限知相配合,积极调动观众的“阅读”观看经验,使观众深度参与叙事,并适时吸纳观众的分析视角,是谍战剧叙事的重要“语法”特征。采用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相融合,是目前绝大多数谍战剧的叙述方式。全知视角使叙述者大于人物,纵横捭阖、灵活把控复杂的叙事,从故事的整体与全局上,叙述者知晓一切并掌握谜底与结局。这几部作品的全知叙事在总体上都以“章回式”的布局,用一个接一个的“重点情节”“小单元”编织了丝丝入扣的叙事网络,展示了事件演变的轨迹。那么,这一张张复杂的叙事网络,网络中的“紧关结要”、“疏而不漏”、“出乎意料”,以及人物关系的纠葛变化,就需要一层层清晰的叙述逻辑,以及叙事中的限知视角⑤才能完成。
与全知视角相配合的限知视角在事件的链条上,将一些关键性信息和精彩片断刻意隐瞒。由此,外在事态和深层原委之间出现了“空白点”和“未定点”,叙述便更显精致与委婉,也更考验叙述者的智慧。比如,在各谍战剧中,计谋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计谋是“心机”与“智慧”的较量,它们必然隐藏重要信息,让剧中人或观众不知情,才使得叙事曲径通幽、别有洞天。《黎明之前》中运用了“苦肉计”、“美人计”等,特别是“反间计”的运用,将限知视角所造成的情节悬念与曲折展示得淋漓尽致。我地下党领导水手审时度势,看清国民党军情八局人员间的勾心斗角后,以生命为代价,精心策划诱导敌人“推理”出李伯涵是共党卧底,而真正的卧底刘新杰却是“清白”的。这一桥段不仅要说服敌人,更要说服观众,它必须具备情节的合理性与逻辑的严谨性。剧中以仅限水手一人知情的限知视角,层层推进,上演了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的乾坤挪移的大戏。犹如多米诺骨牌在环环相扣中已被精确推至终点,却又因大的时局变化导致的变数而全盘倒推回来,这是令人不可思议和惊心动魄的。叙事显然具有复杂性和智性的挑战。这里将前面所有线索归拢和梳辨,“理论推导”下,一切疑点指向的是李伯涵,而不是刘新杰。加之新杰在既定时间坦然出现在大家面前,更证实了上述推导的“合理性”——直到此时,所有“蒙在鼓中的人”才明白了叙述的目的。从新杰的视角才明白了水手的深刻意图;从局长谭忠恕的视角才释然了心中的纠结;从李伯涵的视角才明白了自己输在哪里;从八局“同僚”的视角才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结局;从观众的视角才明白了整个迷局的谜底。水手布设的传奇般的“棋局”,实际上正是利用了众人的心理才使行动步骤和人物反映一步步向着他的计划靠近。而对整体叙事而言,限知视角机智灵活的运用,才构建了叙事过程的变数、张力、歧义的复杂解释,使悬念所营造的紧张与焦虑持续绵延,引发观众探究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结局究竟如何的不可遏制的冲动与渴望。而一个精巧的计谋所辐射贯穿的“情节网”与连续性,也正符合了电视剧艺术的叙事规律,并在张弛有度、环环相扣的情节中显示出了谍战剧独特的“语法”修辞特征。
限知视角的隐藏性与谍战剧主人公鲜明的“职业特点”相结合,同样会产生惊心动魄的戏剧性效果。谍战剧主人公神出鬼没,他们“工作时候”的状态与手段,都可以构成一种“典型情境”,并且这些职业特点会导致关键性的情节与突变。像跟踪、窃听、密写、发报等“常规化”的间谍戏在谍战剧中是被大量使用的,而且一般是通过限知视角来完成。因为限知可以使这些“手段”包含更为丰富的信息,也更加具有神秘色彩。优秀的谍战剧在这些手段的设计上,不仅仅限于一般化的“常识性”“展示”,更着意于将间谍手段与情节的推进密切融合,并使“手段方式”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赋予情节新颖的智趣感。比较有代表性的段落是《黎明之前》中,刘新杰替谭忠恕宴请段校长,他接到谭的电话,被告知共党水手部下已在审讯中死亡。刘明白,这意味着自己原打算的营救计划失败了,而且背着自己提审要犯已说明谭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一气之下掀翻了面前的酒桌,想冲出去拼个你死我活。但他突然发现酒桌底下竟然安装着窃听器。这时他反而不能走了,因为段校长就是敌人不知道的水手。如果不继续“演戏”,他和水手都将暴露。刘恢复平静,水手到来后,他口头上说的是应酬的话,却用眼神示意,用手指敲击“密码”,将真实信息告诉了水手,使他和水手避免了近在咫尺的危险。这里有层层的限知视角:先是新杰的未知,然后是水手未知,最后被蒙蔽的是谭忠恕。层层限知使叙事层层递进、抽丝剥茧,最后水落石出。这一段落的设计是缜密而精巧的,一个“窃听”的核心叙述聚焦点,在限知视角的铺垫下使整个叙事段落显得一波三折又珠圆玉润。因此“职业化”典型情境是一种明处与暗处的设局与解谜,是“游戏”双方支配与应对关系的集中体现,谜语越不好猜、迷宫越复杂,“游戏”越有趣。限知视角无疑增加了迷局的难度,使叙事更加花样叠出、波诡云谲。
毋庸质疑的是,谍战剧中限知视角带来的最为精彩的情节桥段与最鲜明的叙述风格,就是悬念。种种欲擒故纵、草蛇灰线、预警暗示、千钧一发、柳暗花明,是悬念使叙事更加充满波折与活力。悬念包含着惊险,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惊险。在谍战剧中如何把握悬念与惊险也是重要的“语法”内容。
悬念大师希区柯克曾作过形象的比喻:如果谈话时不知道炸弹会爆炸,那么爆炸的瞬间带给观众的是片刻的震惊;如果知道5分钟后炸弹会爆炸,那么这5分钟内每一秒都会令人倍感煎熬,并会使观众十分关注这个谈话的场面。也就是说,预示危机会造成有力的悬念效果。因此,悬念的设计是一种富于智慧的叙述手段,可以引发观众长时间的情感投入,是从内心深处与剧情和人物产生交流。在这几部优秀的谍战剧中,对悬念的铺设往往贯穿始终,并在某些单元与桥段为叙事带来“乱花渐欲迷人眼”却又从容不迫、井然有序的独特效果。比如,在《黎明前的暗战》中,观众已知,中共派遣的与程潜秘密会谈的特使,由于叛徒出卖已经暴露,敌人在火车站要实施诱捕。在已无法通知特使的情况下,我方派潜伏的李浩在火车站冒险接头,试图打乱敌人的计划,而敌人竟让同样潜伏在保密局的我方人员天济做接头“诱饵”。这时,悬念就产生了——“炸弹的爆炸”已不可避免,而叙述视角是我方“当事人”不知情,情节正一步步按“爆炸截点”顺利推进,这样的悬念设计就具有了惊心动魄的意味。而其后在悬念实施过程中节外生枝所带来的情节的突变,就使叙事具有了峰回路转的效果。这种效果是靠限知视角来完成的,李浩会做什么?天济该怎么办?特使到达后能否被挽救?突然出现在现场的神秘狙击手又是何方势力?几方的行为与想法是互不知情的,而观众则一层层逐渐获得谜底。一个悬念带来一系列情节的疑问,对观众产生持续而强烈的心理震撼。犹如“螺蛳壳里做道场”,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限制中,限知视角却充分施展出强大的功力,使叙述中的悬念不是平板的,而是一个玲珑的多面体,营造出戏中戏、谍中谍、谜中谜的叙事效果。
通观优秀的谍战剧,将悬念与重要功能性的、会引发接踵而至的核心事件密切关联,是其运用限知视角完成叙事情节的共性与优长。其中,富有意味的设计是,“我方视角、立场”的悬念。比如《潜伏》中,让翠平去完成刺杀陆桥山的任务,观众已知何时何地怎样动手,也知道游击队长出身的翠平身手不凡,但性格毛糙的她关键时刻能否胜任?是否会发生意外?与敌方设局匡算我方不同,前者观众是在焦虑的过程中希望出现意外,后者使观众在揪心中希望结果如愿以偿。叙述中种种暗示与提示的“吻合度”也是观众更为关注的细节。翠平顺利完成任务,不仅解除了余则成的危险,更标志了自身的成长,是剧情推进上关键性的一环。因此,富有悬念的功能性事件联结着人物命运,使情节具有鲜明的逻辑指向,人物行动中的一举一动,那些或隐晦或明朗的意图,都被置于意义丰沛的背景中,在“规定情境”与“可能变数”之间,“添丝补锦、移针匀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将推理、猜测、预置、干预、解释等叙事包袱一一做足,在欲罢不能的情节吸引力下,使观众获得独特的审美感受。
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相结合,营造出“影灯漏月”般的叙述效果——若明若暗、影影绰绰、天机一线,“横看成岭侧成峰”,将一般性的叙述单元与表述情节的“语词”,结构得更加具有悬念、惊险的效果,使叙事节奏紧张激烈,从而形成了谍战剧独特的、耐人寻味的智性叙事风格。
此外,在叙述视角的问题上,我们注意到,这几部作品大多使用第三人称“旁白”,却多是简单的情节连贯,这是一种“非智性叙述”。但从叙述技巧而言,如果使用“旁白”,就应不仅为了连贯情节,而应使其具有个性与丰富的色彩,能够赋予文本某种特点,才是风格化“智性叙述”。像揭示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旁白”就独具韵味。谍战英雄表面的不动声色下,往往隐藏着巨大的内心波澜,及时反映主人公真切的感受,可以丰满人物的形象,又与情节有机融合,从而产生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像余则成看到牺牲的左蓝时,表面平静,旁白却是“让悲伤尽情地来,但也要尽快离开”;李侠和被审讯的路梦惠如仇敌般撕扭在一起,旁白却是“这片刻的幸福来得太突然也太短暂”……可以说,如此“表里不一”的揭示人物情感的旁白,相对于简单连接情节的旁白更具审美意蕴。而《黎明前的暗战》全剧没有旁白,以一种客观冷静的第三人称叙述,将戏剧性的谍战故事依托于湖南和平起义的真实史实,刻画了众多历史真实人物,营造了更为宏阔的时代氛围,给谍战剧叙事开辟了新的叙述视角。具有独立个性的“叙述者”/旁白,文本就在强调“讲述”;隐藏于幕后的叙述,就是“展示”的叙述方式。⑥运用“讲述”/旁白,就要使之获得独立风格;运用“展示”,就要使之尽显叙述智慧——这应是今后谍战剧在叙述方式上努力的方向。
(二)叙述势能
“在叙事结构当中具有某种动力关系,推动着结构线索、单元和要素向某种不得不然的方向运转、展开和律动,这种动力关系,借用一个近代物理学的术语,便是‘势能’。”⑦在这几部优秀的谍战剧中,叙述势能是很鲜明的。故事的表层情节结构与内蕴的叙事动力和能量被通盘布局。表层叙事是符合“动素模型”的“常规化”叙事内容,主人公被放置于复杂的斗争环境,在刀尖上舞蹈,各种计谋与行动掀起叙事的旋涡与风暴。而在常规叙述内容之外,这几部谍战剧充分挖掘了各个人物之间的性格矛盾与复杂关系,形成弓矢相搭的相互间的张力与弹性,从而使叙事展现出别样的势能意蕴。最为有代表性的情节设计是主人公卧底的“小单位”内部“领导”、“同事”间所形成的勾心斗角。在怀疑与信任相交织的游戏中,在尔虞我诈的相互利用中,叙事因“人事”更显矛盾重重、复杂多变。
如果说表层叙事结构中,那些让观众牵肠挂肚的与敌人一系列心智的较量,构成了九曲十八弯的叙述的重要推动因素,那么,作为谍战剧内核的正义指向、正确信仰的力量,不可扭转的历史、时代潮流,则成就了谍战剧精神的高度,构成了最具推动力与最为根本性的叙述势能。《黎明之前》里,上至局长,下至各个处长,都专业过硬;《潜伏》中的李涯也具有坚定的精神信仰;《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今井一可谓是机关算尽;《黎明前的暗战》中,司马楠心思缜密、手段毒辣。但是,他们都逆潮流而动,一时的胜算改变不了最终失败的结局。由鲜明的叙事立场构建起叙述势能,是这几部谍战剧将主旋律内涵表达得自然与深切的高明之处,同时显示了谍战剧主导意识形态叙事的天然优势与现实意义。可以说,这样的叙述势能也构成了谍战剧最基本与牢固的叙事结构与“语法”基础。
叙述势能的建构在充满“戏剧性”的谍战剧中,还需要在“常量化”、“同质化”的情节中表现“富于包孕的片刻”与“绝境状态”,这也是使叙述具备势能的重要“语法”规则。
“富于包孕的片刻”是18世纪德国文艺理论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出的,他认为画家应挑选整个动作里最耐人寻味的“片刻”来表现,而不要画故事的“顶点”,因为一达顶点,事情的发展已到尽头,不能再有新的“生发”。实际上,对于任何艺术而言,发现与描绘“富于包孕的片刻”都是使艺术获得光彩、产生动人魅力的“密码”。对于叙事艺术,特别是将时间与空间融为一体的影像叙事艺术更是如此。在每一组的动态叙事过程中,在某一片刻,一定蕴涵着某种意义,只是有的包含着丰富的叙事与意象信息,有的则蕴涵量小,只是简单过渡与交代。在优秀的谍战剧中,精巧地设计与运用“富于包孕的片刻”形成情节结构中的内在张力,建构叙述的强大推动力即势能,是一种独特的叙述技巧。玄妙紧张中的“关子”、“急处”、“最后一分钟”等,就体现了趋向“顶点”的“富于包孕的片刻”。像《黎明之前》中,医务处长马蔚然建议以全局体检的方式,排查上身有枪伤的卧底。新杰不得不走进医务室,脱去上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急处”与“关子”,他一旦被检出枪伤,必将暴露。在这一“片刻”,叙事的能量是很大的,它所包孕的情节悬念、人物命运具有相当的“位置势能”高度和“惊险指数”。正是这一“片刻”使叙事用倒叙导入对新杰与马蔚然关系的交代,说明了马蔚然保护新杰的原因。因此,当“顶点”处局长进来追问情况时,新杰自然安然无恙。可见这个片刻处叙事信息的重要性,包含着可“生发”的种种可能,“顶点”处只是水到渠成的一般性结果交代。再比如《潜伏》中,余则成作为军统特务成功刺杀了汪伪骨干李海丰之后,戴笠派特派员在一饭店向余传达了嘉奖令。余走出饭店的“刹那”却看到刚刚还一本正经向他传达“上谕”的特派员,此刻却和一群日本狗男女混在一起,本来余就对国民党前途已持有怀疑,看到这一“情景”更产生了信仰的幻灭感。这一“片刻”包含着丰富的社会信息和人物深刻的精神世界,它所包孕的力量犹如压垮一峰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彻底改变余则成的人生观,为叙述其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起到恰当的铺垫作用。因此,“片刻”往往会改变主人公的人生命运,它包含着“启示性”的信息,小小的“片刻”实际上是使整个叙事生发出一系列悬念的“新生点”。可以说,“富于包孕的片刻”在这些优秀的谍战剧中往往是急风骤雨的前奏;是强大台风的“风眼”;是九曲十八弯的转捩点。它们暗藏玄机、出人意料,有力推动叙事或曲径通幽、或抽丝剥茧、或斧劈千仞,向着更深的层峦叠嶂或别有洞天、豁然开朗处前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一般性叙事不同,在谍战剧中,这样的“片刻”其逻辑关系必须是成立的,严密、合理的,否则会弄巧成拙、功亏一篑,甚至还会解构整个叙事与人物关系。
在谍战剧中,制造叙述势能的另一方式,是建构“绝境”。也就是,一次次将主人公推向束手就擒、无计可施、无路可退的“绝境”,然后让其绝处逢生。就好像“逃脱魔术”一般,让观众清晰地看到主人公是如何被一个个枷锁扣紧、被一层层布罩裹严,然后被塞入难以回旋的狭小空间,但是,他却能最终神奇般地挣脱这层层桎梏,平安无事地回到你的面前。正可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比如《黎明之前》中,谭忠恕为了考验新杰,故意让他去焦化厂抓捕水手下线,新杰已没有时间通知自己人,而自己人也不知道敌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根本无法逃脱。叙事一层层交代了“上锁”的过程,在这样的“绝境”下且看他如何“解套”:新杰将计就计,打死身边的耳目,然后将子弹射入自己人的肺部,使他暂时保住性命,以图日后再营救,而且不会被八局立刻提审,而自己又可被证实对行动是积极而忠实地执行了。《潜伏》中,李涯搞到了能够证明余则成是共产党员的录音带,吴站长放给余听,在“铁证如山”面前,这几乎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绝境”,但余急中生智,指出录音带是可剪辑、可复制的,并以一本“权威”的“间谍专业书”反诉李涯使用的是拙劣的、混淆视听的手段,从而“洗白”了自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被带到波旁酒店,他知道妻子何兰芬就在店中,一旦被叶兴城、冯小昆看到就证明是自己通风报信,那么也就暴露了。但“天无绝人之路”,李侠在酒店旁看到了一家烟花爆竹店,于是他借故点燃了烟花店,噼噼啪啪的爆竹声警示了店内的何兰芬,她迅速撤离,于是李侠躲过了一劫。与变魔术看不见逃脱的过程不同,谍战剧设置绝境所营造的叙述势能正带来“如何解困”的种种艺术表现,展现出叙述的技巧与魅力,会令人产生倒吸一口凉气、如释重负、叹为观止的深层次的审美情感。应该说,前两例“解困”的招数更好,因为它们是从事件与人物的“内部”生发与展开,是让主人公的智慧、勇气、胆识来成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靠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与逻辑推理来推动情节,比起“临时”与“偶然”地借助外部环境或外因来改变事件进程与方向,更具叙述的智慧。
实际上,不仅仅是绝境的设计,对于谍战剧整体叙事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应加强叙事的逻辑严密性与情节推导的合理性。谍战剧叙事的重要支撑点、与观众的信息交流点,是要靠严丝合缝、丝丝入扣的情节,这样的情节“立得住”,整个叙事与人物形象才能清晰、真实。因此,叙事当中只有严密的逻辑才能带来探幽历险的快感,使叙事层次清晰可信。如果出现过多的简单化处理的偶然性、巧合性来推动叙事,就会使叙述露出不严密的马脚,“叙述智慧”也会打折扣。这几部作品中都有一些重要的事件是靠剧中人“无意中”往门口、窗边一站,就听见、看见的“非逻辑”、“非智性”的叙述手段来推动。实际上,这种“临时空中抓来”的“讨巧”处理,跳跃在事件的内部逻辑性之外,会大大降低事件的可信度及与观众的交流感。而从人物性格、心理与事件“内在逻辑”出发的叙述,则更具逻辑的合理性,也能建构起蓄积极久、不可遏制的叙事推动力。因此,使叙述清晰严密,使情节如“常山蛇势”,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具有饱满的内蕴叙事动力,创造性地编织审美“空筐”,让受众的期待视野在理性与感性相交织的叙事图景中获得深层次的愉悦。这是谍战剧“智性叙事”的基本“语法”内涵,也是今后创作中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方面。
二 类型借鉴与融合
作为较成熟的电影类型划分与研究而言,“在刀林剑簇、水火不容的冷战分界线两侧,众多电影文本的叠加令间谍题材成了电影叙事的类型、至少是亚准类型之一。”⑧这里的“类型”应包括特定的叙事规则与观众的熟稔程度,以及二者相叠合所形成的会意的审美趣味。如果将电影间谍题材叙事类型的概念引申到电视剧文本的创作上,可以认为谍战剧是一种“类型剧”。也就是在这一类的题材创作中,有其既定的叙事“常量”,已经形成了特定的叙事“语法规则”,具有鲜明的满足受众审美旨趣的创作倾向,并通过一定程度的热播产生了“累积性”效应。⑨而在目前优秀的谍战剧创作中还出现了一种借鉴家庭伦理剧创作特点的“融合型”创作方式,这就使得当下中国优秀谍战剧的叙事特征具有了鲜明的东方特色与独特的审美意蕴。
在中国的电视剧创作中,“家庭伦理剧”是一种广受欢迎、深度契合观众审美口味,并反映了中国传统人伦文化特点的创作题材。“家庭伦理剧”中的“常量”,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叙事元素,描绘出“身边的人”的鲜活质感,折射与反映出现实、国家与时代的变化。在核心事件里镶嵌进原汁原味的生活素材与人物间活泼生动的对话,更能反映电视剧叙事艺术的特长。因此,“家庭伦理剧”中最重要的是“家庭生活”的情趣与喜悦烦忧,其叙事色彩的浓淡深浅,全凭一件件“家事”来皴、点、渲染。
谍战剧的核心事件是围绕刺探情报、抓出卧底、实施计划等来展现,剧中人物所置身的环境是复杂的;行为与动机是明确的;话语暗藏玄机、“字字珠玑”,家庭生活中的家长里短、卿卿我我,显然与紧张的节奏、严酷的斗争不符。但是,近年来,优秀的谍战剧却以巧妙的叙事技巧将“家庭伦理剧”中的部分“元素”进行改装、置换,将亲切的家常话、温馨的家庭聚会,含情脉脉的情感编织进环环相扣、紧张激烈的“核心事件”叙事中。谍战类型的常量元素与家庭伦理类型的常量元素碰撞、融合后,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优秀的谍战剧不仅仅通过“戏剧性”的情节悬念产生了对观众的吸引力,而且通过“家庭戏”产生了拉近当代观众时空距离的审美效应,并使叙事节奏变得疏密有致、张弛有度。由此,这些谍战剧崭新的叙事特点与叙事风格也被凸显出来。因为,如果说谍战剧中与“谍”相关的一切所产生的“陌生化”与“传奇色彩”令观众获得刺激性的审美愉悦,那么这其中蕴涵的家庭元素则给予观众“亲切感”与“熟稔度”,令观众获得温暖醇厚的审美感受。这两种叙事类型各自都会制造出符合当代受众欣赏电视剧艺术的审美感受,有其独特的“类型属性”,而二者相融合犹如两种色调相调,变化出一种更为奇妙的绚丽色彩,使观众既品味到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隐形战线上英雄们的神秘与神勇,产生望尘莫及的崇高感与敬佩感,又品味到那些来自日常生活状态下的平凡人生的点点滴滴,及其所渗透、携带出的淡淡的甜蜜与忧伤,令人百感交集又回味无穷。应该说,这就是优秀谍战剧类型融合的最为鲜明的审美意蕴。
比如,《潜伏》中,翠平的形象鲜活生动,正是她和余则成假扮夫妻的种种“家庭场面”,使叙事变得风生水起、诙谐有趣。实际上,在原著文学作品中,游击队长翠平始终也没能和主人公建立起夫妻间的情感,她自始至终都不能适应地下工作者的角色,孤独、郁闷、固执,一杆烟枪不离手,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是一个崭新的“地下工作者”的文学形象,并且是一个有文学深度的独特形象。而在电视剧中,叙事将她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了通俗的、符合大众审美期待的女性形象。翠平很快变成了余则成的得利助手,她的性情也由粗鲁莽撞渐渐变得敏感而温柔,她学习文化、谍报工作、甚至还学会了交际,她与余则成之间的感情不断递进,产生了亲人间的牵挂与默契。翠平身上种种“小女人”的性情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更符合受众对她的理想化想象。《黎明之前》中,谭忠恕上有老母、下有小儿,又与夫人感情甚笃,家庭戏使这个反面角色具有了不少人情味;刘新杰和顾晔佳的感情戏则为紧张的剧情增添了舒缓柔和的质感。《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清晰而细腻地描绘了李侠与何兰芬的感情波折,以及相濡以沫的家庭生活。《黎明前的暗战》中,同样设计了天济与其兄长一家及与女友温馨的家庭情境。值得注意的是,与家庭伦理剧中许多“无事之事”的描写不同,谍战剧里的家庭戏最终要和人物命运、特别是使命任务的完成息息相关。像余则成教翠平进门看香灰的痕迹;讲说梦话的故事;学母鸡护蛋边叫边扇动翅膀打转的样态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生活中的“闲笔”,是感情线索上的“动情点”,实际上,它们是叙事的“炸点”,在不经意间铺设与埋伏,与剧情密切联系,前后呼应、草蛇灰线,最终都成为叙事上的关键环节。家庭内外、生死瞬间,处处暗藏着危机,地下工作者的“家庭生活”随时受到敌人的监视与考验。逢场作戏也罢,假戏真作也罢,在时时不能掉以轻心的危险的工作环境中,他们的“家庭生活”如履薄冰,正因如此,那点滴的温馨与瞬间的安宁才更令观众感动与唏嘘。
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大量热播谍战剧都运用了“假夫妻”模式,特别是一些谍战剧滥用这一结构方式,胡乱勾兑温馨家庭戏与紧张悬念戏相融合的“鸡尾酒”,被观众多有诟病。戏剧传奇中的世俗图景如果笔墨运用不当,则会使剧情有拖沓冗长、游离戏核之感。因此,在表现生活的温情与细微处时,要凝练笔墨,时时校正与对准人物的性格塑造与情节铺陈。而找寻新的贯穿性人物关系,特别是男女主人公关系,已是叙事结构上必须要突破的方面。《黎明前的暗战》中将男女主角设置为较量中的“对手”关系,颇具新意,拓展了人物关系的情节处理手段,对今后谍战剧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三 崭新英雄人物形象的叙事设计
“英雄情结”是受众永恒的内心审美渴求。作为类型剧,谍战剧同样要塑造鲜明的英雄形象,才能从心灵的深层打动观众。在复杂的叙事情节中,着力凸显英雄形象,不将人物湮灭于情节网络,而是用人物的性格、个性打戏剧的“结子”,使情节成为人物性格的历史与背景,优秀的谍战剧在英雄人物形象叙事上呈现出诸多新意。
(一)多侧面叙述的“这一个”
谍战剧中的主人公是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他们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方式决定了与“正面战场”的英雄具有不同的“质感”。虽然不能“横刀立马”,但“智勇双全”、特别是具有“传奇色彩”,依然是这些英雄基本的底色。实际上,纵观世界“谍海”,无论是007系列;好莱坞黑色电影中的主人公;苏联、东欧谍战片中的孤胆英雄;中国“17年”经典“反特片”中的男主角;还是香港警匪片中的卧底,主人公无不具有“非奇不传”、智慧超群、信念坚定的特质。因为,英雄在任何一种社会文化以及不同的信仰、价值观、社会动向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英雄是故事叙述和民族文化精髓中固有的东西。而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认同中的英雄,一定闪现“非同凡人”的光辉亮点,并由此成为大众百姓理想的象征与精神的烛照。由传奇、非凡而脍炙人口、喜闻乐见,这正是中国民间叙事传统与大众审美期待中最为典型化的表现。而谍战剧中“间谍”的身份又被赋予了一层神秘感,他们神出鬼没、明码暗语、化妆易容、随机应变,他们的感受与处境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黑夜一半是光明,如此种种都比普通英雄更具鲜明的个性,也更增加了对受众的吸引力。在这些优秀的谍战剧中,英雄主人公都被叙事赋予“过人之处”:余则成含而不露,外表木讷、内心精明;刘新杰貌似玩世不恭,实则集智慧、果敢、潇洒于一体;李侠聪明之极,可以在多方势力中游刃有余;肖天济虽然年轻,但聪明果敢、内心坚强。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信仰执著。正是崇高的信仰赋予他们不屈不挠、从容无畏的生命底气,使他们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与敌人智慧地周旋、斗争到底。威廉·阿契尔认为:“要使戏剧的兴趣能保持长久,就必须要有人物性格”,⑩这样的性格鲜明的谍战英雄以其自身“职业化”特色,赋予叙事类型化意味与大量充满悬念的“戏剧性”,而英雄主人公性格魅力中所包含的与受众审美期待相对应的过硬的“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正是使叙事获得吸引力的稳妥而有效的手段。人物与叙事相辅相成、紧密配合,英雄特质之于当代受众审美心理的补偿,他们的崇高信仰之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弘扬,都使谍战英雄成为了当代大众文化的一种理想代言。
但是,从全球大众文化审美趋向看,“对英雄的关注此消彼长,近年来,结构——解构——后现代潮流一波接一波,那种只盯着主动果敢型的英雄的传统趋于弱化。”(11)而在中国“倘使说过去曾把‘写英雄’当作基本目标和规范的话,如今则把‘写凡人’当作时尚”(12)。因此,在这些优秀的谍战剧中,对英雄形象的刻画,也因深刻的时代文化烙印而凸显出新的特点。除了上述“典型化”、“类型化”的英雄塑造角度,叙事还按照具备“多面性”与“复杂性”的“圆形人物”的“描画法”,布设多重“动情线索”,来表现其作为“凡人”的复杂情感世界与心灵的深海,使人物更具性格化特征。如果说,作为类型化叙述的谍战英雄多表现其行为、动作、执行任务时种种“职业化”的娴熟——这是以“外视点”来观照与塑造人物;那么,将人物的心灵与情感进行剖析,展现其“非符号化”的个人性情与内心境界,就是将人物更为深厚的潜在价值挖掘出来,赋予人物血肉丰满的生动性和更为饱满的艺术魅力。余则成、李侠、刘新杰、肖天济并不始终都是坚强的人,他们都曾有深刻的心灵创伤体验:新杰在“休眠”的10年间“能够谈笑和拥抱的”,都是敌人;他亲眼目睹了许多战友和亲人的牺牲,却还得面不改色。李侠不得不亲自审讯自己所爱的路梦惠,并眼睁睁看着她跳楼而亡。余则成也一样,不动声色地看着牺牲的左蓝,甚至还笑了一下。肖天济同样多次当场目睹了自己同志的牺牲,却只能在无人处痛哭。“间谍”的身份使他们必须隐藏自己真实的感情,承受着深深的心灵刺痛与灵魂的撕裂,却又无以言表、无法排遣,他们无疑在受着“双重人格”的煎熬与折磨。我们注意到,叙事在紧张的情节节奏外,都会花一定笔墨来描写英雄背过敌人时的种种“反映”,以表现他们内心的“脆弱”。比如,《黎明之前》剪辑节奏较快,但在表述新杰情感反映时却运用了“长镜头”,镜头里的新杰步履踉跄着晕倒,或是目光呆滞、继而掩面恸哭,通过“长时间”、有层次的表演,反映出人物难以自制的痛苦。而他怀抱牺牲的顾晔佳时,更是以泪流满面和激烈地捶打方向盘的动作,鲜明地“感性化”地表露出他“痛苦到了极点”。“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谍战英雄实在是比“常规英雄”更多了几分苦楚与难言之隐。种种潸然泪下与黯然神伤将英雄的“凡人”心态揭示出来,对人物“两难境地”中极致化情境下心理状态的细腻刻画,如同多面的折光,延伸与丰富了人物个性。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叙事中类型融合所营造的种种亲情与家庭场面,使硬汉英雄又多了几分“家常”与“柔情”。“英雄泪”、“儿女情”镶嵌在铁骨铮铮、果敢坚毅的“常规化”英雄气质之中,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表现出人物不同的性格侧面。而主人公暴露出的种种缺点、人格上的不完满,也使英雄具有了需要“成长”与改进的凡人样态,随着情节的推进,人物心理空间层次相互交织、联系,展现出个性、性情交叉与复合的多重性。在隐蔽战线的特殊环境下,多样性格素质有机融合后,英雄人物细腻、色彩饱满的性格世界,使之成为了鲜活的“这一个”。
(二)叙述人物深刻的命运感
谍战剧紧张激烈,戏剧冲突与故事悬念似乎构成了最大的吸引力。而实际上,“对观众来说,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人,只有他们了解了冲突中的人物,关心人物的命运,才会真正感受到冲突的尖锐程度,才能真正感受到冲突的意义”(13)因此,优秀的谍战剧讲述英雄人物表面波澜不惊,实则波涛汹涌、起伏跌宕的命运感构成了对观众更大的吸引力。比如悬念是构成与观众强烈“交流感”的情节设计,而在此之上人物命运的悬念是更加令人揪心的“动情点”。余则成、李侠、新杰、天济都是从一开始就受到怀疑,成为被重点调查的对象,他们能否化险为夷?无疑,这些人物的命运一上来就构成了全剧最大的悬念,时时刻刻在提示着危机,刺激着观众的神经。所以,往往不是“潜伏”的“故事性”更好看,而是“潜伏”中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更动人。
命运之中,作为“谍”的身份,英雄人物还有一层特质被表达得耐人寻味。一般的“正面英雄”是在与众多战友并肩作战,与敌人明枪明箭、拉开架式。他们的结局也是“亮堂堂”的,或者慨然赴死、或者凯旋而归,各得其所、痛快淋漓。而隐蔽战线的特殊性,使得谍战英雄在一种深刻的孤独感中去期待,在隐忍中坚持,胜利完成任务后,也不能“功成名就”,因为还可能要继续潜伏或者要隐姓埋名一生,这是他们命运中的必然。新杰与谭忠恕曾探讨了水手是无名英雄,“有谁会记住他的名字呢”;出生入死的新杰后半生亦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余则成继续潜伏,两行清泪蕴涵多少世事沧桑与千言万语难以言说的情感。这样的叙述笔墨无疑赋予了英雄悲壮情怀与悲剧色彩。因而,谍战英雄九死一生换来的这种多少有些暗淡的命运结局,往往引发观众无限惆怅之感,同时也唤起了对这些英雄崇高的精神与坚定的信仰的崇敬之情。
“悲情英雄”命运的“劫数”有时就体现在他们自己的“抉择”上。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明白表示某种抉择,人物就有性格”。谍战英雄的“抉择点”在命运的道路上俯拾即是,有时他们可以深思熟虑,像余则成人生信仰的改变;有时就是刹那间要作出的反应,而这一抉择往往就意味着命运的重大转折。余则成在撤退台湾前毅然决定继续潜伏,在飞机场看到了并未牺牲的翠平,他只能选择相逢而不相识,让分离成为永诀,种种命运的残酷感令人喟叹。可以说,英雄主人公为了崇高的信仰甘愿赴汤蹈火、虽九死其未悔的革命者的意志品质,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义薄云天的侠义精神,都在抉择的答案中得到了鲜明的、淋漓尽致的彰显。
优秀谍战剧对英雄主人公逼近情感灵魂的描绘,以及充满生命博弈的命运线索建构,使人物形象获得了充盈而有深度的展现,赋予了他们当代审美视角观照下崭新的人格内涵与美学品格,确立了主旋律文本人物形象的新谱系。但应强调的是,英雄人物命运轨迹中行为动机的合理性,其种种失意、得意、转折、突变,要符合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合情合理、情理交致永远是保证人物真实可信、血肉丰满的基本准则。此外,叙事应有对主人公“前史”的明确交代,这样才能使其后对人物的行为动机与心理线索,展现得入情入理。像余则成的整体设计就比较完美,而李侠前史的缺失、新杰10年“休眠”的空白,天济前史交代的不充分,就使人物“前景”处的行动与思想显得相对缺乏根基。如何表现人物“前史”,使其具有贯穿合理的性情与人格线索,应是谍战剧叙事需要“补课”的方面。
近年来优秀谍战剧拓展了电视剧艺术的审美空间,在叙事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体现了大众文化视野下主旋律作品的审美意蕴,为今后同类题材的创作积累了经验。它们的热播也构成了鲜明的文化现象,体现了深具时代内涵的、对精神信念的呼唤与追寻,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但在谍战剧大量播出的热潮中,创作者也应清醒地看到,受众已表现出审美疲劳。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复制”、“跟风”,或在艺术表现上急于求成的“变异”与“突破”,都不能使作品达到新的审美高度。要想创作出新的经典与优秀之作,冷却降温后的进一步反思,显然已必不可少与迫在眉睫,只有这样才能打开新的局面、臻至新的境界。
注释:
①即以间谍为剧情主人公,反映他们战斗、生活的电视连续剧。以下简称谍战剧。
②参阅吴素玲著《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③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仅半年来就有50余部谍战剧陆续播出。参阅新华网,2009年10月26日。
④⑦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第76页。
⑤限知视角理论参阅罗钢著《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⑥罗钢:《叙事学导论》,第164页。
⑧戴锦华:《谍影重重——间谍片的文化初析》,《电影艺术》,2010年第1期。
⑨作为“类型剧”的谍战剧,遵循“类型叙事”的规则。具有“间谍”身份的主人公与“动素模型”是最基本的叙事常量。有“类型”就有“超类型”与“反类型”,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在叙事上试图突破“常量”的谍战题材电视剧。像《追捕》、《风语》等,主要在英雄主人公/主体的设计上产生“变异”,力图打破情节的“动素模型”与二元对立,从“非间谍”的身份与角度,来观照特定事件下人性与情感的纠葛。《借枪》则使传统目的“客体”产生“变异”,从而牵动主体一系列行为的偏离常规、与众不同。这样的设计挑战观众既定的审美趣味,必然要求有更多的情节吸引力与逻辑合理性,以及充分的行为驱动力、正义的内涵。目前,这类作品虽有一定的突破,但叙事还未能和观众建立起充分的审美共鸣。如何在突破“常量”的同时,给叙述加分,增强感染力,今后还值得进一步探索。
⑩(13)转引自谭霈生:《论戏剧性》,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91页,第70页。
(11)[美]威尔·赖特:《流行故事中的英雄》,原载美国《大众电视》杂志,王俊花译,《世界电影》,2008年2期。
(12)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
标签:黎明前的暗战论文; 电影叙事结构论文; 电视剧论文; 设置悬念论文; 永不消逝的电波论文; 黎明之前论文; 潜伏论文; 影视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谍战电视剧论文; 战争电视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