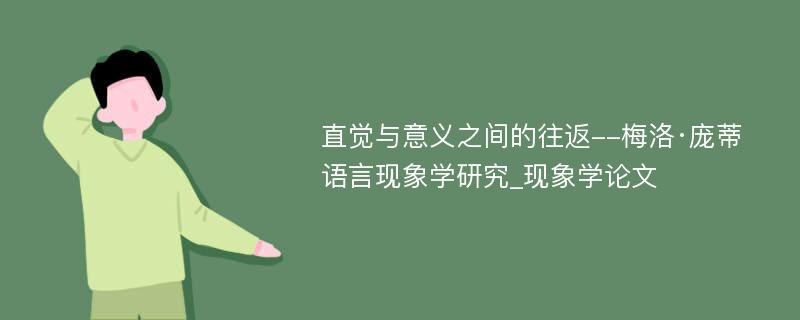
往返于直观与意义之间——梅洛-庞蒂的语言现象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直观论文,意义论文,语言论文,梅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7-0054-08
在做思考活动时,诚如胡塞尔所言,我们一般只生活在含义的意向中,“仅仅生活在语词意义、语词意指的进行中”①,而根本不注意含义的表达形式。但是,一旦我们开始意识到不能很好地表达某个念头和思想,表达的形式如词语就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想对此做认真的理论性思考,有意识地从一般而言的词语的意义回溯到其表达形式,那么一个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作为纯粹的只是一般的“实体”的表达形式是如何可以突然间有了“活的”灵魂,获得生机,而可以去意指意义的?换言之,语言表达意义、指称事物的能力是以什么为基础的?
虽然对这一问题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有众多哲学家在回答方式上却是一致的,他们都采纳了一种意识的、先验的模式,试图用一些先验的要素和结构来解释不同领域间所具有的一一对应关系。本文将简要评析这些关于表达问题的观点,并阐述梅洛-庞蒂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策略,彰显其语言现象学的理论意义。
一、表达何以可能——意识的、先验的回答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探讨了意义行为,他认为,一般的直观行为并不具有自己的意义,其意义是叠加于其上的表达行为赋予的。而表达行为的主体是一个意识的主体。具体到感知这一最为基础和典型的直观行为来说,它“并不构造含义,甚至都不部分地构造含义”②。我们对感知加以表达而形成的意义并不是感知本身就具有的意义,因为当我们对感知加以表述时,同一个感知可有不同的表述,而这些表述具有各自不同的意义。再者,感知者每一个位置的细微变化都会引起感知本身的变化,不同的感知者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感知,因此,我们对感知的表达中呈现出来的意义就不可能是感知本身的。而且,我们的表述一旦形成,一旦表达出来的事态被给予,其含义就不再受具体的感知对象、感知处境以及用来表述的语音的束缚;它会作为新的对象性存在,具有知性对象性的随时性和非实在性。如果说感知对被表达出来的意义还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在胡塞尔看来的,感知可以规定意义的方向,“无论这些陈述的意义如何变化,它还会‘指向’感知的显现内涵”③,感知对象或者其部分永远是我们表述行为的基底。但其作用仅此而已。
对胡塞尔来说,感知本质上不具有自己的意义,这不仅对一般意义上的感知及被感知者而言,而且也是对特殊的可感知形式而言——表达的实体形式如声音和文字这些直观形式也是如此,它们不具有“自己”的意义。它们之所以被我们认为具有意义,是因为同时作为感知者和表达者的意识主体的赋义行为,一种精神性的灌注行为。表达行为,或者说符号行为,起始于直观的感知行为,但它“抛弃”自身,转向意义。
如果一个词语已经具有了意义,那它也不能总是静态地处在纯粹观念的世界之中:我们总是用意义去指涉世界中的事物和事态。于是,这样的问题也会凸显出来:何以意义可以去表达“实体”、事态,或者,用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说法,空洞的含义意向是如何在直观中获得充实的?
与这些问题相关,康德曾经站在先验主义的立场上,试图用图型说来说明纯粹的知性范畴和概念何以能够应用于感性直观对象的问题。在他看来,“图型真正说来只不过是现象或者一个对象与范畴一致的感性概念”④。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则试图通过语言的先验主义来说明语言何以能够描述世界的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思想和语言三者具有共同的逻辑形式,或者说先天地就是同构的:思想是世界的同构性反映或者说投射,而语言是思想的同构性表达或者说投射,在世界的各个层面——对象—基本事态或基本事实—事态或事态—逻辑空间或世界,思想与语言都有对应的东西相互映射。思想和语言虽然不是世界本身,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图像,但它们是世界的逻辑图像。所以,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可见的世界之所以能够得到描述或加以言说,并不是因为它们具有形貌上的相似性,或是同类的,而是因为“图像与被描绘者具有共同的逻辑的摹绘形式”⑤。
这些先验主义的立场能够说明词语意义指称事物、事态的可能性,但不能很好地说明何以平列的两个序列能够现实性地发生对应关系。胡塞尔的现象学试图通过意识体验中的意义赋予行为和充实行为来说明这样的问题。他的思考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试图将观念、意义这样的层面与直观经验的层面融合起来,观念、意义不但与意识活动的意指相关,即它们总是在实际的意指活动中趋向一个意向性的对象,而且在含义充实的行为中能够被直观性的内容加以充实。不过,由于胡塞尔原则上一直没有放弃直观与观念相互分离的信念,虽然他通过“充实意义”即直观行为的构成性观念意义填补二者之间的鸿沟,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也试图将意义概念扩及整个意识行为领域,但意义与直观经验何以能够相互通达的问题在他那里没有最终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反映在表达现象上的问题就是,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何以词语的意义能够适切地指称在直观被给与的事物、事态。
作为不懈地对形而上学和先验结构加以解构的哲学家,德里达破除了西方人关于语音与所指(意义、事物等)具有先天天然联系的神话。其实,这样的解构动作在索绪尔那里就已经发生。虽然索绪尔认为意义与语音的结合是“唯一真正的自然纽带”,但他的思想中本来就有语音只是语言的外在因素这样的观点。“声音是一种物质要素,它本身不可能属于语言。它对于语言只是次要的东西,语言所使用的材料。……语言的能指更是这样:它在实质上不是声音的,而是无形的——不是由它的物质,而是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他任何音响形象的差别构成的。”⑥德里达所做的只是将索绪尔的思想更加推进一步,根本上颠倒了所指——语音能指——文字能指这一秩序。在他看来,语音是所指的直接体现,而文字是这一体现的体现,是原初所指的显现的迫不得已的、有可能导致变异的再现——这样的观点正好体现了西方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在场形而上学。⑦
虽然从对结构主义的解构出发,也在根本上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拉开了距离,但是,德里达并未很好地解决能指与所指的结合问题,因为他最终诉诸一种原始书写,一种纯粹的痕迹,在任何实体性的文字(语音也可以看作一种文字)出现之前纯粹形式性的差异结构。这样的差异结构是在一切具体的语言行为之前的、使得语言行为得以可能的东西,其性质最终说来仍然是先验的。
如果先验主义的维度不能很好地说明词语的意义和指称问题,那么是否可以从后天经验的维度来说明呢?根据约定论,能指与所指起初是相互外在的,能指与所表达的意义、概念之间的对应起始是一种松散的约定,其后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制度。通过这种强制性,词语就可以公共地表达意义或观念,指称事物。简单观念或概念是有限的,但是它们无限的各种结合可以表示千变万化的事物、事态。但问题在于,约定如果是一种理智的、意识的行为,那么在任何语言都未产生前,交流和约定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如何可能发生?这样的悖论是意识哲学无法解决的。
所以,不论是从先验的秩序还是后天约定俗成出发,都不能说明表达何以可能的问题。
二、从表达形式到意义
如果从梅洛-庞蒂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失败,只是由于意识和先验的立场。如果我们不是返回到如德里达所声称的那种不是起源的起源的原初差异结构,而是“回到”我们向来已在其中并从中酝酿、生长出文化世界的知觉世界,那么,表达何以可能的问题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答案。在梅洛-庞蒂看来,知觉世界中形式、结构、意义和感觉性的“材料”是原初地不可分离的,各种表达形式之所以能够表达意义也要溯源于此。作为高级表达形式的人类语言是通过身体动作“自然”地发展出来的,而不是通过意识约定,而后制度性地建立起来的。
在梅洛-庞蒂看来,真正的感知主体是身体。这一点从根本上将他的立场与胡塞尔所持的意识、先验的立场区别开来。胡塞尔强调前谓词、前语言的经验,后期他也承认意识有一种被动的主动性,一种根据沉淀下来的习性而被动接受以前构造性行为产物的行为;感知具有自己的视域,具有自己的前理解,感知物一般是作为类型被感知者感知的。他关于感知与意义关系的理解也有诸多矛盾之处,他后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主张直观行为本身也具有意义。尽管如此,他的感知不具有自己的意义、其意义是主体通过表达行为赋予的观点在他的思想中给人的印象仍然是主导性的。
感知在意义的构建方面具有如此微不足道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作为感知者的主体更多的是作为意识主体起作用的,只有意识主体在对事态做判断,表述自己的感知。但是,这样的以意识性作为最根本的甚至是唯一特征的主体并不在被感知者的世界之中。因为经过现象学的先验还原,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它是纯粹的完全不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先验主体。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知觉主体被胡塞尔悬空,或者说虚置了,其在意义构建中的作用也就被彻底地低估甚至是否决了。梅洛-庞蒂从恢复知觉的首要地位出发,试图恢复身体作为知觉主体的地位。在他看来,知觉不是意识主体的一种意识形式,而是身体最本己的意向性行为,意向性首先是身体的意向性。
但身体的意向性并不是唯一垄断性的意义发生之源泉。身体生活在自己知觉的世界中,它的知觉经验并非漆黑一片,因为意义是知觉现象的原初存在方式。在知觉中,有知觉物体呈现出来,即作为“什么”东西显现出来,“物体只不过是一种意义,是意义‘物体’”⑧。知觉物体的存在和其意义是同一现象的两面,这样的意义是我们在对其作语言表述之前已经具有的前语言性的、沉默的知觉性意义,它是在作为图像的知觉对象、作为背景的知觉场和知觉主体三者所共同构成的格式塔中呈现出来的。意义既不纯粹是主体赋予知觉对象的,也不是知觉对象自在具有的,或者是仅仅在图像与背景的结构中呈现出来的。作为意识的主体的我们,只是发现这些意义,而不是赋予对象以意义,以身体介入世界的我们是意义建构的要素,但却非唯一的要素。最终来说,意义是一种赋予、发现和反映的混合物,处在一种暧昧的状态中。
在知觉场、身体和知觉对象的共同作用下呈现的知觉性的意义在我们的言语表达行为之前都已经被给予。这样的被给予从身体的角度来看,就是身体以一种知觉性的意向意义指向物体,它构成了身体对知觉世界的前理解。根据梅洛-庞蒂的表达理论,知觉性的意义是通过身体动作表达出来而与共在的其他身体存在者交流的。在梅洛-庞蒂看来,表达现象是一种身体层次的原初现象,“身体是一种自然表达的能力”⑨。身体动作或者说身体姿势本身就是一种表达,它有自己的意义。在这种沉默的表达活动之中,身体姿势和意义是同一事态的两面。“动作并没有使我想到愤怒,动作就是愤怒本身。”⑩
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的这种自然表达能力首先奠基于它与被知觉世界的相互表达的关系中。在知觉经验中,身体首先不是像其他物体一样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身体主体,它通过自己的意向性活动与其意向性相关物——知觉客体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在这样的意向性活动发生时,身体并不能感知到自己是意向行为的主体,又是诸多物体中的一个物体。但是,身体也能挣脱与客体联系的意向之线,回顾自身,知觉到自己是一个客体,同时又是一个主体。于是,身体处在既是视看者又是可见者的可逆行的循环之中,一种表达性的关系出现在身体主体和被知觉世界之间,通过它们内在的相互关联而相互认知、相互表达。如果是身体使意义的生成成为可能,那么,意义也通过身体得以表达。意义在身体姿势的变形中生成并被理解,身体于是成为能指。这样,身体在知觉经验中通过自己的身体行为使原初的知觉性意义的表达和理解成为可能。
根据梅洛-庞蒂的身体姿势这一设想,动作的意义是直接指向物体的。一个动作,如他人用手指对我们指出一个物体,立即在动作与被指向物体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动作如同一个问题呈现在我的前面,通向我指出世界的某些感性点,他要求我把世界和这些感性点连接起来。当我的行为在这条道路上发现了自己的道路时,沟通就实现了”(11)。这时,在动作与世界之间,我、他和世界之间,没有符号等任何表象性的东西作为中介。这样的看法直接影响到他对语言意义的看法。
在确立了身体姿势具有表达原初的知觉性意义之后,梅洛-庞蒂进一步认为,人的言语表达是身体动作的一种变形。“言语是一种真正的动作,它含有自己的意义,就像动作含有自己的意义。”(12)不过,无论怎么去定义言语这一表达活动,即使将它定义为一种动作,它与一般动作之间的区别仍然是明显的。梅洛-庞蒂虽未专题地讨论从身体动作到言语的过渡问题,但他在不止一处谈到了从身体动作的本义到其转义的过渡。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同时作为表达活动这一点上,身体动作到言语的过渡究竟是如何可能的。
先来看舞蹈。一般而言,身体是我们拥有世界的一般方式,它的行为仅及于保存生命,它为我们设定了一个生物的世界。但是,应该清楚的是,身体也可以利用它原初的行为来表达新的意义,原初的行为可转化为作为一种表演行为的舞蹈——具有特殊表达功能的“语言”:“有时,身体利用这些最初的行为,经过行为的本义到达行为的转义,并通过行为来表示新的意义的核心:这就是诸如舞蹈运动习惯的情况。”(13)正如其他所有身体行为一样,表演行为不是纯粹“自然”的;毋宁说,它是一种习惯化的制度化的行为。
再来看人的声音。人从自己的发音器官里发出的非语音的声音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所指,这在婴儿的表达活动中尤其明显。人用非语音声音可表达诸如兴奋、沮丧、平和、愤怒、高兴、满意的“内在”情感状态,可以表达自己的要求和决心等。不过,在梅洛-庞蒂看来,这些非语音声音也可以发生一种意义的转换,即从本义到转义的转换。
喉部肌肉的收缩,在舌齿之间摩擦的气流的送出,以及运用我们身体的某种方式突然有了一种转义,并把它传递到我们的外面。爱情在欲望中的出现,动作在生命之初的不协调运动中的出现如同奇迹。为了奇迹能产生,语音动作应该利用已经获得的基本意义。(14)
在梅洛-庞蒂看来,语言最初的时候具有丰富的意义底蕴,其核心是身体姿势的表达意义,“词语的最终意义应该由词语本身引起,更确切地说,词语的概念意义应该通过对内在于言语的一种动作意义的提取形成”(15)。这表明,词语的概念意义少于词语原初的身体姿势之意义。在身体表达的知觉性含义的基础上,词语的概念性、观念性意义开始产生出来。它们越来越远离其最初的源泉——知觉世界。其源头被遗忘之后,词语的意义就被视为与词语的表达形式本身完全可以分离的纯粹的观念。
三、从意义到事物
不同于康德、早期维特根斯坦和胡塞尔的先验主义路径,梅洛-庞蒂的身体姿势表达理论能够很好地说明词语的意义能够指称事物、事态的问题。
首先,根据梅洛-庞蒂的表达理论,我们用词语去指称世界并不是用平行系列的观念世界去表象实在世界的活动,而是身体自发的一种活动。身体自身对其处境就有一种前语言、前意识的理解。身体在自己结构化的、实践化的空间中活动,以习惯的方式理解着世界。在我们借助一个概念理解直接的感知材料之前,在表象一个物体前,身体已经对它身处其中的知觉物体及其变化有了理解和把握,并可以做出适当的反应。我们伸手抓挠身上的疼痒之处,并不需要我们对自己的手、身体部位有表象式的客观感知,对它们之间的距离进行目测或其他形式的测量。身体之所以有这种非凡的理解力,是因为它自身也是一个结构化了的、习惯化了的姿势系统,这一系统在不同的方位中以无数等同的姿势面对不同的任务。这样的系统就是梅洛-庞蒂所说的身体图式,它让身体可以应付复杂的情景而恰到好处。在其中,身体对情景的理解、把握和它的行为是同时的,“理解,就是体验到我们指向的东西和呈现出的东西,意向和实现之间的一致,——身体则是我们在世界中的定位”(16)。身体活动的每一时刻也是身体意向实现的每一时刻,意向并不需要指向作为概念和作为对象的知觉物体。
身体理解、把握并做出回应的能力建立在身体通过习惯把外部空间整合进自己行为空间的基础之上。身体将外物同化为与自己一体的能力更显著地见于它的工具。“学习打字的人确实把键盘的空间和他自己的身体的空间融合在一起。”(17)可以说,梅洛-庞蒂在现象空间或者说身体空间的意义上,一步步加强和放大了身体整合外物的力量和范围,逐步使外物身体化,直至完全变成身体的一部分,体现出了一种客体主体化的思想。盲人的手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盲人的手杖对盲人来说不再是一件物体,手杖不再为手杖本身而被感知,手杖的尖端已转变成有感觉能力的区域,增加了触觉活动的广度和范围,它成了视觉的同功器官。”(18)手杖与身体一体化地参与了知觉活动,它不是在客观空间中被定位的一个客体,它已被组合进身体图式的整体变形中,回应知觉场中的变化。同样,乐器演奏家也不是在思想中或者客观空间中进行演奏,他是在自己的身体空间中,他对乐曲的每一次重复演出,记住的不是客观空间的位置,而是身体习惯在音乐学习和乐曲排练中获得后的一次次发挥。
梅洛-庞蒂的这一思想,即由于工具的介入而导致身体的再结构化,或者说身体图式的重组,一直可以延伸运用到词语这一身体装置,这一文化工具,这一习惯化的、制度化的产物。词语已经高度地与身体整合在一起。同时,身体动作有它自己的意义这一状况也延伸到它的身体化了的工具。“被指向的意义可能不是通过身体的自然手段联系起来的,所以,应该制作一件工具,在工具周围投射一个文化世界。”(19)一方面,言语是身体姿势的一种变形,是一种自然行为;但另一方面,它不同于其他身体姿势的地方在于,它更多地已是一种制度化的主体间的行为,它使用了一种似乎是外在于每个言语主体的工具:词语。身体与词语的分离状况只是初看起来的情形。实际上,词语与身体的融合和一体化比其他工具更为紧密,它事实上已成为身体不可分割的部分,通过不停地学习和使用词语,身体不断地在再结构化中获得新生,它与词语的一体化也越来越加强,以至于使用词语就如使用我们的手脚做事一般。我们做事时不会意识到我们的身体,我们言语时不会意识到我们正在使用词语,我们不需要在言语前从我们已有的词库中选择合适的词语,我们几乎是脱口而出。
我回想词语,就像我的手伸向被触摸的我的身体部位,词语在我的语言世界的某处,词语是我的配备的一部分,我只有一种回想词语的方式,就是把它读出来。(20)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支支吾吾,苦于搜寻词语,就意味着词语与我们身体的结合出了问题。这就如同我们的手脚出了问题,我们就不能灵活地使用它们,开始意识到它们出了问题,意识到该如何有效地使用它们。
其次,梅洛-庞蒂的语言现象学表明:由于语言性的意义、观念来源于知觉性的意义,它们就绝不是凌驾于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经验之上而与其根本不同的东西,它们的普遍性只是我们在感知世界的经验中表象、事态普遍性的一种“变形”,一种变化中的一致性。作为对知觉物体的前理解的“变形”,在维持一致性风格的同时,词语的意义指称事物、事态只是一种向其原初诞生地——知觉世界的回归,由观念性意义向知觉性意义的回归。这也正好能够解决胡塞尔处心积虑要解决的问题:何以我们的含义意向正好可被某个恰到好处的直观性的感觉内容充实?意指意义与直观之间的一致性不是通过观念意义与充实意义之间的一致性来实现的,而是因为观念性意义来源于知觉性意义。当作为意识主体的我们所具有的含义意向与作为身体主体的我们所理解的知觉性意义相一致时,词语的意义就恰到好处地被直观性的内容、事物、事态充实。对此,我们不会感到惊异,因为这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只有反思活动才让我们产生了表达形式何以能够指称以及观念世界何以独立的问题。
通过梅洛-庞蒂的表达问题揭示出来的知觉经验与具有普遍性含义的观念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把思想和意识的普遍性凌驾于一切经验之上的意识论哲学,尤其有强调表达问题的必要。人们在谈到思维和意识时,容易天马行空,认为意识、思维可以超越一切经验形态而存在,可以有纯粹的客观观念;或者走另外一种极端的主观主义路线,认为客观事物的存在形态离不开意识对其结构化的构造行为,从而使事物成为主体的构造物。与之相关的是语言问题,由于找不到语言的根,所以它要么仅仅被视为一种表象的工具,一种客观事物的图像,要么将其神化,成为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如同一些英美语言哲学家所做的那样。因此,当把一种经验形式的表达活动,尤其是知觉经验中身体的表达活动,作为意识和思维由之发生的最原始的根源,作为说明意识、思维与意义、思想的本质的立足点,就会为我们开辟出一个理解哲学问题的新境界。表达问题将会把我们从纯粹思维和纯粹意识那里拽回地面,使我们认识到思维的非思层面。首先是回到原初的知觉经验世界,然后是我们置身其中的语言文化世界。当然,知觉经验世界和语言文化世界不是分离的两个世界。作为高一级的经验结构,语言文化经验奠基于并又超越了知觉经验。这二者既不能分离,也不能互相被还原。这正如我们做任何事情,既是我们在做,也是我们的身体在做,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说我们不同于我们的身体。
梅洛-庞蒂以看似矛盾的含糊的方式把我们的经验划分为知觉经验和语言经验,就是要为意识找到前意识的基础,为一切普遍性的超越行为、理想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追求,为纯粹的意识、思想找到并非观念形态的基础:人类原初的经验和生活整体。
四、从分解的要素向“原初”的生活整体的回归
对于表达何以可能这样的理论问题,明显有两种解决的策略,一是将表达现象分解为各种要素,即能指、意义、所指称的事物、语法,将它们视为在表达活动之前就已先天存在的要素,然后再通过一些先天的逻辑原则或者中介结合起来;二是将表达活动本身就视为一个实践性的整体,那些可以在我们的理智中加以分解的要素必须从这一整体中获得解释。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是前一路径的典型代表,梅洛-庞蒂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则在后一路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了自己的逻辑原子论立场,不再认为思想、语言、世界之间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不再认为思想和语言是世界的逻辑描画。言语行为从语言图像论解放出来后,显示出各个方面的身手,成为语言游戏论所关注的各种以言行事的活动:计算、提问、评定、请求、感谢、问候、命令与执行等。一个完整的语言游戏是一个语言表达式的实际表达和它引起的反应这两个方面的有机整体。所有的语言游戏不具有为每一个语言游戏共同具有的本质,只是体现出一种相互交叉重叠的相似性,一种家族相似性。概而言之,语词和言语首先是行为中的语言,它们并不具有不变的逻辑层面的意义,其意义源于某种方式的使用。语词指称的世界真正成了我们的世界,因为它是什么样的情形要看我们的语言是如何被使用的:由于我们的语言实践活动而形成了作为我们生活形式一部分的语言游戏,而用语言命名物体并描述世界也是一种语言游戏。一个确定的可以用语言描述的客观世界成了幻象,我们参与其中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
从“理论”向“原初”世界回归,“面向实事本身”,这是现象学发端时的理想,梅洛-庞蒂通过他的知觉现象学应和这一要求,而对于如何从原初的知觉世界到文化世界,他则通过表达现象来说明。他表明,原初的表达现象——身体姿势是身体基于知觉世界的整体而产生的自发行为,它不是一种理智性的表象活动。言语是身体在知觉场中不断再结构化活动中身体姿势的一种“变形”,而语言则是习惯化的言语活动的沉淀,言语活动和语言促使文化世界得以产生。
由于表达活动本身就来源于整体原初的知觉世界,所以表达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结合不是一种理论分析的结果,而是原初地就是一种实践性的综合。梅洛-庞蒂认为,言语表达活动离不开沉默的语言背景,当考虑问题的视野进一步放大之后,言语得以发生的背景在梅洛-庞蒂看来就不仅仅是作为整体的语言,还应囊括作为整体的文化。正是“文化的沉淀”,“赋予我们的姿势和言语一个可接受的共同背景”(21),这一背景对一般意义上的表达活动也是如此。诚如梅洛-庞蒂所言,言语将“自然和文化汇聚到单一的要素之中”(22)。但是,言语或是一般意义上的表达活动的综合性首先应以我与他人存在的内在统一性为基础,这一基础当然是身体、语言等所有自然和文化因素的内在统一性。
文化给表达活动提供了得以发生的机制,正是由于“我们属于同一个文化世界,更根本上而言,属于同一语言,我的和他人的表达活动从同一的机制(institution)中产生”(23)。这样,在梅洛-庞蒂看来,不但单独的语词离开语言整体不表达任何意义,而且离开表达处境,乃至离开作为整体的文化世界也不能表达任何意义:
每一符号只有诉诸某种精神装备,诉诸我们文化工具的某种安排才能表达,所有的符号都如同一个尚未填满的空白表格,如同指向和划定世界中的一个我没有看到的客体的他人姿势。(24)
从整体的观点来看,撇开可见物同时就是可听物,在我们的语言活动与我们的世界之间、在可见与可表达之间本来就是浑然一体的。这些相互联系的各个要素构成了我们生活形式的整体——生活世界,这是一个由人类生活实践形成的独一无二的整体,一个通过语言呈现出来的与语言密不可分的整体。正是这一整体,使得语言对感知世界的表达成为可能。它们的天然隔绝是我们在理智中分析的产物,却不是它们的原初形态,正是我们的生活整体使得它们可以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或者说,它们根本就不存在分离这样的事。从形而上学的云端来到我们真实的生活,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诚如梅洛-庞蒂所言,“哲学的最高点也许仅在于重新发现这些自明之理,思维在思,言语在说,目光在看”(25)。
梅洛-庞蒂的哲学要求我们回到以身体原初的知觉经验为基础的整体的生活世界。他的表达理论虽然有着不尽完善的地方,如依赖于某种原初性的东西,容易遭到解构主义的质疑,从知觉性到观念性意义的说明也不一定让所有人信服,毕竟那些纯粹逻辑层面的观念看起来似乎有着完全不同于我们这个实在世界的禀赋,但是这些思考,依然为我们解决由于先验主义和表象主义立场而产生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尝试。
注释:
①[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第1部分,第41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②③[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第2部分,第18、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④[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69页,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⑤[奥]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第194页,陈启伟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⑥[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65页,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⑦参见[法]德里达:《论文字学》,第2章,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⑧⑨⑩(11)(12)[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537、237、240、241、239页,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3)[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194页。
(14)(16)(17)(18)[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252、191、192、190页。
(15)Maurice 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Paris: Gallimard,1945, pp.208—209.
(19)(20)[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194、236页。
(21)(23)Maurice Merleau-Ponty,La prose du monde,Gallimard,1969,pp.195—196,p.194.
(22)Maurice Merleau-Ponty,Parcours deux,1951—1961.édition éblie par Jacques Prunair,Lagrasse,(B6WA03.jpg)Verdier,2000,p.48.
(24)Maurice Merleau-Ponty,Signes.Paris: Gallimard,1960,p.110.
(25)[法]英里斯·梅洛-庞蒂:《符号》,“前言”第25页,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