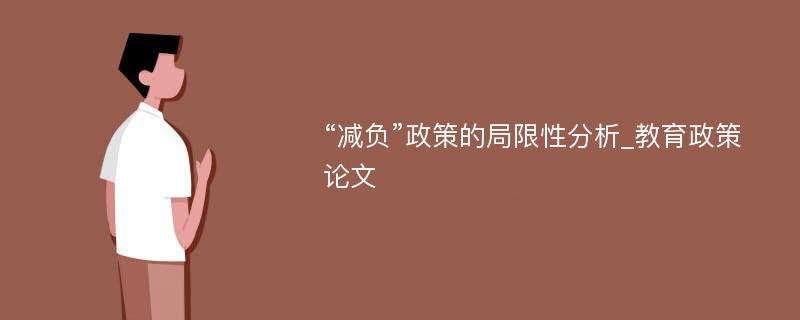
“减负”政策的限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限度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0年1月7日教育部召开“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工作电视会议”,并颁布《关于中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后,学生负担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问题又有了较大幅度反弹。事实上,在这期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几乎每年都会出台相应的教育政策, 以推进“减负”工作,但这些政策大多并未实现预期效应。教育政策的结果与预期之间的偏差正是教育政策限度的体现。换言之,“减负”政策的效力是有界限的。为了更好地制定与实施“减负”政策,让“减负”工作收到实效,对“减负”政策的限度进行理性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减负”政策限度的表现
教育政策的限度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教育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二是教育政策在解决某一问题的过程中并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三是教育政策在解决某一问题的过程中还会引发意想不到的非预期结果。①具体到“减负”政策的限度,则主要体现在后两个方面,即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甚至还引发了新问题。“减负”政策未能完全实现预期,这一点自不待言,众多学者的调查与各种媒体的报道皆可证明。目前缺乏的是对“减负”政策所引发或可能引发的新问题进行冷静而理性的考察。
“减负”政策的推行,缩短了学生在校时间,减少了学校课业,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各种校外辅导班和家教占据了学生大量时间。例如,吴颖慧的调查指出,北京地区93%的孩子都在上辅导班,一个孩子上辅导班的数量最多的超过十个,最少的也有两三个。学校布置的作业很少,有的甚至没有作业,学生交给学校的作业多是辅导班的作业;上课外辅导班,或请家庭教师授课,已经成为孩子节假日的主要生活方式。②结果是,学生的“负担”不但未减,反而给家庭新增了负担——家长需抽时间为子女找辅导班、陪子女上辅导班,并花钱请家教等。有鉴于此,“减负”政策似乎还应该限制辅导班的开设、家庭教师的私下授课等等。如果真是这样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当前少量既没有请家教也没上辅导班的学生家长会平添更多担忧:在城市,孩子们多为独生子女,父母多为双职工。原来孩子们在校时间较长,他们在学校时,父母在上班;他们放学,父母也下班,孩子们的安全时时有人负责,父母无需过多担心。而现在,孩子们在学校的时间少了,在校外的时间多了,而父母的上班时间却无法变更,孩子们有一段时间既没有老师看管,也没有父母照看。在这段时间内,孩子们在干什么?到哪里去了?是上网玩游戏、看电影,还是满街闲逛?会不会遇上意外?会不会与不良少年混在一起?在农村,留守儿童的照看更是一大难题,年老体弱的爷爷奶奶们虽有时间但却无精力时时照顾孩子们的安全。在这个意义上,学校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活动的实施场所,更是一个给予孩子人身关照的机构,所以学生在校时间长反而会受到家长的欢迎。 由学生在校时间缩短所导致的学生人身照顾问题正是“减负”政策引发的新问题。再者,“减负”政策还有可能造成对某些能力较强的学生的不公平。也许他们恰好适应原有“负担”,在这一压力下,他们可以得到最佳发展,而一旦“负担”减轻他们就没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了。③“减负”原本是为维护学生的利益,但结果却造成对学生及其家庭利益的损害,这也是“减负”政策限度的表现。
二、“减负”政策限度的成因
教育政策限度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教育权(权力) 的有限性,导致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不应该也不可能干预教育领域的所有事务; 即使是在国家教育权力力所能及的教育事务上,限于政府人力、物力以及信息收集能力等方面的有限性,其干预也必然存在一定的限度。就某一具体教育政策而言,其限度存在的原因大体有如下几方面:一是教育政策本身的科学性水准;二是教育政策与人们已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等社会心理是否一致;三是教育政策与其他外在制度政策是否协调、互补。“减负”政策限度存在的原因我们可从以下方面分析。
第一,就政策本身的科学性而言,“减负”政策存在一定不足。首先是对“负担”的表述不够清晰。从语义学角度分析,“负担”有两种含义:作动词用,意为“承当、承受”;作名词用,指承受的压力或担当的责任、费用等。“学生负担”中“负担”一词的含义显然属于第二种,且明显是指学生承受的压力而不是担当的责任。从教育学角度分析,“负担”又特有所指。教育学指明,教育活动由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措施三种要素构成。学生的“负担”肯定不是指教育者,减轻“学生负担”也不是不要老师,没有学生的教育活动更不可思议,这样说来,可以成为“学生负担”的便只有教育措施。教育措施又包括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究竟何者为“学生负担”呢?教师运用教育方法的不科学、不合理,无疑会增加学生“负担”,但在实际教育教学活动中,教育方法往往是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而非负担本身。可见,“学生负担”主要指教育内容,即所谓的“课业负担”,如此说来,减轻“学生负担”就是清减作用于学生的教育内容。从类型学的角度分析,教育工作者一般把学生的“负担”分为课业负担、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因为经济负担主要由学生的家庭承受,而不直接作用于学生本人,所以“负担”只能是指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如是,学生“负担”的存在则天经地义。因为如果没有“负担”也就没有教育内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边互动的活动就缺乏载体,因而教育也就不存在了。就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和人的发展规律而言,摒弃那些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教育内容,是非常必要的。但问题是,教育内容减轻到什么程度才不叫“负担”呢?至今为止,这一“度”的界限仍然模糊不清。这也正是“减负”政策的第二个不足之处:对于“负担”的评价缺乏客观的依据。“负担过重”作为一个价值判断,当前还只是一种模糊的推论结果。使用最多的推理与评判依据有如下两种:第一种以当代西方学生的“负担”为标准进行比较。据文献资料反映,美国的中小学生在学校中很自由、很轻松,上课少、作业少。相比较而言,我国的中小学生上课多、作业多,“负担”的确是重一些。然而,中美两国国情相异,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因而“带来了教育的不一样,而这种教育的差异也不能使学生学习的成熟性相同”④。那么,这种“学生负担”比较的可行性就值得怀疑。第二种是以我国中小学生中出现的种种异常现象为依据,得出学生“负担过重”的结论。学生的课业压力过大,确有可能导致学生离家出走、自杀等异常行为;但这类异常行为的存在并不是证明“负担过重”的充要条件,也有可能是由于其他偶然因素导致行为异常。即使所有这些行为皆因学生“负担过重”所致,也须具体分析这些行为发生的次数、频率,有这类行为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是不是足以说明我们的大多数学生已感到“负担过重”。可见,以这些异常现象为依据得出学生“负担过重”的结论也不甚客观。所以,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家长认为“真正负担重的只是一小撮”⑤,这恐怕是学校给学生“减负”的同时家长却给学生“加负”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减负”政策与当前人们既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等存在一定冲突。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里,读书历来是与“勤奋刻苦”联系在一起的,“苦读”似乎已成为学生必须具备的一项“优良品质”。人们虽未对“勤奋刻苦”有明确定义,却提供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典范和劝学的名言警句予以诠释。如“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闻鸡起舞”、“头悬梁,锥刺股”等故事,“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等警句名言。在历史传承中积淀下来的这些故事与警句早就超越了故事与警句本身,而成为一个道德标杆,给后世学子留下的是一种无形的道德束缚与压力。学习必须“刻苦”,要能刻常人难耐之苦,方能有所作为,不然到“空悲切”之时则为时已晚。 以这样的价值观念与文化习俗为标杆,“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游戏中学”几乎与“懒惰”、“散漫”、“怕吃苦”等劣性等同,因为古人早就讲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同样,在这种价值观念与文化习俗的审视之下,“减负”政策是有悖于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人们心中的这类道德规范也就成为对“减负”政策的一种阻抗,也为“减负”政策暗中划定了一个界限。
第三,“减负”政策与当前的某些其他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对于我国当代学生而言,教育更多的只是谋求生存的一种工具和手段。教育既然作为一种生存的有利手段和工具,而且相对短缺,也就必然出现对教育资源(机会)的激烈争夺,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相互竞争以求接受更多教育也就在所难免,只不过这种竞争在一定条件下趋于缓和,在一定条件下又趋于激化。当前我国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显著特点就是激烈的竞争与优胜劣汰。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中,教育过程中学生之间的竞争将趋于激化。也许,在初始阶段学生还不能清醒意识到受教育是为在社会竞争中更好地生存,也就不会有异常强烈的竞争意识,竞争亦相对缓和。然而,孩子的父母们对这一点认识是很清醒的,特别是那些因缺少教育而使生活举步维艰的父母们,更有切身体会。为让孩子在社会中更好地生存,他们不可能不也不得不向自己的子女们灌输这些道理,孩子们也不可能不受影响,从而产生强烈的竞争意识,在教育过程中制造并参与残酷而激烈的竞争。为生存而竞争谁都会不遗余力。为取得竞争的胜利,必须承受相当的重负,这是不言自明的。竞争愈激烈,为取胜而必须承受的压力也必然愈重。再者,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国力较其他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为了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各方面的优越性,就必须加速发展经济,更快地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今天的中小学生正是明天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他们似平注定要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小学生承受更重的压力、更多的“负担”。可见,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建设任务也无形中为“减负”政策划定了界限。
三、“减负”政策的能与不能
“减负”政策限度的存在源于国家教育权力和能力的有限性,国家教育权力和能力的有限性表明国家在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过程中只能承担有限的责任,而不能承担无限责任;寄希望于国家持续不断地制定一系列“减负”政策以达到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目的,而不明晰政策(即国家教育权力) 能与不能的界限,最终只能徒然消耗大量的政策资源。为了充分发挥“减负”政策的功效,有必要厘清其能与不能的界限。
从前文分析可看出,繁重的课业只不过是学生“过重负担”的外在表现,生存的压力才是这种负担的内在本质。当然,生存压力并不是在任何社会历史条件下都会转化为学生的课业负担,只有在教育与社会生活资源的分配产生紧密联系之后,具体而言就是教育与就业发生紧密的联系之后,生存压力才通过既定的教育制度(包括考试制度)转化为学生的课业负担,此时,教育也就从一种闲暇生活方式和一种心智培养方式演变成一种谋生的手段。
从学生“过重负担”的外在表现看,“负担”不仅仅来自学校这种国家化的教育机构,还来自家庭与社会。“减负”政策作为国家教育权力的一种行使途径,不能也不应该侵犯社会教育权与家庭教育权;据此,“减负”政策只能约束学校的教育行动,而不能约束社会教育机构和家庭的教育行动,例如“减负”政策不能禁止社会个体或群体创办各种培训学校或者限制培训学校的招生对象,也不能明令禁止家长送孩子去上各种培训班或者限定家长给子女选择培训班的数量。从国家教育权、社会教育权与家庭教育权之间的界分出发,可看到“减负”政策的能为范围只限于约束学校的教育活动,只能通过学校教育课程的改革、提升教师的教育艺术水平、更新学业评价体系等,发挥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功效。至于由家长或者校外教育机构给学生增加的课业负担,“减负”政策无能为力,只能寻求其他解决途径。
从学生“过重负担”的内在本质看,现代社会人们对学校教育有着过高期望,期望教育能帮助他们向上一社会阶层流动,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并能从事专门职业、享受文明成果等,教育已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的重要手段,有时甚至被某些社会群体视为唯一的手段。于是,学校教育就像一个连通器把成人世界的生存和生活压力传递到尚未成熟的学生个体身上,变成了沉重的课业负担。从这个角度分析,要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只能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减轻成人世界的生存与生活压力,这对于“减负”政策而言实在是不能承受之重;二是适度降低人们对于学校教育的期望,不要孤注一掷式地将所有的生活希望托付给学校教育,这一点是教育政策(不一定都是“减负”政策)能有所作为的地方。如终身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政策、高等教育普及化政策等等,都有助于开拓人们的眼界,为生活的改善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而不必视学校教育为唯一的“救命稻草”。如是,这些教育政策也就成为“减负”政策。
注释:
①张振改.教育政策限度研究——来自个案的启示[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3.
②③⑤“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征求意见座谈会[EB/OL].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70/info1235369982390470.htm.
④大河内一男,海后宗臣,等.教育学的理论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70.
标签:教育政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