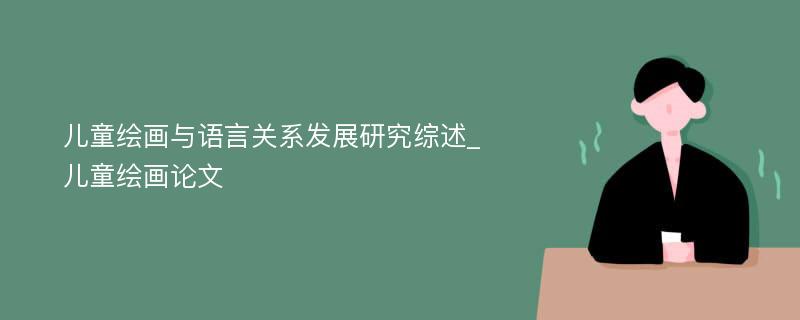
儿童绘画与语言关系的发展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关系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儿童画具有独特的表现方式,是儿童表达自我的一种工具。近一百多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儿童绘画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发展心理学家,把儿童绘画看作儿童心理发展的一面镜子,通过绘画来研究儿童的心理发展。
传统的儿童绘画心理研究一直遵循绘画图形表现的思路,侧重对绘画作品的物理形态(图形本身)的研究,比如线条的运用、画法和图形(形状)等随年龄发展而变化的特点等等。从早期的Kerchensteiner[1]、Luquet[2]、Eng[3]、Read[4]和Lowenfenld[5]等人对儿童画的透明和夸张画法、儿童绘画中缺少空间组织的特点以及儿童绘画随年龄发展而变化过程的研究开始,到后期“画所知”[6-8]还是“画所见”[9-11]的争论以及从信息论的角度,探讨绘画过程中的编码策略问题的研究[12]都关注儿童绘画的图形表现,研究的结果都囿于图形与画法的发展变化之中。
近期一些对儿童绘画编码特点及其发展过程[13]和儿童绘画摹写的语义编码特点的研究[14],都认为语义是影响儿童绘画编码的重要因素。儿童绘画不是简单的摹写过程,它始终伴有语义加工。深入研究和揭示儿童绘画的特点和规律,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画面图形的分析上,还要关注绘画中语义的表达。儿童绘画语义表达的研究究其实质,涉及的是图形和语言这两个符号系统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问题。
2 儿童绘画图形符号与语言关系的研究
Anna Stetsenko [15]在提到有关绘画和口头语言关系的研究时,用“少得出奇”一词来形容这方面研究的数量。下面将从尽可能搜集到的文献中,分析绘画与语言关系的相关研究。
2.1 绘画、语言与其连接纽带——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很早就有对绘画和语言关系的论述。言、象、意是中国哲学史上三个重要的范畴。“言”是指语词或语句,又称为辞或语;“意”是指概念或命题,有时又称为“志”。“言”和“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言”是“意”的表达形式,“意”是“言”的思想内容。所以有“以辞抒意” (《墨经·小取》)、“言者以喻意也” (《离谓》)的说法。在《周易》中,“言”和“意”之间引入了“象”这个范畴。言不能尽意,只有象才能尽意,所以“圣人立象以尽意”。这里的“象”是指用卦爻符号所表示的“物象”,“象其物宜,是故为之象”。王弼对“言”、“意”、“象”三者的关系论述得最为充分。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意思是说,象是表意的工具,只有象才能尽意;言是明象的工具,只有言才能尽象;忘言忘象才能得意。他的思想肯定了言和象在传达意义中的作用,指出了言和象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人在认识过程中要透过言象把握意义[16]。从现代符号学的观点来看,“言”和“象”都是符号,“意”就是言和象所代表和传递的信息,“言”和“象”是达“意”的工具。
虽然Piaget[17]指出,应当把儿童早期符号的发展看成是一个整体,各种符号能力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Chomsky[18]认为,各种符号能力之间根本不存在联系。但是,符号发展的另一方面——与语义或意义相关的部分的关系却不是那么简单。Gardner和Wolf[19]把这种与意义相关的符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符号的“发展之波”(waves of development)。即语义或意义的“波浪”会波及到各个符号系统,是意义这根红线将各个符号系统连在一起。
Lahey[20]提出由形式、内容和使用三个相互重叠的部分组成的语言模型。根据这个模型,他分析了视觉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关系。口头语言的形式包括声音、词汇以及语法。相应的,视觉语言中的形式是指艺术家表达出的物质形态,是以艺术元素和设计原则来描述的。大多数艺术作品都表现了艺术家对作品形式的关注。语言的内容相当于视觉艺术中的意义。意义通常体现在符号中,所以,一些艺术家为了创造意义而有意识地安排和使用符号。在Lahey的框架中,使用是指要达到目标的语言的多种功能。在视觉艺术当中的使用是指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和最终达到的目的。Lahey模型提出的形式、内容和使用恰好与符号的形式、符号的意义和符号的使用者三个因素是相对应的。其中,符号的意义是对这三个部分的连接。可见,绘画与语言都是符号,是建立二者关系的前提,意义是沟通不同符号系统的纽带。
2.2 绘画与语言符号在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相似性与相互作用
Krampen [21]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儿童画中都有被称作“字形”(grapheme)的视觉单元形式。这些单元就像音位一样,根据一系列视觉“语法”排列在一起,形成有意义的画面。这些“字形”是普遍存在的,就像普遍存在的深层语法结构一样。图形符号体系产生了类似于语言的一个结构,所以图形符号可以与语言相类比。他还指出,儿童绘画发展的社会文化方面也同语言类似。儿童在同伴群体内相互学习,他们生成了一整套符号系统。这一套系统不完全是个人的,是从共同的群体中生成的符号体系。个体对符号的采用、整合或对这些图形结构的扩展都具有文化的确定性,和某一种语言的词汇一样都是约定俗成的、规范的。
Elizabeth和Keith[22]通过一项干预研究揭示了绘画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语言与绘画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些重要的特征是相同的。比如在信息的输入与交流方面,两者就有一个共同的模式。他们假设,儿童对外部语言刺激的敏感性也应当表现在对图形刺激的敏感性上。正如许多语言获得的研究所表明的一样,丰富的、适宜的外部语言刺激对儿童掌握语言结构会有积极的影响一样,通过儿童与主试之间的“图形”对话以及故事图的呈现,儿童的绘画技能和绘画形式将会得到重组和改造。他们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外部的图形刺激可以使儿童改变画面形象的大小、增加细节并表现出遮挡、透视等空间关系。
俞建章、叶舒宪[23]则从艺术起源的角度和对考古学、人类学研究资料的分析提出,语言符号在其发生过程中同非语言符号(包括绘画)的错综关系是:孕育、脱胎、超越、并存。Paivio[24]就曾指出,从发展顺序来看,理解形象的确先于理解语言。但是,当儿童具备了口语表达能力时,这两个领域的发展就逐渐趋于一致并且相互作用。这些研究说明,绘画与语言的关系会随着儿童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这种关系中蕴藏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儿童绘画发展与言语发展存在着双向促进关系[25]。
2.3 绘画与语言二者的心理发展阶段的一致性
黄翼先生在专著《儿童绘画之心理》[26]中针对图式期儿童的概念画,明确指出了儿童绘画与语言的关系。他说:“儿童的图画,即是概念的表现,其性质功用,和语言极为相同。因此鲁玛称之为‘图语’(graphic language)。儿童的图画,很像是从语言直接翻译过来的。”他的这种观点触及了图画与语言之间的“转译”问题。
王大根[25]对言语发展特点与绘画发展特点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在涂鸦期(1.5~3岁),虽然儿童可以画出不同形态的线条和形状,但尚无语言意义。但进入符号期(3~9岁)后,绘画与语言的关系逐渐明朗与密切起来。在词的符号期,儿童会自发地创造简单的形状去标示某种物体,并为之命名。图形是他们的语言符号,各符号之间尚无联系,只有“词”的意义。句的符号期,儿童画有了简陋的形象,造型上仍有符号化的特点并形成一个时期的概念化定势。画面略有陈述性,有简单的情节,似乎是些“只言片语”,类似言语中“句”的意义。陈述的符号期,画中的形象仍有概念化、符号化的倾向。但画面有了很强的陈述性,常能表现一个完整的时间或场面。因此,不同绘画发展阶段儿童表现出的特点与儿童言语发展水平直接相关。
Obukhova和Borisova[15]采用观察法,记录儿童在绘画前、绘画中和绘画后的语言,将绘画的发展阶段与每一阶段产生的语言类型进行了比较。他们将学前儿童的绘画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简单形状(圆形、线条、方形)阶段,3~4岁儿童的画具有这样的特点;(2)复杂形状阶段(将各种图形组合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形象,比如房子、树等),4~5岁的儿童画具有这样的特点;(3)图形动态组合阶段,图形的组合常用来描绘一些情节、场景。5~7岁的儿童画具有这样的特点。
与以上三个阶段相对应,言语的发展也区分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简单形状阶段,儿童很少能说出他们画的是什么。仅有的言语表达都发生在绘画结束后,通常用一个词来说明图画的主题或者相关的情绪,词和词所指代的物体建立直接的联系。绘画前和绘画过程中没有言语伴随。Obukhova和Borisova将这个阶段定义为混合性言语(syncretic speech)阶段。进入复杂图形阶段,儿童绘画过程中开始有了言语伴随。语言是用来扩展和丰富画面上看不到的一些内容。这时的言语已经超越了与物体一一对应的关系,实现了语言的概括化功能。在动态组合阶段,儿童绘画之前就开始谈论自己要画的内容,事先组织和设计。语言的计划和组织功能与儿童的绘画结合起来了。
虽然Obukhova和Borisova没有为绘画和语言的关系提供实证研究的数据,但他们指出绘画和语言在功能上具有相似性,即语言和绘画都是实现交流目的的手段和工具。
William和Gardner等从故事讲述、绘画和泥塑三个方面对幼儿园和小学儿童艺术能力的发展特点进行了研究(注:William I S,Silverman J,Kelly H,et al.Artistic Develop ment in the Early School Years:Across-Media Study of Storytelling,Drawing and Clay Modelling.Harvard Project Zero Documents,1979)。他们发现在不同的媒介中,儿童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但发展的趋势大多具有一致性。但由于其研究的出发点是儿童的艺术能力,所以在实验任务的设计方面(如绘画的四项实验任务分别为:自由画、临摹画、拼图和添画)和结果的评价方面(表现能力、表现特点以及表现的独特性)都侧重儿童技能的表现,忽视了儿童使用不同符号体系表达和传递意义的真实能力。
3 儿童绘画与语言关系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展望
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有关儿童绘画与语言关系研究的一些特点与不足。第一,儿童绘画与语言关系的研究以理论论述与现象描述为主,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第二,已有的实证研究数量少,处于零散状态,缺乏系统性的基础研究;第三,已有研究没有直接触及最能体现绘画和语言关系的关键环节,绘画与语言二者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关系究竟如何,至今依然不够清晰。因此,对儿童绘画与语言关系的发展研究需要从理论上建构,找到研究二者关系的切入点,并在此基础上做系统的设计。
从本质来看,绘画与语言都是符号,是儿童进行交流的手段和工具。它们承载着共同的意义,意义是沟通两个符号系统的纽带。因此,二者关系研究的切入点在于两个符号系统间意义的沟通。这种沟通体现在儿童对绘画图形符号及语言符号的使用之中,体现在儿童对绘画与语言符号意义的理解、提炼、升华以及不同符号之间意义的相互转换(“转译”)之中。
当今的认知发展研究日益强调研究的生态效度,呈现出在儿童的自然环境中,以多种方法考察儿童认知发展的趋势。儿童绘画与语言符号的发展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复杂系统。对于二者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关系,也需要通过多种方法,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研究。因此,采用纵向跟踪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对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图形符号与语言符号意义的理解、概括与“转译”,系统探查儿童绘画图形符号和语言符号的发展特点、发展进程以及两者在发展过程中间的同步性、差异性和相互作用是揭示绘画与语言二者在儿童发展过程中关系的新趋向。儿童认知的发展归根结底在于儿童掌握符号的程度和进程。促进儿童认知发展的进程不仅仅在于推进儿童接受和获得符号行为的能力,更主要在于促进儿童创造符号的能力,促进儿童赋予事物以新的意义和价值的符号能力。揭示图形符号和语言符号在发展中的关系,无论对丰富和深化儿童绘画心理的理论研究,还是对幼儿教育实践中利用符号系统间的相互融合,发挥异质符号的综合优势,促进儿童认知和创造力的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