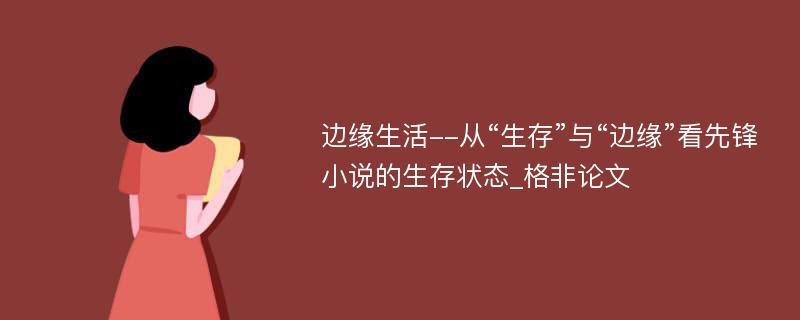
在边缘活着——从《活着》《边缘》考察先锋小说对生存境态的演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缘论文,先锋论文,说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终于听惯了围剿讨伐先锋小说所组成的批评喧哗,现在,可以静下心来思考一下几年前的先锋小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灾难或启示,这是一个需要摒弃偏见和简单类比的课题。由于先锋小说在世纪末遭遇了一种被轰炸被肢解的命运,在各种攻击的姿态下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我们重新审识它时,确有进行大观念上矫正的必要。
先锋小说被种种批评肢解为一个头足倒置的分裂、混杂的世界,为时代提供着支离破碎的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幻象,它不但无法整合人类业已遭到物欲鲸吞蚕食的精神疆域,而且以颓废和毁灭的哀乐加入精神崩溃的变奏。其先天不足表现为欠缺独立个性和民族气派的底蕴,靠着殖民化思潮的输入来延口残喘,它消解了深度,抛空了终极价值,故事向着感觉开放,提供着彼此切割的平面型叙述,它是一种无选择技法、无中心主义、无完整结构的文本实验,解构主义是其理论之源。在表现当代生存实相方面,先锋小说往往无能为力,因为它患有一种“历史的失语症”,先锋作家总是站在缅怀者的地位,放纵着想象,把历史创造成精神的避难所,借此来回避现实境遇中的生存重负,说到底,先锋小说“无从获得一个生存的终极根据来展开对生存事实的审视和统摄”。
这种碎刀零剐式的批评或者是将先锋小说的某些病灶作了放大的说明,夸张的表述,或者是把伪现代派作品和先锋小说混为一谈,或者是无视先锋小说在奇崛的形式下隐藏着极其丰富的生存秘义。如果他们有耐心读完余华的《活着》,格非的《边缘》(均见《收获》92年第6期),如果他们又能掩卷作一番探求性的思考,那么人们也许不会轻易断言先锋小说除了游戏历史和形式游戏之外,就所剩无几了。
在这两部小说中,余华和格非用相当的长度和容量展示了他们对生存境态的由衷感悟,可以说,这是当代先锋小说创作中经过了重锤敲打的力作,它们标示着先锋小说经过了一系列感官和语言的猎奇探险之后,走进了庄重的艺术殿堂,演述着生命在不幸和灾难中保持着自在状态的故事。
“活着”和“边缘”这两个简朴的词语给我们带来了指向幽远的关于生命的妄想,某种相关性的暗示诱惑着我们在闪烁不定的文本中寻找着生命共性的东西,最后,我们找到了一种最朴素的组合——“在边缘活着”,这是生者面临的特异与平凡双向循环的共同境态,也是两部小说中最富本真意义的内质。
这两部发在同一期刊物的先锋小说的近似点很多:
①都以黄昏落日般的老人对一生的自叙性回忆作为叙述角度,并由此建立一种时空由自我调配的叙事框架。
②叙事时间的跨度从本世纪初期到世纪后期,在这一时间弧度内,历史和现实犬牙交错,将在、曾在、此在三维共存,中国产生着无数悠长韵味的生命故事,引得先锋作家频频注目;叙事空间呈现同种模式:由家乡迄逦到异乡,再由异乡回归家园,这种终点回到起点的圆形空间蕴含了一种生命的强大的向心力:落叶归根,混乱趋向平和,喧哗趋向沉寂。在这一寻找归宿的生命漂泊过程中,叙事者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战争中,战争可以说是本世纪最能展现生命一切秘义的主要话题,但主人公充当着战争的局外人,都有想当逃兵的强烈欲望,他们要逃避战争这个将小人物的可怜生命顷时化作血浆肉泥的失控的磨盘。
③历史的转轮在本世纪抛出了一连串震憾中国乃至世界的大事,但大事中的小人物只为自己微细而真实的种种自存问题忙碌着苦恼着无奈着,轰轰烈烈的历史无法扭转他们的卑微处境,他们也无法介入历史的大震荡里而悲壮一回,在此,文本达到了表现大众生命的真情实态的相当的深度。
④隐藏在文本之后的一双巨大的黑手是挤压、危及、消解生命的死亡之影,可以说,在边缘活着的另一重意义是,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叙事者是凭借夹缝中求生存的本能才从死神的手中一次次溜走的,尽管这是一场注定要输的游戏,但他们一息尚存,就支撑着自己的感觉和皮囊,由于死神的魔影在他们周围缤纷地忙碌,致使其他人物一个个相继消失于荒冢中,这样,他们的活着就具有了拨动生命的最敏感的琴弦的力度。
⑤叙事者采取了一种知命式的叙述情调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对于一连串亲人朋友的消亡,对于远逝的苍老而又清新的记忆,这两位耄耋老人也曾泪流满面。但是,活着活着,激情就收敛了,悲喜就发了酵,爱恨就降了温,甚至连奔腾的情欲也不再具有销魂摄魂的能量,浸染着一种湿漉漉的苔藓之色。
⑥整个叙述流程可以在文本中找到恰当的描述,这和《边缘》里那度过于欲火难奈的中年时期的仲月楼的妻子颇为相似:“像一条汹涌澎湃的河流经过险峻的山谷之后,来到了坦荡的平原上,水势变得疏缓而平静”。这一叙述流程实质上暗示了生命的必由之路:无论情欲多么旺盛,生命终究要变得苍老乏力,无论你选择一种怎样的活法,你都会生活在一种边缘状态,这也就是人类生存的永恒困境。
由这些相似点切入文本的内核,我们就能把握先锋小说对生存境态的基本演述:人总是活在某种边缘,边缘是对漂浮不定的生命的最确切的描述,它暗示了生命是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奇特与平凡之间,必然与偶然之间,清醒与沉睡之间,激情与悲情之间的一种永恒的流浪物,处于边缘状态的人体味着生存最模糊又最真切的含义,对他们而言,活着就意味着自在时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一切,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意义都在此凝止。而我们还是可以探究“在边缘活着”的多种含义:
“在边缘活着”意指个人处在大历史的空档中保持着自在的真实。
历史往往被理解为是由伟人、巨人、罪人这些粗大黑点和战争、革命、朝代更替这些粗壮黑线构成的大网,而无数小人物及他们的生命史被疏漏在大网的空隙处。一般追求史诗性效果的作家都着力营构一种理念化的历史框架,他们也写小人物,但小人物往往变成了表现大历史运作的注脚和道具;而先锋作家往往激烈地表现出一种对理念化历史的反动和反讽,他们更为关注历史状态下的小人物怎样活着这个具有人性深广度的艺术课题。在先锋作家看来,所谓历史的有序性和规律性纯粹是历史学家理念的衍生物,是对鲜活生命的一种人为的限定和抽空,文本创作必须颠覆这种骗人的历史观,而到大历史的空档处去寻找一种卑微而踏实的存在物。余华和格非找到了他们,并赋予这些个体生命对抗在历史幻影的能量,让他们生活在历史的边缘,把他们的个体生命史推到表现的前台。这种生命史是时间之流的纷沓的涌动,是心路历程在回忆时的自动曝光。小人物总是要从粗线条的历史大网中漏出来,他们总要避开历史滚动时产生的灼人的火花,而退到命中注定的位置囿于自我真实地活着,不管这种边缘生活是踏实还是空洞,是激烈还是平乏,但“活着”就已经涵盖了一切,这种“活着”因为与历史的边缘状态相胶着而让人深切地体味出生命的轻和重。在文本中,那些急切投入大历史运作的人,结局往往很糟。如《活着》中的县长春生在文革中被逼着投井自杀,《边缘》里的支书路货郎极有可能被一辆装满猪肉的卡车撞死了,他死时,手里紧紧捏着一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此,一种为先锋作家所乐道的揶揄历史的意味泄露出来:历史总在扮演着捉弄人的恶魔般的角色,一不留神,历史就要颠破你的梦想和隐私,剥尽你最后一点尊严,把生命榨成一张丑陋的皮。而退到历史边缘状态的小人物,尽管活得卑微、庸常、甚至有些凄惨,但他们却活得本真,自足,活出了一种意韵幽然的人生况味,这也许是绝大多数个体生命所共同面临的境况,也是先锋作家表现的兴奋点。
“在边缘活着”也意指一种生死无常的临界状态。
余华和格非都酷爱在文本中有组织地编织往来生死间的话题,在他们的很多小说里,主要人物总是一个个相继消解在难逃的劫数里。他们通过对死亡的精微刻写,从而激活了对尘世归宿的多重想象,由此表达出活着的实在与荒谬;人被孤立无援地抛到尘界,注定了要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与重,轻重的力度对生者都会压出一种巨大的困惑感来,在困惑面前,个体生命放弃了探究性思考,自身也融入了谜团之中。生和死都不是解谜的方式,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一边缘状态,在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生者与死者同在,因为死者的虚影总是缠住生者不放,并随时从邀请的姿态对生者作出暗示;而生者由于死者的陪衬、牵连和暗示,已经常常把生界和死界混合起来感受了,这样,阴阳阻隔的界限打破了,轮回在边缘的意义上获得了可能。
活着的前景和死亡的背景共同构成了两部小说最醒目的景观,而主要人物的活着和其他人物的死亡是贯穿文本始终的对比法则。且看其他人物在语言的暴力下如何去死:
在《活着》里,“我”爹被活活气死,龙二阴差阳错成了替死鬼,有庆输血时被抽空而死,家珍得了软骨病安然病死,凤霞生产时大出血而死,二喜被水泥压死,苦根饿后吃得太多被撑死,春生自杀而死,至于战争上的死亡事件却象秋风中的落叶一样平凡而集中,成千上万的伤兵在雪地里被冻死……
在《边缘》中,父亲大吐血而死,母亲经过磨人的病期和冗长的弥留而死,渴望消失在泥土中的小扣最终被送去火化,杜鹃在渐渐扩散的癌症中悄然死去,仲月楼自杀在养猪场的粪池里,徐复观在百岁寿诞前夕寿终正寝,做风筝的老人因贫困而死:伴随战争的暴力死亡更是层出不穷,被奸杀的女人,被枪毙的士兵,被处理掉的伤兵,糊里糊涂相火并的队伍,他们都成了喂养战争磨盘的血肉物……
我们如此不厌其烦地罗列多种形式的死亡事件是为了更好地证明生者的活着状态。叙述者目睹了死亡的暴君对生者花样百出的最后处置,也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人生之旅,他们既活在活人中,也活在死魂的包围中,到他们的生命进入倒计时的阶段、死去的人更能影响他们的生存态,因为他们是将死的人,对死的体验、感受、想象和审视成为他们最后岁月的主要思想内容,这种如“木盆在水面上旋转”的思虑是不可能最终抓住死亡的实质的,但它可以使人无限地逼近死亡,这样,对生的怀疑和对死的质询获得了同样意义:人生是生死之间的徘徊,分不出终点和起点,辨不出阴阳两界的森然壁垒。陷入生死临界区域的老人已经来到了一处地界的边缘,再往前走就是一道深渊,但深渊并不可怕,因为深渊意味着静谧而虚无的时间的无穷绵延和周而复始。他们将古老的哲学命题“不知死,安知生”置换成了一种颇具后现代意味的“生死两难知”的无奈感喟,由此,他们对自己的一生无法作简单的归结,他人的归宿注定了不能由文本来完成,而只能飘游在文本之外,激活着我们的想象,可以想象的是,人们穷其一生都逃不了死影的追逐,在时间的狂流里,他们是两段浸得发黑、质地特殊的枯木,随时都有沉入那道深渊的可能,这一归宿已经没有了悲剧可言,因为它是人生最大的,最普遍的荒谬之处,个体生命的时间意义在此凝止,对后来者的警策意义在此形成,我们应该有所感悟。
“在边缘活着”还意指生者从梦的幻境开始踏上漂流的土地。
先锋小说的人物一直在梦境里滞留太久,他们大都露出在漫无边际的幻觉是旅行的梦游者的神态,即使从那些建构小说的现实材料的空隙中也会飘逸出白日梦的氤氲迷雾,对此,有限的个体生命产生的第一个必然反应是迷失,迷失在幻觉与真实混为一体的精神沼泽里,他们越失越远,抓不到一块摆脱太虚幻境的现实舢板。同时,读者也跟着陷了进去,阅读变成了紧跟言语魔王的冒险远征,熟知的那个真实世界在言语的征讨下彻底解体,现实变成了幻觉的证明材料,前者最后被修改得面目全非。读者好象要被迫着去听精神分裂者的自言自语、自编自导。先锋创作也开始变得象成熟的蚕一样作茧自缚,它耗尽生命能量经营的创造性的丝绒变成了束住自我发展的裹尸布,这正是先锋小说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之所在。但是,先锋小说决不会自缚困死,它总是要撕裂束缚的丝绒而去发挥自己创造性的特长。
余华和格非这两个当代文坛的“寂寞高手”在《活着》和《边缘》里试图和读者达成某种理解和契约,他们笔下的人物开始挣脱幻想的囚笼,回到结实的土地上来。尽管他们离开的是恶梦集居的地带,来到的是一种难以定性的边缘地带,但边缘状态并没有随着命运的迷舟而在梦河上漂泊,又没有被突然泛起的虚无混乱的波纹淹没,同时,它也没有被肆无忌惮的破坏性语言描绘成人间地狱的可怖幻景。活在边缘状态的人还是生生不息的凡人,他们活动的背景不再是虚无地无限地后移,而是有了历史的定格和现实的补缀。生存状态的意义不是靠将现实拖入梦境来暗示,而是通过跳出梦境踏入现实来揭示。这样的转移动作,余华比格非做得更彻底、更漂亮,格非还留有梦境浸泽文本的虚拟成分,并对记忆修改时光保持着一种迷醉。但是,这两位目光常常痴迷的作家对土地都投注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余华:“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象女人召唤他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
格非:“只有在战争进行的间隙,安详而平静的农事才会激起我们对泥土的渴望”。
这些信息说明,先锋小说的人物也开始脚踏实地的活着。如果我们认真辨识这两部小说中的人物群像,上述结论会得到更有力的支撑。福贵他们大都是容易被确认的芸芸众生,他们不只是精神的外壳、故事的玩偶、或表示生存关系的符号,他们已有了生命的自发的内容,有了表达欲望和情绪的实在形式,他们活着的方式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他们带给我们的不再是幻觉旅行的踏实感,而是在土地上站立的踏实感。不过,边缘地带的土地却不是静止的、单色的,它有些象神话中的“飞毯”,使人物处于永远的漂荡之中,正是这种漂荡感让文本获得了动态的意义,也给我们的探讨提供了多种可能。
与“在边缘活着”相适应的是“边缘情感”的悄然生成。
我们可以从叙述情调入手来分析边缘情感。
《活着》的叙述情调朴素、简约、剔除了芜杂的修饰语,保存着主句能指信息的可靠,通过日常口语的还原来淡化生活的大苦大难。
《边缘》的叙述语调低缓、忧郁,有种无法说明的忧伤、悲悯,修饰语较发达,复杂的句式往往包含着闪烁不定的含义,通过恍恍惚惚的呢喃来寻觅生存表象下沉睡的原始意义。
但是,这两种自叙语言的本质有相通之处,不妨比较两段:
……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
——引自《活着》
……死,附着在我身上,在我的血液中流淌。我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引自《边缘》
自叙者如此心平气和地谈论自己的老之已至,死斯将临,好象在谈论一件要抛弃的物品。从表层看,这是一个镇定自若的世界,一个被语言从容控制的世界,在此,激情受到了钳制,痛苦受到了限定,叙述触及的是不可避免的迟早要发生的事实,情感仿佛出现了一个“真空态”,即所谓的“零度情感区”。而从深层来分析,他们情感变得如此镇静,是因为他们也曾爱过、恨过、恐惧过、忧伤过、绝望过,是这些太多的情感打磨使他们不再为情所困,被情所迫。但不能说他们的情感是零度的,这是一种被压缩的、在深层奔涌的、象地下河一样的情感,称之为“边缘情感”更为合适。
“边缘情感”总是力度在情感的两极间保持某种从容的平衡。福贵在所有的亲人都死了之后的感觉是:“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边缘》中的“我”在经历了生死变幻的许多戏剧性场面后,并不指望“一场筵席好得没有尽头,何况,这场筵席我早已厌倦了,所以,我没有理由去抱怨什么”。
“边缘情感”在生关死劫时常表现出左右盼顾的走神。福贵被困在战场时感到“死活已经不重要了,死之前能吃上烧饼也就能够知足了”。《边缘》中的“我”第一次上战场时最大的感觉是想拉屎。在此,“烧饼”和“拉屎”的含义是相当丰富的,仅就凸现情感而言,这们很真实,很有意味地显示了人类情感区的复杂的变幻和个人体验在不可思议的时刻表现出的横生的意趣。
“边缘情感”又在恍恍惚惚之间达到了一定的心理深度。余华通过福贵不但写出了小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个人遭遇,更重要的是,这种遭遇的内化,使小人物的心灵史融入了人类和民族的精神历程中,获得了一种普遍性的意义。格非通过“我”要力图表现在时间狂流中,个体意识所面临的巨大困惑,所以,“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我躺在母亲的身边,在一个遥远的夜晚沉沉入睡,当我在晨曦中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这是纷乱错杂的时间将人带到了清醒和沉睡之间的某个地方。故,格非在《边缘》中是将时间与人的关系作为一个最深沉的意象来表达的,而时间与人的关系唯有在深层的心理体验中才能真正沟通起来。
“边缘情感”还时常要打破物我的界限,寻找一种适当的外化物。福贵给那条与他相依为命的老牛取上了他自己的名字:“福贵”,因为“我左看右看都觉得它像我,心里美滋滋的,后来村里人也开始说我们两个很像,我嘿嘿笑,心想我早就知道它象我了”。《边缘》中的“我”感到自己就是一只乌鸦,在成千上百种鸟类的世界中占据了一席最为糟糕的位置,甚至只不过是它在天空中投下的一缕阴影。物化的情感更多的是一种暗示,暗示了漂游的意绪实在难以定位,于是只好在客体中去寻找某种神秘的关联。
我们的结论是,“边缘状态的活着”在当代神话写作中还要予以更充分的表现,这一历史使命只能由先锋作家来完成。因为先锋小说关注的焦点问题有两个:即人的危机和如何进入终极状态,这两个焦点问题都与“在边缘活着”有关。边缘生活已经成为现代人共同面临的困局,它将大多数个体生命定格在大历史空档中,定格在生死之间的阴影中,定格在永恒的漂流过程中,边缘人消解了激情与诗性,悲剧和喜剧,从容镇定是他们最大的表象,“人不过一死”是他们最后的思想,生命的孱弱无能是他们逃向命运的最好借口。在当代,由于商品魔王君临一切,高科技让人与自然日趋分离,生存空间被糟踏得千疮百孔,边缘人获得了文明的全部病毒,他们更能够抛空价值,更能够醉生梦死,更能够听凭潮流的引导,更能够放任文化洪水的黄化和沙化。—这一切状态的触目惊心之处及其内在的深刻原因等待着先锋作家来更好的表现和揭示,历史赋予了他们表现人的危机和进行文化救赎的双重使命。先锋作家唯有穿透边缘状态才能进入极限体验,余华和格非为先锋的探索确定了方向,寂寞而睿智的灵魂要奔向那里,才能放射出极地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