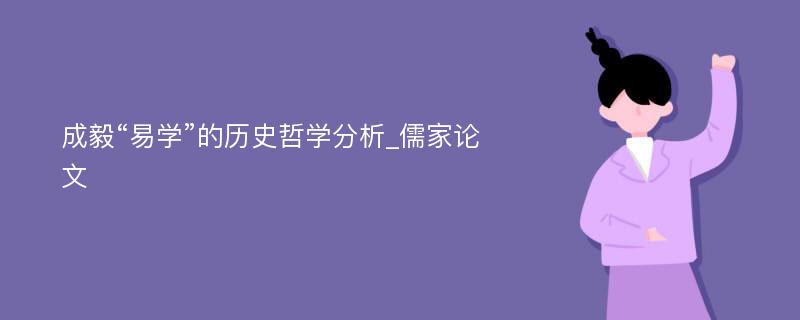
程颐易学中的历史哲学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探析论文,历史论文,易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82(2009)01-0045-10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乃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和易学家。程颐力图从儒家经典、尤其是《周易》中探求一种“大中至正”之道,并将之上升为最高的理性原则和文化精神,即“天道”或“天理”,以之作为个体心性修养的准则与依据;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对这种“大中至正”之道的设定,来考察社会历史,以规正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阐发《周易》的思想,程颐对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历史价值和评判标准、历史本体与历史现象等历史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下面,我们拟对之作一个初步探讨。
一、“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论历史发展的动力
没有变化则没有历史,变化何以可能实际上也是历史何以可能的问题。我们认为,程颐的易学中有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首先就是因为他在解读《周易》时,对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生生不已的变化如何可能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从而也就对历史何以可能的问题进行了解释。
程颐认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有理的贯通,此理中包含着阴阳的对待,如彼与此、上与下、质与文等等,此阴阳的对待成为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故为生生之本。他解《周易·贲》之《彖》说:
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①
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都是生生不已的,生生不已的原因在于“道”或“理”中所存在的阴阳对待。阴阳的相互作用则为“二”,“二”为“文”,“文”是阴阳的相错、相杂;孤阴、寡阳则为“一”,“一不独立”意味着不存在单独的孤阴和寡阳,阴阳是相对待而存在的。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构成了天之“文”,人类社会之伦序构成了人之“文”,天文乃天之理,人文乃人之道。所以,程颐说:
“道二,仁与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无无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有是则有非,无一亦无三。②
天下没有一物不是阴阳对立的,因为只有“二”,只有阴阳的对待,才会有生生不已的变化。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生生不已的不竭动力与源泉在于阴阳的相互作用,善恶、是非均是如此。一阴一阳为道,道是所以阴阳者。阴阳开阖,没有先后之分,不是说今日有阴,明日有阳。阴阳就像人的形与影一样,形影一时,有便齐有。道不是“一”,也不是“三”,故而能够生生不息。
阴阳的对立,为什么会导致宇宙生生不息的发展呢?这是因为阴阳这对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对立的双方不仅在性质上是相反的,而且在力量上是不平衡的。阳代表在对立关系中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一方,阴则代表在对立关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一方。这种性质的相反和力量的不平衡导致了阴阳双方总是处于动态的运动过程中。在这种动态的运动中,有两个原则体现出来:一是阴从阳“则能成生物之功”,从而生生不息;二是“亢龙有悔”、“阴疑于阳必战”,亦导致事物的发展、变化。
对于阴从阳“成生物之功”的情况,程颐解《周易·坤》之卦辞“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说:
阴,从阳者也,待倡而和。阴而先阳,则为迷错,居后乃得其常。西南阴方,东北阳方。阴必从阳,离丧其朋类,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贞之吉。③
在后天八卦方位图中,坤为老阴,位处西南;艮为少阳,位处东北。西南为阴卦之位,作为阴卦的坤往西南,虽阴卦处阴位,“西南得朋”,但却难成生物化育之功;坤往东北艮卦之阳位,虽阴阳相左,为“东北丧朋”,但却因此阴阳相和,可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贞之吉”。
阴阳常不齐,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阳主阴从不是静止不动的,其间阴阳的力量对比有可能发生变化。变化之一就是阳常盈不止,阴消过于极,导致“亢龙有悔”。程颐解《乾》卦上九爻辞,认为上九之爻性为阳刚,又处于一卦之“上”的位置,这是在阳刚的基础上复用阳刚,刚而又刚,事物就会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就导致“亢龙有悔”。之所以称乾卦之上九爻为“亢龙”,就是因为它不知进退存亡得丧之理。要使这种转变不发生,程颐认为应该在天德阳刚的基础上用“柔”,刚柔相济则和,从而天德阳刚能持久不衰。《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之所以吉,乃在于在天德阳刚的基础上用“柔”,从而刚柔相济得“吉”。变化之二是阴常盈,与阳相抗,阴不从阳,则阴阳相敌而战。程颐解《周易·坤》上六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认为阴本来是从属于阳的,然阴盛极之后,则与阳抗争。坤之上六爻就是这种情况,上六爻位于坤卦之极,为阴之最盛,阴盛而又复进不已,则必与阳战。天地是阴阳之大者,玄乃天之色,黄乃地之色,阴进而抗阳,导致阴阳俱损,故云“其血玄黄”。阴阳相抗,其前提是阴常盈而盛,相抗的结果是阴阳皆伤,事物将要发生激烈变化。
天地人三才之道,因阴阳之消长阖辟而生生不息。人道和天地之道一样,无常而不变之理。泰极则复,否极则倾,变易是不可止的,这种阴阳的转换使事物变化无穷,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为阳。在阴阳的消长过程中,阳无终尽之理,此阳尽则彼阳即生,因为事物不论怎么变化均有一主导,此即为阳。因阳之生生不已,故变化无穷,生机无限。程颐说:
消长相因,天之理也。阳刚君子之道长,故利有攸往。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④
程颐将阴阳的消长相因看成是天理,天理不是静止的,而是呈动态的发展趋势,所以,《剥》之后为《复》。“一阳来复”,阳动于下,为“动之端”。静不能见天地之心,因为天地万物都处于流变的过程中,动才是“天地之心”。阴阳至简至易,万物由阴阳而出,但参差万变,无由得齐,不能安排定,所以可以称之为变易。事无有常而不变者,理随事之变而变,于变中方显理之恒常。程颐说:
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凡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能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惧人之泥于常也。⑤
阴阳的生生不是循环,生生是创造,是新旧的更替。程颐说:
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天地间如洪炉,虽生物销烁亦尽,况既散之气,岂有复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气?其造化者,自是生气。至如海水潮,日出则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固已无也,月出则潮水生也,非却是将已涸之水为潮,此是气之终始。开阖便是易,“一阖一辟谓之变”。⑥
天地之气是日新的,气尽则物散,阴阳阖辟又生新气,生成新物,此新物不由旧气而成。故阴阳不仅仅是生生不息,而且“变化日新”。物至极盛则穷,穷则变,从而生生不已。从水火相用的“既济”,到水火不相用的“未济”,就是极而生变的体现。既变之后,于“未济”中当求“济”,从而形成新一轮的生发过程。事物不会有穷尽之时,它总是处于一种变化、发展之中。
就人类历史发展而言,也和天地万物一样,都有阴阳的对立。与邵雍的观点不同,程颐认为,阴与阳在人类社会中不一定就是小人与君子的代名词,人类社会中,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等,都可以纳入到阴与阳的范围。阴虽然与阳有性质不同的一面,更重要的是阴与阳两者有相和的一面。阴与阳相和,虽为阴,仍然可以称之为君子,因为“阴为小人,利为不善,不可一概论。夫阴助阳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阳者小人也。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⑦阴亦可称君子,阴害阳、害义才可称之为小人。阴阳刚柔须相济为用,不能仅以纯刚用事,以纯刚用事则过乎刚,以刚为天下先,则凶之道。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相和方可成生物之功。
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动力在于自身所包含的阴阳对待。社会危机的加剧,使人们强烈地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就好比在《周易》中,《蛊》卦取象山下有风,风遇山而回则吹物而乱,故“蛊”有坏乱之义。但乱与治是相对的,因乱而有治乱之需要,所以说治必因乱,乱则开治。程颐认为,这种治乱的相因和转换,并不存在一种外在的、超越的力量对之进行主宰,而是源自事物内部的阴阳对待与流行。程颐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因是一种内在的原因,这种内在动因的确立,使得历史可以成为人的历史。因为人可以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使历史的发展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进。
阴阳的对立与发展是最具生命力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阳胜阴或者阴抗阳的过程。阴阳对待中既有创造、毁灭,也有和谐。因此,历史的进程既不会是单纯的直线进步,也不会是只有重复没有更新的循环。历史的创造在于对阴阳的调整。其中,阴阳之和是一个适度的、动态的流动过程。阴的变化导致阳的相应变化,同样,阳的变化也应同时导致阴的相应变化,阴阳之和不是某个固定的点。如果阴阳的变化没有能够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那么,这种阴阳之和的状态就可能被打破,因为统一体因阴阳的失衡而解体。阴阳动态平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有问题出现和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这样一来,流动的历史便形成了,而不可能存在一个静态的、不发展的过程和阶段。人类社会内在具有的阴阳相互作用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因,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生生不已的。程颐以阴阳概念来涵盖人类社会中所存在的一切矛盾现象,认为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如此,阴阳的交互作用还使自然界的一切都处于变化的过程中。可以说,阴阳的对待使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呈现出一种历史的过程。
二、“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论历史规律与历史价值的评判标准
阴阳对待使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生生不息的变易过程,这个变易过程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易》之书,承载有事物发展、变化之道,程颐说: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⑧
开物成务是个变化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本身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道一以贯之。变易中有道,此变易之道表现为性命之理、幽明之故、事物之情等。《易》之书尽包变易之理,如果我们把变易理解成历史,那么,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变易之理,就是道。
天道的变化是有规律的,此规律可以《易》卦来说明之。程颐解《乾·彖》曰:“天道运行,生育万物也。大明天道之终始,则见卦之六位,各以时成。卦之初终,乃天道终始。乘此六爻之时,乃天运也。”⑨天道运行,生育万物,其运行之规律,有如乾卦六爻之变。乾卦六爻,亦可称之为六时,一时有一时之用。不仅《乾》卦之六爻,《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是对天道的说明。对于天道的把握,程颐强调“顺”。圣人、君子不逆天道而行,而是随顺此道,或进或退,时行时止,不失其正。人法天道而行,如影之随形,与时偕行,则无咎。
易之道至大而无不包,至神而无不存,作为易道之表征的《周易》之卦与爻,也不能拘之以一时或一事。程颐说:
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时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穷,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时而索卦,则拘于无变,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则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谓卦爻彖象之义,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然后可以谓之知易也。⑩
时不同,卦有异,爻位无定,事物的变化发展也没有穷尽。卦、爻之义不是用来说明一时一事的,卦爻拘于一时一事,则易道无变亦非通,非易之道也。人具有能动性,可以在历史发展中去把握事物的变易之道,通过对易道的把握,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知易”。知是人之知,易乃事物的变易之道。对于此易道,人可以知之、用之,达到对道的把握。只知道《周易》卦爻彖象之辞,而不知卦爻彖象之义的运用,拘于无变,窒而不通,则不可谓知《易》。
程颐肯定《易》有变易之道,认为变易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规律。历史是一种变易,历史的发展也有其规律。历史是生生不息的,历史的规律则是常存不移的。程颐论天道之运行,即认为天地生生不息,其中有生灭消长者,亦有常存不移者。程颐说:
盖阴阳之气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长而无穷者。(11)
消长无穷只是天地的特征之一,就根本而言,则天地又不仅仅是消长无穷,亦有常存不移者,此常存不移者乃消长无穷之本。只讲消长无穷,尚不足以认识天地万物。有人提出“终日乾乾”可以尽括《周易》之理,程颐认为是不正确的,“终日乾乾”并不能尽得《易》之理,它不过是讲《乾》九三爻之爻义。终日乾乾是通达《易》理的重要路径,但路径不等于目的地,理无方所,其神妙处不能仅以终日乾乾来概括。阴阳之气有消长无穷,亦有常存不移者。程颐的易学历史哲学要探究生生不息的历史变化背后是否有恒常不变的规律存在。他认为阴阳之度,日月寒暑昼夜之变,莫不有常而不变的规律存在,这就可以称为道或中庸。变化中有不变者,圣人要探究变化中的不变,求道之所以恒久不变者,则可以不变统万变,得天地万物之情。
以“随时变易以从道”的易学思想为指导,程颐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历史价值评判标准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孔子著《春秋》,欲为百王之通法,亦是要求得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恒久不变之道。
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为一王之法,欲为百王之通法,如语颜渊为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12)
程颐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在周王道已绝,先王之业复兴无望的情况下,希望通过探求历史发展百年不易之大法,以为后世之垂范。此理想的规范不是主观的意志,而是充盈在天地间的大道理,是天道的表现。人君要“王天下”,就要上奉天时以立人之道,故孔子《春秋》所言,可以成为百王之通法。程颐肯定了有百王之法的存在,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是要求得百王不易之理,而不是仅为了说明某一朝或某一代的功过得失。历史的发展不是一种无目的的盲动,而是可以有一个理想的规范。孔子作《春秋》,就是为了确立这么一种规范。所以,在历史的发展中存在基本的理,理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导引和支配的作用。程颐讨论历史事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要透过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去寻找这个历史事件之后所反映的一般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程颐说:
看史必观治乱之由,及圣贤修己处事之美。(13)
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14)
读史不是要记住一些史料,著史也不能只是记录一些史实。史以载道,历史叙述的重点是天道、人理之事,读史的过程也是对天道、人事之事进行理解的过程,通过这种理解,达到学以致用。一些看似偶然的、彼此之间缺乏内在联系甚至正相反对的历史事件之间可能存在和反映着相似的历史原理。如历史上孔子尊周与孟子勉齐、梁以王两件史实,虽然事迹各异,但精神是一致的。孔子和孟子所处的时代各不相同,孔子所处的时代,周之典礼尚存,循之可以达致天下之治,所以,孔子救世则要尊周,要求各诸侯王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孟子所处的时代,周之典礼不存,天命已坠,民不以周天子以主,故孟子济民则要“勉齐、梁以王”,鼓励齐国和梁国之君“王天下”,以救天下为己任。事各不同,但体现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对历史事件的考察,不能就事论事,而要深入到历史事件的背后,去探讨历史事件所体现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精神,从而形成对历史事件的正确评价。这就是“随时变易以从道”的精神。
对于历史发展的评判标准,程颐倾向于以儒家的道德仁义的精神来界定。从功利的角度还是从道义的角度理解历史发展,这是程颐所关心的。从总体上来说,程颐持一种客观主义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事件中存在着规律,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这种因果联系或规律是一种客观精神,程颐称之为“理”、“天理”或“道”。虽然这种规律和联系有待于人们的理解和认识,但不论人们理解认识与否,它们都是存在于历史事件中的。读史者要通过对历史行为的考察,力求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精神。程颐以一种绝对的历史价值观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反对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反对把追求功利作为从事某种历史活动和某个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的最后根据。历史活动是由具有不同利益的个人和集团来进行的,历史的主体不同,在历史实践中各自的利益和需要也不同,应该以哪一种标准来对历史的功过进行评判,就成为了一个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难以回答、难以操作的问题。如果“以成败论英雄”,历史就只能是强者的历史,程颐的“王道”政治的思想正是要反对这种思想。他认为历史中存在着一种永恒的道义,不能以“成败”而只能以“道义”去考察历史及其发展。
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15)
研究历史是要寻找历史的意义,探寻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以这种从历史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来指导人们的现实行为,事成不等于合“理”,事败也不等于悖“理”。“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将他见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误人处。”(16)程颐认为,存在一种判断历史事件价值的永恒道义标准,在历史发展的领域有一种普遍适用的价值评价体系。尽管他也承认在这普遍的价值评价体系的观照下,历史必然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但这其实还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
应该说,历史的评判标准既然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一种工具,那么它就必然有着某种主观的因素在其中。但程颐否认历史的评判标准具有主观性,他坚持认为历史的评判标准是客观的,这个标准具有“公”的特征,所谓“公”,就是一种道义,这个标准具有永恒的价值。当然,程颐考察历史时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功效性,在符合道义的大前提下,程颐认为功效性和功利的原则是必须要予以考虑的。如
问:“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与他战,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佗成列,图个甚?”
问:“用兵,掩其不备、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师,当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须要胜,不成要败?既要胜,须求所以胜之之道。”(17)
我们认为,程颐这种“公”、这种道义的历史价值和历史真理标准,是在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具有历史性。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文化对人有重要的塑造作用,人的历史创造性也是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来进行的。程颐将文化因素看得很重,认为儒家文化是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理念,而没有反观到这种文化本身也是历史形成的。程颐要发明儒家文化的精神,以服务于当时的现实,应该说,他对《周易》等儒家经典的解读与阐发,本身就已经实际地对传统儒家的思想和精神有重大发展,这就已经体现出了文化的历史性。但程颐自己并没有这种自觉,他坚持儒家的道义精神是亘古长存的理念。这种理念在后世不为人所知、所行,而时代又需要这种精神,于是自己就以复兴儒学这种精神为己任。他倾向于认为自己所阐发的就是亘古不变的儒学精神。这样,在他看来儒学的精神不是发展的,而是先验的存在,文化的历史发展被作当是对先验理念的揭示。
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苟能通之以道,又岂有限量?天下更无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18)
历史文化精神的历史性在现代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这种历史性虽然不排除它的基本精神的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基本精神或多或少都要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这种改变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人的历史性、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尽管这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不是凭空来进行的,而是必定处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和一定的文化氛围中,但这种创造性的积累,不断地改变着旧有的文化传统,使文化的基本精神在潜移默化和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改变。因此,人不仅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创造者。一般说来,人们在认识历史时,是带着某种文化的成见的,这种文化成见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其形成受到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具有历史性。一些文化成见可能具有相当长的历史适应期,因而表现出某种持存性。对于这种持存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人们容易将之看成是一种永恒的精神。这正是程颐认为客观、永恒的道义之所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我们看来,这种永恒的判断历史事件价值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这种价值观念不可能是永恒的,而只能是历史的。现实的历史发展往往并不按照这种既定的道义展开,而是有着多样性和差异性,更多的时候还是对这种道义的破坏。在程颐所处的时代,人们还不太可能意识到这种貌似神圣的思想本身并不是超越于时空之外的,而不过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生成和发展的。
历史地看,程颐认为文化基本精神亘古不变的观点,在当时具有某种合理性。农业文明本身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社会的稳定性,这是保证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因此必须强调秩序。所以,“天不变道亦不变”,在当时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当然,程颐关于“理”、“道”的普遍性的论说,将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的积淀看成是普遍性的本体,将一种历史性的社会文化心理看成是永恒的,并以这种永恒的理或道来观察、处理社会、历史事务,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行为。
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论历史现象与历史本体的关系
程颐认为,在社会历史中存在一种抽象的、不变的形而上学本体。“随时变易以从道”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道既是历史的规律,也是普遍性的本体,它在随时变易的生成中体现自己。随时变易的世界与道是现象与本体的关系。在探讨《周易》卦爻象、卦爻辞与义理的关系的过程中,程颐提出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命题,对本体与现象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理论的阐释。这个命题对于探讨历史本体与历史现象的关系亦有某种启示意义。程颐说:
易有圣人之道者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其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19)
显象的存在,以《易》言之就是象与辞;以幽微的方式存在,以《易》言之就是理。理与象、辞,一者至微,一者至著,但两者同出一源,没有间隔,这就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程颐这个思想,就《易》而言,是要建立起卦爻象、卦爻辞与义理之间的关系,认为象、辞与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是微与显、体与用的关系。同时,这个思想也是程颐整个学术理论的基础。程颐以“道”或“天理”来论宇宙的本体。程颐所谓“道”或“天理”,既有生成之意,亦有本体之意。就生成言,道生阴阳,阴阳交感生成万物;就本体言,则所以阴阳者为道,所生成之阴阳中,又蕴含有道。由阴阳之变化,有形神之生,有情伪和万绪之起,是以万物莫不有理,莫不遵道而行。故程颐说:
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阳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絪緼交感,变化不穷。形一受其生,神一发其智,情伪出焉,万绪起焉。(20)
事物的变化,不离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有道或理主宰于其中,这也可以说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易,亦可称之为易道,易道主宰事物之吉凶,生成事物之大业;易道的内容,至简至易,无非为阴阳之道。《易》之卦乃阴阳之物,《易》之爻乃阴阳变化之象征。易之道与《易》之卦与爻亦是体与用的关系。任何事物,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都可以阴阳之义来界定,也都可以《易》之卦、爻来表征。卦爻乃易之有形有象者,此有形有象者可以言辞来表达和掌握,但易还有未形未现者,这是更为根本的易之道,它不可以名求,乃形而上者。易之卦与爻只是对易之道的表征。易就是变化,变化中有天理,这就是易之道。易不仅是《周易》这部书,易也不是离开天地万物而别为一事,易道即是天理流行,就是生生不息,离开天地万物,则无易,亦无易之道。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易是个甚,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不要将易又是一个事,即事尽天理,便是易也。(21)
本体虽然是无形无象的,但其实在性并不因此而减少。无形无象的宇宙本体与具象事物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程颐说:
有本必有末,有实必有文,天下万事,无不然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22)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23)
本与末、质与文,即宇宙本体与具象万物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有然者,亦有所以然者。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命题试图把抽象的天理与具体、丰富的存在物结合起来,认为天理是普遍的理念,但却并不缺乏具体存在的确定性。普遍性的理与特殊性的具体存在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能将普遍性的理落到实处,使抽象之理获得其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又能将特殊性的具体存在纳入到理的范畴中来,使个别的、特殊的事件具有了理的普遍性。
由这个思想出发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就可以发现,历史本身既有以显象的方式存在的历史事件,也有以幽微的形式存在的历史本体,二者是一体的,是无间隔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是有历史本体在其中起作用的,历史事件能彰显和承载历史本体,历史本体又能作用于历史事件,使历史事件呈现出某种秩序。“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提出,意味着天道必将在社会历史中呈现自己,社会历史也必然反映天道发展的内容。程颐历史哲学的目的恰恰在于要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找到一个永恒的、坚实的基础,甚至要为多变的人性寻找到一个不变的基础。这种不变的基础的存在前提是变易,是具体内容的不可重复和间断。程颐说:
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谓之达道。所谓达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行。所谓达德者,天下古今之所共有。(24)
历史的事实当然是独一无二的,但历史的本体却可以是普遍的。如果历史事实之间不存在共同的普遍性,历史理解就是不可能的,历史也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程颐认为,天地间存在着理,理可贯通形上与形下,事不同,理则同,事有先后,理则一时俱有,故“体用一原,显微无间”。
对于“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这个命题的理解,程颐首先强调理是普遍的存在,是万物之本体。为此,程颐认为理可以统事,并在易学上提出“得其理则象数在其中”的观点。有一件事颇能说明此问题:
邵尧夫谓程子曰:“子虽聪明,然天下之事亦众矣,子能尽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尧夫所谓不知者何事?”是时适雷起,尧夫曰:“子知雷起处乎?”子曰:“某知之,尧夫不知也。”尧夫愕然曰:“何谓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数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后知。”尧夫曰:“子以为起于何处?”子曰:“起于起处。”尧夫瞿然称善。(25)
邵雍是北宋易学中的数学派,他以数为宇宙万物之本,注重以数推万物之理。程颐是北宋易学中的理学派,认为得其理则象数在其中。邵雍以数来推雷之起处,程颐认为这是不知物理之表现。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明了物理就不必用数去推,必待数推之后方知,正表明邵雍不知。在程颐看来,天打雷有其理,得其理则知雷之起处,不待数推。有理而后有象与数,这在易学上既可以解释为理在事先,也可以解释为有理则有象与数,理为象数之根本。程颐认为,“义”不因事才“见”,“性”也不须待物才有。理在物之先,但又贯通于具体的物之中,具体的物各个不同,通过明其理,则具象万变的物就具有了统一性。因明理,人们对于具象万变之物也就可以理解和把握之。所以,顺天地之道而治民,亦不过顺理而已。由天地之道而推之于人之道,也是如此。内能修身,则外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内外本一理。
道的普遍性并不排斥表现道的历史事件的个别性和单一性。不同历史事件能体现同一之道的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事件是重复的和完全相同的,如果是重复的,也就没有历史。虽然体现着同一之道的精神,但不同的历史事件是有着自己的特性的。程颐倾向于认为,理不是固定的循环。历史并不是一个计划好了的图纸,一旦掌握了这张图纸的秘密,人们就能掌握整个历史的发展。道的呈现是一个过程,过程是重要的,在行动和历史中,道的实在性才能得到表现。在某种程度上看,道在历史的发展中,其行程具有不可预测性,道的这种普遍性有赖于历史事件的特殊性来加以表现;历史事件尽管特殊,但却蕴含了道的普遍性。所以,
命之曰易,便有理。若安排定,则更有甚理?天地阴阳之变,便如两扇磨,升降盈亏刚柔,初未尝停息,阳常盈,阴常亏,故便不齐。譬如磨既行,齿都不齐,既不齐,便生出万变。故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而庄周强要齐物,然物终不齐也。尧夫有言:“泥空终是著,齐物到头争。”此其肃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义以方外”。如春,观万物皆有春意。尧夫有诗云:“拍拍满怀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不止风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万古兴亡手,出入几重云水身。”若庄周,大抵寓言,要入佗放荡之场。尧夫却皆有理,万事皆出于理,自以为皆有理,故要得纵心妄行总不妨。(26)
邵雍认为“万事皆出于理”,历史就是理的展开,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卷舒万古兴亡”的一只“手”存在,在这只“手”的作用下,历史的发展呈现出有规律性的循环,所以“出入几重云水身”。人一旦掌握了理这只“手”,则“拍拍满怀都是春”,在现实中“纵心妄行总不妨”,历史的发展就在主体的理解和掌握中了。和邵雍有所不同,程颐认为“理”是在“易”中展现自己的,在“易”中才表现出“理”。所以,历史并不是“安排定”的,“安排定”则不称其为“理”了。体用虽然是一源的,但程颐认为不能光得其大体,大体虽得,不等于就能运行万物、经国理民。得大体还须有用,这就要借助于“术”,术乃形而下者,道体与术结合,才能治天下国家。如果弃术从道,忽视形下之术,那么,作为大体之天理亦不能发明之。在程颐看来,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不是说体即是用,用即是体。用是表现体的,无用则体不能显。就此而言,则体用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论道而不论事,则道亦不显。在某种情况下,程颐更强调事“累高必自下”,由形而下才能达到形而上,道不是空谈,而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
今之语道,多说高便遗却卑,说本便遗却末。(27)
道只是理体,此理体不能离开具体的形而下的物事。万物皆存此至理,一事虽小,也必有其理,于一事上可以穷尽至理。理是抽象的,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但这是从其统摄万物的这个角度来看的,不如此,则理不可能统摄万物;另一方面,理的内容的表现形式是具体的、历史的,也是形而下的。贯通形上与形下,就是将理的超越性与理的表现形式的具体性、历史性结合起来,这种思想是程颐等宋代新儒家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的改造与发展。孔子“罕言性与天道”,注重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考察,因此,孔子哲学较少本体论的内容,更多地表现出强烈的实践性。而程颐等宋儒则将现实性与本体进行结合,力图为现实性找到超越的内容,这在易学哲学上就表现为将卦爻象、卦爻辞与卦理相结合,将本体与现象进行结合,将普遍的形而上学的理与现实的特殊性进行结合。
对于历史本体与历史现象,程颐一方面设定先验的天道和理作为历史的理体,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本体之理体有赖于在历史中生成和发展,历史本体与历史现象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理论的张力。程颐并不认为历史就是“理”的简单外化,历史具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很多时候还构成了对“理”的偏离。理虽然是本体,但它要通过不断变化的历史现象来表现自己,并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体现。这样,理的普遍性与理的实现的历史性得到了统一。
四、结语
程颐的易学思想中包含了很多历史哲学问题。北宋儒者普遍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待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们的理想和追求。程颐也不例外。他解读《周易》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能确立起永恒的、“大中至正”的历史评判标准和价值体系,探索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动因。在他看来,社会之所以未能摆脱种种弊病,就是因为人们不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他想通过自己艰苦的理论探索,在历史事件中发现理和规律的存在,为社会找到一个理想的发展模式。当然,程颐并不是专门的历史哲学家,他可能也没有建立一种历史哲学的自觉意识,但他重视研究历史与社会,其易学探讨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及其表现、历史价值和评判标准、历史发展动力等历史哲学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不自觉地将中国历史哲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①程颐《周易程氏传》卷第二,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08页。
②《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53页。
③程颐《周易程氏传》卷第一,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06页。
④程颐《周易程氏集》卷第二,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19页。
⑤程颐《周易程氏传》卷第三,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62页。
⑥《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3页。
⑦《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九,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9页。
⑧程颐《周易程氏传·易传序》,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89页。
⑨程颐《周易程氏传》卷第三,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97、698页。
⑩程颐《周易程氏传·易序》,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90页。
(11)《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8页。
(12)《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三,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2页。
(13)《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四,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3页。
(14)《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2页。
(15)《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九,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8页。
(16)《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九,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8页。
(17)《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7页。
(18)《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4页。
(19)程颐《周易程氏传·易传序》,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89页。
(20)程颐《周易程氏传·易序》,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90页。
(21)《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页。
(22)程颐《周易程氏传》卷第三,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08页。
(23)《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8页。
(24)《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八,《中庸解》,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56页。
(25)《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一(上),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9、270页。
(26)《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页。
(27)《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