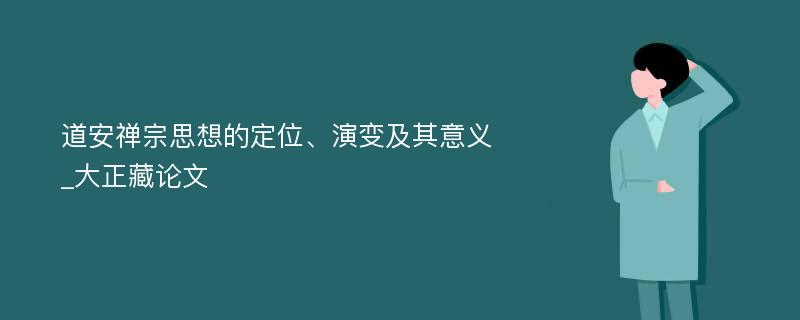
道安禅学思想:取向、演变与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禅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人。永嘉六年(312)生,“家世英儒,早失荫覆,为外兄孔氏所养。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乡邻嗟讶。至年十二出家”(注:《高僧传·道安传》,汤用彤校本,177页。)。二十四、五岁时游学邺中,师事佛图澄。永和五年(349),因冉闵之乱,率徒离邺避难。其后十馀年辗转於河北、山西、河南的牵口山、飞龙山、太行恒山、武邑、濩泽、王屋女休山、陆浑、新野等地(注:方广锠1999,145-174页。方广锠先生对道安辗转避难的路线的详细考订是近十年来道安研究方面最引人瞩目的成果。作者以道安生平几个重要的确定时空坐标点为参照,对各种相关史地资料作细致的梳理甄别、排比推定,基本上澄清了因为《高僧传》等基本文献自身存在的时空错乱而导致的种种歧说。窃以为是宇井伯寿、汤用彤、横超慧日、任继愈、方立天诸先生的有关研究之后最为重要的成果。但此文大醇微疵,仍有需补正之处,笔者将撰文拾遗补阙,此不详述。)。兴宁三年(365),避至襄阳,讲经研学、整理经典十五年。太元四年(379)春,苻丕陷襄阳,将道安献送长安,为苻坚所重。其后以译经为主,直至太元十年(386)逝世。
与支遁在早期禅学史中的暧昧形象不同,在所有研究著作中,道安都是被大书特书的重要人物。然而这也给我们的研究增加了困难:既然已经有这么多的研究著作对道安生平和思想的方方面面作了深入的研究,那么我们自然也不可能为了标新立异而塑造一个迥然不同的道安形象。尽管如此,我们仍将力图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发明:一是历时地来考察道安思想的变迁,从这种变化当中来凸显道安禅学活动的深化以及其中不变的主旨;二是将道安的禅学活动置於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中来考察,特别是将其置於南北方不同的文化氛围中、通过与支遁禅学活动的对比来展示道安禅学活动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重要意义和对后世禅学演进的深远影响。前者是从宗教哲学的内在角度来分析道安禅学活动演进的内在逻辑,后者是从文化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外在视角来分析道安禅学活动的外部激励因素。当然,在以下的叙述中,这两种视角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同时,为了叙事的明快起见,我们将所有史料厘衡、史实考辨方面的有关争议以及我们的取舍放在脚注中处理。
纵观道安一生,其为学凡有四期:第一、河北求学期。师事佛图澄、与法护译场诸僧交游皆在此时(注:安公在邺中与凉州诸僧交游事见《渐备经十住梵名并书叙》(《祐录》卷九,苏校本,331-332页)。)。第二、河北教学期。此时安公特重禅观,注解《道地经》等禅学经典便是在此期间进行的。第三、襄阳讲学期,此时将《般若》诸经的注释和讲解作为课徒授学之中心,弥勒净土信仰之践行亦在此时。第四、长安译经期,此时虽不废讲学,然以译经为其要务。
由於道安为学的第一期基本上只是学习和接受佛教教义,谈不上有太多的发挥,而且也缺乏可供分析的合适文本,因此我们可以存而不论。以下主要就道安为学的后三个时期来说明:道安对禅学的关切乃是贯穿其各个时期思想、活动的中心线索,也是我们理解道安其人其学的关键。在第二阶段,我们将着重通过考察道安对禅经的注解来分析其禅学思想在义理把握、诠释方法、为学宗旨等各方面对前人和同时代的其他人的超越。在三、四两个阶段,我们将着重阐明:尽管道安学术活动的具体内容已经由第二阶段的禅籍研究转向般若学研究和译经活动,但激励道安热忱於这些活动的内在动力仍然是对实际禅修之道的关切,它们与第二阶段的学术活动在精神气质上一脉相承,是道安禅学活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河北时期的道安禅学思想
——道安禅学对前人的修正与超越
道安在河北教学期间最重要的禅学活动便是对早期禅经的注释。《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十二门经》、《道地经》、《人本欲生经》、《了本生死经》等禅学经典的注释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注:关於安公注解各禅经时间之确定,参见汤用彤1983,142页、173页;宇井伯寿1979;横超慧日1958,203页、206-210页;荒牧典俊1982,252-253页;镰田茂雄1985,350-353页、371-372页。其中《安般注序》不悉作於何时,但一般都认为与其他禅经注序大致同时。本文为了便於和康序比较,故以此为例分析道安禅学思想。又,此处河北乃泛指黄河以北,故涵摄道安在河北、山西两省之讲学。)。以下我们以《安般注序》为主,同时结合其他注序来分析道安的禅学思想及其与前人、同时代人的异同。
道安作《安般注序》的直接动机是他认为“魏初康会为之注义,义或隐而未显”,故而希望更有所发明。由於康注、安注本来面目均已不存,因此康注中具体有哪些地方令道安觉得意犹未尽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比较康序和安序,我们还是能够看出道安对康僧会禅学思想的继承、修正和发展(注:对《安般守意经》和康僧会序文的详细分析,请参见笔者博士论文《汉魏两晋禅学研究》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相关部分。限於篇幅,此不详述。)。
首先,道安继承了陈慧、康僧会一系对禅修基本方针的理解。陈、康一系对禅定之道的基本理解是“弃”和“损”:“禅,弃也,弃十三亿秽念之意”(注:康序,《大正藏》卷五五,43a;苏校本,243页。)。安序承袭了这种解释:
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也。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致於无为也;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致於无欲也(注:安序,《大正藏》卷五五,43上;苏校本,244-245页。)。
在《阴持入经序》中道安也说:“阴结日损,成泥洹品(注:《大正藏》卷五五,44c;苏校本,248页。)。”可见这是道安对禅定之道的基本理解。
其次,道安对禅定神异效果的重视,也是与陈、康一系的思想一脉相承的。所谓“得斯寂者,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注:安序,《大正藏》卷五五,43c;苏校本,248页。),与康序所说的“得安般行者”所具种种“神德”之间的一致性乃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时期道安的其它注序也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对禅定神异效果的重视和赞叹。如:
其为行也,唯神矣,故不言而成;唯妙矣,故不行而至。统斯行者,则明白四达,立根得眼,成十力子,绍胄法王,奋泽大千。若取证则拔三结,住寿成道,径至应真。此乃大乘之舟楫,泥洹之关路(注:《阴持入经序》,《大正藏》卷五五,44c-45a;苏校本,249页。)。
夫道地者,应真之玄堂,升仙之奥室也(注:《道地经序》,《大正藏》卷五五,69a;苏校本,366页。)。
归精谷神,於乎羡矣(注:《道地经序》,《大正藏》卷五五,69b;苏校本,367页。)。
不滞者,虽游空无识,泊然永寿,莫足碍之,之谓真也(注:《大十二门经序》,《大正藏》卷五五,46a;苏校本,253页。)。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注序所包含的神明住寿思想。笔者在分析康序的本土思想特色时曾指出,延年益算是本土神仙方术最基本的价值目标,康序对此颇为重视,序中不乏所谓“制天地,住寿命”之类的渲染。但若以佛教教义格之,则天地万物均为因缘和合而成,皆有成住坏空之流转,“世皆无常,会必有离”(注:《佛遗教经》,《大正藏》卷一二,1112。),大雄如佛,亦不得永驻世间。道安对前人禅学思想中存在的误解多有修正,但对此却基本沿袭旧说,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现象,它无疑显示了本土固有观念对国人理解禅学的巨大制约。
与这种最基本立场的一致性相比,更突出的是道安就康氏对禅学所作解说的修正。
第一,道安纠正了康僧会对一些禅学基本观念和佛教重要名相的误解。“阴”是佛教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康僧会将“阴”解释成为心(“识神”)的微妙作用,并以此来说明禅定修行的主体能力,这显然是与佛教教义对“五阴”之阴的基本规定大相异趣的(注:宣方1998,22-23页。)。这种误读,在道安所作的各种禅经注释中,得到了纠正。如《阴持入经序》指出:“阴持入者,世之深病也”、“阴入之弊,人莫知苦”(注:《大正藏》卷五五,44c;苏校本,248页。),明确地将“阴”作为应当否定的“病”、“弊”来看待,这与康氏对“阴”大加赞叹相比,自然要恰当得多。
同样,对於安般禅的解释也是如此。康序虽然对安般禅的神异大加渲染,但是却没有对安般的基本含义作出明确的解释,而安序则一开篇就明确指出:“安般者,出入也(注:《大正藏》卷五五,43c;苏校本,244页。)。”康序将四禅与安般六事相比附,出现了对两者关系特别是“止”与三、四禅关系的不正确论述(注:宣方1998,24-25。),而安序则不作这种牵强的比附,将两者视为独立的两种方法:
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也。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致於无为也;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致於无欲也。无为故无形而不因,无欲故无事而不适。无形而不因,故能开物;无事而不适,故能成务。成务者,即万有而自彼;开物者,使天下兼忘我也。彼我双废者,守於唯守也。故《修行经》以斯二法而成寂(注:《大正藏》卷五五,43c;苏校本,244-245页。)。
这里基本上是将安般六事和四禅视为“成寂”(获得禅定)的两种平行的方法。尽管严格说来,这一解释也不尽准确,因为安般六事是得定的基本方法,而四禅则是为衡量定境深浅而划分的四个阶段,前者属修行方法,后者属於内证境界,所以不能将两者等量齐观,但安序的这一观点以康序的有关误解为背景而提出,显然是强调两者互相独立的一面,因而有其积极意义。
第二,与这种比较明显的修正相比,道安的这些禅经注序还有一种不太引人注目、然而却更为普遍地存在并且更为深刻的变化,这就是力图按照佛教教义本来的体系结构来解释禅学的倾向。如《安般注序》称:
安般居十念之一,於五根则念根也。故撰《法句》者,属《惟念品》也(注:《大正藏》卷五五,43c;苏校本,245页。)。
将安般置於十念之一,说明安般在五根中属念根、在《法句经》中属《惟念品》,都是力图将安般禅——推而广之,是将整个祥学——放在佛教思想体系的整体结构中加以诠释,来说明禅学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作用。这不仅表明道安希望按照禅学本来面目来认识禅学,而且还体现了他努力将各种具体禅法加以统一、整合的强烈愿望。
与这种追求统一融合的禅学旨趣相一致,道安在注解禅经时更多地采用了融会各种禅经互相发明的诠释方法,而不像康序那样基本上依靠援引外典来申述禅学的基本观念,也不像同代先达竺法雅那样滞拙地以格义的办法来阐明教义(注:参见汤用彤1983,143页。当然,融合《老》、《庄》,以玄学思想与佛教义理互相发明是当时的普遍风尚,道安也不例外(汤用彤1983,169页),而且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道安注解禅经用语同何(晏)、王(弼)著作措辞之间的相似(刘贵杰1991,259-261页)。)。这种方法保障了道安对禅学的解释较前人更为信实。
以上我们以与佛教教义相符合的程度为标准,得出了道安禅学思想较前人和同时代其它人更接近禅学本来面目的结论。不过如果我们的分析到此为止,则未免过於肤浅,因为我们仅凭常识大概也能得到类似的结论,只不过是经过一番分析显得更精密些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来追问:道安禅学的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些变化?
前面我们在分析康僧会禅学话语的拟定读者时曾指出,康僧会对禅学神异特性的强调是与其宣教的对象与语境密不可分的,同样,道安禅经注序的这些特点也是由其特定的读者对象和宣教目的所决定的。康僧会为了吸引一般民众对禅学的兴趣,因而不得不强调禅学神异的一面;而道安对禅学的诠释则首先是为他本人及其所统辖的僧团的实际修行服务的,因此更注意厘清各种禅观的相互关系、以及禅学在整个佛教教义体系中的位置、作用。而安世高译介的小乘禅经因为“善开禅数”,即善於从禅定实际需要出发,将佛教教义用数法组织起来,特别适合於研学和自修的需要,所以受到道安特别的青睐。纵观道安这一时期注解的禅经,可以发现基本上都是安译小乘禅经。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典大多前人已有注解於先,(注:如《安般守意经》有陈、康之注、《阴持入经》有陈慧注、《了本生死经》有支恭明注、《大十二门经》有前人所作《悬解》之传,等等。)道安再施训释,除了有校正前人不准确的解释这一用意之外,更深一层的用意是将其从一般的字句释义、文义疏通进而转化为可以用以指导实践的自修指南。这一点在各篇序文中均有较明显的体现。如:
造兹注解……冀未(疑当作“于”)践绪者少有微补(注:《阴持入经序》,《大正藏》卷五五,45a;苏校本,249页。)。
然童蒙之伦,犹有未悟,故仍前迹,附释未训。……傥孤居始进者,可以辩惑焉(注:《了本生死经》,《大正藏》卷五五,45b;苏校本,251页。)。
每惜兹邦禅业替废,敢作注於句末,虽未足光融圣典,且发蒙者傥易览焉(注:《十二门经序》,《大正藏》卷五五,46a;苏校本,253页。)。
这里处处将初学者设定为读者对象,并不是简单的谦辞而已,因为这些“发蒙者”不是一般的义学之徒,而是“践绪者”、“孤居始进者”,即远离尘嚣、隐居山林、躬自习禅的初学者,具体地说,首先是指追随道安辗转皞泽、飞龙山等地避世修禅的僧众。道安研究禅经的直接目的,便是为了替这些矢志修禅的同道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禅修之道,因此如何有利於实践是道安在注解禅经时考虑的首要问题(注:正是这种注经旨趣的差异,决定了道安与前人注经方法和侧重的不同。我们提到,道安在注解禅经时更多地采用了征引各种禅经互相发明的诠释方法。这里可以进而指出,道安采取的方法决不只是罗列各种经典一致或相近的说法以广见闻,而是注重思想的会通,一切以便利实践为的骛,因此“每览其文,欲疲不能。所乐而玩者,三观之妙也;所思而存者,想灭之辞也……其义同而文别者,无所加训焉”(《人本欲生经注》,《大正藏》卷五五,45a;苏校本,250页)。前面分析得出的安序与康序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安序强调在佛教教义的整体结构中认识禅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禅学的作用、地位的鲜明特色,从根本上说,也是由道安禅学服务於实践的本旨所决定的。又,“三观”是指经中所说的身观、五阴观、六衰观,这是小乘禅学的基本禅观,支谦所译的《佛说四愿经》亦有此三观,并谓由此可以断生死、得道证果(《大正藏》卷一七,538c)。)。
这种特定的对象性,决定了道安注经时一再强调禅修乃是解脱之道最基本的实践。如:
夫执寂以御有,策本以动末,有何难也……兹(安般禅)乃趣道之要径,何莫由斯道也(注:《安般注序》,《大正藏》卷五五,43c;苏校本,245页。)。
(禅修)乃大乘之舟楫,泥洹之关路。於斯晋土,禅观弛废,学徒虽兴,蔑有尽漏。何者?禅思守玄,练徽入寂,在取何道,犹睹於掌,堕替斯要,而悕见证,不亦难乎(注:《阴持入经序》,《大正藏》卷五五,45a;苏校本,249页。)。
夫绝爱原,灭荣冀,息驰骋,莫先於止;了痴惑,达九道,见身幻,莫善於观。大圣以是达五根,登无漏,扬美化,易顽俗,莫先於止(按丽本“止”作“正”,此句疑衍,盖系由前一行窜入),靡不由兹也(注:《道地经序》,《大正藏》卷五五,69b;苏校本,367页。)。
这里不仅从正反两面反复申述禅修的重要,而且勉励徒众禅修并非高不可攀,十分鲜明地体现了道安注解禅经的实践导向。
这种鲜明的实践性,决定了这一时期道安禅学的一个重要倾向,即在止观兼行、定慧并重的基础上更强调止和定的基础作用。道安禅学的基本立场是止观兼行、定慧并重。各序在使用“禅观”、“禅业”、“禅定”等词时,多是兼指止和观两方面;“止”“观”二词一般合用,即使对举,也以等列居多。但是,从小乘禅学的立场来看,“止”是较“观”更基本的一个阶段,只有在禅定收敛身心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以禅观破除烦恼。道安禅学的出於实修的需要,有时在止和观、定和慧两方面当中相对而言更强调前一方面。如《十二门经序》云:
是乃三乘之大路,何莫由斯定也。自始发迹,逮於无漏,靡不周而复始习兹定也。行者欲崇广德,而不由斯法者,其犹无柯而求伐,不饭而求饱,难以获矣。醒寤之士,得闻要定,不亦妙乎。每惜兹邦禅业替废,敢作注於句末,虽未足光融圣典,且发蒙者傥易览焉(注:《大正藏》卷五五,46a;苏校本,253页。)。
这里“定”的具体所指是十二门禅,当然也包括“慧”的含义(序中有“慧定”一词)。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以一个“定”字泛指禅学的全部内容,显然是认为定是禅修最基本的目标,言定则慧在其中矣。
二、襄阳、长安时期道安禅学思想的发展和深化
兴宁三年(365),道安为躲避战乱南下襄阳。襄阳地处南北往来之要塞,道安居此,立即感到江南般若学研究的执浪扑面而来,十分关注佛教发展的各项进展的道安对此自然不会无动於衷,因此立即投入对这一学术主流的研究。此后十五年间,其为学重心由禅经注释转向了般若学。但是这种具体关注内容的变化并不表示道安对禅学兴趣的衰退,相反,正是对禅修实践一如既往的重视以及寻求各种禅法的统合之道的强烈愿望,成为道安这个时期的学术活动的内在动力。
首先,道安的般若性空学说直接来源於其禅学研究。对此,汤用彤先生阐述甚详,兹引录於下:
安公可谓自禅观以趣於性空者也。《阴持入经序》作于濩泽,有言曰:“以慧断智,入三部者,成四谛也;十二因缘论净法部首,成四信也。其为行也,唯神矣,故不言而成;唯妙矣,故不行而至。”《道地经序》(亦作于濩泽)亦曰:“其为像也,含弘静泊,绵绵若存,寂寥无言,辩之者几矣;恍惚无行,求以漭乎其难测。圣人乃为布不言之教,陈无辙之轨。”《安般注序》(不悉作於何时)曰:“寄息故无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以致於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致於无欲。”在《人本欲生经注》内释想受灭尽定曰:“行兹定者,冥如死灰,雷霆不能骇其念,火燋不能伤其虑,萧然与太虚齐量,恬然与造化俱游。”所谓无言无为、静寂逍遥,语虽出於《老》《庄》,而实同於安公之般若。盖“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道行序》)“泊然不动,湛尔玄齐”(《随略解序》),亦何异於冥如死灰。故安公之空,发於禅也(注:汤用彤1983,176页。)。
其次,道安的般若学研究是其禅学活动的继续和深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此前道安对禅学神异效果的理解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般若学研究客观上对此起到了一定的修正作用。如前所述,在注释禅经阶段(特别是在较早的一些注序如《道地经序》和《阴持入经序》中)道安对禅学神异的阐释仍有神仙方术思想的痕迹,最明显的莫过於神明住寿的思想。而般若学强调般若正智的启蒙涤惑的慧照功能,因而对禅学神异的强调也是侧重於思想的觉悟和自由这一层次,而像神通变化这类神异由於只是描绘色身(肉体生命)在具体时空中的自由,相形之下反倒不是那么重要了。受此影响,道安在描绘修行的境界、果位时也不再对“归精谷神”、得道“升仙”(《道地经序》)、“泊然永寿”(《大十二门经序》大肆渲染,而更强调以心性的觉悟为禅修的根本目的。一个明显的例证便是这一时期的注序中,不再在人格神意义上使用“神”、“仙”等词语,具有强烈黄老色彩和实存意味的“谷神”等词语也不再出现。这种变化虽然未必表示道安自觉地抛弃了神明住寿思想,但客观上起到了削弱神异禅学影响的作用。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般若学研究使道安对止观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入。道安主张止观双运,定慧并重。但在注解禅经阶段他更强调以止为基础,止能生观,定能发慧。这也是小乘禅学的基本立场。而大乘禅学则认为,菩萨六度的修行当中,最重要的是般若波罗蜜的修行,包括禅波罗蜜在内的其他种种修行都受其统率。具体到禅观修行,便是在止观关系上更强调以观统止,而对般若学的研究使得道安对大乘禅学的这一基本立场有了深刻的认识。《合放光光赞虽略解序》是道安表述其般若思想的很重要的一篇文献(注:序文明确指出《光赞》於晋泰元元年(376)五月二七日送抵襄阳,其时道安居襄阳已有11年,又此序系作者於经旨“寻之玩之”后所撰,故其中所表当是道安襄阳时期思想的成熟形态。),其中写道:
痴则无往而非缴,终日言尽物也,故为八万四千尘垢门也;慧则无往而非妙,终日言尽道也,故为八万四千度无极也。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正而不害,妙乎大也(注:《大正藏》卷五五,48b;苏校本,266页。)。
这里强调一切修行的浊净邪正都以“慧”之有无为转移,与以前强调一切禅观智慧均由“定”之修持为基础,侧重点显然有异。
当然,对慧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将修定的重要性降低。从理论上讲,这两个方面本来就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而从道安的实际禅学活动来看,他对戒律建设的重视以及对净土信仰的践行(详后)都表明他对修定的关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具体化了。因此道安这一时期禅学思想中体现出来的以观统止的新趣向与其说是对前一时期禅学思想的修正,毋宁说是前者的深化。
这种深化是道安禅学思想发展的内在的逻辑的必然,而般若经典本身只是为这种深化的实现提供了契机。对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追求是道安佛学思想的最大特色,具体到禅学领域,便是力图统合各种禅观并在佛教教学的整体结构中理解禅学的地位和作用。如前所述,在道安注释禅经的宗旨、方法中,就已经体现了这一风格。但是经典文本自身的这种局限,制约了道安这一风格的充分发挥,因为在这些禅经当中,各种具体的行法如数息观、不净观、四谛观、五阴观、十二因缘观、十二门禅等,都是纷然杂陈的,而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有什么统一的原理,在这些经典内部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表述。这一点自然不能让追求融会贯通的道安满意。而般若类经典恰好提供了统一各种禅观的最基本的原理,这就是以般若波罗蜜的修行统率各种具体禅观的修行。特别是《般若经》的《放光品》在列举了所有种种禅观的名目以后,明确地指出“菩萨为得般若波罗蜜故,行持如是种种禅那波罗蜜”(注:横超慧日1976,213页。)。带着寻求各种禅观的统一性这一问题意识进入般若学研究的道安,自然对此格外注意。其注序中千行万定藉慧以成的思想,正表明了他这种追求统一性和系统性的禅学趣向的进一步深入。
道安长安时期的译经工作,也正是以这种对禅学统一性和系统性的追求为内在动力的。就此而论,同样是其禅学活动的继续和延伸。襄阳时期的般若学研究只是部分地解决了禅观统一性问题,即找到了将各具体禅观(“多”)统一於共同的价值目标——般若智慧(“一”)的基本原理,但这些禅观彼此之间的兼容贯通(“多”“多”关系)则仍未得到有效的说明,而且这后一方面可以说是难度更大的一项工作。
新经典特别是有部论典的相继传来,为道安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与般若经典完全以般若空观为题旨相比,《阿毗昙八犍度论》与《毗婆沙论》等有部论典从有部立场出发对所有法数作了完整、系统、缜密的组织,其中也包括对所有禅观在整个佛教教义学中作用和地位的详细解释。道安对此推崇备至:
其为经也,富莫上焉,邃莫加焉。要道无行而不由,可不谓之富乎?至德无妙而不出,可不谓之邃乎?其说智也周,其说根也密,其说禅也悉,其说道也具。周则二八用各适时,密则二十迭为宾主,悉则味净遍游其门,具则利钝各别其所。……其将来诸学者,游槃於其中,何求而不得乎(注:《阿毗昙序》,《大正藏》卷五五,72a-b;苏校本,376页。)!
有部论典这种宏富、深邃、系统、完备(“富邃洽备”)正是道安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体系,难怪他在《毗婆沙序》中悲欣交加地写道:
余欣闻秦土忽有此经,……载玩载咏,欲疲不能。……然后乃知大方之家富,昔见之至狭也。恨八九之年,方窥其牖耳(注:《大正藏》卷五五,73c;苏校本,382页。)。
总之,从早年注释禅经、带领徒众在颠沛流离中坚持习禅修定,一直到晚年投身於译经事业,终於夙愿得偿,对解脱之道的探究和实践一直是道安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道安的弥勒净土信仰和宾头卢信仰
与注释禅经、研究般若、翻译论典等一系列理论活动相比,道安制定戒规、奉行净土等实践活动更强烈地体现了道安对解脱实践的重视。
《高僧传·道安传》记道安“每与弟子法遇等,於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注:汤校本,183页。),据此可知道安的净土信仰是弥勒信仰。
道安与法遇等人立誓往生的具体时间不详,汤用彤先生认为“必在襄阳”(注:汤用彤1983,155页。)。按汤著所据,乃因僧传载昙戒与安公等同愿生兜率,而昙戒为南阳人,由此推测其“当在南阳为安公弟子”(同a),进而断定立誓之事必在襄阳。不过当时安公名满天下,四方同志不远万里闻风辐辏者每每有之,仅此似不足断定其事必在襄阳。参诸安序,衡以情理,立誓之事也有可能是在其南下襄阳以前。今试申述如下:
道安信奉净土的初衷,不是想求个人的福报,而是因为当时汉地通识者寡,经籍疑义滞而难决,所以希望往生兜率,得见弥勒以为决疑解纷(注:详后,并见汤用彤1983,156页。)。而这种心情,在他濩泽时期所作禅经注序中已屡屡见之:
安未(碛沙藏、元本作“来”)近积罪,生奉百罹,狄戎孔棘。世乏圣导,潜遁晋山。孤居离众,幽处穷壑。窃览篇目,浅识独见,滞而不达,夙宵抱疑,咨诹靡质。……世不值佛,又处边国,音殊俗异,规矩不同,又以愚量圣,难以逮也。冀未践绪者少有微补,非敢自必析究经旨(注:《阴持入经序》,《大正藏》卷五五,45a;苏校本,249页。)。
安宿不敏,生值佛后,又处异国,楷范多阙。仰希古贤,滞而未究,寤寐忧悸,有若疾首(注:《十二门经序》,《大正藏》卷五五,46a;苏校本,253页。)。
予生不辰,值皇纲纽绝,猃狁猾夏,山左荡没,避难濩泽,师殒折,周爰咨谋,顾靡所询。……天竺圣邦,道岨辽远,幽见硕儒,少来周化。先哲既逝,来圣未至,进退狼狈,咨嗟涕洟。故作章句,申己丹赤。冀诸神通,照我喁喁,必枉灵趾,烛谬正误也(注:《道地经序》,《大正藏》卷五五,69c;苏校本,368页。)。
因经文疑义“滞而未究”而“寤寐忧悸”,故希神通大圣“烛谬正误”,由此可见当时道安就有愿生兜率之强烈动机。虽然仅此不足以论定立誓往生之事必在此时,但从其心态揣测,则似有相当之可能。此外,慧远为道安之得意弟子,长期追随道安,而立誓往生之事慧远不预其席,似亦说明其事以在慧远师事道安之前更为可能。
道安与弥勒信仰的渊源,还可以更向前追溯到出家之初。僧传记道安未受戒以前所读之第一部佛典为《辩意经》。此经已佚,不过后来北魏法场所译的《辩意长者经》现存,该经篇末便提到弥勒授决之事(注:汤用彤1983,156页。)。道安后来誓愿往生弥勒,应该与这种第一印象不无关系吧。当然,道安弥勒信仰更重要的来源,大概还是法护译籍。道安以前译出的弥勒经典,有《弥勒本愿经》、《弥勒成佛经》、《弥勒经》、《弥勒当来生经》等(注:见《祐录》相应各卷,《大正藏》卷五五,8a、8b、18a、18b;此外《祐录》卷十二有《弥勒六时忏悔法缘记》一卷,乃自第一经抄出,按道安曾制定三科六时之戒规,此亦或系其门人抄出。),其中后两经译者不明,而前两经均系法护所译。
道安时期的净土信仰,主要有弥勒净土和阿弥陀净土两种。从流行的程度来看,阿弥陀净土已有后来居上的气势。我们在僧传、尼传中看到的这一时期的净土信仰,基本上都是阿弥陀信仰。(注:昙戒临终愿生兜率,侍疾弟子问“何不愿生安养(阿弥陀净土)”,亦可证当时之风尚。)这大概与《法华经》的风靡於世有很大关系。那么,道安为什么对弥勒净土情有独钟呢?
这可能与弥勒菩萨的一个重要职能有关。经言弥勒从佛受记(预言),继释迦而为未来世佛,故留驻世间为众决疑。道安信仰净土,主要原因便在於此。这一点可以从道安弟子的追忆得到证实。僧睿回顾罗什以前般若学的发展,认为道安的性空宗最得其实,但犹恨未尽,而其原因则在於经典匮乏。最后他说:
先匠所以辍章於遐慨,思决言於弥勒者,良在此也(注:《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大正藏》卷五五,59a;苏校本,372页。)。
可见道安愿生兜率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便在於希望能够藉此澄清经典疑义。
道安信奉弥勒,当时大概知之者甚众,因此苻坚遣使奉送五尊佛像致敬,其中便有结珠弥勒像一尊(注:《高僧传·道安传》:苻坚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汤校本,179页)。)。只是道安对於弥勒净土信仰的具体行法,我们却不得而知,好在僧传有几则记载有助於我们作出大致的推定。僧传载道安每次聚众讲法都要“罗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晖,烟华乱发。使夫升阶履闼者,莫不肃焉尽敬矣”(注:汤校本,179-180页。)。《昙戒传》称传主“博通三藏,诵经五十万言,常日礼五百拜佛。……后疾笃,常诵弥勒佛名不辍口”(注:汤校本,204页。)。据此推测道安之信奉弥勒,大概也不外乎诵经、礼拜、称名而已,与真正的观想念佛禅法似有出入。但念佛为禅法之一种,这一本义道安还是很清楚的。道安《婆须蜜集序》言“(婆须蜜)集斯经已,入三昧定,如弹指顷,神升兜术”即是其证(注:《祐录》卷十,《大正藏》卷五五,71c;苏校本,375页。《婆须蜜集序》《祐录》题为“作者未详”,然《婆须蜜菩萨所集经》与《僧伽罗叉经》均为僧伽跋澄赍来,出经方式完全一致,《僧伽罗叉经序》为道安所作,此序与其文风一致,当亦是道安所作。对此学界未闻有持异说者。)。
道安之弥勒信仰似与有部学说颇有渊源。婆须蜜(有部第八祖——此据僧祐《萨婆多部记目录》)神升兜率事已前见,今再举罽宾诸师为例。罽宾为有部东方师之重镇,该国宗匠升入兜率值见弥勒之事经传记载颇丰。道安《僧伽罗叉经序》、《婆须蜜集经序》均记僧伽罗叉(即《修行道地经》之作者,有部第二十九祖)死后升入兜率与弥勒会晤;僧传记佛驮跋陀罗曾入定“暂至兜率,致敬弥勒”(注:汤校本,70页。);《慧览传》言罽宾禅师达摩比丘“曾入定往兜率天,从弥勒受菩萨戒”(注:汤校本,418页。)。若再考虑到道安所注禅经多为有部经典,尤其是道安对《修行道地经》之推崇,则有部学说对道安禅学思想之影响实在不容忽视。
僧传记道安临死以前瑞相云:
后至秦建元二十一年(385)正月二十七日,忽有异僧,形甚庸陋,来寺寄宿。寺房既迮,处之讲堂。时维那直殿,夜见此僧从窗隙出入,遽以白安。安惊起礼讯,问其来意,答云:“相为而来。”安曰:“自惟罪深,讵可度脱。”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须臾浴圣僧,情愿必果。”具示浴法。安请问来生所往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报,尔夕,大众数十人悉皆同见。安后营浴具,见有非常小儿,伴侣数十,来入寺戏。须臾就浴,果是圣应也。至其处二月八日,忽告众曰:“吾当去矣。”是日斋毕,无疾而卒(注:汤校本,183页。)。
据此则后人认为道安求仁得仁,固无所憾也。
与弥勒信仰相近,道安事迹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信仰,即宾头卢信仰。宾头卢为不入涅槃、在世护法之阿罗汉,其性质与弥勒菩萨相近(注:汤用彤1983,157页。)。僧传云:
安常注诸经,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堪远理,愿见瑞相。”乃梦见胡道人,头白眉毛长,语安云:“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弘通,可时时设食。”后十诵律至,远公乃知和上所梦宾头庐也。於是立座饭之,处处成则(注:汤校本,183页。)。
《十诵律》之译出,时在道安殁后二十年,故此事亦颇有神异色彩。从学术的立场来看,这种神异事迹的真伪当然是我们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不过我们关心的也不是这一事件本身的真伪,而是这一事件为什么受到慧远以及后人的重视。在辑录慧远与罗什问答而成的《大乘义章》中,罗什时确否定了阿罗汉住寿一劫有余的说法,而且指出经典中明确提到凭借神通力而长驻於世的阿罗汉只有宾头卢而已,此外更无所闻。这一点可能是后人重视此事的一个主要原因(注:关於宾头卢信仰及其在后世的流传,道端良秀之《罗汉信仰史》有较详细的论述(道端良秀1983,27-37,43-83)。又,敦煌文献中有《请宾头卢疏》之残片(S10621,《英藏敦煌文献》,第13册,82页),亦可证此。)。
四、道安禅学活动的历史语境和历史贡献
纵观道安的禅学活动,其特点有二:一为面向实践,即以有利於僧团之实际修行为一切举措之出发点;二为融会贯通,尤其是融贯禅观与般若智慧,使禅学在教义学的整体中得到阐释。对此,我们前面已予以充分说明,以下再联系道安所处时代之氛围来考察影响道安禅学这两大特色形成的因素及其意义。
从根本上说,面向实践和融会贯通乃是佛教的根本立场和本质要求。佛教是追求解脱的宗教实践活动,包括般若思想在内的佛教理论都是从以禅定为主的实践中产生的,也必须在禅定中重新体征才能够成为修行者的自觉,因此面向实践乃是其基本要求。而禅观实践如果不与佛教教义特别是般若智慧相贯通,也就不足以与外道的习禅修定相区别,更谈不上解脱觉悟。因此这两个方面都是佛教的本质要求。
但当佛教从其原有文化土壤移植到另一种文化、特别是相当成熟、相当发达的华夏文化土壤中时,这种根本立场和本质要求的重新实现便需要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快慢迟速不是佛教单方面所能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由接受佛教的文化自身的“生态环境”决定的,尤其在佛教传入的早期更是如此。
道安时代的华北地区战火不断,哀鸿遍野。仅冉闵篡立之时便诛杀二十余万人(注:《晋书·石季龙载记》: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死者二十余万……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数诛之,於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中华书局本,2792)。)。连年兵燹使人们饱尝离乱夭殇之痛,深感人生的无常和苦难,从而对佛教思想有了更亲切的感受和更深刻的认同。如果说南渡士民因为偏安东南得以喘息、对佛教的认同基本上还停留在思想观念层面上的话,那么不能或不可能南下的北方士民则因为有更多的切身之痛而有更强烈的解脱实践要求。这种时代氛围构成了道安禅学活动实践取向的最广阔的背景。
在这种宽泛的民众心理基础上,有几个文化地理的因素对於佛教的流行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第一,随着晋室迁播,中原土族纷纷南下,玄学清谈在北方几乎销声匿迹,传统儒学也花果飘零,由此造成的文化空缺亟待填补,而佛教正好充当了替代性的文化主体。第二,北方胡族大举移居中原腹地,改变了原有的文化格局。仅在石赵秉政三十年间,就徙氏、羌、胡羯各族数十万人填充华北、中原(王仲荦1979,252)。佛教在这些少数民族中本来就有相当的影响,这些民族的迁入扩大了佛教在华北、中原传播的群众基础,这些民族的上层人物、特别是执政者对佛教的支持使得佛教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存空间。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佛教在北方地区迅速传播开来。而教徒规模的壮大必然对佛教实践的深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道安僧团等一批注重修行实践的僧团就是在这一历史潮流中应运而生的产物。
具体到道安僧团,从其门徒来源上看,有相当一些人来自邺中(注:从道安的履历来看,他曾三次入邺:一为咸康元年(335,年24)入邺师事佛图澄,二为永和五年(349,年38)应石遵之请入邺居华林园,三为永和十二年(356,年45)还邺居受都寺。当其三入邺中之时,“徒众数百,常宣分化”(汤校本,178)。佛图澄在邺中经营多年,当地四众弟子,多其门下,故谓道安僧团中应不乏昔日佛图澄门下。),佛图澄的神异对他们影响很大,因此对通过禅定实践获得种种神异非常有信心,这也是促使道安僧团特别重视禅定实践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道安早期禅学活动中所体现的对神异的重视,与此也不无关系。
正是当时南北方文化氛围的差异,使得道安禅学活动有别与同时代南方的支遁等人。
支遁禅学活动的语境是江东的玄学清谈,为了引起玄学名士对禅学的兴趣与关注,支遁投其所好,塑造了完全老庄化的禅学形象,使得禅学话语成功地进入了当时的学术主流,成为玄学的新时尚。就其将禅学由上流名士所不屑的“炫异惑众”的神仙方术形象转变成为文化精英普遍重视的玄远思想境界而言,支遁功不可没。但从禅学作为严肃的解脱之道的思想本旨来看,支遁这样做同样也模糊了禅学的本来面目,是对早期神异禅学矫枉过正的一种反动。流弊所致,便是使得人们对禅学的兴趣往往停留在文句的欣赏、思想的玩味上,而真正践躬修习者却寥寥无几,说禅之风远甚於习禅之举(注:当时南方特别是吴越诸山也零星地散布着一些习禅者,如法崇(居剡之葛岘山,“茅庵涧饮,取欣禅慧”;禅法不明,观其言语,颇具玄风,且“尤长法华一教”,与支遁相近,当系念佛一类)、帛僧光(=昙光;石城山、章安寒石山,禅法不明,多有神异,灭后形骸不朽)、昙猷(=法猷;台州赤城山,禅法不明,多有神异,僧传记其持咒、攘星等事)、慧开、慧真(余姚灵秘山,禅法不明)、慧元(武陵平山,僧传记其常习诵禅经,食疏幽遁,永绝人途)等,但当时影响似均不大。按水野弘元先生《禅宗处理以前のツナの禅定思想史序说》中不列法崇、慧元,而增法虔一人(剡山,支遁同学,僧传但谓其“精理入神”,对照支遁伤悼之词,应是以名理见长)(水野弘元1957,15-54页),未见其当。)。站在信仰者的立场来看,这种风气於禅修实践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道安的禅学活动始终把实践放在首要位置。无论是注解禅经,还是制定戒规、整肃教团,还是信奉净土、致敬弥勒,都是其解脱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注:一个反映支遁与道安禅学思想细微差别的例子是:在支遁的诗文中总是把“禅”和“思”合用,而道安的著作中却见不到“禅思”一词,相反却经常能看到“禅定”并称,甚至直接用“定”来指称禅学,表明了两者对禅学两个方面的侧重不同。)。
就道安禅学活动面临的历史课题而言,它与支氏之禅学活动又是一致的,即都必须提升禅学的文化品位,引起人们对禅学真正严肃的关注。只是因为各自所处的文化语境有别,导致了两者对这一历史课题的回应方式的不同。道安南下后研究重点转向般若学,是其自身思想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对南方佛学思潮的回应(注:另一个不应忽略的制约因素是文本意义上的。较诸篇幅不长、内容单薄的早期禅经而言,般若经典无论是篇幅还是思想都要宏富得多,从而给中国僧人提供了更大的阐释空间。特别是法护译籍的重新发现和流行,极大地促进了般若学研究的进展。)。这也说明了一时一地的文化语境对佛教思想发展的制约。
总之,道安的禅学活动乃是时代文化的精神产儿,有其深刻的政治、文化、思想背景。
关於道安在佛教史上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汤用彤先生有堪称经典的评定(注:汤用彤,136页。),本来无需笔者再呶呶置喙,不过鉴於本文是一篇禅学史研究论文,故此着重从这一特定角度再略赘数言以为结语。
第一,道安系统整理了此前译出的禅经,为之作注写序,澄清了前人的一些误解,加深了人们对禅学的认识。第二,道安制定戒规(注:汤用彤,1983,152-155页。),倡导禅定修行,真正严肃的以解脱为宗旨的大规模的佛教修行实践可以说是从道安才开始的。第三,道安综合了自汉以来佛学的两大发展趋势——以安译禅经为代表的有部思想和以支谶、竺叔兰、法护译经为代表的大乘思想,将禅学和般若思想相融贯,力图在佛教教义学的整体架构中诠释禅学的作用和意义。这种融会贯通的思想取向,从其直接影响看,是为鸠摩罗什介绍大小乘融贯的禅学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而从长远来看,它确立了后世中国禅学强调融会贯通的基调。第四,道安提倡净土信仰并身体力行,开后世净土信仰之先河。第五,道安培养了一大批禅学人才,为禅学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切实的推动作用。
道安禅学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神明住寿的思想不符合佛教禅学本义、禅观的具体行法仍然阙如等等,但这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客观局限(注:而且,根据本文的观点,前一条的历史作用具有两重性。),是不能深责於道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