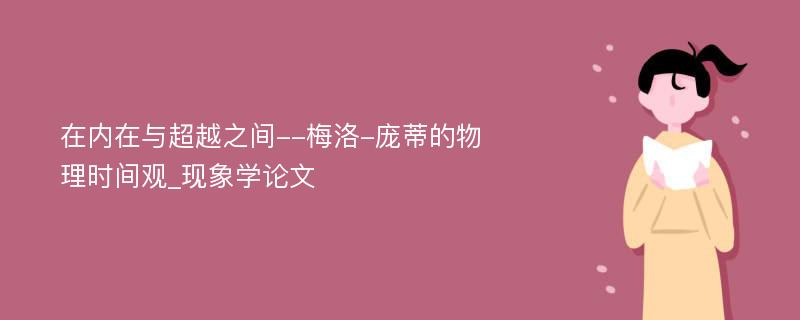
在内在性与超验性之间——梅洛-庞蒂的肉身时间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肉身论文,时间论文,超验性论文,梅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4)01-0108-07
时间问题一直是现象学的核心问题。无论在胡塞尔的意识分析中,还是在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中,时间分析都起到一种奠基性或前提性的作用。被誉为“第三位现象学经典作家”的梅洛-庞蒂也同样重视对时间的分析。在《知觉现象学》中,他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时间性问题,而散见于其他地方的关于时间的论述还有很多。本文主要探讨《知觉现象学》一书的时间观念。梅洛-庞蒂的时间分析借鉴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许多思考,但由于它始终围绕着在世存在的主体的肉身性而展开,可以说是为重建肉身主体而服务的,因此,它最终又呈现出不同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风貌。
一
梅洛-庞蒂是从在世存在的主体出发来思考时间问题的,这看起来与海德格尔一样。但从一开始,梅氏的主体概念就比海氏的形式化的“此在”概念及传统哲学中基于意识自主性而建立起来的主体概念(胡塞尔依然归属于这一传统)蕴含了更多的内容。在他看来,在世存在的主体有空间的、时间的、性的等各种维度,我们应该在“各个维度的相互交织中来研究主体”,并“重建我们的主体概念”[1](P470)[2](P514)[3](P411)(注:本文所引《知觉现象学》一书中的文字,以法文原本为依据,又参看了中文本和英文本。因此,文中同时列出了此书三种版本的页码,依次为法文本、中译本和英译本页码。);主体应该是一种肉身化的主体。由此出发,梅洛-庞蒂不仅批判了物理学的客观时间观念,也批判了柏格森和胡塞尔式的作为内在意识的时间观念。他认为,时间既不在事物或客观世界之中,也不在意识状态之中,而是产生于主体与事物的关系中,它是主体的一种生存维度。
客观世界没有时间,这是因为,在客观世界中只有永恒的现在,没有将来和过去。“将来和过去处在一种前存在和永恒遗存之中。”[1](P471)[2](P515)[3](P412)也就是说,客观世界过于充实,它完全被现在所占据,以至没有空隙让将来或过去进入其中。要使两者进入,就需要一个缝隙,需要一个能使坚实的事物虚无化的主体。这也是萨特,甚至胡塞尔的观点,但他们把这种使事物虚无化的能力单纯地归之于意识;而梅洛-庞蒂则把它转移到了我们的肉身存在上来。他认为,只要我在世界中存在,事实就不可能以其纯粹坚固的面目示现于我。因为事物向我的呈现必须以我“朝向客观世界的有限的视角”为前提,它不可能一下子把它的所有方面呈现于我,我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整个事物包览于我的眼底。因而,显现给我的事物始终是有限的,也是敞开的。过去和将来的进入正是以这种事物向我的有限敞开和连续呈现为前提的。梅洛-庞蒂由此重新分析了时间是一条河流的著名隐喻。他认为在这一隐喻中,暗含了一个处在河流中或河流边观看的人。“当我说前天冰川融化形成的水流在目前流过时,我暗含了一个处在世界中的某个位置的目击者;我比较他看到的连续景象,他在那里目睹冰雪的融化,他顺流而下,或者两天以后,他在河边看到他在源头投下的木块流过。诸‘事件’是被一个在客观世界的时空整体中的有限观察者分割的。”[1](P470)[2](P514)[3](P411)但如果我们考虑事件本身,那么,冰雪的融化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结果就只是一个单一不变的存在,在其中没有事件的位置。“变化假定了我所处的和我从那里看到事情之展现的某个位置;如果没有目睹事件发生、其有限的视角是事件之个别性的基础的某个人,那么也就没有事件。时间必须以一种对时间的看法为前提。”[1](P470)[2](P514)[3](P411)
同样,梅洛-庞蒂认为,时间也不存在于意识中。这即是说,时间不是意识之内的对象。因为“作为一个意识的内在对象的时间是一种被夷平了的时间”,如同在客观世界中一样,它不再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过渡综合,而只是一系列的现在。“换言之,它根本不再是时间。”[1](P474)[2](P519)[3](P415)过去并不像大脑痕迹或某种身体结构那样沉淀在我们的身体、意识或无意识中,以至只要有某种神经冲动的启动就能打开它。记忆或某种保存下来的知觉,“至多只可能是让人想起过去的一个契机,而不是被人认识到的过去。”[1](P473)[2](P517)[3](P413)比如说,我眼前的桌子把我带到了过去,因为在这张桌子上留下了我的名字,留下了斑驳的墨水痕迹。但是,这些印迹本身不在过去,我也不是由它们推出过去。我之所以能从中想到过去的事件,“是因为我从别处得到了过去的意义(sens,即方向),是因为我在自身中带着这种意义(signification)。”[1](P472)[2](P517)[3](P413)可以说,是这种意义本身才使我与过去相遇。比如说,这些印迹直接唤醒了我过去的生活的欢乐与痛苦,唤醒了某一时期求学的艰难等等。自然,这种呈现的过去不是过去本身,而只能是透过现在的视点所看到的过去,就像“透过在卵石上流动的水所看到的卵石”。[1](P478)[2](P522)[3](P418)换言之,过去只有在与现在(或现在的事物)的关系中,才能呈现出来。对于将来也一样,我们不可能用意识内容构造出将来。“因为将来尚未存在,不能像过去那样在我们身体上烙下标记,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解释将来与现在的关系,只能通过类似于现在与过去的关系来解释它。”[1](P473)[2](P518)[3](P414)正如只有基于现在我们才能看到过去,将来也是通过现在而展现的。当我们说,我们展望或筹划一个将来时,首先要使将来这个方向(sens,即意义)向我们打开。由此,将来向我们涌来,它促迫着现在,取消着现在,就如当我们站在沙滩上时,脚下的沙子不断地被涌上的潮水卷走而使我们失重一样。因此,“将来不是在观察者的后面作准备的,而是在观察者的前面酝酿的,就像暴风雨是在地平线上出现的一样。”[1](P471)[2](P515)[3](P411)这也就是说,时间是从将来流向现在的,而现在又不断地转向过去而为将来腾出空间。这看起来与海德格尔的观点相似,但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两者的差异。
总之,梅洛-庞蒂认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种整体的时间关系。“时间是在时间的各个部分之前被我们想到的,时间关系使在时间中的诸事件成为可能。”[1](P474)[2](P518)[3](P414)这样一种整体的时间关系既不是客观自在的,也不是在意识之内的意识材料;它产生于我与事物的活生生的关系,因此,它既是超验的(超验性),又是为我的(内在性),总之具有暧昧性,而这种暧昧性最终又奠基于同样浑沌莫名的主体的肉身性中。
二
这种整体的时间关系是如何显现的呢?梅洛-庞蒂认为,这需要借助于一种时间综合,借助一个时间场。胡塞尔在分析内在时间意识时,已经勾勒出了一种时间场结构。在时间场的中心,是一个处于现实性高潮的“原印象”(Urimpresion),它被刚刚过去之物(“滞留”)和即刻到来之物(“前摄”)的晕圈(Hof)围绕着。正是这层非课题化的晕圈,使每一个刚刚消失之物,在其消失后仍在我们的意识中保留着,并作为晕圈呈现给下一个到来之物,从而使连续性成为可能。[4](P21)梅洛-庞蒂继承了胡塞尔的这种时间场结构,只是进一步把它从纯意识领域扩展到了肉身在世的知觉场领域。“胡塞尔把滞留和前摄称为把我限定在一个周围域中的意向性。这些意向性不是来自一个中心的我(Je),而是来自后面拖着它的滞留视域,前面被它的向将来的前摄钩咬住的我的知觉场本身。”[1](P476)[2](P521)[3](P416)由此,梅洛-庞蒂区分了两种意向性。一种是有意识的意向性,梅洛庞蒂称之为“行为意向性”(l'intentionnalité d'acte),另一种是更
原初的,属于前意识活动领域的运作意向性(l'intentionnalité opérante),或作用
意向性(fungierende Intintionalitat)。(注:这两种意向性的区分其实胡塞尔本人已
经作出了,但梅洛-庞蒂无疑更加强调了这两个层次的意向性的区分,或者说,进一步“
扩大了”意向性概念。[1](Pxiii)[2](P14-15)[3](Pxviii))后一种意向性是梅洛-庞蒂
所特别强调的,正如知觉包含着意识,他认为运作意向性是行为意向性的奠基,并使行
为意向性成为可能;而在时间的知觉场中起作用的主要就是运作意向性。也正是由于它
,时间才不可能局限于纯粹的意识领域,而是交织于主体与事物间的关系中。
处在时间知觉场的中心的是作为原印象的现在。但如何界定现在呢?胡塞尔已经指出,对现在的体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当下这一个点,即“原印象”的知觉,这可称之为狭义上的现在,另一种是对由时间场所形成的具有广延的一个时间段的知觉,如说出一个句子所需要的时间段,这是一种广义上的现在,它甚至是一种更原初的时间知觉,因为对现在的任何描述,都需要意识对时间的一种集中,作为“点”知觉的时间实际上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梅洛-庞蒂主要是在广义上来说现在的,而这也是由知觉场的特性所决定的。由此,“尽管可以说我的现在就是这个瞬间,但它同样是今日,今年,我的整个一生。”[1](P481)[2](P527)[3](P421)当我们乘火车时,车窗外的树像一阵风似地过去了,而远处的山峦却几乎不动,但两者都是我所体验到的现在。“同样,如果我这一天的开始部分已经过去,那么我这个星期的开始部分则还是一个固定点。”[1](P420)[2](P525)[3](P420)因此,我们对现在的确定是取决于相应的时间背景,取决于过去和将来的存在的。现在的这种既确定又不确定的性质同样处于超验性与内在性之间,具有暧昧的特征。
但是,如果说我们能把具有一定广延的时间段界定为“现在”,那么,又如何保证这一时间段的同一性呢?靠的就是胡塞尔所谓的时间的“过渡综合”。它指的是,当时间从一个时刻转向另一个时刻时,前面的时刻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仍然滞留在后面的时刻中,只是发生了变化,沉入了当前时刻的水平面之下,只要我伸出手去,透过薄薄的时间层,我就能挽起它。接着而来的时刻又把刚刚还在的当下推入过去,从而使在我之前的时间层变厚。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每一个现在重新肯定了它驱逐的整个过去的呈现,预期了整个将来的呈现。”[1](P481)[2](P526)[3](P420)因此,现在并不是自身封闭的,而是不断在追赶着一个过去,同时迎迓着一个将来。由此,我们才可以把一连串的瞬间(狭义上的“现在”)当作一个广义的“现在”来看待,因为它们在同一个时间场中,具有共同的方向和意义(séns),正如一连串的单词可以组成一个句子一样。因此,
时间的过渡综合使时间不再是呈现在意识中的连续单一的时间点,而是具有厚度的时间
层。正是在这一点上,梅洛-庞蒂批评胡塞尔,认为“胡塞尔的错误就在于他是从一个被
看作是没有厚度的,作为内在意识的现在场(Prasensfeld)出发来描述(时间的)嵌合的。
”[5](P277)在这种具有厚度的时间的基础上,梅洛-庞蒂后来发展起了一种垂直时间观
。“垂直”一方面指包蕴于一定的时间结构或时间形式(Zeitform)中的内在经验或时间
质料(Zeitmaterie)的丰富性,另一方面指时间从“原始的存在”(être brut)或“野性
的存在”(être sauvage)中绽裂出来、相互交错而具有的纵深和厚度。[5](P 237,244
,247,321,325.etc.)从这里可以看出,梅洛-庞蒂始终强调时间的肉身性特 点,在后
期,他甚至直接说时间就是一种肉质(chair)。而在《知觉现象学》中,时间 的这种过
渡综合也是基于肉身在世的运作意向性的,所以它不是一种理智综合,而是一 种感知综
合。理智综合只有在感知综合的基础上才具有时间意义。[1](P478)[2](P523) [3](P418
)所以梅洛-庞蒂甚至直接就把感知综合称为时间综合。[1](P276)[2](P305)[3 ](P239)
由此出发,梅洛-庞蒂含蓄地批判了自奥古斯丁以来把过去与明确的记忆联系在 一起的
传统时间观。“如果我们只能在明确的记忆形式下拥有过去,那么我们每时每刻 都应该
试图回忆过去,以便证实过去的存在,就像舍勒谈到的一位病人,他需要不断地 回头张
望,以便确证物体还在那里。”[1](P479)[2](P523)[3](P418)事实却是,我们 在感知
综合的原初性中,就已不容置疑地肯定了过去,而明确的记忆只不过是知觉的一 种极端
状态而已。
如果说处于时间场核心的现在对我来说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包围着现在的过去和将来也应该为我们存在,它们也同样有一种“内在性”和“超验性”。所谓内在性,是指它们是在我的身后或周围能让我看到或感受到的东西,所谓超验性是指它们在显现为我的明确活动的对象之前就已经在我的生活中存在。[1](P418)[2](P4528)[1](P364)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谈论我们的出生和死亡。在海德格尔那里,死亡对此在来说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对死亡的先行领会使时间呈现为一种从将来向过去的当前的流逝,从而也向此在给出了一种本真式的返回自身、担当责任的生存方式。梅洛-庞蒂同意死亡的不可逾越、不可体验性,但他似乎不太欣赏本真式的与非本真式的死亡领会之区分。这是因为,与海氏标举时间性的此在不同,梅氏更强调空间性的共在的可能性。所以在梅洛-庞蒂看来,死亡主要呈现为一种围绕着生存的死亡的氛围,“就好像有一种始终处在我的思想视域中的死亡本质一样”,“就好像我的生命有一种死的气味”。[1](P418)[2](P459)[3](P364)在这个意义上的死亡是与出生并重的。因为两者对我来说都不可能是体验的对象(超验性),但又共同作为一个包围着我的先验场而存在(内在性)。在这个场中,“我感到自己在一种我不能想象其开端和结束的无尽头的生命流动中随波逐流”,我感到我的现在存在的“偶然性”,感到自己“被超越的焦虑”。[1](P418)[2](P459)[3](P364)不过,与海德格尔相比,梅洛-庞蒂似乎更重视过去,因为作为肉身性的存在,我们不可能摆脱过去,就像身体不可能不拖着它的影子。所谓时间的厚度、肉身的不透明性等靠的正是过去的沉淀(sediment)。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提到了一种“世界的无限记忆”[1](P84)[2](P103)[3](P70),它是我们的记忆的基础。在他后来的思想中,这种世界的记忆与“世界的肉质”(chair du monde)联系在一起,而过去和现在也同样是一种“肉质”,它们可以相互交错,由此,“一个时间点的建立(Stiftung)就可以无需‘连续性’、无需‘保留’,无需虚构的心理‘支撑’而过渡到其他时间点。”[5](P321)在这里,梅洛-庞蒂没有提到将来,将来似乎缺少这种“肉性”的沉淀。
我们也可以从这种时间场的角度来看待永恒。传统的时间观把永恒看作一种自在的时间形式。它就像一个喷泉,水流升腾而又倾注,但水柱的外形却没有变化。把时间比作河流所依据的理由也就在这里,“不是因为河流在流逝,而是因为河流就是流逝本身”。[1](P482)[2](P527)[3](P421)我们大概也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赫拉克里特所说的永恒:“世界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这种永恒观说到底就是一种排除了置身于时间视点中的观看者的自在时间,因此,永恒的时间也就是没有变化的永恒的现在(注:海德格尔也指出:“传统的永恒性概念的含义是‘持久的现在’。”[6](P424注1));这正是我们上面所批判的纯粹存在于客观世界中或意识内部的时间。但是,梅洛-庞蒂指出,这种普遍性的永恒,“只是时间的一个次要属性,只能导致对时间的不本真的看法,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时间上区分终点和起点,我们甚至不能想象一个周期”。[1](P484)[2](P530)[3](P423)永恒最终必须扎根于以现在为中心的呈现场。因此,“永恒不是时间之外的另一种秩序,而是时间的氛围。”[1](P451)[2](P493)[3](P393)比如说,“如果我专注地、不带任何想法地打量这房屋,那么它似乎就具有永恒性,并且从它之中流逸出某种凝滞。”[1](P83)[2](P101)[3](P69)但我之所以感受到这种永恒,是因为这是我现在(或其他某一时刻)看到的房子,相比于这一短暂的时刻,这房子呈现出一种持恒性或凝滞性,即使它的外观可能会有所改变,即使它明天就会倒塌,它的现在存在依然是恒真的。我们可以说上帝是永恒的,因为上帝没有一个置身于时间中的肉身性视点。但这样的说法毫无意义。之所以我们说上帝永恒,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永恒,是因为我们在我们有限的、沉重的肉身存在中感受到了一种超越的渴望。因此,我们只能通过现在,通过肉身化的时间视点来把握永恒。“每一个现在都像一个楔子那样契入时间,并宣称拥有永恒。”[1](P450-451)[2](P493)[3](P393)所以害怕老去的雷吉娜渴望成功,渴望永恒。而对于永生不死的福斯卡来说,生老病死、成功失败等等,这些变化都失去了意义,因为他经受着永恒,因为在永恒的眼睛看来,任何个别的、短暂的存在都失去了其独特性,因而不再有属于它的意义;因而不死其实是一种“天罚”。(注:蕾吉娜和福斯卡都是波伏瓦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中的人物,参见《人都是要死的》,译林出版社1997年版。)只有从现在的视点来看,永恒才显示出永恒的价值。
三
从上面这种时间场的结构分析出发,梅洛-庞蒂重建了他的肉身主体性。我们还是从现在说起。现在由朦胧的过去和将来的时间晕圈所包围,正如意识被含糊的知觉场所烘托。因此可以说,现在是肉身化的时间。因为在现在中,时间实现了自身,拥有了自身。因此,现在是自知的时间。“在时间的中心有一道目光,或如同海德格尔所说有Augen-blick,有某个人,词语由于他才有一种意义。”[1](P482)[2](P528)[3](P422)“在这里,出现了光线,在这里,我们不再与一种处于自在中的存在打交道,而是与一种其整个本质像光线一样在于使人看见的存在打交道。”[1](P487)[2](P533)[3](P426)这就是意识的产生。意识说到底就是对现在的意识,我可以回忆过去(或想象将来),虽然回忆到(或想象到)的内容是过去(或将来)的,但回忆(或想象)这样一种活动却是当下的,它同时也使过去(或将来)的内容当下化。在现在中,我的意识和我的有意识的存在达到了一致,或者说,两者是同一个东西。由此,在现在中,时间性阐明了主体性,或者说,时间是主体的。但反过来,也应该说,主体是时间的。因为意识之为意识,就在于它是对“时间和世界的一个整体计划或看法”[1](P485)[2](P531)[3](P424),这个计划需要在流逝的“多”之中展现出来,正如主体在它的每一个动作中体现出来一样。因此,没有一种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的、固定不变的先验主体性,“主体性不是与自我的固定的同一性,和时间一样,对主体性来说,要成为主体,重要的是向一个他人(Autre)开放和摆脱自己。”[1](P487)[2](P534-35)[3](P426)主体只能在时间性中绽出自身,投射自身。时间性不仅使主体性成为可能,也使主体的认识、自由及主体间的交往成为可能。
梅洛-庞蒂认为,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是通过时间的过渡综合与空间的过渡综合一块来展开的。(注:在这两种综合中,梅洛-庞蒂认为,时间综合是一种更为基本的过程。“空间综合和物体的综合是以这种时间的展开为基础的。”[1](P277)[2](P306)[3](P239)因此,他有时甚至直接把知觉综合看作是一种时间综合,相应地,在知觉层次上的主体性也就是一种时间性。[1](P276)[2](P305)[3](P239)。)虽然我在任一时刻都只能看到物体的某一方面,但我依然能完整地把握一个物体,能把不同时刻看到的物体形象认作同一个物体。这是因为,在每一时刻,我所看到的物体形象都处于同一个知觉场中,它已经综合了所有其他时刻的物体形象。“时间的每一刻时刻都充任所有其他时刻的见证,……每一个现在最终都融合了要求所有其他时间点承认的一个时间点。因此,物体是从所有的时间被看到的,正如它是从所有的角度被看到的一样。”[1](P83)[2](P101)[3](P69)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永恒也是可以把握的。比如说,当我处于热恋中时,我可以说:“我永远爱你!”因为在那一刻,我感到永恒之门在向自己敞开,我感到自己确实把握了爱之真谛,这种爱能使我能超脱时间,超脱身体,即使我事实上无法超脱这些。[7](P35-36)我们通过瞬间把握住了永恒,正如通过某一角度理解了一幅画一样。
但是,另一方面,梅洛-庞蒂也指出,由于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通过现在的视点看世界的,因此,我对物体的把握始终是不完全的,物体始终具有超越于我,超越于时间的自在性。为了更完整地把握物体,我们总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对他人,对自己的理解也是这样。现在我能对我的童年作出大致确定的评价,勾勒出它的发展线索。但我却不能这样界定我的现在。因为我还置身于其中,我正体验着现在;为了理解它,我还需要往“后”挪一点,我需要一个观看它的时间位置。“实际的体验从来不是完全可理解的,我理解的东西从来不能与我的生活严格地相合。”[1](P399)[2](P437)[3](P347)这也就是说,“我对我的时间的拥有始终是滞后的”,我不能完全与自己保持同一,我不能终极地理解自己,因为那样一个时刻始终处于尚未到来的将来视域。[1](P398)[2](P436)[3](P346)正如《俄狄浦斯王》的结尾所说的:一个人在其没有跨过人生的界限之前,在没有摆脱最后的苦难之前,不能说他是幸福的。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盖棺论定”的意思。不过这样一种说法已经借用了他人的视角,已经从时间的视角转移到了空间的视角。说到底,现在视点的优先性和有限性最终表明的是作为一个来源不明的肉身主体的命运,我之所以最终能超越它而直接把握事物或理解他人,只是因为事物和他人与我一道呈现在同一个被感知的时间场中。
自由的实现也离不开时间场。就生存论而言,由于我们是肉身性地存在于某一处境中的,我们不可能像萨特那样“假装我是虚无并基于虚无而不断地选择自我”[1](P516)[2](P565)[3](P452),因此没有绝对的自由,而只有一种通过接受处境并在处境中作出决断的有条件的自由。就时间上而言,要使自由成为可能,它要求我们的决断既能针对某种先前的情景,又能进入将来,产生它的影响;它要求后面的瞬间能得益于前面的瞬间,因此,每一个瞬间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应该是敞开的,既能越出前面的瞬间,又能接纳后来的瞬间。因此,梅洛-庞蒂的自由观不同于萨特的自由观,进而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的自由观。海德格尔要求通过对死亡的先行领会而回到个人的本真存在中去,从而作出自己的选择,担当自己的责任。这是一种基于将来,也因此与萨特一样是基于虚无之上的决断的自由。但梅洛-庞蒂认为,由于“我们始终以现在为中心,我们的决断来自现在,因此它们总是要与我们的过去有联系,它们从来就不是无原因的;即使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打开一个可能是全新的周期,它们也应该在以后被重新作出,它们只有在一段时间里才能使我们摆脱离散性。”[1](P489)[2](P535)[3](P427)因此,他不同意海德格尔那种一劳永逸式的“向死而在”的说法。即使我们能暂时摆脱现在和过去,从将来的视点看自己,但因为我们始终“在世界中存在”,始终拖着来自过去的沉重的肉身,所以,我们将不断地被拖回到现实中,我们必须不断地作出新的决断。而所谓的“向死而在”,将是一场在过去与将来之间展开的无休无止的斗争。因此,自由总是有条件的有限的自由。与我们的知觉场和时间场一样,自由也有一个“自由场”。[1](P518)[2](P568)[3](P454)
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也是通过一个活生生的现在展开的。梅洛-庞蒂认为,由于他人和我们一样,是在同一个知觉世界的呈现场中涌现的,由于我的现在既能向我不可能再经历的过去开放,也能向我尚未经历、也许永远不可能经历的某个将来开放,所以它也可能向我的活生生的体验之外的时间性开放。所以我的时间性和他人的时间性有可能在同一种现在中相遇,由此获得一个社会性的视域。[1](P495)[2](P541-542)[3](P433)梅洛-庞蒂的时间观为我们重新看待主体间性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收稿日期:2003-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