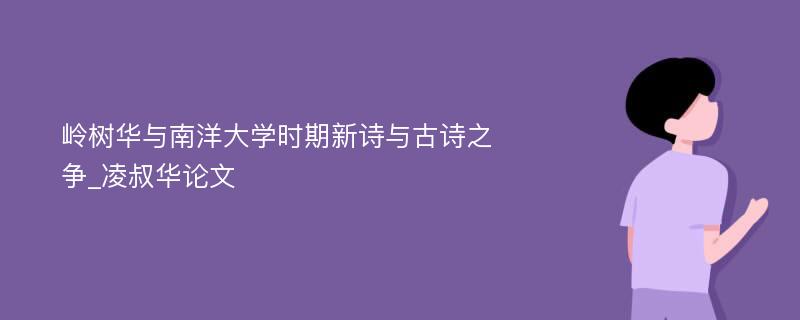
南洋大学时期的凌叔华与新旧体诗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洋论文,旧体诗论文,之争论文,时期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有四五年我远走南洋教书去,那些地方,那些中土青年,到底是中国人,生活思想一切都唤起我过去的一切。”①
凌叔华(1900-1990)于1977年7月致巴金的信中,回忆了她二十年前在南洋大学的教书经历。
凌叔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女作家。从1920年代开始,受到周作人的鼓励而发表创作,在文坛崭露头角,被誉为“中国的曼殊菲儿”(Katherine Mansfield),与冰心、林徽因等女作家齐名。
凌叔华与夫婿陈源(1896-1970,笔名西滢)于1926年7月结婚。1942年陈源奉国民政府派令,于伦敦主持“中英文化协会”。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巴黎成立,陈源被任命为首任常驻代表,后因巴黎生活费昂贵,多寓居伦敦,仅开会期间赴会。1947年,凌叔华和女儿陈小滢离开中国,前往伦敦。②离开中国以后,凌叔华较少以中文写作和发表新著,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绘画方面。
1956年,凌叔华应邀从英国到刚成立的新加坡南洋大学执教,授课之余,她鼓励和推动学生组成“南洋大学创作社”,从事写作及文艺评论③。在南洋大学期间,她大多写作散文,完成了散文专书《爱山庐梦影》。
《爱山庐梦影》是凌叔华唯一的散文集,值得深入研究,笔者将另文详加阐析。关于凌叔华在南洋大学时的情况,资讯不多,学术界讨论得也很少。笔者在蒐罗材料时,找到凌叔华友人苏雪林(1897-1999)的晚年回忆,提及了凌叔华的南洋大学生涯:
南大〔按:指新加坡南洋大学〕来台湾找人,应聘者有台北师范大学潘重规等,我名亦在其列。我怕南洋气候不适合,不敢去,荐原在英伦侨居的凌叔华自代。凌到南大后即教我的功课,但凌与那边中文系主任刘太希摩擦得相当厉害,仅教一年即未被续聘。④
受到苏雪林此番话的影响,便有论者以为凌叔华只在南洋大学(以下简称“南大”)教了一年或一年半的书⑤。而曾经受教于凌叔华的南大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则为老师抱屈,认为苏雪林厚诬凌叔华,凌叔华不但在南大教了四年,直到第一届学生毕业,况且,刘太希(1899-1989)从未担任南大中文系系主任一职,更不可能发生与凌叔华相龃龉之事,故而指责苏雪林之不当。⑥
凌叔华与刘太希是否果真有所恩怨矛盾,不是笔者本文关心的重点。苏雪林的记忆容或有误,但不失为一丝线索,帮助我们梳理凌叔华在南大期间的事迹。而顺着这一丝线索,笔者发现苏雪林之言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凌叔华与刘太希的意见不合,个人因素姑且不谈,其有迹可循者,乃延续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对于古典旧诗和白话新诗孰优孰劣的争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新马华文文学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件小事。
二、凌叔华与南洋大学中文系
在南大的四年,是凌叔华一生中最为正式,为期最长的大学教职⑦,在此之前,她的身份主要是作家和画家。
早在1944年,凌叔华在四川乐山苦于贫病,曾经委托在美国的胡适(1891-1962)代为觅职,信中表达了期待去美国的大学任教的渴望。⑧她说自己无论新旧文学、中国艺术都可以教,教国语也愿意,因为在英国的陈源收入甚微,她不能就食。在凌叔华致胡适信函中所附的个人工作履历,她的教书经验只限于1927年在燕京大学教过一年中国艺术史和中国绘画。
去美国教书的希望落空,凌叔华到伦敦后依然面临经济窘困的情况。她于1987年接受郑丽园女士的访谈时说道:“由于国民政府退居台湾,薪资无法随着国外生活水准调整,反而削减许多,我整天枯坐愁城,也不是办法,于是逼得想得开,也开画展,也教起书来。”⑨
鬻画贴补家用并非她当时所愿,她在给英国女作家Virginia Woolf的丈夫Leonard Woolf的书信中,抱怨欧洲人不懂得欣赏她的画作,只愿意接受合乎西方审美标准的艺术。⑩
二次大战结束,第一所华人自办的中文授课大学——“南洋大学”创立,不久后发生首任校长林语堂(1895-1976)与校董事会意见不合,集体总辞的事件。(11)新校长人选未定时,由文、理、商三个学院与教务长共同组成“校务委员会”,1955年12月30日,南大公布首批聘请之院长及教授名单,其中并没有凌叔华,中文系唯一的女教授是苏雪林。(12)
苏雪林与凌叔华早在1930年代与袁昌英(1894-1973)并称为武汉大学的“珞珈三女杰”,交情甚笃。苏雪林举凌叔华以自代,后来的南大执行长潘受(1911-1999)的访谈中,也谈及苏雪林推荐凌叔华之事。
去南大教书,凌叔华后来说:“现回想起来,当时到南洋换换空气也是对的。”(13)
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本科生正式开学上课,凌叔华于该年五月抵达新加坡,现存的凌叔华照片中,有凌叔华与丈夫陈源1956年在新加坡的合影,可知当时夫妻同行。(14)
凌叔华在南大中文系开设“新文学研究”、“新文学导读”、“中国语法研究”和“修辞学”等课程。(15)凌叔华在南大任教的期限,根据南大的校史,是从1956年到1959年。1960年4月,南大举行第一届学生的毕业典礼,凌叔华于那年春季返回英国。1956至1957年度南大中文系系主任为佘雪曼(1909-1993),1958至1960年度为涂公遂(1906-1992)。(16)
苏雪林的日记透露,凌叔华在南大期间曾经与她通信。在教完第一学期课程,即1957年的一月底,凌叔华前往台湾,并在2月4日及5日与苏雪林一同参访台中白沟古物保存所,观赏原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并游日月潭。(17)
此外,趁着在亚洲之便,凌叔华曾经去香港度假,重游她童年及新婚时期居住过的日本,也到过北京和广州等地观光探亲,并且返往于伦敦和新加坡。至于她在南洋的活动,此文不涉及。
1957年下半年,刘太希应聘于南大,有别于先前到任的潘重规(1908-2003)等诸位先生,他的职位是副教授,担任“历代诗选”、“诗经”等课程。
仔细观察那时南大中文系的教师背景,可以看出相互的连带关系,而凌叔华则被孤立于外。
佘雪曼与潘重规同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涂公遂和刘太希同毕业于燕京大学,凌叔华也是燕大毕业生,不过是外文系。凌叔华处于传统中文系的毕业生之间,更具体地说,是章太炎(1869-1936)、黄侃(1886-1935)的后学门生之间。
这些“章黄弟子”以南大为传承师学的基地是很自然的事。佘雪曼编选的《南洋大学基本国文》是文学院各系中文必修课的教材,开宗明义第一篇“当代”部分就选了章太炎《论散文骈文各有体要》一文(18)。“章黄弟子”彼此的姻亲关系,在海外更显紧密。潘重规为黄侃的女婿,其夫人黄念容后来在1957年也成为南大中文系的讲师。(19)刘太希是潘重规的舅舅,潘重规逝世时,其治丧委员会撰拟潘重规的生平事迹,说他当年远赴南洋教书是本于一片孝心,为便于接出困于大陆的母亲,即刘太希的姐姐,后来果然如愿,家人团圆。(20)
凌叔华置身系友、同门以及亲眷的关系网络以外,已经格格不入,何况她本来热衷艺文,不属于学术圈。位居教授之职,凌叔华在南大的学术工作罕闻。从当时南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出版品看来,凌叔华参与的仍是艺文形态的活动。1958年端午节,南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以手写印刷的形式出版《中国艺文》创刊号“纪念屈原特辑”,凌叔华写了《发刊词》,推崇屈原的崇高人格和真挚动人的作品。(21)《中国艺文》后来好像没有延续出版。1959年9月起,南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出版了排印的《大学青年》刊物,一直维持到1962年12月,共出版11期。《大学青年》第一期上,有一幅凌叔华的墨竹画,算是她对该刊物的支持吧。(22)
南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还在1959年12月出版了第一期《中国语文学报》年刊,作者几乎都是中文系的老师,凌叔华没有文章刊载,而有涂公遂《诗与政教》、潘重规《亭林诗钩沈》、黄念容《文选黄氏学》等论文,显然采取的是义理、考释、训诂等国学研究的途径,尤其是黄念容的文章,直接发扬了父亲黄侃对于文选学的贡献。
南大的毕业生后来回忆与师长们的相处,都对当年云南园求学的日子充满了怀念与感激。中文系第一届生朱炎辉和刘太希、涂公遂的交往较多,他敬佩刘太希“为人处世,都从真入手”,毕业多年之后,还曾经去台北探望两位老师,并获赠老师的墨宝。(23)中文系第四届学生陈凌提及中文研究会康乐股发起清晨太极拳活动,向潘重规、黄念容夫妇学习杨家太极拳108式。(24)
而经历过五四运动,享誉中国的著名作家凌叔华莅临南大讲堂,其轰动可想而知。笔名“骆明”的作家叶昆灿(1935- )也是南大中文系第一届的学生,他记得选读凌叔华“新文学”课的同学非常多,不过“凌教授课并不教得怎样生动”,“她的音量太小,语调又不高,再加上是大班上课,因此就当时说,有些人实在难免会有点儿失望,因为对五四的期望太高了。”(25)即使如此,骆明还是极为肯定凌叔华的教学:“但是她有许多亲身的经历。同时,凌教授为人诚恳、朴实、坦白,一副光风霁月,名家风范,实在令人敬服。”(26)
另一位中文系第一届学生余秀斌(1930- )和凌叔华的互动最为频繁。余秀斌能诗善画,多次著文感念凌叔华为推动新华文学所付出的力量,她表示自己对于书画艺术和古筝的喜好受到凌叔华的感染,在凌叔华离开新加坡后始终保持联系,去英国探望过凌叔华,最后还赴北京参加凌叔华的葬礼。(27)
三、凌叔华与南洋大学创作社
凌叔华推动新马华文文学主要在于她支持学生组成“创作社”。“创作社”之名,很容易令人联想起1921年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成立的现代文学社团“创造社”。骆明后来谈过“创作社”有别于“创造社”(28),但愚意以为主张写作表现自我的理念应该还是相通的。
有别于前述的南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创作社的成员不限于中文系学生,主要的骨干有骆明、尹镜培(笔名汀上红、萧子云,1934- )、梅炎添(笔名东春梅,史地系学生,1934- )、黄建邦(笔名汀上白,1933- )、谢添顺(笔名而已,1932- )、章邦枢(笔名符剑,1934-1977)等人。也与学生团体的刊物不同的是,创作社对外公开征稿及发行,许多在创作社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者,当时已经是作家或是学者,例如1958年6月出版的第一本书《夏天的街》,书名取自书中作家威北华的同名散文,此外还有柳北岸(1904-1995)、韦晕(1913-1996)、龙榆生(1902-1966)等人的文章,以大学生的活动能力和社交经验,能够邀集到这些有分量的作品,猜想创作社的顾问凌叔华或多或少也发挥了一些影响力。
《夏天的街》包罗了白话诗、散文、小说等文学创作,以及文艺评论赏析、翻译作品等内容,面世之后反响十分热烈,褒贬之声交相而出。新加坡文化要人连士升在1958年7月16日的《海滨寄简》中赞赏《夏天的街》里的文章(29),对创作社主编如此内容丰富的刊物,予以鼓舞及支持。然而,编辑者删改了锺祺(1927-1970)的一首诗《给一个孩子》,论者以孔子删诗之事为之维护,言下之意,编辑也有权删改作者的作品,重新引发史上孔子删诗之说的争论。再者,《夏天的街》第一篇,即史忱的《马华文艺的道路》一文,也造成当年文艺界最受关注的激辩。康白扬在《星洲日报》文艺版发表了《理论与实际》,批评《马华文艺的道路》,指出该文看不出“道路”在哪里?史忱的反击兴起了正反双方众人的笔战,称为“史康论争”,为期一个多月。
由《马华文艺的道路》笔战掀动牵涉的问题,包括马来亚社会的发展、文艺理论、哲学术语的定义、批评的态度等等,归结于如何评价《夏天的街》这本书。《夏天的街》被誉为1945年以来当地最有分量的文艺刊物,但也有人颇不以为然。文学史家方修,当年是《星洲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对于《夏天的街》还是相当肯定,并且乐观其成的。(30)
笔者目前没有资料显示凌叔华是否卷入《夏天的街》相关的风波之中,困扰她更大的,是校内的人事问题。她那时欧游回新加坡,7月23日写信给尹镜培,提到“这一次回来因为课忙及校中的人事问题,我未看全文,不愿参加意见。”并且特别提醒社员们应该赶快向连士升表达谢意。然后说:
你们不知是否还有从前那些社员?我希望社员无论减少到如何少,对外的礼貌以及应有的行动均要做到方好。(“星洲”的批评如需声明启事道歉,也要做到。)(31)
言下之意,部分创作社的社员似乎在第一本刊物出版之后就有所动摇而离去。
凌叔华明白表达她对人事问题的心情:“南大日来表面上似乎寂静许多,但人数少,是是非非更多;我很不耐烦把日子如此过掉!”又说到:“我再一的想过,为了免除我以及你们以后被人指点的烦恼,以前曾想把书公开作为你们社的书,还是不公开的好。……你们几个人将来要看或要借都可以,别人我暂不借。”语重心长,耐人寻味。
1957年11月21日至25日,凌叔华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个人画展,连士升、潘受,以及南大中文系的学生刘森发(笔名刘贞)都在报端盛加赞誉。传说凌叔华画展筹得的款项将资助创作社出版,不过后来并没有实现,本来《夏天的街》预定于1958年3月南大主体建筑(即今日之“华裔馆”)开幕落成时作为庆贺的献礼,出版经费的问题最后还是由六位骨干社员各自出资五百元,加上刊登工商广告而解决。
创作社前后一共出版了四本书,分别是《夏天的街》(1958年6月)、《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1959年10月)、《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1960年10月),以及《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1962年4月)。其中《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还曾经再版,销售了三千本,在当时可谓盛况空前。凌叔华于1960年春天离开新加坡,因此她作为顾问的创作社刊物只有前两部。随着基本成员毕业,后者难继,况且经费拮据,创作社后来解散,但是在新马华文文学的历史上,创作社的刊物仍是值得重视的研究素材。
1948年间,为定位“马华文艺”是否具有主体性,抑或是中国文艺的支流,所谓“侨民文艺”,文坛上曾经激烈讨论。南大创作社的刊物延续了这个议题,回顾过往,寻思现况,展望未来的前景,都是极富意义的。
1960年,南大中国文学研究会更名为“中国语文学会”,设立“马华文学资料室”,8月间举办了“马华文艺座谈会”,讨论有关“马华文艺的发展路向”问题。南大中国文学研究会虽然和创作社是不同的组织,同样关心马华文艺且付诸行动,后来举办的资料展和征文比赛,出版《大学青年》杂志,也对扩展马华文艺的史料、理论和创作颇具贡献。
四、诗 时代 未来
相对于南洋大学创作社提倡白话文学和强调马华文艺异于“侨民文艺”的独特性,刘太希和涂公遂、潘重规带领学生们写作古体诗,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
由前述凌叔华给尹镜培的信看来,人事的困扰非一日之寒,如果要追究,可能自1958年上半年涂公遂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便更加恶化。笔者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矛盾,若基于利益或意气之争,其实乏善可陈;前辈学者作家的纠葛,亦非后生可置一词。因此,本文无意深掘凌叔华与南大中文系教师的怨隙,只想从文学史的角度,剖析其文学理念之差异,并将之置于五四以来诗歌创作与阅读的脉络中观察。
凌叔华支持的南大创作社刊物,以及南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出版的《中国艺文》创刊号“纪念屈原特辑”,登载的诗歌作品都是白话新诗。(32)她在《南洋商报》商馀版连载的《新诗的未来》一文,后来于1960年以小册子的形式,由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出版,并收入《爱山庐梦影》中。
《新诗的未来》的写作背景是:“近来因为新诗销路的不景气,有些有心人未免疑虑起来。”这些“有心人”或者对于新诗不求甚解;或者“重古而贱今”,重申“新诗没有押韵,没有平仄,也没有音节,诗只是分行写的散文”,如此的论调,始于章太炎。
凌叔华直接点明刘太希、潘重规等人的太老师章太炎批评新诗的不当:“章太炎约在三十四五年前讲演国学时说新诗(白话自由诗)不能算是诗,因为它没有韵律。这似是而非的道理倒也继续传布了许多年。”(33)
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国学,曹聚仁将笔记刊载于上海民国日报,后来汇集成《国学概论》一书。章太炎认为中国诗至元、明、清三代甚衰,一无足取。“诗至清末,穷极矣,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34)所谓“向下堕落”,便是沦为白话新诗。
章太炎反对因提倡白话而去除文言,并且指出没有好的小学根基便无以写出好的白话文:“余谓须有颜氏祖孙之学〔按:指颜延之、颜师古〕。方可信笔作白话文!余自揣小学之功,尚未及颜氏祖孙,故不敢贸然为之。”(35)
不受韵律约束的白话新诗在章太炎眼中不算是诗,他说:“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36)曹聚仁曾经以此向章太炎请教,倘使“诗”的归类准则是以押韵与否为界,那么有韵的“百家姓”,四字一句,逢偶押韵,算不算诗呢?章太炎的回复是:“以狭义言,诗之名,则限于古今体诗,旁及赋与词曲而止耳。以广义言,凡有韵者皆诗之流。箴诔哀词,悉入诗类。”(37)
身为“新月社”成员之一陈西滢的妻子,与徐志摩、胡适等人皆有深交,凌叔华拥护新诗的立场始终如一。即使她个人并不创作新诗,她曾经在1924年回答泰戈尔的提问时说:“旧的没味,新的常不觉要模仿欧式,也很无聊,不如不作爽快。”(38)
在《新诗的未来》中,凌叔华表示不否认旧诗有伟大之处,但是她抗议过分贬抑新诗,“活活的要淹死它”。何况“我们攻击新诗的话,只是老调重弹,简直没有多少道理。”(39)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成功,当初反对白话新诗的声音逐渐沉寂,写作旧体诗依然大有人在(40),甚而当初主张新诗的青年,到了1950年代也“爱上旧诗的典雅易写,公开的发表他们五七言绝句与律诗。”(41)凌叔华一方面责怪写新诗的人不够努力,同时也认为守着旧诗是“依赖成性”。
她针对排斥新诗者的质疑,参照西方学者研究语言学、音韵学和自由诗(Verse Libre,凌叔华认为和中国新诗相似)的成果,从声调和音节等方面陈述欣赏新诗的标准。例如她采用埃之钝·施密士〔按:即Egerton Smith〕于The Principles of English Meter[Metre]所说的“自由诗虽不必有诗的形式,但它得有一基本音节(Base Meter)”,再三举中国古典诗和新诗为例,指出其音节构造相同之处,也就是以三拍子和四拍子为吐音的尺寸(Foot of Meter),证明新诗也有旧诗优美悦耳的节奏。凌叔华说:“有了自由自在的心境,方能产生达意抒情的诗篇,如一定要他用二三千年前的文字来写他的新创作,那无异把他下了监牢,却叫他歌颂牢狱一样的矛盾。”(42)
凌叔华的风格一向温柔婉约,很少出现像《新诗的未来》一样具有“火力”的文字,她对新诗的思考和研究,与她在南大教授新文学和修辞学等科目不无干系。其实平心而论,凌叔华的观点早在曹聚仁和章太炎商榷新诗的书信里便已经谈过,曹聚仁认为:“语体诗之为诗,依乎自然之音节,其为韵也,纯任自然,不拘拘于韵之地位。”(43)凌叔华是归纳整理旧诗与新诗,将曹聚仁所说的“自然”的具体内涵呈显出来。
《新诗的未来》,可谓是凌叔华“爱之深,责之切”之作。南大中文系的教师圈,以“章黄弟子”为核心,他们秉承师学,对于白话诗的态度,以刘太希为例,可以说是“选择性的接受”。
在谈到诗歌吟诵,刘太希认为:
有人说:白话新诗不能朗吟,我以为读白话诗文,与读文言诗文的道理原无二致。不过白话是将文字口语化,文言是将文字音乐化而已。(44)
在《诗与时代》一文中,刘太希强调:诗乃是人类的心声、是艺术的,但是必须经过升华、藻饰,以及导正,必须雅而不俗,文而不鄙,才能陶冶性情,美化生活,中和情感。他说:“近年一般标榜新文艺的先生们,既以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少英雄自居,我们提出孔子之说来论诗,当然是不对胃口的。”并且批评:
只知将现代洋化的名词,硬搬到诗句之中去,实只是负鼓盲翁的弹词莲花落一类的作品——硬捧为代表现代的诗,即只有引致人类心灵,走向低趣味的情趣,将本来优美的语文,驱入日以粗犷鄙俚的方向去。这实不免于漠视了诗的使命与其艺术性。这一漠视,实不自现在始,而是沉溺了三四十年的结果。(45)
因此,刘太希以实际的行动“拨乱反正”,和学生们作旧体诗词唱和。1960年3月,南大举办“大学周”活动,4月2日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佘雪曼、刘太希、涂公遂、史次耘等师长,和学生联吟诵咏,庆贺毕业,诗作集结为《云南园吟唱集》(46)。同年8月,南大中文系学生唱和填词,作《南风词集》,刘太希为之作序,阐扬“南风”之“风”义:“夫风,冷〔按:当为“泠”〕然善也。冷〔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是风也,南洋之风也,君子之风也,风之时义大矣哉。”(47)
《南风词集》出版时,凌叔华已经离开新加坡。我们从南大中文系第一届同学毕业通讯录里的师长赠言看出,系主任涂公遂题词、潘重规作诗、刘太希写的是白话文,循循善诱为人处世之道,而凌叔华则毫无只言,好像淡出了中文系。
五、结语
研治新马华文文学的学者,大都强调鲁迅对南洋地区白话文学的重要性(48),并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对南洋的冲击不如中国(49),毕竟当时是为侨乡。二次大战期间,影响当地的是前往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的郁达夫(1896-1945),而郁达夫新旧体文学皆写,其旧体诗颇受侨民重视。⑩研究者如李庆年博士也曾经指出,古典旧诗和白话新诗的争论在南洋不如在中国强烈。(51)
新马华文文学写作的形式问题,是新体还是旧体,其实明显不如前述定位自身属性,是“马华文艺”,还是“侨民文艺”;是走社会写实主义的路线,抑或个人情性的抒发等等议题来得迫切与关键。在这样的地域背景和时代前提之下,刘太希等人的古诗正统观,以及凌叔华将中国诗歌的未来冀望于白话,这些三四十年前的旧案,在中国已经不是话题,即使把战场转向南洋,也无济于事,只透露了领军的健将们步入老年,急于传嗣新旧体诗“命脉香火”的焦虑。
至于直接受到老师影响的南大学生,又是如何取舍新旧体诗的创作呢?
如同新旧体诗之争在南洋未能造成话题一样,不乏兼擅古典与白话诗歌的作者,南大创作社的成员也参加云南园吟唱雅集,例如南大中文系第三届学生,后来曾经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的黄孟文(1937- ),接手过南大创作社的编务,在《云南园吟唱集》中作有七言律诗和词一阕。又如黄应良,凌叔华曾经在1959年11月,为黄应良的新诗集《时间的河流》作序文,收于凌叔华的《爱山庐梦影》。《时间的河流》多为四五句的小诗,颇有民国初期新诗的痕迹(52)。黄应良欣赏闻一多,写过析论闻一多的文章(53),观点和凌叔华《新诗的未来》相通。他担任《云南园吟唱集》的筹备委员,《云南园吟唱集》收有他的词七阙,水墨兰石图一幅。
其实,凌叔华也写过旧体诗,存世的凌叔华手稿有《湖区杂记》诗数首,其第二首为:“重重叠翠映湖光,幽径闲行草木香。且作江南山水看,梦回依旧是他乡。”(54)诗意淡雅平浅,流畅自然。
再者,凌叔华和当时南大中文系几位老师们都善于书画,前述1957年11月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个人画展之外,凌叔华并于1959年8月15日在马来亚槟城展画。而涂公遂和刘太希也于1960年3月在槟城举行书画联展。(55)
1960年,凌叔华、潘重规夫妇离开新加坡,涂公遂和刘太希也于1962年离开。涂公遂留别刘太希的诗句中,流露了世衰道微,失意于异乡的无奈情绪:
道息文丧路百歧,余生何地了歌啼。早知自业蚕成茧,久敛禅心絮著泥。玉石忍看俱坏灭,鸱鹓且许任诃诋。九夷风雨同幽晦,仰屋徒嗟盗变齐。(56)
随着南大中文系第一届的老师们陆续离开,私人恩怨与诗学主张都逐渐消解于南洋。更激烈的战火,攸关南大存废命运的争执,在1960年代狂热爆发。1980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并,对于许多南大学生和校友而言,“合并”两校意味着“关闭”南大。南大从此走入了历史,有关南大中文系最初的记忆,凌叔华、刘太希等人,以及中国诗歌未来的思索和坚持,都和南大的历史一起,藏存于新加坡的一隅。
注释:
①凌叔华著,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下册,928页。
②秦贤次编《凌叔华年表》,见凌叔华著《凌叔华小说集》(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6),484页。陈学勇《凌叔华年表》,《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1期,128-143页。
③余秀斌《凌叔华与南洋大学创作社诸成员》,魏维贤、张玉安主编《“面向21世纪的东南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365-391页。
④苏雪林《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91),212页。后来苏雪林于1964年9月至1966年2月在南大教书。
⑤石楠《另类才女苏雪林》(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325页。张昌华《珞珈三杰》,大公网,2007年3月14日(www.takungpao.com:82/)。
⑥朱炎辉《苏雪林厚诬凌叔华》,《南大第一届(1959)中文系纪念文集》(新加坡,非卖品,1999),254-259页。
⑦凌叔华于1927年在燕京大学教过一年中国艺术史和中国绘画,1956-1960年任教南洋大学,1967-1968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讲授中国近代文学。其后于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等校有中国近代文学和书画艺术的专题讲座。
⑧同注1,下册,922-925页。此信朱洪订为1943年,见《凌叔华致胡适19通信时间考》,《学术界》2001年1月。按信中提及梁启超之弟子吴其昌(1904-1944)该年在乐山病逝,故当从陈学勇之说。
⑨同注1,下册,970页。
⑩Sasha Su-Ling Welland,A Thousand Miles of Dreams:The Journeys of Two Chinese Sisters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Distributed by National Book Network,c2006),p309.
(11)林语堂于1953年12月至1955年4月任南洋大学校长。
(12)南洋大学,《南洋大学创校史》(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189页。
(13)同注1,下册,970页。
(14)傅光明翻译为《古韵》,依据《古韵》而编著的《凌叔华的文与画》,129页。
傅光明《凌叔华:古韵精魂》(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81页。
(15)具体授课情形为:1956年下学期“新文学研究”(必修课),1957年上学期“新文学导读”(选修),“中国语法研究”(必修)。1957年下学期“修辞学”(必修)。
(16)《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1956-1966》(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49-58页。《南洋大学史料汇编》(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出版,1990),174页。
(17)“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编《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台南:“国立”成功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99),第2册,192-195页。
(18)佘雪曼编撰《南洋大学基本国文》(新加坡:友联出版社,1957年增订再版),1-4页。
(19)中文系第二届毕业班(甲组)特刊出版委员会编《中文系毕业班特刊》(新加坡:南洋大学,1960年)中,有凌叔华与第一届毕业生的合影,在分别和甲、乙两组的毕业生拍摄的团体照里,黄念容取代了凌叔华的位子,成为中文系唯一的女教师。照片又见于《南大第一届(1959)中文系纪念文集》。
(20)潘受有《赠潘石禅教授诗》,其中提到:“板舆一路春先后,佇共高堂拜母仪。”见《潘受诗集》(新加坡: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2004),185页。
(21)《中国艺文》创刊号“纪念屈原特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著录的出版时间为“196-”,笔者根据该刊作于6月20日的“编后语”判断,应该为1958年。又,南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在1957年出版《艺文》,内容以古典文学为主。
(22)附带一提,该期有黄念容的专文《文心雕龙五讲》。
(23)同注6,《难忘刘、涂两位老师的教诲》,229-233页。
(24)陈凌《云南园的生活痕迹》,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史论集》(八打灵再也: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4),14-15页。
(25)同注6,骆明《三十年怀想——悼凌叔华老师》,249-254页。原载1990年6月21日《联合早报》文艺城版。
(26)南大中文系第一届学生梁丁尧也有同样的看法,见梁丁尧:《从南大精神谈到中文系》,陈嘉庚国际学会学术小组编《南大精神》(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陈嘉庚国际学会,2003),110-112页。原发表于2003年8月7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27)余秀斌,《凌叔华教授与新华文艺》、《敬悼凌叔华教授》、《怀念凌叔华教授》,见《心湖的涟漪——余秀斌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人文出版社,2000),1-51页。
(28)同注6,《三十年怀想——悼凌叔华老师》,249-254页。
(29)连士升,《海滨寄简二集》(新加坡:南洋印刷社有限公司,1960),1-4页。
(30)以上有关《夏天的街》引发的论战问题详参方修《一九五八年的马华文艺界》,《新马文学史论集》(香港:三联书店;新加坡: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1986),103-108页。
(31)同注6,《凌叔华教授给同学的信》,26-30页。
(32)“纪念屈原特辑”刊登的是桐叶的《汨罗江上的涟漪》。
(33)凌叔华《爱山庐梦影》(新加坡:世界书局,1960年),88页。
(34)章太炎主讲,曹聚仁编述《国学概论》(香港:创垦出版社,1953),104页。
(35)《白话与文言之关系》,《国学概论》,121页。
(36)同注34,176页。
(37)同注34,188-192页。
(38)同注1,《我的理想与现实的泰戈尔先生》,602页,原作于1924年5月6日,原载同年5月12日《晨报副刊》。
(39)同注(33),89页。
(40)详参于友发、吴三元《新文学旧体诗漫评》(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朱文华《风骚余韵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41)同注33,88页。
(42)同注33,103页。
(43)同注34,《国学概论》,189页。
(44)刘太希:《古典诗文吟诵》,《千梦堂集》(新加坡;联邦教育用品社,1961),223页。
(45)同注44,《诗与时代》,136页。
(46)《云南园吟唱集》(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1960)。
(47)同注44,《南风词集序》,228页。
(48)王润华《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51-76页。
(49)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朱崇科《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
(50)陆丹林编《郁达夫诗词钞》(上海:上海书局,1962)。秦贤次编《郁达夫南洋随笔》(台北:洪范书店,1978)。
(51)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马华旧体诗(1912-1926)》,262-377页。方修也指出:新旧体诗之争在新马华文文学史上经常零星出现,但都成不了论战的气候,往往无疾而终,见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新加坡:世界书局,1976)。
(52)黄应良《时间的河流》(新加坡:世界书局,1959)。
(53)黄应良《闻一多的新诗论》,以多等编《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新加坡:南洋大学创作社,1960),21-33页。
(54)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计蕾编选《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凌叔华》(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书前手迹照片。
(55)颜泉发《分流与整合:“马来西亚华人中国绘画”概念的梳理和思考(1919-1965)》(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博士论文,2005),112页。参考姚梦桐《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会,1992)。锺瑜《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1900-1965)》(吉隆坡:正山国际设计艺术集团,1999)。
(56)《次韵太希留别》其一,涂公遂《浮海集》(香港:珠海书院文史学会,1981),6页。
标签:凌叔华论文; 南洋大学论文; 文学论文; 新加坡华人论文; 章太炎论文; 文艺论文; 中文系论文; 星洲日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