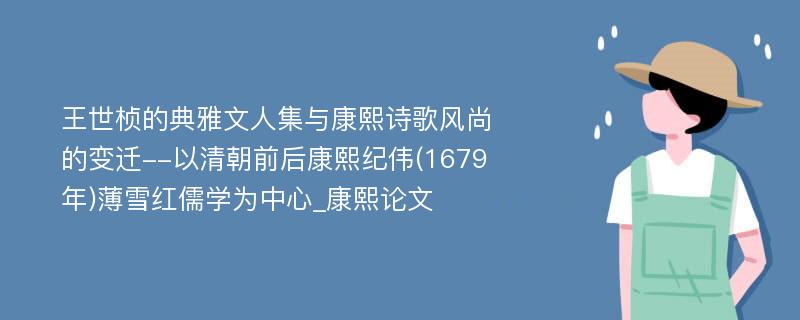
王士禛的文人雅集与康熙诗坛风尚的变迁——以清康熙己未(1679年)博学鸿儒科前后为重点考察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鸿儒论文,诗坛论文,博学论文,文人论文,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4)03-0085-04 一、博学鸿儒科前后以王士禛为中心的交游雅集 清康熙己未(1679年)博学鸿儒科前后,是清代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全面转型期,而诗坛则处于群龙无首、急需整合期。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京师诗坛基本情况是:职志京师诗坛多年的龚鼎孳已离世,清顺治年间影响较大的宋琬、曹尔堪等诗人或去世,或离京,施闰章、朱彝尊、潘耒、陈维崧等诗人或散布江南,或游幕一方;京师有影响力的诗人仅剩王士禛、汪琬、李天馥等,清康熙诗坛期待“领袖式人物”的出现。 从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秋荐征之士入京至十八年(1679年)三月博学鸿儒科考试结束的大半年时间,各地名流雅士聚集京师,相当于举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人雅集。“车马黄埃那可歇,交游冠盖喧城阙。花筵纵饮数论文,灯市联吟曾踏月。”[1](卷23)时人诗作重现了当年京师交游雅集的喧嚣繁盛。被征博学鸿儒入京后相互交游唱和,自己的小圈子与他人的小圈子相互交叉形成大圈子,大圈子交叉扩展形成交游网。这张网由几个重要点连接而成。这个起连接作用的点,就是以王士禛、冯溥等为主的“领袖人物”。“领袖人物”向来在文学风气的转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严迪昌就曾说过:“领袖式人物无论在学术抑或是在文学的领域内影响和作用,最突出的是团聚号召力,其对养成或开创一种风气的推促能量,往往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2](P212)文学风气的转移和流变不仅与政治经济、文化思潮有关,作为创作主体的文人之间的交游雅集,特别是有“高位主持诗教者”参与的圈子,都会因论诗旨趣的相通或谈艺论诗过程中思想的碰撞而融汇形成相似观念,由小圈子影响及大风气,从而对诗文流变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领袖人物—小圈子—交游网络—大风气”的层层递进推促了诗坛风尚的变迁。 博学鸿儒科诏开之时,王士禛虽未主盟诗坛,但其诗学观念、诗歌宗尚已经具有较大影响。而博学鸿儒的进京,则为其诗坛地位的提升与诗学观念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更大平台。交游雅集活动作为载体,则连接了王士禛与博学鸿儒形成“小圈子”,影响了“大风气”。其交游雅集活动主要有: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冬,王士禛、施闰章、陈僖访王弘撰于昊天寺。十八年(1679年)正月初七日,王士禛、王弘撰、梅庚、施闰章小范围雅集。正月十五日,王士禛、施闰章、梅庚、吴雯、洪昇、孙枝蔚六人小集,作踏歌之游。二月四日雪后,王士禛召集李因笃、潘耒、梅庚、董俞即景拈王维诗句“积素广庭闲”韵赋诗。是年秋,陆嘉淑、邵长蘅和梅庚月夜过访王士禛,四人效宛陵体作诗。九月初九日,王士禛招陆嘉淑、阎若璩、邵长蘅、梅庚、陆元辅饮,用陶诗“悠然见南山”句限韵赋诗。 博学鸿儒科期间的文人交游雅集活动非常密集,遇有节日,特别是花朝节、上巳日等传统文人节日,都有较大规模的雅集活动。小规模的聚会则更为频繁,几乎不限时间与地点,春花、秋月、夏雨、冬雪都可以成为聚会的由头和雅集上的诗作题材。雅集内容多为赏花、踏雪、郊游、登高、礼佛、祝寿、送别等,活动内容名目繁多,邓汉仪之子邓方回作有《征辟始末》,对京师大吏的大规模宴集活动作了描述:“时都中喜招客聚饮者,若司马宋公德宜、学士李公天馥、宫詹沈公荃等,宴集至数十人,皆一时名流,号称盛举。”“主正曹正子与家君称夙契,亦屡会宾客,尝数十人。”[3]陈维崧也描述了当时宴集行乐之事:“时于五夜阑,或在百人座。分曹掷帽呼,联袂摄衣坐。欢笑无不为,乐事任人作。”[4](卷6)交游雅集这一士人生活方式的繁茂,昭示了士风重心的转移。博学鸿儒科期间,士林交游主要体现为繁茂的诗酒倡和、登临冶游,以及无关宏旨的题图雅集。交游雅集在士人生活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士人重新回到“歌酒的酬应”和“清狂的冶游”生活状态。从雅集内容来看,淡化民族矛盾和润色鸿业、黼黻太平的诗作开始成为符合时代潮流和士人趣味的“正统”文学,诗学宗尚也向着淡化国是的“神韵”理论和倡导和平雅正的“盛世清音”方向演进。康熙诗坛风尚变迁的信号在王士禛组织的交游雅集中也透露出来。 二、王士禛的交游雅集与“神韵说”诗学宗旨的传播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遗民诗坛严重衰微,遗民诗歌已不再适应此时社会形势的发展和政治、文化环境的需要,久享太平的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风气来引领诗坛。正如魏泉所言:“当承平日久,一种曾经流行一时的东西渐渐会开始隐隐遭人厌弃,所谓久而易穷。此即可谓‘天时’,当此之时,一些小圈子中最早出现的能反映人们共同心理的新思潮和新趣味,就相对容易对大风气的改变产生作用。”[5]王士禛及其“神韵说”就是在这一转型时期脱颖而出。“神韵说”淡化矛盾、远离现实的内容,以及清新淡远、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获得统治者和士人的欣赏。此时,王士禛虽未宗盟诗坛,但已经开始承担“月旦评”的职责,俨然一个开辟风气的时尚巨子。正如潘耒所言:“惟公在金门,巍然秉月旦。……大雅辟榛芜,烛龙正璀烂。”[6](《梦游草》上》)博学鸿儒科期间,王士禛及其“神韵说”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通过“小圈子”的传播,影响了“大风气”。 与冯溥、曹广端、王熙等人的交游雅集相比,王士禛组织的雅集规模较小,内容也以谈诗论艺、清谈雅言为主。所交往之人,除了性情淡泊、耽寂守肃的吴雯、邵长蘅外,其他多为早年相知的诗坛名流,如施闰章、朱彝尊、陈维崧、李因笃、潘耒、陆嘉淑等人。邵长蘅在《青门旅稿》中详细记载了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京期间与王士禛的交往:“己未客都门,寓保安寺街,与阮亭先生衡宇相对,愚山先生相距数十武,陆冰修仅隔一墙。偶一相思,率尔造访,都不作宾主礼。其年寓稍远,隔日辄相见,常月夜偕诸君叩阮亭门,坐梧树下,茗碗清谈达曙。愚山《赠行》诗有云:‘踏月夜敲门,贻诗朝满扇。’盖纪实也。”[7](卷1)王士禛与来往宾客在清凉幽静的月夜“诙谈杂仙鬼,清话探史籍”[7](卷1),文人雅兴,令后世艳羡不已。王士禛交游范围较小,但由于参与雅集的宾客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谈论内容又多与文学艺术有关,因此,他们的思想就更容易碰出火花,形成相似的诗学观念和创作理念。 文人雅集自然少不了吟诗作赋。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二月初四日的一场雪后,王士禛召集李因笃、潘耒、董俞、梅庚、邵长蘅宴集,清谈永夜。此次集会以“雪”为主题,用王维诗“积素广庭闲”为韵赋诗。王维原诗为《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寒更催晓箭,清镜减衰颜。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借问袁安舍,翛然尚闭关。”描写雪后景致,静谧空灵。用“积素广庭闲”为韵,是应雪景之意,又与王士禛“神韵说”的审美观念密切相关。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上“诗文评点”谈自己喜爱的咏雪诗,王维的这首诗赫然在列,他说:“余论古今雪诗惟羊孚一赞及陶渊明‘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及祖咏‘终南阴岭秀’一篇,右丞‘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韦左司‘门对寒流雪满山’句最佳。”这些咏雪诗都具有空灵蕴藉、冲融恬淡的艺术特征,与王士禛“神韵说”提倡的审美追求相契合。王士禛从小接受的就是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人的诗歌,重视诗歌的风神与韵致,追求“清远”的意境,崇尚“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以“积素广庭闲”为韵赋诗,有利于引导雅集文人的诗风走向清新悠远。事实也是如此,此次聚会所作诗歌大都风神雅致、冲淡恬静。如邵长蘅诗云:“斜日淡寒辉,冰溜承檐滴。翛然拥炉坐,空馆闭愁寂。”[7](卷1)风韵闲远宁静,格调清冷悠寂。就连历来以“硬”、“厚”为诗作特色的潘耒,此次作品也是意境悠远、清灵纯净,如“春江把瑶草,怀人渺无处。悠悠出岫云,天边忽相遇”[6](《梦游草》上)等诗句。 王士禛的“神韵说”引导诗歌走向模山范水的路子,以“冲和淡远”、“清新缥缈”的审美风格引导着诗坛走向。这类具有“神韵”意味的“含蓄蕴藉”诗,往往只是描写清新悠远的景物,缥缈俱在天际,读者从中看不到作者的情绪。因此,王士禛的“神韵”诗被人批评为“诗中无人”,“神龙见尾不见首”。实际上,这类诗作不是不含有感情色彩,只是诗中蕴含的感情与其诗风一样,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看似虚无缥缈,实际上最终还是归于“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只是王士禛“神韵诗”中的“温柔敦厚”与朱彝尊等人的“清雅醇厚”不同,“神韵诗”的“温柔敦厚”是以“清新淡远”的面貌表现出来的。除了有意以“神韵说”来引导诗风走向,王士禛还以“神韵说”所蕴含的“清远”、“清奇”审美观来奖掖评价他人。如王士禛《和施愚山喜梅耦长至》有句云:“新诗冰玉质,故人兰蕙芬。”即以“冰清玉洁”来评价梅庚诗作。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月,梅庚见怀王士禛,王士禛作《和耦长十月十八日初雪见怀之作》,诗云:“清才忆梅尉,高唱寄梁园。”对梅庚诗许以“清才”。清新淡远、清心静气是王士禛所倡导的审美品格,也是他所欣赏的诗人品性。 己未博学鸿儒科期间,康熙帝开始有意树立“神韵说”为正统,王士禛作为馆阁文臣,自然以辅佐康熙帝的“文治”为己任,自觉地以“神韵说”来引导诗坛创作走向“盛世清音”。王士禛“神韵说”淡化现实矛盾、扭转质实诗风的作用,钱钟书曾说道:“渔洋谈艺四字‘典’、‘远’、‘谐’、‘则’,所作诗皆已几及……明清之交,遗老放恣驳杂之体……诗若文皆然。……‘爱好’之渔洋,方为拯乱之药,功亦伟矣。”[8](P98)在促使诗风转变的过程中,博学鸿儒科前后王士禛的交游“小圈子”作为传播诗学观念的媒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王士禛与“宗唐”“宗宋”诗学主张的论争 诗歌宗唐与宗宋,一直是清代诗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清代初年宗唐一派的论调占据主要地位,但到了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博学鸿儒科诏开时,宗尚宋诗的理论经钱谦益、黄宗羲、吴之振等人的大力提倡,已经到了与宗唐派分庭抗礼的地步。张尚瑗《六莹堂集序》曾言:“本朝三十年以前,蒙叟之旨未申,学诗者犹王、李也。洎今而宋、元诗格,家喻户晓。”[9]所谓的蒙叟之旨,即钱谦益“称宋、元人,矫王、李之失”的诗学主张。而所谓的“本朝三十年”,大概指的是清康熙十三、四年,而实际上在十七、八年间宋诗热已然成为“全国性潮流”。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初,毛奇龄到京师时,“时值长安词客高谈宋诗之际”[10](《序言》)。其时,王士禛的诗学宗尚也是倾向于宋诗的,这在他晚年自述平生论诗变化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明:“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长庆以后已有滥觞,而淳熙以前俱奉为正的,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11]王士禛提倡诗歌“宗宋”的时间,据蒋寅考证,当在清康熙十五、六年间服阙回京任职户部之时[12]。潘务正则认为至迟在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间[13]。这期间,他以文人雅集为媒介,在博学鸿儒中提倡学习宋元诗,把宗尚宋诗的风气推上了一个新高潮。 博学鸿儒科期间,被王士禛引为同道的也多为宗宋派诗人,如孙枝蔚入京之时随身携带了一本黄庭坚的《山谷集》,明确昭示其诗学宗尚。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元宵节,王士禛、施闰章等人约孙枝蔚作踏歌之游,孙枝蔚有诗《元夕早寝,施尚白使君、王贻上侍读同梅耦长、吴天章、洪昉思诸子过访,颇见怪讶,且拉之作踏歌之游,灯火萧然,败兴而返,因成二绝》,其二云:“踏歌朝士最能文,鸥鹭鸳鸯许作群。不见开元诸子弟,方知战伐久纷纭。”[14](P1283-1284)“开元诸弟子”当为宗唐诗派的代名词。宗宋派与宗唐派诗人的论战激烈而持久,从侧面表明了当时诗歌流派观念冲突程度之深。 王士禛不但自己提倡宋诗风,还在博学鸿儒中宣扬宋诗,特别是其中符合“清新淡远”审美要求的诗歌让人认识到宋诗的真面目。王士禛《池北偶谈》载:“宋梅圣俞初变西昆之体,予每与施愚山侍读言及《宛陵集》,施辄不应。盖意不满梅诗也。一日,予曰:‘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此谁语?愚山曰:‘韦苏州、刘文房耶?’予曰:‘乃公乡人梅圣俞也。’愚山为爽然久之。”[15](卷18,“梅诗”条)这件轶事当发生在清康熙十七、八年间,其时王士禛对梅尧臣的诗歌兴趣正浓。施闰章作为坚定的宗唐派诗人,竟然连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的作品都不涉猎。王士禛通过援引诗句对施闰章进行熏陶和感染,使其缓解了对梅诗乃至整个宋诗的抵触情绪,不仅为宋诗正名,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时人专宗一朝一派的狭隘诗学观念。王士禛对宋诗特别是梅尧臣诗作的宗尚不仅表现在为其正名并进行传播上,还表现在引导雅集宾客学习并仿效“宛陵体”上。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陆嘉淑、邵长蘅和梅庚月夜过访王士禛,四人效“宛陵体”作诗,加深了众人对宋诗的理解和认识。 虽然提倡宋诗风,但王士禛并未否定唐诗风,这样的观念在一次与施闰章的谈诗论艺中透露出来。陆嘉淑《渔洋续诗集序》记载了王士禛与施闰章的这次论诗:“窃尝见先生与宣城施先生论诗矣,宣城持守甚严,操绳尺以衡量千载,不欲少有假借。先生则推而广之,以为姬姜不必同貌,芝兰不必同臭,尺寸之瑕,不足以疵颣白璧。两先生疑若矛盾,乃其披襟扣击,简牒往复,商略评次,往往各当于意乃止。此倡彼和,丹铅错互,欣然并解,若水乳合,何也?先生曰:‘吾别裁不敢过隘,然吾自运未尝恣于无范。’”[16](P688)这段故事发生在清康熙十八至十九年九月陆嘉淑客居京师时。这次论辩是发生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呢?陆嘉淑云:“今操觚之家,好言少陵者,以先生(指王士禛——引者注)为原本拾遗;言二谢、王、韦者又以为康乐、宣城、右丞、左司;其欲为昌黎、长庆及有宋诸家者,则又以为退之、乐天、坡、谷复出。而先生之诗,其为先生者自在也。……若夫宣城力砥其泛滥,新城弘奖其品流。”[16](P688)原来是时人按照自己的好尚来理解王士禛的诗歌宗尚,王士禛在论争中表明自己在诗学宗尚方面不会无界限,但对前人的取舍也不会过于狭隘,这种观念也间接表明了他对宋元诗的态度。 虽然博学鸿儒科前后王士禛对学习宋元诗的兴致正浓,但实际上,王士禛是反对诗歌门户观念的。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王士禛在《黄湄诗选序》中云:“近人言诗,好立门户,某者为唐,某者为宋,李杜苏黄,强分畛域,如蛮触氏斗于蜗角而不自知其陋也。”[17](卷2)王士禛提倡学习宋元诗歌是为了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是对宗唐的补充,而非宗宋就反对宗唐。而且,博学鸿儒科后,康熙皇帝直接掌控文坛,参与诗坛的整饬与重组,王士禛身处翰林院,得为天子近臣,其诗歌审美观念与诗学宗尚也就唯康熙帝马首是瞻了。因此,博学鸿儒科后,虽然王士禛还未完全回到宗唐的道路上来,但他开始倡导消除门户成见,兼师唐宋,这恐怕是其“返回唐音”的前兆。其实,在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博学鸿儒科诏举前后,对诗坛影响最大的并非诗歌的宗唐祖宋问题,而是诗歌为谁“服务”的方向问题。其时,正是收束诗坛“无所归依”状态的关键时刻。博学鸿儒科前后的交游雅集是以淡化遗民情绪,促进诗坛走向“盛世清音”为最终目的的。在这种目的指导下,宗唐和宗宋只是一种诗法手段。不管是冯溥、毛奇龄等人提倡的盛唐博大气象,还是王士禛宗宋的诗学倾向,最终都要为盛世文治提供相应的文学格调。 博学鸿儒科期间,王士禛的“小圈子”传播“神韵说”诗学主张,迎合了士人的审美趣味,淡化了社会矛盾,扭转了质实诗风。博学鸿儒科后,康熙帝扶植王士禛及其“神韵说”成为正统,通过诗坛推促“盛世文治”。另一方面,王士禛以交游雅集为载体厘清诗学宗尚,提倡宋诗风,又不反对唐诗风,“兼师唐宋”的诗学主张影响了康熙诗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专宗一朝一派的狭隘诗学观念,有利于诗人继承传统,独创新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