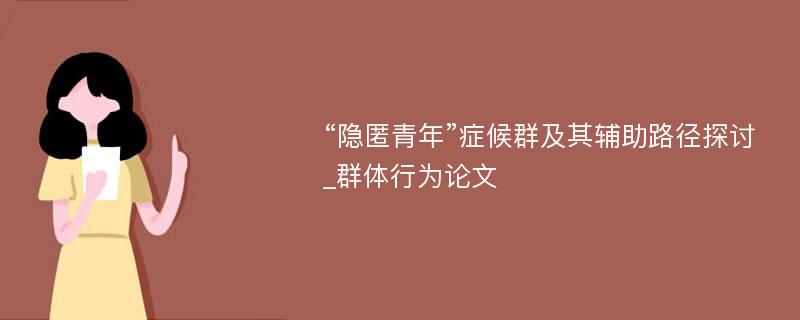
“隐蔽青年”症候群及其援助路径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症候群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十年来,作为现代青年的心理社会问题之一,“隐蔽青年”现象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了精神医疗、社会工作、心理学等各领域的广泛关注,并有逐渐定性为青少年时期的某种新型“征候群”的趋势。“隐蔽”,或称之为“宅”,源于日语的“Hikikomori”,在英文中时常直接使用,或被译为social Withdrawal。此现象起初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源于NHK电视台在2002年至2005年间所播出的一个系列节目。节目中曾推测全日本约有50万-100万青年人处于“隐蔽”状态。英国BBC也在2002年10月连续推出了两期探讨有关“隐蔽青年”的节目,从而将隐蔽青年的问题带入欧美社会。BBC的节目播出之后,多数英国观众表达了同类现象在英国亦广泛存在的担忧。同时,意大利国内发现的隐蔽青年群体开始出现在欧洲各国报端。此后各类报道涌现,类似现象正出现在除英美、欧陆之外的韩国,甚至港台地区[1]。笔者则通过介入上海市的各区精神卫生中心以及青少年社会服务机构,发现了中国内地大城市的“隐蔽青年”人群。
至今为止关于“隐蔽”的研究,主要有三大视角。首先,有影响力的研究来自于对隐蔽的社会心理要因分析。具有现代社会特点的“个体化”被认为是包括“隐蔽”在内的青少年“自我萎缩”现象增加的重要原因[2]。从社会要因出发研究隐蔽青年的精神医生齐藤环认为,年龄大于25周岁的“隐蔽”青年具有该症候群的典型性,诊断的主要标准是:在排除由于其他精神疾病作为第一要因而引起这一状态时,案主连续在家中长达6个月以上的“隐蔽”生活状态,并同时没有参加任何社会活动[3]。其次,从医疗诊治、尤其是精神医疗角度的研究则发现,精神医疗以及精神保健福祉的领域,对“非精神疾患性质”的隐蔽青年群体较为关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对“非精神疾病”的隐蔽青年群体的“医疗化(medicalization)”倾向日趋明显。在日本,受到政府机构委托,其下属的“厚生省培训班”发布了《社区卫生中针对“隐蔽”的应对手册》[4]。受该手册影响,“隐蔽”在社区卫生领域被明确界定为精神医疗的对象,标志着“医疗化”程度的提升。再次,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展开的研究认为,隐蔽青年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该青年在“人际关系”中遭受的困难、挫折所引发的。有研究结果显示,隐蔽的原因与人际沟通经验有密切相关性。隐蔽青年通常拘泥与维持一个统一的自我形象,而对于碎片化、表面性的沟通疲于对应、无法应付,从而无法维持一般的交往关系。这并不意味着,起初就回避与他者的交流,而是在青少年时期寻求与他者建立深厚关系时,因挫败而将自己“隐蔽”了起来[5]。
当然,“隐蔽青年”不仅仅只是发达国家所独有的社会心理问题。在我国,尽管尚未有对隐蔽青年群体的专项调查(类似调查的开展面对来自家庭、社区等多重困难),笔者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接触精神医疗社会工作,其中我国的青少年精神健康问题突出,这一群体中精神疾病数量在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背景之下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和城市“三失青少年”人数有所增加的趋势是相一致的。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社会工作实务和研究领域以及相关学科对这类人群的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原因在于,“隐蔽青年”并未像失足青少年那样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过直接的破坏,因而很少能够直接进入公众的视野。然而,从其加重家庭负担、造成人力资源浪费,甚至加剧区域社会“原子化”程度等状况来看,如何直面并解决“隐蔽青年”群体日益增大的问题成为一项值得探索的紧迫课题。
首先,对“隐蔽青年”现象的研究有助于现代青年研究的理论发展。该群体特征的考察对“NEET族”青年群体的进一步细化、补充将起到重要意义。原本应当自立并迈入社会人阶段的NEET一族(中国称之为“三失青年”)已呈现出一些新的分化。其中有一类青年人从离校之后既不参加工作,也不继续学习或接受培训,更为显著的特征是长期呆在家中,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而依靠父母的收入赖以生活。就“不参加社会活动”这一特征上,可以说明NEET族与隐蔽青年两个群体间的联系。其次,NEET族中包括了参加社会活动、甚至有活跃社交活动的青年,比如长期追星、频繁参加朋友聚会等,而隐蔽青年则是一群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的NEET族。这一群体的隐蔽生活以及所造成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他们也是急需关注和接受援助的人群。研究特殊群体的援助方式和路径是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紧迫课题。本文在梳理隐蔽青年有关争论的基础上,通过典型的临床案例分析“隐蔽青年”征候群的一些特征,进一步探究对隐蔽青年的有效援助路径。
二、“隐蔽青年”症候群的发现及其争论
1.心理学视野下的隐蔽青年
对“隐蔽”青年的心理学解释中,最值得一提的是E.H.埃里克逊和小此木启吾。埃里克逊把因学习或研修期间加长,从而延迟承担社会责任的青年期定义为心理社会的“延缓偿付(moratorium)”的时期。受此启示的精神科医生小此木启吾就将这类青年称之为“延缓偿付的人”[6]。若将“隐蔽青年”理解为“长期不与他人交往,在社会上不自立”的人,类似的青年在以往的各个时代都曾出现过,无非是在称呼有些不同而已。追溯到中国古代,如陶渊明般的“隐士”,隐居而不仕,大约属于最高境界的“隐蔽青年”。早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夏目漱石就曾将喜好文学而又“大隐”于世的青年人叫做“高等游民”——他们虽是从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却坐食其家中殷实的资产,沉浸在西洋文化之中,对经济人世却漠不关心。作为森田疗法的创始者,森田正马大约是将“与人相处的恐惧”以“隐蔽”为核心对这一病态加以细致记录的第一人[7]。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高度经济增长期”,日本社会曾出现了大批大学生留级的现象。有学者对此现象试图以病理性的概念加以描述,认为是神经症的一种,称这些不上学的“隐蔽”大学生为“意欲减退型”的留级生[8]。之后,这些缺乏意欲的学生被建构成为一群“冷漠学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2.“隐蔽青年”的三大争议
围绕现代的“隐蔽青年”问题,在日本存在着三大争议。这些争议对中国的隐蔽青年问题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争议之一:隐蔽青年是否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1964年,精神医生鑪幹八郎就曾以“学校恐惧症”概括类似现象[9]。1992年文部省的《关于不登校问题》的报告书亦有涉及。可见,“隐藏”(Hikikomori)在一开始是在“不登校”现象之中潜伏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此现象随着时间和社会变迁,人们的认识没有发生变化,主要的变化表现在对这一现象的“长期化”日益担忧。
争议之二:是“隐蔽青年”的实际状况和被建构的社会印象之间是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一般隐蔽青年固有的社会印象是,不参加社会活动、缺乏社会经验等。2003年在日本的61个精神保健福利中心和582个保健所实施调查的结果表明,被认为是“隐蔽”的青少年中约7成以各种形式外出、并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因此,对于“隐蔽”的定义方式也是值得反思的,似乎并不完全应该以“原因”为主加以定义,而应当以怎样的状态属于“隐蔽”来定义会显得更具有概括性[10]。
争议之三:在于学界对于“隐蔽”行为的价值判断存在分歧,前后呈现出一种变化。起初,“隐蔽”被认为是一种对社会的不适应状态,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越轨行为。不过,有学者认为,这是坚守“自我特性”的一种行为表现[11]。有精神医生则认为,“‘隐蔽’既不是临床的疾病,也不是某种疾病而引起的症状,只不过是为了实现个体的生活方式而采取的非特异的行动模式”而已,而对此加以强制性介入的行为则可能引起当事人的暴力、自伤、精神疾病症状、甚至自杀。因此,对当事人在其“隐蔽”期间加以肯定、保护的态度方才是正确的对待方式。
到了现阶段,面对上述争论,意欲急切地对这一行为的是非加以判定似乎显得有些草率。从隐蔽青年们的话语和生活方式之中,往往可以折射出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难以填埋的沟壑[12]。在各种争论中,尤其值得社会工作者关注的不是对有“隐蔽”现象的个体如何评价的问题,而是有必要探讨是何种原因促使个体选择了“隐蔽”。不从违反就学、就业的相关社会规范、判定是否是越轨行为入手,而是从个体价值观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纠葛入手,反思将“隐蔽”作为“不适应现象”、甚至将其作为精神症候群的社会立场使得隐蔽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在中国,“隐蔽青年”尚未引起大众社会足够的关注,主要原因之一是这群人对公共社会秩序、经济生产、生活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仍然是潜在的,而没有显著表现出来。当然,对其所在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只不过在家庭这一私密空间中,潜在的危机被中国式的浓厚亲情关系所掩盖。这一掩盖的过程极有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危机事态的扩大,而当危机不得不最终暴露在社会和公众面前时,无论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干预有多及时,对家庭生活已经造成的负面影响却很难快速消解,危机干预也就变得十分被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下,公众仍然未意识到,“隐蔽”所可能包含着的精神病理学特征,如果“隐蔽”现象中所呈现出的精神病理学的特征,那么运用社会工作、心理学甚至精神医学等途径的介入,也就变得十分迫切和重要了。
三、“隐蔽青年”典型案例及其特征
“隐蔽”所对应的日语词原意并非精神医学的专业术语,通常指“萎缩、后退”、“窝在家中”等意思,在上世纪末才进入学界,成为一个概括青年心理现象的概念(尽管,概括同一现象的日常话语中的“宅”也有类似的含义)。在此,笔者不妨通过一个典型的案例来对照一下“隐蔽青年”典型个案的精神病理学特征:
青年A,男性,23.5周岁,性格显得老实。小学时代交友正常,并参加过少儿足球队。中学阶段在学习上、运动场上表现皆出色,并结交了至今仍保持来往的朋友。因在中考中失利,未能进入市重点高中,此后,其和同学交往渐少,自认为有劣等感。中考后进入一所普通职业学校,所学专业也非第一志愿。职校时代,在学习和人际关系比较适应顺利毕业。不过,在就业上很不顺利,最终依靠父亲的人际关系,进入了一家高科技企业。但在第一个月的新员工培训中又强烈感受到了劣等感,虽坚持完了研修,却未最终正式签约,打起了退堂鼓。自此以后近2年来,A一直呆在家中,陷入了日夜颠倒的生活。近期,偶尔去附近的图书馆和公园,不过仍因无工作,刻意回避原来的朋友、同学。来自社区的社会工作者在接触A的家人时了解到,A几次谈到自己内心深处一直在期待着某一天能够出现全面的转机,但并没有信心迈出行动的步伐,结果仍然过着“隐蔽”生活。
在此期间,其父母虽然很担心A的境况,但从未对A进行严厉的责备,也未对A的状况和将来进行相互间的深入沟通。在日常生活当中,父母与A的交流几乎停留在最低限度,相互之间似乎是在想办法回避可能发生的直接而剧烈的冲突。
1.“隐蔽青年”症候群的特征
在探讨关于A的案例之前,首先,有必要简要回顾将“隐蔽青年”作为症候群的精神病理学特征。在迄今为止的精神医学领域,这一症候群的精神病理学特征通常概括为:一是以居家生活为主;二是不接受教育,也不就业,无社会活动;三是上述两种情况持续了6个月以上;四是排除患有其他精神疾患的可能性;五是在人际交往上,除了家族成员等亲密关系之外,几乎没有人际间的互动。之后,有学者对上述特征加以分析,认为未有其他精神疾病症状,而仅仅表现为“隐蔽”的,可以称之为“原发性隐蔽”[13]。
上述案例中的A呈现出了“隐蔽青年”症候群的一些较为典型的精神病理特征。首先,案主抱有一种“未战先忧败”的态度。主要是因人生中有过至少一段“未战先忧败”的经历,并深受影响。A的“未战先忧败”之经历看似是发生在求职经历中,其实从他中考失利时就已埋下了爆发的种子。之后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交友中,A都不再自信。失败之后,A的选择不是面对失败奋起改变,而是在行动之前就事先退缩。退缩是为了避免新的失败,因此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消极的适应方式。
其次,“理想之自我”犹存。从案例中还可以看到,当年中考失利,仍然进入了职校学习的A并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重大失败或挫折。在与社会工作者的谈话中,A时而流露出期待突然转变,对成为理想中的那个“我”有着一定的期待与想象——一个应当实现的理想或目标其实并未被A所抛弃,始终在其内心深处徘徊;然而,因未有过直面失败、再次出发的经验,无从对理想中的自我做出必要的反思与修正。无法对自我进行反思与修正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来自其家人。A的家人对于A一直以来的肯定态度从未改变。监护人始终抱有类似于“本来我家孩子是个优秀的孩子”、“绝对不会长久如此”的想法,这些意识成为其维持继续隐蔽的一把外在的“保护伞”。
再次,“自我决定意识”十分淡薄。社会工作者了解到案例中的A在面对就业、未来发展的问题上,本人的主张或希望是非常模糊的,所做出的选择都来自于父母之意。本人“想做的事”、“想在某领域有所作为”的自我意愿并不强烈,甚至连爱好都不太明显。同时,自我决定能力不足使其无法面对社会现实,无法一下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应聘求职、获取工作并融入社会生活。
最后,回避来自他人的评价。在行动模式上,呈现出尽量回避他人评价的倾向。A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是,对温存心中的“理想自我”有威胁的任何行动都感到惧怕,并极力回避。因而,社会工作者在起初直接和A谈话,试图让他正视现状,提出在认识现状的基础上将实现理想自我付诸行动的建议,但都遭到了A的回避或拒绝。
2.原发性“隐蔽青年”症候群的家族关系特征
家族关系的特征之一是亲子关系的过度依赖。东亚国家的亲子关系通常表现在子女离巢时间相对于西方家庭要晚若干年。据日本有关机构的调查,至今为止成年子女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比例依然很高,其中20岁-39岁的未婚子女中的68%仍与父母同居[14]。中国家庭生活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推崇子孙满堂,共享天伦之乐,努力创造条件实现父母与子女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子女即便已经有了工作与收入,在食宿上仍依赖父母的也不在少数。而问题在于,过度相互依赖的亲子关系就会成为产生“隐蔽”青年的温床。结合现代青年群体中“延迟偿付”期的出现,过度依赖的亲子关系将进一步拉长“延迟偿付”期,同时“隐蔽”青年在家族的经济、生活等多重庇护之下,更加难以摆脱这种类似“寄生”的方式。
至今为止,实证研究常通过“家族评估量表”为基础而改造的测量工具,通过与其他症候群的比较,从而概括了隐蔽青年的家族关系特征[15]。主要特征有,家庭内部具有明确的规范。这一规范来自于父亲或母亲,或父母协商的结果。而青年本人对家庭规范未有过任何不满,甚至未感受到过来自规范的束缚。其次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极端缺乏,尤其对于负面情感未有共同面对的经验,也没有产生过共鸣。其中父母对于子女的情绪,尤其是愤怒、沮丧、悲伤等未有关注。当然本人也不主动将烦恼向父母倾诉。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人之间却缺乏相互之间积极的沟通与情绪的确认,以消极的方式相处,对彼此的行动模式之影响是巨大的。家族成员间的类似关系特征在多数隐蔽青年的案例中都较为明显。
四、“隐蔽青年”援助的可能路径探讨
如何对隐蔽青年进行援助?主要集中在两条路径上:一是针对其本人的实际状况(排除其他精神疾病可能之后),对其进行援助和支持。二是对其家庭的援助。对家庭的援助方法需要首先对家庭的状况加以综合评估。对于家庭成员的援助,主要可集中在整合公共资源、提供政策支持与切实的社会心理服务方面。这类支持可以使家庭成员维持身心稳定,从而为隐蔽青年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对隐蔽青年的具体援助方法有哪些?首先,对其本人进行援助,选择怎样的方法是十分重要的。从社会工作介入的方法来看,可供选择的方法不少。不过,临床社工的实践中,运用个案方法可能会导致的“移情”后果处理起来相对比较困难。亦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面对长时间因不上学、不工作而导致有对人恐惧的青年人,运用个案方法或心理咨询等方法都未能得到很好的效果,而将提供一个同时代的青年人集体活动的场所却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16]。因而本文着重探讨小组方法的运用。为改善“隐蔽青年”的“自我意识淡薄”、刻意回避他人评价等状况,帮助其改善人际关系、恢复并增进其社会功能,运用小组工作法是可以取得良好效果的。
从起源看,小组工作被认为来自宗教性的仪式,当时就被用于自我探究及人际关系的改善。不过,真正成为一种助人方法源于1910年Moreno创设的“即兴心理剧”,将参加者分别划分为导演、主人公、辅助自我(即剧中的演员兼导演助理)和观众,将参与者的现实生活及关心的问题即兴表演出来,从而促进精神净化或洞察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牛津小组”、“禁酒同盟”的成立而得到进一步推广。自20世纪60年代后,各种心理学理论和实践对小组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养料。如今的小组疗法综合了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罗杰斯倡导的基本心理会心小组(basic encounter group)、Perls的格式塔疗法、Berne的交流分析、May的存在主义心理学、甚至中国的“禅”、印度的瑜伽,成为一个综合性极强、可操作较高的治疗工具,并实际运用在社会工作、教育、临床精神医疗及等各个领域。
在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领域,小组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即“非结构式小组”(non-structural group)和“结构式小组”(structured group)[17]。非结构式小组通常由10多位互不相识的人组成,在毫无课题、毫无角色分工与任务的状况之下,自由发展而成的小组体验活动,可以形成一个自由讨论的“场”。
参照“非结构式小组”,面向“隐蔽青年”展开的活动中有一种称之为“自助小组(self-help group)”的形式尤其值得一提。通常,自助小组是指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并不直接参与(可以间接参与),由当事人们自主聚集开展的小组。小组有共同活动的“场”显得很重要。其重要效果往往表现为,参与援助的人往往通过发挥其援助他人的作用,而使自己也能得到援助。这一效果的实现能够很好体现“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理念。从这一角度出发,自助小组即含有改变自身想法与行动的“自我改变的机能”,又体现出作用于社会环境的“社会变革机能”。在包括自助形式的小组活动中,都非常重视“邂逅(encounter)”的作用,自主聚集在一起的隐蔽青年通过邂逅,增加改善人际交往中的自我封闭倾向的可能性,在与邂逅者的交往中相互影响、相互引导,促成对以往的行动模式加以反思。这类小组主要着重体现是小组成员自我改变的功能。
另一种较为常用的是结构式小组。结构式小组需要在限定的时间之内,朝着实现商定的可实现的、具体目标,通过一定的阶段,完成一定量的任务和解决相应的课题。通常,小组领袖事先需要说明小组目标、具体任务和安排,经过成员们认可之后才能正式开始。在小组任务完成、整个小组介绍之前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即通过回顾和分享整个小组过程而将体验加以深化。从实践来看,针对隐蔽青年等群体展开的结构式小组仍然需要遵循此类小组活动基本原理,即:小组成员由少数人构成;具有阶段性进阶的现实目标;重视成员间相互协作的过程;重视成员的体验与情感反应;成员自身的积极反思;导入心理援助[18]。
除了对隐蔽青年本身的援助之外,对隐蔽青年所在家庭成员的社会支持和援助也是十分必要的。通常小组目标可设定为营造一个安心的生活环境,并促使家族成员之间的积极互动的有效恢复来增进本人的自信心,同时提高其自我评价。如果为了能够更好的重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类似的小组实践可借鉴“居住型的小组”所采取的方式。通常,“居住型的小组”需要将食宿等日常生活搬移到家庭空间以外的地方,但又不同于住院照顾,而是多集中到能够提供居住设施的一些福祉机构中[19]。入住设施之后,在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的支援下,让案主们和家长一起参与到一些农业、手工业活动及日常生活的劳作之中,从而改善其在家庭、超越家庭的人际关系中的自我封闭与萎缩的倾向。从这一点而言,居住型小组活动的方式所探索的,正是在结合家族成员间互动的基础上,为促成各家庭之间的社会支持提供便利,从而减轻照顾者压力,有利于隐蔽青年早日拜托隐蔽生活的方式。这也正是对WHO所倡导的“普及、增强社区精神卫生保健”观念的一种可操作化的实践。
五、结论与讨论
尽管本文中的典型案例来自于精神医疗社会工作的援助实践,但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然而,隐蔽青年在中国从个别案例,逐渐呈现出某种群体性症候群的特征,并日益显现出一系列消极影响则是不争的社会事实。在这一背景之下,本文通过追溯隐蔽青年问题的起源,并结合典型的非精神疾病性隐蔽青年的典型案例,探讨了这类青年症候群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试图将焦点集中在小组工作上,探讨援助隐蔽青年的可行路径。
时至今日,在国外,精神医学、社会工作、心理学等学科在探讨青年隐蔽问题上已积累了大量的成果;而在中国,这一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并在如何理解和援助隐蔽青年的问题上,学界和实务界都仍存在着一些分歧。本文作者从“隐蔽青年”典型案例的特征入手,将其问题集中在人际关系、沟通问题上时,其援助路径的选择自然聚焦到了小组工作上,试图探讨如何通过增进良好的人际互动、建立起隐蔽者与家族成员、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效联系,并重视集团体验以及家庭之外的中间设施的利用。当然,就案主的人际互动与沟通能力的重建这一复杂问题而言,任何线性逻辑和简单结论都是应当避免的,就此意义而言,本文只是笔者探索“隐蔽青年”问题的一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