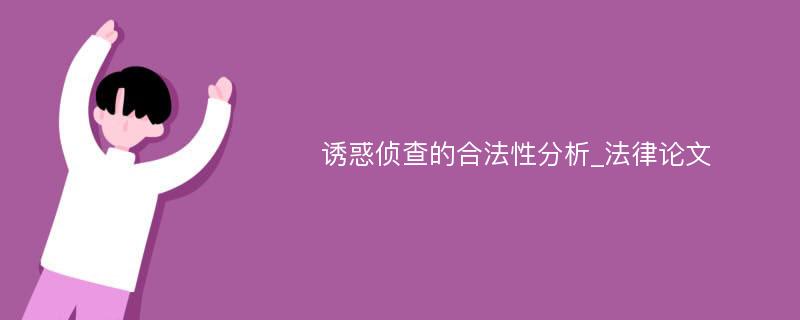
诱惑侦查之合法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法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诱惑侦查,又称为侦查陷阱,是指侦查机关设置圈套,引诱侦查对象实施犯罪,并将其及时(在犯罪现场或人赃并获)拘捕的一种侦查手段。这种侦查手段的优势在于,整个犯罪过程在侦查机关严密的监控之下,绝无犯罪嫌疑人逃脱、毁证、匿赃之虞,而且案件一经查破,所有的调查取证工作也几乎同时结束,案子破得干脆利落,耗时短,也难以翻供翻证。因此,这种侦查手段越来越受到侦查机关的青睐,并在侦破毒品犯罪、假币犯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广西桂林某城区检察院统计,该院在1998年至1999年6月受理这两类案件94件130人,其中就有80.85%的案件运用了诱惑侦查手段。但要指出的是,实践中通行的做法并非就当然地在合法性上不存在问题。笔者认为,诱或侦查从实体法上看,违反了罪责自负的原则;从程序法上看,违反了侦查手段法定的原则,违反了刑诉法规定的追究犯罪的程序和步骤。
一、从实体法上分析
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法律,其三大基本原则是:罪刑法定;罪责自负;罪刑相当。在本文的讨论中,主要涉及罪责自负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是,任何人只对自己行为导致的危害社会的后果负责,并承担因此而依法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不对他人的犯罪行为负责;也不能要求他人替自己承担罪责。一句话,刑法只能要求行为人对自己能够控制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负责。基于此,刑法对胁从犯规定了较一般犯罪为轻的刑罚。这是因为,胁从犯罪,从犯意的产生到行为的实施,行为人均处于被胁迫、挟持的地位,危害后果的产生,不完全是行为人行为的结果,其中搀杂了胁迫者的推动因素。与之相比较,诱惑侦查的情形又如何呢?先看两个例子:
案例一:王某是某钢铁厂库管员,其少时好友白某为一盗窃团伙头目。一日,白某找到王某,要求王某在夜间当班时行行方便,让其“弟兄”从库房拉些钢筋去卖。王某碍于情面,推脱不过答应了。后来又恐自己受法律追究,向保卫部门报告了此事。在公安机关安排下,王某假意配合盗窃行为,公安机关则全程监控整个盗窃过程,在该盗窃团伙销赃时,将其人赃并获,并以此为突破口,破获了该团伙作下的十几起案件,打掉一个销赃专业团伙。
案例二:吸毒人员李某(系公安机关的反毒“特情”)找另一名吸毒人员张某,称欲向其高价购买毒品海洛因30克,尽管张某从未有过贩毒行为,但在暴利诱惑下,铤而走险,从他人手中购来海洛因20克卖与李某。张某因贩卖毒品罪(未遂)获刑十年。
上述两个案例在实践中并非是极端的例子,二者均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在案例一中,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并不十分明显,他们只是在暗中静观事态发展,未人为干预盗窃行为过程。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库管员王某的“配合”,该盗窃恐难实施,而王某的“配合”又是公安机关授意所为。因此,如果不考虑排除王某“参与”犯罪的程度和所起作用,要求白某等人承担全部责任恐非完全公平合理。在案例二中,如果不是“特情”李某主动的暴利引诱,很难想象从未贩过毒的张某会以身试法。此案中,诱惑侦查的作用被发挥到了极致:从犯意产生到交易过程的安排,都离不开“特情”甚或说是公安机关的作用。法院判决张某承担刑事责任的公正性因此遭到公众的质疑。
以上分析说明:诱惑侦查,由于主动权掌握在公安机关手中,它可以决定案件发展的方向和程度,可以决定行为人犯罪情节的轻重。这就使这种侦查手段从根本上违反了这样一个法理:侦查机关只应对已然的犯罪进行侦查,而不能制造犯罪、诱人犯罪;其根本的任务是制止犯罪,而不是坐视犯罪发生后再惩罚犯罪人。
有论者将诱惑侦查划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认为前者只是使被诱惑者已有的犯罪意图及倾向暴露出来,或者只是强化其固有的犯罪倾向,促使其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如案例一),因而是合法的侦查行为;后者是对原无犯罪倾向的人实施诱惑,引诱其形成犯意,并促使其付诸实施(如案例二),因而是非法的。(注:龙宗智:“诱惑侦查:在合法与非法之间”,载《检察日报》2000年1月20日,第3版)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妥当。姑且不说这种两分法存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难以涵盖形形色色的诱惑侦查情形的弊端,更重要的是,为犯罪提供机会与引诱产生犯意二者相较,均缺乏正当性。后者之非正当性自无争议,为犯罪提供机会,使本可被制止于萌芽状态的犯罪发生又何来其正当性?这种划分的另一个缺陷时,难以解决犯意是“暴露”还是“产生”的证明问题。
二、从程序法上分析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因此,侦查手段就是除强制措施以外的进行案件调查的方法。在司法实践和学术研究领域,人们强调的比较多的是罪刑法定,诉讼程序中的强制措施法定也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对侦查手段的法定却重视不够,这也是诱惑侦查等所谓的侦查手段被大量使用,而无人探究其合法性的原因。事实上,刑诉法已分别用专节对可以依法采用的侦查手段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它们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至于技术侦察措施,根据国家安全法的规定,只能由国家安全机关采取,且须经过严格的审批手段;采用测谎仪也可视为一种侦查手段,但这种手段在我国尚处于摸索试点阶段,并未由立法加以肯定和全面铺开。惟独诱惑侦查,其使用已呈普遍态势,其侦查结果均得到了公诉机关、审判机关的认可,获得了普遍认同。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司法机关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未曾意识到自己正在使用着非法(法律未规定)的方法与犯罪作斗争。
在刑事诉讼领域,强制措施法定与侦查手段法定同等重要,这不仅是保障人权的需要,也是确保办案质量的需要。我们难以想像,不受制约、节制的侦查权不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不会制造冤案、错案。人类社会的现代法制文明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警察办案也必须遵循严格的操作规程,对严重违反者可作“合法诉讼之抗辩”。从法庭公正审判的角度看,作为判决的基础和依据的事实,是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质证、认证以后确认的事实,是符合“法律真实”的事实。把它与侦查手段法定结合起来,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保障人权外,程序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保证实体真实、准确。在司法上应当树立的观念是,违反程序规定必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如刑讯逼供,并不必然冤枉好人。但我们应当像抛弃沿用几十年的刑讯逼供一样,抛弃诱惑侦查,其道理是一样的。
诱惑侦查之非法性正表现在违反了刑诉法先有犯罪事实,后有立案侦查,然后才是侦查手段的运用的规定。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犯罪事实是已经发生而后被发现,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然而实践中采用诱惑侦查并未遵循这一条规定。大量的案件恰好相反,是先有诱惑,后有犯罪,再有侦查;有的甚至是诱惑实施犯罪与侦查同时进行,或者说诱惑实施犯罪就是侦查手段如案例二。其违法性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特情”对本无犯罪倾向的人引诱犯罪,与教唆犯罪有类似之处;二是侦查机关违背先有犯罪事实后立案侦查的程序规定,凭空启动侦查程序。
作为一种司法力量,侦查权与审判权一样均具有被动性,这种被动性的特征对于审判权而言,决定了法官或者法庭只能等案上门,居中裁断,而不能主动挖掘案源,挑起讼争;对于侦查权而言,其启用必须是已发现了犯罪行为或犯罪结果,即侦查机关只能制止和追究正在进行中或者已然的犯罪,而不能凭想象和猜测去侦破案件,追究犯罪。对于警察言之,这种被动性或可称之为保守性。而司法权(包括侦查权)的保守性,是人类社会法制文明的成果之一,反映了警察国家与法治国家的一大区别。正如有学者指出,法治中隐含的是一种消极的政治观(注:刘军宁:“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权力能力”,载《读书》1994年第5期。),“既然法律本身包含着产生专横权力的巨大危险,那么,法治的使命就是把法律中专横权力之恶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而法律所要避免的恶只能是法律本身所造成的恶,可见在止恶的方式上,法治采用的是守株待兔,而非主动出击的战略。”(注:董郁玉等著:《政治中国》,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253页。)应当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下,这一描述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和行使侦查权也是适用的。
另外,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实践中绝大部分诱惑侦查则违背了该条,属于以引诱的方法收集证据。但要指出,该条的规定并不能完全涵盖诱惑侦查,尚需完善有关立法对其加以规制。
三、规制诱惑侦查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诱惑侦查目前没有法律依据,基本上属于违法行为,应予严格规范。但正如前述,诱惑侦查的情形非常复杂,各具体情形在合法性问题上表现程度又各不相同,简单地一概否定或者一律肯定之,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和做法。鉴于目前同毒品犯罪、假币犯罪斗争的严峻形势,以及诱惑侦查在追究犯罪上的功效,应当对其区分具体情形分别加以规范。
笔者认为,对如下两种情形的诱惑侦查应予禁止:
第一,诱惑犯罪。诱惑侦查中违法程序最为严重的莫过于此,应予严厉禁止,并通过立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对被引诱者则适用“合法诉讼之抗辩”,免除其刑事责任。
第二,为搜集证据。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刑诉法第四十三条,应予禁止,违反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
对以下两种情形的诱惑侦查原则上允许,但要通过立法规定适用的条件和程序:
第一,为寻找犯罪人。这种做法的前提是已经有犯罪事实存在,诱惑侦查的目的只是为了确认犯罪嫌疑人,寻找到承担责任的主体,既不是诱导犯罪,也不以引诱的方法搜集证据。如为破获系列强奸案,侦查员化装为过路妇女出现在现场,引诱犯罪人现身,即属此类。
第二,为破获职业犯罪团伙。如为破获职业贩毒集团,在其寻找买主时,侦查员冒充买主与其交易。这种做法分两种情况,如果侦查员主动找到犯罪人要求交易的,属诱导犯罪,为非法;如果侦察员只是被动迎合犯罪人的要求的,为合法。
规制诱惑侦查,还要严格掌握“特情”的使用,要严禁“特情”诱人犯罪;其作用只应限于向侦查机关传递有关犯罪的信息,不能挑动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