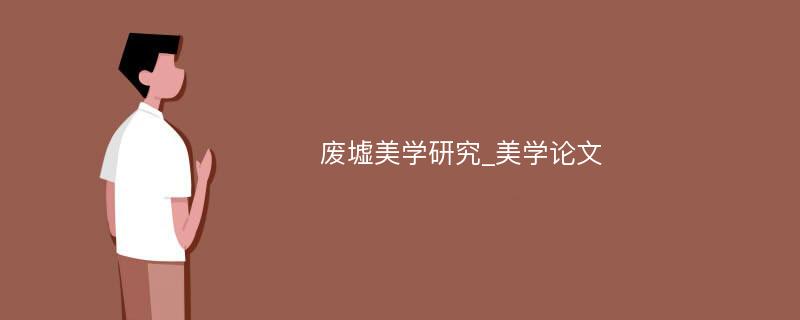
废墟美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废墟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4)09-0070-04 梅内纳·威内斯在《令人着迷的物》一文中写道:“任何社会变革都会通过其中人与物关系的变化而昭显出来。”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显然,通过对腐败的事物、死亡的事物、无用的事物,以及日常生活中一切的废弃物与人的关系进行考察,我们都可以寻找到社会运行的秘密踪迹。对于这些废墟或垃圾,我们倘若给予积极而富于哲学意义的思考,甚至给予热情的审美关注,我们可能会获得一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图像。罗科1635年在《论丑》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自然界里,最丑的事物是腐败、死的东西、饥荒、贫穷等等。……这些,你如果仔细地看,其实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物。”他同时接着说:“腐败是一种丧失,但也赋予每个新时代、赋予太阳底下的一切以生命……”[1]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安迪·沃霍尔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他说,如果你尝试着改变你的品位,那么即使是剩余物,在本质上也是美的。的确,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审美价值,关键在于你是否具有一副审美胸襟。如果你的审美观念是独特的,那么,即使是废墟或垃圾,也可能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审美存在。废墟美学,顾名思义,就是对废墟或垃圾进行审美鉴赏或审美判断的美学。 目前,随着现代社会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剧,废墟或垃圾的问题得到越来越有力的凸显。关于其审美关注也不断增加,在摄影、绘画、装置艺术、大地艺术等一些艺术领域,废墟不断成为艺术家思考和表现的对象。但与此相关的美学理论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关于废墟美学的思考甚至是阙如的。学者巫鸿在谈及研究视觉艺术中废墟的价值时,曾深情地说道,对“废墟”的研究,“不仅希望辨识出废墟的一个地域性另类历史,更关键的是要承认不同文化和艺术传统中关于废墟的异质性观念和特殊再现模式的存在”[2]。 巫鸿说得没错,对中西不同文化视域中的人们关于废墟或垃圾的美学态度进行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通过史性梳理,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废墟美学建立的动态历史过程,而且通过比较两种不同文化对待废墟的美学态度,可以发现它们关于废墟的异质性理解。 在谈及中国传统文化对待废墟的审美情感时,最好是先尝试着和西方传统文化对废墟和垃圾的态度做一横向比较。 总体上说,西方传统文化对待废墟的审美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人们往往把废墟同丑陋、瘟疫、恐怖、死亡等否定性因素联系在一起。奥吉亚斯牛圈也许是西方最臭名昭著的肮脏地方了,它30年未曾打扫,肮脏不堪。英雄赫拉克勒斯的英雄功绩之一就是引阿尔裴斯河和珀涅俄斯河的河水把它冲洗干净。由此可见西方人对待废墟和垃圾的基本态度。西方文化中的地狱名声也好不到哪里去,据文献记载,那里纯粹是一个充满了硫磺、烈焰和垃圾的恐怖场所,这一点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但丁的《神曲》中即可看出。西方至少至18世纪、19世纪,才开始对废墟进行审美关注,之前对垃圾和废墟的态度一直是否定的,除了偶尔对一些著名的废墟如古罗马竞技场等发出一些历史的叹惋外,其他废墟和垃圾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几乎是无价值的,甚至应该是被摒弃的。 中国传统文化对待废墟和垃圾的态度与西方显然不同。面对荒芜的历史废墟,中国人油然而生一种深沉的历史悲怆,并时时有一种时光不再、天命无常的惶恐感。这一点确切地反映出中国人独特的时间美学观念。“易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中国哲学由于相信气本体论,认为阴阳二气氤氲不已、周流六虚,万物由此皆变动不居,因此信仰变化,缺少柏拉图式的永恒理念。由物事变迁,很容易滋生一种难抑的悲怆情感。特别是在面对历史废墟时,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黍离之感。面对殷商故墟,周公在《尚书·酒诰》等文中,一再追述殷商灭亡的原因,认为正是其苛政、滥酒、沉湎美色、亲近佞人等致其覆灭。周公的这种黍离之感影响后世至深,在《诗经·黍离》中,诗人更是直接发出了“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的感慨。此后,描写黍离之感便成为中国文人面对历史废墟时自然表现的主题,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刘禹锡的《乌衣巷》、杜甫的《春望》等在根本上都是对一种黍离之情的直接书写。 如果说,中国人面对历史废墟容易滋生一种黍离之感主要基于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美学观念以及与生俱来的史性意识及忧患精神,特别是基于儒家文化那种深切的道德关怀和政治意识的话,那么,对自然废墟的欣赏则主要受道家文化和禅宗文化的影响。 道家文化对卑微无用之物表现了极度的尊崇。老子在《道德经》中,多次表达自己对卑微、破敝、枉曲、黑辱、雌柔等边缘性事物的崇仰。在《道德经》第二十八章中,他曾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老子这里所说的“雌”“辱”“黑”等事物,说到底,都是一些被主流价值极力排斥的边缘之物。虽然是些边缘无用之物,但在老子看来,却具有无往不克的价值功能。 后来的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子关于卑微事物的论断,直接提出了“无用之用”的思想。比如在论说臃肿的社树、不鸣之鹅、形残之人时,庄子都指出了无用之用的价值。虽然庄子作为通达至人,并不泥执于无用之谈,从而提出了“可不可”“然不然”的主张,但他的基本思想指向是趋向于“不可之可”“不然之然”的。特别是庄子关于畸人形残德全的赞美,基本上可以认为他是把残缺、无用、卑微等作为更有优势价值的,他甚至认为大道若缺、大道若闷。道家文化关于残缺无用事物的思考,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受其影响,在诗文绘画中,枯藤老树、古道西风、荒山寒水、残碑断碣等成了艺术表达的重要意象。 禅宗文化对中国废墟美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禅宗文化的法性论思想,即“无相为体”“诸法空相”的观念,特别是其“实相无相”“无相而无不相”的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世界万有,皆不过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不要说荒芜衰敝之物,即使是繁华物象最终亦不过一场梦影而已。基于禅宗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文化态度一般都较为萧瑟寂寞。表现在艺术上,一般偏重于对了无生意、荒寂无聊之事物的表现。但是正像宗白华所言,正是在这一萧瑟荒寒的景象中,潜藏着一团热烈的宇宙生气。 西方的废墟美学滥觞于18、19世纪。这个时期,随着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崛起,西方人开始对历史废墟进行感伤的凝视与吟唱。对此,艺术史学家保罗·祖克(Paul Zueker)曾说道:“我们这个时代有关废墟的流行观念都是18、19世纪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霍勒斯·沃皮尔(Horace Walpole)等人的浪漫主义的产物。”[2] 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工业社会日益取代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的商品也不断占据社会的重要位置。在这样一个历史过渡时代,怀着对已逝时代的眷恋,在19世纪的西方城市如巴黎、柏林等地,出现了一些经常漫步街头的“浪荡子”。“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波德莱尔、宏大“拱廊计划”的写作者本雅明,都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著名的“浪荡子”形象。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美学特征,就是借助蒙太奇的艺术手法,不断地从城市废墟中寻找人类曾经的光荣与梦想,以期从现代性的空间维度透视人的生存状态。 就波德莱尔而言,他的美学真可被称为废墟美学。波德莱尔关于美的理解不仅仅是建基于其关于艺术的具体阐释上,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其对城市废墟或垃圾的“惊颤”性发现上。在《恶之花》中,波德莱尔像一个厌倦人生的流浪者,盲目而有兴味地穿梭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窥视着这个城市颓败和死亡的秘密,以此来挖掘隐藏在其中的美的力量。在《恶之花》中,腐尸、瓦砾、墓地、破钟、烟斗、喷泉以及衣衫褴褛的妓女、醉汉等都成了诗人念念不忘的表达主题。 在为《恶之花》写就的序言中,波德莱尔曾这样表达自己关于美的认知,他说:“什么是诗?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和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发现“恶之美”,是波德莱尔对于美学史的贡献。波德莱尔认为,恶本身就是一种美,恶之中存在美的根源。波德莱尔的这种美学观明显具有阶级色彩,是他对底层民众生活经验的深切同情。基于此,波德莱尔提出,美并不仅仅与愉快相联系,相反,美更多地和忧郁及不幸相联系。他甚至说:“愉快是美的最庸俗的饰物,而忧郁才可以说是它的最光辉的伴侣,以至于我几乎设想不出(难道我的头脑是一面魔镜吗?)一种美是不包含不幸的。”在《火箭》中他还大胆宣言:“我发现了美的定义,我的美的定义。那是某种热烈的、忧郁的东西,其中有些茫然、可供猜测的东西。……神秘、悔恨也是美的特点。”[3]波德莱尔的美学充满了悲剧色彩,他对城市废墟景象的描写及对拥挤人群的震惊体验都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本雅明。 如果说波德莱尔是一个城市“拾垃圾者”形象,因为他“在大都会聚敛每日的垃圾,任何被这个大城市扔掉、丢失、被它鄙弃、被它踩在脚下碾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搜集起来”(本雅明语),那么本雅明就是一个“收藏者”形象。本雅明严格继承了波德莱尔的思想遗风,他充分展示了自己与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内在紧密关系,以一种奇特的眼光搜寻着这个城市已被遗忘的物质碎片,表达着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在宏大的“拱廊计划”中,他乐此不疲地表现着各种历史废墟(垃圾)如西洋景、农贸市场、煤气路灯、明信片、帽徽店、螺旋式台阶等。这些历史遗存或社会衰亡意象作为一个已经消逝了的时代的物质象征,它们的“原真性”在这个以复制技术为主体的社会日渐枯萎。通过对它们的窥视和描写,本雅明表达了内心深处深沉的现代性忧虑及浓厚的古典主义情结。 波德莱尔和本雅明对城市废墟和垃圾的审美观照和艺术书写奠定了西方废墟美学的思想基础,其对于城市生活中废墟和垃圾的惊颤发现和神圣书写,亦成为日后的典范。 在某种意义上说,杜尚亦是一个废墟美学或垃圾美学的追随者。作为法国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尚有力地打破了日常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严格界限。他在艺术创作中经常直接把生活现成品甚至是废弃物贴上标签当作艺术品,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废墟或垃圾的艺术化。比如,杜尚就曾经把废旧的自行车车轮、旧衣架、小便器、旧木门、破布片、废纸张等,作为构筑他的艺术作品的重要元素。其经典作品《手提箱里的盒子》,本质上就是一个垃圾美学的经典呈现,手提箱的外部完全由破旧的碎布片拼合而成,里面则凌乱地堆放着一些旧物什。而《泉》则是直接把一个小便器作为介质当成了艺术品。正像瓦尔特·赫斯所说,杜尚通过现成品艺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在最硬的物质里的狂想”(康定斯基语)。他甚至通过把“两个或多个好像本质上陌生的元素”,置放在一个“对它们也是本质上陌生的平面上”,由此产生出“最强烈的诗意的火焰”[4]。艾柯对这种前卫艺术的批评是深刻的,他说,新写实主义通过“重新发现工业世界的残骸和各种毁坏物件的碎片,拿来组装成新形式”,其“兴趣就是不在于创造任何和谐,而是打破一切秩序和一切正统的感觉模式,寻找能够穿透潜意识深处、穿透物质的原始状态的新感觉形式,最终目标是要暴露当代社会的异化和疏离”[1]。无论如何,杜尚以日常生活中无用的现成品为基质,以视觉的“无所反应”为基准,从而打破了印象派以来绘画的纯粹可视性标准。 以生活中废弃的现成品作为艺术品的重要构件,似乎成了继杜尚之后一些超现实主义者遵循的重要法则。比如在汉诺费尔的希维特儿把磨坊的排泄物聚拢来构成荒谬、意晦的构图。对于另一些人,像阿尔卜,激起迷惑的、被拾来的自然断片(树根、石块)仅仅通过拔根、绝缘、移置,获得一种完全另样的、“超自然的”意义[4]。 后来的装置艺术也深受由杜尚开创的这种现成品艺术的影响,并把它发展到了更极端的地步。苏珊·桑塔格曾说,装置艺术是一种集绘画、拼贴和雕塑等为一体的一种混杂物,它“使用了形形色色、令人发笑、主要为垃圾形态的材料,包括式样各异的盘子、报纸剪贴、玻璃片、机器部件以及艺术家本人的袜子”[5]。即装置艺术往往是把人们已消费过或未消费过的物品直接拿到合适的空间或场域作为表达自己内心或概念性观念的媒材。出于对此类新艺术形式的回应,苏珊·桑塔格呼吁一种与新文化相应的新感受力,这种新感受力要求艺术具有更少的内容,更加关注“形式和风格的快感”。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提及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沃霍尔通过把名人头像、坎贝尔浓汤罐、可口可乐的瓶子等作为自己艺术的主题,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艺术的商业化。在沃霍尔1975年写就的《安迪·沃霍尔的哲学》一书中,他以半是严肃半是诙谐的口吻讲起自己如何利用剩余物或者垃圾的哲学观。他首先承认,“剩余物本质上就是好玩的”,“如果你能拿过来,使它至少变得有趣,那么你的浪费就不像不拿过来那么多”[1]。沃霍尔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在他这里,垃圾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艺术化,而且充分实现了自身的商业化,垃圾、艺术与经济达成三位一体。 当代社会,废墟或者垃圾不仅完成了它的艺术化,而且更实现了自身的生态化。 如今,随着传统工业社会的衰落,后工业社会日渐崛起。然而,工业社会留下的废墟和垃圾如废旧的工厂建筑、旧机器设备设施以及被污染的大地等,却成了当代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一切,成了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当今艺术和审美观念的变迁,人们对废墟和垃圾有了不同的认识。人们发现,通过对废墟或垃圾的生态改造和审美改造,废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可人的艺术品。在西方,较早地利用工业废墟进行风景式园林改造的是1863年建成的巴黎比特·绍蒙公园,它通过对一座废弃的采矿场和垃圾场填埋而建成。 将工业废墟通过生态学和艺术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改造,已经成为西方对工业废墟的基本处理方法。大地艺术亦成为西方处理工业废墟时首选的艺术形式。大地艺术原来选择的艺术场地都是荒凉贫瘠远离人烟的,但后来随着生态观念的介入及艺术观念的改变,大地艺术开始把审美目光转向被废弃的工业废墟。西方著名大地艺术家史密森(Roberts Smithson)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提出“大地艺术最好的场所,是那些被工业和盲目的城市化所破坏的、或是被自然自身毁坏的场所,认为艺术可以成为调和生态学和工业学的一种资源”[6]。 西方对待工业废墟及生活垃圾的这种审美态度及艺术化处理方法很具有理论启示意义,通过将废墟生态化、艺术化,废墟最终超越了它的原始意义,变得富有美学内涵。西方废墟也由此完成了它在审美中的三次裂变:否定化——审美化——生态化和艺术化。 中国人对于废墟的美学态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变。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达达艺术、波普艺术、装置艺术及极简主义等艺术思潮的涌入,中国人开始转变原来的废墟美学观,重新审视日常生活及工业中的废墟和垃圾,并对之进行审美化、艺术化的表现和处理。近年,随着生态学思想的普及,人们开始以生态学和艺术学的眼光来对工业废墟及垃圾进行审美处理,大地艺术随之而起。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废墟必须提及,这就是巫鸿先生所说的战争废墟,如圆明园等。战争废墟不仅仅是一种审美对象,它更是一种历史文化记忆,需要人们永远铭记。 废墟是一种历史,是一种记忆,更是一种艺术,一种关于未来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