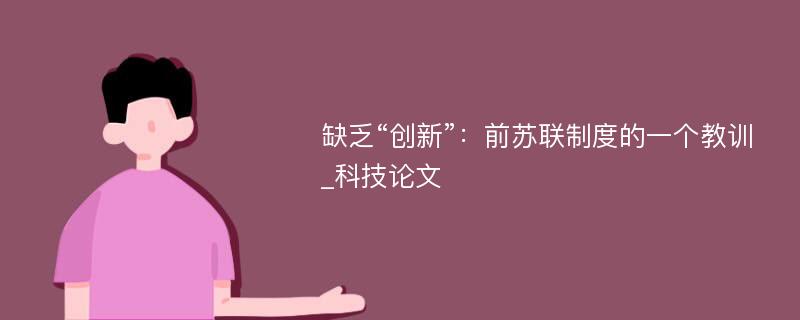
“创新”缺失:前苏联体制的一个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苏联论文,缺失论文,教训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1
20世纪以来,熊彼特(J.A.Schumpeter)率先提出,现代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的企业家,他们的创新意识和活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主要因素是科技的进步,而不是有形资本和劳力投入的增长(阿勃雷莫维茨,M.Abramovitz、索洛,R.Solow);现代经济增长的实际过程是创新迅速增加了技术和社会知识的存量,它们被广泛和有效地加以利用(库兹尼茨,S.Kuznets); 知识进步是单位投入的产出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丹尼森,E.F.Denison)……。这些看法, 都印证了马克思指出的,现代大工业的效率主要“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
在熊彼特提出“创新”(innovation)概念的时候,西方国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5—20%,1960年代,这个比例上升到50%, 80年代,达到60—80%,1990年代以后,甚至逼近了85%。财富主要来自智力的开发,来自有组织的研究和开发(R&D)活动, 科技创新愈来愈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所谓“创新”(innovation),就是个体性质的发明走向市场,并获得社会认可的过程,它包括新设想、研究开发、中试、产业化、市场价值实现和扩散等一系列环节。一般说来,科技创新的社会化途径包括:一是建立维护创新者优先权益的制度,“技术进步率的提高既缘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出自发明者具有获取他们发明收益的较大份额的可能性”〔2〕。二是通过国家采购开辟创新产品的最初市场, 减小创新产品的市场不确定性。三是军事科技的溢出(Spin-off)效应, 在和平时期大规模地转向民用领域。
战后很长一段时期,美苏争霸的基本格局导致了它们由国家权威主导的,具有强烈军事色彩的创新体制。这种体制尽管为谋求战略优势提供了卓有成效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它主要为军事目的服务,由于军事科技往往涉及国家安全,其扩散关山重重;因此,这种科技创新所面对的是非常有限的军用市场,而任何创新如果没有广阔的市场是很难实现其真正价值的,也就是说,军事科技如果不能成功地转向民用必然“大材小用”。
事实上,
成功的“军转民”(transform military into civil )模式及其创新体制转换正是日后大国夺取科技—经济主动权的关键。
美国政府在战后大力介入军事科技的R&D活动, 但也有意引导军事科技向民用领域的溢出,典型的如核技术之于原子能利用、火箭技术之于航空航天开发、电子信息技术之于计算机开发,这些“溢出”效应大大节约了有关民用科技创新的成本,缩短了研发周期。美国一些大公司(如通用电器、 杜邦、 贝尔、 AT&T )所采用的“工业实验室”(industrial laboratory,德国人19世纪末创建)数目激增,1970 年代中期已增至15,000个,是战前的5倍。 工业有组织的研究和开发是一个重要的创新〔3〕,美国企业的R&D投资逐渐扩大(近年来甚至超过了资本的投资),创新“被归入美国企业的最核心部分。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科学研究实验室里的成就现在已成为企业决策者制定最重要决定时的必要组成部分”〔4〕。不过在1970年代以前, 由于被军事科技的溢出效应所掩盖,这种创新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
1970年代中期,冷战开始降温,军备需求急剧收缩;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日本、西欧咄咄逼人的竞争,美国企业加快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并掀起了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在这个浪潮中,军用和民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通用的高科技产业化逐渐成为美国经济最耀眼的增长点,并造就出一批高科技产业巨人。1980年代,美国企业的R&D投入开始超过联邦政府的投入(1997年,企业投入5.1%的增长率甚至超过联邦政府投入4.2%的增长率近1个百分点)。
1993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当年成立“国家科技委员会”(NSTC,总统、副总统任正副主席),并提出本世纪末将R&D投资从占GDP的2.6%提高到3%;将政府对民用科技与军用科技的R&D资助比由40∶60调整到50∶50。同年,中止了施行10年的“星球大战计划”(即“战略防御计划”,SDI), 启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即“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II;继而又推出“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CII)。美政府接连发表《为了国家利益发展科学》(1994)和《为了国家利益发展技术》(1996)的报告,强调为科技发展创造一个“促进创新和竞争的环境”,把“促进民用技术的开发、利用和商业化”列为首要战略目标。这些报告不仅明确了国家创新目标,而且阐发了面临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政策,特别重视发展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之间,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共同推进科技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伙伴关系;而政府既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制订者,也是这个体系参与相互作用的合作者。
近年来,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 高科技的扩展效应使得美国经济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2
曾几何时,为了与美国争夺霸权,苏联(前苏联,下同)也被拖进一轮又一轮的军备竞赛中去,苏联政府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动用大量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军工企业有职工500—800万,产值甚至超过了民用工业产值),国家预算的科研经费有3/4用于军事科技领域。苏联的R&D经费占GNP 比重从1960 年代后期起就超过了美国(1980年代中后期,达到4—5%,但其GNP只有美国的一半), 全苏科学家和工程师最高时有150万人,占世界总数的1/4。
苏联的R&D投入巨大, 在军事和宇宙开发领域的科技水平可与美国分庭抗礼,他们体制的种种缺陷也被其军事超级大国的面貌所掩盖。实际上,“由于绝大多数科研经费投入军事领域,由于大量科研成果被封闭于军事部门,由于部分被转为民用的科研成果也要耗费转移的时间和成本,因此,苏联科研投资的效益很低。”〔5〕军事领域以外, 苏联科技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分属科学院系统、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它们各自为政,彼此隔离,经费结构也不合理(1987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者比例为12.8∶60.3∶26.9,美国为12.1∶21.1∶66.7〔6〕,开发能力明显落后)。 科技创新(苏联的提法是“科技进步”,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иПрогресс)的各个环节被割裂,从科研、设计、试验,到真正投产往往已经过时了(平均周期10—12年;美国为5年,日本为3年)。如果说这种现象在冷战形势下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愈到后来,它就愈变得不合时宜了。
问题在于,苏联“大多数科学研究所对科研工作中获取尽可能大的效益没有物质上的利害关系”〔7〕,它们完全依赖于国家订单, 不关心,也不屑关心市场变化。而企业缺乏自主经营的运行机制,没有竞争压力,也就几乎谈不上进行创新的活力和动力;“企业从科学研究所那里得到的只是资料,而为了采用新发明,企业必须具有相应的干部,用于改建的财政资金,计划重新调配的后备资源,而重要的是必须具有对随着技术创新而来的生产改造的责任心”〔8〕。 创新往往意味着改变习以为常的工作节奏和设施,还要冒完不成生产指标的风险,而以产值衡量业绩的计划体制使得企业宁愿沿袭传统方式行事,“这种体制与试验、创新是格格不入的”〔9〕。
苏联国民经济几十年一贯制以粗放型为主,追求“重”、“大”、“产量”,经济增长中粗放因素占了2/3以上,1970年代以后甚至达到3/4。由于集约因素,包括创新能力比较弱,导致设备老化(工业设备更新率不到3%)、技术落后(除军事领域外, 平均落后于西方国家10—15年),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巨大(苏联的单位产量石油消耗比美国多1倍、钢消耗多70%、水泥消耗多1.4倍),投资回报率低,回收期限愈来愈延长。苏联经济集约因素弱小突出地表现在,企业的R&D 经费和科技人员均只占全苏R&D经费和科技人员总数的4%〔10〕,这显然与他们庞大的科技能力很不相称。
1970年代以后,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苏联模式再也创造不出1950—60年代的辉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1980年代比1960年代下降了4个百分点)。 当西方国家将电子信息技术迅速扩散到民用领域之时,苏联仍然把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稍逊一筹的此类技术限制在军用范围内(这里恐怕还有思想控制的原因)……。1980年代后期,他们在高科技领域的劣势已经很明显(20个关键技术有8个全面落后,9个大体落后),计算机发展水平只有美国的15.2%,生物工程只有14.6%,新材料只有46.8%……〔11〕。
苏联当局不是没有看到这些问题,他们也感受到新技术革命的压力,并提出一些应对性的改革方案,如下达新技术研制的计划指标,制定《科技进步综合纲要》和数以百计的专项纲要,建立(部门的)科学生产联合公司、跨部门的科技综合体、(以大学为主的)科研生产联合体等等,但这些方案要么因为创新的非市场性,而无法兑现,要么因为“拉郎配”,而成效甚微。真正的科技—经济体制改革付诸阙如,“领导人所期望的只是一个较‘圆滑平稳’的、充满美好词藻的宣传品,而根本不是一场激进的经济改革。他们需要的,充其量只是这样一个文件:带有一些技术治国论色彩,能较为领导人所明了,并能在科技发展问题上为他们规定出一些‘组织措施’来。”〔12〕他们在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市场取向和企业主体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不敢动作,而总是朝着完善计划体制方向搞改革,结果越改体制越僵硬、越落后。
冷战时期,靠奉行“要大炮不要黄油”政策支撑起来的苏联军事力量确实可与美国相抗衡,但它同时也拖跨了国民经济,苏联在军事上最强大的时期, 也是国民经济最不堪重负的时期(苏联军事开支长期占GNP的8—10%,是官方数字的3—6倍)。特别是世界形势一旦发生了有利于和平方面的变化,苏联体制的深刻弊病就暴露出来了,“在苏联的经济制度中,‘发明’根本不能为其所用,而且也不会用在与‘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完全呈对比的民间经济之上(所有发明之中,只有1/3在经济领域内找到应用途径。即使如此,进一步的普及推广也极少)。”〔13〕他们没有找到“军转民”的有效途径,许多发明无法进入市场,科技优势难以形成真正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80年代,苏联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只有美国的55%和20—25%,1987年,其GNP被日本超过,以后更是每况愈下。
计划体制可以依靠行政命令,动员各种资源进行集中投入,在某些领域取得某种优势,但它面对新技术革命,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和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就显得无所适从了。苏联体制的迟钝表现并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因为高度集中和指令性计划淹没了创新的主动性和进取心;决策层没有看到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革命性意义,仍然迷信机器制造业的主导地位;部门垄断、条块分割造成的本位主义和相互隔绝,妨碍了创新的社会化及其扩散(特别是军事科技的扩散)和经济增长向集约方式的转变。结果,“世界发达国家在70年代完成了这一转变,而他们却错过了这种转变,原地踏步不前,这个失误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致命的影响。”〔14〕
从根本上说,计划体制(而非R&D 活动本身的计划)抑制了科学的本性,偏离了创新的发展轨迹,“科学有其自身特有的一套价值,有其自身特殊类型的社会组织,有其自身独一无二的发现与发明过程。”〔15〕“计划的”创新是不可思议的。更有甚者,这个体制还“培养”出一个学阀—官僚阶层,他们在其中占据了有利位置,形成了一个个小圈子;为了维护与旧体制联系在一起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他们对任何改革措施均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这种态度至少也从上面起到了延误创新的作用〔16〕。更不用说管理体制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泛滥成灾,仅部级、 次部级的科技主管部门就有近百个, 每年耗费在审批科研项目上竟达35万个人(力)时(间)。
苏联当局对由创新引起的组织(体制)变革麻木不仁,甚至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拒斥。至于在科技界,搞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大批判和人身迫害(如对生物遗传学长达20年的批判,对系统论、控制论的批判、对管理科学的批判,株连一批又一批科技人员),设置种种自欺欺人、横加干涉的审查制度,均极大地挫伤了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这就不仅仅是什么啼笑皆非的事情了。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落伍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创新,而苏联科技由于体制僵化和社会化途径阻塞,没有抓住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性机遇。这,至少催化了苏联的灭亡。
3
新技术革命悄悄地改变了大国的力量对比,直至冲垮了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近30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国之间以科技—经济实力为主的综合国力较量代替了为谋取战略优势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掌握和运用高科技的能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从国内条件看,供给方面,可发掘的资源潜力已相当有限,需求方面,短缺经济时代基本结束(买方市场初步形成),从而使得粗放型经济已经没有多大可扩张的空间;从国际条件看,发达国家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的产业调整带动了世界性产业结构的大改组,高新技术产业正逐渐取代传统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y-based economy)或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也就是说,国内国际这两个条件都对我们的科技—经济现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我们过去的科技体制基本上沿袭了苏联那一套,这种体制的主要弊端是科技和经济相脱节,经济发展得不到科技创新的推动,而创新活动又缺乏有力的经济支持。至今仍然表现为:一、科技投入不足,我国的R&D投入与GDP之比一直偏低,没有超过0.7%(世界平均为1.4%,发达国家达到2.2—2.7%),人均R&D经费仅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5;二、科技产出不高,我国每十万人的科技论文/专利申请数只有2.2 篇/5.6件(发达国家一般在100篇/件以上),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40%之间(相当于发达国家40年代的水平);三、创新能力不够,我国的技术引进费用比R&D经费高得多, 在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国际科技竞争中处于明显弱势,高新技术产业对GDP的贡献仅为5%左右(发达国家均在20%以上);四、技术储备不强,主要表现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结构分布不合理(经费比例6∶28∶66, 合理比例大致为15∶25∶60)。
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内在的联动性。创新作为现代经济社会的一个内生变量,只有在合适的体制中才能发挥有效作用,具体而言,创新的行为主体应遍布于社会的基本单位,主要是企业中(因为创新乃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必须通过市场来实现,企业的作用是其它社会组织无法替代的)。但在计划体制下,企业只是一个生产单位,既缺乏创新的动力,也缺乏创新的实力;体制改革必须使企业真正成为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真正成为创新投入、研究和开发、科研成果转化和创新利益分配的主体。“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17〕
相反,体制缺失,或沿用旧体制就会阻碍创新。“如果要使科学可以充分地为社会服务,就必须进行变革,而且必须进行相当激烈的变革……如果没有这些变革,即使能在科学上作一些小小的改进,纠正某些弊端,也不能使效率低下的、浪费的和令人沮丧的制度产生根本变化。”〔18〕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不仅在微观层面上代表企业争取市场主动的行为,而且在宏观层面上也显现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创新又是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关键;并日益成为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
我国正经历由传统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时期,还有许多影响创新的不确定性,如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权益分配的不确定性、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因此,国家(政府)的作用及其导向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这种作用和导向主要表现在:一是完善并运用市场机制,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二是组织和协调创新系统中各部门各环节功能的相互关系;三是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目标,并引导各方面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归根结底,是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环境。
收稿日期:1999—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