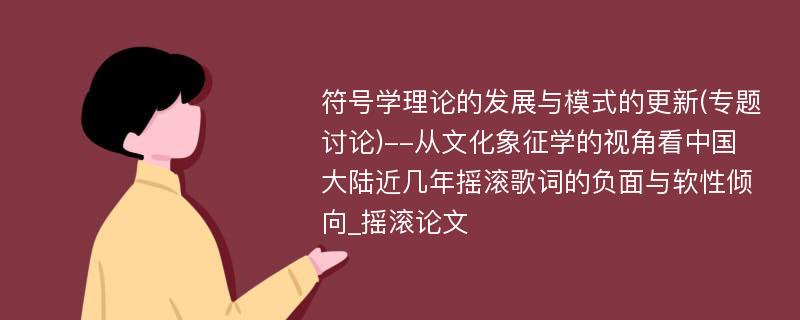
符号学理论发展与模式更新研究(专题讨论)——从文化符号学看近年大陆摇滚歌词的阴柔化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学论文,专题讨论论文,阴柔论文,符号论文,摇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摇滚是流行歌曲一种特殊的体裁。体裁(genre又译为“文类”),其最大作用,是指示接收者应当如何解释眼前的符号文本,引起读者特定的“注意类型”(type d’attention)或“阅读态度”(attitude de lecture)。正如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在《结构诗学》一书中提出读者对诗的期待一样,人们对摇滚歌也有一种与其他歌曲不一样的“诗性”期待。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摇滚,与美国“垮掉的一代”诗歌,有着共通的精神取向。金斯堡等人强调诗的自由发挥、自我解放等反抗理念,在摇滚中都得到精神上的应和:从最早的摇滚乐以及后来的变体,例如重金属、哥特摇滚、后朋克等,都是以对抗文化体制为主调。摇滚从起源到发展,都有强烈的“雄性”特征,其音乐与歌词都以激昂狂放、张扬个性为主调。
歌词是摇滚歌曲的核心,是摇滚歌曲意义最显露的载体。许多杰出的摇滚歌手都与一般流行歌手不一样,自己作歌作词,因而被称为“摇滚诗人”,摇滚歌词因而被称为“摇滚诗”。电影符号学家克里斯汀·麦茨指出,电影中一部分代码可以称为“社会—文化代码”,它们会超越电影,进入它从中得以产生的、更广大的社会—文化语境,比如服装、面部表情等。但是还有一些代码是电影独有的,比如长镜头、特写镜头以及电影特殊的编辑技巧等。摇滚歌曲也有两套符号代码,一种是和社会语境相通的文化代码,例如最基本的男性姿态、男性措辞;另一种是歌曲这种特殊的艺术文类所采用的特殊代码,比如歌曲“我对你唱”的抒情模式,以及歌曲中主体强度在歌词、曲调、演唱、制作中的复杂分配。
在歌的传播过程中,演唱给予歌的文本最突出明显的传播性别标记,演唱者是歌的“肉身面孔”。歌的表意性别的其他标记是分析出来的,但演唱者直接把性别强加在歌上。这种“演唱赋形”是音像录制技术发达的当代社会特有的,历史上并不存在。历史上的歌者基本上没有留下名字,即便有记载也只是记录某歌手曾唱过某位诗人、词人的歌,诗词作者是主导性别元素。进入现代,歌曲一旦经过演唱赋形,后来的演唱者在性别上往往很难更换。
在歌曲的“文本性别”上,摇滚主要是一种“男歌”。摇滚歌和其他流行歌曲一样,其文本性别并不取决于作者的生理性别。在歌的生产传播过程中,词曲作者、演唱者、传唱者等,都参与文本性别建构,但是我们看到大多摇滚是男性词作者、曲作者,写给自己,甚至写给女歌手唱。
从文化符号学上说,符号发出者的意图意义、符号文本意义与文本接收者的读解意义,三者是不同的。具体到文本性别上,歌曲创作者的性别、演唱者的性别、听者理解的性别,可以是三种不同的性别身份[1]。
但是男性摇滚歌手唱的歌却往往由男性词曲作者创作,男性歌手所长,为男性听众所喜爱,其性别身份相当一贯,因此加重了符号性别建构中的男性意义,这也是男性摇滚占主体并形成男性文化的主要原因。
一、性别无意识:80年代的摇滚歌词
歌词是歌曲表意的起点,歌词性别因为歌词表意才出现。歌词性别有个很突出的标志性限定方式,即人称代词。歌曲基本的表达方式是呼与应,“我对你唱”是歌曲最基本的抒情模式,歌词抒情主体与抒情对象的性别规定往往会在文字中直接呈现。
在华语摇滚歌曲中,尽管摇滚歌曲题材广泛,最早也是最多的歌曲依然是情歌。摇滚歌曲哪怕以爱情为主题,与一般情歌也有很大不同,大部分摇滚情歌的歌词只是以爱情为表层意义,写的是超出爱情本身的社会意义。这种文化含义既是文本发送者意图,也是歌众阐释模式,摇滚歌曲的创作者、演唱者以及传唱者等,都知道摇滚特殊的意义期待:它不会只是男女之间的缠缠绵绵的情意倾诉。比如中国大陆摇滚运动的开场歌曲、1986年崔健的《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从歌词的抒情模式中,我们或许还不能完全确定它的文本性别,但仔细赏析,陕北民歌“信天游”的粗犷旋律和摇滚曲式的奇异融合,以及男性粗壮嘶哑声音构建,很快会使歌曲的文本性别朝“男歌”气质倾斜。
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
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没有使一个男人失去爱情,相反,在男人一再强调的道白中,女人似乎还是实现了男人的幻想:一无所有的男人更应该被爱,因为男人的价值在他自身。这首歌隐藏着强烈的男性性别强势。
有论者明确指出:“摇滚建构的王国无疑是一个未受限制的性世界,一个甚至不曾向人类的另一半——女性提供任何理想或范型的男性世界。”甚至说,“摇滚是一种男性化的艺术,男性是摇滚的主体,而女性则只是客体或对象”[2]。实际上,摇滚歌中的抒情对象——女性,都是一个虚指,作为文化性别范畴的“你”(或“她”),并没有固定的、具体的形象,却常常是男性(抒情主体)欲望及幻想主体的投射。类似《一无所有》这样的歌不屑于专注“我与你”的爱情,在爱情背后是一种存在身份定位意义的追问。的确,从80年代中期诞生起,摇滚歌曲在中国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总是以一副超越凡俗人世的姿态出现,向着精神的高度飞升,摇滚本身成为对俗世俗事批判的文化符号,它的文化含义被无限放大,它的男性性别特征却被掩盖了。
尽管崔健承认,《一无所有》最初的创作灵感的确是一首情歌,但谁都不再把这首歌作为情歌来解读,青年听众从中听出并唱出他们的抗争意图,批评家则特别强调它的文化颠覆意义。的确,摇滚与一般流行音乐很不相同,它是音乐本身的反叛,也是对被商业浪潮迅速庸俗化的社会文化的抗议。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摇滚并不是超越性别的。摇滚歌词中“我”对“你”的强烈召唤以及不断的反复追问,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男性中心隐喻,透析出歌者内心的焦灼、迷惘、愤怒。这种文化指涉通过象征化的性别欲求得以表现,而这种性别欲求又以女性主体性虚构化为前提。
在这里,正可以用上阿尔都塞提倡的“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阿尔都塞认为文本的清晰话语背后隐藏着意识形态的沉默话语,阅读可以顺着作者的意图在文本层面上阅读,更应该注意文本的空白、沉默、失误、歪曲,看出这些裂隙背后的意识形态真相。阿尔都塞的弟子马歇雷更是强调“症候式阅读”要在作品文本的“字缝”中找出“作品与意识形态与历时之间”的错位运动造成的痕迹,最后看出受意识形态控制的文本掩盖的历史运动[3]。
这种故意模糊性别意识,在文化符号学上也被称为“中项的非标出性偏边”[4],即看上去无性别的歌实际上偏向文化中被标出的“正常”的男性一边,从而给男性标准以“正常”的外衣。
男性标准被认为是社会正常标准,这是女性主义研究者很早发现的问题:宏大叙事代替了女性叙述。但是在摇滚歌曲传播研究中,“倾斜”和“不对称”很少有人讨论,这是因为摇滚歌曲不被质疑的“文化”性质遮盖了性别政治的压迫性,似乎没有饱满充沛的阳刚之气就不配是摇滚。
乐评人金兆钧的这段话味深长:“古老的历史中的瞬间辉煌,在千百年后居然成为了中国摇滚们的精神源泉。中国情绪最终在某个特殊的角度上,给了以反叛而闻名的摇滚乐以潜意识中的沟通。这种执著无疑地带有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也正因此而使摇滚乐获得了一种远比现实的愤怒更为深厚的基础。”[5]
中国摇滚这种表面的“一无所有”,也许并不是一件只能获得文化史无穷赞美的好事。在抗争庸俗的掩护下,绝对的男性主宰,似乎已经成为摇滚的题中应有之义。毕竟,在这首歌的抗议姿态中,女性的“你”是犹豫的,是与浊流站在一起的,是备受责问、需要说服的,最后必须认同面对激流敢于挺身而出的男性主体。
二、90年代摇滚歌词的性别阴柔化转向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变化出现了:崔健摇滚歌曲的转型似乎也意味着大陆整个摇滚歌曲的转型。他的这一首《花房姑娘》很能说明问题。
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
我不知不觉忘记了方向,
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
你不知不觉已和花儿一样
你要我留在这地方,你要我和它们一样,
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噢,不能这样,
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噢,姑娘!
歌词中,抒情主体和歌者性别身份统一都为男性。与最早的《一无所有》相比,抒情对象——“花房姑娘”的女性身份比较具体了,也不再是只配听“我”吼喊抗议的对象。歌曲更像一首情歌,唱出歌者对姑娘的迷恋。但到歌曲的最后,一再反复的嘶喊“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这些模糊的能指“老路”,竭力冲淡情歌意味,努力指向更多的文化隐喻——叛逆,虽然依旧是自身欲望的一个挣扎,更多的则是对当下消费文化的一种抵御,但是阳刚之气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和崔健的《花房姑娘》相比,90年代张楚的《姐姐》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这是一个以男性“我”为叙述主体的男歌,但是阳刚之气被搁在一边,出现强烈的女性依恋。
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
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
他坐在楼梯上也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
噢,姐姐,我想回家
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
噢,姐姐,我想回家
牵着我的手,你不要害怕。
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复杂的叙事性的文本。似是情歌却又不是情歌。围绕着“我”的两个角色,一个是“父亲”,另一个是“姐姐”。前者是曾经对我施暴被我痛恨,而现在苍老得不再是我对手;后者是曾经遭受欺凌,现在却是我渴望且依赖的对象。一般来讲,“父亲”和“母亲”才是一对对称的范畴,歌词中“姐姐”替换了“母亲”实际上是两种文化隐喻。“姐姐”是我呼唤的对象,也是我鼓励和期盼的对象,“牵着我的手,你不要害怕”,是“我”期盼听到的抚慰之声。“姐姐”是男性自我的一个缺失,长大的男人依恋没有长大的无需自己负责的年龄。
这首摇滚最重要的意义是中国摇滚性别色彩的转向。《姐姐》从歌者到歌词甚至到希望,都给摇滚蒙上了一层阴柔的面纱,“姐姐”成了一个拯救者角色,担负起文化拯救的任务。正因为“姐姐”特殊的身份意义,使得评论家对这首特殊的情歌给出不同的解释。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张楚的这首歌毫无摇滚特有的反叛、倔强,只是试图达成与现实的妥协,或者说,试图向现实(姐姐)索取一种略可安慰的疼爱。朱大可的评论很精辟:“这种情歌式的撒娇,成了信仰危机的一种临时解决方案……作为一种幻象,女性在张楚的音乐文本中是一种与现实对峙的纯洁力量,是一种异于创作者自身的拯救的希望。”[6]
在90年代中期,这种女性化是非常稀少的,但是到90年代末,中国的大陆摇滚歌词的阴柔化倾向已经非常明显。许巍的《在别处》:
就在我进入的瞬间,我真想死在你怀里。
我看到我的另一个身体,飘向那遥远的地方。
我的身体在这里,可心它躲在哪里。
歌词写出了现代人内心深刻的分离以及精神世界无处归依的恐惧。表面上它是一首过于直露的情歌,但是歌者软弱、无助的诉说,使阳刚之气在最需要的时候忽然“飘向遥远的地方”。
另一首郑钧作词作曲的《回到拉萨》:
爬过了唐古拉山遇见了雪莲花,
牵着我的手儿我们回到了她的家。
你根本不用担心太多的问题,
她会教你如何找到你自己。
本来在大多数摇滚歌曲中,女性就是一个流动的文化隐喻。“摇滚神话”体系的建立,是以“女性”作为一个欲望对象来确定男性抒情主体的自我文化身份。在这首歌词中,“雪莲花”明显是女性化的一个代称,可能是个叫“雪莲花”的女性,也可能就是承载着异域文化的理想化身。但不可否认,词作者用“她”来描述,将自己放在一个被“引导”的位置(“牵着我的手”),将现代人的压抑、爱情理想和社会憧憬融在一起中,呈现出一个毫不“刚强”的男性形象。这时候,摇滚的男性气质已经消融成一般情歌的萎靡软弱。
三、21世纪初摇滚性别的间隔出现
21世纪初,中国大陆摇滚部分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摇滚情歌化路线,同时还出现了两种特别现象:一是出现性别倾向更加含混的乐队组合、歌曲,例如“二手玫瑰”是一支非常奇特的摇滚乐队,这个全部由东北汉子组成的摇滚乐队,被誉为近年来“中国最妖娆的民族摇滚乐队”。
“二手玫瑰”一出场,它的性别颠覆意义就非常耀眼。很快有评论者特别注意到,“‘二手玫瑰’,这个名字充满性别的暧昧和时间叙事的隐喻,事实上它却是以东北‘二人转’及相关民俗为文化依托的男人乐队的指称。”[7]97
乐队成员都是东北人,他们将东北的民间“二人转”和摇滚融合,创造出很奇异风格,他们的乐风源自东北民间男女对唱调情的“二人转”,在抒情、幽默、戏谑的音乐之中,“依靠他们独特的平民化、大众化、人性化风格,打通了中国摇滚与中国民间艺术的桥梁。”[7]97而在表演上,男歌手经常穿着女性服装,甚至头戴大红花,将自己打扮得过分突出女性化。“二手玫瑰以妖艳和民族味十足著称,乐队将东北二人转的音乐元素与现代摇滚乐嫁接,夸张的表演、朴实戏谑的唱词,再加上民乐的奇幻运用,使观众的视觉和听觉都充满了刺激和震撼。”[8]
“妖艳”、“妖娆”,本是极富女性色彩的词汇,却用到一个男性乐队身上。
在歌词上,这种性别含混表现得更为奇特,比如这首《征婚启事》:
那天我心情实在不高兴啊
找了个大仙我算了一卦
他说我婚姻只有三年的长啊
我那颗爱她的心有点儿慌啊……我做个艺术家我娶个艺术家我嫁个艺术家我回你个艺术家
这时我惊奇的发现我是否怀孕了
歌词中性别混乱,先是男性,又变成女性,然后是男性、女性一起出现,最后却分不清是哪种性别怀孕,而且有意地用语义混乱的措辞:“发现我是否怀孕”。虽然歌词想表达的依然是对失落的理想岁月的怀念,但是语存讥讽。李皖的评论倒是一针见血:这是“对一个答案暧昧的问题的暧昧的怪腔怪调的捉弄”[9]。
但偏偏这样一支自我取消男性气质的乐队,受到文化界高度的赞扬,有人说这些声音“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摇滚乐返回地上重构自身话语功能的希望所在。”[10]或许,这种希望也包含了对性别话语的重构可能。
面对摇滚歌词中男性文本性别特征的模糊和女性的能指缺席,我们可以套用戴锦华对中国电影的批判:“这些渴望与压抑的故事,将典型的男性文化困境移置于女性形象,女人又一次成了男人的假面。”[11]摇滚歌曲就是这样,借重歌曲这种基本的抒情模式,对男性的文化身份做了一种性别位移。
四、阴柔化不是女性化:21世纪初女性摇滚的性别抗争
大陆的女摇滚诗人很早就诞生了。1989年组建的第一支女子摇滚眼镜蛇乐队,以及早期指南针乐队中的罗绮,都是最早一批女性摇滚诗人。但早期的女摇滚诗人走的都是“去性别化”道路,她和男性诗人一样关注社会文化,她们的歌没有特殊的女性色彩,没有鲜明的女性意识抗争。
21世纪初,中国大陆新诞生的一代摇滚女诗人文化姿态很不同。她们似乎顺从社会性别认同,却在文化缝隙中找到了女性对抗策略:阴柔化不是女性化。女性必须有“不同的声音”,要在歌声中揭露出“声音如何在关系中发出,如何依据关系展开或被限制”[12]的性别历史状况,并努力把被塑造的、被建构的声音和女性自己的声音区别开来。应当说这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在摇滚从本来应当有的阳刚之气走向阴柔化时,女性摇滚却脱颖而出,对文化的性别符号公式化压力提出反抗。比如摇滚女诗人姜忻所作的《我不是随便的花朵》就是一个佳例。
在那里我才找到真正的自己
于是我知道自己不是随便的花朵
只为梦幻的声音而绽放
虽然一切就像流水奔腾不复返
那些声音不会枯萎
从文化符号学上看,“花”是关于女性的一个核心“概念比喻”(conceptual metaphor),也就是不限于某种语言表达而可以用各种不同的符号的比喻。自古以来,“花”是一面装扮女人的魔镜,中国女人一直被禁锢在这面魔镜中孤芳自赏或孤影自怜。从古老的民歌开始似乎就有了“花”与女性命运同构的文化投射。比如《茉莉花》,“花”喻女人,“采花”与等着“被采”,奠定了两性关系的基础。中国大量的古典诗词更是对“花”作了渲染铺采。就连李清照这样从男性文化中凸现的女性豪杰,也只是呐喊出“此花不与群花比”,最终也没有挣脱出还是一朵“花”的命运。现代歌词中,尽管词作者多面创新,从不同的角度充分拓展,歌中出现了《海上花》、《水上花》等多种“花”歌,但始终没有打破“花”和女性的同构关系。“花”依然是一种美的象征,甚至女性气质的某种隐喻,对花的赞美,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女性气质的赞扬和保留。“花”的命运似乎成为女性与身居来的命运。
而姜忻这朵“不随便的花”,打破了“花”的几千年定式意义:它是一朵拒绝凋零的花、拒绝既定命运的花,是一朵属于女性“真正的自己”的花,而不是专门被男人摆弄欣赏的花。尽管女歌手还是沿用了“花”的意象,但女性化不是阴柔化,表达了一种以花抗花的现代意识。
另一个女摇滚歌手张浅潜的《另一种情感》也力图表现出一种反抗。歌手似乎有些戏弄文化规约性中代表“男性气质”的“英雄气概”,歌词在嘲讽和赞美之间给了一个模糊答案,结果让男女感情变成了“另一种情感”:不是一般情歌中的声嘶力竭的渴望与怀念,或者是抱怨与责怪,而是女性的独立意识:
昨晚你怎么来到我的梦里面
相对无语陌生又安全
我想赋予你英雄的气概
可它会在哪儿为我真实的存在
张浅潜的歌词具有克里斯蒂娃说的特殊的语言力量,能够发出“语言的内不驱动力……我们可以看到诗的语言经济学,而在这个诗语言经济学中,一元的主题将找不到它的立身之地。”[13]歌词的这种诗性功能是一种拒绝和分裂,它使文化的定式意义分裂和增衍,它破坏单一意指,来演绎艺术的异质性别倾向,导向多元意义,可以说这是语言内在力量对性别文化秩序的报复。
女摇滚歌手同样借助情歌的呼唤话语方式,达到这个边界。主流文化所支持的文化,不可能得力于另一种形式的文化,而只能来自文化本身被压抑的被宰制的力量,来自构成文化所掩蔽的女性性别异质性。
奇怪的是,在社会上女强人辈出的时代,杰出女性在经济上、政治上、学术上迥出伦辈之时,女性在情感上的解放却比经济上社会上地位迟缓得多,感情中的性别定位比社会定位要固定得多。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本身倾向保守。女性解放毕竟只是少数女性中的要求,大部分女性在解放意识上滞后。而大众文化,尤其是流行歌曲,其传播的性别意识迎合大多数人的需要而不是少数女性精英的思想和文化姿态。
我们承认,在娱乐化的今天,“流行文化使女性趋向于妥协,因为流行文化与女性政治态度关系不大,而是女性幻想的领域。”[14]即便如此,摇滚女歌手依然是歌坛上异军突起的一支队伍,她们充分利用“摇滚神话”去践踏这个神话,唱自己的歌,去颠覆很多女性既定的文化陈规。女性摇滚歌手脱颖而出,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只有依靠她们以及女性歌众敏锐的“症候式的阅读”,才能对文化向男性的中项偏离有所纠正。
五、摇滚歌词阴柔化的意义
应当强调的是,歌曲并不能直接“反映”社会现实中的性别关系,而只能很曲折地再现性别政治,因为歌抒写的是社会中人的具体感情和态度,而感情态度并不一定是现实。
从符号修辞学上看,歌词有一种强烈的“褒义倾斜”,题材上不传播社会上认为“不宜”歌唱的内容,歌曲的遣词造句上也倾向于使用褒义词汇。虽然说不出的口的感情往往可以唱出,但歌曲往往并不直接宣泄赤裸裸的欲望。歌词的这种“褒义倾斜”的心理机制,也让歌词阐述者向褒义倾斜。这样,一旦宣诸歌词,文化禁忌相对淡化,歌就成了被社会正常秩序压抑的集体潜意识的宣泄口之一,歌词从而成为分析社会心理传播的材料宝库。
从文化符号学角度,可以看到摇滚作为男性符号,表达的意义越来越暧昧、阴柔化倾向越来越强。一方面,这与当今中国文化中男性扮演的社会角色相对应,当男性不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情愿随波逐流时,80年代摇滚初期的抗争就成为越来越淡漠的记忆;另一方面,它的阴柔化倾向却是一种从既定性别文化语码中解放自己的努力,尽管这个过程还很漫长,远远还没有达到性别意识的理性深度,更没有能动摇消费社会对性别的更加定型化压力,但这个趋势对现代意识的性别建构却具有一份特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