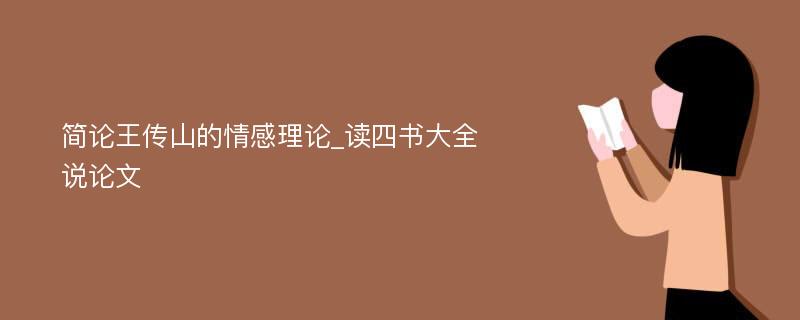
王船山之情论发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之论文,情论发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1-0065-07
本文意在对船山之情论做一个具体而微的阐释,该阐释将推进我们对船山之人性论乃至其全部思想的整体理解,它同样将有助于让我们在本原的层次上去领会人心、人性之丰富性和复杂性。整篇文章按如下的思路展开:(1)首先讨论的是王船山对情的具体论述,这涉及三个方面,亦即情之本性、独具特色的情感独体论以及情与不善之来源的关系。这就构成前三小节的内容:情作为变合之几、好恶之几与独用之情、情与不善之来源。此中颇有不少特出的精彩之处,如论好恶之几、独用之情的学说,就可通于刘蕺山的纯情说,后文对此将略作对比、引申。(2)在阐明王船山对情的领会与规定之后,本文力图将此情论置于船山人性论乃至天道论的整体之中来揭示其人性论的独特,亦此即将情放置在天人回环、心性情才的整体之中来进行讨论。鉴于文章的篇幅,对此本文只能略作探讨以引发兴趣。(3)最后,作为范例和证明,本文将试图用船山对理与欲之关系的规定来阐明以上所述情论的正当性,盖性即是理、欲即是情之下游,理欲关系所展示无非就是性情关系。以下依次论述。
一、情为变合之几
船山将情展示为阴阳变合之几,此是船山对情的一贯看法,散见于各部著作之中。以下即选取几段引文以对此进行说明。
《诗广传》卷一有云:
情者,阴阳之几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应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1]
船山于此明确表示:所谓的情,就是阴阳之几,此阴阳之几动于心而与天地之产相应者即为情。内有其情,则外必有其物;外有其物,则内可有其情。内外交相成,而情物不相离。这也表明情向来就已经伸展、铺开在天地之间。
在《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中,船山论此更详,其文有云:
1.情元是变合之几,性只是一阴一阳之实。情之始有者,则甘食悦色;到后来蕃变流转,则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种种者。性自行于情之中,而非性之生情,亦非性之感物而动则化而为情也。[2]
2.情固是自家底情,然竟名之曰“自家”,则必不可。盖吾心之动几,与物相取,物欲之足相引者,与吾之动几交,而情以生。然则情者,不纯在外,不纯在內,或往或来,一来一往,吾之动几与天地之动几相合而成者也。[3]
3.故知阴阳之撰,唯仁义礼智之德而为性;变合之几,成喜怒哀乐之发而为情。性一于善,而情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也。[4]
在第一条引文中,船山以情为阴阳变合之几,以性为一阴一阳之实。最初所有的情即是所谓的甘食悦色之情,后来便蕃变流转、生出喜怒哀乐爱恶欲种种情来。性虽行于情之中,却各自有体,不是性生情或性感物而动以化为情。在第二条引文中,船山更明确地揭示了情之来源和特性:情之所生在于吾心之动几与物相取、物欲之足以相引与吾心之动几相交,是吾之动几与天地之动几相合而成者。至于此情本身,则不纯在外,亦不纯在内,在乎内外、往来之间。第三条引文的内容同于第一条,船山于此处以阴阳之实撰为仁义礼智之性,而以阴阳变合之几为喜怒哀乐之源,性无不善,喜怒哀乐之情则可以为善、亦可以为不善。
根据此处的展示,船山主要将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视为情之真正内容,其根源则为阴阳变合之几。但根据船山对人心、道心的如下论述:“今夫情,则迥有人心、道心之别也。喜、怒、哀、乐,兼未发。人心也。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兼扩充。道心也。斯二者,互藏其宅而交发其用。”[5]船山也将四端之心视为某种情、不过却是性之情。所以实际上,情在船山这里可以分为两种:性之情和变合之情;前者为四端等心,后者为喜怒哀乐等七情。前者无有不善,而后者则可善可不善;在本节引文中,第一条可包含两种,后三条则主要侧重喜怒哀乐之情。正是基于此种区分,船山既有所谓好恶之几、独用之情的独体说,亦有情为不善之源的说法。以下即分别对此二者展开论述。
二、好恶之几、独用之情
以好恶之几、独用之情为人心之独体,可谓船山思想中的又一个特色。通过此一说法,船山展示了情在人心中的本源地位。此情作为连绵不断之初几,是独体,是诚之几,是人极之所自建,是圣功之钥,是圣治之枢。以下便借两段文字对此进行阐明。
《诗广传》卷一有云:
夫人之有好恶,独用之情也。不忧其害而固恶之,恶之而患有所不避。无所望益于彼而固好之,其好之也,亦无借以致益于彼以纾吾好。[6]
船山于此明确地指出:人之有好恶,是其独用之情。圣贤有圣贤之好恶,庶民有庶民之好恶。此好恶之情不忧害、不避患、不望益,此中所体现的恰恰是本原之好恶的刚严和笃实。正因为此好恶是独用之情,所以其用甚大。但庶民不能用其全,而圣贤则真能用此独用之情以成其至善无恶之独体。
对此好恶之几的大用,船山于《尚书引义》卷四中有云:
1.夫圣人之所履一于幽,以向明而治天下者,其所会归,好恶而已矣。好恶者,性之情也。元后之独也,庶民之共也,异端之所欲泯忘而任其判涣者也。圣人之好恶安于道,贤人之好恶依于德,才人之好恶因乎功,智人之好恶生乎名,愚不肖之好恶移于习。八政之举,惟好斯举;八政之废,惟恶斯废;五事之效其贞,惟好斯勉;五事之戒其淫,惟恶斯惩。好之兴,而恻隐、恭敬生于兆民之心,以成仁让;恶之兴,而羞恶、是非著于兆民之心,以远邪辟。其动也,发于潜而从违卒不可御;其审也,成乎志而祸福所不能移。是独体也,是诚之几也,故允为极所自建也。[7]
2.好恶者,初几也;思者,引伸其好恶以求遂者也。好恶生思,而不待思以生。是好恶为万化之源,故曰极也……皇哉好恶乎!人而无好,则居不就其所协,勿论彝伦之叙矣。人而无恶,则居且安于不协,勿论彝伦之斁矣。性资情以尽,情作才以兴,缄之也密,充之也大,圣功之钥,圣治之枢也。[8]
在第一段引文中,船山指出:圣人之所以履幽向明而治天下者,即为好恶,此为万治之所会归。在船山看来,好恶是性之情,元后有之、庶民共之、异端虽欲泯忘之而终不能。但不同之人,其好恶之情形亦有所不同:圣人的好恶以道为安,贤人的好恶以德为安,才人的好恶因乎功业,智人的好恶生于名声,愚不肖的好恶则在习气的洪流中打转。圣王之治天下,即以此好恶为准:八政之举废,惟其好恶斯举斯废;五事之贞淫,惟其好恶斯免斯惩。好之兴,则恻隐与恭敬之心日生于兆民之心,斯以化成天下仁让之风;恶之兴,则羞恶与是非之心日著于兆民之心,斯以戒天下远于邪僻。于此,船山将好恶之情和四端之心联系起来,好恶之情从本源上就和此四端之心融结在一起。此好恶之几虽发于潜隐之中,而既发则从违不可以御;此好恶之几既审之后则成乎志,既成乎志则一切祸福皆不能移。所以船山称赞此好恶之情为独体、为诚之几,为极之所自建。好恶之用大矣哉!在第二段引文中,船山更从其他方面强调了好恶之情的本原性及其大用:好恶之情即是所谓的初几,而思则是引申此初几以求完成此情者。所以好恶生思,而不是思生好恶,这就表明了好恶之情相对于思的一种优先性和本源性。所以船山称此好恶为万化之源、极之所自建。人如果无好之情,其居就不会趋于协和一致;更不用说彝伦之叙了;人如果无恶之情,其居就会安于不协和,更不用说彝伦之斁了。性资此好恶之情而尽,才资此好恶之情以兴起大用,其藏也密,其用也大而无极,所以船山又称赞它为圣功之錀、圣治之枢。
船山对好恶之情的阐发在心体上揭示出一个纯情的独体:在某种程度上,此纯情的独体可以称为万化之源,思、四端之心、七情、人伦、政治皆由此本源而出,所以船山称赞它为极之所自建。此纯情之独体以四端之心为开端、以思尽其用,故能为天下之大本。有趣的是,稍前于船山的理学大家刘蕺山对情也有类似的看法,其独体观和船山的思想颇有相通之处。蕺山有所谓的纯情、四德七情说,唐君毅和陈荣灼二位先生曾特地提出以作表彰。以下就籍二位先生对蕺山之说的阐发以与船山之思想做一番对照,从而帮助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理解船山的纯情独体说。
刘蕺山在《学言中》有云:
1.中庸言喜怒哀乐,专指四德言,非以七情言也。喜,仁之德也;怒,义之德也;乐,礼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其所谓中,即信之德也……推之一动一静、一语一默,莫不皆然。此独体之妙,所以即隐即见,即微即显,而慎独之学,即中和即位育,此千圣学脉也。[9]
《学言上》中亦有云:
2.喜怒哀乐,性之发也;因感而动,天之为也。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心之发也;逐物而迁,人之为也。众人以人而汩天,圣人尽人以达天。[10]
从这两条引文来看,刘蕺山将喜怒哀乐作为性之情,此即是所谓的四德,而信则表征贯穿此四德之中体。此中体即隐即见、即微即显,无分于动静语默,亦即所谓的独体。慎独之学本乎此,中和之德、位育之功出乎此,所以蕺山视其为千圣学脉所在。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则是所谓的七情,它们发自人心,追逐外物而迁流不息,此非天性而是出于人为,故非性情之本体。根据唐君毅先生的阐释,刘蕺山亦将此作为性情之本体的中体视为“纯意”、“纯情”之独体,且此独体具有“自感”的特性:“此纯情与自感,则有一自始至终、周而复始之历程……由此周而复始,更不偏向此四者之一,或滞住于此四者之一,即见此心有内在之‘中’,如天枢在天运之中而不动。此即主乎此心之纯情自感之周而复始之运中之‘意’所在也。”[11]陈荣灼先生曾指出:“唐先生关于蕺山哲学解释的主要独特之处明显表现于对‘纯意’与‘纯情’之强调。”[12]在唐先生之阐释的基础上,陈荣灼先生更指出蕺山的独体说可以从现象学存在论的角度来加以阐发,在本源的层次上恰可与法国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的生命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Life)相通。此种观察与比较属于中西思想的深层对话,饶有深致,应该进一步加以发掘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沟通中西思想两个传统。
将刘蕺山的纯情独体说和船山的独体说做一个比较,至少可以发现两点不同:(1)与蕺山以喜怒哀乐为四德不同,船山以恻隐等四端之心为纯情并将喜怒哀乐等视为七情。(2)蕺山重视此纯意、纯情之体的自感,而船山更强调了好恶之几的重要性。但此种不同实际上只是表面现象,在独体说上,这两个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赢得的是同一个视野,亦即都强调此纯情之独体、强调纯情的本源性。两者的说法在具体表现上有所区别,但在精神的趋向和洞察的层次上,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阳明后学泛滥的背景中,能找到两位大思想家之间的这种共鸣,颇为有趣,大概这就是思想自身的命运吧。
三、情与不善之来源
现在来探讨喜怒哀乐之情与不善之来源的关系。实际上,此一问题完全通于第一小节所论述的“情为变合之几”,也和“习与性成”等问题密切相关。只是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对性习问题作出深入讨论,但如果我们能对情与不善之来源的关系问题赢得一个深入的领会,对性习问题的讨论将会有事半功倍之效。在船山看来,情与不善之来源的关系可确切地展示如下:情为阴阳往来变合之几,于此变合之际,若吾心之往几与物之来几不能相合以正,则不善即此而成矣,此即为不善之来源。然于此变合之几,情亦未必为不善,关键在于吾心之能否自作其主宰。吾心若能自作主宰,则无不善之情。
在《读四书大全说》卷八中,船山从习与性成的角度论述了不善之来源:
1.习之所以能成乎不善者,物也。夫物亦何不善之有哉?如人不淫,美色不能令之淫。取物而后受其蔽,此程子之所以归咎于气禀也。虽然,气禀亦何不善之有哉?如公刘好货,太王好色,亦是气禀之偏。然而不善之所从来,必有所自起,则在气禀与物相授受之交也。气禀能往,往非不善也;物能来,来非不善也。而一往一来之间,有其地焉,有其时焉。化之相与往来者,不能恒当其时与地,于是而有不当之物。物不当,而往来者发不及收,则不善生矣……乘乎不得已之动,而所值之位不能合符而相与于正,于是来者成蔽,往者成逆,而不善之习成矣。业已成乎习,则熏染以成固有,虽莫之感而私意私欲且发矣。[13]
2.后天之动,有得位,有不得位,亦化之无心而莫齐也。得位,则物不害习而习不害性。不得位,则物以移习于恶而习以成性于不善矣。此非吾形、吾色之咎也,亦非物形、物色之咎也,咎在吾之形色与物之形色往来相遇之几也。天地无不善之物,而物有不善之几。非相值之位则不善。物亦非必有不善之几,吾之动几有不善于物之几。吾之动几亦非有不善之几,物之来几与吾之往几不相应以其正,而不善之几以成。[14]
在如上两段引文中,船山对不善之来源作出了追溯,其关键则在于情、习。情、习之所以能为不善之来源则在于在气禀与物相授受之际:化之相与往来者不能当于其时其地而有不当之物,而气禀之往亦不能与此时位、物相当而得其正,则往者(气禀)成逆、来者(物)成蔽,如此则不善成矣。习于此种不善之中,则不善之习成矣。既成乎习则相互熏染以成其固有①,如此虽莫之感而私意私欲且发矣。在第二段引文中,船山则着重从“几”的角度正面地阐释“习与性成”:吾之形色与物之形色往来相遇之几是不善的源头,吾之往几与物之来几不能相应以其正,则不善之几以成。这里所谓的“授受之际”、“相遇之几”,探本而言,完全通于情之为“变合之几”,盖变合之处即是授受、相遇之处。而且船山此处的论述还表明:人之本性之至善的,而情、习所引起的不善是后起的。
于《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中,船山更对此情(任不善)之地位做出阐明:
1.然则才不任罪,性尤不任罪,物欲亦不任罪。其能使为不善者,罪不在情而何在哉![15]
2.才之所可尽者,尽之于性也。能尽其才者,情之正也;不能尽其才者,受命于情而之于荡也。惟情可以尽才,故耳之所听,目之所视,口之所言,体之所动,情苟正而皆可使复于礼。亦惟情能屈其才而不使尽,则耳目之官本无不聪、不明、耽淫声、嗜美色之咎,而情移于彼,则才以舍所应效而奔命焉。[16]
3.盖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其体微而其力亦微,故必乘之于喜怒哀乐以导其所发,然后能鼓舞其才以成大用。喜怒哀乐之情虽无自质,而其几甚速亦甚盛。故非性授以节,则才本形而下之器,蠢不敌灵,静不胜动,且听命于情以为作为辍,为攻为取,而大爽乎其受型于性之良能。[17]
在第一条引文中,船山明确指出:就不善之来源而说,才不任罪,性尤其不任罪,即便物欲亦不任罪,只有情任此罪。在第二、第三条引文中,船山表明了情之所以任罪的原因所在:按理说,才之尽应该尽于其性,但性不能直接使才,唯有情能尽其才之用。所以亦唯有情能够使得耳目口体皆得其正而复于礼,此即用正情以尽才于性。但情自有其体用而不必依于性,此则或有可能与私意私欲相连而使耳目之官耽于美色、淫声、私利的海洋之中,以相杂相熏相染而成不善之习气,此即一切不善之来源。虽然人有恻隐等四端之心,但此四端之心体微而力亦弱,必要得喜怒哀乐之助方能成其大用。但喜怒哀乐之情既得乘权,或不听于性而乐与私意私欲相取。而才本为形而下之气,不能敌此喜怒哀乐之速与盛,且将听命于情以随情私意私欲矣,此则不善之所以成。要之,结合船山对往来变合之几的论述以及此处对情之地位的揭示,船山以情为不善之源头的说法很容易得到理解。而正因为不善来源于情,情为阴阳变合之几而无实体、无根,所以不善亦无实体、无根。故而人随时随地能复其至善之本体,以其至善之纯情独体无时无刻不在也,此亦船山思想之一特色。
四、情与心性、天道
情并非遗世独立之物,它总是和心、性、才、欲等交织在一起,也只有将情放置在心性论乃至天道论的整体中,我们才能赢得关于情的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实际上,在船山这里,对情的论述从来就不是单独展开的,他总是将情和心性才欲、天道阴阳等结合起来进行讨论。船山对于心性情才的总体见解,本文于此处不能详论,但其总体见解大抵可以归结为下:(1)心为阴阳翕辟之不容已,性为阴阳动静之实,情为阴阳变合之几,才为阴阳融结之形质。此是从天道论上来展示人性,人性一切特性皆出于太极阴阳五行至诚之道,所以心、性、情、才从本源上来说均有善而无恶。(2)从心性方面而言,心作为意向伸展之统一体统摄性、情、才于自身之中:性为心之本体,且在心上有其表现,此即所谓四端之心亦即道心。情为心感物、应物之用,心不感应则无有所谓情,故心为情之主导,情之所以可转化者正在于心为情之主宰也。才供心情之用以就功者也,尤其听命于情,但心为情之主宰,故才实际上最终仍听命于心。所以心是统性情才而言者,惟心能尽其性、惟心能诚其意、惟心能正其情、惟心能尽其才、惟心能公其欲。于人而言,心就是一切之本、一切之源,心之地位由此可见。也正是因为心之核心地位,我们只有结合心之特性才能恰当地领会情之本性。(3)由于天道为至诚之本原发生、心为意向之自我伸展的统一体(实际上,此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一切展示都要至于此本原的流动体中来进行。此流动体本身是一切原初意义的活泼发生场,其中并无绝对限定之物,所以性、情、才皆非限定之物:性虽有其实体,却是随着命之日降而日生日成的,故习可与性成;情为变合之几,永远具有一种当下活泼发生的特性,更非限定之物,故治情者必要以性主之;才虽有其比较固定的形质,但天理周流、天气洋溢,此形质亦可以理、气养之、化之,正因为才非定体,变化气质才是可能的。由此可见,船山之心性情才论完全融合在天道论的原始整体之中。
对此,船山亦有明确的意识,《周易外传》卷四有云:
凡夫万有之化,流行而成用。同此一日之内,同此天地之间,未有殊才异情,能相安而不毁者也。情以御才,才以给情,情才同源于性,性原于道,道则一而已矣。一者,保合和同而秩然相节者也。始于道,成于性,动于情,变于才。才以就功,功以致效,功效散着于多而协于一,则又终合于道以始。是故始于一,中于万,终于一。始于一,故曰“一本而万殊”;终于一以始,故曰“同归而殊途”。[18]
在船山看来:天道无非此万物之化之流行,天地之间的万物相互殊才异情,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更新,无有所谓相安而不毁者,凡此天地之间皆是此变化日新之洪流。其变化情形如下:由情以御才,由才以给其情,情和才源出于性,而性则一出于天地一阴一阳之道,追溯到天道之本源发生,已是不可复加之极致。至于道体自身,则遍运乎一切有形无形之中而为其实体,是所谓统万物而一体同流者也。所以天地万物之化,始于道、成于性、动于情而变于才。才以就其功,功以致其效,万物各有其功效而散着、充盈于天地之间,然万物必协于一,故又终于道以始,此即所谓的理一分殊。从始于一来看,此即“一本而万殊”;从终于一以始来看,此即所谓的“同归而殊途”。虽然船山于此处没有涉及心,但很明显他已经将性、情、才打成一片并将它们置于天道流行的整体之中来加以展示,这就印证了我们上面的说法。
以此天人回环、交尽视野下的心性情才论为背景,前面三个小节对情之诸种特性的展示就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情从根源上就来源于阴阳感应之不容已、是心与万物之间的不断互动,所以它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变合之几。在此变合之几中,有先天者、有后天者(亦即所谓的先天之动与后天之动、在天之几与在人之几),先天之情原本于性之发,此即所谓好恶之几、独用之情,亦即道心或纯情,它是至善无恶的;后天之情原本于心之动,此即所谓七情六欲,此中即有善有恶而人心之权衡于此觅得其用武之地,习之关键地位也正在此中体现出来。先天之情之所以是至善的,那是因为它出于天道阴阳感应之至诚(具阴阳之实);后天之情之所以有善有恶,那是因为它出于阴阳翕辟之几(未必具阴阳之实)。
五、例证:船山论理与欲
此处再以船山对理欲关系问题的讨论作为范例来展示船山之情论的正当性与通达性。盖理即是本心、即是性、即是道,而欲虽然有种种不同区分(如原初之欲和后起之欲等),却总归属于广义上的情,因为欲也是在变合之几处才有的。所以船山对于理欲关系的探讨,其实也就是从另一个侧面来展示其对心性情才的领会与规定。大体而言,船山虽以欲为情之下流,但并不以欲为不善之物。欲本身可说是中性的,其善与不善视乎它是否合乎理,欲之大公者即为理。此即船山的理欲合一之说,以下对此略作说明。
《读四书大全说》卷八有云:
离欲而别为理,其唯释氏为然。盖厌弃物则,而废人之大伦矣……即此好货、好色之心,而天之以阴骘万物,人之以载天地之大德者,皆其以是为所藏之用……于此声色臭味,廓然见万物之公欲,而即为万物之公理;大公廓然,物来顺应,则视之听之,以言以动,率循斯而无待外求……孟子承孔子之学,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19]
船山于此指出:离欲而别为理,是佛家的教法,儒家却不如此。离欲而别为理,则可以厌弃物则、废除人伦矣。在船山看来,好货、好色之心未必为不善,若能即此心以体察天地阴骘万物之大德并以此而立人道之大德,则此好货、好色皆可用之于善,而理即在其中矣。此即所谓于声色臭味中,见得万物之公欲即为万物之公理;即此声色臭味而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则心安理得而无待外求。基于此种见解,船山更称赞孟子说:孟子能真切地继承孔子之学,故可以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近乎大而化之境界。
于《诗广传》中,船山更反对所谓的薄欲之说,该书卷二有云:
吾惧夫薄于欲者之亦薄于理,薄于以身受天下者之薄于以身任天下也……是故天地之产皆有所用;饮食男女皆有所贞。君子敬天地之产而秩以其分,重饮食男女之辨而协以其安……厚用天下而不失其淡,淡用天下而不歆其薄,为君子者,无难无易,慎为之而已矣。[20]
船山甚至担心薄于欲者亦可能薄于理,所以他并不排斥饮食男女之欲乃至物欲,但他认为:天地之产,应该皆得其用;饮食男女,应该皆有所贞。所以君子敬天地之产而注重其秩序,重视男女之辨而协和之以安;故能厚用天下而不失其淡,淡用天下而不羡其薄。君子之所作所为,以慎为之而无难易之别,如此则即人欲以达于天理,理欲合一矣。
《读四书大全说》卷四亦有云:
圣人有欲,其欲即天之理。天无欲,其理即人之欲。学者有理有欲,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于此可见: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治民有道,此道也;获上有道,此道也;信友有道,此道也;诚身有道,此道也。故曰“吾道一以贯之”也。[21]
此处船山将学者之理欲、圣人之理欲与天理打成一片,认为天理、人欲之间并无截然的分割,人欲之各得即是天理之所在,而一切修身之道即在此中。船山于理欲问题上看得通透,从根源上就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故有理欲合一的说法。
这样一种对于理欲关系的通达见解,和船山对于心性情才的总体见解完全是血脉相通的。理出于天道至诚之流行,然道心、本心、本性即是理也,盖道心、本心与本性无非在人之天道之至诚流行;欲为情之下游,虽为下游却和情一样可善可恶,盖在变合之几处,善恶的走向取决于人心之权衡,人若能即人欲以见天理,则所谓人欲之行亦无非天理之流行。由此,理与欲之关系即相当于道心或本性与情之关系:即欲见理即是所谓的即情见性,欲得其所即是理得其所,情之贞定即性之贞定。船山之学问运思,其无往而不通达,正在此中体现,而其对理欲之关系的论述也正证明了此上对船山情论之阐释的正当性与通达性。
注释:
①船山此处的熏染说,颇与唯识家所讲的“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现行”的学说相类。由此或可推断其可能受到唯识家的影响。当然,船山自己的思想也完全容纳这种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