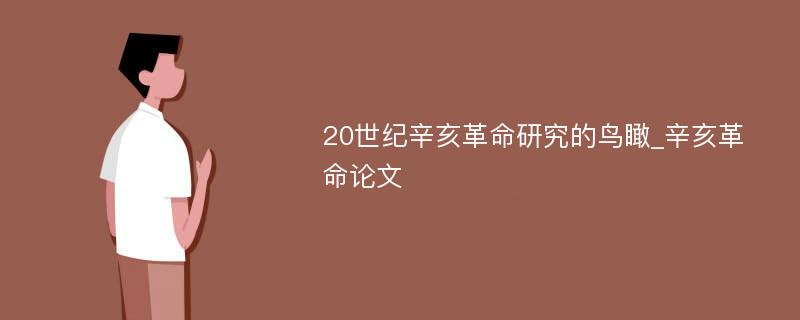
20世纪辛亥革命研究鸟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鸟瞰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末,人们纷纷对本世纪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结。作为历史研究者,借此机会对百年来辛亥革命研究作点小结,也是很有必要的。辛亥革命史在学科分类上只能是一个小小的三级学科,而从革命进行的当年到今天,从国内到海外,曾经从事和正在从事辛亥革命研究的人何其多,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凭笔者有限的学识、见闻,凭这万字左右的文章,实在难以全面地勾稽铺陈,一一论列。取巧之法,乃就管见所及,仅对中国大陆20世纪的辛亥革命研究作一鸟瞰式回顾,即使如此,也还不免挂一漏万,疏漏之处,恳请识者鉴谅。
1
辛亥革命不仅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三次巨大变革之一,也是20世纪世界上伟大的事件之一。其深远影响在事变当时就已被具有眼光的人们所认识。 因此, 关于这场革命的著述几乎在革命准备时期就开始出现了。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这是一个关系到国际法的复杂案件,立即引起法律专家们的关注,他们发表文章对此案件进行研究,随后将其作为典型案例收进了国际法教科书。这恐怕是对这场革命中的重要事件的最早研究。后来孙中山到了日本,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其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于1902年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次年章士钊据以译编为《孙逸仙》,在国内刊行,一时风行天下,成为鼓吹革命,宣传孙中山思想与业绩的重要著作。这应该是最早关于辛亥革命领导人的传记作品了。1911年出版的《大革命写真图》(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中国革命史》(苏生著)和1912年出版的《中国革命记事本末》(郭孝成编)、《辛亥革命始末记》(渤海寿臣编)、《共和关键录》(观渡庐编)、《浙江革命记》(顾乃斌撰)、《湖北革命实见记》(胡石庵著)等则是关于辛亥革命的早期记录。如果说前几种多是报章资料和文件汇编的话,那么《浙江革命记》述秋瑾之死至杭州光复始末,《湖北革命实见记》记武昌首义之经过,皆为系统的史事记载,虽然这些作品以今天眼光来看,还算不上科学的史学著作,但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说,均可视为那个时候的当代史。特别是胡石庵氏还提出了写作信史的几条原则:“从实以记,不偏不党,不讳亲,不避仇;不畏强御,不轻弱贱;是者是,非者非;善者善,恶者恶;得者得,失者失;可取者取,可舍者舍;可美者美,可丑者丑;可褒者褒,可诛者诛”(注: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至今对于治史者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不久,人们可以从容地编纂历史,出现了有一定编著体例的著作。钱基博所编《无锡光复志》内容共分6篇:匡复、军政、财政、民政、司法、自叙,初备专志规模;而谷钟秀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史》,在绪论和结论外,以三编分述组织政府时代、临时政府时代和北京政府时代史实。以上关于辛亥革命的最初著述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史料,作为辛亥革命研究的起点,其创榛劈莽之功不可没。
后来,有更多的辛亥革命参加者撰写回忆录式的著作,其中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居正《辛亥札记》、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记实》、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等,由于有亲身经历为依据,并保留了大量原始材料,更有的作者具有一定的传统史学功底,采用记事本末或别的体裁叙述历史,附录大事年表或名录传状等等,不失为有价值的辛亥革命史著作,至今还被一些辛亥革命史论著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或加以引用。
30年代以后,国民党开始着手党史的编纂和研究,辛亥革命史被纳入其中,出现了一批以辛亥革命命名的著作,较有影响者为左舜生、郭真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些人物传记,特别是孙中山的传记因其逝世,后来又被推崇为国父而猛增。由于动员华侨参与国内建设和抗战的需要,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著述也占有一定比例。这些著述大多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打上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统,写革命领导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一党一人划线,衡量是非,月旦人物,不乏删削史实,涂饰功过之弊。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由于突出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历史功绩竟以不符事实为由遭国民党政府的查禁。
然而有几位国民党人士以比较严肃的辛亥革命著述而被列入史家名录,他们的作品或以资料搜罗丰富取胜,或以体例比较严谨见长,或则长期致力于若干史事的考订,比较具有参考价值。如,曾经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邹鲁,继早年编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之后,编著了《中国国民党史稿》,按组党、宣传、革命、列传四篇分别记述革命团体的建立、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历次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尤以党人传记史料价值为高。少年时代即参加兴中会,民国初年曾任稽勋局局长的冯自由,用主要精力从事辛亥革命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著述,以收集到的一批辛亥革命参加者提供的资料为基础,编撰了《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华侨革命开国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等,其中《革命逸史》根据有关资料撰成革命史实220余条,举凡兴中会、同盟会会员事迹、 历次武装起义经过等均有较详细记述。该书兼采传闻异说,参以典故和嘉言懿行,不少为他书所未载。学者出身的罗香林,则利用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所征集的资料,撰著了关于孙中山传记的两部著作《国父家世源流考》、《国父之大学时代》,根据有关资料,考孙中山家世源流,记其早年生平事迹,常有他书所未载之史实,足资参考。因当时条件限制,这些著述除观点上的局限性外,史实上也不乏以讹传讹的情况。《革命逸史》部分材料采自他人原稿,失于校核,每多错讹失实和自相矛盾之处,今人若撰考订文字,其篇幅可在原书之上;《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其结论影响甚广,但亦引起若干反对意见,邓慕韩、谭彼岸、邱捷与李伯新先后就此撰文辨误,指出该书“国父上世源于广东紫金”说不能成立,并根据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仍认定翠亨孙氏源出东莞。
30年代末至40年代,出现了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辛亥革命史的著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从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对象、动力等问题的分析入手,论述了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这些科学论断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制定革命方针提供了历史的借鉴,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虽为政治宣传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书中一些观点,如关于袁世凯是大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等提法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黎乃涵(黎澍)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1954年改订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重新印行)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辛亥革命的少数开创性成果之一,书中论述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与妥协、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大独裁者与政党政治、洪宪帝制及其失败的史实,说明辛亥革命“成以妥协——强黎元洪为都督;败亦妥协——让临时大总统与袁世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除了论述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揭露帝国主义利用辛亥革命进一步加紧对中国侵略的罪行外,还把辛亥革命时期几种政治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条分缕析地理出了一条线索。这类著作虽然有着为当时革命斗争服务的鲜明政治色彩,史料的运用方面也略显粗糙,但由于运用了唯物史观,改变了观察历史的视角,不仅在1949年以前关于辛亥革命的众多著作中独树一帜,而且为1949年后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如果说,1949年以前,国民党人关于辛亥革命的著述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打下了史料方面的基础的话,那么,共产党人则为新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总之,1900—1949年在辛亥革命史学上是一个奠基的阶段。
2
195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旭麓著《辛亥革命》一书,可视为新中国史学界专门研究辛亥革命的开山之作,它与在此前后发表的胡绳武《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形成》等论文一道,标志着辛亥革命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门分支学科的诞生。随着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的到来,出现了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第一个浪潮。那年,毛泽东、吴玉章等分别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等文章,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作了许多深刻的论述;黎澍、荣孟源等还就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文章达二百余篇之多。
50年代的辛亥革命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辛亥革命的原因、革命团体的形成和革命思想的传播、孙中山领导的武装反清斗争、帝国主义的干涉等方面,并就辛亥革命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总的说来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有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陈旭麓的《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胡绳武、金冲及的《论清末立宪运动》等。从资料情况来看,也处于草创阶段。人民出版社出版《孙中山选集》,开新中国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编纂之先河,此后,大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相继出版,其中《辛亥革命》资料有8巨册, 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也影印再版,辛亥武昌起义的参加者撰写了《辛亥首义回忆录》(4辑) ,加上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和《云南杂志选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50年代末,在“反右”和“大跃进”运动的干扰下,刚出现发展势头的研究暂趋沉寂。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辛亥革命研究重现活力,不仅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辛亥革命研究工作者不顾当时物质条件的艰难,潜心学术研究,积极参与讨论,并在武汉举行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代表新中国建立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最新成就的成果《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文集》。这一年刘大年发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不同意那些夸大满汉矛盾,把反满斗争看做是所谓“国内民族革命”,或者是“中国人反对‘非中国人’的运动”之类的荒谬观点,而认为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时期里服从不同阶级的利益。辛亥革命中的反满斗争是资产阶级发动的,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注: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 该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民族问题的理论为依据,用纵览全局的方法系统分析反满问题,开扩了读者的眼界。一批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研究中坚的中青年学者崭露头角,除了前述陈旭麓、胡绳武、金冲及、李时岳等人外,还有章开沅、林增平、李文海、龚书铎、汤志钧、隗瀛涛、吴雁南、张磊等人,以他们高水平的研究论著赢得人们的关注。“文革”后辛亥革命史研究能够迅速恢复、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其基础就奠定于斯时。
这一时期学术讨论的空气比较浓厚,围绕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热烈的争鸣。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也是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并延伸到对于作为辛亥革命两支动力的会党和新军的探讨。同时,人们对帝国主义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等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60年代前期在有关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全国政协号召高龄政协委员撰写回忆录,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政协委员撰写了许多回忆文章,由全国政协选编了6卷本的《辛亥革命回忆录》, 还有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版的回忆录,如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等,这些回忆录取材多据亲身经历和见闻,不少内容为他书所未载。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近代史所编《辛亥革命资料》(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华书局编《秋瑾集》以及广西、广东、内蒙古、上海、江苏等省市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丰富了辛亥革命研究的资料库。
60年代以前的辛亥革命研究,在初步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存在着“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的“四多四少”现象,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由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本身不够成熟和我们多数研究者还比较年轻以外,极‘左’思想的干扰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注: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三十年》,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29页。)。
这一阶段由于研究本身的不够成熟和多数研究人员的比较年轻,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尚停留在“小册子”状态,不仅篇幅有限,内容也多为知识性、介绍性读物,缺乏研究深度。研究人员多为单枪匹马的个人爱好者,以辛亥革命为共同研究方向的人员相对集中的研究群体很少。那时的学术讨论明显地带有为革命领导人言论作注脚或用革命领导人的言论去套史实的倾向。当时史学研究中还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常常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道路和方法去苛求资产阶级革命。如中国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获得胜利,历史研究中就对辛亥革命时期部分革命党人主张的“中央革命”(即在北京或其他大都会举行武装起义)持否定态度。外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结论也成为衡量和评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搬用列宁批判新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一些观点,对老民粹派——民意党人的暗杀活动给予了全盘否定,中国史学研究者对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也持全盘否定的态度。甚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反对的错误倾向强加在辛亥革命党人身上,套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批判机会主义分子主张的议会斗争道路是“议会迷”的说法,把主张通过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权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也说成是“议会迷”。其实,“中央革命”也好,暗杀活动也好,“议会斗争”也好,尽管作用有限,成败难料,但都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表现了他们为了实现革命目标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辛亥革命研究,虽然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成绩还是巨大的。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北京万人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外,学术活动基本停顿,辛亥革命60周年的1971 年也未像50周年那样举行学术讨论会,只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和人民出版社的“学点历史丛书”中可以见到有关辛亥革命的小册子。至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数为“四人帮”的政治阴谋所左右,辛亥革命被歪曲成“反孔与尊孔”的“儒法斗争”,章太炎被奉为尊法反儒的“法家”,其著作《秦政记》、《秦献记》受到过分的关注,其他人物则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辛亥革命史研究遭到严重摧残,不少研究人员受到残酷迫害,学术园地一片凋零。
3
1976年10月,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文化大革命”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十年动乱”那种不正常气候下受到压抑的人们,终于有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1977年,樊百川的《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载《历史研究》第1 期)和李润苍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载《四川大学学报》第4期)两篇文章以拨乱反正的勇气, 对“四人帮”践踏历史研究的科学准则,歪曲辛亥革命史实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初步的揭露和清算。就在这一年,以章开沅、林增平为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成立,次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正式建立,金冲及和胡绳武也着手修改他们在1962年写成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的初稿,这标志着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队伍重新集结,中断了10年之久的研究工作重新恢复并开始步入正轨。随后,学者们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章开沅就如何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解放思想,突破禁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本身来说,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反对简单武断的“好坏分类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这些对辛亥革命史研究带有指导意义的言论,在与陈腐的封建史学糟粕彻底决裂的同时,大力肃清“左”的思想的影响,使史学真正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轨道,得到繁荣发展(注:章开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页;《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伴随着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的到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春天也来到了。80年代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辛亥革命史研究改变了从前单兵作战的状况,涌现出一批以辛亥革命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等都是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人员相对集中,成果比较丰富的研究机构,还培养了一批以辛亥革命为主攻方向的硕士和博士,这些史坛新秀已成长为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方面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以中南地区学者为主,得到全国各地有关学者支持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和全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的成立,更是辛亥革命史学史上的大事,后来部分省市也相继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或孙中山研究会。湖北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也成立了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广东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发起成立了孙中山基金会。这些学术团体都分别联系和团结着一批研究者与热心人,构成新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网络。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创办的大型学术集刊《辛亥革命史丛刊》、《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注:《辛亥革命史丛刊》原由中华书局出版,至第9辑。现拟改名为《辛亥革命研究》, 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继续出版。《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和《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已于1993年合并改名为《辛亥革命研究动态》,由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联合主办,继续印行。),以及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创办的《孙中山研究论丛》等刊物,作为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学术园地和精神家园,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支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机构和团体在开展学术讨论,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促进出成果,出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辛亥革命史研究结束了从前“小册子”的时代,各具特色的学术专著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对辛亥革命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显示了新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高水平。80年代有几部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问世。它们是: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由鄂、湘、豫、川、黔、粤等省有关学者集体撰著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120万字), 金冲及、胡绳武合作撰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150万字), 李新等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同人集体撰著的《中华民国史》(多卷本)等。这些著作,或以内容全面,体例完整见长,或以主线突出,史实详尽取胜,或以史料丰富,论述精当著称,均可谓辛亥革命史学史上的精品之作。此外,研究各地辛亥革命的著作不论在篇幅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新的突破,让人耳目一新,如,隗瀛涛的《四川保路运动史》、贺觉非、冯天瑜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吴剑杰的《辛亥革命在湖北》、王天奖、邓亦兵的《辛亥革命在河南》、冯祖贻、顾大全的《贵州辛亥革命》、杨渭生的《辛亥革命在浙江》、魏长洪的《辛亥革命在新疆》以及湖南史学会编的《辛亥革命在湖南》等,均对本地的辛亥革命进程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从中观或微观研究的角度,弥补了以往辛亥革命史注意全国较多,地区性研究比较薄弱的不足;而林家有的《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一书,更是填补空白之作。人物研究的著作比较突出的有张磊的《孙中山论》、李时岳、赵矢元的《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尚明轩的《孙中山传》、姜义华及唐文权、罗福惠的同名的《章太炎思想研究》、迟云飞的《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章开沅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以及关于邹容、陈天华、秋瑾、蔡锷、黎元洪等人的传记在研究人物生平和思想方面都有较大进展。
第三,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时开创的每十年举行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惯例,在1971年辛亥革命60周年时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后,于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时得到恢复。这时我国大陆学者已开始注视到国外史学的新进展,翻译出版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如周锡瑞(美)《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韦慕廷(美)《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薛君度(美)《黄兴与中国革命》、史扶邻(美)《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陈志让(加)《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等。同时,大陆学者走出国门,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上,我国大陆与台湾学者同堂讨论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开海峡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学术交流之先河。为了回应海外学术界提出的挑战,大陆学者对许多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与深入研究。这样,不仅把被“十年动乱”耽误的研究工作恢复起来,而且把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引向世界,使之成为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显学。于是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中国大陆各省八十余位学者和来自中国港澳地区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朝鲜、法国、印度、日本、罗马尼亚、泰国、英国、美国的四十余位学者出席。后来又有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及香港和美、日、韩、德等国家学者参加了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后两次会议与1961年第一次会议相比,不仅规模有所扩大,参加者范围更加广泛,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新进展;而且研讨内容有所拓展和深化,显示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魅力和活力。这种逢五、逢十以纪念促进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表示纪念的作法得以推广,198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199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几次青年学术讨论会、地区学术讨论会,使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出现一个又一个热潮,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
第四,研究领域日益拓宽。除了对辛亥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及其社团、重要的革命团体、资产阶级与农民、会党、新军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排满问题、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预备立宪与立宪运动、武昌起义、南京临时政府与各地军政府、辛亥革命时期中外关系(帝国主义的干涉、日本志士对革命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民国初年政局和“二次革命”、辛亥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秋瑾、张謇等)、重要史实和史料的考订等问题进行更深入研究并获致新的进展外,还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章开沅在《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等文章中,提出了“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的构想,强调不仅要注意人们历史活动背后的经济动因,也要注意到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社会诸因素,以至某些自然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即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素质以至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等许多方面的影响。他自己以及他所影响的一批青年学者,从辛亥时期的“国魂”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商会与“市民公社”、中国早期现代化、“排满”宣传与社会动员等课题入手,深入到当时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术境界。其他学者还从人口、自然灾害、游民、土匪、社会风尚等问题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作了广泛的探讨,获得许多新的认识。9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对社会心理的研究热潮,对辛亥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领袖人物的政治心态的考察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格,对当时社会心理、“反满”情结的剖析深化了人们对辛亥革命历史局限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一部分学者对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及其原因作了重新审视,有人甚至对辛亥革命“失败说”提出了质疑。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城市性质、城乡关系、社会力量配置的影响、对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等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不少学者还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问题;对人物和社会群体的研究也有新的成就,如对革命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和比较次要一些的人物以及对立面人物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比以前要细致得多,包括了对转变中的士大夫阶层、留学生、国内新式学堂学生、海外知识分子、女知识分子等的研究;从区域社会的角度研究地方辛亥革命,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等等,都是很有新意的;对民国初年社会政治状况的研究长期以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改变,对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民国元年前后国民的“参政热”、政党政治与民初国会等都有比较多的研究。辛亥志士们不仅为革命后的法制改革确立了理论原则,设计了实施方案,而且制定了共和国的根本大法——《临时约法》,并开始着手建立一套适应共和政体的法律制度体系。对辛亥时期法制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以往的辛亥革命史对这样一个重要课题缺乏专门研究,中国法制史对此也未予以足够重视。现在这一学术空白由体例完整,史料翔实,观点鲜明的专著《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邱远猷、张希坡著)填补了。另外,新近出版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朱英著),从“国家——社会”这一新的理论视角,着力探讨了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的发展变化,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辛亥革命研究的领域。在近代史研究中,近年有学者提出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的观点,认为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打断了清末“新政”的进程,通过清政府的改革,中国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还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造成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些看法,一部分学者发表文章,指出辛亥革命是清朝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是辛亥革命的产物,清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不可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从而再次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
第五,80年代以来辛亥革命史料的整理出版出现了大丰收的局面。1981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是辛亥革命史料出版的两个高潮期。档案资料是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而过去利用较少的一种史料,随着档案馆开放程度的提高,馆藏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湖北省暨武汉市政协及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合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章开沅等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等,为辛亥革命研究者提供了利用档案资料的方便,甚至提供了澄清有关史实、突破已有结论的可能。还有一类专题资料汇编,如,《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以及大型的《北洋军阀(1912—1928)》、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其中关于辛亥革命的有《拒俄运动》、《白朗起义》、《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等,这些资料汇编囊括了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和报刊资料等等,使人们减少许多案头翻检之劳,提高了研究的效率。辛亥革命人物的文集和年谱,特别是年谱长编,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是研究辛亥革命和有关人物生平、思想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有关出版单位在出版这类资料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文集类出版物除《孙中山全集》、《黄兴集》、《章太炎全集》、《宋教仁集》、《秦力山集》、《蔡锷集》、《邹容文集》、《谭人凤集》、《陶成章集》等以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人物文集丛书》(章开沅主编)收录了比较次要一些人物的著述,推动辛亥革命研究者把视野扩大到少数领导人以外的更多人群、扩大到革命营垒以外的各种类型人物身上,使人们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致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理解。年谱除《孙中山年谱》、《黄兴年谱》外,《章太炎年谱长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孙中山年谱长编》、《黄兴年谱长编》、《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的相继问世,为辛亥革命人物研究带来极大方便。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和《民国人物碑传集》是继《碑传集》、《续碑传集》、《碑传集补》之后的又一种碑传集精品,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各地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和80周年,竞相挖掘本地辛亥革命资料,《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四川辛亥革命史料》、《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以及浙江、陕西、广东、云南、山东、江西、湖北等地政协文史资料专辑各具地方特色,有力地配合了各地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这个时期还翻译出版了几种有关辛亥革命的外国资料,如,《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分别译自外国的外交文书、议会文件与新闻记者的书信、日记和新闻稿,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资料。
辛亥革命研究已走过了百年历程,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成绩斐然。然而从总体上看尚未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薄弱环节以至空白地区很多,还有许多课题值得我们花大气力去探讨,还有大量工作有待我们努力去做。辛亥革命研究当然不可能永远处于高潮之中,但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像法国大革命研究已跨过第二个100年一样, 辛亥革命研究在新的100年里将会继续深入进行下去,并取得更大的成就。
标签:辛亥革命论文; 孙中山论文; 孙中山诞辰150周年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辛亥革命纪念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