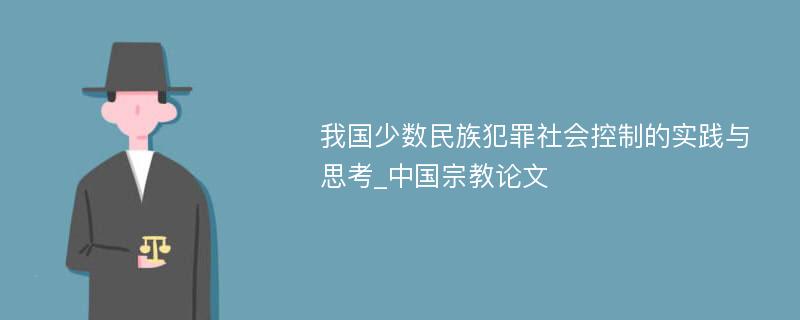
中国少数民族犯罪社会控制的实践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7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41(2005)01-0061-05
中国少数民族犯罪如何实现社会控制,是在提出中国犯罪控制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型的背景下讨论的。少数民族的经济地理和人文状况决定着犯罪控制必须关注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在犯罪控制的既往实践中,我们正是在尊重民族政策发展民族平等的框架中进行。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机关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从本民族地区犯罪问题的特点出发,采取灵活的办法,既有效地控制了犯罪,又较好地维护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如何完善和发展我国少数民族犯罪的社会控制,也是今后对少数民族犯罪控制实践进行反思的一个当然结论。
一、中国少数民族犯罪社会控制的实践
根据笔者长期在民族地区的调研和走访,发现国内部分民族地区已经对少数民族犯罪的社会控制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的积累是在党和政府民族团结平等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考验。
(一)尊重民族习俗处理重婚案件
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多发犯罪来看,重婚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婚问题较为突出,重婚不论是原始群婚,对偶婚的遗风,还是换房制度的遗俗,或者是封建思想的结果,都与我们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婚姻家庭制度格格不入。它必将遭到禁止,直至最后消亡。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旧的婚姻习俗的残存,早婚、私婚现象比较普遍,重婚问题尤为突出。综合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婚案件,发现重婚一般有四种情况:其一是家庭中的兄或弟去世后,女方为抚养子女,留下来与兄或弟自愿结婚,使已有婚配的兄或弟形成事实上的重婚。凉山×族群众通常称之为“转房”。其二是婚配的女方不育或无男孩,为传宗接代,男方另娶而形成重婚。其三是因为早婚,感情不合,女方出走又与他人非法同居,形成事实上的重婚关系。此外,因喜新厌旧,私婚后形成重婚的占据一定比例,但并不显著。可见,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婚问题十分复杂,在处理重婚案件时,必须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根据我的走访,民族地区控制重婚现象的实践中有若干措施:(1)对于封建思想严重的重婚,前妻(夫)不告诉的主要由基层组织进行教育,并由基层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后,宣布解除非法婚姻关系。(2)对于因喜新厌旧的重婚,前妻(夫)不告诉的,一般按重婚罪处理,情节轻微的作免予刑事处分,并判处废除其非法婚姻关系,情节严重的按刑法重婚罪判处。(3)对于重婚情节严重,前妻(夫)不告诉而由基层组织提出的,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起诉,由审判机关依法判处。
(二)发挥调解手段的功能
在有的少数民族中,男女结婚后,按传统习俗,并不马上同房,女的仍然在娘家居住,甚至去“游方”、“行歌坐月”(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社交活动),时间长了有的另有所爱,背弃前者,再娶再嫁。在这种情况下,男方带领多人到再嫁者家里宰猪、挑粮,甚至砸房,大吃一顿,以此作为“修赔”(赔礼)。按照法律规定,这种行为可能造成伤害或毁损财物等后果,但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和落后的习俗,对待这类案件,凡是没有致人重伤或致死人命,仅造成经济损失或轻微伤害的,一般是采取调解的方法解决,不以犯罪论处。
(三)发挥民族上层人物作用
少数民族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以及同一民族之间,因为闹坟山、争山林、争耕地、宅基地,水源矿藏,“串姑娘”以及其他权益或习俗经常引起械斗,并时常因械斗而造成严重后果。这类案件因涉及民族问题,比较敏感,往往掺杂着古老的乡里感情,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仇怨,情况复杂,处理不慎往往影响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
根据我对民族地区办案实践的观察,发现少数民族犯罪(民族地区的矛盾与纠纷的处理)的处理往往是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发动民族上层代表人物,利用他们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威信和号召力,对群众作好说服教育工作,维护民族地区的治安秩序。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民族上层人物带头违反法律时,更要谨慎处理。
(四)从宽处理封建迷信犯罪
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和落后、愚昧的习俗,由此而造成的各类案件较多。例如有的少数民族村寨中有了病人或遇有牲畜死亡,只要有人怀疑或指认是某人“放鬼”造成的恶果,被怀疑“放鬼”的人就要遭到不幸,轻者被抄家或逐出村寨,重者被活活打死。封建迷信案件是一种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司法实践中,对于有意利用“放鬼”这种迷信活动加害他人,指认或暗示他人为“放鬼”者,而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分子,要依照政策和法律严肃处理。但是如果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浓厚的迷信思想因素,对封建迷信案件的参与人一律以犯罪论处,并不妥当。在民族地区的长期司法实践中,从宽处理封建迷信犯罪已经成为一条成功的经验。
比如,在我国地处边远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近几年来“背马”搞封建迷信活动比较突出,由此引起的杀人、伤害、抄家等刑事案件也较多,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
(1)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比较落后,群众缺乏科学知识,把“背马”当成是能避鬼的人。××族流传的酒歌中称:“没有头人城墙要倒(地方要乱的意思),没有背马鬼要闹,没有铁匠田要荒……”故而“背马”在××族中地位较高,××人从生到死都要“背马”来背,就是牲畜有病,庄稼不好也要“背马”背,群众还自愿给“背马”一定钱物作报酬。
(2)“背马”有一定的欺骗伎俩,往往以迷信为手段造谣惑众,骗取财物,引起杀人、伤害、打砸抢等刑事案件。如云南红河县××族农民李某和周某,听信“背马”妖言,认为李父病死,周两个孙子死去,是某某人“背死”的。两人怕他继续“背死”人,即共同将其杀害。还有的“背马”利用“送鬼”、治病等手段强奸、玩弄妇女。
(3)“背马”问题的认识。如有的文化部门片面强调“背马”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人,专门召开“背马”会议,公开为“背马”平反,甚至还要酝酿成立“背马”协会,结果“背马”的身价越来越高,一些青年人纷纷投师“背马”。
如何看待“背马”?如何处理“背马”活动中的违法和犯罪问题?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司法机关在执法中掌握的原则是比较恰当的:即对“背马”一般不以“巫婆”,“神汉”看待,群众按民族习俗,请“背马”进行民族形式的“背马”活动,并自愿给“背马”酬金,不以犯罪论处;“背马”借封建迷信活动进行犯罪活动的,严格按照刑法论处,但略为从宽。
(五)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犯罪活动是十分复杂的。既有严重刑事犯罪,又有普通刑事案件,还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反革命案件。对于一些普通刑事案件,一般依法从宽处理,但对那些严重刑事犯罪案件能否适用“两少从宽”的政策呢?回答应是肯定的。对一些属于严重刑事犯罪的人犯,尽管其罪行严重,但因其确有困难,问题无法克服,可以挽救而又不会继续危害社会,群众公认放回去比关起来好的,可以通过特殊途径从宽处理。
二、中国少数民族犯罪社会控制的完善
我们的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形成针对犯罪的有益经验,如何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少数民族犯罪的社会控制,我以为需要考虑到习俗的力量、积极利用其本身的组织形式、发挥上层人物的作用、培养一批民族执法干部等。
(一)发挥少数民族传统习俗的积极作用
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犯罪控制,发挥少数民族传统习俗的积极作用,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正如哈特兰所描述的那样:原始人远非卢梭想象中的那样,是自由自在而又无拘无束的生灵。相反,他的一切都处于其所在群体的习俗的禁锢之中,这不仅反映在社会关系上,也包括在其宗教、巫术、劳作、工艺行为中,总之,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束缚在历史悠久的古老传统的锁链上。美国顶级的人类学权威之一洛伊博士同样表述:一般说来,和我们成文法相比,(原始人)更愿意服从习俗惯例这类不成文法,或者确切地说,他们自发地服从于不成文法。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类型的“原始人”。少数民族地区的某些传统习俗,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群众管理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无形的行为准则。少数民族公民,会选择更为服膺习俗的统治。例如,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许多苗族、侗族村寨从很早以前就有“议榔”、“起款”的习俗(就是起誓遵守某一款约)。议榔之前选出几个“榔头”、“理老”拟定款约,经全村寨人举行喝鸡血酒的仪式后,款约就对人们有了约束力,任何违犯它的行为,都要受到一定的处罚,轻者赔礼认错,罚款,重者抄家砸房,殴打体罚,甚至逐出村寨。实践证明,“议棉”和“起款”的形式是易为群众接受的,只要剔除落后的、有害的内容,赋予它新的内容,加以改革,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以黎平尚重镇为例证,我们可以发现习俗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
侗族聚居的黎平县尚重镇,地处边远,是一个居住着7千多人的小镇。1985年前,各种刑事案件的发案数在30起以上,尤其是盗窃,抢劫,流氓、强奸几种犯罪,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严打”斗争中,镇党委从这里的实际情况出发,布置各村寨订立各项村规,不少村寨沿袭过去的传统习俗,通过了款约。之后,群众不仅自觉遵守所订款约,并积极揭发违约者。镇政府根据群众的揭发并经司法机关查证后,对已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对有一般违法行为的,进行遵纪守法教育,这样更激发了群众的自治积极性。1985年内,全镇没有再发生过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只发生过5起,违法的人也很少。由此可见,这些款约对维护当地社会治安起了很大作用。
侗族是我身属的民族,保存各种旧有的习俗。比如:起款、议榔等。类似于今天的乡规民约。在民族聚居的社区内,习俗比法律能获得更为广泛和更有内心确信的遵从。当然,不能排除习俗中的部分封建文化因素和非现代化因素对民族聚居地区的消极作用,在发挥习俗对维护民族地区稳定的作用方面提出这些因素,更好地运用这些因素加以协调。
(二)利用和改造少数民族中原有的某些组织形式
利用和改造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有的某些组织形式控制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是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综合治理的一条成功经验,在今后的民族地区犯罪控制工作中也要坚持并发展完善。例如,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和云南宁蒗彝族地区的“家支”制度,原先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政权性质,它虽然对家支成员之间没有统治和隶属的关系,但对个人或家庭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在控制犯罪的过程中,凉山彝族自治州对彝族中的家支活动,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对于家支非法行使司法权,如对业经国家政法机关判处的案件,家支再行处罚和算人命金等,予以制约和取缔;对于家支主动出面调解各种刑、民案件解决纠纷的,则大力支持,并将家支组织纳入基层调解委员会和治保委员会,帮助他们学习法律知识,逐步把它们改造成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基础力量。
同样,侗苗族的“房族”和瑶族的“油锅组织”,也是一种类似于彝族“家支”的可以利用的组织形式。侗苗族的家庭结构是以同姓同宗近亲血缘组成“房族”,若干个近亲房族又联合组成同姓大族即“宗祠”。“房族”和“宗祠”建有严格的“族规”。“款”是侗苗民族以地域为纽带结成的地方联盟组织,并有大小之分。“小款”相当于一个村,“大款”由数十个村构成,可以跨乡、跨县,跨竹。侗苗人民的“大款”组织是一个协商解决不同地区之间纠纷的议事机构,具有平等性和联防性的特点。比如说,侗苗民族“款坪说款”是由“族长”或“寨老”主持召集纠纷当事人以“款约”来明辨是非、解决纠纷的一种传统方法。根据我的走访观察,实践中多将“大款”改建为地区民间纠纷联防联调协作委员会,这些联防联调组织吸收“族长”或“寨老”参加,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共商联防联调事宜,组成公议会或公议庭,依据法律、法规、政策以及乡规民约处理调解各类纠纷。
瑶族中的油锅组织是瑶族社区中类似于彝族“家支”的一种形式。瑶山地处黔桂的荔波、从江、榕江、三都及广西南丹、环江等两省几县交界的月亮山麓,远离县城,山高林密,交通闭塞,商旅不通,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个体家庭每遇灾害和不幸,只有依靠群体间的相互关怀和帮助,才能渡过难关。古老的氏族“油锅”组织由此产生并长期发挥着重要的社会职能作用,时至今日,仍为广大瑶族群众所竭力拥戴,呈现顽强生命力。油锅组织要求有事互相商量,大事人人到场,互相间全力支持和帮助。“油锅”,瑶语称为“玻卜”,意思是“爷崽”,汉译为“油锅”,意为“同在一口锅里吃饭的人”。这是一种以家族为单位,建立的一种特殊社会组织,可以是一个父系家庭组成的血缘集团,所有的成员同出于一个父系祖先的亲属,彼此间都有血缘关系,聚族而居,互相照应。每个“油锅”都有自己的名称、有自己的头人。各“油锅”成员同住一地,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各“油锅”有自己的领地、有公共墓地。同一“油锅”的成员严禁通婚,成员有互相继承财产的权利,并且有定期的会议制度。(注:新兴的“威赏”瑶寨的个例,可以为我们观察残存的“油锅”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威赏”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兴盛起来的瑶寨,位于樟江河谷黔桂交汇处,全寨8户瑶族人家,33口人,分布于4个互相呼应的小山坡。威赏寨8户人家都姓何,3户来自板告寨,5户来自董蒙寨。董蒙寨和板告寨原来就同属一个大“油锅”。在威赏寨,凡大小小务,由一退休的原乡干部出面、接洽和组织实施,因其曾是乡主要干部,见识广、通汉语、晓政策。他接受任务后,就先与两老住户商量,协商确定后,再通知全寨施行。寨中“秩序”井然,一切有“法”可依。从立寨到今10多年中,从未发生争吵斗殴事件,喂养的家禽家畜,如有损害他户庄稼的,少量则免为不计,只是互相道歉即下,如数量多的,则全寨共同讨论赔偿,当事人不提苛刻要求。起房盖屋全体参加,若造房日子选对主家生日时辰的,主家还行回避,由全寨代为营造。因威赏寨靠近荔波至南丹公路干线,1993年时,一住户两头水牛被外族强盗偷走。半夜被偷,清晨主家才发现,主持祭祀寨神的巫师立即赶到寨神坛前,撒上几粒米,念动诵词禀明寨神。全寨大小全体火速出动,兵分几路查找失落的水牛。很快将失丢的两水牛找回,只是未抓得贼人。失主备办酒肉,感谢全寨支持。)这种油锅组织应当在瑶寨中继续完善并发挥作用,剔除消极因素,发挥积极因素,维护瑶寨的社会治安秩序。
(三)利用民族地区的宗教组织形式
宗教在少数民族地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非常坚定。少数民族中的宗教神职人员或宗教理论造诣较深的学者,他们仍然是少数民族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宗教组织是一支可以利用的犯罪控制形式,在信教徒中神权看成至高无上的力量,教徒对宗教的信仰和崇拜超出对国家法律的崇仰。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一直处于紧密联系之中,以我所长期工作和生活的贵州省为例,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较为复杂。黔西南早在上一个世纪末,外国传教士就在民族地区设教堂、做洗礼并发展信徒,以致在少数民族中培养了一大批神职人员,这些神职人员一直是群众的“精神领袖”。根据统计,黔西南近四万天主教徒中布依族占大多数,回族自清朝雍正朝迁入贵州,并逐步定居在黔西南中部、北部的城镇及农村。回族基本上是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伴随人口的迁徒,伊斯兰教在黔西南也得以扎根。根据1990年统计全州有伊斯兰教活动场所21个,阿訇18人。可以说,贵州省境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已经成为民族地区稳定和民族地区安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我们应该化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因此,发挥宗教组织对民族地区犯罪控制、秩序维护的积极作用应当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四)发挥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作用
在过去的民族工作中,我们曾经利用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发挥了许多作用。这些上层人物有的在政府工作,有的产生于民间,但不无例外的是,他们对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村寨、姓氏基本上都有自然领袖和长者,他们深得民族群众的敬重,并负责处理民间纠纷维护民间秩序。他们是民间自然生成的权威。
少数民族居主在偏僻边远的山区,行政权力不能有效地到达个体民族公民。这种情况呼唤乡土自然生成的秩序。根据笔者的走访,进入调查视野的每个聚居的边远民族山寨,都有“头人”之类的自然领袖来仲裁寨内、族内事务。南盘江边板其乡马黑村,清道光27年(1847年)秋,所立乡规民约镌于石上:“我等生居乡末弹丸,少睹王化之典。”又坝江村碑述:“凡于寨中,虽属壤地褊小,亦皆莫非王土”;并且规定:“一切田土婚姻之事者,最要投明寨老里长人等。宽容理论了息”。由此观之,即使在少数民族的视野中,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的“边远”,文化与汉族存在不同,需要民族上层人物对社会治安秩序的维护。当前民族工作中的上层人物一般是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中以及在某一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人士,可能具备行政干部身份,也可能不具备行政干部身份。他们包括少数民族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学有专长的专业技术人才、归国人士、海外侨胞、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宗教人士、社团及其他方面的负责人士以及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后裔等,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分为不同的层次。控制少数民族犯罪,维护民族地区的治安秩序,必须依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良好群众基础,发挥他们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巨大影响力,才能处理好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
(五)尊重和倾听本民族群众的意见
少数民族犯罪,一定意义上因民族内部习俗引起,对于少数民族犯罪,各民族有自己历史传承的处理办法。我们在维护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对某些轻罪案件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或采取非刑罚化处理,都是尊重少数民族群众意见的结论。司法实践中,对于民族内部发生的犯罪案件,如何处理,不能采取鲁莽的工作作风,既伤害民族感情,又不能顺利开展工作。走访过程中,笔者曾经获悉两起案件因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而获得不同的结果: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高中女学生杜某挑草木炭回家存放,引起火灾,不仅自家房屋被烧毁,且蔓延全村烧毁50户,烧死1小孩,损失很大。有关机关未征求苗族群众的意见即批捕杜某,结果当公安人员前去捕人时,被全村苗族群众包围,不让捕杜某。提出的理由是:杜某不是有意放火,是不慎失火,其家先被烧毁,且她是该村苗族祖祖辈辈唯一的高中生,至于因失火造成的损失,群众愿意自己解决。根据苗族群众的意见,有关机关决定对杜某的失火行为不予追究。
广西田林县有个瑶民犯罪,但公安机关未向瑶族群众讲明情况就将犯人逮捕。当民警将被捕者押至半路时,瑶族群众追赶上来,强烈要求放人。但经过进行法制教育,说明犯罪分子罪行的严重危害性和刑法的严肃性后,结果瑶族群众自己把罪犯交送出来,表示任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
案1首先采取的是不顾及民族感情,不尊重少数民族群众意见的方法,因此受到抵制。但在有关机关征求群众意见之后,同群众商量对杜某免予刑事追究,才获得群众的支持。案2中,公安机关因为没有与瑶族群众沟通就贸然地逮捕瑶族公民,自然会受到瑶族群众在不理解的情况下的围攻,当公安机关与瑶族群众顺利沟通之后,才获得群众的支持并表示主动交出犯罪的瑶族公民。由此可见,在办理少数民族犯罪的案件时,必须尊重和倾听少数民族群众的意见,否则会引起民族纠纷,酿成事端。
(六)培养一支少数民族执法队伍
宪法规定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区域自治的范围内,各少数民族对经济、政治、文化各项事务享有自治权。少数民族公民在民族聚居区内更能贴近群众,同时也熟悉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因此,培养少数民族执法队伍,整顿少数民族社会治安,控制少数民族犯罪是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必须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刑法、控制犯罪的过程中表现出三个突出作用:一是在接待群众来访,在处理不懂汉语地区的案件和平息械斗,保证案件的及时、准确处理上,起着重大作用;二是较易深入当地民族群众完成调查、侦查任务,广泛收集证据和意见,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也便于审判人员与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直接对话,这有益于全面了解案情,防止主观片面,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三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多民族杂居地区,他们可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判,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布告和其他文件,能够使当地居民清楚地了解案件审理的情况,知道被告人犯的什么罪,犯罪的原因和思想根源,以及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和应受什么样的惩罚。这不仅能够教育犯罪分子,促使其认罪服法,接受改造,而且还可以加强当地民族群众的法制观念,提高他们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自觉性,起到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