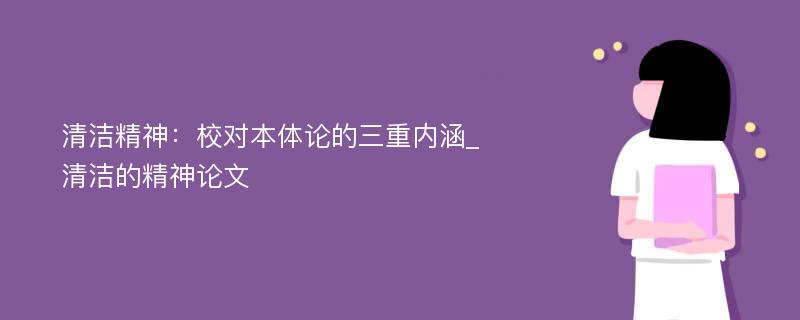
“清洁的精神”:校对本体论的三重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内涵论文,清洁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校对在操作性的编辑流程中往往被人们视为雕虫小技,但在理论性的编辑学体系中却极有必要被我们上升到本体建构。尤其是经由“清洁的精神”的指引和警醒,校对本体论或许可以包括以下三重内涵:首先,在立场上,我们必须真正地清楚校对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艰难的工作;其次,在方法上,我们必须辩证地对待积极出手与消极等待的矛盾关联;第三,在态度上,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实践一丝不苟的校对精神。当然,“理在事中”、“用以显体”的哲学原则,也决定了理性阐释有必要与具体事例相结合,因为具体事例的感官力量有助于校对本体论朝着我们这一个编辑共同体更好地敞开。
一、从《四库全书》看:校对为何如此艰难
如果说中国出版史上只有两个兼具政治性与文化性的大型出版事件,那么,由近及远,一个是20世纪“文革”时期“毛泽东著作系列”(还包括毛泽东像以及单张语录)总计108亿册(张)的出版,一个是18世纪乾隆时期“四库全书系列”(包括《四库全书》7部、副本1部,《四库全书荟要》2部)总计31万多册的编纂。前者全部是用机器印刷的,但从校对的角度看,据说曾有群众反映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的那张彩色像中,毛泽东头发的纹路里出现了“修党”的字样,幸亏这是虚惊一场[1]。后者基本上是用人工抄写的,校对问题就可谓多矣,对此我们不妨细读《编辑之友》2000年第5期发表的《〈四库全书〉的校对》一文。
《四库全书》在从1773-1787年长达15年的编纂历史中,先后使用过誊录3800人。这些誊录分为3批每隔5年继续工作:前两批各有1400名,系功名性服务者,规定每天誊写1000字,超额3/4者考核列为一等,——他们完成了《荟要》本和藏于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行宫文津阁、奉天行宫文溯阁的“北四阁本”的缮写工作;第三批共1000名,系功利性雇佣书手,规定千字佣金2钱5分,——他们完成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的“南三阁本”的缮写工作。
至于校对人数,依据乾隆四十七年(1782)奉旨开列的“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计有总校官1人、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39人、天文历算纂修兼分校官3人、缮书处总校官4人、缮书处分校官179人、篆隶分校官2人、绘图分校官1人[2](卷首P11~16)。上述229名校对官是北四阁本的,要是加上《荟要》本的总校4人和南三阁本的分校若干,估计编纂《四库全书》总共任用过300多位校对。
正如方家一再指出的,除了乾隆皇帝心态上的急于求成外,编纂组织体制上的誊校失调确实是导致四库本错讹较多的重要原因。首先,从人力配置看。誊录一般是常年在馆的,但每天上岗的校对则很少。以1782年的“在事诸臣职名”为例:一方面,总校官5人、兼任分校官42人乃至篆隶和绘图分校官3人并不是每天都到缮书处领取书稿来校对的,这样北四阁本的229人中就少了50人;另一方面,初校、复校制度的设立,使得缮书处179位分校官必须分为两股力量,大部分力量用于初校,小部分力量用于复校。其次,从具体工作看。四库馆要求每名誊录至少日写1000字。如此,对于北四阁的初校、复校而言,其日校对量的底线约为1.6万字。具体计算方式是:1400名誊录日写1000字,总数即是140万字;对此进行初校、复校,总数即是280万字;280万字分摊到缮书处179位分校官身上,平均即是每人1.6万字。南三阁的日校对量在底线上与北四阁大抵也差不多。1.6万字的日校对量显然使人能够承受,但事实上,每名誊录的日写量并没有上限——毕竟四库馆是依据实际缮写字数而议叙选拔或计发佣金的,何况随着书写的熟练,速度可以倍增。如此,校对的任务也将倍增,每名分校每天校对量达到了5万字以上[3],年校对量的最大值就是1825万字。对于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从事着校对这一枯燥工作的人们来说,这一数量是相当巨大乃至不能接受的。最后,从实际效果看。乾隆皇帝其实深知如此巨大的校对量是不可能不出差错的,所以,他不仅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对整个写、校工作设立了种种规范化甚至极其严厉的措施来“防患于未然”,而且在《四库全书》告竣之后还通过反反复复的大规模检校以“亡羊补牢”。此类“亡羊补牢”的举措共有3次:第一次是1787年进行的,主要由四库馆总校官陆费墀负责并自掏腰包去检校文渊、文源、文津三阁;第二次是1787-1790年间展开的,主要由四库馆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先后去检校文津、文溯两阁,修订费用亦由两人认赔;第三次是1791-1792年间完成的,主要由纪昀负责并自掏腰包去检校文渊、文源、文津三阁。因为错漏一而再、再而三地暴露,所以要频繁地去检校。尽管这样,1794年春还是发现文渊阁本《盐铁论》缺写卷末《杂论》一篇,等到调取文津阁本查对时又发现每卷首页均漏写“明张之象注”一行,至此,年迈的乾隆算是方悟校书之难了。
在乾隆看来,《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件稽古佑文的国家大事。当年在《四库全书》缮书处担任分校官的人员也基本上是进士出身的,而且大多在文渊阁、翰林院、国子监和各政府机关出任要职。编纂的任务如此重要,校对者的素质如此之高,但形形色色的错漏居然也无法真正地、全面地降伏。据《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7月18日头版报道,著名出版家、中华书局前总编辑傅璇琮指出:文津阁本和文渊阁本两个版本的差异竟达50%以上。这一差异显然大多数是可以从校对角度去理解并研究的,由此可证校对是何等艰难的一项工作。
“校对如扫尘,旋扫旋又生”。只要作者之误和手民之误依然存在,校对的这一本性无疑今日亦然。一方面,再优秀的作者也不全是与绝对真理为伍的,否则,资深编辑金文明所写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书海出版社2003年版)就不会成为畅销书了。另一方面,再先进的电脑排版软件也不全是在“忠心耿耿”地效劳,否则,《咬文嚼字》2002年第7期就不会有6篇文章的第一行文字被电脑莫名其妙地删去,以致编辑部宁愿承受重大经济损失,又全部重印了这期刊物。从而,貌似雕虫小技、实则至关重要的校对,理应受到当代编辑社群在立场上的高度重视。
二、积极与消极:以“陈平原准则”为例
2001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于对作者负责的考虑,询问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是否需要寄回《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的原稿。陈平原灵机一动,请他们将书稿挂号寄来,准备得便时与1998年出版的著作相对照。不久,他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一篇对编辑的功能和职责进行反省的短文。文章指出:对于一个编辑而言,面对作者的文字,看准了,可以“积极”出手;面对专业问题或引文,则最好“消极”对待,尽可能采取保守疗法,而不要轻举妄动[4]。这一被笔者命名为“陈平原准则”的校对理念,对于编辑出版界来说,显然在方法上是相当发人深省的。
细绎陈平原的叙述,可知积极出手要克服的是作者既定的无心之失,消极对待则是为了预防手民可能的有心之过。就前者而言,当陈平原在《散文小说志》的原稿中不小心地将“焚书”、“时弊”误写为“焚术”、“时蔽”,没有将“摹仿”、“刻划”、“其它”规范化地写为“模仿”、“刻画”、“其他”时,足以表明常识性笔误、非规范性用法是作者之误最普遍的情形,此乃“无心之失”。就后者而言,当编辑将陈平原原稿中的“叔孙通”、“米家山水”、“东京以降”、“感慨悲歌之士”、“鄙倍之气”错改为“孙叔通”、“作家山水”、“东汉以降”、“慷慨悲歌之士”、“鄙俗之气”时,足以证明想当然地擅做修改是手民之误最基本的体现,此乃有心之过。
编辑出版事业以文化的积累与传播为己任,专业性的学术刊物尤其如此,从而,在假定编辑在校对过程中已然具备积极出手这一职业素养的前提下,消极对待无疑就成了最值得重视的问题。原因在于,尽管从编辑业务的角度看,编辑是内行,作者是外行,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作者却是专家,编辑则是杂家。这样,即使对于作者在文稿中出现的引文或专业问题心存疑惑,编辑也应该首先在心境上无为而治——暂且认为作者是正确的,然后在行动上有为而发——或者与作者直接交流看法,或者自己去图书馆中查询相关资料,或者双管齐下,以求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
在编校一体的意义上,可说校对工作将关涉标点符号、语言文字、文献史料、思想观点四个方面。前两个方面属于自己的业务,并且始终处于“常态”之中;后两个方面则是他人的专业,而且一直置身于“变态”之内。标点符号是否准确地运用好比一件作品的皮,语言文字是否规范地使用好比一件作品的肉,文献史料是否正确地处理好比一件作品的骨,思想观点是否合适地表达好比一件作品的髓。如果说皮、肉、骨、髓代表着依次提升的四种不同的境界,那么,从标点符号纠错、语言文字校正到文献史料勘误、思想观点商兑,显然再次证明了消极对待远比积极出手更为关键。
在医学实践中,治疗皮、肉是简单的,根治骨、髓则是艰难的。同理,在校对实践中,要不易恒常地做好自己的业务并不难,但要变化无穷地应对他人的专业却不是轻而易举的。譬如,“学战”是一个晚清人耳熟能详的词,历史学者罗志田在一篇讨论近代中西文化竞争的文章标题中就使用了这个词,足见它也正是该文的主题;但是,或许因为这个词不符合今人的习惯,所以文章发表时该词被编辑删掉了,结果——“仅看题目便给人以不甚知其所云的感觉”[5]。正是经由这个例证,我们在此必须一如既往地提倡编辑学者化,亦即,任何一个当代意义上的编辑不仅要以“十字街头”的方式去“泛化”自身的学术性内功,还应以“象牙塔”的方式去“纯化”自身的学术性内功[6]。惟有经常“泛化”地去把握一般性的学术动态、长期“纯化”地去进行自身的学术研究,编辑才有可能与作品展开深度对话,编辑对于作品的消极对待才会转变为一种真正意味上的积极。
要做的不是加法而是减法,要表征的不是错漏百出而是“清洁的精神”,这是校对工作的本体境域。因而,这里还要强调的是,编辑固然可以从职业要求出发为文稿纠正标点符号、错别字乃至文献史料方面的失误,但《著作权法》毕竟不允许他擅自修改作者的思想观点。编辑的职权是有限的,作者的权利才是无限的。问题在于,是否每一个作者都真正懂得善意而又理智地使用自己那一无限的权利呢?在作者尚未做到这一点时,编辑又应该做些什么并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呢?“无错不成书”的惨淡现实,其实注定了我们这个编辑共同体今天必须努力地期盼:当且仅当(实际生产部门)出版前的审校在本体上优先于(行业管理部门)出版后的审读,读者才将拥有健康、良好的阅读命运。
三、“李易简现象”:在默默中永恒
对于《文史哲》这份知名度、美誉度极高的学术期刊,即使存在某个每期必阅、每文必读的理想型读者,他也未必会去慧心地体味该刊主编蔡德贵发表在2002年第4期封三上的那篇文字。这篇文字除了谈校对的重要性外主要关注的是一个人——李易简。
“李易简对文科学报的多年校对,给他打下了丰厚的文科知识基础,使他干起校对来,如鱼得水,如车得路。他左眼盯住原稿,右眼瞄准清样,左手按住原文,右手改正差错。他的一副火眼金睛,就像探雷器,一个个地雷无一不被发现;又像扫描仪,一眼扫去,错字会自动跳出来,无一漏网之鱼。在他眼中,‘牧族敦宗’应为‘睦族敦宗’,‘陈川颖堂’应为‘陈川颍堂’,至于‘附马’应为‘驸马’,‘杨雄’应为‘扬雄’,更是不在话下。甚至于‘闻说奇才盛世行,子平今日又悬□’,他也一眼看出在‘悬’字后面应有一个‘旌’字。功夫老到至此,真让人敬佩。”[7](封三)令人感喟的是,将校对这门绝活演绎到了化境的李易简却只是一个编外校对,而且在其长达94年的人生之旅上历经磨难。
生于1908年的李易简在1962年时因机构精简而退职,从此靠每月领取30元补助金生活。生活的贫困、前途的渺茫以及时代的动荡,促使这个普普通通的下岗工人走进了期刊社,尤其是对当时乏人问津的大学学报情有独钟。1970年他被《厦门大学学报》聘为责任校对,同时也负责校对过其他大学学报。1984年则是李易简校对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直到这一年,他的校对技术被到厦门出差的《河南大学学报》编辑意外地发现,得到赞许;也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做《文史哲》的业余校对。毫无疑问,业务名声的增大使得李易简更加坚定了做好校对工作的精神信念。高峰时期,他同时给40多家学报和多种社会期刊从事校对业务,还校对了5部个人专著以及道光版《晋江县志》。1994年后,由于身体状况方面的原因,他不得不将许多杂志的校对工作推掉了,但始终坚持为《文史哲》进行校对,直到逝世前的一个多月,还在用高倍放大镜校对着《文史哲》2002年第2期……
李易简从1984年起为《文史哲》做的校对勘误表,一期不缺,集稿盈尺,已经成为《文史哲》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其实也是属于整个编辑共同体的,因为“李易简现象”将在校对本体论的态度层面上惠赐给我们最有益的启迪。校对确实不是“手持三尺定山河”的壮观举措,但谁又能否认其“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文化功勋呢?“细心静心责任心,心心相印;汉字数字拼音字,字字正经”[8],这副横批为“沉默如金”的对联或许最恰当地诠释了校对工作的本来面貌及其人文价值。正因如此,对于校对工作,作为职业编辑的我们也必须像编外校对李易简那样充满事业心,“勿以善小而不为”,老老实实地去做,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优秀的成绩,在对文稿的“千锤百炼”中尽最大的可能去召唤并敞开大学学报乃至整个学术期刊的“清洁的精神”。当然,像《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003年聘请知名编辑学专家、河南大学教授宋应离、张如法审读,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每篇文章后对责任编辑、责任校对同时署名,这也是强化校对责任感、提高校对业务的必要措施。
如上所述,《四库全书》编纂的回顾,有助于我们彻悟校对工作的清醒立场;“陈平原准则”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掌握校对工作的合理方法;“李易简现象”的咀嚼,有助于我们拥有校对工作的老实态度。有此清醒的立场,有此合理的方法,有此老实的态度,也就等于我们已经完成对以“清洁的精神”为宗旨的校对本体论的承诺与推定,也就等于我们有能力在“编编辑辑、辑辑编编,涂涂抹抹、抹抹涂涂”的微观语境中参与并达成“匠心编成鸿篇巨著”、“妙手涂出锦霞满天”的宏大叙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将校对工作从雕虫小技上升到本体建构,无疑责无旁贷地成了我们这个编辑共同体在全球化的传媒时代中不断进行身份认同、逐渐强化家园意识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