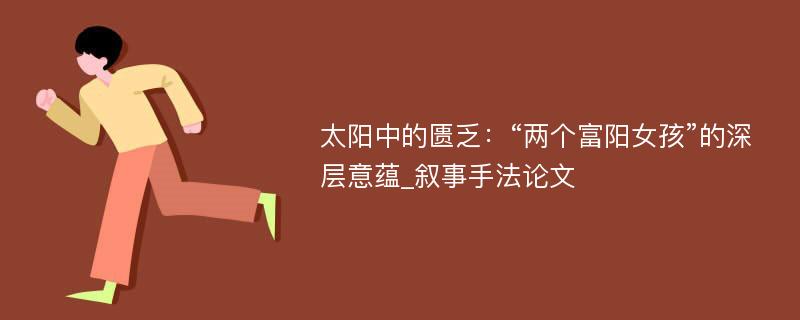
阳光下的剥夺——《两位富阳姑娘》的深层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富阳论文,意蕴论文,两位论文,姑娘论文,阳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6)—06—0082—05
麦家的短篇小说《两位富阳姑娘》,是新世纪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小说发表于2004年,在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上,这篇作品被列为短篇小说第一名,① 可见它得到了权威性的认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夏志清说:“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1] 《两位富阳姑娘》的被发现,正显示出文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和意义,而对它的品评,则可以不断呈现真正的小说杰作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与美学的意蕴。
悲剧的力量
《两位富阳姑娘》讲述的是一个美被无辜毁灭的悲剧故事。故事的背景是“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②,“一人参军,全家光荣”③,穿军装戴领章帽徽最被人艳羡、追慕与景仰,青年人“几乎都满怀当兵的理想”的“文革”时期,具体时间是1971年冬天。被毁灭的这位富阳姑娘本来有着无比美好的人生前景,命运已经眷顾于她:作为一个美丽纯洁但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她被招了兵,穿上军装,到了部队,即将戴上领章帽徽成为无上光荣的女兵。但是灾难却在她毫无知觉的情况下遽然降临。在到部队后的复审体检中,由于她的同乡、跟她一起入伍的另一位富阳姑娘的嫁祸与军医的失职,她被错当成“作风不好”、“有问题”的人而被遣送回家,回家后又被盛怒的父亲毒打和严逼,蒙受巨大冤屈、遭到沉重打击的她,无奈之下只有以死洗冤,喝农药自杀。她死后才真相大白,她是那样清白无辜!她的死因而让人无比痛惜。在清楚了她蒙冤受屈的原因,目睹了她在横祸飞来却蒙在鼓里,冤枉受到残酷的打击,无法反抗更不知道应该反抗什么,无以申诉更不知道什么需要申诉,面对伴随着暴力的道德与伦理的巨大压力和必须作出的生死回答,她只能无助地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过程,这时,故事内外的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无法不产生巨大的惋惜与伤痛,也难以不受到良心和道义的谴责。这位富阳姑娘的遭遇,让每一个有良知、有爱美之心、有恻隐之心的人不忍面对,不敢面对。这样的悲剧故事,使《两个富阳姑娘》成为新世纪文学,也是当代文学中最有悲剧艺术力量的小说。
亚里斯多德说:“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摹仿”。[2]37 又说“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2]8 写好人而产生悲剧效果,即引人产生怜悯与恐惧之情,是因为这里所写的是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④,也就是“好人受困难的折磨”[3]。《两个富阳姑娘》的悲剧力量就来自于“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故事的主人公是个19岁的纯洁的姑娘,皮肤白嫩,胆小听话,“‘就像一只小绵羊一样’,性格内向,懦弱,自小到大对父母亲的话都言听计从”,不会也不敢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尤其在男女关系方面,事后也证明她还是个处女。但就是这样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受到天大的冤枉,被当成最为人不齿的“破鞋”,不仅有“作风问题”,而且有“欺骗组织的问题”,因而受到十分严重的处置,遭到劈头盖脸的打击,在当时的境况下,除了死没有什么能证明她的清白,洗雪她的冤屈。无辜而被加害,清白受到玷污,弱者遭受暴力,真正是“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这个人越是美好,越是无辜,她所遭受的厄运就越有悲剧力量。美好、无辜的人遭受的厄运后果越严重,悲剧故事的感染力就越强。《两位富阳姑娘》就具有这些基本的悲剧要素。在这个悲剧故事里,不仅主人公是美好而无辜的,她遭受厄运的结果也让人惨不忍睹。但它的艺术震撼力,还来自于更重要的悲剧因素,那就是富阳姑娘这个十分美好的生命,是被迫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并且是至亲的人(他的父亲)在误会和误解中致使她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悲剧冲突的双方都是好人,而且是至亲的人,这种在亲人的误会中造成的好人的悲剧,是悲剧中的悲剧。它引起的情感反应不是一般的怜悯和恐惧,而是巨大的憾痛与惋惜。对于悲剧的当事人来讲,这种悲剧的结局更难承受的是施加毁灭性力量的一方,因为真相大白后他需要在悲剧无可挽回中承受无尽的悔恨。一个人在有生之年承受这样的心灵折磨是比失去生命更可怕的厄运,因为失去生命等于磨难已经终止。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两个富阳姑娘》的悲剧效果中才带有让人恐惧的成分,它缘于“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
艺术作品所创造的悲剧性,来自于悲剧叙事。麦家是个叙事意识很强且善于叙事的作家,《两个富阳姑娘》这个故事,其强烈的悲剧审美效果,是从逼真而生动的场面、人物动作与心理的刻画,形象和细节的描绘,以及事件经过与原因的叙述,也就是从叙事行为与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小说用十分富有匠心的结构一步步展现了悲剧事件的发生及其前因后果。铺垫、蓄势、悬念、突转等手法的运用,让故事在层层剥笋后显露出它惨白的悲剧内核,使得故事内外的人心灵不由得不剧烈震颤。作品一开头用陌生化的手法交代了事件的起因:一位富阳姑娘在部队新兵复审体检中被查出不是处女,于是按“老规矩”被退回原籍。接着就推出了它的后果:这位被遣送回来的姑娘服毒自尽了。出人意料的死的结局,是故事讲述兀然出现的一个高峰。因为小说描述给我们的是痛苦而惨烈的死:她是喝了半瓶剧毒农药敌敌畏七窍流血而死的。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眼间变成了一具冰凉的尸体。这具尸体的姿态和颜色是那样怪异,骇人,“让人感到瘮人”,连“在战场上什么样的尸体都见过”的军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小说这样写她死后的身体姿势:
……说她是平躺着的,其实头和脚都没着地,两只手还紧紧握着拳头,有力地前伸着,几乎要碰到大腿。总之,她的身体像一张弓,不像一具尸体,看上去她似乎是正在做仰卧起坐,又似乎在顽强地做挣扎,不愿像死人一样躺下去,想坐起来,拔腿而去。
可见她死得多么不情愿,多么不得已,多么惨烈。小说还这样写她服毒而死后身体的颜色:
……她脸上、手上、脖子、脚踝等裸露的地方,绵绵地透出一种阴森森的乌色,乌青乌青,而且以此可以想象整个人都是乌青的。……她本来是很白嫩的(这一带的姑娘皮肤都是白嫩的,也许是富春江的水养人吧),想不到一夜之间,生变成了死,连白嫩的皮肉也变成了乌青,像这一夜她一直在用文火烤着,现在已经煮得烂熟,连颜色都变了,吃进了当归、黑豆等佐料的颜色,变成了一种乌骨鸡的颜色。
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死。不仅白嫩的身体变得乌青,“她的嘴角、鼻孔、耳朵等处都有成行的蜿蜒的污迹”——“这是血迹”。可以想见这是多么痛苦地死。就算她有道德问题,不够资格当兵,难道应该接受这样的惩处,领受这样痛苦而可怖的死亡?在死亡,而且是自杀带来的死亡面前,生命的尊严和价值陡然凸显出来,原有的是非观念被质疑,悲剧性事件通过情感的冲击唤醒了人们对死者的同情心,同时也就瓦解了小说开始时设置的道德评判。而这种情感的冲击是由小说叙事的文字创造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带来的。
自杀是生命对无法承受的存在困境的彻底逃避,是一个人留给世界的最后的语言。对于陷于罪错压迫的个体而言,消极的自杀是对蒙受冤屈的最有力的申辩。根据小说叙述的暗示,这个富阳姑娘的死就可能属于这种情况,它意味着这一悲剧事件另有隐情。它引起读者新的阅读期待。随后的叙述和交代,就证实这个姑娘的死是被逼的,她在死前留下了遗言,告诉她的亲人,她是冤枉的。既然是被逼死的,自然需要回答是谁逼死了她。又一次让人感到意外和吃惊的是,作出回答的是她的父亲,父亲说:“是我把女儿逼死的。”小说叙事把事件过程引向了悲剧的内核,即悲剧冲突发生在亲人(在这里是“父亲”和“女儿”)之间,并且是强者对弱者施加不应施加的暴力招致悲惨的结果。这一次是通过人物动作的描写来制造悲剧效果的。还沉浸在女儿参军的荣耀里的当村长的父亲,突然遭遇到让他发懵的变故——她刚参军的女儿被部队退了回来,由人武部的同志送到家里,还“白纸黑字告诉她女儿犯了什么错”。女儿当兵未成,反有辱家门,这巨大的打击使他又羞愧又恼怒,于是有了根本不问情由,完全丧失理智的思想和行为。据叙述人描述:
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想说什么,只想打死这个畜生。他这么想着,上去就给女儿一个大巴掌。后来,在场的人武部同志告诉我,那个巴掌打得比拳头还重,女儿当场闷倒在地,满嘴的血,半张脸看着就肿了。但父亲还是不罢手,冲上去要用脚踢她,幸亏有人及时上前抱住他。
父亲的暴行还不只如此。慑于人武部的警告,他一时不敢再打女儿,而是盘问女儿“是哪个狗东西睡了她”,女儿一再否认并说是冤枉的,这样他愈加认定错在女儿,忍无可忍,再一次对女儿暴力相加:
当时一家人刚吃过夜饭,桌上的碗筷还没收完。父亲抓起一只碗朝她掷过去。女儿躲开了。父亲又操起一根抬水杠,追着,嘴里嚷着要打她。开始女儿还跑,从灶屋里跑到堂屋里,从堂屋里跑到猪圈里,又从猪圈里跑回堂屋,跑得鸡飞狗跳,家什纷纷倒地。回到堂屋里,父亲已经追上她,但没有用手里的家伙打她,而是甩掉家伙,用手又扇了她一耳光。还是下午那么严重,她也像下午一样倒在地上,一脸的血,不知是嘴巴里出来的,还是鼻子。
如果说前面描写的这个姑娘死后的样子让人惨不忍睹,那么在这里,懦弱、听话的女儿在不知道自己到底闯了什么祸犯了什么错的情况下,只能毫不反抗、连躲避也不可能地承受盛怒的父亲的痛打,被最应怜爱自己疼惜自己的人打得那么严重,这样的情景令人更其不忍。
人伦中最可宝贵的父女亲情,被野蛮惩罚的暴行所替代,实是人心中最美好神圣的感情遭到了残酷的践踏,这也是一个人可以舍弃这个世界的最大理由。突然而至的悲剧冲突要以死亡来平息了,于是故事讲述出现了最富悲情的一幕。当狂怒的父亲高喊着“打死这个畜生”,被母亲奋力挡住,母亲喊女儿快跑时,“女儿爬起身,却没有跑,反而扬起一张血脸朝父亲迎上来,用一种谁也想不到的平静的语调,劝父亲不要打她,说她自己会去死的,不用他打。”无辜受辱被逼,她只有以死维护自己的尊严,也让受累的亲人得到解脱,何况不明真相的父亲暴怒若狂,没有留给她活路,父亲要她做的选择是:“你要么报出那条狗的名,要么死给我看。”她无法再用语言为自己辩护,只有选择死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她不知道是什么说明她不清白,因而不知有简单的办法可以证明她十分清白)。她做出死的决定,意味着她与父亲的悲剧冲突宣告结束,因此她说出这一决定是那样冷静,冷静得“让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急管繁弦的叙述突然出现一个静场,视觉冲击被内在的悲情替换,悲剧故事向人们的良知发出了询唤,悲剧本来有了回旋的余地。但可惜没有人听懂这样的询唤,因为误会这只制造悲剧的魔掌使人们闭目塞听,没人能够抓住改变事情结局的机会。悲剧不可逆转,悲剧冲突的双方都受着蒙蔽。直到人死后对尸体进行检查,才发现是把人弄错了。经过几经起伏的铺垫和峰峦迭起的蓄势,叙事用一个突转,解开了悬念,暴露出事件的悲剧实质,让人大惊诧,大悔恨,大遗憾。小说叙事这样揭示事件形成过程与真相,使悲剧效果更强烈,它的确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4],唤起人们对悲剧主角的大同情。在知道真相后再回头看这个不明不白受冤枉而死的姑娘,原来是一个多么纯洁美好的生命,真正是一个“比一般人好的人”。她被部队弄错检查结果后,是在亲人的逼迫下,在亲人抛下她之后,一个人死在自己的家里的——不,不是家里,而是在她家的猪圈里。她不愿意她的死玷污亲人的房屋,就是死,她也为活着的亲人着想,可见她一点也不埋怨(她自杀前一个人在堂屋里呜呜哭了半夜那是委屈和伤心以及对亲人挽留的等待)误解她和为了自己的名声而不惜伤害她的亲人。特别是父亲对她那样凶神恶煞,把她往死里逼,她不但不反抗,甚至不怨恨,而甘愿遵从父亲的意志,以死作答,仅给她的严父留下令人心痛的遗言:爸爸,我是冤枉的,我死了,你要找部队证明,我是冤枉的。事实证明,她的确是冤枉的。好人受冤枉得到悲惨的结果,这是人类最恐惧的悲剧。作者在进行这样的悲剧叙事时,故意采用不介入的态度和冷静的语调,与他的当事人身份和故事的离奇、悲惨形成反差,造成悲剧叙事的方法与悲剧事件的视觉的和心灵的冲击力之间的艺术张力,强化了悲剧效果。《两位富阳姑娘》的悲剧力量大概来自于这些方面吧。
谁是加害者
中国小说学会的小说年度排行榜评委会自称有“学会的标准”,即“兼容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水准”。[5] 《两位富阳姑娘》能以第一名进入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想必符合中国小说学会的这一评审标准。除了上面所谈到的艺术魅力之外,《两位富阳姑娘》这篇小说应该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一定的人性深度。
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悲剧,往往由人性与历史的合谋造成。《两位富阳姑娘》这个悲剧,又是有哪些因素导致的呢?或者说,是谁加害于那位清白无辜的富阳姑娘,使她断送了鲜花般美好的人生呢?
从小说向我们讲述的事情经过,我们似乎不难找出把这位富阳姑娘推上绝路的几个人。一是她的父亲。如果不是她的父亲得知她有作风问题而被部队退回,恼羞成怒,发狂般地对她施以暴力和威逼,她最多是蒙羞而活,断不至于丢掉性命。设若她的父亲珍视女儿的生命胜过珍视自家的名声,理智地对待和处理这件事情,说不定还可以查清问题,还女儿清白,女儿重返部队也不是不可能。是父亲的不理智和狂暴将她逼上了死路。父亲是最直接的加害者,也惟有他的加害使这个故事最富有悲剧性。二是跟她一同参军的同乡,另一位富阳姑娘。她才是失去贞操、有作风问题、且不老实、应该给遣返回家的人。她在部队对新入伍的女兵进行例行复检时,被查出已不是处女。由于心虚、感到丢脸和害怕,她在体检军医的询问下,谎报了她老乡的姓名(刚刚入伍,在女兵中她只知道她最熟悉的老乡的名字),借以逃脱肯定有的歧视和可能有的处罚。是她的嫁祸,使自己的同乡蒙受冤屈,不明真情,无法回答父亲的责问,以致更加激怒了父亲,无端与父亲形成悲剧冲突,最后在道德、伦理和暴力的多重压迫与打击下悲惨死去。这个富阳姑娘犯了女性当兵的禁忌而又不敢承担责任,是这场悲剧的起因,所以她是真正的肇事者。不管是否出于故意,都是她害死了自己的同乡。所以,“用军医的话说,即使把‘她’枪毙都够罪!”三是曾经诊断死者“有问题”的那位军医,一个牛高马大的胶东人,军区某部长的夫人。是她的粗心大意、简单从事,以致张冠李戴,让好人受冤领罪。悲剧发生后,她被派到死者的家乡再度查体,发现弄错了人,一脸惊恐,说明她不是没意识到自己充当了悲剧制造者的同谋。事实上,对于姑娘的冤死,她犯有不可推脱的过失。她在夸大别人的罪错时,其实是在掩盖自己的草菅人命。四是作为悲剧事件的见证人,负责遣返姑娘回乡的司令部军务科长。他是被动地卷入这个悲剧事件的。为执行公务,他经手了这件事,经历了他先前没有料到的变故,美差变成噩梦,也因此了解了悲剧的全部过程以及悲剧产生的原因。本来姑娘的死跟他没什么干系,尽管人是他送回的,人死后是他处理的善后。但当真相查清后,他始而震惊紧张,继而厌倦恐惧,最后也反思了自己,不由忏悔起他也加入了制造悲剧的行列。在送这位姑娘回富阳的火车上,不明何故遭到遣返、十分畏惧的姑娘,曾恳求他告诉她犯了什么错误,他也完全可以告诉她,然而在一念之间他却打了官腔,致使这个姑娘失去了洗清冤屈、纠正错误处置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才堕入本来可以避免的命运的深渊。
我们似乎有理由认定这几个人就是悲剧主人公富阳姑娘的不同性质的加害者,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好人遭受厄运负有责任。虽然他们并不是恶的化身,他们并未料到自我开脱、自我保护、对荣誉的顾惜、对耻辱的规避等等这些情有可原的做法,会致他人于死地,但是他们身上存在的人性的弱点,也就是人的自私本性,吊诡地趋善行恶,合伙制造了悲剧。然而,麦家讲述这个发生在特定年代里的悲剧故事,肯定还带有拷问历史的意向。从叙述的设计就可以看出,故事在引导我们追索悲剧的真正导演。这个故事的起点,是一种反讽表达。作为语言多义性的一种形态,反讽是“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6],它“表示的是所说的话与所要表示的意思恰恰相反”⑤。在小说的反讽式叙述中,文字与意义并不相配。“反讽可以毫不动情地拉开距离,保持一种奥林匹斯神祇式的平静,注视着也许还同情着人类的弱点;它也可能是凶残的、毁灭性的,甚至将反讽作者也一并淹没在它的余波之中。”[7] 《两位富阳姑娘》的故事之所以成为悲剧,它的逻辑起点今天看来十分荒诞,女兵到了部队首先要接受检查,看处女膜是否完好。这个荒谬的做法,在小说叙述中并没有受到质疑,相反它是作为一个真理在故事中被所有的人所维护,不管是制造悲剧,还是承受悲剧,或是制造悲剧同时又承受悲剧的人,都丝毫不怀疑它是否合理。叙述者正是毫不动情地拉开距离,平静地、克制地讲述这个以处女膜为轴心的故事的,处女膜好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弱点。处女膜问题是一个叙事前提,从这个轴心开始,展开了惊心动魄、伤心惨目的悲剧,但它自己却安然无恙地注视因它所发生的一切。这就是这篇小说的高妙之处。只有真正理解小说的特点与功能的人才会这样处理有价值的题材,这样讲故事。只要我们感受到叙事的反讽意味,就能领悟这篇小说真正的思想意蕴。就是说,只要逆着悲剧展开的方向,回到故事的轴心上去,制造悲剧的黑手就能被我们捉住。处女膜是故事的纽结。处女膜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祸福,它也就成了祸源,悲剧的诱因。
小说的历史批判意识,也在这里得到显露。姑娘处女膜完好才有资格当兵,这不是军人职业的需要(鸭板脚不能当兵才是,因为鸭板脚影响行军),而是道德需要。处女崇拜反映的是一种道德观念。女性参军需接受处女膜检查,体现了部队对入伍者严格的道德要求。这样的要求发生在“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足为怪,它表明革命队伍追求人的高度纯粹化。这一道德要求来自于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号召中国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8] 解放军一度被视为革命的大熔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就是革命道德的建设被置于崇高位置而产生的价值观。然而革命化和道德至上的结果又是什么呢?《两位富阳姑娘》以个案形式作出了回答。由于处女膜检查的失误,害得一位姑娘自杀,凶手不就是杀死过无数中国妇女的贞操观念吗?原来,革命的政治道德里,掺杂的竟是极为腐朽的封建旧观念。是观念假人之手杀死了这个本该有着美好人生的姑娘。革命追求纯粹化,却是在戕害生命,它的泛道德化的本质是反人道。这就是小说貌似平淡的故事讲述中隐含的革命的悖论。《两位富阳姑娘》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以独特的方式检讨了20世纪的革命历史。
处女崇拜又是一种权力崇拜。道德标准说到底是权力意志的体现。“新兵入伍后,部队要对他们作一次身体和政治面貌的复审。”复审合格,才能戴上领章和帽徽,真正成为部队的人,领章和帽徽象征着一种政治荣誉和权利。所以在新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兵不是公民的义务,而是一种政治权利的享受。部队无形中演变为一个利益团体,它实行严格的准入制。身体和政治面貌就是两个基本尺度,也是绝对尺度。作为男权社会的遗存,女性进入这一团体,还有贞操这个附加条件。失去了贞操,就失去了当兵的资格;失去了当兵的资格,也就失去了一种政治权利。这种政治权利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在反复的强化中,它的重要性和价值可以超过人的生命自身。那位女儿被部队遣送回家的父亲,在得知的女儿是因为有作风问题而被退回,立即羞愧难当,恼怒至极,一方面是新旧合一的道德感使他蒙受耻辱,更重要的是已经获得的政治利益的丧失使他发急、感到绝望。所以,在逼死女儿,醒悟到女儿受了冤枉,经过坚持,为女儿洗清了不白之冤后,他向部队提出的唯一要求竟是让部队带走他的才15岁、不够参军年龄的小女儿。这样的顶替,既可以挽回家族的荣誉,又能够获得失去的权利。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算已经知道部队对女儿的死负有主要责任也无需提出赔偿要求了。
对权利的趋附是人类的本性,但富有悲剧色彩的是,追求权利,必为权利所役。况且在道德化的权利分配背后,往往隐藏着君临一切的权力意志。《两位富阳姑娘》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展示了权力意志通过道德召唤来实现对人的思想控制。8名女兵中的一位富阳姑娘被查出处女膜是破的,这就说明有作风问题了。不仅有作风问题,还有更大的问题,由于她只有19岁,自己说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说明她表上填的和嘴上说的都有问题,这是欺骗组织的问题,比作风问题更大。“欺骗组织,就是对组织、对党、对人民不忠诚”。所以她的问题被看得比那个查出是鸭板脚的男兵的要大得多,“大得到了简直吓人的地步”。就是说,道德缺陷比生理缺陷更严重,因为生理止于身体,看得见,道德关乎思想,不好控制。这里的反讽泄露了革命时代的秘密:加入革命(队伍)的首要条件是“忠诚”,所谓“忠诚”就是交出自己的灵魂。在这样的要求下,人的隐私自然是不能保留的,女兵检查处女膜于是天经地义。政治荣誉和权利的获得,是以隐私权的被剥夺为代价的,其后果是人的生存被扭曲。小说里自杀而死的富阳姑娘的被痛苦扭曲变形的身体,极富象征性,那是道德化的统治意志对生命的扭曲与戕害,也是生命对非人道德的控诉与抗议。死者是被扭曲的,活着的人也无不被扭曲。死者扭曲的身体,折射出加害于她的人灵魂的扭曲。“父亲”是最突出的例子。女儿遭人所害遇到危难,最能给予安慰、保护和解救的是父亲,但恰恰是父亲给了女儿致命的打击,万万不该地亲手掐灭了女儿生的希望,也表明道德观和利欲早就泼熄了他人性中爱与善良的火焰,这是追求人民解放的革命权力意志对人实行普遍剥夺带来的结果。
收稿日期:2006—09—16
注释:
① 参见中国小说学会、齐鲁晚报社主编《2004中国小说排行榜》,作家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② 除了批判、斗争,“文革”也是一个全民学习的社会。当时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
③ 征兵时使用的极有影响力的标语口号。人民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以文学艺术为主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叙事,形成了当代社会的军旅崇拜,至“文革”时期,对解放军的崇拜达到高潮,这一口号更是常用常新,具有极强的号召力。
④ 亚里斯多德说:“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亚里斯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2月版,第38页)
⑤ 参见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