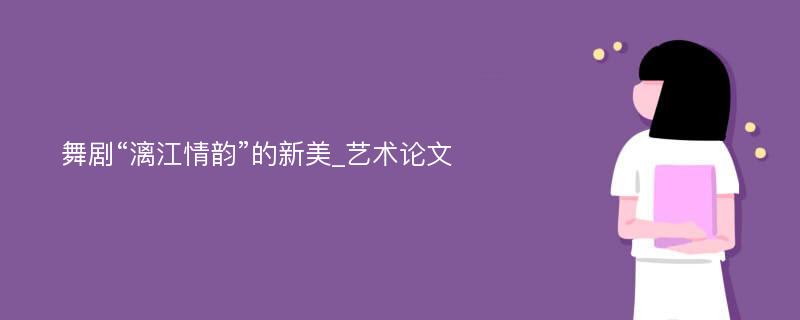
舞剧《漓江情韵》的新和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漓江论文,舞剧论文,和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以为,《漓江情韵》(以下简称《漓》剧)的成功主要在于她新和美的表现形式与其优美、崇高的内容有机地契合、相通和统一。
《漓》剧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三个构成要素,即:创世目标的伟大;爱恋情愫的深沉;自我牺牲的悲壮。这都是与社会人生息息相通的具有积极、崇高和史诗性美的感召力的特质,极有益于观众的审美情趣与审美思考。与上述内容相适应的是她新和美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这是紧紧地托负着她的内容向着艺术的广度、高度和深度拓展、运行的契机。这种新和美的外在形态,遂成了《漓》剧内容与形式——艺术的契合相通,气韵生动,也是最能激发观众心灵感受与审美思考的。
《漓》剧的创编者们在艺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上,有三个在我看来是很关键的突破。
一、《漓》剧在内容的组织结构上,包括剧情结构、人物关系、时空关系等等,不再依托于戏剧思维或文学思维的“规范”框框,使舞蹈真正地成为舞剧内容的表现要素。这是《漓》剧对于过去传统惯例的一大突破。的确,倘若按“舞剧也是剧”的戏剧思维方式来要求的话,《漓》剧剧情,或许根本就不能算是剧情。如:“石扑向大地,擂响铜鼓,阳光灿烂。”这三句作为一段剧情连在一起,倘若以戏剧或文学思维来衡量,既不能作为剧情来表现,也不能作为诗情(诗句)的组合。因为这三个完全不同质的概念,在这里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对于舞剧,不仅可以作为剧情,甚至在《漓》剧中很有利于揭示觉醒了的民族的心理素质和人物的情感表现。用舞蹈主体思维来衡量,这里的“大地”、“铜鼓”、“阳光”,并非是具象的摄取,而是艺术抽象的组合,具有深邃的意蕴:那大地,是铜铸的巨鼓,是民族精神力量与权威的象征,那阳光是民族魂的召唤,标志着人类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和觉醒!
《漓》剧的艺术指导张苛老师曾指出:“不要用戏剧思维来要求舞蹈;不要用文学思维来要求舞蹈。”也就是说,“要确立舞蹈主体思维”。舞剧以舞蹈表演艺术为主体,而舞蹈是以有节奏、能表情的人体动作为主要手段来表现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或其它物的生活情景、情趣。《漓》剧正是在确立舞蹈主体思维的前提下,以淡化故事、淡化情节、淡化人物关系、淡化有限的时空观念和强化人物内心情感的表达形式,来达到无限的抒发情感的自由,从而把作品的审美价值推向无限的境界。这就是她成功之所在。
舞蹈长于抒情而拙于叙事。舞蹈是人体动作的舞蹈,人体动作能真诚、强烈地表现任何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舞蹈在表达情感方面,不仅优于文字、戏剧,也胜过语言。我认为,任何艺术种类或体裁,都有自己一定的表现范围及其方法、手段,都有自身可拓、可塑性的潜在能力和弘扬光大的显性能力,不存在谁依附谁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舞蹈创作总是离不开以文学或戏剧思维主导下的情节束缚,无视或忽视以舞蹈思维为主体的动作情愫的发挥。弄得一时间舞台上千篇一律,一个相貌。至于表现某种深沉含蓄内容和情愫的“情绪舞”类,似乎被列入了创作和演出的禁区,谁也不敢光顾。舞蹈如此,舞剧更不用说了,一个“剧”字,就够吓人的。在过去,舞剧中的“剧”,非以戏剧(包括文学)的思维套路作为创作和评论基准不可。其中,所谓剧情结构的“启承转合”规律,所谓戏剧情节的“矛盾冲突”,所谓人物内心的“思想斗争”,所谓“正反面人物”地位、行为、结局的设置,还有什么“戏胆”、“戏眼”等成了不可逾越的定式和生硬的教条,乃至成了舞剧能否成为舞剧而生存的生命线。这种传统的舞剧创作和舞剧评论基准,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形成了舞剧艺术创作和评论工作的僵化与限制,无疑不利于舞剧艺术创作的繁荣,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舞剧艺术的萎缩。今天我们看到的《漓》剧,她之所以能以其独特的新和美的风貌出现,显然是得益于摆脱上述羁绊。
二、《漓》剧另辟蹊径,突破了依赖现成舞蹈动作和程式化规范的惯例,充分发挥人体动作显能与潜能来传达情感,使舞蹈艺术形式美亦即人体本质美达到表现的自由。《漓》剧以崭新的和奇美的风姿显现于中国当代舞坛,独创了一条新路。
舞蹈艺术形式美必须通过人体美来表现。人体美的本质是什么?就舞蹈这一艺术门类而言,人体美的本质应该是指经过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提炼、运用的身体各部位的动作、动律、神韵、表情等,使认识、情感、意趣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艺术形象外观或外在形态显得美的那种性质。而那种性质的美的获得,就是形式美的表现自由。《漓》剧创编者们明白这一点,也选择了这一点。该剧以石、水、树三种自然形态的客观物质为主要刻划对象,采用模拟、简化、强化、幻化的艺术抽象手段,以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着意表现天地人特定意义的生命形式美。
那“石”,钟情于“水”,艳羡于“树”。与“水”之爱恋,情深意切;与“树”之情结,朦胧缠绵;与天之斗,与地之争,生命之顽强,抗争之豪壮,终成创世之祖,民族之魂!那“水”,既是人曲线的身段、美的双肩,又是水的波纹、水的涟漪、水的涛浪、水的漩涡,她绕着奇山异石,在漓江中流连,一环套一环,成为“石”的“轻柔的怀抱”,绵亘千古而不悔!那“树”,柔美的形态,婆娑的姿影,虽是“勾魂的手”,但却有良知、有灵性、有体温、有爱情、有哀怨、有歉疚、不管她来自月宫,也不管她是仙还是神,最终也要为“石”和“水”的自我牺牲所感化而献出了一切,以同样美的精神风貌留给了人间!……在这里,赋予表演艺术家的不是制约,不是束缚,没有任何人为障碍的设置,有的是遏止不住的创造冲动,是热血的沸腾,是情感的迸发,是表现自由的广阔天地。正是这样地经过编导、演员心灵的再创造,使剧中本为自然属性的石、水、树与人的艺术形象,互为彼此,交替作用,递进组合,构成情结——其间恋慕、鸿濛、沉迷,曾也令人凄婉,但终有所归:“水”幻化为悠悠漓江,“石”幻化为巍巍群山,“树”幻化为香香金桂。一切都在超脱之中,不再有隔膜,不再有哀怨,不再有凄婉,只有爱和美留存于世,循环往复于千古。其审美意义多么悠远、宽阔、无限!
这就是天—地—人的生命形式的美,是美的原质,美的本性!剧中三个艺术形象之豪情、钟情、恋情、爱情、悲情等的展现,没有哑剧表达成份,没有情绪中断痕迹,没有现成舞蹈动作或程式“规范”的干预,也没有生造的高难度动作技巧,更没有为哗众取宠故意搞什么“反律动”的虚饰。《漓》剧也显然是依据舞蹈美学规律,在形象上对石、水、树,进行严格的艺术抽象,即对具象(表象)进行艺术需要的选择、改造、提炼、变形,使之成为新象。这正是艺术形式美的表现自由之功力所产生的审美效果。
三,《漓》剧大胆而创意性地运用元素编舞法作为艺术家的创造天地,并将之纳入意象流动的审美大屏幕,让审美者去品评、领悟其中之新与美。这也是一项高明之举。
元素编舞法,是这几年刚刚引进,在国内刚刚兴起的一种编舞方法。根据这种方法,在人与物间的关系上,就人体对其模拟而言,从元素的发展趋势出发,可以由一个小指头的动作类,发展到全身的动作类,并且还可以能动地由一元到多元,由单向到多向地发展、变化或变形,可以构成一个或一套动作组合,也可以构成一个舞蹈或舞剧片段,甚至还可以构成为一个舞剧的整体动作结构。采用元素编舞法编的很成功很有特色的舞蹈,这些年在舞台上并不罕见。但作为一个大型舞剧来说,采用元素编舞法,贯通全剧,恐怕《漓》剧尚属首例。
元素编舞法的运用和意象流的运用,是贯穿《漓》剧全剧的,可以说它们是《漓》剧在利用新观念新方法于创新上的一对同胞姊妹。根据美学和艺术心理学原理,意象是艺术意念或艺术想象的产物。它强调突出情感在艺术创作中的目的性和统帅性。
什么是“意象流”?“意象流,即意念之象在感情河里流。”(《漓》剧艺术指导张苛语)这个说法再通俗贴切不过了。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不拘泥于现实生活的真实,不拘泥于某一种手法的运用,重视情感的表现和艺术家主体意识、意念造象即意象的渲染与流动性。它常用的手法是:比兴,夸张,回闪、幻化等。因此,在艺术的内容选择、艺术的结构方式、艺术的表现形式等等,都显得比较跳跃、灵活。它能够给外物景象(自然物象)染上一层情感的色彩,使之不再是自然事物自身,而造成为溶合一定认识、理解和想象以后的客观形象;它能使现实情感与主观想象结合起来,把主观感情客观化,构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典型的艺术形象,从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能溶合神话与人话、古代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内容于一身,籍用原始的活力与时代势力的碰撞,善与恶的拼搏,生与死的争斗,汇聚成无羁的联想,狂放的思绪,激荡的情感,磅礴的气势,使作品从内在到外在都得到充分的自由的表现;它能够把意造与实在(虚拟与自然)、华美与质朴恰当、巧妙地交织组合,使作品形成虚实结合、华实并茂的艺术典型或独特的形象风格。为此,在表现事物的过程中,它可以采取既简化又强化,既淡化以幻化的手段,也即简化情节及其过程,强化突出重点,淡化时空关系,强化情感抒发,等等,促使静态意象、动态意象、局部意象、整体意象,都在情感的驱动与发展变化中以及时空、场景的幻化与重新对接、组合中呈现“流动”的令人激赏的艺术画面。
《漓》剧创编者们称《漓》剧的创作方法是“意象流”方法,在我看来是切实的。《漓》剧共由八个舞段组成,在这里,故事情节被淡化了,时空联系被淡化了……但是,人,物,事,环境,场景,却活了,活得有形,有象,有声,有色。非常有效地勃发起编导的创作欲望和演员再创造的激情!
除上面说到的以外,《漓》剧的新和美,在音乐和舞美方面的表现,也相当出色。有道是:“精雕细刻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我深信,刚刚诞生的舞剧《漓江情韵》,在其成长中,经过不断的修改、提炼、润饰和演出,将会成为我国当代舞坛上一株新异精美的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