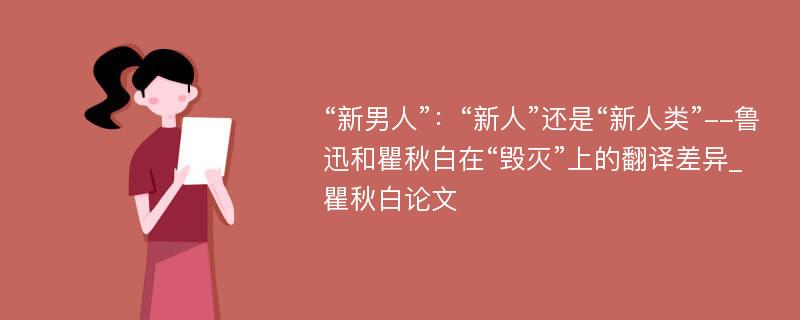
“新しい人間”:“新的人”或“新的人类”——鲁迅与瞿秋白关于《毁灭》的翻译分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鲁迅论文,分歧论文,人类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1年9月30日,上海大江书铺出版了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长篇小说《毁灭》。10月,鲁迅又沿用该纸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①两个月后,瞿秋白致信鲁迅,首先高度评价了《毁灭》中译本的出版,称赞这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②而后,他就围绕“翻译”问题与鲁迅展开探讨,提出了“翻译”的“文化政治”:“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③在接着批评了严复、赵景深的“顺与不顺”的翻译观之后,瞿秋白转而指出,鲁迅的译文做到了“正确”,但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并具体列举了《毁灭》中的句子与之探讨。信的最后,他又特别重提了前面举过的第一个例子,认为其“比较重要”,“不仅仅关于翻译方法”,这就是“新的……人”的问题。④
准确说来,瞿秋白例举的是《毁灭》中译本前收录的弗理契“代序”里引述的小说原文⑤:
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有一种——
“对于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这种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也比不上的。”
更正确些:
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
“渴望着一种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这个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⑥
这是瞿秋白从俄文直接翻译过来的,他自己提供了两种可能的译法,并说第二种“更正确些”。而他要以此来指正的《毁灭》中译本里的文字则如下:
这最后的原因是因为他胸中有一种:
“强大的,别的什么希望也不能比拟的,那对于新的,美的,强的,善的人类的渴望。”⑦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在《毁灭》“后记”里说明过,这篇弗理契的序文是“朱杜二君特为从《罗曼杂志》所载原文译来。但音译字在这里都已改为一律,引用的文章,也照我所译的本文换过了”。⑧因此,虽然“代序”非鲁迅所译,但引用的小说“原文”确系其译笔。小说中的鲁迅译文连续两次提到了“新的……人类”,瞿秋白所谓“新的……人”的问题就出在此。因为这不是简单的措辞推敲,而关乎小说核心意思的理解,所以瞿秋白非常细致地向鲁迅作了说明:
《毁灭》的主题是新的人的产生。这里,茀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个普通的“人”字的单数。不但不是人类,而且不是“人”字的复数。这意思是指着革命,国内战争……的过程之中产生着一种新式的人,一种新的“路数”(Type)——文雅的译法叫做典型,这是在全部《毁灭》里面看得出来的。现在,你的译文,写着“人类”。莱奋生渴望着一种新的……人类。这可以误会到另外一个主题。仿佛是一般的渴望着整个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事实上,《毁灭》的“新人”,是当前的战斗的迫切的任务:在斗争过程之中去创造,去锻炼,去改造成一种新式的人物,和木罗式加,美谛克等等不同的人物。这可是现在的人,是一些人,是做群众之中的骨干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人类,不是笼统的人类,正是群众之中的一些人,领导的人,新的整个人类的先辈。
这一点是值得特别提出来说的。当然,译文的错误,仅仅是一个字眼上的错误:“人”是一个字眼,“人类”是另外一个字眼。整本的书仍旧在我们面前,你的后记也很正确的了解到《毁灭》的主题。可是翻译要精确,就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⑨
瞿秋白解释说,弗理契和法捷耶夫用的俄文字眼都是一个普通的“人”字的单数,不但不是人类,而且不是“人”字的复数。因此,小说中这个意思应该是“新的人”,或者译成中文的“新人”。这一点从“代序”的正文部分也可以看出,因为也是从俄文直接翻译的,所以凡是用到这个词的地方都译成了“新人”,如瞿秋白例举的引文下面就有一句:“但他同时又知道这个新人的日子还没有到来。”⑩隔了一段引文(鲁迅的译文),又有出现:“但是无论如何,这位新人——美的,强的,善的,——已经觉醒了,他挣扎着,要摆脱那过去的遗产,然而这些东西却非常的巩固,因此,新人的诞生,其结果同游击队的命运一样,往往——毁灭。”(11)也就是说,从俄文翻过来的译本(瞿版、朱杜版)用了“新人”,从日文翻过来的译本(鲁版(12))则用了“新的人类”。从瞿秋白所谓传达法捷耶夫小说“主题”的角度来说,只能译成“新人”。“新的人类”非但不准确,而且是不正确的。
对于瞿秋白有关“翻译”的意见,鲁迅有所接受也有所保留,涉及到瞿、鲁二人对“文艺大众化”等问题的理论构想差异,这里暂不赘述。对于瞿秋白所举几个具体译例,特别是“新的……人”的批评,鲁迅则表示接受。他在回信中坦率承认自己的翻译有误,但同时交代了自己翻译之时的思考过程和困惑:“将‘新的……人’的‘人’字译成‘人类’,那是我的错误,是太穿凿了之后的错误。莱奋生望见的打麦场上的人,他要造他们成为目前的战斗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当他默想‘新的……人’的时候,却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13)之所以“默想”后选择了“人类”的译法,原因之一便与底本的语言有关:
“人”的原文,日译本是“人間”,德译本是“Mensch”,都是单数,但有时也可作“人们”解。(14)
依据日译本和德译本,仅就词语本身而言可有双解,并不知道哪个意思合适。就像以日语为例,按照《广辞苑》的释义,“人間”辞条的意思有三个(15):①人居住的地方。世界。世间;②(作为社会存在的,以人格为中心来考量的)人。同时指那个全体→人类;③人物。人品。而根据语境来判别,小说中“人間”的意思只能出自第二个,但究竟是译成“人”还是“人类”,单凭辞典释义是无法解决的,仍需要回到文本,通过上下文的理解来确定。这里,我们会联想到鲁迅、朱镜我、林伯修对卢那察尔斯基《关于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的翻译,三个版本都是重译自藏原惟人的日译本。文中第二节有一个关键的句子:“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现在当和文学相偕,成为向着新的人类和新的日常生活之生成的过程的,强有力地精力底的参与者了。”(16)三人都把原意的“新人”译成了“新的人类”。这说明从日文重译是常会发生这种“舛误”的,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左翼文艺阵营对于“新人”包含的特殊意义尚未有足够的敏感或完全的了解接受。“新人”在事实的层面,语词的层面都有待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产。由此也再度证明,翻译不仅仅是语法语汇的技术问题那么简单,更牵涉到语句语用的深层意义问题,所以才有了鲁迅辩解的原因之二:
他在目前就想有“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我于是想到他的出身,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识分子,由此猜测他的战斗,是为了经过阶级斗争之后的无阶级社会,于是就将他所设想的目前的人,跟着我的主观的错误,搬往将来,并且成为“人们”——人类了。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还自以为这见解是很高明的哩,这是必须对于读者,赶紧声明改正的。(17)
依照瞿秋白对“新人”的解释,有三个方面最为重要:第一,“新人”虽然是普通的“人”字的单数,但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种新式的人”,“一种新的‘路数’(Type)”或者说“典型”;第二,“新人”是“在斗争过程之中去创造,去锻炼,去改造成”的一种新式的人物,因此是要产生于“现在”,而非“将来”的;第三,“新人”不是“一般的人类”,不是“笼统的人类”,而是“群众之中的一些人,领导的人,新的整个人类的先辈”。而在鲁迅看来,莱奋生设想“目前”就有“新人”,似乎过于理想了。连他自己都非无产阶级出身,更何况“新人”是要在经过了阶级斗争,超越或消灭了阶级之后的“无阶级社会”才能出现的,所以那应当是属于“将来”的,不是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到达点,而是全体人们的变革结果——“新的人类”。归纳起来,两人的分歧并不来自翻译的技法,而是关乎小说核心意思的理解:“新しい人間”究竟存在于“现在”还是“将来”?“新しい人間”到底意味着作为“新的整个人类的先辈”的“一些人”还是作为“新的整个人类”的“全体人们”本身?或者,更应该倒过来追问:两人对“新しい人間”理解的不同侧重到底意味着什么?尽管鲁迅说“将‘新的……人’的‘人’字译成‘人类’,那是我的错误”,“必须对于读者,赶紧声明改正”,但他“默想了好久”,认为“太穿凿了之后的错误”并非没有意义,之所以提出来,也表达了即便接受对方的说法仍珍视自己思考过程的某种坚持。更何况,恰恰相反的,鲁迅的此一“误读”、“误译”或许为捕捉他文字深处最真实的想法提供了入口。当然,这些都需要首先回到鲁迅对整部《毁灭》的“阅读”中来考察。
查鲁迅日记书帐,1929年5月2日“同广平往内山书店买书三本”,其中就有“壊滅一本”(18)。鲁迅自1929年下半年起译,1930年12月26日译毕。后又据英、德译本参校整理(19),直至1931年出版。购书之际,正是“革命文学”论争渐歇,鲁迅努力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翻译“科学底文艺论”的时候。而该书的翻译,也是他在翻译了诸多俄国19世纪文学,苏联“同路人”文学之后,第一次译介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毁灭》中译本里,除了小说本文,鲁迅还特意收录了法捷耶夫的自传,藏原惟人的《关于〈毁灭〉》,苏联文学理论家弗理契的《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并撰写了“后记”,此前分章连载于《萌芽》时,还撰写了《溃灭》第二部第一至三章的“译者附记”,更声称自己“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20)足可看出该书对于鲁迅非同一般的意义。
法捷耶夫的《毁灭》问世后,国际国内的左翼文艺界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这并不在于小说写了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刻画了英勇主义的情节,甚至藏原惟人还觉得“不过是写这么一点事而已”,“整个的情节的窘促,和各个场面的兴趣完全不同,也许就是这作品的缺点之一”。(21)各方对小说的称许和关注都不约而同集中在了人物身上,集中在了作者塑造人物的方法之上。如藏原惟人认为:“这作品的主眼,并不在它的情节。作者所瞄准的,决非袭击队的故事,乃是以这历史底一大事件为背景的,具有各异的心理和各异的性格的种种人物之描写,以及作者对于他们的评价。而在这范围内,作者是很本领地遂行着的。”(22)弗理契也认为:“他的主要成功,在于指示我们——可以说在我们文艺中是最先的——其所描写的人不是有规律的,抽象而合理的,乃是有机的,如活的动物一样,具有他各种本来的,自觉与不自觉的传统及其偏向。”(23)就像法捷耶夫自己表达的,他时刻关注着“人”:“战争场面也好,英雄伟业也好,本身都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吸引我兴趣的,是无法在小说人物——他们从未脱离过人的存在,并且拥有为了数百万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至死的勇气——头脑里臆造的普通人的心理。”(24)他概括地说,《毁灭》的主题是“人的精选”,“人的最巨大的改造”,(25)或者是像弗理契“代序”的副题或给小说建议的另一个标题:“关于‘新人’的故事”,“新人诞生的诗”。可以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学少有的开拓性尝试,也是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文学”创作难以企及的高度。(26)
鲁迅对《毁灭》的“阅读”同样聚焦在“人物”,不妨先来看看他为该书撰写的广告:
《毁灭》……不但所写农民矿工以及知识阶级,皆栩栩如生,且多格言,汲之不尽,实在是新文学中的一个大炬火。(27)
《毁灭》……是一部罗曼小说,叙述一百五十个袭击队员,其中有农民,有牧人,有矿工,有智识阶级,在西伯利亚和科尔却克军及日本军战斗,终至于只剩了十九人。描写战争的壮烈,大森林的风景,得未曾有。(28)
两则介绍里,鲁迅都突出了游击队员的组成,不是一个均质的、纯粹的“革命人”组成的队伍,而是农民、矿工、牧人、知识分子各个阶级混在一起的大众集体,正是这样的战士们在进行着革命斗争。在“后记”里,他一开始就抓住了法捷耶夫描写大众“群体”的方法——“从中选出代表来”,也就是瞿秋白所谓的“路数”或“典型”。鲁迅指出,矿工觉悟最高,意志坚定;农民有落后因素,可生死关头还是殒身革命;牧人描写不多,但有果断无畏的品质。而他最关注的还是美谛克和莱奋生这两个知识分子形象。
有意思的是,在藏原惟人的《关于〈毁灭〉》里,是先分析了莱奋生这个队长和“人才”,然后分析木罗式加、美谛克与华理亚的,并且强调的是美谛克和作为矿工的木罗式加的对立,一个虽有流氓习性,却真挚豁达勇敢,一个向往革命,却没有坚固的确信和强韧的意志。在弗理契的《代序》里,也是先指出了莱奋生的“新人”诞生,然后并列说明美谛克、华理亚、木罗式加的旧人或“毁灭”的结局。而鲁迅的“读法”与他们不同,强调将美谛克和莱奋生并置在一起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并没有详细交代莱奋生的出身,只是回忆性地述及了一些童年的经验,藏原惟人和弗理契的分析也没有特别指出他的知识分子出身,或许更侧重他现在的“队长”身份(29),但鲁迅却要把他明确为“知识分子”,哪怕只是在“袭击队中的最有教养的人”的意义上。在美谛克和莱奋生的对比中,表达着鲁迅有关知识阶级与革命关系的认识和设想。
鲁迅首先深刻剖析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美谛克,认为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思想”与“行动”的分裂:
他反对毒死病人,而并无更好的计谋,反对劫粮,而仍吃劫来的猪肉(因为肚子饿)。他以为别人都办得不对,但自己也无办法,也觉得自己不行,而别人却更不行。(30)
而在另一篇“译者附记”里,也曾有类似的说法:“他要革新,然而怀旧;他在战斗,但想安宁;他无法可想,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子——朝鲜人的猪肉——为什么呢。因为他饿着!”(31)特别是从“吃猪肉”这事可以看出,美谛克的分裂不仅存在,甚至不能贯彻到底,所有看似高尚和完满的逻辑,一旦遭遇真切和实在的“饿”,也就显露出了其中的“伪”来。而美谛克对自己的缺点有所自觉,可并不能在“实行”的意义上改正,于是成为了“孤独”的“个人”。尽管鲁迅觉得他能承认“自己不行”,算是“还有纯厚的地方”,但并不因此同情和宽恕他,更说如果读者也对美谛克谅解,“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点,于自己的这缺点不自觉,则对于将来的革命,也不会真正地了解的”。(32)
相对应的,鲁迅接着分析了另一种知识分子——莱奋生,认为法捷耶夫确切指出了他“之所以成为‘先驱者’的由来”。这也就是瞿、鲁二人有关“新的……人”的争辩段落,即第二部第五章“重负”里莱奋生在游击队陷入绝境时的心理活动:
莱奋生满心不安了,因为他的所想,是他所能想的最深刻,最重要的事,——在克服这些一切的缺陷的穷困中,就有着他自己的生活的根本底意义,倘若他那里没有强大的,别的什么希望也不能比拟的,那对于新的,美的,强的,善的人类的渴望,莱奋生便是一个别的人了。但当几万万人被逼得只好过着这样原始的,可怜的,无意义地穷困的生活之间,又怎能谈得到新的,美的人类呢?(33)
为了便于进一步的分析,这里同时附上该译文所据的藏原惟人日译底本,以作参照:
そしてレヴイソンが昂奮したのは、彼が考えたすべてのことが、彼が考えうるもつとも深刻な最も重要なものであつたからである、——なぜというのにこのすべての欠陥と貧窮との克服のなかに彼自身の生活の根本的な意義があり、そしてもしも彼のなかに大きな、他のいかなる望みとも比較することのできない、新しい、美しい、強い、善良な人間への渴望がなかつたならば、なんのレヴイソンもなくて他の誰かがあつたであろうから。しかし幾百万の人々が原始的な、哀れな、無意義に貧しい生活をすべて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あいだ、新しい、美しい人間について語ることがどうして可能であろうか?(34)
引用了小说原文之后,鲁迅说道:“这就使莱奋生必然底和穷困的大众联结,而成为他们的先驱。”(35)既然如此,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鲁迅是如何来“阅读”这一段落的。第一句“莱奋生满心不安了”就很有意思。鲁迅一向讲求“直译”甚至“硬译”,对于日文和中文里有现成汉字相通,意义相近的,一般直接照写,不再另选其他语词,所以经常能从他文章里见到“绍介”、“运命”这类不合现代汉语词规范,(36)实则直接来自日文的表述。但在这里,日译原文是“そしてレヴイソンが昂奮したのは”,“昂奮”即“興奮”,意思跟汉语中的“兴奋”相同,这在磊然译本中翻成为相近的“激动”(37)。也就是说,藏原惟人对俄文原意的传达无误,而鲁迅却有意无意把法捷耶夫/藏原惟人的“昂奮”译成了“满心不安”,前者是积极的、激动的,对自己的想法充满信心;后者则是紧张的、焦虑的,对自己的想法带着游移。如果跟下文联系起来看的话,或许可以做这样的区分:“昂奮”侧重在第一个“新的……人类”,即“倘若他那里没有强大的,别的什么希望也不能比拟的,那对于新的,美的,强的,善的人类的渴望,莱奋生便是一个别的人了”,也就是说,强调了对信念的坚定,对“新人”产生的确信;而“满心不安”更侧重在第二个“新的……人类”,即“当几万万人被逼得只好过着这样原始的,可怜的,无意义地穷困的生活之间,又怎能谈得到新的,美的人类呢?”换言之,鲁迅的读法/译法更强调着作为理想之前提的“现实”的艰难性,革命的艰巨性。而如果用“满心不安”来统摄两个“新的……人类”的话,则恰好构成了所谓“现实底的理想之必要,执着现实之必要”(38)这种鲁迅独有的“现实主义”。
若再引入瞿、鲁二人的翻译分歧,使用瞿秋白的“新人”,则这段里莱奋生的渴望“新人”联系着他作为游击队长对迫切的战斗任务的关注,对克服一切困难,在斗争过程中创造、锻炼“新人”的强调。同时,因为对“几万万人”实况的联想是由上文里美谛克的缺点引发的,所以“怎能谈得到新的,美的人呢?”就意味着考虑如何从群众之中创造骨干,或骨干创造的艰难。而使用鲁迅的“新的人类”,则这段里莱奋生的渴望“新的人类”联系着他作为先驱者对革命前景的认定,只有“先驱”才能以不同于大众的高度从目前的战斗中把握到整体的意义,也就是鲁迅下文说的“施行权力”或“他确信他的力是正当的”,正是对整个社会主义的强大希望与渴求,使他必然和穷困大众站在一起。同时,因为“几万万”大众贫弱、愚钝的现状,目前就想有“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只能等待“无阶级社会”,将其“搬往将来”——并且成为“人们”——人类了。如此看来,瞿、鲁二人的“理解”差异关键在于偏重“结果”还是偏重“过程”,瞿秋白是在“解释”苏联文学中反映的“革命,国内战争……的过程之中产生着一种新式的人”,固然给出了一种生产“新人”的渠道:在斗争过程之中去创造,去锻炼,去改造成一种新式的人物,但鲁迅仍多少带着“中国问题”的“联想”与“设想”,态度微妙地游移于这种“新人”在“目前”出现的可能,仍通过把“新的……人类”“搬往将来”的设置,留出了“目前”的未知的斗争空间。当然,鲁迅最后也认同了瞿秋白的解释,但毋宁说在他那里,正因为多了这一层“误读”的曲折和执拗,才有中国语境下“新的人类”作为远景,“新人”作为现在空间的“不在场者”,更加需要革命的“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39)需要“其间的桥梁”了。(40)
就像上面分析的,鲁迅论述莱奋生必然和穷困大众联结,成为他们的先驱时,对“几万万人被逼得只好过着这样原始的,可怜的,无意义地穷困的生活”有相当的重视,作为“较强”者和这些大众前行的莱奋生深信:
驱使着这些人们者,决非单是自己保存的感情,乃是另外的,不下于此的重要的本能,借了这个,他们才将所忍耐着的一切,连死,都售给最后的目的……然而这本能之生活于人们中,是藏在他们的细小,平常的要求和顾虑下面的,这因为各人是要吃,要睡,而各人是孱弱的缘故。看起来,这些人们就好像担任些平常的,细小的杂务,感觉自己的弱小,而将自己的最大的顾虑,则委之较强的人们似的。(41)
这里说的是“先锋队”或“新人”的重要性,大众以之为“队长”、“骨干”,他们“于审慎周详之外,还必须自专谋画,藏匿感情,获得信仰,甚至于当危急之际,还要施行权力了”。(42)与此同时,鲁迅的这段引文也带出了大众与革命的关系:大众的革命动力不是消极的自我保存,而是来自不下于此的重要“本能”,这种“本能”很大程度是不自觉的,“平常”、“细小”,但属于“活的个体”。通过对这种“本能”的承认和承担,“先驱者”既是“群众之中的人”又是“群众之中的骨干”,与大众一道“前行”。同是知识分子出身,美谛克与莱奋生的另一个区别也就与这有关,如鲁迅指出的,美谛克来到群众之中时,曾感到一种幻灭:“周围的人们,和从他奔放的想象所造成的,是全部相同的人物”,但法捷耶夫即刻说明:“因此他们就并非书本上的人物,却是真的活的人。”(43)而莱奋生正是充分把握了这一点,带着大众“前行”。于是又回到“思想”与“行动”的关系,按照鲁迅的说法,作者于莱奋生自己和美谛克相比较之际,曾漏出他极有意义的消息来:“但是,我有时也曾是这样,或者相像么?”“不,我是一个坚实的青年,比他坚实得多。我不但希望了许多事,也做到了许多事——这是全部的不同。”(44)换言之,这构成了鲁迅从法捷耶夫《毁灭》的“阅读”中逐渐明晰起来的历史意识:正是“思想”与“行动”一致,有“希望”更有“实行”,充分带着对大众“本能”的承认和承担前行,才可能发见“新人”从目前“渡到”将来的“桥梁”。而循着这一路途,鲁迅更可能从“《毁灭》”的序列中不断“阅读”着《静静的顿河》、《士敏土》、《铁流》等等,豫想/豫约着“充满着原始力的新文学”(45),“新国家”与“新人”。
注释:
①迫于当时的出版环境,大江书铺版略去了《作者自传》、《关于〈毁灭〉》、“著作目录”、《代序》和《后记》,仅存译文与插图六幅。“三闲书屋”版则予以补全。该书后来翻印多次,影响巨大。具体的版本流变,可参看周国伟编著《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48-252页。鲁迅译《毁灭》的第一第二部曾刊发于《萌芽》,后收入单行本时做了多处修订,可参看孙用著《〈鲁迅译文集〉校读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因为修订基本属于语句语汇等的调整,而且不涉及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所以除特别指出的地方外,本章所据译文为以“三闲书屋”版为底本的2008年福建教育出版社《鲁迅译文全集》版本。
②瞿秋白:《论翻译》,《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4页。
③同上,第505-506页。重点号为原文所有,以下同。
④参见瞿秋白:《论翻译》,《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512-13页。
⑤弗理契《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中对《毁灭》原句的引用一共九处,瞿秋白在信中都列举了出来。不过他列举的并非是中译本中的译文,而是他自己根据俄文直接翻出的这九个句子,所以他说“不再引你(指鲁迅)的译文,请你自己照着号码到书上去找罢。”参见瞿秋白:《论翻译》,《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510页。
⑥瞿秋白:《论翻译》,《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510页。引号外的句子是弗理契引用时的串连文字,引号内的句子则是法捷耶夫的原文。
⑦弗理契:《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鲁迅译文全集》第5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49页。解放后出版的磊然译《毁灭》里没有收录弗理契的《代序》,并且依据的底本已经是1959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法捷耶夫文集》第一卷里的《毁灭》修订本,跟鲁迅所据藏原惟人1928年日译本及其俄文底本有很大不同(藏原惟人后来也曾根据1947年出版的俄文修订本重新修订了日译本),但大致仍能够找到与这一译句相对应的句子,略作参照:“巨大的,任何其他希望都不能与之比拟的,对于美好的、强有力的、善良的新人的渴望。”参见法捷耶夫:《毁灭》,磊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⑧鲁迅:《〈毁灭〉后记》,《鲁迅译文全集》第5卷,第412页。
⑨瞿秋白:《论翻译》,第513页。
⑩弗理契:《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鲁迅译文全集》第5卷,第249页。
(11)同上。
(12)鲁迅版主要以藏原惟人日译本为底本,但也参考了德译本。
(13)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94页。
(14)同上。
(15)参见新村出编『広辞苑』(第六版),东京:岩波书店,2008年,第2153页。
(16)卢那卡尔斯基:《关于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之任务底提要》,《鲁迅译文全集》第4卷,第375页。朱镜我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到了现在,文艺批评无疑地,是与文学相并地肩负着以强力的精力的参与者底资格去促进新的人类及新的日常生活底生成过程底使命。”参见A.Lunatcharsky:《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底任务之大纲》,朱镜我译,《创造月刊》1929年1月第2卷第6期。林伯修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现在这无疑地是和文学并立而负有这样的使命,即应该成为向着新的人类及新的日常生活底生成底过程之强有力的精力的参与者。”参见卢那查尔斯基:《关于文艺批评的任务之论纲》,林伯修译,1929年2月《海风周报》第6、7期合刊。相对应的,如后来郭家申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中译本则用的是“新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毫无疑问,它当前的使命就是同文学一道,紧张地、精力充沛地投身于新人、新生活的形成过程中去。”参见卢纳察尔斯基:《马克思主义批评任务提纲》,《艺术及其最新形式》,郭家申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26页。
(17)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94页。
(18)鲁迅:《日记十八》,《鲁迅全集》第16卷,第132-133,170页。据《鲁迅全集》第17卷的日记书刊注释:“壊滅《毁灭》。小说。苏联法捷耶夫著,藏原惟人译。东京战旗社出版。”并没有给出日译本具体出版日期。《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中也没有著录该书。笔者手头所持为1952年青木书店出版的青木文库本,藏原惟人在“解题”中说该书翻译于1928年版,1929年出版。但检索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均未发现此一版本。只有1929年南宋书院版,属于“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第7篇”,1930年战旗社版,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小说选集第1篇”,但前者年份对,出版社不对,后者相反。而据鲁迅购入时间为1929年5月2日来看,则可排除1930年版。是否为南宋书院版的误记,或是其他可能,尚无法推定。
(19)鲁迅日记载:1930年11月28日“下午校《溃灭》起”;1931年5月13日“夜重复整理译本《毁灭》”;1931年9月15日“夜校《毁灭》讫”。参见《鲁迅全集》第16卷,2005年。
(20)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94页。
(21)参见藏原惟人:《关于〈毁灭〉》,《鲁迅译文全集》第5卷,第242-243页。
(22)藏原惟人:《关于〈毁灭〉》,《鲁迅译文全集》第5卷,第243页。
(23)弗理契:《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鲁迅译文全集》第5卷,第248页。
(24)フアデ一エフ:「日本譯への序文」,『壊滅』,蔵原惟人訳,東京:青木書店,1952年,第1页。
(25)转引自李辉凡:《二十世纪初俄苏文学思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55页。
(26)如直到后来,鲁迅更以此作为“标杆”,来评价萧军《八月的乡村》那样的作品,说它是很好的一部“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参见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96页。
(27)鲁迅:《三闲书屋校印书籍》,《鲁迅全集》第8卷,第503页。
(28)鲁迅:《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鲁迅全集》第8卷,第505页。
(29)直到1951年藏原惟人为修订版《毁灭》撰写“解题”时,仍是强调了莱奋生的“指导者”形象。参见蔵原惟人:「解題」,『壊滅』,東京:青木書店,1952年,第250页。
(30)鲁迅:《〈毁灭〉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362页。
(31)鲁迅:《〈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371页。
(32)同上。
(33)法捷耶夫:《毁灭》,《鲁迅译文全集》第5卷,第362页。
(34)フアデ一エフ:『壊滅』,蔵原惟人訳,東京:青木書店,1952年,第173-174页。
(35)鲁迅:《〈毁灭〉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365页。
(36)当然,所谓“现代汉语词”的规范在当时也是形成中的东西,对于何为“现代汉语”、“现代白话”有着各种争辩与设想。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跟日语相比较时体现出来的特征。
(37)参见法捷耶夫:《毁灭》,磊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38)鲁迅:《〈艺术论〉(卢氏)小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326页。
(39)参见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238页。
(40)参见鲁迅:《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第150页。
(41)鲁迅:《〈毁灭〉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365页。鲁迅在“后记”中的引文跟他小说里的译文略有出入,原译文为:“驱使着这些人们者,决非单是自己保存的感情,乃是另外的,粗粗一看,是隐藏着的,连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还没有意识到的,不下于此的重要的本能,借了这个,他们才将所忍耐着的一切,连死,都售给最后的目的……然而他又知道,这本能之生活于人们中,是藏在魂灵的深处,在他们的细小,平常的要求和顾虑——也很细小,然而是活的个体——的下面的,这因为各人是要吃,要睡,而各人是孱弱的缘故。看起来,这些人们就好像担任些平常的,细小的杂务,感觉自己的弱小,而将自己的最大的顾虑,则委之莱奋生,巴克拉诺夫,图皤夫那样的较强的人们似的。”参见法捷耶夫:《毁灭》,《鲁迅译文全集》第5卷,第334页。
(42)鲁迅:《〈毁灭〉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365-366页。
(43)同上,366页。
(44)同上,367页。
(45)鲁迅:《〈静静的顿河〉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379页。
标签:瞿秋白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鲁迅论文; 毁灭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