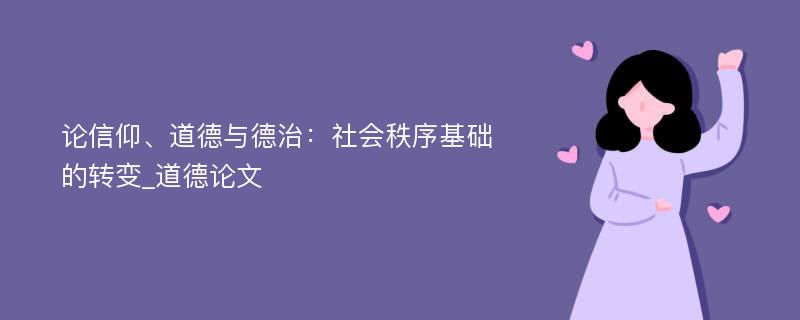
论信仰、道德与德治——社会秩序基础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治论文,秩序论文,道德论文,基础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信仰行为与信念行为
就人的道德行为的性质而言,有两种:一种是世俗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另一种是宗教信仰作用下的道德行为。抽象地看,这两种道德行为都是善。但是,这两种道德行为发生的前提和结果都是不同的。世俗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在根本上是基于人的道德存在的,它的直接前提是人的道德信念,其目标是为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生活的健全。事实上,人的普遍道德行为是能够带来社会整体上的和谐和健全的。而宗教信仰作用下的道德行为则不是为了现世社会生活的和谐和健全,而是为了个人来世生活的幸福。但是,就其客观效果而言,这两种道德行为都能够在社会秩序的获得上发挥巨大作用。
在名义上,几乎所有宗教都会提供对作为最高主宰的神的无私奉献的观念。实际上,宗教道德行为是一种最为自私的行为,是信徒为了自己得到“救赎”而不得不作出的道德行为选择。虽然一些东方宗教在这方面表现的较为隐晦,比如佛教要求信徒“无所求而自得”,即不要在道德行为中注入直接的动机。然而,在实质上,佛教信徒的道德行为还是出于免堕“轮回”之苦的目的。就行为发生的直接前提来看,现世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是基于信念的,而宗教道德行为是基于信仰的。因此,我们需要对信仰和信念的不同加以区分。
从词源学上看,或者从信仰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信仰与信念是有联系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信仰与信念的功能性差异日益明显。所以,对它们作出区分是必要的。在宗教产生的路径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宗教的教义和思想来自于世俗的观念,是将世俗社会中流行的道德主张和规范以宗教信仰的形式再现出来。而且,一旦以宗教的形式再现的时候,就被神圣化了。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也可以把宗教看作是现世伦理精神和道德要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的结果。当世俗道德转化为宗教教义的时候,道德信念也同时转化为宗教信仰。这时,道德自身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它已经不再属于道德的范畴,不再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而是以宗教的形式存在和属于信仰的内容。伦理学探讨善以及善成为可能的途径,宗教也讲善并提出了致善的道路。但是,伦理学设定为道德最高境界的善与宗教所倡导的善并不是一回事,致善的道路也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至多也只是形式上的相近而已。
二、道德行为的社会治理前提
宗教中的信仰概念在世俗的社会科学中受到了滥用。在整个近代社会中,一些富有理想的法治主义者往往带有宗教信仰的情结,他们希望在法制社会中培养起对法律的信仰,并用这种信仰来弥补法律形式化、工具化的缺陷。可是,需要指出,对于信仰的任何期求,都是属于陈旧的意识形态的范畴。因为,任何信仰都是建立在塑造出某一终极信仰实体的前提下的,对法律的信仰也就是把法律置于这样的终极实体的地位上。当终极实体确立起来之后,就会沿着这一终极性实体的边缘,生长起体系化的信仰客体,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个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体系的结构,是属于等级化的结构,是权力关系的体系。所以,任何信仰都倾向于造就等级化的权力关系。反过来,信仰也是与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社会中的信仰普遍化的时代,往往也是权力关系占支配地位的时代。有了权力关系,就会生成权力作用机制,就会产生权力支配的行为。
在权力关系走向衰落的地方,信仰也必然会趋向于衰落。权力关系与信仰是互为前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任何形式的信仰都必然会造成社会的等级化和权力关系化;另一方面,在等级化了的和权力关系化了的社会中,必然会产生出某种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信仰决不是一个社会中的少数人通过努力可以建立起来的,也不是少数人通过努力可以消除的,更不是某些知识体系的发展可以取代的。甚至,一个社会在不同的信仰之间作出选择,也是受着社会的等级化的状况和权力关系体系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所以说,信仰的出现是有着客观基础的,如果一些人不顾及信仰的客观基础,一味任性地去研究如何确立某种信仰体系,或者,如何消除某种信仰体系,都只能属于巴比伦人建造“空中花园”或“通天塔”之类的浪漫追求。
在我们所描述出来的历史图式中,倾向于产生信仰的等级化社会是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严格说来,无论是宗教性的或非宗教性的信仰,都应当是这一社会中的事情。当这类社会开始走向解体的时候,实际上信仰的基础已经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动摇。但是,由于代之而起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还是一个以权力关系为轴心的体系,它所赖以产生的社会中还没有实现充分的实质性平等。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信仰还会存在。但已经远不像在等级化的和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发挥作用的社会中那样重要了。即使信仰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还是生命的依托,但对于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已经不只有决定性的意义了。
在此,我们也看到,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总是与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发挥作用的地方,必然有着某种或某些信仰与之相伴。所以,信仰的存在也可以看作是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特征或者基础。如果一个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信仰危机的话,实际上是统治型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危机。如果经过若干时日,信仰危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重新确立起了信仰,那么这个社会实际上又恢复了它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或者,这个社会进入一个不再确立任何形式的信仰的时期。那么,它实际上是已经找到了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替代形式。
在对人类已有的信仰普遍发挥作用的社会进行考察时,人们不难发现,凡是存在着信仰的社会,都会以权治的形式出现,属于依靠权力进行社会治理的历史阶段。即使在现代社会,凡是具有信仰特性的人群,也会在其中表现出权力关系的线索并会非常注重道德的作用。但是,就其对道德的重视而言,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有时可能是一种假象,信仰并不会产生德治化了的社会治理,不会在实质意义上生成依靠道德的社会治理。因为,虽然信仰对道德意识的生成是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信仰本身并不必然与道德相联系。信仰可以造就道德化的行为结果,但并不一定造就道德行为。有信仰的人,可能会出于极其自私的目的去行善,他行善的行为表面上是道德的,而实质上却不能看作为真正的道德行为。在社会治理活动中,有信仰的社会治理者并不一定时时处处地在他的社会治理活动中作出道德行为选择,反而常常会倾向于使用强制性的治理手段。也就是说,信仰之于人,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力量,是在人的精神创造实体化之后又反过来压迫人的力量。如果人在这种信仰的前提下生成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的话,那并不是道德规范的作用结果,而是信仰的结果。在本质上,并不属于道德性的。道德与信仰是不同的,道德根源于人的自觉,是一种内在的主观力量。
三、从信仰秩序到德治秩序
道德直接生成一种信念,而不生成信仰。但是,由于人们往往容易把这种来自于人的内心自觉的主观信念混同于来自于外在的压迫力量的信仰,才会把道德与信仰联系在一起。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来说,信念的复归是一个历史过程。远古的人类崇拜自然事物,崇拜外在的力量。随着人对自然征服能力的提高,人类越来越发现了自身的伟大,因而开始崇拜自我创造的东西。宗教是从对外在事物崇拜转向对人造事物的崇拜的过渡形式。宗教中的神是人创造的,但又不被承认为人的造物,却被看作为外在于人的存在物。当宗教中对神的崇拜这种过渡形式为新的崇拜所取代时,人的自我创造物开始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近代社会对法制的态度就是如此。其实,人类的一切信仰和崇拜只是现象,信仰和崇拜并不是目的,虽然在个体的人那里常常被误以为目的,而对于群体、对于社会来说,信仰和崇拜的背后蕴涵着对人的某种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建构。至少,信仰和崇拜是有益社会秩序的,而一定的社会秩序是服务于特定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秩序。
由于上述原因,信仰和崇拜一直在人类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和建构某种(些)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努力中绵延不绝。无论是远古的神圣信仰还是近代以来极力推荐的世俗信仰,历史长河流经的每一阶段,都以特定的方式延续着信仰的“蕃火”。人类果真离不开信仰吗?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会得出肯定的答案,但若深入分析,则不必然如此。就人类社会的结构和生活方式而言,越是简单,越倾向于生成权威较强、普遍性较高的信仰,当社会结构和人类生活方式变得复杂化时,信仰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的共同基础就会发生动摇,当社会结构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复杂性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就包含着摧毁一切信仰的动力,不仅神圣的信仰难以成立,世俗的信仰也会受到无情的扬弃。复杂性的社会历史阶段是人类朝着自我的复归,人与自己生存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和合为一,人用理性和现实的态度审视和对待自己和他人以及赖以生存、生活的社会结构制度模式和规范体系。
信仰可以在约束和引导人的行为中带来一种秩序,但它绝不是德治秩序,尽管它与权力作用体系下的等级秩序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德治的客观基础是伦理关系,主观依据是道德,是在伦理关系基础上产生的道德行为模式,或者说是作为社会治理的道德行为模式。德治并不必然与信仰相联系,信仰并不必然产生德治,德治也并不必然要求信仰的支持。信仰与德治在历史上的联系,或者仅仅是表面现象,或者只是一种假象。这也说明,那些所谓的德治,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德治,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着德治的特征而已。我们看到,在欧洲中世纪,信仰就不是与德治联系在一起的。在那个时期,所拥有的那种超强力的信仰恰恰成了德治的对立物。比如,尽管绝大多数宗教教义都主张宽容,事实上这些宗教煽动起来的仇恨远远多于宽容。宽容与一切信仰和崇拜都是不相容的。真正的宽容,也就是一切信仰和崇拜的终结者。反过来说,也同样可以成立,只有在信仰和崇拜终结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宽容才开始萌动,才作为一种普遍行为而存在。
对神的信仰是人的自身能力弱小的证明,只有当人不能够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不能预知自己的未来、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努力行动而无法得到预期结果时,才会有着对神的寄托。社会历史的进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大大提升了人的能力,人类已经可以解决绝大多数面临的问题,因而使对神的信仰已经不那么重要,一旦人可以用自己的行为不断创造人间奇迹,各个宗教杜撰出的神迹对人的诱惑力也就大大下降了。
在西方国家,20世纪的思想家们不断重复着宣布:“上帝死了,”也就是说对神的信仰开始走向终结。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既然失去了神圣信仰对人的行为的约束,那么应当用什么来取代这种约束力量呢?有些思想家和政治家试图确立起世俗信仰来取代神圣信仰。其实,神圣信仰的终结也就是一切信仰的终结,当神圣信仰不再发挥作用时,世俗信仰也不可能填补起神圣信仰消失时留下的空缺。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选择只能是道德,只有道德才能造就出普遍的真正合乎人的社会生活需要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