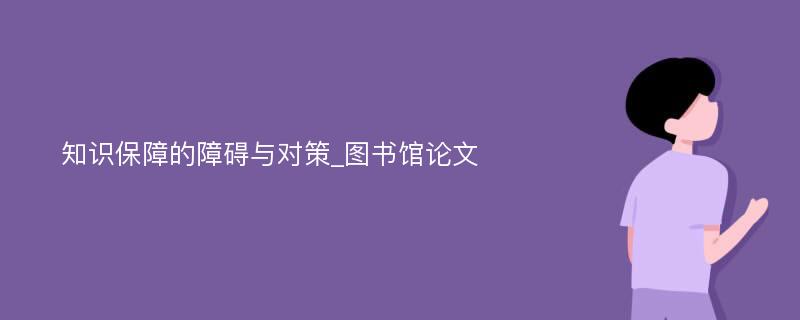
知识保障的障碍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障碍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研究的情报工作从文献保障发展到知识保障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其内涵从知识的载体形式深化到知识的各种类型和形态;其方法从文献的分类序化发展到依据思维脉络的知识聚类与整合;其管理从与科研的行政性“条块”分离走向知识性的多向、多层次联合。“情报”不再仅仅是知识的存在信息,更是具体的知识;情报工作也不仅仅是单向的“服务”,还是营造综合各种类型与形态知识的环境,并且是促进知识环境生成思维“与境”[1]的机制。所有这些变革都体现着以人为原点的特征。以人的知识需要为知识组织的原点,以人的知识管理为构建知识环境的原点。
1 障碍的根源在于图书馆的“依辅性”
以人的知识需要为原点就是对针对性的“意义”的追求,即针对科学思维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来提供“有意义”的知识。因而情报工作需要从传统的文献组织深化到知识组织。但是这种深化正面临着两方面的障碍:一是情报人员的“深化”能力;二是情报部门的“深化”条件。
以人的知识管理为原点就是通过相关人员的隐知识链接而实现人际间的知识交流,实现情报与科研的联合与协调,形成组织成员的互动与联动。因而需要改变科研组织单纯的行政管理方式,而致力于营造适合思维特征与规律的知识环境,以及促进这种环境“与境化”的机制。
以人为原点的情报特征就体现在这样的“能力”、“条件”和“机制”当中。但是,“重科研轻情报”是一些科研机构及有关主管存在的普遍现象,因为文献情报工作向来是“依辅性”的:依附科学组织,辅助科学研究。这种依辅性是历史的,也是人为的。历史上,图书馆作为整合知识的专门机构,却“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从来都是处于辅助地位的”,[2]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其人力、物力和财力一并从属于所依附的机构或部门,其职能永远是辅助性的“服务”。因而节制重重,地位低下;图书馆也“人为地”被列入“依辅”,这不仅是领导们的主观意识,也是图书馆人的自我意识,同时也是研究人员的情报“消费意识”。“为科研服务”是科研图书馆理所当然的信条,因而图书馆人顺理成章地在人事序列中列属“科辅”,研究人员便心安理得地“坐享”服务。人们无从认识情报与科研的共生共荣关系,对研究型的科研图书馆办成了借借还还的“资料室”安然自若,而馆员参与到科研当中却带着半“地下”性质。一些领导对图书馆的要求也就是“天天开门,防火防盗”;或有要求高一点的,就是“人有我有”,聊装门面而已。
在这种依辅观念主导下,“专业对口”成为图书馆进人的唯一标准,而不同专业、多种层次的人才合理配置成为奢谈;馆员进修深造无人过问;图书经费“多年不变”,动辄还要被“挖一块”。所以,科研图书馆的普遍现状就是:缺乏“深化”能力,缺乏“深化”条件。图书馆仅仅是知识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表象已清楚不过,综合各种知识与情报方式的知识保障体系尚不在人们的意识当中,知识管理的“环境”与“机制”自然是天方夜谭。
2 正确认识图书馆的本质属性
图书馆的依辅性是历史的局限和人为的偏见使然,终将随着知识经济法则的健全、完善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淡化,图书馆终将转化为“具有独立性、先导性、主导性的社会机构”,成为独立的知识实体:“知识管理的实体机构”,“知识生产的实体机构”。[3]其实这样的“转化”已经在科学组织的情报工作中初显端倪。
知识实体才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我们说情报工作“从文献保障发展到知识保障是一场根本性变革”就是这种含义。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保障无法依赖以往那种“大而全”、“小而全”的作坊式文献管理,必须是社会化的知识整合、知识生产。其整合的知识范围是社会化的,综合了人类所有相关的已知;其知识生产的意义也是社会化的,是一切社会生产必备的知识资本。在科学领域更是如此,因为“人类的科学研究、知识应用中的80%的劳动将建立在对已有知识的科学整序劳动之上,只有20%的劳动是实践活动的创新”。[4]即80%的劳动是在整合知识,形成相应的知识体系;而20%的劳动是在大脑的知识自组织作用下形成思维的“与境”,“引起知识结构的某种调整”,“在原有的几个概念关系上出现变化”。[5]因此,知识整合与保障不是科研的附属品,更不像传统图书馆的文献管理与保障那样只能作为科研的“依辅”,而同样也是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科研,并与创新的科研共同构成科学研究的完整内涵。失去知识整合这一面,科学就是畸形的,科学终极的知识创新就是没有根基的。
“依辅性”使得科研当中可以社会化、集约化的“80%”囿于科研人员小作坊式的“自耕自种”,知识聚类难免偏狭、偶然与随意,显然已制约了科学的全面发展,抑制着知识这一最重要社会资源的开发与价值实现。
3 消除障碍的对策
淡化情报工作的依辅性,使其真正成为适应知识经济规律与法则的知识实体,这是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个发展过程。虽然“环境”与“机制”的建构还属天方夜谭,但作为情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型图书馆当前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知识保障来赢得自身的发展,率先在科研体系中获得独立的地位,成为完整的知识环境与机制建设的“先导”,成为整个图书情报事业发展趋势的“先导”。
首先应是观念的更新。各级科研管理部门的领导及相关人员都应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增强知识保障的自觉意识,不再把情报工作仅仅看作是科研的辅助,只重视知识创新的那“20%”而忽视知识整合的“80%”,而是将这“80%”与那“20%”同样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因为“80%”的知识整合是更普遍的社会需求,具有更普遍的社会意义;即使在科学研究的内部过程及成果当中,我们依然不难看到这“80%”与“20%”的依存关系。因而知识整合也应当是科学组织的基本社会职能。正是基于这种知识经济的现实和认识,科学研究的组织不再是封闭性的,而应当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共同体”,是知识的整合与创新的共同体,即所谓“科研”与文献情报工作协同并进的共同体。
其次,加快图书情报立法及相关制度建设,增强知识保障的强制性。忽视情报的损失是潜在的,但也是不可低估的。科学界常有投入巨资和人力而进行了重复研究,常有刻苦攻关而到结项时却发现别人早有专利注册,更常有一些课题本身就缺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或者没有新意。这还不包括因信息屏蔽或缺失而造成的判断错误和决策失误。因而图书情报立法是科学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知识经济的必然。必须,也只有通过立法才能保障图书情报工作发展壮大的一切必要条件,包括各级各类型图书馆社会职能的认定,图书情报人员的多学科、多层次配置及岗位资格任证,图书情报经费的财政比例或占所属单位经费总额的配比,以及图书馆作为知识实体的一切社会运作的法律依据。
在科学组织和规划中,更应当对情报工作做出具体细则。比如将与学科属性对应的知识整合与组织作为研究目标之一,作为组织的一种基本社会职能,而不仅仅是“科研”的辅助;在课题设计中要有知识保障的硬性规定,注重“与境”生成的环境因素,以减少判断与选择的随意性;在人员组合中要考察知识构成及其交流、协调机制;在经费配比中要考虑到知识组织的系统性、连续性、前瞻性,以及知识开发的基本物质和技术条件。此外还应规定一些合理的多向投入办法和规则,比如由科研管理部门对课题经费按比例提成,注入知识开发;支持图书情报部门与有关单位开展知识资源的共建与共享,减少重复;多途径、多方位地接纳社会资助,以及以资源优势来广泛开展社会性的有偿知识服务。
第三,确实把图书馆作为独立的知识实体来建设。传统的手工加脑力方式无法承受网络时代的海量信息,只能是“一箪食,一瓢饮”。图书情报必须数字化、网络化:知识的数字化整合、网络化检索。因此,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应当切实纠正“重科研轻情报”的倾向,以对情报工作的具体支持、扶助及要求来改善和增强其“深化”的条件,把整合知识的图书馆与创新知识的研究所等同对待,统一规划,加强协调,如在科研规划中确立与科研目标一致的专题文献分析项目、专业数据库建设等专项知识组织计划;在科研管理中规定具体的情报工作考评方案;在行政上根据情报工作的特点而给予图书馆适当独立的运作权限,促进其个性化、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实际上许多研究所及研究人员早已走向社会,并主动地将所承接的社会课题中的知识整合部分按市场方式交给图书情报人员去做。这虽然还是自发,但体现了图书馆向知识实体发展的趋势和迹象。
第四,图书情报人员不能驻足于分类编目的文献序化,还是吃大锅饭的状态,等着天上掉馅饼,脱不掉“依辅”的劣根性,而应当努力地自我提高,自我更新,不仅要做本行的专家,还须成为有关学科的行家,懂得知识环境下的情报过程,从而增强从文献中析出情报的“深化”能力。如此才能与研究人员形成沟通,理解其思维的不确定,通过在科研体系中积极的知识保障作用来提升自己的价值和地位,赢得有关领导和研究人员的承认与尊重。
第五,知识保障的最终实现还在于研究人员的情报接受。因而研究人员同样需要更新观念,改变思维方式。作为情报认定和利用的主体,研究者自身的情报接受能力是无法靠外界来“保障”的,那种忽视知识环境利用,满足于经验性的浏览、追溯的情报方式实在有类于狭隘的小生产作派,严重滞后于时代的步伐。因而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情报意识、情报悟性和情报技能,不做被动的受惠者。瑞典情报学家菲埃尔勃兰特指出:“促使人们积极利用图书馆情报资源的一种方式就是教育读者如何从可以利用的资料中获取情报”。[6]这些“可利用的资料”今天已扩展到知识的各种类型与形态,并随着组织的知识管理深化而在逐步形成多向多层交互的知识环境。情报的接受者不能还是只会简单的文献浏览与追溯,或一般性的网络信息检索,而必须专心于、致力于对于知识环境中的“意义”加以理解(评价)、联想、感应、判断,以及由此而做出最佳选择。
总之,知识保障不是图书馆单方面的事,也不仅限于人类的“已知”,而是一种直面思维的、容纳各种各类知识的、多向多层次交互的情报体系。然而这种“保障”的保障却在于把图书情报工作从先天的“依辅性”中解放出来,并在于引入知识管理的模式来建构促进思维的知识环境与机制。在这种环境与机制作用下,科学的组织才能真正成为部门之间联合与协调、成员之间互动与联动的、知识保障的组织,成为知识的整合与创新共生共荣、协同并进的“科学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