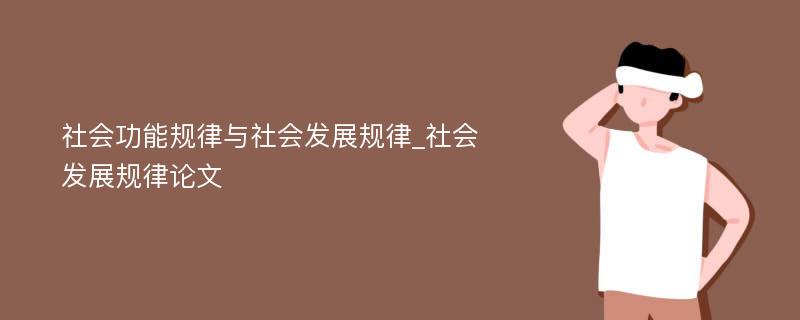
社会功能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发展规律论文,规律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往往把社会运动的规律表述为“自然规律”和“自然历史过程”。完整地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规律的观点,首先应该作出社会功能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区分。否认或忽略这一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区分,如同常见的那样,把社会运动规律等同于社会发展规律,就无从展示马克思社会运动的“自然规律”这一基本观点的丰富内涵和严密的科学性。而且,这种偏颇的理解有时也会给社会实践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一、作出社会功能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区分,是马克思本人的科学发现,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是否还发现了社会功能规律?答案原本是肯定而明确的。但是,由于后人对马克思社会运动规律观点的理解出现不应有的偏颇,而且由来已久,因此,要弄清这个问题,就有必要从马克思是以怎样的方式表明自己既发现了社会功能规律又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说起。
《资本论》第一版于1867年问世后,马克思为自己的著作在“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3卷第15页)而颇感欣慰。同时,马克思也注意到, 欧洲某些学者“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各种相互矛盾的评论所证明”(同上,第19页)。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方法是“辩证方法”和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同上,第20页)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翻译并摘了伊·伊·考夫曼评论《资本论》方法一文中的一段文字。其中包括下面三句话。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3 卷第20页,引文中重点号系引者所加)。
马克思对考夫曼的这一段评论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3卷第23 页)马克思的这一肯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称赞考夫曼对自己的“实际方法”本身的描述是十分恰当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接受了考夫曼对自己运用辩证方法发现的两类社会运动规律即“那种规律”和“发展规律”所作的概括。在认定考夫曼的描述反映了自己的科学立场的同时,马克思注意到考夫曼虽能成功地描述自己的辩证方法,却不能正确地评价这一方法。马克思继而在这篇著名的跋中,又通过纠正考夫曼的误解,向世人解释了自己具有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神秘形式的辩证法的本质区别。
显然,考夫曼教授的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他对马克思的社会运动规律作过细致而深入的研究。这不只是反映在他对社会运动规律作出了“那种规律”和“发展规律”的区分上,还表现在正确地说明了马克思发现这两类社会规律的顺序——“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3卷第23页)而且, 考夫曼对两类社会规律的概括也是字斟句酌,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对两类社会运动规律各自的性质所作的规定。这样,在我们知道考夫曼作出的“那种规律”和“发展规律”的区分是符合马克思本意的同时,还得到了为马克思首肯的两类社会运动规律的定义。如果考虑到马克思“一般是不下定义的”(《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卷第110页)那末,这两个定义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可谓弥足珍贵。考夫曼留下的唯一缺撼是,他当时还无力给“那种规律”一个特定的称谓。12年后,另一位俄国人弥补了这个缺撼,将“那种规律”直接称为“活动规律”。他就是弗·依·列宁。
列宁在1894年出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和《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两篇文章中,至少不下五次地把“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并列起来使用,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两个方面详细地论述了这两类社会运动规律。
列宁认为,《资本论》的问世之所以标志唯物主义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一个重要的根据在于,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发展”(《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卷第112页引文中重点号系引者所加)。而且还“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同上,第110页)。在从辩证法方面论述这两类社会规律时,列宁以同样的篇幅转述了马克思摘引过的考夫曼的一段评论,并说明马克思从对《资本论》的无数评论中挑选出这一段评论,“是因为这段对辩证法的说明,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十分确切的”(《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列宁指出, 马克思的辩证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同上,第135页)。列宁在另二处还进一步说明, 辩证法之所以要求研究社会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首先是因为每一个社会经济形态本身都客观地存在这两类社会规律。“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一种这样的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同上,第372页)。 “……而这种经济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是需要作客观研究的。”(同上,第404页)
列宁的上述分析是有充分根据的。马克思形成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观点,并作出社会活动(功能)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区分,是马克思彻底改造神秘形式的辩证法使自己思想走向成熟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使在旧哲学中相互隔绝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实现有机结合的必然结果,而绝不是从外部强加到马克思的理论上去的。
众所皆知,马克思在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的相互关系上的观点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未形成自己“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卷第118页至119页)。而在马克思完成了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综合之后,认为,“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3卷第9页)。马克思的观点发生这样的转变,是他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重新观察和研究社会的结果。面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和运用,又使马克思更加确信只有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同上,第23卷第410页)。应该说,正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使马克思“……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卷第110页)。
由于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形态看作是历史客观存在的过程或发展阶段,而且是即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3卷第11页)的过程或发展阶段; 同时也是由于马克思把生产力的水平和“现实生活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3卷第410页)。作为观察和研究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出发点和根据,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必然还要去做另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通过准确地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上,第13卷第20页)。马克思发现并证明了这种必然性,并把它称为“自然规律”。“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正在实现的趋势”。(同上,第23卷第8页)。那么, 马克思这里说的“自然规律”又是什么性质的规律呢?显而易见,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本身固有的规律。这是通过自己“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从而维护和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发挥作用的规律。一句话,这就是考夫曼说的“那种规律”和列宁称谓的“活动规律”。
马克思是首先发现社会活动(功能)规律,然后才发现社会发展规律的。这是作为既是唯物论者又是辩证法家的马克思研究社会运动规律经历过的研究过程,也是唯物辩证法所要求的不可颠倒的理论顺序。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3卷第24页)。 马克思只有发现了一个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才能发现这个社会消亡的条件;只有先解释了世界,然后才能去论证如何改造这个世界。这个顺序像一个机体只有先存在才能死亡一样,是不能颠倒的,也是不应该颠倒的。正因为这样,如果说马克思只发现社会的发展规律,却没有发现社会的活动(功能)规律,也就显得十分荒谬了。
二、在当代条件下,前苏联学者研究社会功能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取得的某些进展
列宁发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社会功能规律及其与社会发展规律相互关系的研究,总的来说是处在停顿状态。直到1962年,前苏联学者B ·П·罗任打破了这种不应有的沉寂。他指出:“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功能规律之间的区别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在我国的一些著作中一般都没有作过这样的区别,而是将社会的一切规律都归结为社会发展规律。然而在列宁的著作中,是既谈到了社会发展规律,又谈到了社会功能规律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上述两种规律反映的是不同的相互关系”。(B ·П·罗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导论》李广泉、王书坤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罗任对功能规律的称谓,没有沿用列宁当年使用的“活动”一词。应该说,列宁用“活动”一词称谓考夫曼尚无力概括的“那种规律”,也是较为恰当的。只是在自然科学、“一般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了长足发展的今天,用“功能”替换“活动”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因为按现今的理解,功能不仅包含活动本身,还包含活动的能力和功能发挥的目的性。
在罗任的研究中,他认为功能规律反映社会经济形态的实际活动力,反映社会生活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现象。罗任这一定义使用的“实际活动力”,是颇有份量的。它强调功能规律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社会联系与社会关系,只能是历史自然形成的并客观存在着的,而不能是潜在的或由人为促成但还没有成熟的。罗任还根据两类社会规律各自的作用范围和内容的不同,区分出分别属于功能规律和发展规律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
自罗任提出应该重视社会功能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区别以后,两类社会规律问题在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学者中间愈益受到重视。这表现在两个研究方向上:一个方向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为依据,进一步整理他们区分出社会功能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探讨马克思形成两类社会规律观点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对两类社会规律的研究始于何时的问题上,Г·A·巴加图里亚认为,从1844年4月起,“马克思不论在研究社会功能规律和发展规律方面,还是在论证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都前进了重要一步”。(B ·A ·巴加图里亚:《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的形成》,载《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沈真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86页)。B·П·库兹明在自己颇有影响的著作中,以相当大的篇幅重复引证和评价马克思当年曾摘引过的考夫曼的一段评论。库兹明指出,马克思对考夫曼一段评论的肯定,表明马克思“对世界上存在的最复杂的系统——社会——进行了深湛的研究,从而给我们留下了对社会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实用逻辑,留下了进行此种研究的最重要的原则”。库兹明认为,考夫曼的一段评论概括出马克思辩证法的三个特点,表明“马克思的辩证法首先是社会系统的辩证法”。(B ·П·库兹明:《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贾泽林、王炳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78页—181页)。
另一个研究方向是,两类社会规律的研究进入70年代后开始和“一般系统理论”结合起来。诸如A·П·亚历山德罗夫,B·Г·阿法纳西耶夫,B·Г·维诺格拉多夫等许多学者, 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论述或关注过两类社会规律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只要是系统,就必然具备综合属性和规律性,社会这个最复杂的系统当然更不能例外。而用系统方式认识和管理社会,“不揭示功能规律,就不能想象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整体的自我管理系统,也就不能区分一种形态与另一种形态的差别、显示出每一种形态的质的特征。……社会系统组成成分的相互作用特点(它来自这些组成成分的本质),是社会系统特征的主要规定者。离开功能分析是不可能揭示、研究这一特征的”(B ·Г·阿法纳西耶夫:《系统与社会》贾泽林、苏国勋等译,知识出版社第153页)。 在这一方向的研究中,阿法纳西耶夫对社会功能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作过比较充分的论述。
阿法纳西耶夫在运用系统方式认识和管理社会系统的范围内对两类社会规律的研究,带有明显的系统分析特点,他对社会功能规律的规定是:“功能规律是把这种或那种社会经济形态描述为相对稳定的系统,这个系统在某一个(有时是很长的)时期内保持自己的实质特征和质的规定性。功能规律反映系统的结构、构成因素和要素的组合,反映活动和功能发挥的秩序,反映系统各组成要素的时间和空间联系,反映这一系统与同它有功能联系的系统的关系。换言之,功能规律是社会系统在其根本性质范围内运动的规律”(B·T·阿法纳西耶夫:《社会系统的功能》,载前苏联《社会学研究》1980年第2期。 参阅阿法纳西耶夫《系统与社会》贾泽林、苏国勋等译,知识出版社第148页)。 较之考夫曼的定义,阿法纳西耶夫还注意到功能规律发挥作用的空间方面,而在时间上说明了有时是“很长的”时期。另外,他尤其强调功能规律要求社会系统稳定地和长期地保持自身的实质特征和质的规定性。
“发展规律,它所描述的则是系统发生质的改造的机制,即一个系统灭亡,另一个新的、较先进的系统取而代之的机制。发展规律是系统质的更替的规律”(B·T·阿法纳西耶夫:《社会系统的功能》载前苏联《社会学研究》1980年第2期。 参阅阿法纳西耶夫《系统与社会》贾泽林、苏国勋等译,知识出版社第152页)。 较之考夫曼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定义,阿法纳西耶夫的上述规定增加了系统分析的内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述社会发展规律时,认为“质的更替”是可以分阶段进行的,“发展规律不仅可以说明一个社会经济系统为另一个更先进的系统代替的机制、顺序,而且还可以说明在系统基本质的范围里的(先进的或后退的)变化,系统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B·T·阿法纳西耶夫:《系统与社会》贾泽林、苏国勋等译,知识出版社第152页)。阿法纳西耶夫的这个“补充”, 究竟是丰富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容,还是由于他把“系统质的改变和系统质范围内程度的变化等同起来而模糊了这一规律的性质,还有待于做更深入的研究。
从70年代初到前苏联解体前的一段时间里,社会功能规律及其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相互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已对社会发生影响。“功能和发展”、“功能规律与发展规律”作为科学概念,不仅为哲学、社会学和从事社会管理研究的学者接受并以相当高的使用率出现在他们的著述中,并且成为社会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常用语汇。
三、社会功能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各自的历史使命、作用方式以及两类规律间的相互关系
在考夫曼的定义中,已经包含对社会功能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各自的历史使命、作用方式所作的基本要点式的描述。至于两类社会规律相互间的基本关系,这不仅为马克思规定的两类规律的性质所决定,还反映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基本观点中和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分期的论述中。在当代条件下,人们研究两类社会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并非仅仅出于理论上的需要,尤为重要的是,以马克思的观点作为指导思想去观察和管理社会。这就需要从表现形式上对两类规律各自的历史使命、作用方式、特别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详细的解释。本文下面围绕上述问题所作的探讨,虽然是力图从马克思的社会运动规律的基本观点出发作出阐述,但毕竟包含个人的某些理解,只能是一种粗浅的尝试。
功能规律是每一个社会经济形态本身固有的规律。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存在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生活的种种现象以及现象之间相互联系的秩序(方式)是受这类规律支配的。功能规律把社会中一切现实的东西都认为是合理的存在,维持并表现社会既成结构的性质和稳定性,借助于它所能支配的种种社会现象、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来保证和促成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这正是社会功能规律的历史使命所在。功能规律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它的作用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类规律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以完整而明显的方式直接地作用于种种社会现象、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从而保证既成社会的正常运转。
发展规律是未来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反映者,它是促成新的、更强大的生产力代替旧的、低水平的生产力的规律,它是促成新的、更先进的社会关系代替旧的、落后的社会关系的规律,它是促成低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向高级的社会形态转变的规律。发展规律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的历史使命在于:促成社会不断地进化和进步,并最终使既成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为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至于说到发展规律的作用方式,它较之社会功能规律要复杂得多。这首先是因为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方式在其存在的两个阶段——发展规律与功能规律在旧社会经济形态中并存的阶段和发展规律在它所反映的新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形成的阶段——是不同的。关于这个问题,不妨结合对两类规律相互关系的分析一并加以阐述。
社会功能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相互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一是在发展规律的生长、发育和成熟过程中;二是在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整个人类历史的宏观进程中。
从第一个角度看,每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具体的发展规律,总是在它要否定的那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孕育和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规律和功能规律并存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母体”中,发展规律必须依赖于功能规律才能发育和成熟。而且,发展规律也不会一下子整体地成熟起来,它往往是首先在社会的一个领域或几个领域逐渐地积累起与该社会经济形态固有的功能规律进行“较量”的力量。例如,物的依赖关系,在封建社会的晚期首先在商业和金融业等领域成熟起来。发展规律在功能规律起支配作用的社会母体中逐渐地发育和成熟,不断地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创造着它所需要的因素、条件和前提。在此时,发展规律虽然也发挥作用,但总的来说,它作用的范围不是整个社会,而且即使是在能起作用的领域,它作用的形式也往往是隐蔽的或间接的。
在两类社会规律于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并存的时期内,发展规律总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隐蔽到公开的过程。当发展规律所代表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产生以后,这个具体的发展规律便演变成这个新社会经济形态的功能规律,并开始以功能规律应有的作用方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此后,在它不断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它又促成一个与自身相对立的并最终要取代自己的规律——代表另一个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的生成与壮大。尽管发展规律是代表未来的规律,但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客观存在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的功能运动总要比社会的发展运动更为重要。换言之,对一个社会经济形态而言,功能规律是主要的规律,而发展规律是次要的规律。历史暂时也只能作出这样的安排,因为功能规律所支配的社会如果不能长期地正常运转,发展规律所需要的社会因素、条件和前提也就不能完全形成。
从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宏观历史进程来考察,发展规律永远是主导规律。正是发展规律体现出现存社会的“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并且总会成功地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来临。发展规律从弱小到强大,从在一个或几个领域与功能规律抗争,到最终将其取而代之,是由一连串的创造、进取和革命实现的。这期间,新与旧的搏斗为人类留下了种种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真理与谬误,美好与丑恶的生动史实。最终,总是发展规律所代表的先进的、革命的力量战胜功能规律代表的落后的、守旧的势力。尽管这种碰撞和斗争往往是艰难而长期的,但历史殷殷以待的那个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终会到来。黑格尔生动地描绘过这一新旧社会交替的时刻:历史(社会)“……静悄悄地向着他的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世界的结构,……但这个逐渐地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然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象闪电一般照亮了新世界的形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版上卷第6页至第7页)。
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宏观历史进程,是在社会发展规律的引导支配下完成的,并且仍在继续地进行着。社会经济形态一次又一次地更替留下一条长长的历史轨迹,人们完全有理由把这条轨迹看作是社会发展规律运行留下的一条线。不过,不应该忽略更不应该忘记的是,发展规律的这条线,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点”连结而成的。这一个又一个的“点”恰恰是由于社会功能规律长时期地稳定地发挥其支配作用才能出现的。如此说来,如果没有功能规律这些“点”,又那里会有发展规律这条“线”。因此,从人类社会的宏观历史进程来看,社会功能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原本是相互依赖和互为表里的。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如果不能正常地发挥其功能,也就不能有所发展;相反,如果功能的发挥不是以发展为目标,则必将丧失其自身的存在价值。现象层次上的这种功能与发展之间的相辅相承的关系,也反映在作为本质层次上的功能规律与发展规律的相互关系上。
综上所述,马克思发现两类社会规律并揭示出二者的相互关系,不仅向人们展示了某个社会经济形态自身运动的机理,而且深刻地揭示出社会经济形态更替促成人类社会实现连续文明的机理。马克思这一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完整的科学学说的建立,使他创立的“社会经济形态”概念获得了确证,也使他的社会运动的“自然规律”的基本观点具备了实质性的科学内容。正因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观点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严密的科学性,它在理论上是不容置疑的。而且,经验早已告诉人们,在管理社会的实践中对两类社会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容不得半点含糊和任何一种偏颇。倘若夸大功能规律而忽略或无视发展规律,会使人们看不到社会的新增长点和实行社会局部变革的可行性,从而使社会发展速度过缓遭到陷于停顿。反之,如果夸大发展规律而忽略或无视功能规律,会诱使人们把社会萌芽状态的东西误当作成熟了的新事物,把明天甚至后天才能做的事情纳入了今天的议事日程,从而也就难免会采取一些“每小时都在倡导,每分钟都在进行,而后来每秒钟都在证明其不巩固、不稳定和不可了解的前进步骤。”(《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33 卷第442页)。
※“ΦУНКЦИЯ”,既可译作“功能”,又可译为“职能”。国内译著,后期多采用功能一词。考虑到本文使用的译名的一致性,未征得原译者的同意,引文中原为“职能”字样的,一律改为“功能”。特此说明,并致歉意。
标签: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经济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