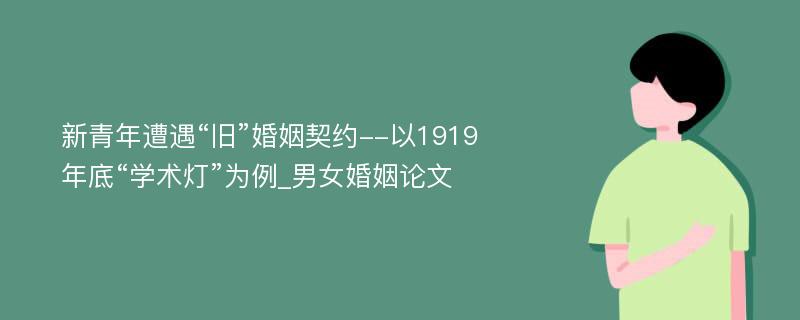
新青年遭遇“旧”婚约——以1919年底《学灯》讨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婚约论文,为例论文,新青年论文,年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5)01-0117-08 近代中国婚姻家庭史的研究,曾是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热门话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社会风俗史和婚恋思潮的论著,就宏观勾勒了婚姻家庭观、婚礼、婚俗等方面的变化趋势。①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者,则对“新”、“旧”史观、男性精英文本、女性自己的叙事、出版媒介做了批判性的反思。②在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台湾和大陆学者探讨民初婚恋观时,有的试图在方法论上运用国外妇女史研究的理论,有的从具体文本或个案入手,注意观念与现实的矛盾。③前人的研究成果给了笔者启发,有些研究的视角和思辨性的论述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有些研究方法仍值得反思,比如:以部分文人志士的言论来说明人们家庭生活的变化;截取不同时间、地点、语境的片段材料,线性串连出社会的变迁;写作中有“现代”的价值评判。 那么如何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推进呢?若关注个案,却局限其中,甚至与前人在相同问题上使用的材料都较为雷同,而无发覆,这样的研究意义不大。但是从某种程度而言,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窃以为也许可从几个方面努力:一、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对待文本或个案,要进得去出得来;二、在时代的脉络中明白具体的人、事,体会历史人物思想行为的多面性;三、写作立论时,避免理论先行和价值评判,应在论述中揭示历史的复杂性。接下来,本文以1919年底《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对“男子可否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妻”的讨论为例,尝试以上述方法对婚恋问题延伸探讨。 一、晚清“传统中国”婚姻择配形象的语境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婚姻”的结合不是基于男女的爱情和幸福,而是为了孝顺父母和繁衍后代。明清律例规定男女婚配权在父母手中,这是“传统婚姻”的“重要特点”,“符合礼法的要求”。[1]诚然,《大清律例》把男女婚姻的主婚权赋予他们的尊亲,很多案例也显示家中的长辈习惯按自己的意愿为后辈安排亲事,甚至在后辈幼年时就为其定婚。但是若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限于评判这样的择配方式,那么无益于对历史事件做同情之了解。 尊亲乐于早替晚辈谋婚事,而且倾向于在熟人圈中择配,或是基于彼此的情谊,男方读书聪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促因,这类故事在一些晚清名儒年谱中得到流传。比如:道光九年(1829年),裴荫森七岁,拜同邑庠生卞文英就学,他“读书聪慧”,卞先生曰:“吾欲得快婿也!”故将女儿许配于他。[2]幼年定亲的撰记文风有溢美谱主之嫌,但在科举盛行的时代,择婿重才学、慕功名的现象可能也是事实。张謇在年谱中记到:同治九年,十八岁,应江南乡试,中一等十六名。“至隶学籍后,议婚者百余家。”先是,璞斋先生的夫人孙氏看中张謇,但没有议婚。乡试发榜后,孙夫人兄长见张謇考中,便促其姐议订婚事。他们提出两个条件,一须居城,一须合买宅同居。张謇不愿与父母分家,谢绝了这门亲事。他另外求婚徐氏,因徐为农家,富有田业,徐女能“持衡册课佃人”,而张家也有田,母亲希望有一位懂得田事的媳妇做帮手。[3]这个故事还说明,张家讨媳妇有多种现实因素的考虑,婚事的议定是儿子与父母沟通协商的结果。 女性在自己的婚事中似乎比较被动,但这不是绝对的现象。明清某些贞女的例子可以这样解读,她们在守贞问题上坚持己见,以激烈的自残行为反抗夫家退婚,反抗再被父母配婚,这也是她们争取婚事主动权的方法,守贞其实是“独身”的特殊生活形态。④清代华南地区有的女性自梳不婚,她们靠做女工,女佣而独立,甚至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财源,有的女性完婚后不在夫家随丈夫居住(不落家),这些情况为我们展现了婚姻问题的另一面相。⑤ 晚清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中国婚姻择配形象,被来华外国商人,基督教传教士,以及逐渐了解到西方文化的中国读书人营造出来。1872年苏州的一位美国新教牧师就认为中国连姻一事,“悉遵父母之命,半惑媒妁之言。”婚后伉俪有乖,难保反目;“西国连姻则不然,男女及年,父母皆命自择,一语既成,终身无悔。”[5]这样的比照,常常被论者置于更宏大的中西文化比较的语境中,从而得出孰优孰劣的判断,借家事论国事,隐含中国当变法之意。1887年《申报》登载文章《原俗》,主张以西人之长补中国人之短,文章举例中国人与西人对待婚配的不同态度,“西人婚姻必从男女之所自愿,使男女先会面若朋友然,往来数次,各相爱悦,然后告之父母,为之婚配。中国人闻之颇以为异,不知男女之欲,本乎所性初,不可强为。中国之婚姻,男女初不见面,但凭媒妁之言,重以父母之命,强合成婚……此又西俗之优于中国者也。”[6] 中国夫妇之间有无感情,感情深浅如何?这样的话题引起一些来华外国人的兴趣。1899年,英国在华商人立德的妻子Mrs.Alicia Little向母国的读者介绍中国人的生活:“我们一向以为,爱情与婚姻紧密相连,但在中国,二者各自独立!”[7]英国传教士麦高温认为中国家庭的维系靠爱,但他不说中国人结婚是因为有爱。他惊讶于新婚夫妇在婚前从未见面,没有互相表示过爱,也没有通信,表示海誓山盟,更没有到对方家中拜访,以增进彼此的了解。[8] 以改良社会风俗、实现国富民强为己任的中国读书人开始重新阐释个人、家、国之间的关系,他们在自由、文明等新概念的语境下,把男女关系、婚姻问题纳入国事的论述范围,进一步论述“中”、“西”婚俗的差异。至少在1901年,“婚姻自由”一词已经出现,男女自行择配是婚姻自由的指标。该年三月,梁启超在日本办的《清议报》登载一封来信,作者托名“凤城蓉君女史”,文中有语句显示其为广东人。“她”开篇就说:“平男女之权,夫妇之怨,自婚姻自由始也。”然后用“自由”、“文明”、“天演”、“群治”等新概念的词汇,在进化论的语境中,解释欧美是太平的大同社会,文明的自由社会,男女关系是平等和谐的。[9]在1903年的名著《女界钟》里,金天翮谈到中国人的婚姻生活与欧洲人的婚姻生活有差异,把它们上升为野蛮与文明的分野,并从进化论角度论证中国时下的婚姻处在媒妁时代、卜筮时代和金权时代,他还赞美“西国”一夫一妻的婚姻是神圣、洁净的爱力作用。“婚姻者,世界最神圣,最洁净的爱力之烧点也。”[10] 这些新词汇所阐释的观念,是清末以来中国社会思想转变的关键。婚姻与自由、与男女平权观、国家文明进程挂钩,正是清末西学东渐背景及维新变革语境下读书人的发明。而且随着报刊媒介的出现和增多,这些论述有了传播的平台。民国以后,尤其是经历新文化运动破旧立新的打造,自由的婚姻观与所谓“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择配行为愈加水火不容。 二、应对“父母之命”:新青年理想的恋爱观 清末,男女之爱也被推崇和升华。陈撷芬认为“吾中国人心散乱,皆因无爱情耳!苟女子一旦幡然而明,知国为至宝,彼岂不以其爱父母,与夫从一而终之爱情,移爱于国,移爱于同胞乎?其结团体也,必致永久不散,死生相共矣!”[11]有革命党人把爱情与国运挂钩:“社会何自成?成于男女之交合,基于男女之爱情,人类无爱情即无社会。男女之爱情深者,其家必兴,其国必强,其种必蕃盛。”[12]也有人把爱情看做世间最大的“凝合力”,“盖凡人皆有一种慈悲性,爱情即寓于慈悲性之中,故其爱情盛者,其爱国之心亦盛。”[13]换言之,理想的夫妇关系基于男女爱情,理想的男女爱情又可外化为爱国之情。从爱情的角度审视夫妻关系的方式,象征近代婚姻价值取向的产生。 民国以后,“恋爱”一词风行,既指男女之间的感情心态,又指男女交往相爱的行为。1919年,瑞典教育家爱伦凯(Allen Kay)的婚姻家庭观传入中国,她认为无论怎样的婚姻,有恋爱便是道德的,即使经过法律手续的婚姻,没有恋爱总是不道德的。婚姻是男女双方绝对自由的结合,不受形式的限制。[14]爱伦凯的思想经北大罗家伦介绍,又被其他鼓吹新式婚姻观的青年们在报刊上频频宣传,影响较大。李达更是猛烈批判无爱的婚姻:“夫妇间若无恋爱便无道德,离婚也可再婚也可。若勉强敷衍,就变成了一对机械的男女。男子好比嫖客包娼,不过是要满足兽欲,女子好比妓女包吃,永久卖淫于某男子,不过是一种得钱米的手段。”[15] 在恋爱至上的思潮中,1919年10月28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起讨论男子可否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妻问题(简称“一个问题的讨论”),这一话题的制造,再次激发了五四新青年对婚姻问题的兴趣。至11月23日编辑宗白华宣告讨论结束为止,登载文章30多篇,发表意见者31人。翌年2月,留美学生潘建卿的文章被登载,至此讨论才告停。 能确定的一些讨论者的真实身份:郭虞裳,南洋商业公学校长,中华工业专门学校教员,寰球中国学生会会员,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16]沈雁冰,北大预科毕业,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已婚。[17]王崇植,就读交通大学,[18]有父母代定的未婚妻。施存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他投稿《学灯》时,另一篇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文章《非孝》,也于同年同月登在《浙江新潮》上,此文旋即引起浙江政界、学界的轩然大波,施存统被迫离校,1920年他东渡日本,接受了共产主义。[19]瞿爱棠,在上海中华公义会设立的贫民学校任职,[20]当过《劝业场日报》的主编。[21]张闻天,1917年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是沈雁冰弟弟沈泽民的同学,1918年初与父母代定的未婚妻结婚,1920年留学日本。[22]宗白华,曾读金陵中学,同济医工学堂中学部,1916年升入同济预科部,但他无心学医,离校自学德国文学和哲学。1919年8月协助郭虞裳编辑《学灯》,11月正式接任主编一职,1920年赴德国留学。[23]谢循初,金陵大学毕业,1919年留学美国易理诺大学,1920年转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心理学。[24]余鹏(投稿署名),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童子部会员。[25]吴保丰,交通大学学生,1923年入美国密歇根大学。[26]邰爽秋,东南大学学生,1923年入美国芝加哥大学。[27]王会悟,沈雁冰的表亲,湖州湖郡女校毕业,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工作,1920年认识李达,第二年两人结婚。[28] 十五位男性不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妻,都认为恋爱是婚姻的要素。侯可久说:“爱情就是道德,爱情以外无道德。不是自由意志的结合,便是不道德的爱情。”[29]田业表示为求幸福计,为发挥“平等、自由、博爱的共和精神”,应“绝对不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妻,若“顽固”的父母不许退婚,那只有终身不婚。隐涯认为父母代定的婚约剥夺了人生的“自由”、“平等”、“幸福”。邰爽秋总体主张不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妻,但是假如定婚时自己满意,以后眼界高了,拿“牛马婚姻”为借口想要离婚,这样的青年当被“唾弃”。瞿爱棠说要打破“机械式”的婚约,“要破坏到底,方才可以说建设。”觉非认为“结婚是恋爱的果子”,解决婚姻问题首先要普及教育,打破轻视离婚、再婚的心理,还要增加女子经济的能力。谢循初和周了都高呼“恋爱神圣”。张闻天主张自由恋爱,男女社交公开。宗白华认为“婚约须建立在自由恋爱的原理上”。 Vy生和少澂认识到社交未公开,打破“专制机械的婚姻”,害处不少。姑且“酌量的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妻(前提是订婚时经过了自己同意)。沈雁冰勉强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妻,男子娶了旧式女子,可以使她有知识,“解放”她,让她做个“人”。[30]吴保丰主张不必立刻解除婚约,改良社会不可太缓,也不可太急,男子要做妻子的导师,将新思潮灌输给她们,使她们觉悟。沈炳魁主张承认父母代定的婚约,他的理由是:社交不公开,男女教育不普及,旧势力太强,使得青年没有能力实行恋爱自由。 有六位男性觉得应视情况而定。王崇植分析到:“觉悟”的青年男女,都不满意父母代定的婚姻时,可解除婚约;有“觉悟”的男子与“没有解放”的女子被父母定婚,男子表示不满意,想解除婚约时,需双方都无精神上痛苦才行;“觉悟”的女子同“没有觉悟”的男子定婚,女子表示不满意,尽可解约。[31]赵康提出男女可先请父母同意他(她)们认识联系,若两人产生恋爱则结婚,若不合就取消婚约。昂霄、青心认为若未婚妻与自己有同等学识,那么应该承认婚约;若她“顽固”,没有“新思想”,就绝对不能承认婚约;若男子有喜欢的第三者,只可牺牲未婚妻。潘建卿认为是否承认父母代定的婚姻,因人而异,恋爱是婚姻的主要原因,但婚姻不止于恋爱,婚姻的成否还在于“是否合乎社会的制裁”。他主张建立教育和经济的生产机关,收容脱离家庭的男女。[32] 女性的态度中,浙东女子王扫石认为“恋爱是婚姻的唯一条件”。絮因女士说到,新青年们都说要妇女解放,所以他们当然得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妻,不应以她美、恶、新、旧、有才、无才来论;新女子不满意未婚夫,则可以解约。Miss Y.K.King不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夫,“不甘心为旧制度牺牲自己的幸福”。王会悟主张做得到“人道主义”的男青年可以不废约,做不到的索性解约。幽清女士认为“爱情最神圣”,可以与未婚夫通信,了解他考察他,不满意则解约,解约不成,大不了脱离家庭,等待时机与父母缓和。 讨论者有基本共识:婚姻当自由,以爱情(恋爱)为要素。而男女自由结婚的条件是双方要有交际认识的可能,换言之自由结婚须有社交公开的环境。讨论者们提出婚姻自由、恋爱结婚、社交公开的诉求,恰恰迎合了此时“男女同校”运动的舆论。上述已知身份的讨论者,都曾是或正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甚至有些彼此认识或互为朋友,同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少年中国学会是青年活动团体,会员大都从事教育实业,该会发起的宗旨之一是“转移末世风俗”,[33]主要干事王光祈、康白情、徐彦之等都是北大学生,他们正是鼓吹男女同校、社交公开的先锋。[34]王光祈更是直言不讳地对沈雁冰说,男女交朋友是两性调剂的问题,这是他主张男女交际的根本理由。[35]身为“新女性”的王会悟也曾在《少年中国》杂志发表文章支持男女公开社交。 《学灯》编辑宗白华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他曾致信少年中国学会的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提出编辑月刊的几点意见,“我们对于一种事体,一种现象,一种主义,一种学理,还没有彻底的了解觉悟,就不应当拿出来鼓吹青年……至于一切新主张,新名词,像自由恋爱等类,尤其要在科学上,社会学上,人类进化史上的彻底研究,方才可以讨论,还说不到主张。”他希望《少年中国》的文章,篇篇都有“学理的价值”,评论社会的文字,“有自然科学的根基”,“有实际现象的考察”。[36]宗白华的编辑理念在他自己编辑《学灯》时得到了体现,“一个问题的讨论”就是非常实际的问题,经他筛选登载的文章,大都既有观念的论证又有解决问题的主张,天马行空喊口号的文章较少。 三、知易行难:新青年婚恋的困境 “一个问题的讨论”中,是否以牺牲自我达到解放女子、改造社会的目的,即是否对旧式女子实行“人道主义”,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沈雁冰坚持“人道主义”观,却遭到许多人批评。也许是因为他的恋爱论让人误解了,他说:人会变,恋爱会变。“少年时候的爱情延长到老时,是否同是这爱情呢?”还是由于两人共过一生,共育儿女等因素沉淀出来的“夫妇爱”?结婚、离婚不应以恋爱为要素。既不涉及恋爱,那么男女在人格和精神上都不会苦了。男子娶了不社交无知识的“可怜虫”,便可引伊到社会上,解放她,让她做个“人”,这岂不比单单解约,独善其身好得多么?世间一切男女,莫非姊妹兄弟,援手救自己的姊妹,难道也要忖量值得与否,也为着恋爱么?(他附注:“文中所有的‘恋爱’指性的恋爱,所有‘爱情’指普通所谓爱。”) 沈雁冰区分了“恋爱”和“爱情”的概念,他首次说到“恋爱”一词时,后面括号英文单词Love,若用同义替换法解读,那么“Love=性的恋爱”。他的意思是恋爱有性的因素,以性欲结合的夫妻关系不会长久,结婚和离婚都不应该以性欲为要素。他区分了恋爱和爱情,爱情是普通的爱,换言之是博爱,可以是手足之情。正因为没有男女之间道不清的情愫,无性欲的驱使,无精神上痛苦,所以不会离婚。他坚持“人道主义”观:“诸君是以自由恋爱看得很重,我是以利他主义看得很重。诸君仿佛以破坏手段改革,我愿以建设的手段改革。”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与自身婚姻状况有关。1918年的农历春节一过,他就与儿时被祖、父选定的孔家女儿结婚了,新娘是缠过脚的女子,婚后他才发现新娘只认得孔字,还有一到十的数目字,她闭塞到不知道北京和上海。他给妻取名德沚,送其进学堂,但改造计划不大理想,毕竟德沚过了求学的最佳年龄,在家没有学习的兴趣,进学堂又感到吃力。[37]尽管学业无大成,但她在丈夫的影响下投身妇运工作,也算有所改变。[38] 同样主张“人道主义”的还有王崇植,他说道:“稍为牺牲一点,等到结了婚,息心静气把伊的性情学问陶冶一回。大概女子的性情,柔顺的多,刚悍的少。训练了一番,虽则我们不能得到十分自由,家庭幸福也决不至完全没有。”他讲述了亲身经历:他的婚姻在幼年就被订好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向兄长提出抗议,却遭亲友的批评,而且引发了未婚妻家里的风波。后来他觉得未婚妻也是人,如果为着自己的幸福却让她做“弃妇”,恐怕她只有自杀吧!想到这些,他便“为人道主义屈服”,承认了未婚妻。 讨论中有部分共识:若新女子不满意未婚夫,尽可解约。若父母给儿子定亲的是名新女子,男青年可以承认婚约。而男子若有喜欢的第三者,只可牺牲未婚妻。其中侯可久的话最为尖锐,他认为女子被解约后如果自杀也没什么要紧,“反而是种解脱”,“新思潮进来的时候死掉几个人,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然而,我们读到这样的话,切不能误以为作者的思想就是如此简单。用激烈的言语破旧立新,这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惯用的手段。一年后,侯可久的妹妹云凤(“旧式”女子)因舅母的说合嫁给了“面貌不扬,态度荒唐”的人,她不能承受婚姻的痛苦,侯可久愿意“牺牲一切,帮助伊脱离婚姻”,但他没有成功,1922年云凤厌世自杀,成了“旧婚姻制度底下的牺牲者”,侯可久非常伤心。[39] 当《时事新报》热火朝天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湖南长沙发生了一起新娘在花轿中自杀的惨案。死者赵五贞,受父母逼迫嫁给同城商人吴凤林做填房。悲剧引起报刊舆论的关注,长沙周南女校的几个师生还追踪报道此案,她们把矛头指向“旧礼教”,并评价《学灯》的讨论:“万恶的婚姻制度不知坑死了多少女青年。但是我为什么单指女青年,因为男青年对他父母所定的未婚妻尚有商量的余地,所以《时事新报》上提出‘现在青年对于他父母所定的未婚妻应该怎么样?’一个问题就引起了许多的答案。或合或离,他们都有完全自主权。女青年的自主权恐怕除掉‘不自由毋宁死’六个字外没有别的答案了。”[40]且不论男青年是否真有“完全自主权”,但男性知识青年至少可以在报纸上发表对婚姻的看法,而很少有女性能够做到,没有读写能力的女性连“发声”的机会都绝少。 三十一名讨论者中,自曝被定婚的有两人。王崇植纠结之后承认了未婚妻,但Miss Y.K.King仍在抗拒中,她是名17岁的女学生,在几个月前被定了亲,她的反抗没有成功,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如果读了这些讨论的文章,便相信如此多解决退婚的办法是有效可行的话,就会落入讨论者们臆想的陷阱。因为Miss Y.K.King的无奈让我们警醒:“诸君说得天花乱坠,我还是一筹莫展!”人们也许易于控制自己的思想,可以在心里不承认父母代定的婚姻,但实行退婚之举,却不是容易操作的事。 四、民国初年退婚、离婚的法律环境 在众多讨论者中,只有一人提到通过法律解决退婚问题。欲结婚先退婚,这正是“五四”以来新青年遇到的特殊情况。不承认父母代定婚姻者,也是主张退婚或离婚的人,然而这种离婚是单方面的意志,没有法条可供援引。1912年,法典编纂工作尚未启动前,民国政府决定暂时援用清代律例(废除与民主国体抵触各条),至于“大清民律草案”,因清廷未审议颁行,所以民国政府决定不予援用,此后民事案件的处理,依照宣统二年(1910)《钦定大清现行刑律》(简称“现行刑律”)中的相关规定。 《钦定大清现行刑律》是由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对《大清律例》删订而成,关于男女婚姻的律条,修改不多,仍然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或父母已故,由余亲主婚,携女改嫁的寡妇有女儿的主婚权。婚约的解除依下列几种情况而定:已定婚但毁约再定者,后定之婚无效;若自己离家在外,家中尊亲为自己定了婚事,那么这门婚事也是有效的,若在外未成婚却自行定婚,那么自定的婚姻无效,应从尊亲所定;婚期已过五年,女方无过而男方不娶,或男犯罪女犯奸者,可解除婚约。关于离婚,主要针对妻犯“七出”,但丈夫逃亡三年不还,妻可告官离异。[41] 清廷对自由结婚持反对态度。1907年学部奏议女子师范学堂及女子小学堂章程时,就提出务必“严切屏除”“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如不谨男女之辨及自行择配,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事)。”[42]1909年,留日归国的浙江女子张维英在江西某女校任教习,设立了“自由结婚演说会”。该事被学部所知,遭到取缔。[43]在新律层面,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也不承认自由结婚。编撰者在“婚姻”章的立法说明中讲,自由结婚只是一种理想。青年们总有少不更事,或考虑不周的时候,让他们自由择配,容易产生负面效果,引发婚姻悲剧。“婚嫁为平生大事,苟大拂乎男女之意,恐将来夫妇反目,即难忘家室之和平。”但“不取自由婚者,所以示人纪之大防。”“婚姻”章第一节第二十二条规定:“结婚须由父母允许”。关于离婚的条件有如下几条: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婚者,可以离婚。如男未满三十岁,或女未及二十五岁者,离婚须经父母允许。夫妻一方,若发生以下九条情事之一,可呈请离婚:重婚;妻与人通奸;夫因奸非罪被处刑;夫妻一方谋杀另一方;夫妻一方受彼方不堪同居之虐待或重大侮辱;妻虐待或重大侮辱夫之直系尊属;妻受夫直系尊属之虐待或重大侮辱;夫妻中的一方恶意遗弃另一方;夫妻任何一方生死不明达三年以上。[44] 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基础上修订民法,却未能审定颁布。虽然如此,在民间婚姻案件的诉讼及审判中,“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仍被援引,这可从大理院的解释例中得到反映,而且男女婚姻自主权逐渐得到司法机关的承认。1915年底大理院对河南一起婚姻纠纷案发表意见:“查民法原则,婚姻须得当事人之同意。现行律例,虽无明文规定,第孀妇改嫁,须由自愿,则室女亦可类推。以定律言,婚姻固宜听从亲命。然苟乖乎礼教,背乎人情,审判衙门,仍有裁夺之权。”[45]时逢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特殊时期,大理院的解释非常谨慎,既认为婚姻须当事人同意,是自愿行为,又认为“亲命”不容忽视,然后指示审判机关须结合“礼教”、“人情”灵活处理具体案件。此后,遇有婚姻纠纷,大理院不再明言维护礼教,但仍然纠结于法理人情。1916年该院针对四川一起控告悔婚案说到,婚姻当事人虽有定婚,但也不能强迫一方履行婚约。只能“以平和之方法,勤加劝谕,除此而外,实无强制执行之道。”[46]1918年底大理院复函福建高等审判厅:“婚姻应以当事人之意思为重,主婚权本为保护婚姻当事人之利益而设。故有主婚权人,并无正当理由拒绝主婚时,当事人婚姻一经成立,自不能藉口未经主婚,请求撤销。”[47]此话暗含两层意思,其一:在结婚行为中,“父母之命”不再有强制力;其二:若父母无正当理由不主婚,子女依然可以结婚。不过这些解释例,没有广为公布,也未得到普通民众的了解,1919年《学灯》“一个问题的讨论”中,无人提及。 但是,“五四”以后,婚姻自由的观念被知识青年极力颂扬,离婚自由的思潮也迅速兴起,若离婚行为完全自由,不受限制,这就意味着挑战了法律的权威,离婚的法条将形同虚设。司法部对此非常担忧,几次下令严禁“自由离婚”的风气,不准各地审判机关受理不符合法定离婚条件的离婚诉讼。[48]故而,当新青年遭遇旧婚约时,无法因自由之名,通过法律渠道摆脱既定婚约,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 民初的《时事新报》是进步党的机关报,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深受梁启超的影响,⑥该报副刊《学灯》在破除“旧”婚制,宣传自由婚恋的舆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学者却较少关注它在这一方面的史料价值。本文以1919年底《学灯》的材料为基础,分析知识青年鼓吹或实践“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情况。但本文不愿局限于此,《学灯》这场“一个问题的讨论”,并非孤立的事件,我们应该把此时婚恋观的变化和讨论放进历史脉络和社会环境中来看,这样有助于明白历史人物思想的语境和言语的动机。因为一种观念的出现,有其发生的条件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再者,观念也是人的思维,与人物成长生活的环境,接受的教育,以及自身的经历有关,而人的思想也有矛盾的时候。笔者试图注意历史的复杂性和人事环境的联系性,反思如何在婚姻家庭史的研究中有所推进。但笔者只是学术研究路途上的学步者,想法和做法有待继续改善。 注释: ①比如:郑永福、吕美颐:《中国近代婚姻观念的变迁》,《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徐建生:《近代中国婚姻家庭变革思潮述论》,行龙:《清末民初婚姻生活中的新潮》,同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徐永志:《晚清婚姻与家庭观念演变述论》,《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②这方面的论著很多,有的被译成中文,比较经典的是:Dorothy Ko(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Susan Mann(曼素恩)著,定宜庄、颜宜葳译:《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高彦颐著,苗延威译:《缠足:“金莲崇拜”极盛而衰的演变》,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③吕芳上:《法理与私情:五四时期罗素、勃拉克相偕来华引发婚姻问题的讨论(1920-1921)》,(台湾)《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1年第9期。许慧琦:《〈妇女杂志〉所反映的自由离婚思想及其实践——从性别差异谈起》,(台湾)《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4年第12期。侯杰、王思葳:《五四时期新女性的悲剧命运评析——以张嗣婧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11月。周叙琪,《民国初年新旧冲突下的婚姻难题——以东南大学郑振埙教授的离婚事件为分析实例》,收入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关于贞女现象的新近研究,参见卢苇菁著,秦立彦译.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⑤关于自梳和不落家的研究,可参看叶汉明:《主体的追寻——中国妇女史研究析论》,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初版,第175-245页;萧凤霞Helen F.Siu,“Where were the Women? Rethinking Marriage Resistance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South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Vol.11,No.2(December 1990),pp.32-62. ⑥关于《学灯》的研究,参见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2-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