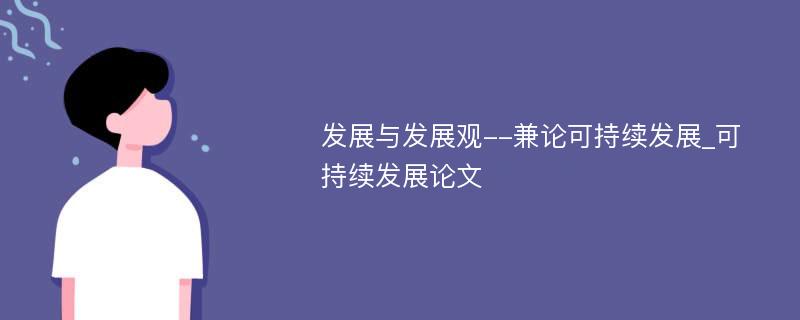
发展与发展观——兼论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本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审视以往的行程,谋划自己的发展战略,以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而在不同的发展战略后面,又是以关于发展的不同理论为支点的。
对各学科研究发展的成果给以宏观审视,把“发展”本身作为对象加以考察,这是哲学所面临的课题。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理论见解,也可以是一种发展模式,还可以成为可供选择的发展战略,同时它又是一种发展观。
我国在跨世纪的系统工程中,已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确定下来。开展对发展与发展观的研究,包括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一
对当代发展理论历史进程的一般考察,是正确理解现实和未来发展的必要前提。
二战结束以后,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谋求战后重建、恢复和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各种研究发展的理论便应运而生。“发展”成为了诸多学科关注的热点。仅就理论流派而言,就有发展纯理型学派、心理学学派、传播学派、社会学学派等等。新的发展学科更是层出不穷,如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战略学、发展伦理学、发展美学,以及未来学发展理论等等。这些不同的学科,虽然其研究的专业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视角却一致,即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上。在这诸多的发展学科、发展理论中,有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罗森斯坦等人的“大推进平均增长理论”、还有“基本需求论”、“增长加公平论”等等,这其中又有诸多的增长模式,如卡尔多增长模式、新古典学派的增长模式等。在未来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理论中,有战后初期的“经济增长论”、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论”、卡恩的“大过渡理论”、托夫勒的“权力转移论”等等。
概括地说,就战后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线索而言,大体上是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增长论”到“增长极限论”,再到“综合发展观”,到“可持续发展论”,以及相伴而行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等历史演进过程。
1.经济增长论
这种观点在发展理论中出现最早,在经济发展的起初阶段,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发展学是从发展经济学开始的,然而发展经济学起初实为“增长经济学”。战后西方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增长理论,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提出了若干经济增长模式和理论。当时一般学术界还没有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多数学者实际上是认为“发展=增长”。这种发展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战略是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目标的。这种观点把经济的增长作为发展的唯一绝对的标准,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其具体表现就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百般追求。这种“发展=增长”的观点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却带来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许多问题,带来了“没有发展的增长”或“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严重后果。于是人们对这种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产生了怀疑。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增长与发展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也日益加深了。本世纪60年代末以后,关于发展离不开增长,但“增长不等于发展”的见解,在更大的范围内取得了共识。国际学术界几乎普遍认为,不能把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而应当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加以区别。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含义较窄,通常指纯粹意义的生产增长;而发展的涵义较广,除了生产数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和某些制度的变化;不仅包含经济增长,还包含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等等。而且,这种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其他各种相关因素对增长的制约,那么总有一天,这种增长本身也是难以维持的。
2.增长极限论
这种观点在当今的发展理论研究中影响很大,大家都知道这是罗马俱乐部在70年代为批判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而提出的。增长极限论认为,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浪费使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再这样下去,环境将被严重破坏,并且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增长极限论的确给人类敲响了一个巨大的警钟,告诫人们要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看待发展问题。
1972年,受罗马俱乐部的委托,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等人提出了第一个报告,即《增长的极限》。这个报告一出版,就在全世界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增长的极限》的中心论点是:人口的增长、粮食的生产、投资的增加、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消耗都具有一种指数增长的性质。也就是说,过一段时间就增加一倍。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个时期达到极限。原因就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地球是有限的,空间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吸收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作者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极限到来时的可怕情景:由于粮食不足造成的饥饿和死亡,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消耗殆尽,环境急剧恶化。这样,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就要受到威胁,世界末日就会到来。
《增长的极限》一出版,立即在全世界思想界和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把这本书看作是悲观主义的代表作,有人甚至认为这本书反映了资产阶级对前途的绝望情绪;也有人指出了本书存在的一些技术上的不足之处,如所用模式的缺点、对于科学技术进步作用的忽视,等等。但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则认为,在人口爆炸性增长、资源大量消耗、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梅多斯等人能一反世人的俗见,把长期受到忽视的问题尖锐地提到人们的面前,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导致罗马俱乐部对世界发展持比较悲观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忽视了人类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动作用以及科学技术进步所能发生的积极影响。法国学者就曾指出,罗马俱乐部所制定的一系列“全球模式”,局限于以“增长——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而把人——社会、人——文化、价值、体制结构等极其重要的关系和因素排除在研究之外。这样,他们的立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批评,可以说是一语中的。
3.综合发展观
经济增长论是由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增长极限论和可持续发展是由未来学家提出来的。发展问题的日益突出促使人们对发展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多学科的介入,极大地丰富了发展观,于是,一种新的发展观——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佩鲁的《新发展观》一书可以视为综合发展观的代表作。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应当是整体的、综合的。这种观点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
佩鲁的《新发展观》序言中讲到:“自柏拉图时代以来,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思想产生于矛盾,而发展这一概念恰恰造成了我们时代一个重要的自相矛盾的事实:向往进步但又对其后果心存疑虑……。对整个发展问题的看法同时就是理解现实和现时代的钥匙。”[①]佩鲁在书中关于影响发展的各方面因素应予综合考察的观点,对于理解现实和现时代的发展,确有重要意义。佩鲁的《新发展观》是一本从哲学的理论高度来论述发展问题的重要著作。他认为,新的发展就是为全人类和一切人的利益服务的发展,也就是促进人类和一切人自身的发展。文化价值在发展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发展战略上,新发展观强调发展战略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所谓整体的,是指发展模式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观点,既要考虑到作为整体的社会——人的各个方面,又要看到人们相互依存关系中出现的多样性;所谓综合的,是指各个部门、地区的协调一致;所谓内生的,则是指充分正确地利用本国的力量和资源来促进发展。[②]新发展观认为,“新的发展”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能输出的模式,要实现新的发展,必须改变现存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新的发展战略力图改变发展各个子系统联系不紧密的状况,强调发展的各个侧面是互相紧密依存的。
可见,佩鲁的发展观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他十分重视联系的多层次性与全面性。
4.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
当代发展研究中真正把以人为中心提到发展观高度的是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该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指出:“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社会发展与其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不难看出,在以人为中心发展的各种观点中,尽管歧义很多,对“人”的理解不尽一致,但其共同点是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
5.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80年代提出的,并且围绕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讨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和辩论,终于在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期间达成共识:“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可以看作是增长极限论的续篇。这种观点认为以往的发展模式尤其是西方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已走入绝境,强调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的基础之上,重视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
从上述可以看出,关于发展的各种理论和观念,都不仅与某一特定阶段的历史条件相联系,而且也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相联系的。从“经济增长论”到“增长极限论”,再由“综合发展论”到“可持续发展论”,以及“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等等,大体上反映了人们所走过的历史发展进程,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条件下对于影响发展的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程度;发展的观念一般地总是在不断进步的。但是不同的发展论断在历史演进中的关系,并不是以先后顺序一个全错另一个全对的关系,而是在历史间断性、前进性的同时也存在着连续性、互补性。相互吸收,辩证扬弃,是发展理论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一种发展理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用,一定要以那里的具体国情具体条件为转移。这个基本点,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种发展观的不可移易的真理。比如说“增长”,把社会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划等号,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忽视了导致发展的其他因素,忘记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因为它导致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后果。但这并不是说,似乎可以离开经济增长而言发展;果如是,那一定是空谈发展。发展学家M·A·西纳索在给佩鲁《新发展观》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也说,什么是发展呢?“发展,既指发展的活动,又意味着结果的状态。”[③]增长与发展的关系又如何呢?“增长是规模的一项指标,它是从发展中获得自身意义的,这种发展虽然同增长保持着差异,但又围绕着它,并在增长取得进展时显示出自己的效益。”[④]这就是说,没有结果的“发展”活动是无意义的。而发展,虽然不能等同于增长,两者有“差异”,但发展又必须围绕着增长,而不是避开或抛弃增长,并且只有在增长取得进展时才能显示出效益,即达到有结果的发展。
发展与增长的差别性,使我们不能把两者混同,两者的同一性又使我们不能把它们绝然割裂开来。
二
可持续发展,是关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人类文明进展到新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跨世纪工程的一个基本要素。因此,在概览了发展理论的历史进程之后,有必要对此作些分析。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观是本世纪70年代以后提出的,二战以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经过劳资关系的调整等措施,特别是把科技发展成果应用于经济发展,使得一些发达国家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但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都是以各种资源的巨大消耗、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一些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人口的急剧增长、资源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等引起了一些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未来学家、哲学家、环保学家的关注。前面提到,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作为研究人类困境的第一个报告问世。这一报告对以往的发展模式作了反思,提出:如果不改变发展模式,“只要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正反馈回路继续产生更多的人口和更高的人均资源需求,这系统就被推向它的极限——耗尽地球上不可再生资源。”[⑤]这就是有名的“增长的极限论”。这个研究报告中的悲观结论受到许多人的反对,但其中所提出的观点却包含着合理的因素,而“增长极限论”在全世界引起的巨大反响和争论本身,也标志着人们对以往发展模式的反思。
1981年,美国农业科学家莱斯特·R布朗出版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走向持续发展的途径,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布朗的这本书被认为是对“可持续发展观”的首次系统阐述。
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了人们代际关系即一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问题,这是此前的发展论中较少或根本没有系统论述过的。与此相关联,布朗还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情景作了一些描述:“持续发展社会同我们现今所处的社会,在某些方面将有所不同。人口规模多少处于稳定状态,能源利用将有效得多,经济将主要依赖可再生产能源来维持,其结果,人类和工业活动范围将更为分散,远不像在靠像石油支持的社会中那样集中在城市。”[⑥]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基于对以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问题和面临的人口、资源等一系列难题应运而生的,它是对人类传统的单纯追求产量、产值的片面发展的历史反思的结果。
可持续发展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也带来了一些特点。
回顾历史,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的确一次次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历史的发展揭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要报复我们。每一次这样的胜利,在第一步都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今天,人类文明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的力量,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这种力量空前强大,使得人们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显示出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支配力,但是与这种“支配力”相伴而行的是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力。这种破坏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在某些领域使环境的破坏成为不可逆转的,使某些资源成为不能再生的,使自然界本身自我修复、自我再生的能力有根本丧失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迫使人们不能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了,改变观念和“端正”态度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就是改变过去那种人与自然的对立斗争以及一味“征服”的旧观念,而代之以符合时代特点的新观念。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的新关系,是人们所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这种观念转变包括:应从历史上那种人与自然的对立斗争转变为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从一味向自然索取转变为考虑持续发展,并且以未来发展来规划现在。
以未来发展规划现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使人类与地球从“互相为敌”的怪圈中解放出来,而且人类必须采取主动,这也是观念转变的重要一点。一些学者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赖以生存”,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小小寰球”变得似乎愈来愈小了,“人满为患”的说法反映了一定的现实。有论者提出:“这个地球不是我们从上一代人手中继承下来,而是我们从下一代人手中借来的”。这就是说,我们讲发展不能只顾今天,而不顾明天,不能只顾发展而不顾环境,不能只顾利用资源而不顾保护资源。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符合当代人的利益,又不危害未来人类利益的发展,只有这种发展才能持续永久,才能保障人类在地球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下去。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使发展成为在今天是现实的、合理的,同时又能使明天的发展获得可能的空间和条件,因此也是为未来发展创造条件的发展。
三
放眼望去,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是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体,而这个复合体生态系统中的人文因素则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概括地说,体制的失调,行为的偏颇,价值观的混乱等人文因素都可能造成对复合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都会影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首先,体制对复合生态系统的影响。在旧时代,传统的政治体制旨在管理众人,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变迁伴随着千百年来的改朝换代:而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失调又辐射着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而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不同时代的体制在世世代代的人类有序和无序地排列组合起来的同时,自然资源也就成为相互对立阶级之间斗争的无辜牺牲品。人类的体制在不同时代由不同民族、国家、政府所操纵,各不相同的目标、操作方法在许多情况下相互矛盾、相互掣肘,导致复合生态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相互排斥,从而造成了不利于人类的后果。
资本主义的掠夺和竞争使得工业革命后已屡受破坏的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在通过消耗大量资源为代价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体制的不健全,形势判断的失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等等,既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也会造成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更不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在深化改革中,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非常有利于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也是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
其次,文化对复合生态系统的影响。人类文化始于对自然环境的认识。生态危机表面上是人和自然矛盾的激化,其本质是人类文化的危机,即人类文化的失衡引起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紊乱,“文明人跨过地球表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⑦]生态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直接的,而对人类文化的摧残却是难以定量的。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很值得重视。例如,把天人合一当作修身养性的道德准则,这也有可取之处。在备受生态危机冲击的西方,许多学者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寻找挽救地球的真谛,不是偶然的。
我国古代朴素辩证自然观的“阴”表示保守性、柔弱性;“阳”表示进取性、刚韧性。“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像,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⑧]概括了自然界阴阳的互补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达到“仁”的境界,便和天地浑然一体。朱熹的“温然利人爱物之心”[⑨]将爱人之心和爱自然统一起来。
荀子曾告诉人们不能逆自然而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恶辽也辍广”。[⑩]
节俭美德在我国代代相传,使得今天的中华民族在占世界7%的耕地上,生产了占世界20%的粮食,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虽然骄奢淫佚是历代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但是,古代关于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等有机自然观,在满足人类合理需要的同时,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思想源泉。中国传统文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目标,许多仁人志士不畏权贵,反对奢侈生活。孔子提倡朴素的礼乐制度,“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故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蓄聚有数,车器有限,以防乱之源也。”[(11)]庄子提倡安于自然赐予的生活,“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12)]在消费时尚不断翻新的今天,享乐主义不仅败坏了人的素质,而且也在洗掠自然界,这不仅给经济发展增加沉重的负荷,而且使得文化滑坡。古代先哲提倡节俭、反对浪费对保护自然资源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而人类对环境变化机理缺乏研究,则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一条日益扩大的鸿沟把我们同真实的世界分隔开来。”[(13)]面对急剧变化的大自然,人类文化的进步落后于生态循环的节奏,“世界要求我们所做的,是要我们适应从一个文明时代走向另一个文明时代的急激变革。”[(14)]人类必须从文化上自救,在生态意识、生态思维上实现和自然的平等相待,这也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
第三,价值观对复合生态系统的影响。传统的价值观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出发点,以征服自然为进步特征,从而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这种价值观的后果一方面误导人们不择手段地向自然索取,不是理智地思考人类应该怎样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而是能利用多少就利用多少,多多益善。另一方面,更为可怕的是当生态平衡失调的同时,人类的价值趋向也走向混乱,造成人类的自我异化。传统价值观在强化复合生态系统的经济子系统的同时,削弱了社会、自然两个子系统的功能,致使复合生态系统紊乱。实现持续发展,必须更新传统价值观,普及和强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价值观。
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不是在空中楼阁中实现的,而是植根于现实世界的自然环境。生态平衡是复合生态系统的关键一环,走出生态危机的怪圈是实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实现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注释:
[①][②][③][④]佩鲁《新发展观》第1页、第2-3页、第201-202页、第3页、第10页。
[⑤]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⑥]莱斯特·R·布朗:《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页。
[⑦]弗·卡特、汤姆·戴尔:《表士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⑧]《周易·系辞上传》。
[⑨]《文集·仁说》。
[⑩]《荀子·天伦》。
[(11)]《孔子集语·齐侯问》。
[(12)]《老子》80章。
[(13)][(14)]佩切伊《未来一百页——罗马俱乐部总裁的报告》,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页、第1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