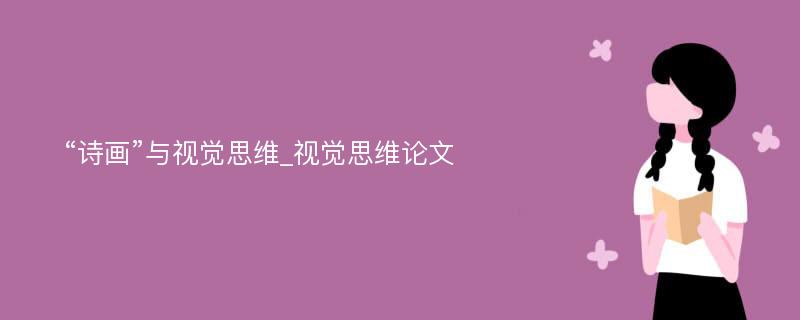
“诗中有画”与视觉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论文,视觉论文,诗中有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的思维绝然超不出他的感官所能提供的形式。
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
一
问题可以从东晋陶渊明的这首名作开始。
……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其五
(为了论说的方便,诗中暂不讨论的部分略去不录。)
结句“此中”的“此”即“采菊东篱下”以下云云,是诗人所描绘的一幅纯粹的视觉图画,这一点当无可疑。也就是说,诗人从“图画”氛围的感知中直接升华到了一个形而上世界而沉吟于其中。但是对于境界本身,他却拒绝用概念语言表述出来。后来的读者反复把玩,悉心悟解,多方诠释,其努力的意向大致都在于要在诗篇突兀而神秘的结尾处寻绎出那结果,那“真意”的究竟,而诗论中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一类断语的意指,用心也在于从诗的有尽之言、可玩之味里去穷尽那末言之“意”。
诗末一句令人向往之处正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多义的悖论。因为从句意的内部分析来看,这句仿佛极耐寻味的诗的言语内涵只是明确表明:诗人“什么也没有说”。
当然,可以绕过问题的正面,比如说从文化图式的背景联系中进行解读。那么,就“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文化心理的逻辑说,这里的有感而“欲辨”与“忘言”而未辨——试图言说与终于未说的内心对立,以至后者对前者的最终取消,恰是以“无”的形式表达着一种否定意义的“有”:人沉迷在同宇宙自然的亲和状态中,对于自身本质里外在和相斥于自然的“异物”——语言文明的自觉舍弃,这一放弃正表达着抒情主体向造物真宰全身心地消融同化。
无论这种方式的解读能为诗的欣赏传递多少消息,总无法超出诗的“背面”,它所能给予的也只限于精神意义方面的告语。当我们意识到,对《饮酒》的上述解读,还仅仅是徘徊在本文的暗示层次、并没有直接接触诗的语言形式和它所承当的诗的特殊言说方式,那么就不难看出,诗的文字间还有某些更重要的东西尚在我们眼前闪烁不定。
这个尚待发现的成分其实是诗的语言形式所直接表明了的。
首先,“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两个意项间的对立,明了地指说着“所感”和“所言”之间的相悖与阻隔。“忘言”可以具有主动和被动两重意味。亲和自然舍弃言语是为主动性的忘言,这是我们在文化的阐释中已经把握了的。而被动忘言才真正反映着感受与传达之间所存在的客观距离,表述着人类概念语言由于表意功能上的有限性而不能回避的困境。这一意蕴,显然来自陶渊明时代一个时尚的哲学话题,魏晋玄学中著名的“言意之辨”。这可以说是一个深刻地影响和表述了中国诗美学的形而上学话题。
“言意之辨”问题来自《周易·系辞上传》:“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立象以尽意’。”在玄学中,“意”概念援自《周易》“圣人之意”,是一种特指,略相当于儒、老学说中的最高本体“道”,或者主体对于道的把握,并不包含一般的凡庶之“意”。陶诗《饮酒》里“此中有真意”之“真意”便直接取自玄学,特指至高的宇宙真理、真宰之意、终极真象。而相应地,“欲辨已忘言”作为被动选择,毫无疑问,自然是“言不尽意”命题的诗化演绎。
接下来的问题是,陶诗在本文内(而不是由分析得到的言外之意)是否已经表达或显示了诗人领会到的某种“真意”呢?只要从抒情主体自身的主观立场来判断,那么无论从本文意象的理解或从由语言形式所赋与的逻辑结构来看都应当说:是的。
如上文所述,令诗人沉缅于中的造物“真意”就寓于“采菊东篱下……飞鸟相与还”这一派由他亲临目见的视觉图景当中,也就是说,诗里的图画已经在诗人眼中显露了“真意”。诗人在感性地拥抱着山野深秋的时刻,就以自己的有机生命直感到至道的真象。在这通彻透明的瞬间,他任情地让自己留驻在感性直观里,不自觉地超离了语言申说的庸常界域。以感性图景孕涵至道真意,作为美学思潮其根柢又可直接寻绎到玄学的“立象存意”。
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立象存意,是玄学对于“言不尽意”问题进行解决的对策之一,也正是陶诗所依凭的思维骨架。玄学认为,至道(天意)不可直接言说,对它的诠释和体悟,必须借助具有象征性的可感形象。用于象征的形象带有自觉的人为选择或创造的品质,而区别于随机性、任意性很强的原始象征。例如圣人所制的《周易》卦象。这种凭借中介的认识途径就是所谓“象生于意”而“象者,所以存意”。而属于有形现象的“象”并不拒绝接受语言的描述和阐释,“言者,所以明象”,圣哲能以精奥幽玄的语言解说象的内涵,通过对“象”的言语释读间接抵达终极之“意”。
作为哲学思维,玄学认识论的终点和目的在于“意”。作为认识初始阶段的“象”在认识结构中仅处于形器、现象的层面,没有终极存在的意义。抽象认识的彼岸既已抵达,引渡的舟楫和涉渡过程本身就自然该被扬弃。“得象忘言”、“得意忘象”明了地反映着义理思维的抽象目的。
如果仅仅是这样,魏晋诗学与思辨哲学之间就必然要在思维里程的这一驿站分袂而行——因为艺术思维的核心要点正是不能舍弃、反而必须执着于可感形象,以凸现感性形象为目的。这一点不言而喻。但事实上晋宋山水诗的艺术精神不仅不与玄学相背离,而且毋宁说前者的生长乃是受后者思维成果的孕育,在诗史上它(山水诗)是一种相当“哲学”的艺术。使诗学与哲学之间相通不悖的链条何在呢?
祖述老庄的玄学,虽然不能象庄学那样由唯美的生命激情生化出诗化的哲学,但它在认识论领域却留下地步,使诣玄蹈虚的义理冥思与体实触物的生命感受之间保持流通。魏晋诗学对于哲学的依属,托赖于玄学的抽象玄想与形器世界的互不隔绝。
这种连通,表现于“象”作为名理范畴所具有的特殊规定,表现于特殊含义的“象”在抽象达意的过程之中与过程之终并不被真正丢弃,而是作为最高本体(意,义理)和终极认识的有形载体,作为“意义的形式”和具有“意义”的形式,屹立于认识的终端。
王弼以之作为认识中介的“象”,实际上被赋予了两重概念,或者说,存在着两种不同层次、不同概念的“象”。第一种象是为粗重形器范畴,指偶然、个别的有形物象与现象,即所谓“存意莫若象”之“象”,即一般泛言的宇宙诸象。它们与形上意义的连结还是偶然的、不稳定的,对于“存意”、达意来说,至道或本体,既可以寄载于此象,也可以存寓于彼象。“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1]这种粗浅现象的象存在于认识的第一个逻辑阶段。当认识之足跨历这一台阶,直接面对着绝对真理时,心灵沉浸于致道的自由,人的智慧却陷入困境。他将发现,借助智慧所理解的最高对象却无法用智慧(语言所表征的思维)来胜任表达,因为真理本身是不具形式的。庄子所谓“道在蝼蚁”,无形的真意只在大千世界一切现象之中闪烁。因此,大概可以说,对于觉悟的眼睛来说,现象就是真理本身。悟道的这一瞬间的“象”,已经蜕弃了第一阶段的具体和偶然性,在虚玄之光的透视之下表现出抽象和形而上的品质,发生了质的转变。在慧观中得到升华的高层次之象,孕涵、显示着真理又不同于超形式的真理,它同时具有不可思议性和具体可感性,可以同时被体验为意义和现象、内蕴和形式,由此而显得既极具神秘,又十分亲近。这就是道器一元、混沌空灵的大“象”。
因此,《周易略例·明象》进一步分析道:“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就是说,真理既已寄形于现象层次的“象”(第一种象),那么,同最高意义发生了约定联系的象就不再是原来意义的象了。如果人们要捕捉、认定这个有意之象,那么所认定的可以说只是意义本身,与它相联系的象则是同它相为表里的形式体现而已。
明确了这一点,便可方便地理解玄学所说“得意而忘象”、“得意在忘象”。忘象,就是在会悟真理之际,忽略它所依托的寓体的具体个别性状,不再执着它原来所是的那个“象”。而第二概念的有意之象,由于它本身即是意义,便不必再认真留意于它形式上的存在。“忘”,只是忽略、不拘执罢了。如果说,这是对“象”的一次否定,那么它所抛弃的只是“象”的低级层次。
结构完整的、脱离个别性而具有形上性格的,包含或象征着深刻意义的高层次之“象”,就是以意象表现为基本特征的中国诗的主体形式,也就是中国诗论所谓“诗中有画”的“画”。
二
公元十世纪,宋代苏轼明确提出“诗中画”与“画中诗”的命题,比之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称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晚了15个世纪。然而,这种皮相的比较,并不具有多少理论认识上的意义。因为苏氏与西氏命题的美学内涵,实际上截然异趣。比较两者,所能窥见的是中西艺术在本质性格与发展历程上的深刻差异而非理论进境的深浅迟速。希腊诗人的论断根于西方学界源远流长的“摹仿说”,所强调的是不同艺术形式之客体对象的同一性。西摩尼得斯对自己的论点解释说:“因为绘画把事情当时的状况画出来,文学在这事情完成之后,把这事描绘出来。”[2]而苏轼所代表的宋代艺术美学恰恰是反摹仿说的。
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古人说“自然”一般指先天的某种妙理,并非客观的自然对象)。莫可楷模,出人意表。
黄休复《益州名画录·逸格》
古画画意不画形。
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耳,非精鉴之事也。
欧阳修题画语
徐生画鱼,庖中物耳。虽复妙于形似,亦何所贵。
黄庭坚《题徐巨鱼》
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
陈与义诗
苏轼所持“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的骇俗之论,就孽生于他的时代风气中尚气质、崇义理、菲薄形器之求这一审美流向,同时又代表和反映着风气。苏轼在其他处所有过许多此类的议论,例如他对王维吴道子的品鉴:
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如其诗清且敦。……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王维吴道子画》
这一风尚,这一艺术本体论的出发点对于“诗中画、画中诗”的本题具有何种规定意义呢?对于命题的阐释给予了怎样的限制呢?
诗画互藏命题的重要性质,正来自对诗、画各自本体的观念领会。也就是说,苏轼所指诗中的“画”,只能是他所认定和领会的那种画,那种“论画”的观念里所体现的论者认为“应该是”的画。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与下文“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3]两个意义段在这里为互文的关系。就是说二语中的诗理、画理可以相互发明。论画不必以形似,同时,作画如同作诗一样,不必“定是此画”;反过来,作诗也象画画一样不必拘泥于所赋对象之形表和“自性”,不必斤斤在诗的可见形态和外部表意中寻求诗的全部读解,诗的“达诂”。
据此可以无误地悟解苏轼所谓“诗中画”的应有涵义。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4]这两组命题之所以采用互为倒文的奇突形式,用意在于引起读者的形式关注,从形式的关联中意会到其内容是相互包含的。就是说,“诗中有画”的这一画,只是指“画中有诗”的那种画,即与诗的元素(某种精深的哲思或最高意义)相互含有、混成一气的画,这就是同匠人之画相对峙的、非斤斤于形似的、为文人作者主观意度、胸次和想象所涵育、所诗化、所抽象了的空灵之画。
在另一层意义上,“诗中画”的说法也被借用来指称一般意象思维所得的诗中图景。这种图景不一定含有深微妙理而可能只是作者即兴情意的对象化。描绘了这种图景的诗虽然也是诗,但不是苏轼所崇扬所理想的诗。
对“画中诗”的索解也应该如此。
明乎此,可知“诗中画”的性格规定实际上源于玄学的存意之象,“可忘”之象:忽略寓意形象的个别性状,着眼于象征,蕴无形(意、“诗”)于有形,视有形若无形(“可忘”)。将无羁的精神浪游寓存于可感的视听形式,又于具象的有形寓体中洞见无垠的形上世界。在这些特征方面,可以说“诗中画”就是玄学之“象”。
征之事实,苏轼所激赏的王维诗(主要是山水诗)中那些空彻迷蒙、水月镜花般地氤氲着禅意的意象不正是如此吗?倘若对这些意象不作超然、“抽象”的领会,不是就必然要陷入苏氏所批评的“论诗必此诗”和王夫之所指出的“以神理取象,在远近之间。才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5]的困境吗?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山居秋暝》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送梓州李使君》
请潜心体会一下这些深邈的意象吧。它们确实为视觉呈现了鲜明着实的对象,有形有色,生机盎盎。但这都是些不可采撷的花朵。它们并非在向人展示其颜色与婀娜,并非展示其在真实水土间的可靠存在,也并非在述说本身的生灭衰荣。而只是暗示着自身所包藏的一个永恒的寓言或谜语(这就是“画中诗”)。虽然从理论上说,某种精神意义在个别现象上的显示都是偶然的,萍水相逢式的,“义苟在‘健’,何必马乎?”出于这一原理,存意之象和“诗中画”都可以称为“抽象”的、模糊的、不必拘执和可替换的。然而,当某个有情生命在心灵的烛照下为主观化的某种意义或情绪所捕捉、所寄居,两者常在多次反复的心理过程中相互媾合,溶解,人们遂将不自觉地认现象与寓意为一体,对它们的心理反应就会发生一种相当稳固的认知与思维间的对应联系。这种形意的结体关系通过描述图画形象的诗语形式被保存下来,成为一个个意识积淀的有形载体。近似于此的过程,早在原始时期就在思维的神殿中自然地发生、存在和绵延,它通过文化心理的延续机制漫长地形成并制约人的“视觉思维”。
三
格式塔美学代表人物鲁道夫·阿恩海姆在他的《视觉思维》等一系列著作里,用大量的心理试验结果和分析证证,试图说明:人眼绝不是大自然的一面忠实的镜子,人的视觉对于对象的反应和反映,永远是有选择和有组织、受主观因素作用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从古至今的全部世界史的工作成果。”[6]作为这一本质的功能体现,人眼本能地“抽象”自己的对象。这一过程在一切视知觉现象中发生、存在。而图画行为(广义的绘画)在本质上与人眼反映客体的主观化性质完全同一,或者说,图画也就是借助物质材料对主观视象的如实复制。那么,从客体的自然存在到人的视觉或图画对它的主观“抽象”,其间发生着怎样的转变呢?
其中真实发生的事情不是别的,而是这些抽象风格的绘画把它们再现的“题材”从物理现实中“转移”出来。……换句话说,绘画所描绘和解释的,是一些普遍的性质,即一切思维活动所关心的那些性质。
——阿恩海姆《视觉思维》
视觉对对象的“抽象”过程就存在着思维,或者说,“抽象”行为本身就是思维介入知觉活动的一种体现和证明。知觉活动在主体既定的思维机制的引导下生成,反过来,推理性的逻辑思维也并不象以往心理学所认定的那样:脱离人的直接经验、依靠纯粹的抽象形式的推演来进行,而是与感性经验直接沟通。“知觉包含了对物体的某些普遍性特征的捕捉,而一般人认为的思维如果要真正解决点什么问题,又必须基于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种种意象。在知觉中包含的思维成分和在思维活动中包含的感性成分之间是互补的。正因为这样,才使人类认识活动成为一个统一连续的活动。”[7]
格式塔美学为我们提示了一个新的视点:对于中国诗意象思维这一原始问题的叩问,应当也必须涉入心理学的发掘领域去探询解说。
“意象”一词,无论对其构词成分的“意”与“象”之间的关系作何种设置,它的构词意图在于强调“象”乃是含有意义的形象,即存意之象,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表明,有含意的形象是诗思维的特有范畴和表意方式——相对于寻常感觉中所存在的“无意”之象而言。然而根据视觉思维说所证实的原理,一切视觉现象中都有思维机制在发生作用,一切视象都体现为主观认识选择的结果,“无意之象”在知觉活动中是不存在的。“存意”作为“象”的限定本来就属多余。这也就是说,诗人也好,艺术家也好,都并非在以一种异于常人或常态的心理方式进行自己的心灵运作,而只是在人类心智活动的本性和本然形态上更为敏感更为自觉地驰骋着创造性思维,所谓形象思维,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一种特有的思维类型,而是一切形式的思维都具有的一种结构要素。
在这个结论里能够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周易·系辞传》和玄学“立象尽意”的现代心理学解释;或是反过来说,可以看到现代科学思维的古老深邃的心智渊源。从这一心理学命题出发,完全可以对中国诗比兴传统、意象思维作一次重新的审视。
诗歌意象思维的中心要义在哪里呢?应当在于“象”在诗歌写作中——在以语言文字为表意形式的诗歌中的主体和先决地位。对于达意尽意来说,“象”(作为视觉及其他感觉对象的形象)处于第一义的位置。“存意莫若象”,无论从哲学或心理学意义上说,形象的直观感知都直接与情悰、思绪相连通,因此是“意”的最直接形式也是最为亲近、最为可靠、最有表现力的形式,因此说“莫若”。“莫若”之“莫”,形式上是对“象”以外的一切形式的排除,但在本命题中,实际上仅仅针对“言”的形式:“言”并非达意的最优形式,而是第二形式,间接形式,只在通过对感觉形象的陈述来实现自身的形式存在和价值。诗歌思维的直接现实不是语言而是感觉图象。玄学中“意—象—言”的结构关系,与《视觉思维》的论题冥然默契。
没有人否认语言能帮助人们思维,现在需要作出回答的是:语言的这一职责究竟是通过语言本身的性质完成的,还是通过它的间接作用完成的,即通过语词所指的对象或句子所谈的对象完成的。如果是后一种,帮助思维的东西就不是语言本身,而是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媒介。……
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语言成为思维的不可缺少的东西呢?这种东西决不是语言本身!我们认为,思维是借助于一种更加合适的媒介——视觉意象——进行的,而语言之所以对创造性思维有所帮助,就在于它能在思维展开时把这种意象提供出来。
……
在思维活动中,视觉意象之所以是一种更加高级得多的媒介,主要是由于它能为物体、事件和关系的全部特征提供结构等同物(或同物体)。
(省略部分是作者的论证。)
——阿恩海姆《视觉思维》
还可以从反面说明语言媒介的间接性。人类在各个时代使用语言表达心理内容时,不约而同地遇到过无能为力的尴尬困境。这不是指那种由于对语言运用的拙陋而造成的词不达意,而是语言本身的极限——语言的本体构成与功能期待之间所固有的距离所蹈入的困境。
语言的局限之根本缺陷就在于它与陈述对象的非同构性。而“视觉媒介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它用于再现的形状大都是二度的(平面的)和三度的(立体的),这要比一度的语言媒介(线性的)优越得多。”[8]
对于表现非线性的、神秘、模糊而难以捉摸的心理现实来说,情况就更是如此。
将艺术的诸形式视为人类情感(生命感受)符号的符号美学家苏珊·朗格,特别强调语言作为逻辑“推论形式”在传达主观现实方面的软弱无力。她认为,语言
只能大致地、粗糙地描绘想象的状态,而在传达永恒运动着的模式、内在经验的矛盾心理和错综复杂的情感、思想和印象、记忆和再记忆,先验的知觉……的相互作用上面,则可悲地失败了。
——苏珊·朗格《哲学新解》
按照朗格的逻辑,语言表达功能的尽头,正是艺术诸形式的起点。语言形式只能作为逻辑思维的符号,而艺术形式则是作为情感(生命感受)的符号被创造出来的。朗格在阐释诗——语言艺术的哲学时遇到了自己留下的悖论,她难以圆通地说明何以由推论性符号的语言充当形式媒介的诗歌,却又能胜任情感符号的角色。
使苏珊·朗格尴尬的悖论,在意象诗范畴里,正可以由视觉思维的思路来消除。在以呈现视觉(或兼有其他感觉)图画为主体的意象诗里,语言的首要职能不是别的,而只是唤起人们经验中的感觉表象,将感觉经验中被文化心理不同程度地先期赋予了一定意义的感性形象唤醒,凸现给阅读想象。语言作为视觉(及其他感觉)形式的转换形式实现自己的功能。显然,这恰恰吻合玄学命题中关于言的间接表意功能(“象以存意”,“言以明象”)的定义。
以这种眼光来重读读者已经熟悉的古代作品,会另有一番心会: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声声慢》
请特别留意最后一句。以言愁著称于史的女词人,在这里,明明点明自己是在说“愁”,却同时又感叹,这一切,单凭一个“愁”字是说不尽的——然而,众所周知,这一首《声声慢》又早已成为历代读者公认的将人生愁苦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典范之作。显然,这里实际上示现着两种不同形式、不同形态的“愁”。其一即“怎一个‘愁’字了得!”的“愁字”,这是文字之“愁”,概念之“愁”,即苏珊·朗格所说的“推论性符号”的语言对于“愁”的本体所能给出的表述。“怎一个‘愁’字了得!”恰恰诉说着概念语言对于传达生命感受的无能。另一个“愁”则是“杯酒”、“过雁”、“晚风”、“满地黄花”、“梧桐细雨”……是诗人用整幅画面——呈示自己视觉、听觉、肤觉、时空感等多种感觉的立体动态图画——所塑造所唤醒的那一个活生生令人肝肠寸断的“愁”的可触形象,即那一言难尽的“这次第”。是这个感觉性的形象直接透彻地传达了“愁”的意绪,而语言则充当着再现感觉表象的符号手段。语言形式本身并不与生命感受相同构,但它唤起作为生命感受直接寓体的感觉表象,接受者从寓体自然、主动地体验并还原出诗人的情绪感受,而并非消极地接受已被抽空血肉的“愁”、“怨”一类语言符号所传递的空洞信息。唯对语言精研琢磨、深悟妙理的使用者更明白此中消息,《声声慢》的这一句“怎一个愁字了得”就可以看作智者对推论性语言言情功能的明确斩截的否定。
可感的过雁、梧桐等,既是可“诗”(以语言描述)的,也多是可画的。“诗中画”可以说就是对这种“有意义”的感觉表象的指称。虽然诗中的图景或不限于视觉,或者,具有绘画所拙于表现的时间维度,凭这一点,说某些诗语不可画是不错的。例如,多为人所称引的张岱的这段诗评:
王摩诘《山路》诗:“蓝田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尚可入画,“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则如何入画?又《香积寺》诗:“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泉声”、“危石”、“日色”、“青松”,皆可描摹,而“咽”字、“冷”字,则决难画出。
——《琅嬛文集》卷三
然而,这类情况却不能据以否定诗的构成中意、象与言的关系。因为意象是包含视觉以外的其他感觉形象的,而诗中之“画”也并非指一张物质形态的静态绘画,而是心理表象中那种存在于立体空间的、动态的、并可具有时间延续性的感性图景。一般对苏轼评王维“诗中有画”之“画”,多认定为物质的现实的绘画(张岱的意见可作代表),揣摩苏氏立说的初衷,其对于诗中呈现的究竟属于“表象的画”或是物质的画,似乎并不十分在意。当然,由语言文字呈现出复合感觉的、表象的画,这正是语言艺术足以骄视物质的绘画之处,但苏轼之意,原着眼于两者之同(无差别境界)而不在二者之异。
四
视觉思维学说使我们从古典诗学的一些老话题中获得顿悟,产生更透彻更痛快的析解。
宋人以禅喻诗,后人多方解说。视觉思维所开启的认识论原理也可以使这一问题得到中肯而明了的解决。禅诗之喻在于两者思维方式上的相通,这一点是无争的。认明这种相通思维的本相最方便的路径,就是从禅宗“不立文字”问题下手。有意见以为“不立文字”渊于庄子“得意忘言”[9]。这当然可以阐明“不立文字”的初旨。然而禅宗标榜不立文字却终于“不离文字”,语录充栋,关于这一悖论,议解纷纷。如果从中国美学意象思维——也不妨说“视觉思维”的习惯方式着眼分析,一切疑难便豁然开朗。先看禅宗中人为“不立文字”而建立的文字。例如对最高问题(如何是佛?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如何是佛法大意?)的回答:
昨夜三更时,雨打虚空湿。
电影忽然明,不似蚰蜒急。
林间鸟噪,水底鱼行。
彻骨彻髓,遍天遍地。
楚王城外,汝水东流。
君山点破洞庭湖。
清波无透路。
——《五灯会元》
“对于提问并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这是一般的概念思维对于禅宗语录作出的意义判断。而以“象”的思维也即诗的思维方式来看,禅师对于提问是给出了回答并且可以说是“正面”的回答的。由于问者对于回答的形式期待是与提问形式一致的逻辑概念形式,这才会对于答语感到突兀,感到答非所问。禅宗不立文字,真相于此可见。这里的所谓文字,即逻辑语言以及它所对应的概念。禅宗就是要尽量避开用抽象概念、尤其是俗界执为正常的概念同学禅者对话,以从思维形式上斩断枉念,接近万法真谛。不立文字即不用常规概念。而禅宗悟道的思维方式,恰恰是意象的——禅门所重的慧观,所谓“观”,正是以视觉为主的复合感觉。他们也使用语言,大量的描绘视听感受、视听意象的“形象”语言,这些“语词所指的对象和句子所谈的对象”与诗完全一样。《诗品》作者司空图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实际上也来自禅宗观念。一“字”即禅宗“文字”之“字”,表概念的语言之“字”。这种字,是诗、禅都不可容纳,都应该避忌的。以“自家实证实悟”参透了诗禅关系的严羽所提倡证悟诗法的途径,实际上也须借重意象思维,并非教人凭空从抽象冥想中一味死参而得见灵山。正是他提醒人作诗“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理路指脱离意象的抽象思维而不包括凭借意象的抽象思维,因此严羽才又说:“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穷理的目的非他,即要在可见可闻可感可触的“象”中寄寓和表现出为主体所把握了的“理”——生命或宇宙真义。对于严羽以否定形式所肯定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的“别材”究竟指什么,“意象思维”或“感觉思维”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回答。因为唯有新鲜的、有个性有生命的意象才是书中(此偏指经书)所得不到的。
再有“情—景”关系的命题。
原始兴象的“象”与意义的联结是内在自足的,象征物与所象征的精神本体,在原始思维的混沌体验中几乎是一元的。“兴”的思维通过悠久的文化积淀嬗递为意象感知方式,在意象思维中,形而下与形而上、具象与抽象的一元性仍相当完好地保存着。“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人的主观世界,完全可以在与特定对象的这样默然无语的“相看”(对看)中交流和发露,而排斥、同时又包含着一切言说。枫桥的“月落乌啼”、“江枫渔火”与“夜半钟声”固有的表情意义本无待于某个浅薄外向的愁客向人多作一字的饶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难言况味,也不一定必须有“正无语凝咽”的提示才能让人领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所包藏的胸襟、意度更不是任何直陈式的抒情文字所能道出的。然而,当语言体系的符号功能随着人类心理机能的多元化和复杂进化而日渐完备,语言艺术中运用定义性的语言符号直接述说抒情主体的内外部动作行为成为重要的方式,在一种文明化和理性化的理解中,对象化的意象直观方式同陈述性的心理自白遂发生了结构性的二元对立,被视为二水分流、各擅胜场的不同抒情方式,甚而在写作中将意象表现降格为辅助性的言情手段,所谓“景”与“情”的范畴之产生,即这种分化的理论反应。从形态演化的大趋势着眼,以山水诗为典型的意象诗歌的写作,正是对于象征型的原始一元思维的自觉回归。
历代睿智的诗论,在情景问题上,无不以极力消除情景对立为立说宗旨。“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虚景,景总含情。”[10]“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11]王船山对情景结构的本质可谓深得三昧。“情景”之设,是为“意—象”结构的一个推演或一次分裂,两者的初始关系互为表里,在形态上本是一元的。“情皆可景”,相当于意以象存,一切意皆寓于象;“景总含情”,相当于象以存意,一切象皆有意之象。
情景两项间的二分观念之所以有害,是因为它不仅造成对抒情诗表意系统的内在统一性的人为割裂,同时也破坏了意象思维一方自身的有机结构,无形中否定了“象”对“意”的本然含有、先天内地——把所谓“景”看作了需要由即兴发生的意向通过概念性的情感表述来赋予意义的空洞的物质容器,也就是把视觉(感觉)中的思维机制同情感思维活动对视觉表象的原始依存关系,同时否定掉了。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和“一切景语皆情语”。[12]可以看作立象存意古老命题千载之下的悠远回响。
注释:
[1]《周易略例·明象》
[2]普鲁塔克《雅典人的光荣》,杨绛译。
[3]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
[4]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5]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7]阿恩海姆《视觉思维》。
[8]阿恩海姆《视觉思维》
[9]见张育英《禅与艺术》第三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0]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谢灵运《登山诗》评语。
[11]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
[12]王国维《人间词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