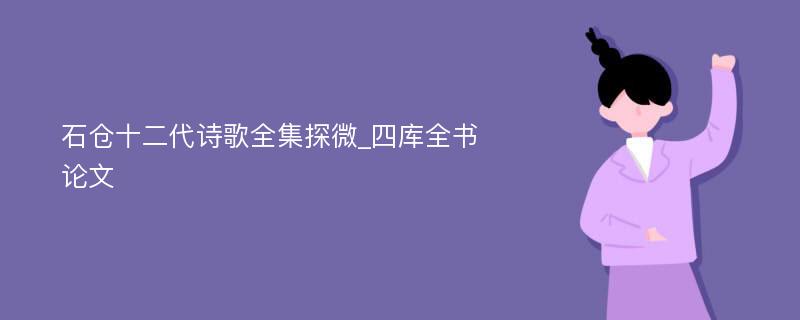
《石仓十二代诗选》全帙探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选论文,石仓十论文,全帙探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石仓十二代诗选》是明末著名的学者、诗人、藏书家曹学佺所编纂的一部历代诗选,所选之诗根据时间的先后共分为《古诗选》、《唐诗选》、《宋诗选》、《元诗选》、《明诗选》五大部分,《古诗选》又包括了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个朝代,再加之后面的四个朝代,故称为“十二代诗选”,亦名《石仓历代诗选》(注:是书封面题签为“石仓十二代诗选”,每集首行之标题亦为“石仓十二代诗选”版心则为“历代诗选”,大概曹学佺是有意于“石仓十二代诗选”作为书名。然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89 总集类四“石仓历代诗选五百六卷”条云:“旧一名《石仓十二代诗选》,然汉、魏、晋、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实十一代,既录古逸,乃缀于八代之末。又并五代于唐,并金于元,于体例名目,皆乖剌不合。故从其版心所题,称《历代诗选》,与义为谐。”《四库全书》所言有理,后人常以《石仓历代诗选》称是书,本论文欲究其原貌,故依是书原题签而定书名为《石仓十二代诗选》。)。是书是曹学佺一生所编辑的最大一部书籍,也是我国诗歌编纂史上规模宏大的一部诗歌总集。但是,由于成于乱世,又加之编纂过程中的种种原因,《石仓十二代诗选》至今已散佚不全,难窥其原貌。更为糟糕的是后人对此的著录各执一词,颇有出入,以至于时人无法知晓其真实情况。为此,笔者经过一番考证探究,企图展现是集所刊刻卷帙的全貌,以求教于方家。
查考现有的图书著录和馆藏情况,对《石仓十二代诗选》皆有所记载,可见此书曾流布广泛。据本人收集的资料和实地调查,《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善本书目》、《西谛书目》、台湾《丛书子目类编》、《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等国内外大型书目都有详细的著录;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天一阁藏书楼、华师大图书馆等国内外十几个图书馆都藏有此书(注:按《中国善本书目》的著录,目前国内共有九个图书馆藏有此书。其中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藏有卷数最多,其他图书馆(除天一阁藏书楼)所藏均与国图所藏的部分相同。因此,本人重点查考了国图、上图、首图、故宫、天一阁、华师大六个藏有此书最多的图书馆。)。然而,从各书目的著录来看,相互间著录不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各图书馆的馆藏来看,都非全本的《石仓历代诗选》(注:1981年版的《中国丛书综录》在“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中记载首都图书馆藏有《石仓历代诗选》全本,此著录误。首图现馆藏的仅是此书的一小部分,卷数和《中国善本书目》的著录相吻合。1959年初版的《中国丛书综录》,即标明此书没有完本馆藏,其中仅列的国图和上图也均是残本。)。因此,从目前存世的文献资料中无法确切知晓《石仓历代诗选》的真实面貌。
为了研究的方便,可将《石仓十二代诗选》分作两部分来展开研究。其中《古诗选》、《唐诗选》、《宋诗选》、《元诗选》为前一部分,《明诗选》为后一部分。对于前一部分的诗选,内容相对较集中,各类著录情况相同,有多部完整的本子馆藏于世,相互之间亦无丝毫差异,情况比较明了。而有关于《明诗选》的部分是该诗选的重点,卷帙繁复,特别是次集以下各集不但没有相一致的著录,而且没有确切的卷数,许多公私目录都以为已经散佚多时,无从编辑,仅录其前面几集以偏代全。如《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著录为888卷, 明诗选录一至六集,似乎已是足本,《四库全书》仅收506卷,止于明诗次集, 认为次集以下“今皆未见,殆以散佚”。(注: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九,总集类四。)
现在被普遍认为最完备的《石仓十二代诗选》足本著录见于《中国丛书综录》,所著录诗选共计1255卷。其明诗部分不但包括了明诗选各集及其续集再续集,而且也有十个以地域划分的诗集(包括社集)。然而《丛书综录》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目录,没有标出具体的馆藏情况。检阅《中国善本书目》,所著录的情况,前一部分与之相同,而明诗选却与之相差甚远。
《善本书目》著录中没有确定《石仓十二代诗选》的总卷数,只罗列了九个图书馆各自的馆藏子目和书籍的具体存世卷次,皆为不全之本。把所有本子相加,舍去重复之卷数,其具体情况如下:
古诗选13卷 唐诗选100卷拾遗10卷 宋诗选107卷 元诗选50卷
明诗初集86卷,明诗次集140卷,明诗三集选100卷,三续集15卷,明诗四集132卷(存131卷),明诗五集52卷(存50卷),续五集4卷,明诗六集100卷(存66卷),明诗七集100卷(存22卷), 明诗八集101卷(存25卷),再续集□□卷(存4卷)。
社集28卷(存13卷) 闽闺秀集1卷 闽集1卷 楚集20卷(存1 卷)
从上推知,《石仓十二代诗选》的“善本”约为1207卷,而在大陆存世的仅有939卷(注:此处的“善本”为作者臆撰。 另《善本书目》中明诗再续集卷数不得而知,但在国图藏有是集的卷四十七,由此推得,再续集最少也有47卷。1207卷是把再续集作为47卷来加以计算所得。再案《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2月出版)记载“是书共刻多少卷,今不得而知,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九馆所藏皆不全之本,全部相加,舍去重复之卷数,共存九百二十四卷。”此总卷数有误,盖引自早先仅供参考的油印本《善本书目》著录而没有真正加以查核。油印本的明诗八集著录为13卷(卷37~39,44~55),明诗续五集只有 1卷,这样,总共少了15卷,错为“存九百二十四卷”。与之相似,《善本书目》著录为939卷实际上并非精确, 因为是书偶尔出现有上、中、下三卷合称一卷、不同卷帙重复刊刻为同一卷数等情况,所以大陆实际存世的确切卷数应比939卷要多一些。)。
通过对《中国丛书综录》和《中国善本书目》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明诗选著录最大的不一致就是:前者有十个地方集(包括社集)共247卷,后者仅有楚集和闽集,却卷数不相吻合;而后者有七集和八集共201卷,前者却只到六集为止。根据《丛书综录》的编撰原则, 非所原书刊行概不载入(注:见《中国丛书综录》编例四。),所以十个地方集不会是误记或者是有目无书。同样的,翻检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其中一部诗选,确也有七、八两集。由此可以断定,此两者著录都非《石仓十二代诗选》的足本,或者是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版本。
又上海图书馆所藏另一部《石仓十二代诗选》的卷首目录后录有一题跋,为民国十九年(1930)年慈溪冯贞群所作,跋云:
曹氏所选明诗,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百卷,七集一百卷,八集一百一卷,九集十一册,十集四册,续集十册,再续集九册,三续集五册,四续集四册,五续集一册,又五续集三册,六续集四册;南直集八册,浙集八册,闽集八册,社集十册,楚集四册,川集一册,江西集一册,陕西集一册,河南集一册。搜罗浩博,明人别集散佚赖此以传者尚复不少。
冯贞群是浙东较有名气的藏书家和文献研究者,《鄞县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就是他1935年对天一阁藏书的全部著录。以上对明诗选各集的著录出自何处在题跋中并未交代,但可以肯定的是,冯贞群若不是亲所经眼或者有目可依,不会道听途说地草率下笔。而且题跋中八集以下均是以册计集,这只有在书籍面世后才可能出现的情况,(或是钞本,或是刻本)所以此著录不会是一个有目无书的空目录。
冯氏对明诗选的著录虽然基本上囊括了《丛书综录》和《善本书目》的著录,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足本。然而地方集和八集以下都未列出具体的卷数,明诗选到底有多少卷仍无从查知。
根据本人所掌握的资料,近代以来,对《石仓十二代诗选》收藏最多的当数郑振铎先生。郑先生搜求是书达二十余年,凡有经眼,必倾力购之。(注:国图所藏《石仓文选》卷首有郑振铎亲笔题记:“石仓诗选余求之二十余年,尚未得其全。礼邸藏本已东去,是终天之憾。……”又参见《西谛书话·劫中得书记》中“石仓十二代诗选”条。)在《西谛书目》著录中,《石仓十二代诗选》存839卷, 其中有“明诗七集卷四十五,明诗八集卷一、三至十四、十七至二十四、二十六至四十、五十九、六十三至六十五、七十八至八十、八十三至九十六、九十八、一百、又三卷卷次未刻,浙集八卷卷次未刻,闽集七卷卷次未刻,社集二十八卷卷次未刻。”郑先生曾撰文记录其搜访此书的曲折经过,并对其中的明诗选作了详实而精辟的评价,他在文章中说道:
《石仓十二代诗选》为明代诗选中最弘伟之著作,其明诗一部分尤关重要。《四库全书》所收,明诗仅至次集而止。谓三集以下均佚。《汇刻书目》载其全目,亦谓六集以下为钞本。实则石仓所刻明诗,不止六集。所谓礼亲王府藏本,于明诗六集外,别有明诗续集五十一卷,再续集三十四卷,闺秀集一卷,南直集三十五卷,浙江集五十卷,福建集九十六卷,“社集”二十八卷,楚集十九卷,四川、江右、江西各五集,陕西集三卷,河南集一卷。于六集中,三续集十三卷,四续集九卷,续五集四卷,五续集六卷,六续集二卷,均刻本也(《汇刻书目》作钞本,系据《啸亭杂录》,误)。群目为最足本。尝为陶兰泉所得。后兰泉所藏丛书悉售之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此书亦东去不返(此本有礼王府藏印,必即为《汇刻书目》所云之本;惟《汇刻》所举,尚有七至十集,此本无。恐《汇刻》误记。以“九集”本即“社集”也)。十五六年后,乃乾尝得残本百余册,中有明诗七集及八集十数册,却有溢出礼亲王藏本之外。后乃乾所藏归于北平图书馆,其中七集及八集则归于南洋中学图书馆。……一月后,书乃至。凡一百二十册,均为明诗,竟有八集三十余册,“社集”十五册(以其中间标作九册,姑绍樵目之为九集)。矜贵之至。八集数册及“社集”全部,其卷数尚为墨钉,未刻。……“社集”所收者凡二十九卷,均无卷数次第;……殆随得随刻,姑不记卷数。以作者皆闽人,且皆学 同社,姑曰“社集”。不知较礼亲王藏本(仅二十八卷,此本多一卷)异同如何。(注:见《西谛书话·劫中得书记》中“石仓十二代诗选”条,第335页至338页,三联书店1983年出版。)
西谛的这段记录对于《石仓十二代诗选》的研究可谓是弥足珍贵,他明确无误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他见过的最完整的目录——礼亲王府藏本目录。从他叙述的口气中,似乎这个藏本是当时比较珍贵和普遍被人认可的,是著录《石仓十二代诗选》的一个可靠的足本。通过这个礼亲王府藏本目录,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得出结论,《中国丛书综录》的著录是一个完整的藏本目录,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礼亲王府藏本。遗憾的是此本已悄然东去,无缘求见。然而,礼亲王府藏本到底是不是一个足本?如果是,那么为什么西谛书目中还有溢出礼亲王府藏本目录的七、八两集,而且冯目中更有九集、十集?可幸的是郑先生在文中不但指明了是集的流向,而且也记录了是集著录的传承,根据上文中的记载,《汇刻书目》著录了礼亲王府藏本目录,并且也认为这是“载其全目”的一个足本。而汇刻书目又是直接抄自《啸亭杂录》,也就是说,《啸亭杂录》有《石仓十二代诗选》最权威和被郑先生认为是最原始的著录。
《啸亭杂录》是一部以笔记形式辑录个人读书所得、逸闻考证的书籍,其作者是清朝汲修主人昭梿,即礼亲王,所谓的礼邸藏本就是他所收藏的《石仓十二代诗选》。在《啸亭杂录》中,礼亲王的记载如下:
《四库全书提要》云:《石仓十二代诗选》五百六卷,曹学佺著。学佺工诗,去取颇有别裁。其明诗分初集、次集。《千顷堂书目》尚三集、四集、五集、六集,三百八十四卷。近佚云。今余家所藏,则一千七百四十三卷。较《四库》所收多至千余卷矣:古逸诗十三卷,唐诗一百卷,拾遗十卷,宋诗一百七卷,元诗五十卷,明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百卷,七集一百卷,八集一百一卷,九集十一册,十集四册,续集十册,再续集九册,三续集五册,三四续集四五续集一册,五续集三册,五六续集一册,南直集八册,浙集八册,闽集八册,社集十册,楚集四册,川集一册,江西集一册,陕西集一册,河南集一册。九集以下不分卷,以册代卷,其曰“三四续四五续”,仪例难通,而雕镌完好,刷印清楚,自是闽中初拓精本。法时帆祭酒颇加赏鉴,为近世难觅之本。惟七集八集中数卷为王功伟明经携去,以致遗佚,不复得为全豹,殊堪扼腕也。(注:见上海文瑞楼印行的校正大字本《啸亭杂录》卷七。引文中“三四续集四五续集一册”因难以句读而未加标点。)
很显然,《啸亭杂录》的记载虽然具体,但不够确凿。在上文中,总卷数1743册已经知道,说明礼亲王是全面检阅过《石仓十二代诗选》的卷帙。但是,这个总卷数对应到具体分集的卷数上却不能一一落实,那些以册代卷的分集到底有几卷他却避而不谈,因此,这1743卷是如何拼加所得我们不得而知。(注:这种情况的出现,最大的可能是由于礼亲王为了反映家中所藏书籍的原貌,因此在叙述时,以最初得到的原本状况加以记录,不掺入自己爬梳整理的具体意见。而1743这个卷数显然是经过整理后所得出的总数,是对家藏《石仓十二代诗选》的一个总的记录。)然而,礼亲王的记载却和冯贞群的题跋相暗合,除“仪例难通”的几册无法确定其到底为何分集外,其他两者丝毫未差。(注:在此两者的著录中都未提到“闺秀集”。翻检现存的唐、宋、元、明(一、二集)各代诗选,都在集末录有“闺秀”一卷,作为诗选的其中一部分,这是诗歌选集编纂的一般规则。案国图所藏标有“闺秀集”的一部《石仓十二代诗选》,其社集、福建集、闺秀集都连在一起。社集不标卷数,共录13人(卷)。而第14卷就是《柯亭集》,为莆田柯茂竹所著,卷首行题识为“石仓十二代诗选 福建集卷”未标卷数。第15卷《云窗小句》和第16卷《澹若居集》,其前面的题识是“石仓十二代诗选 闽闺秀集”,同样未标卷数,并且仅此两集而已。国图的这个本子肯定是残页相拼补而成的不全之册,但从中也许可窥知闺秀集是福建集中的一部分,数量不多,因此礼亲王和冯贞群都没有单列出《闺秀集》一卷。)
再比较礼亲王和西谛的记载,两者对于“礼邸藏本”的著录存在着极大的不同。从总卷数上来说,前者比后者要整整多出488卷,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从具体的分集上来看,前者有九、十两集,而后者认为只止于八集;后者有四续集、续五集,而前者只有仪例不明的“三四续集四五续集一册”,并且还没有闺秀集。由此可以断定,郑振铎先生其实是没有见过《啸亭杂录》的著录。因为礼亲王在《啸亭杂录》的记载不可能是误记(注:不管冯贞群的著录是否抄自礼亲王的题识,两者著录的一致证明《啸亭杂录》的记录是比较可信的。不然,以冯贞群的身份是不会如此自信地加以题跋的。此外像郑先生所说的“以其中间标作九册,姑绍樵目之为九集”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在国图馆藏的《石仓十二代诗选》上常常出现后人将书籍上所刻的卷数改作其他的数字,比如把明诗次集“卷一”改作“卷八十七”(明诗初集86卷)。但是,礼亲王所记载的九集和十集本人以为并非如此,乃是原书所刻而成,故礼亲王的记载应该是可以相信的。),要是郑先生经眼过此“全豹”的书目,必然会在他的记录中提到并加以评析。因此,西谛和礼亲王对《石仓十二代诗选》的著录虽然同出一源,但各有所长,对于《石仓十二代诗选》的研究可以起到相互参照、相互补充的作用。
查考明代以来的有关公私目录,确实没有比《啸亭杂录》更为详尽的著录。翻检上海图书馆所藏的那部有七集和八集的残本,其八集卷中有五册卷首页上都盖有“礼邸珍玩”的藏书章,说明此本就是礼邸藏本。以此对照西谛在前文中所谈到的“中有明诗七集及八集十数册,却有溢出礼亲王藏本之外。后乃乾所藏归于北平图书馆,其中七集及八集则归于南洋中学图书馆”(上海至今尚有南洋中学,校史悠久),可以肯定,这即是西谛所说的归于南洋中学的那十数册书籍了。再案《啸亭杂录》中“惟七集八集中数卷为王功伟明经携去,以致遗佚,不复得为全豹,殊堪扼腕也”语,很有可能现藏于上图的那几册七集和八集的凋零之作,亦就是被王功伟从礼邸所携走而遗佚的几卷。可幸的是最后被乃乾所得,得以保存至今,不然也该东去日本了。由此可知,西谛认为是溢出礼亲王藏本之外的其实就是礼邸藏本中的一部分,西谛因为没有亲见,所以产生了误解。藉此类推,礼邸藏本诚如礼亲王昭梿所言,应该尚有九集和十集,那流落日本的一部也不是个完全的本子。(注:从现存的明诗选残卷中也可证明九集和十集的存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百名家诗选八十九卷”(清魏宪编)云:“宪以曹学佺有十二代诗选,止于天启,因选是集以补之。”查阅《石仓十二代诗选》的六集各卷,其诗人大致年代在天启间(可见魏宪也错误地认为明诗选仅到六集为止)。现存于上图的明诗八集中,有歙县吴子玉、新安王仲修、江陵胡宗仁等人的集子,这些诗人都是活跃在万历以后的年代,因此可推知八集乃选崇祯以前之诗人诗作。比较八集和六集收录诗作的时间,明诗选是按朝代先后而编纂的体例毫无疑问了。而在国图所存的明诗社集中,录有马季声、陈惟秦等人的诗作。案曹学佺《三山耆社序》云:“是日与会者王伯山文学年八十四,……予学佺为最少云。直社芝山龙首亭自不佞始,愿与诸君岁岁续兹盟焉。崇祯丁丑八月之十三日。”崇祯丁丑年即崇祯十年(1637),曹学佺编纂社集直到崇祯末年,那么一般来讲明诗选正集的编纂也会选到崇祯末年。因此,明诗选九集和十集刚好填补了从八集到社集之间这一时期的空白,大概是选录崇祯一代的诗人诗作。)
综合以上的分析,西谛的记录和礼亲王的著录其实也并无出入,只不过是对《石仓十二代诗选》前后不同面貌的两种记载而已。因此,我们可以比较确切地知道曹学佺在有生之年已经完成了《石仓十二代诗选》的编刊工作,从古初到明末,该诗选确实存在着一个完整的足本,(注:历家公私目录都没有指出《石仓十二代诗选》实未编竟,考查前人有关对该诗选的论述,也似乎是刊刻完毕,只是散佚太多。所谓的《中国丛书综录》和《中国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藏本,都只是著录了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六集以后几乎散佚无存,现在人们便以为以上两者著录皆为完本,以讹传讹。)也即是礼亲王所称的“闽中初拓精本”,该足本的群目如下:
古诗选13卷。唐诗选100卷,拾遗10卷。宋诗选107卷。元诗选50卷。明诗选初集86卷,次集140卷,三集100卷,四集132卷,五集52卷, 六集100卷,七集100卷,八集101卷,九集11册,十集4册,续集51卷,再续集34卷,三续集13卷,四续集9卷,五续集6卷,续五集4卷,六续集2卷;闺秀集1卷,社集29卷,南直集35卷,浙集50卷,福建集96卷,楚集19卷,四川集5卷,江西集5卷,江右集5卷,陕西集3卷,河南集1卷。(注:鉴于各图书馆的《石仓十二代诗选》,这个足本目录只是理论上成立,是个大致的数目。实际上曹学佺刊刻如此庞大的书籍,在卷帙数目上难免出现重复或是遗漏的情况,尤其是到明诗选六集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编刊相当的粗糙,错误叠出。如八集选中同样标为“卷三十”、“卷四十七”的各分别有三卷(并非是上、中、下分卷),而事实上是不同的三个诗集;“卷十八”、“卷二十五”、“卷三十七”、“卷五十”等各分别有二卷。由此推定,这种情况在其他的集子中同样存在,因此全诗选的确切卷数就不得而知了。)
和初刻的足本目录相比,现存于国内图书馆的《石仓十二代诗选》实在都是凋零之藏。国家图书馆的珍藏最为丰富,然这一部书并非是完整流传下来的同一本子,而是经过了后人的拼接而成,其群目包括了明诗选的一集至六集以及三个续集,除上图、天一阁以外所有国内外馆藏存目都无出其右者;上海图书馆珍藏了四部《石仓十二代诗选》,其中一部有明诗选七集和八集若干卷,乃世之孤页,弥足珍贵;而天一阁图书馆虽然所藏不多,但有明诗选中的楚集一卷,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妥善的保管,此卷纸张粘合在一起,薄薄一叠,无法翻动,难以检阅其详细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