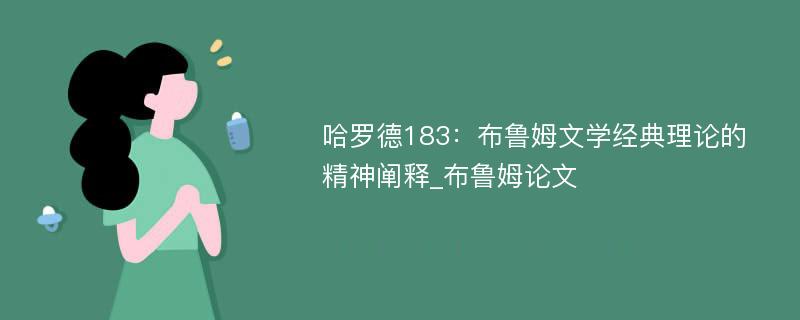
哈罗德#183;布鲁姆“文学经典”论的精神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鲁姆论文,精神论文,哈罗德论文,经典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文学经典(“正典”,canon)问题,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以具有高度审美原创性作为经典本质特征,推崇经典背后强者诗人对自我的肯定,强调经典能让人们懂得承受自身、面对孤独与死亡等人类终极命题,这些理论观点与他的前期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和宗教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渗透的,如果忽略掉他对于浪漫主义价值的重估和诺斯替主义等宗教体验,就很难理解他后来何以近乎固执地坚守这样一种经典标准。本文试图结合布鲁姆早期的浪漫主义诗歌批评与宗教研究,来探讨布鲁姆后期《西方正典》中经典理论的渊源、底色与特质问题。
一、浪漫主义的自我崇拜与经典的原创性
哈罗德·布鲁姆从少年时期开始对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就一直怀有特殊的偏爱,事实上,对于浪漫主义诗作的熟稔与推崇也的确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来对于经典问题的讨论。从早期关于浪漫主义诗歌分析开始,布鲁姆就非常重视作家关于自我、存在等问题的思索,欣赏内化的带有孤独感的诗歌氛围,鄙薄所谓社会意义,在其后对于经典特质的研究中这种观念表现得更加充分,他质疑文学的政治道德意义而推崇内化的审美感受所发挥的作用,认为“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①,强调经典背后“君王”般自我的存在,他希望实现的是更加具有人文色彩、关注诗人主体性的诗歌批评。对于这样的审美立场既是他一贯的诗学主张,也与浪漫主义诗歌本身的诗性特质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浪漫主义代表着一种高度内向化、自我化的诗学,它最大的特征便是热情地张扬自我肯定、自我崇拜和自由无羁的意志,抗拒一切外在于自己的规则。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角或是脸色红润的农民或是牵着龙虾漫步街头的奇装异服者,尽管二者迥异其趣,但在蔑视规则和保持心灵自由的意义上而言却是同一的。浪漫主义诗人珍视内心的冲动和激情,热衷于不断检视自我抑或思考人类的终极性存在。
浪漫主义对于主体自我和精神力量的强调深刻地体现在布莱克的一段自我表白中——“精神的内容是真实的……(物质的内容)是在谬见之中,它的存在是一种欺骗……我对自己宣称不要去注视外在的物质创造物……它就像我脚上的污垢,并非我原本的一部分。有人会问‘什么?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一团圆盘形的火焰——多少有几分像一枚基尼②吗?’哦,不,不,我看到的是不可计数的众天使大声说着‘神圣,神圣,神圣是万能的主耶和华。’我不再质疑我肉体的和无所作为的眼睛,我更想质疑一扇关乎景象的窗子。我透过它观看,而不是用它观看。”③精神是永恒、真实的,物质则仅仅是一种虚像,机械的自然主义也许会将太阳比作一枚基尼,然而在浪漫主义诗人眼中,它永远不能停滞于这种肤浅的物象层面,而必须升华出更贴近精神内核的体验,这也就是所谓的“透过”它观看。
这里涉及“心灵/自然(mind/nature)”这一对概念。在布鲁姆眼中,浪漫主义诗歌并不体现诗人对于自然的追求或者与自然的和谐,而是他们在追求自身的心灵力量并运用想象与自然对抗。这也许与通常我们对于浪漫主义诗歌的直观感受并不十分一致。譬如为人们所熟知的浪漫主义代表诗人华兹华斯便常常在诗作中袒露自己对自然的向往与喜爱,他吟咏简单质朴的田园生活。就像普遍的观念所认为的,华兹华斯对于工业化的都市所带来的种种痼疾感到排斥,在他眼中,自然是更为完整和健康的,是他渴望回归的故乡。然而布鲁姆却表示,浪漫主义诗人不会从社会转向自然,而是会从自然转向自身,内心是比自然更完整的东西。在布鲁姆看来,浪漫主义诗人不会仅仅将目光停留于自然的物象,而是力求感悟深层的精神内涵。所以,他认为布莱克和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都是反自然的,“自然”永远不能被作为解释浪漫主义诗人的充分的语境,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相关因素,诗人需要从中取走一些东西,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超越它以实现真正的自我体认。
在对华兹华斯诗歌及其影响的分析中,布鲁姆概括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自我神话学”。他说:“在《徒步远足》中,孤独者的形象是浪漫主义最基本的原型的一个典型代表,这种人与他人不相往来,整天沉浸在自己的过分的自我意识中……(这是)对浪漫主义的自我神话学作的最充分的陈述。”④在后来的《西方正典》中,布鲁姆也一再强调经典是面对每个人自身的,是内省的,并认为很多“强者作家”都具备一个包罗万象的君王般的艺术自我,任何伟大的诗人都在永久地敏锐地倾听自我,这是其全部创造活动的源泉,代表着旺盛的生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浪漫主义自我意识的一种回应。
有研究者将布鲁姆的美学立场定义为“唯我主义”⑤,的确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他所继承的浪漫主义精神——一个大写的“我”。在他眼中,海明威和托尔斯泰等作家也都在文字间注入了深刻的自我崇拜,把他们的自我融入事物的本性之中。经典作品中也许不一定会流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但是一定会标有作家的明显个人印记。布鲁姆认为有些作家在写作中会故意隐匿自我,以尽量客观冷静的姿态来描述对象,有些则毫不掩饰地热情颂扬,但这是作为叙述者的自我,在其背后的作家自我则无一例外都是非常强大而有力的。文学的经典性就形成于创作者主体性的高扬,布鲁姆认为“在陌生性意义上而言的原创性超越其他一切品质,是能够使一部作品成为经典的品质。”⑥而布鲁姆所谓“陌生性意义上而言的原创性”,就是强力作家与前辈大师们“竞争”(agon),对抗强大的文学传统所产生的深刻的“影响的焦虑”的结果,他们“渴望写出伟大的作品”,“渴望置身他处,置身于自己的时空之中”,“渴望与众不同”,从而“获得一种必然与历史传承和影响的焦虑相结合的原创性”。⑦
布鲁姆并不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肯定这种创作主体的自我崇拜,他还在建构一种美国文化精神的意义上寻找这种“自我”。布鲁姆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爱默生主义者——“没有历史,只有传记(no history,only biography)”⑧,任何意识形态语境都是需要超越的,惟有强者诗人自我实现的神话才真正具有诗学价值。爱默生是对美国文化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诗人,他告诫人们要信任自身、依赖自身,其学说非常具有感染力,其学说被认为是美国的世俗宗教。他曾经这样宣示美国精神的新纪元,认为“我们依靠别人的日子、我们漫长的学习其他大陆的日子,渐进结束了。”⑨爱默生关于“自我”的肯定为美国精神的建立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他认为人们需要相信自己是创造世界的力量,那种认为自己是自然世界的迟来者、世界在很久以前便已经完成了的观念是有害的,他还以极其高涨的热情宣称“我”就是上帝,只要“我”将自己从肉体、欲望和个人意志中那些脆弱与不洁的部分中解救出来,就可以达到自我的这种神性。对于先哲与他们曾经创造的历史,爱默生提醒后人不必过分谦逊和膜拜,“人应当学会发现和感受他自身心灵内部瞬息划过的微弱的光芒,这要胜过流连于诗人和先哲天空的光辉。不注意自我的思想——只因这思想是人自己的——会使人自我消解。在每一部伟大的著作中我们都可以辨识出我们自己的忽视掉的思想:它们以一种带有陌生感的尊严重新回归到我们这里。”⑩布鲁姆认为爱默生最重要的天才即在于,他认为我们在文学中感受到的光辉本就是我们自身的,阅读就是找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虽然爱默生的学说已经成为了美国人的世俗信仰,但是这一信仰的实质正在于不轻易信仰任何东西,它警告我们不要盲从任何规定好的形式。“祈祷意味着意志的疾病,信条则意味着智慧的疾病”(11),从这个被布鲁姆称为是自己最喜欢的爱默生的句子中不难读出这位伟大诗人充沛的自信力。旧有的世界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负担,而是等待超越的对象,神圣的自我永远可以实现这一伟业,只要我们懂得如何面对自己和相信自己。
惠特曼是布鲁姆文学经典序列中所确认的美国诗歌源头,是他极为推崇的“美国风土的诗人”(“the poem of our climate”),布鲁姆盛赞他成功而永久地改变了美国的声音和形象,改变了美国人的自我和美国宗教。而布鲁姆对于惠特曼诗歌的赞赏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惠特曼对“自我”的歌唱,他将惠特曼理解为一个真正的忠实于自我的浪漫主义诗人,反对从社会政治层面理解惠特曼,认为“对惠特曼的解读必须要超越于‘民主诗人’,虽然惠特曼坚称这是他自己的身份,但他实际上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犹疑的和个人化的诗人,远比他自己公开标明的情形要复杂”(12)。他借用斯蒂文斯的看法,认为惠特曼“不是神灵,但他与日出日落共进退,吟唱着分裂的自我和那不可知的灵魂,点燃了比自然之火还明亮的火焰”(13)。斯蒂文斯被布鲁姆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布鲁姆强调他在其诗作中高声唱出了自我之歌,宇宙万物都是围绕着“我”、听从“我”的召唤的,晚风吹拂橡树枝叶的沙沙声是在为我叹息,群山之上的天空因为我的疲乏而沉睡,朝日升起时的万道霞光是在为我欢快地呐喊,整个宇宙都在吟诵着关于“我”的歌,这是一种尼采所说的强迫星辰绕着自己运转的强力意志。在布鲁姆看来,斯蒂文斯是在寻找着“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崇高正是‘自我’的一面镜子”,(14)而这个“自我”是带有布鲁姆所想象的美国精神特质的。同样,狄金森的《斜光》之所以被他奉为美国诗歌的巅峰之作,是缘于它意味着“一种新的完全个人化的自我依赖,一种重大的废名行动,一种否定之举,其深刻性和辩证性足以媲美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散文”(15)。
这种对绝对、永恒的上帝式自我的肯定与崇拜曾被以赛亚·柏林概括为“浪漫主义信仰滚烫的中心”(16),在那里,“瞬间、碎片、暗示、神秘的微光——这些才是捕捉现实的唯一路径。”(17)这也正是大卫·费特对于布鲁姆的浪漫主义“想象”给出的解释,即这种想象是依靠自身途径而独立达成的启示性幻想,是稍纵即逝且没有明确指示物的。(18)布鲁姆认为心灵不能被束缚于某种自然物中,它所获得的感受虽然不能凭空产生,但却是灵光一闪的刹那,与任何明确的自然现象都没有依赖关系。浪漫主义诗歌高度内在个人化的情感体验和原创性的展现依赖的就是主体这种强大的想象力,布鲁姆非常欣赏那些语言汪洋恣肆的幻想性诗歌,推崇雪莱等人精致而陌生的诗句,“想象”被他视为浪漫主义诗歌理论的全部中心,是一种对于反叛与创造的膜拜。“我们的生命毕竟就是……一场‘持久的苦难和孤独’。只有一种力量,即想象能够拯救生命”(19)。浪漫主义有着不屈的创造的意志,带有狄德罗所说的罪犯式的艺术气质:蔑视规则,热爱权利、崇高和辉煌,不愿也不屑被正常的生活所约束,因此超拔的想象是其突出的精神标志。
在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研究中,布鲁姆非常重视那些具有超凡想象力的诗人。这一天启式想象的论断在诗人布莱克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布鲁姆崇敬他身上那种重新想和重新看每件事情的勇气,并曾经引用他在临终前四个月所写的一封信,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已经离死亡的大门非常切近,变得非常虚弱,成为了一位蹒跚衰弱的老人,但这些并不妨碍我的精神、生命与永存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想象力,虽然这愚蠢的身躯在日渐衰退,在上述那些方面我却正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强大。”(20)在布莱克与布鲁姆的眼中,想象力的意义都可以达到人的最本质属性的高度。而且,这种想象力的实现是晦涩的、神性的,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味道,为“天启”所激发,是一种超验的感受性。于他们而言,可以对庸人解释清楚的事情便不值得去留意。布鲁姆认为,在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在宗教观念中它意味着世俗世界中的神圣存在,而在文学的眼光里,则意味着诗的想象,一种审美感受力的空间。艺术想象即是作家强大主体的自我实现方式,能够创造出作品的“陌生性”(strangeness),亦即“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21)他认为莎士比亚最高超的技艺便是卓越的想象,惠特曼则具有一种神话般清新的创新性,每一位强者诗人都有着杰出的想象能力。布鲁姆在描述很多诗人的经典性时,其实就是对其启示性想象的描述,譬如在论述伍尔芙时,布鲁姆写道:“每一次新鲜的领悟与感知都会引起现实在她面前摇曳不定,而思想只是出现在她那受恩时刻边缘的暗影。”(22)事实上,这样一种物我合一、以内在本性去融合和亲近外物来体察世界本质的方式,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称其为超验也好,灵感也好,都是经典文学创作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重要环节,反过来又成为文学经典性得以生成的一个内在质素。
二、宗教情怀与自我的终极反抗
在布鲁姆看来,浪漫主义诗歌天启式的想象以及超越意识形态因素、回归诗人自我心灵的诉求与时代整体的文化背景有关,其中宗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譬如,当时英国的宗教传统倡导心灵的独立性,认为人们只需依靠自身而并不需要任何外部力量便可以与上帝对话,“这一宗教异端的主要特征就是它坚持理智和精神的独立性,坚持在道德问题上个人决断的权利,坚持每一个心灵内部的个人之光,唯有这样,才能够理解《圣经》——并且认为,应当允许所有的人在他和上帝之间,不需要任何的中介或屏障。”(23)这种崭新的宗教观念带来了一种激动人心的希望,自此人们无须借助所谓仁慈的僧侣集团,仅需依赖自身便可以获得救赎。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作用下,在文学领域里,浪漫主义诗人极力倡导诗歌是个人自我的实现,是优先于神学和道德哲学的,它的意义不需要依赖于神学、哲学来显现。
布鲁姆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一种诗歌的流溢。其实这句话反过来同样是成立的,他的诗学观念同样有其宗教信仰的投射,就像美国的一些研究者所分析的:“他认为阅读经典不会使人们成为更好的公民,也谈不上促进社会的进步,同时,这种阅读也并非为了娱乐或消遣,有时它带来的甚至是一种强烈的苦痛,那么这项痛苦事业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身的孤独,这种孤独最终的形式是与死亡的相遇’,这种指导就是一度归于宗教的职责范围的,从根本上来讲布鲁姆是在世俗的写作中寻找宗教体验:‘因为我本人偏好在莎士比亚或爱默生和弗洛伊德的文本中寻找上帝的声音,根据我的需要,我对但丁戏剧的神性可以毫不费力地注意到’”(24)。在布鲁姆看来,“经典是具有宗教起源的词汇”(25),因此,他用来界定“经典”的“canon”一词不同于“classic”,在后者的等级感之外是带有浓厚宗教意味的。
从被布鲁姆誉为“美国经典的核心”的惠特曼的诗作来看,生命是漂泊的,永远在渴望宁静的归宿,“我们变迁无常的、自己也不明白来自何处的,如今罗列在你眼前,而你在那里走动,或者静坐,无论你是谁,我们在你足下的漂流物中躺卧。”(26)而“死亡”则是当一切归于寂灭时必然迎来的最终命运。既是必然如此,也就无需恐惧,所以他说:“可爱的和缓的死亡来临了,起伏地环绕着世界,安详地来临了,来临了。白天、黑夜,所有人、每个人,迟早会来临的柔和的死亡。”(27)布鲁姆将早期惠特曼的总体诗歌意象概括为“黑夜”、“死亡”、“母亲”和“大海”,具有无边的延展性,也是原初的、令人敬畏或安宁的力量。无须具体的描摹,单从这几个意象来看,一种终极思索的意味便已扑面而来,而这正是布鲁姆所认为的伟大作品必须具备的品格和勇气。在分析斯蒂文斯等人的诗歌时,布鲁姆也作出了类似的解读。在后来的《西方正典》一书中,布鲁姆多次论述经典与生命、死亡等终极命题的密切关系,一再谆谆教导人们放弃浅薄的愉悦,要去追求更为深刻的自我反省。无论是在对浪漫主义诗作的分析还是对“经典”的研究中,布鲁姆都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人类生存孤独感的体认。
研究布鲁姆的宗教背景,也许我们可以从经典文本的这种生存孤独中读出更多的东西。布鲁姆称我们每个人在堕落为造物之前都身处地狱之中,因而每个人都能体验到旷野中的自由,体验到美国想象中整个的孤独,自由和孤独的体验是人类最早最深刻的体验之一。布鲁姆一直表示自己是古代和现代诺斯替主义的虔诚信徒。所谓“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便是人类在宇宙中的孤独境遇,认为生存是严酷的,人类置身的这个世界是知识的反面的产物,它远离爱和关怀,代表着一种无序、邪恶、统治与压迫,宇宙并非像希腊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具备理性甚至神圣的法则,并因此值得被膜拜与虔诚地沟通,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阻碍人的自由。人因为具有知识而决定了他只能是这个无知世界之中的异端,于是他不可避免地感到一种对周遭环境的怀疑、疏离与那种深重的脆弱与孤独感。人有着一颗高贵的灵魂和澄明的内心,然而正是这种优越性决定了他被离弃的命运。诺斯替主义将“灵魂”拆解为“灵”与“魂”两个不同的部分,认为“魂”受制于肉体,代表着无可逃离的规定性、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灵”则代表着自我存在的精神核心,它不可被定义,也拒绝臣服于任何预先决定的本质,是一种自由的、自我决定的力量,代表着最优越、最古老、永不沦为堕落的受造物的一部分,它从根本上怀疑任何权威的合法性。
在布鲁姆对于经典作品的分析中,时常可以看到他对孤独境遇的关注,无论对叶芝、华兹华斯还是卡夫卡等人的论断,存在本身的紧张感都似乎格外吸引布鲁姆,对他而言,经典正是为了帮助人们扩展自身孤独的生存。被认为是浪漫主义传统最后支柱的诗人叶芝,布鲁姆称其复燃了浪漫主义的天才观念,并赋予它一种悲剧性的尊严,内在的孤独感是叶芝最根本的诗学祷告,这位伟大的诗人告诉我们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时,才会忽然发现黑暗变为光明、虚空变为丰饶。布鲁姆也十分推崇华兹华斯的《荒屋》等诗歌,认为华兹华斯最不可思议的天才便在于“他教会人们如何感同身受他人的各种颠踬困顿”(28),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带有一种质朴的哀伤,譬如那位眼光凝重而孤单的老乞丐,他费力地搜寻袋中的食物,手颤抖着,却极力不让面包屑散落,尽管碎屑还是不可避免地散落一地。布鲁姆认为这个形象朴素地呈现了人的尊严与意志,我们读过之后同样会感同身受的原因则恰恰在于孤独的生存是每个人始终都要面对的。而那些敏感的强者诗人则对这种处境更为清醒,他们就像拜伦所描绘的那样一些离群索居的人,由于渴望超越而安于孤独,并追求和享受这种孤独,欢愉在他们看来是肤浅和麻痹性的,“他几乎渴求不幸,即使风景变换,仍将寻找深处的阴影。致命的轻蔑在他心中,对一切……他总是陌生人,在一息尚存的世界里……高昂地飞腾或深深下沉,同那些人一起呼吸,他觉得是判决……”(29)。布鲁姆深受尼采超人意志学说的影响,认为痛苦往往代表着比欢乐更深刻的体验,他在现代作家中十分推崇卡夫卡,认为后者是当代犹太人的焦虑大师,深刻地展现了意志与存在之间的冲突,他的情书表达了世界上最为忐忑焦虑的心情,他的小说则永远带有一种压抑和扭曲感。卡夫卡曾经在日记中称自己总是感到内心世界的那个时钟走得飞快,几乎像是着了魔,然而外部世界的那个时钟却始终仅仅以平常的速度费力地走着。(30)这种卡夫卡式的不协调正是诺斯替主义传递的情绪,即那种被抛进一个异质世界中而感受到的深刻孤独。
布鲁姆也曾多次直接就以“诺斯替主义”的说法来形容某些经典作家,例如叶芝,“写到午夜时分上帝将赢时,他是指死亡会胜利,因为上帝与死亡在叶芝的各种诺斯替式景象中,几乎是同义的。”(31)他认为狄金森有着诗人中最为出众的心灵,她在阐明美国宗教上是无人可比的,而布鲁姆眼中的美国宗教正是“把奥菲士主义、超验启示主义和诺斯替教融合成民族意识”(32),狄金森所作的便是对这种意识的审美体现,这是她最突出的原创性。此外,布莱克、狄更斯、卡夫卡都有着一种诺斯替式的观点,“大法庭好比卡夫卡的审判庭和城堡,是一种诺斯替式图景:法律已被宇宙的主宰即造物主篡夺了”(33)。他对贝克特的分析也同样借助了这种宗教观念。在他看来古代诺斯替教是异端神学中最消极的,在它的体系里,由于一位伪造物主惹下某种祸端,导致创造物等同于堕落,所以诺斯替教是抵制繁衍的,借用博尔赫斯在《死亡与罗盘》中提到的说法,他们认为“镜子和父亲都是可恶的,因为两者都使人类数目增长”。为了抵制堕落的繁衍,造物主甚至制造了大洪水,而贝克特笔下的汉姆正是这样一种伪造物主,他“渴望摧毁所有生命:人类、动物以及自然。”(34)诺斯替式景象往往与宇宙的消极和无序、生存的困顿等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无可逃避的孤独命运,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善用这种生存的孤独,一如经典文学那样。
布鲁姆曾经研究过宗教中的“天使”、“梦”与“复活”问题,对于人类灵性中的复活形象怀有深深的敬意,认为这些形象见证着人类的需要和欲望,它们既代表着人类的局限,也意味着一种超越的可能。他曾经深入地研究过美国的“摩门教”,认为其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具有一种强大的宗教想象力,而摩门教最重要的宗教想象便是人与上帝的同一。这一教派认为人和上帝同样是起源性的,力图消除上帝与人之间的区别。这在西方宗教中是少有先例的,布鲁姆认为它体现了美国民族独特的宗教信念,即神与人同样有血有肉,“美国宗教的上帝根本不是造物主的上帝,因为美国人根本不是受造物,因此,美国人至少是上帝自身之内的一部分。”(35)美国精神在本质上否定高踞于人的心灵之上的造物主,上帝不过是万物之中的一物,同样具有局限性。在摩门教教旨中,勤奋与遵守普遍法则是人的美德,这种德行可以帮助人像上帝本身一样实现不朽。
在对摩门教的研究中,布鲁姆分析了他们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教义——为死者施洗。他认为这其间所反映出的对待死亡与诞生的态度是一种巨大的追寻罗曼司行为,施洗本是为了生者灵魂的纯洁和净化,而摩门教徒则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持之以恒地为自己和他人的祖先进行施洗,由摩门教徒代替这些逝去的人接受洗礼,在执事呼唤生者的名字之后,代替者就浸没在水中完成仪式。这一教义被布鲁姆认为是约瑟夫·史密斯最大胆和最值得称道的创新,因为在这背后体现出一种巨大的宗教热情和拯救的雄心,也正体现着他们对复活或永生的巨大热忱。
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情结中传递出对末日审判的渴望,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性嫉妒则实际上掩盖着对不能永生的恐惧。事实上,布鲁姆正是将经典看作一种复活或永生的方式,“自由和孤独的自我从事写作是为了克服死亡……我们共同的命运是衰老、疾痛、死亡和销声匿迹。我们共同希望的就是某种形式的复活,这希望虽然渺茫却从未停息过”(36),因为“诗可以使世间最善最美的一切永垂不朽;它捉住了那些飘入人生阴影中的一瞬即逝的幻象”(37)。
注释:
①[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②基尼:英国旧时金币名。
③From Harold Bloom,Genius:A Mosaic of One Hundred Exemplary Creative Minds,New York:Warner Books,2002,p.362.
④[美]哈罗德·布鲁姆著,吴琼译:《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⑤阎景娟:《文学经典论争在美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⑥[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262页。
⑦同上,第8页。
⑧Harold Bloom,Genius:A Mosaic of One Hundred Exemplary Creative Minds,p.359.
⑨Ibid,p.180.
⑩Harold Bloom,Genius:A Mosaic of One Hundred Exemplary Creative Minds,p.180.
(11)Ibid,p.181.
(12)Ibid,p.303.
(13)[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215页。
(14)Harold Bloom,Genius:A Mosaic of One Hundred Exemplary Creative Minds,p.194.
(15)[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237页。
(16)[英]以赛亚·柏林著,吕梁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17)同上,第115页。
(18)See Graham Allen,A Poetics of Conflict,Hemel Hempstead:Harvester Wheatsheaf,1994,p.4.
(19)[美]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第233页。
(20)Harold Bloom,Genius:A Mosaic of One Hundred Exemplary Creative Minds,p.358.
(21)[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2页。
(22)同上,第344页。
(23)[美]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第162页。
(24)Paul,Gray,Hurrah for dead white males!,New York:Time,Oct 10,1994,Vo1.144,Iss.15,p.62.
(25)[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14页。
(26)[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朱立元 陈克明译:《误读图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189页。
(27)Harold Bloom,Genius:A Mosaic of One Hundred Exemplary Creative Minds,p.307.
(28)[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202页。
(29)[英]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第143页。
(30)关于这一说法,参见[奥]卡夫卡著,叶廷芳译:《卡夫卡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31)[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232页。
(32)同上,第234页。
(33)同上,第243页。
(34)同上,第403页。
(35)[美]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第41页。
(36)[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414页。
(37)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标签:布鲁姆论文; 诗歌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美国宗教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爱默生论文; 西方正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