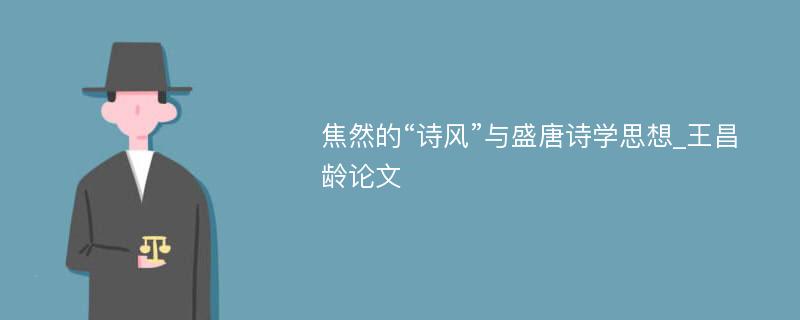
皎然《诗式》与盛唐诗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唐论文,诗学论文,思想论文,皎然论文,诗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文学批评(理论)史都将皎然及其《诗式》置于中唐来讨论(注:唯一的一个例外,是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在这部书中,罗先生在盛唐与中唐之间设置了一个转折阶段,即从唐玄宗天宝中至德宗贞元中。这个阶段的前半段主要是元结、杜甫等人的诗学思想,后半段的代表人物则为皎然。),其依据主要是皎然生活的年代。就是说,由于皎然主要活动于大历、贞元年间,而且据皎然《诗式·序》中所言,《诗式》编定成书在贞元五年(789年),故皎然及其诗学思想理所当然地被划归到中唐。但这样一种处理恐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姑且不论在盛唐和中唐之间还有一个转折时期,即使将这个转折时期也归属到中唐,能否就据此断定《诗式》所反映的诗学思想是中唐特有的呢?提出这一疑问的理由在于:《诗式》编定成书的时间与皎然实际写作该书的时间有一定的间距,而且皎然诗学思想的形成还可以再往前追溯;更重要的是,《诗式》所反映的诗学思想与盛唐诗学精神颇多相似,而与中唐诗学精神不尽吻合。
一
皎然的生卒年史籍不载,据当代学者考证,皎然大约生于开元八年(720年)前后,卒于贞元末(800年左右)(注:如漆绪邦先生的《皎然生平及交游考》一文(原载《北京社会科学》1991年3期)认为:“皎然约生于玄宗开元八年(720)前后,约卒于德宗贞元八年(792)至贞元二十年(804)之间,具体年份,皆不能确指”。李壮鹰先生的《诗式校注》认为皎然生于开元八年,卒于贞元末,亦即公元800年左右。张伯伟先生的《隋唐五代诗格校考》则认为卒于公元798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的话,那么认定皎然主要的活动时期在大历(766-778)、贞元年间(795-804)就有欠准确了。道理很简单,大历初年时皎然已经四十六岁,而大历、贞元年间只占皎然一生中的五分之二,所以要说主要活动时期,恐怕还得再提前二十年,亦即从天宝(742-755)中算起。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既然我们讨论的是皎然的诗学,那么就应该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其诗歌创作的高潮时期,特别是《诗式》的写作时间,这样才能对皎然诗学作出较为合乎史实的评价。
关于《诗式》成书时间,一般认为是在贞元五年(789年),根据则是皎然《诗式》卷一《叙》:
贞元初,予与二三子居东溪草堂,每相谓日:世事喧喧,非禅者之意,假使有宣尼之博识、胥臣之多闻,终朝目前,矜道侈义,适足以扰我真性,岂若孤松片云,禅坐相对,无言而道合,至静而性同哉?吾将深入杼峰,与松云为侣。所著《诗式》及诸文笔,并寝而不纪。……至五年夏五月,会前御使中丞李公洪自河北负谴,遇恩再移为湖州长史。初与相见,未交一言,恍然神合。予素知公精于佛理,因请益焉。……他日言及《诗式》,予具陈以夙昔之志。公日:“不然。”因命门人检出草本,一览而叹曰:“早岁曾见沈约《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诗箴》,三子之论,殊不及此。奈何学小乘偏见,以夙志为辞焉?”再三顾予,敢不唯命!因举邑中词人吴季德。……公欣然,因请吴生相与编录。有不当者,公乃点而窜之,不使琅玕与珷玞参列,勒成五卷,粲然可观矣。
这里将《诗式》编撰成书的过程交待得很清楚:《诗式》得以编辑成书,公之于世,完全是湖州长史李洪一手促成的,时间也正是在贞元五年。但这并不是《诗式》实际的写作时间,因为李洪看到的,是皎然在贞元初即已“寝而不纪”(中止写作)的“草本”。那么,是不是可以将《诗式》写作的时间定在贞元初呢?也不行,因为贞元初只是皎然中止写作的时间,而不是他开始写作的时间。
关于《诗式》的写作时间,《诗式》卷五曾经提到,谓“时在吴兴西山”。西山即杼山,因位于吴兴西南,故名。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皎然上人传》所说更为具体:“(皎然)往时住西山寺,定余之暇,因撰序作诗体式,兼评古今诗人,及撰《诗评》诸卷,皆议论精当,取舍从公,整顿狂澜,出色骚雅。”据此,皎然写作《诗式》是他在“西山寺”,亦即吴兴杼山妙喜寺居住时的事。那么,皎然何时隐居西山呢?《皎然上人传》记,与皎然同居妙喜寺的,还有灵澈、陆羽等人。陆羽曾在寺旁建亭,于癸丑岁、癸卯朔、癸亥日落成,当时湖州刺史颜真卿题名“三癸”,皎然特为赋诗,合称三绝。癸丑岁即大历八年(773年)。从常理推论,皎然入居妙喜寺当在此之前。而据漆绪邦先生的《皎然生平及交游考》,皎然归隐湖州,挂籍妙喜寺,约在大历三年。这时皎然尚不到五十岁,如果《诗式》的撰写在这一时期的话,那我们只能说《诗式》是皎然中年所作,而不能归到晚年。
又明人徐献忠《吴兴掌故录》记:“中丞李洪刺湖州,枉驾杼山,请及诗文。昼曰:‘贫道投笔砚二十余年,一无所得,冥搜物类,徒起我人,今弃之久矣。’洪搜之人间,仅得十卷。”话虽不可全信,但说皎然晚年少有著述,却是不错的。《诗式·序》说应李洪之请,荐同邑文人吴季德帮助整理编定《诗式》一事,既表明此时皎然已很少动笔,同时也意味着《诗式》纯属昔日旧稿。
而且,就算《诗式》确实为皎然中年后所作,在此之前,还有一个皎然诗学思想形成的时间问题。据释福琳《皎然传》记载,皎然一生的活动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他青少年在杭州灵隐寺受戒出家时期,二是他漫游各地时期,三是中年以后归隐杼山时期。皎然的诗文创作,主要是在前两个时期。用福琳的话说,此时皎然,“特所留心于篇什中,吟咏情性,所谓造其微矣。文章隽丽,当时号为佛门伟器哉。后博访名山法席,罕不登听者。然其兼攻并进,子史经书,各臻其极。凡所游历,京师则公相敦重,诸郡则邦伯所钦,莫非始以诗句牵劝,令人佛智,行化之意,本在乎兹”。由此看来,皎然诗学思想的形成,应该是他青壮年时期的事,从年代上说,主要是在天宝年间,亦即在皎然二十到三十五岁这一时期(注:据漆绪邦先生的考辨,皎然受戒出家的时间约在大历二年至三年春,而非如释福琳所说为青年时期。但这一点似无关紧要,从皎然归隐后的交游来看,此时他已颇有诗名,是知皎然诗学思想的形成当在此之前。)。而从《诗式》一书来看,尽管不乏佛学的影响,但其主导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似乎是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与晚年皎然完全倾心佛学并不吻合。
据张伯伟考证,王昌龄《诗格》大致作于天宝元年至天宝七年(742-748年),李珍华、傅璇琮先生的看法还要更晚一些,为王昌龄被贬龙标期间所作,时在天宝十年至天宝十五年;而我们知道殷璠《河岳英灵集》成书于天宝十二年(753年),因此,就算五十岁以后皎然才开始写作《诗式》,其与王、殷二人所作相差也不到二十年。
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考虑。大历、贞元期间,虽然诗坛已渐呈中唐气象,但盛唐余韵犹在。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大历十才子和韦应物、刘长卿、李嘉祐、戴叔伦等诗人,包括诗评家皎然,大多生长于开、盛世,“经历过开、天盛世的生活,受过盛唐精神的熏陶,受过盛唐诗歌的影响。这些,在创作中很自然都有所反映。他们中的大多数,时不时地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盛唐诗歌的那种昂扬风貌,那种风骨,那种气概,和那种浑然一体的兴象意味”(注: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0页。)。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皎然《诗式》表现出盛唐诗学思想的某些特征,当然是合乎情理的。
考辨《诗式》的写作时间,无非是为了说明将皎然诗学归入盛唐阶段来讨论,较之归入中唐恐怕更为合理。当然,写作时间只是一个方面,比这更重要的,更有说服力的还是《诗式》所表现出来的审美倾向和理论重心。
二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撰写的文学批评史或文学理论史中,皎然《诗式》所以被放到中唐,一个相当重要的理由,是认定署名“王昌龄”的《诗格》一书并非王昌龄本人所作,而出自中唐人的伪托。研究者们注意到,皎然《诗式》与王昌龄《诗格》在诗歌创作主张、审美旨趣和理论关注重心等方面都十分接近,既然《诗格》为中唐时人所作,那么与之相似的《诗式》理所当然地应该归到中唐。这个推论在逻辑上并没有错,可如果《诗格》确实为王昌龄所作呢?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倒过来,根据二者的相似而将皎然《诗式》纳入盛唐诗学来讨论呢?
认为《诗格》非王昌龄所作,最早大概始于四库馆臣。《四库总目提要》卷195评司空图《诗品》时说:“唐人诗格传于世者,王昌龄、杜甫、贾岛诸书,率皆依托。即皎然《杼山诗式》,亦在疑似之间。”四库馆臣所以会有如此看法,主要原因当如李珍华、傅璇琮先生所说,撰写提要的人主观上就认定唐代诗格一类著作浅俗低下,不可能出自名家之手(注:参见傅璇琮《唐诗论学丛稿·谈王昌龄的〈诗格〉》,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再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未能见到清末才传入国内,由日僧遍照金刚所编撰之《文镜秘府论》。事实上,正是《文镜秘府论》一书的传入,为研究者质疑四库馆臣的旧说提供了坚实的依据,无论是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是后来李珍华、傅璇琮、张伯伟等先生的考证,都仰仗了《文镜秘府论》所记载的材料。
那么,《文镜秘府论》的记载是否可靠呢?对此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相信空海所记确为王昌龄所作,虽然掺杂了少量他人的文字,如罗根泽、王梦鸥、李珍华、傅璇琮、张伯伟诸先生均持此观点;二是表示怀疑,如罗宗强先生就认为上述诸人的考证“还有一些问题令人疑惑不解”,如引王昌龄本人作品而称古诗云之类,“且全书多为作诗法之琐碎程式,与开元天宝间文学思想主要倾向之重风骨、兴象,重诗之整体风貌者异,实不似出自开、天盛世作者之手”。罗先生明确指出:《诗格》并非王昌龄所作,鉴于皎然《诗式》引述王昌龄语与《文镜秘府论》所记文异而义同,因此很有可能是王昌龄去世后,皎然撰《诗式》前约三十年间的人伪托(注: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150-151页。)。
罗先生的怀疑不能说没有道理,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无百分之百的把握认定今本《诗格》确为王昌龄所作;我们甚至不能肯定空海大师所见《诗格》确实出自王昌龄之手。这里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比如说,空海是通过何种途径得到王昌龄《诗格》的?王利器先生的《文镜秘府论校注》引空海《书刘希夷集献纳表》:“此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边偶得此书。古代《诗格》等,虽有数家,近代才子尤爱此格。”(注: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此处所说“作者”可以有两种解释:1、《诗格》一书作者;2、某个诗歌作者。第一种显然不通,空海抵唐时,王昌龄已去世近五十年,以空海的学识和交游,他不会不知道王昌龄早已不在人世。至于第二种,虽然说得过去,但终觉勉强。所以,这段文字只能说明空海在唐期间见到过一部署名王昌龄的《诗格》并将之携回日本,而不能作为王昌龄确实作过《诗格》的证据。再比如说,皎然《诗式》曾引述王昌龄论诗语,是否能够证明皎然见过《诗格》呢?也很难说。《诗式》卷二“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条道:“王昌龄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谓一句见意为上,事殊不尔。”并没有提到《诗格》。简而言之,我们真正可以肯定的,只是空海在唐期间见到一部署名王昌龄的《诗格》,而此书与后来流传的王昌龄《诗格》在内容文字上颇多吻合。
但王昌龄是有可能作《诗格》的。首先,王昌龄确有论诗语,这有皎然《诗式》为证。尽管我们同样不知道皎然看到(或听到)的究竟为何,但皎然作为一个诗论家,至少在真伪问题上不应失误。而且皎然生活的时代离王昌龄更近——罗宗强先生以为皎然看到《诗格》当不晚于贞元初,这是比较保守的看法,实际上很可能更早,因为《诗式》的写作肯定在此之前。至于早到什么时候,这不好揣测,但如果皎然看到王昌龄论诗语的时间距王昌龄去世的时间越近,后人作伪的可能性就越小。其次,辛文房《唐才子传》记:“昌龄工诗,缜密而思清,时称‘诗家夫子王江宁’。”此说如果可信的话,则王昌龄应该向后学传授过作诗技巧。虽说传授作诗技巧与写作《诗格》并不能简单等同,但毕竟多了一分可能,正如张伯伟先生所说:“既称‘夫子’,则王氏曾向其后学传授诗律,因而有《诗格》之书,也是很有可能的。”(注: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此外,李、傅二先生文也从文章体例的角度论证了这种可能,认为如《文镜秘府论》所引“十七势”以王昌龄本人诗为例,“论文意”虽略有布局而不免于零散重复,都可看出一些讲授的痕迹。
王昌龄既负诗名,又确有论诗语,后人若有伪托名,亦在情理之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时间。如前所述,皎然曾见过王昌龄论诗文字,我们姑且假定他看到的是一部署名王昌龄、以“诗格”为名的著作,而此事距王昌龄卒至多不过二十余年,此时王氏故旧以及曾问学于王氏者尚有不少在世,作伪者如何才能瞒天过海,欺世盗名呢?再说了,作伪者的动机是什么?盗名很难说通,获利似乎也不大可能。
比较而言,可能性最大的恐怕还是编辑整理。上文引空海《书刘希夷集献纳表》,说其中“作者”一语可以有两种理解,是否还可以有第三种解释呢?就是说,空海有没有可能遇到某个持有王昌龄《诗格》手稿或记录稿并对之进行整理的人呢?这个可能性应该说是存在的。罗宗强先生列举的疑惑之一,是《诗格》“起首入兴体十四”之十一引王昌龄本人诗为例而称“王少伯诗”。确实,若是作者自撰,不应自称姓字,但若是他人记录整理就属正常了。同样,如果空海真的是从某个整理者手中得到《诗格》一书,那么称其为“作者”,也不是绝对不可以。
我们再来看四库馆臣否定《诗格》为王昌龄作的理由。对此李、傅二先生的文章已作了辩驳,这里再补充几句。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表明,一个在创作上有突出成就的诗人并不一定是一个优秀的诗论家,相反,那些在创作上相对不大有名的人反倒在诗学上有过人的建树,譬如六朝时期的刘勰、钟嵘,宋代的严羽,清代的叶燮、王夫之等便是如此。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以创作著称的诗人就绝对成不了诗论家,而不过是想澄清一个事实,即就单个诗人来说,其诗歌创作的成就并非总与诗歌理论研究的成就成正比。因此,不能因为王昌龄在诗歌创作上享有盛誉便要求他在诗歌理论方面也达到同样的高度,何况所谓高度,只能是相对于唐代诗学发展的某一阶段而言。一般说来,诗学作为诗歌创作经验的理论总结与概括,与创作相比,其发展总是相对滞后的。这里说的相对滞后,既可以是时间上的相对滞后,也可以是理论深度上的相对滞后,所以,尽管可以说盛唐诗歌是整个唐代诗歌发展的顶峰,却不能据此认为盛唐诗学必然也取得相应的成就。应该承认,从唐代诗学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盛唐后期出现王昌龄《诗格》这样侧重讨论诗法技巧的著作,倒是顺理成章的。相反,若是缺少了这个环节,难免令人有断裂残缺之感。
罗宗强先生指出:《诗格》“全书多为作诗法之琐碎程式,与开元天宝间文学思想主要倾向之重风骨、兴象,重诗之整体风貌者异”。这不错,但此种差异尚不足以否定《诗格》为盛唐时期人所作。首先,罗先生上述结论的得出,主要是建立在将《诗格》与殷瑶《河岳英灵集》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但这两部著作的性质有所不同:《河岳英灵集》为唐诗选本,侧重在对盛唐诗歌作整体观照,从宏观上把握盛唐诗歌的基本美学特征。殷璠之所以提出风骨与声律并重,以“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作为评判优秀诗作的尺度,既是基于他对盛唐诗歌审美特征的理解,同时也和选本偏重鉴赏的角度相关。至于《诗格》,则为诗歌创作论,它关注的主要不是盛唐诗歌具有什么样的审美特征,而是通过何种方式,运用何种技巧去创造出兼备风骨、兴象的好诗。换言之,《诗格》讨论的是诗歌创作层面的具体问题,如构思、结构、语言形式等。而且,如果《诗格》真的是王昌龄为后学讲授诗法的产物,那么它当然不免于浅俗,甚至细碎。所以,承认这两部著作在旨趣和体例方面存在差异,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能产生在同一时期。其次,对于《诗格》“全书多为作诗法之琐碎程式”,也应放到具体的历史时段来评判。我们承认,相对于晚唐以至宋元以后诗学论著,《诗格》的稚嫩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将其与初唐同类著作相比,便不难看出它有所发展,有所深化,譬如讨论感兴的获得、诗境的创造等,均为初唐近体诗学所罕论。更重要的是,即便是讨论创作技巧层面的问题,《诗格》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与《河岳英灵集》仍不乏相通相近之处,具体的比较我们留待下文,这里只想说明《诗格》的体例及所关注的问题与盛唐诗学并行不悖。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倾向于肯定《诗格》一书为王昌龄所作。
三
纵观《诗式》全书,可以看出存在着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即自然而不废人为,人为而不失自然。先看皎然在《诗式》卷首所言:
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彼天地日月,玄化之渊奥,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授。至如天真秀拔之句,与造化争衡,可以意会,难以言状,非作者不能知也。洎西汉以来,文体四变,将恐风雅寝泯,辄欲商较以正其源。今从两汉已降,至于我唐,名篇丽句,凡若干人,命曰《诗式》,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若君子见之,庶几有益于诗教矣。
这段话道出了皎然写作《诗式》的动机,也可以看作是他论诗的纲领。在皎然看来,诗歌所以能够与圣贤之作比肩,为“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诗歌是诗人心智活动的产物,这种心智活动能够洞见天地鬼神之奥秘,故其产物得以与造化争衡,与自然同功。所以,一方面,皎然以“天真秀拔之句”为诗之极致,它仿佛出自造化之手,给人以“可以意会,难以言状”之感;另一方面,再好的诗,到底还是诗人的艺术创造,仍有其可以言说、探讨,以至于传授、学习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诗式》的写作才成为必要。所谓“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就是希望学诗者通过对规矩法度的掌握,进而达到一种“大巧”的境界。
在论“取境”一段中,皎然将这种人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表述得更加明白。针对那种反对苦思,以为“苦思则丧自然之质”的观点,皎然指出:“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皎然的意思是说,苦思和自然并不构成矛盾,相反倒是一种必要的互补。高手之为高手,就在于他能够将苦思出以天然,如庄子所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在《诗式》中类似的表述还有不少。如“诗有二废”:“虽欲废巧尚质,而思致不得置;虽欲废言尚意,而典丽不得遗”。“诗有六至”,“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这是要求看似对立的两端恰到好处地结合。又如“诗有四深”(“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用律不滞,由深于声对;用事不直,由深于义类”),要求技巧的运用须臻于化境,不显斧凿之痕。“诗有四离”(“虽有道情,而离深僻;虽用经史,而离书生;虽尚高逸,而离迂远;虽欲飞动,而离轻浮”),要求把握好创作的分寸,避免似是而非。所有这些,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人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思想。
对于声律、对偶的态度亦复如此。一方面,皎然不满于沈约声病说的细碎,谓:“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绝对否定声律对偶,《诗式》“对句不对句”条道:“夫对者,如天尊地卑、君臣父子,盖天地自然之数。若斤斧迹存,不合自然,则非作者之意。”又《文镜秘府论》南卷引皎然语:“或云:今人所以不及古者,病于俪词。予云:不然。六经时有俪词,……但古人后于语,先于意,因(意)成语,语不使意,偶对则对,偶散则散。若力为之,则见斤斧之迹。故有对不失浑成,纵散不关造作,此古手也。”可见,皎然真正反对的,只是那种过分拘于声律以至于有损自然之质的做法。
这种强调人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甚至影响到皎然对历代诗人的评价。在历代诗人诗作中,皎然最为推崇的首先是旧题为李陵、苏武所作的古诗,以其“发言自高,未有作用(着意构思)”之故也。不过,对于“始见作用之功”的《古诗十九首》,他同样评价极高,与苏、李诗等同视之。其中原因,就在于《古诗十九首》“以讽兴为宗,直而不俗,丽而不朽,格高而意温,语近而意远,情浮于语,偶像则发,不以力制,故皆合于语而生自然”。换句话说,《古诗十九首》虽有“作用之功”,却能给人以自然天成之感。与之相似的还有谢灵运。当然,作为谢灵运的后人(皎然俗姓谢,据说是谢灵运的第十世孙),皎然对谢灵运的颂扬不无偏爱的成分,但皎然所以将谢灵运置于高手之列,主要还是因为谢诗与其诗学理想相吻合,即所谓“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
这样一种自然而不废人为的诗学理想,与盛唐诗学的审美价值取向并无不同。我们看殷璠对声律的态度:一方面,他主张“夫能文者,非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纵不拈缀,来为深缺”;而另一方面,他又承认“预于词场,不可不知音律焉”(《河岳英灵集·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河岳英灵集》一书的入选标准:“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王昌龄《诗格》亦然。《文镜秘府论》南卷引王昌龄语:“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练,发言以当,应物便是。”这里强调了自然感发,不假雕饰,但王昌龄并不绝对否定声律章法。他同时还说:“凡文章体例,不解清浊规矩,造次不得制作。制作不依此法,纵令合理,所作千篇,不堪施用。”与此相联系,王昌龄既主张诗歌创作应该“专任情兴”,又不赞成那种完全忽视诗歌创作技巧的做法,以其“盖无比兴,一时之能也”。殷、王二人的这些见解,与皎然所论无疑是相通的。
与《诗格》相似,《诗式》讨论的中心问题,仍为诗歌创作论,大致包括辨体、作用、技法三个方面。
辨体即分辨不同的诗歌体格,亦即不同诗歌各自的主导特色。“辨体有一十九字”条共罗列了十九种,各用一字予以概括:
高:风韵朗畅曰高;逸:体格闲放曰逸;贞:放词正直曰贞;忠:临危不变曰忠;节:持操不改曰节;志:立性不改曰志;气:风情耿介曰气;情:缘景不尽曰情;思:气多含蓄曰思;德:词温而正曰德;诫:检束防闲曰诫;闲:情性疏野曰闲;达:心迹旷诞曰达;悲:伤甚曰悲;怨:词调凄切曰怨;意:立言盘泊曰意;力:体裁劲健曰力;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
皎然辨体,与刘勰《文心雕龙·体性》联系作家创作个性讨论作品风格不同,他所概括的十九体也有别于今人说的风格。大概皎然的意图仅在于指出诗歌依其内涵可以划分为若干类型,使学诗者能够进行判别而已。十九体也不同于王昌龄《诗格》中的十七势,就是说,不是着眼于诗的句法、章法,而是着眼于诗的整体风貌。相应地,皎然所说诗体也并非得之于一句一联的安排,而是得之于诗境的选取。“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诗境的特色决定了全诗的整体风貌,因此问题的关键,还是落实在诗歌的创作环节。若与王昌龄“三境说”相比,可以看出皎然对境的划分更加具体,其特定的指向性更加明确:体有十九种,那么与之对应的境也应该有十九种(实际上当然不只这些),诗人在进行创作构思时,就必须根据自己特定的表现意图去加以选择,并将其转化为蕴含在诗作中的审美意象。这样,皎然所说“取境”就隐含了创造诗歌意境的意味。在此意义上说,尽管皎然有关境的论述不及王昌龄丰富,其表述也不够系统,但他确实将中国古典诗学之意境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作用”一词在《诗式》中屡见,其含义与一般所说有别,可以说是皎然诗论一个较为重要的术语。除了上文提到的“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和谓《古诗十九首》“始见作用之功”、谢灵运诗“尚于作用”等外,《诗式》还将“明作用”单列为一条,表明皎然对此问题的重视:
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时时抛针掷线,似断而复续。此为诗中之仙,拘忌之徒,非所企及矣。
又评谢灵运“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二诗时说:
夫诗人作用,势有通塞,意有盘礴。势有通塞者,谓一篇之中,后势特起,前势似断,如惊鸿背飞,却顾俦侣。……意有盘礴者,谓一篇之中,虽词归一旨,而兴乃多端,用识与才,蹂践理窟,如卞子采玉,徘徊荆岑。
从这两条材料来看,皎然所说“作用”,似乎侧重在诗歌整体的谋篇布局。所谓“抛针掷线:似断而复续”,应该是就诗篇的结构而言。而“势有通塞”、“意有盘礴”,也可以理解为两种不同的结构方式:前者为一线贯穿,首尾照应;后者为多处点染,左右回环。联系“明势”条所说:高手述作,其势如高山大川,或高峻,或深广,要之“萦迥盘礴,千变万态”,可见取势实为“作用”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既不同于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所说特定文体固有的创作要求,也不同于王昌龄“十七势”讲句法的变化,而是突出了诗人创作时的构思安排。
但事实上,“作用”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取势,除此之外,诸如取境、取象(比)、取义(兴),甚至用事,都是诗人“作用”的对象。我们看皎然以五格评诗,其第一格为“不用事”,第二格为“作用事”,而于“用事”一条兼论比兴,便知“作用”涉及范围极广。质而言之,皎然标举“作用”,是将其作为与自然天成相对的一个概念,用来指称诗人的艺术构思乃至艺术创造活动。其基本精神,或可用皎然反驳不要苦思的一段话来概括:“固当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趣),写真奥之思”(《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
《诗式》谈诗歌创作技法,不似王昌龄《诗格朔日样细碎,这大概与皎然强调人为与自然相统一的诗学观念有关。其中如“对句不对句”、“三不同(偷语、偷意、偷势)”等条涉及技法,却表现出一种灵活的态度和不蹈袭前人的精神。不过,皎然另一部诗论著作《诗议》仍有一些常识性的论述,如“诗对六格”、“八种对”、“十五例”之类,可以看出其与《诗格》的关联。
那么,皎然这些诗歌创作理论与盛唐诗学精神是否一致呢?罗宗强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指出:“大历初至贞元中这二十几年,随着创作中失去了盛唐那种昂扬的精神风貌,那种风骨,那种气概,那种浑然一体的兴象意味,而转入对于宁静、闲适,而又冷落与寂寞的生活情趣的追求,转入对清丽、纤弱的美的追求,在理论上也相应地主张高情、丽辞、远韵,着眼于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理论探讨。”(注: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158-159页。)我们承认,大历以后诗歌创作与盛唐相比确实有所变化,但理论上主张“高情、远韵、丽辞”,探讨艺术形式、技巧却非此时所特有,即使撇开《诗格》不说,殷璠《河岳英灵集》也不乏此类意见。其评论人唐以后诗歌的发展:“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诵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这难道没有高情、远韵的意味?再看他几则评语:,
眘虚诗情幽兴远,思苦语奇,忽有所得,便惊众听。顷东南高唱者数人,然声律宛态,无出其右,唯气骨下逮诸公。自永明以还,可杰立江表。至如“松色空照水,经声时有人”;又“沧溟千万里,日夜一孤舟”;又“归梦如春水,悠悠绕故乡”;又“驻马渡江处,望乡待归舟”;又“道由白云尽,春与清溪长……”;并方外之言也。
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幽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至如“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又“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数句并可称警策。
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
这里所说“情幽兴远,思苦语奇”;“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以及评王维诗一段,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殷璠对高情、远韵,还有丽辞的明确首肯呢?
还可以略说几句的是皎然的“复变之道”。《诗式》卷五有“复古通变体”一条,专论复与变的关系:
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又复、变二门,复忌太过,诗人呼为膏肓之疾,安可治也。如释氏顿教,学者有沉性之失,殊不知性起之法,万象皆真。夫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
复、变之道即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不难看出,皎然虽说作者须知复、变之道,但他此论的重心,却是落在如何新变上。换句话说,皎然于复、变二者并非等同视之,而有意突出了变的重要性。所以他不仅反对“惟复不变”,而且认为“复忌太过”,变则不忌。与此相联系,对于“复多而变少”的陈子昂,皎然认为并不象卢藏用称誉的那样,五百年来仅此一人;而对于“复少而变多”的沈栓期、宋之问,他却许以为“诗家射雕之手”,颇表推崇。平心而论,此评确实有对陈子昂认识不足,和对沈、宋肯定过多的偏颇,但是也应该承认他并非无的放矢。“后辈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何则?大不工剑术,而欲弹抚干将太阿之铗,必有伤手之患”。从根本上说,复古也罢,新变也罢,都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真正懂得诗为何物,否则,新变固然可能导向舍本逐末,而复古也难免不会流于唯古人之马首是瞻,以仿古为能事。
或许正是有见于此,皎然特别强调创作要有一种超越前人的意识。《文镜秘府论》南卷引皎然语道:“凡诗者,虽以敌古为上,不以写古为能。立意于众人之先,放词于群才之表,独创虽取,使耳目不接,终患倚傍之手。或引全章,或插一句,以古人相粘二字、三字为力,厕丽玉于瓦石,殖芳芷于败兰,纵善,亦他人之眉目,非己之功也,况不善乎?”他批评那些徒得古人形貌的诗作:“或有所至,已在古人之后,意熟语旧,但见诗皮,淡而无味”。显然,皎然的这些看法,对于促进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它也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王昌龄《诗格》中类似的见解。如:“夫文章兴作,先动气。气生乎心,心发乎言,闻于耳,见于目,录于纸。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攒天海于方寸。诗人用心,当于此也。”又如:“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巧运言词,精练意魄,所作词句,莫用古语及今烂字旧意”(《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是否可以说,这种诗歌创作上的自信和开拓精神,正是所谓盛唐气象在诗学领域的反映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皎然《诗式》与王昌龄《诗格》的某些相似便并非偶然了。
当然,与王昌龄相比,皎然诗论仍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更有新的发展。比如说,在审美倾向方面,皎然在推崇人为与自然相统一之外,还表现出对高、逸风格的偏爱,而这是王昌龄《诗格》所没有的。又比如说,皎然论诗,以“但见情性,不睹文字”为诗道之极,故他认为“诗人造极之旨,必在神诣”,非“意冥”、“神会”不足以认识诗之精妙,而作者“天机”之有无遂成为诗歌创作的先决条件,这也是王昌龄所不及的。皎然对王昌龄的见解也不乏批评修正。如王昌龄认为诗以“一句见意为上”,而皎然则不以为然,认为一句见意、多句显情皆属佳作;又如关于对偶,王昌龄谓“不可以虚无对实象”,而皎然却说:“夫境象不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凡此等,可以对虚,亦可以对实”(《文镜秘府论》南卷引)。所有这些,都表明皎然与王昌龄诗学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这些差异的形成,恐怕更应该归因于个人的经历和处境,而并非由时代、社会的不同所决定。较之时代、社会的影响,皎然作为佛门中人这一因素当更为重要,无论是他对高、逸的偏爱,还是他诗论的玄妙色彩,都可以由佛学的影响得到解释。可以说,正是佛门崇尚空寂、超脱现实的审美取向决定了皎然将高、逸置于诸体之首,而佛学精于思辨的学术风气又使他对诗歌理论更深一层的探究高出时人。
然而,如果撇开这些差异,从总体上来考察《诗式》与《诗格》的异同,那么应该承认,时代、社会之于二书的影响毕竟甚于个人因素的作用,如基本的审美倾向、所关注的理论重心、对前人作品的态度,以及表述方式等等,都明显带有盛唐时代、社会和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痕迹。因此,对于处在盛、中唐之交的皎然,与其将他属后,视为中唐诗学的前响,不如属前,当作盛唐诗学的殿军。
四
应该说,皎然诗学的归属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文学批评史、思想史写作的方法和观念问题。
早期的文学批评史基本上是作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而出现并由此获得存在价值的。这也是早期批评史作者的一个共识,如郭绍虞就曾表示:“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因为这——文学批评,是与文学之演变有最密切的关系的。”(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页。)王瑶更说:“文学批评史正是一种类别的文学史,像小说史、戏曲史一样。”(注:王瑶:《中国文学批评与总集》,《光明日报》,1950年5月10日。)受此观念的影响,早期的文学批评史在阶段的划分上往往与文学史相一致,并基本上采取了按年代、人物或流派编排史料的结构模式,一种类似于韦勒克所说的“学说志”的模式。这样一种批评史在印证文学史方面的确不无助益,但过分强调批评史与文学史的一致而忽略了二者的区别,则显然有碍于研究的深化。罗根泽说得好:虽然文学批评有助于了解文学创作,批评史有助于了解文学史,“但文学批评不即是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史不即是文学史”(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新版,第11页。)。至于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思想史,其与文学史的差异恐怕还要更大一些。如果说文学史主要是一种“事实的历史”,那么理论史和思想史无疑更多编著的成分,更需要编著者主体性的介入。也就是说,对于理论史、思想史的研究,重点不在按时间先后描述批评活动的发生发展,而在探寻用以指导批评实践的文学观念及理论原则的变迁,因此,除了从总体上把握各个历史阶段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轨迹之外,还必须引入单元思想的概念,研究某种具体的文学思想及相关理论命题、范畴的发展演变,与其它文学思想的关联,等等。简言之,批评史的撰写虽不能完全避免学说志的成分,但不能仅仅是学说志。
如果我们遵从早先批评史家的观念,强调以批评史去印证文学史,或者我们相信一定时期的文学理论总与文学创作的发展保持同步,那么皎然诗学思想当然可以归到中唐阶段来讨论,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唐文学思想表现之一端。但如果着眼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机制,着眼于某种诗学思想单元的形成衍变,那我们应该还有另一种选择。唐代诗学,尤其是近体诗学作为一个整体,它自身的发展成熟显然是相对落后于诗歌创作实践的,在此境况下,我们根据什么来对一定时期的文学思想作阶段性划分?又根据什么来确定盛唐诗学的基本特征呢?文学史的分期不一定适合于批评史的分期,而且,传统的唐诗发展阶段划分——初、盛、中、晚只是一个粗略的划分,其具体时限往往不甚分明。所以,完全按照所谓初、盛、中、晚来划分唐代诗学或文学思想发展的历程,就难免会有强为牵合、割长就短之弊。同样,某个理论家生活的年代也不应作为划分时段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相比之下,其思想理论在历史发展链条中所处的位置才更值得关注。事实上,某一思想单元的萌生及其形成,往往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朝代或文学创作时段,更不会与之相始终,在所谓初唐文学思想与盛唐文学思想之间,或中唐文学思想与晚唐文学思想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界限。因此,对于那些跨越不同时段的理论家的归属,我们尤其不能仅仅根据其活动的主要时期来判定。
皎然的情况正是如此。从唐代诗学,特别是近体诗学发展的历程来看,皎然《诗式》的意义或价值主要并不在于开启中唐诗学,而在于为初唐以至盛唐的近体诗学作了理论上的总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是殷璠的《河岳英灵集》、王昌龄的《诗格》,还是皎然的《诗式》,都提出了若干新的见解,而且,尽管各家所论不尽相同,但去异存同,可以看出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构架。那就是:在对待前人文学遗产的态度上,古今兼顾,复变并举;而在创作思想上,则是以感兴为基础,既推崇自然天成,同时又强调诗人艺术构思的重要;相应地,在表现形式上,一方面肯定声律、对偶、用事等因素之不可少,另一方面又要求形式技巧的运用必须服从于情感的传达。显然,这样一种兼收并蓄的襟怀、通达的态度和辩证的眼光,正是唐代近体诗学趋于成熟的表现。
